陳文兄,傳記作家。一九六零年三月出生在廣東省雷州半島。是國內最早利用私人照片和生活符號記錄個人歷史和傳播個體生命價值的民間思想者。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文兄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廣東省
- 出生日期:1960年3月
- 職業:傳記作家
- 代表作品:《吃飯長大》、《老兵照片》、《誰隱居在茂德公草堂》、《最醜的那個人》
個人履歷,人物生平,成就及作品,社會評價,《白紙黑字》,記憶的碎片《白紙黑字》,
個人履歷
十八歲離開故鄉,曾在河北,山西,陝西,北京,海南等地生活與工作,現居住廣州。八十年代末離開體制,閒雲野鶴,遊走江湖,以寫作謀生。以本名陳文著有《吃飯長大》、《老兵照片》、《誰隱居在茂德公草堂》、《最醜的那個人》等私人傳記從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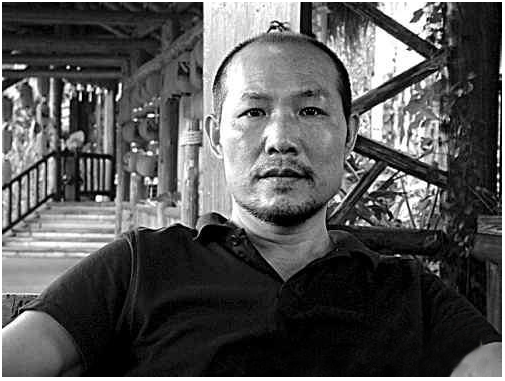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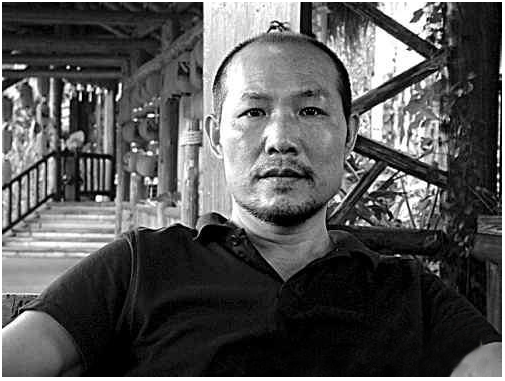
人物生平
二十年來,陳文兄一直拒絕各種高官厚祿的誘惑,堅持生活在民間,保持著觀察者冷靜的狀態,記錄這個世界。他用六年時間整理自己二十年的記事本寫成的《白紙黑字》即將出版。
成就及作品
2003年1月1日出版——《吃飯長大》
2007年5月出版——《老兵照片》
2008年出版——《誰隱居在茂公德草堂》
2010年8月出版——《最醜的那個人》
2011年12月1日出版——《白紙黑字》
社會評價
42歲時,廣東雷州人陳文想寫一本自傳。他當過兵,下過海;非名人非官員,雖有車有房,但在廣州這個改革開放前沿的花花城市,他甚至連“有錢”都算不上。普通人一個,有什麼可寫的?兒子取笑說,你頭頂都沒有毛,趕什麼時髦。
但陳文還是花一年多時間,折騰出一本“個人生活檔案”,收錄自己吃飯長大的點點滴滴。當小時候看病的藥方、第一次用毛筆寫的作文這些已經泛黃的“原始檔案”攤開在面前,陳文找到了“史”的感覺。
陳文寫自己的故鄉。
1960年3月25日,父親陳樹坤、母親李石蓮把他帶到人間。一睜開雙眼,他就在雷州半島的小鎮上。童年印象最深刻的,是鎮上唯一的娛樂場所——公社禮堂。那是“大躍進”年代,全公社的社員用砍樹賣木材的錢建的。陳文的父親是供銷社的小頭目,“70年代,供銷社的權力很大,腳踏車、縫紉機、肥皂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憑票供應。母親在百貨商店賣布,經常不用布票買些卡其藍尾布回來做衣服給我穿,我穿不下了再讓二弟、小弟穿。”
陳文寫自己當兵。
1978年,中越邊境局勢緊張,知青陳文選擇去當兵。當年12月28日,一節悶罐車拉著跟陳文一樣左臂綁著白毛巾的上百名新兵,離開當時中國大陸最南端的鐵路終點站——廣東遂溪,向北行駛。一路上,陳文看到一列一列兵車南下,火車上都是大炮坦克,他隱約感覺到:要打仗了。軍列走了三天,在雪花飄飛的深夜,停在了一個小站,借著朦朧的燈光,陳文看到站台上寫著:河北。從此,看見了故鄉以外的天空。
入伍後,陳文每月領6元津貼,糧食定額45斤。和所有戰友一樣,他“認真學習,刻苦改造世界觀,遵守紀律,嚴格訓練,踏實肯乾,內務衛生好”,終於獲得了部隊嘉獎。那一張32開的白紙片嘉獎令,是他所有工作的目標,也是讓全家人最興奮激動的大喜訊。
軍隊生活給陳文留下深刻印記。在這本個人傳記中,陳文本人最大的一張照片,是他穿著65式軍裝。帽上一顆五角星,衣領別著兩面紅旗,上衣兩個口袋。照片從較低的角度仰拍,陳文腰裡別著手槍,咧著嘴,發自內心的喜悅。“‘文革’中很多領導都穿65式軍裝。這款軍裝流行的時間最長。”
陳文最終沒上戰場,而當了一名基建工程兵。這支部隊從1966年組建以來,擔負了國家大中型建設項目和單項工程132項。陳文後來查資料得知,自1966年至1983年,該部隊完成的建築安裝工作量,累計折合83億元。到了1982年,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撤銷基建工程兵的決定》,陳文因此退伍。
陳文寫自己下海。
1993年,海南房地產熱到了發燒的程度。陳文已是海南海星雲龍灣度假村的員工,下海後,工資猛然從體制內的38.5元漲到3000元。度假村開張之初,幾個年輕人鋌而走險,打出“雲龍灣,有錢人的海灣”的廣告。那時有錢人還不多,只有零零星星的人開著名車來到“自己”的海灣度假。於是陳文決定把廣告語改一個字,用一個由18名少女組成的“情”字,壓住“錢”字。廣告轟動海口,雲龍灣一夜成名。
1994年,陳文代表公司參與外資合作,在廣東籌建電廠。1996年春節過後,美方公司董事長率隊來中國,解決合作中出現的矛盾與分歧。陳文帶著他坐船過瓊州海峽。海上忽起大風,美國人坐立不安,要求輪船開回去避風。陳文介紹了毛澤東詩詞“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美國人的頭搖得比船還要厲害,“不可理解,在風浪中怎么能散步,風浪就是風浪,庭院就是庭院,這是兩個概念,你們中國人錯了。”兩個月後,工程基本完成。卻趕上國內經濟巨觀調控,國家整頓小型電廠項目。由於政策原因,更由於中美雙方的文化差異,“我們之間的分歧變得比瓊州海峽的風浪還要大,投資一個多億的項目最終擱淺”。
陳文還寫自己的生活瑣事。
七八歲時,每晚在油燈下看母親繡毛主席像。1976年,一個調皮同學在他耳邊小聲地說出偉人過世的訊息,陳文一巴掌打在他臉上:“反動,毛主席怎么會死呢?”第一次到北京,穿著軍裝陸戰靴在天安門照相,回來被領導批評:“你的頭怎么能高過天安門城樓?”陳文愣住了,“我沒想到,我只想紅旗在我頭上高高飄揚。”
1984年,陳文走進廣州黃華路四號大院,這裡曾經是民國的造幣廠,也曾是國民黨廣東省的黨部,後來成了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所在地。陳文在這裡讀了4年中共黨史,明白了任何組織也與人一樣,有犯錯的時候。“我們那時學的歷史,都是政黨史、偉人史。”陳文曾經用顏料,仔細地把自己黑白照片裡的上衣染成紅色。但他未曾敢想,有朝一日,普通人的照片也可以被收錄下來,寫成自己的歷史記憶。
陳文也寫自己的諸多“糗事”。情竇初開時,穿一套2號軍裝走南闖北,每次上火車就幻想身邊或對面坐一位美麗的少女,最好是漂亮的女大學生或者女兵,然後就想法子與她說話,越說越投機,然後就告訴她自己會寫詩,在某某報刊發表過作品。然後她就被吸引,留下通訊地址,當列車抵達終點,兩人戀戀不捨地分別,然後就揮霍青春的激情,一封接一封地給她寫信,再然後她就成為自己的妻子……有一次,他終於在列車上遇到一個漂亮得讓他心動的女兵,一個人守著一張餐桌。陳文壯著膽子走上去,本想說你很漂亮是哪個部隊的,但說的時候卻成了另外一句話:你身邊的凳子有人坐嗎?女兵看了陳文一眼說:有。隨即抬起一隻腳,踩在凳子上。“那一隻美麗的腳,幾乎把我踩暈過去。”
陳文有時把家裡收藏的舊照片、舊證件翻出來曬太陽,“是我快發霉了嗎?”他自問。幾年來,頭髮快脫光了,眼睛也開始昏花,經常莫名其妙地想到死亡。“毛主席死的時候,我感覺生命是可以永恆的;給犧牲的戰友寫事跡報告時,我感覺那是生命到達沸點時的飄舞;我在廣西憑祥南山烈士陵園,給6個遂溪籍的烈士一人點了一支煙,他們與我同年入伍,但參加了自衛反擊戰,再也沒回來;外婆去世時,她從故鄉的老屋走出,常駐我的心田。無論是長眠於上個世紀的偉人,還是草芥一般普通的生命,21世紀的燦爛陽光,一樣照耀著他們的墓地。”
陳文於是決定寫一本書,寫自己的歷史,以及那個時代的公眾記憶。最後梳理出三條線索:文字、照片和簡短概括。入團申請書、結婚證、計畫生育證、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調動工資轉移證、組織鑑定表……全都收羅進書里,還拍了照片。他去找出版社,第一家沒同意。“一個小人物的傳記能賣得動嗎?”對方質疑。
市場最終給了陳文驚喜。這本記錄了個人歷史的《吃飯長大》,出版後3次加印,總量已達兩萬多冊。有人說,陳文的書,好就好在是普通人寫的普通的生活,沒有那種期望的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也沒有成功的慶祝,有的是我們似曾相識的記憶碎片,有的是酸甜苦辣的舊事,它最大的力量在於勾起我們對自己走過的路的聯想,完成了一場集體懷舊。而陳文自己說,他寫的是“口碑歷史”,英文叫“narrative history”,通過大量人物對自己平凡生活的回憶來反映時代。
“做這種記錄有意義。無數個人的歷史集中在一起,就成為民族的歷史,國家的歷史,人類的歷史。這樣的說法也許‘大’了些。在東方文化的骨髓里,承認個體生命的價值,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陳文說。
在出版了自己的口碑歷史後,陳文有了更宏大的計畫:做一部軍人的口碑歷史。他投入20萬元啟動資金,蒐集退伍老兵的私人相片。許多老兵紛紛送來自己的照片,展示了那個時代軍人精神面貌和生活場景。他們之中,有能熟記1000個首長電話的通訊兵,有救死扶傷的衛生兵,有寫劇本的文藝兵,有在邊疆工作的鐵道兵……他們如此平凡,永遠都不可能被寫入正規的軍史。正因如此,當他們拿到印著自己照片和名字的《老兵照片》時,潸然淚下。一個老兵買了120本《老兵照片》,寄給自己曾服役的部隊;更多的老兵輾轉打聽陳文的電話號碼,從外地趕來送照片。還有人找到陳文,請他給自己的家族寫一本口碑歷史。
18個朋友給陳文的書寫了點評,再一次彰顯了這個男人的交際之廣。有朋友說,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中,占據主要地位的向來都是影響歷史進程的英雄或者梟雄,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成了建築金字塔的基石,浩大穩固卻遠離輝煌。但正是這些波瀾不驚的平凡人生和不入史冊的草民活法,才是真正流淌於地母胸中的大地精靈。陳文把《吃飯長大》送給知音,在扉頁上端端正正地題寫:每個人都可以寫一本這樣的書,你的更精彩。
《白紙黑字》
繼《最“醜”的那個人》之後,廣東本土作家陳文,日前推出了新作《白紙黑字》。陳文表示,對於這本匯聚自己20年間的經歷和思想的隨筆,他採用的是一種隨心所欲和百無禁忌的語言,他用白紙黑字的記錄來審視生命,這是送給忙忙碌碌的人們的一碗清水。
新書6年創作而成
據悉,《白紙黑字》的創作時間大概有6年。陳文告訴記者,這6年只是一個“串珠子”的過程。“整個過程就是自己把思想的碎片像珠子一樣串起來,但我不知道哪些是珍珠,哪些是泥巴。有些文字可以追溯到我的中學時代,包括《水鴨太多》、《搶瘋子》這些故事,還有我當兵時候的一些記憶。”2010年8月,陳文的書稿就已完成,他卻把書稿鎖在抽屜里冷卻了三個月。其後,他帶著列印好的書稿去了從化溪頭村,住在農民家裡,靜靜地修改。“我希望這本寫於世俗中的文字,在隔世的環境裡能脫去媚俗,乾乾淨淨地擺在讀者面前。”
記憶的碎片《白紙黑字》
陳文的《白紙黑字》有一種誠實、謙卑的品質,他對生活和生命本身的記錄,不是審視的,說教的,志得意滿的,而是有一種可貴的平等的態度。所以,他對那些碎片、細節,有一種著迷,並且願意花很長的時間和筆墨去記錄它。我欣賞他對生活的態度,對碎片的姿態,他是真正把生命史還原成了個人史,而我們又能通過這種個人史,看到時代內部的東西,之前很少人用這個方式來書寫和記錄,他的碎片記憶中,有很多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的東西。
我對《白紙黑字》的定位是:記憶的碎片,溫暖而感傷的個人史。
廣東文學的狀況是自己眼中看的,和別人眼中看的,有斷裂。自己覺得不錯,自己覺得自己影響大,但出了嶺南,幾乎就沒人知道了。這種認識上的差異,也表明它的現狀堪憂。
陳文這樣拒絕體制的作家,是游離於廣東文學界的,和廣東本土文學並無多少聯繫。但陳文這樣的寫作,卻可能是廣東文學中最具優勢的。也就是說,廣東社會這三十年,對文學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極其豐富而複雜的經驗,這種經驗,以及這種經驗對個人、對中國社會的衝擊是巨大的,也是全新的。但廣東的作家很多都是盲目地在追隨北京或上海的潮流,總是想用取悅的方式試圖分享北京所主導的話題,卻遺忘了屬於廣東自己的優勢——那就是如何寫出一種經驗的複雜、疑難,以及這種經驗的疼痛。陳文的寫作,是一種重視經驗、尤其是重視個人經驗的寫作,他所提供的經驗的碎片,使我們看到一個社會的變化,看到了一個人生命的成長,它有別於北方的寫作,有別於主流寫作,這就是他存在的意義。
這種獨特個人心靈史,倒比一般的小說,還有市場。它短小,輕鬆,有個人感悟,每個人都能從中找到會心一笑的地方,讀起來不累,有收穫,市場前景應該不錯。小說或敘事類文學太多了,眼花繚亂,大家都不知怎么選了,如果沒有突出的個性,反而不好賣。我覺得《白紙黑字》這樣的書,是能夠慢慢賣的,因為它所提供的材料、感受,別的書無法代替。
這個社會正在轉型,或者說正在發生巨變,我知道,很多人對社會的亂象,對社會中那些層出不窮的、無可救藥的現象持有悲觀的態度。我自己,很長一段時間也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我的看法有改變,我覺得,無論是有話語權的人,還是普通小民,都不應該輕易放棄,不能把我們自己的權利拱手相讓,要堅信,現狀終歸是可以改變的,只要每一個人都努力,每一個人都發出聲音,每一個人都不藐視自己的努力和聲音,現狀是可以改變的。我們應該聯合起來,積極一點,為改變這個社會做些努力。我經常在想,假如那些壞人都可以團結起來一起幹壞事,為何我們不能?應該做事,應該發聲。
陳文的《白紙黑字》,正是在用他的方式發聲。這個聲音是細微的、軟弱的,但是真實的,是對自己和自己的生命誠實。這種真實,是整個社會要回到常識、回到理性的基礎。索爾仁尼琴說,一句真話有時比一個世界的分量還重。首先要真實地面對自己,接著才是責任或理想,才談得上改變。
欠缺的是,陳文沒有對一些問題作更深入的思考,我其實是希望他的書中有一些異峰突起的段落,也就是說,我希望在一些問題上,他可以作長篇大論,這樣整部書的節奏感也會更豐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