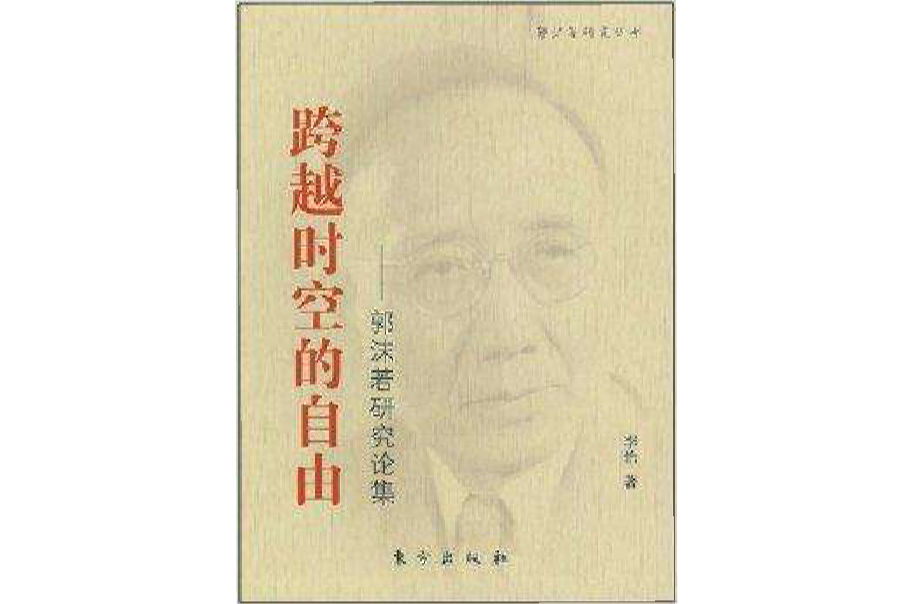《跨越時空的自由:郭沫若研究論集》是《郭沫若研究叢書》的一種,是一部試圖站在當代思想文化發展的視角上重新剖析郭沫若思想、藝術成就的著作,系作者多年的郭沫若研究的成果結晶,它包括郭沫若研究的區域文化視野、郭沫若研究的比較文化視野、郭沫若詩歌研究、郭沫若文化觀念研究、郭沫若研究學術建設問題等幾個大的方面,通過這樣的研究,希望建構起郭沫若研究的新的闡釋框架。
基本介紹
- 書名:跨越時空的自由:郭沫若研究論集
-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 頁數:201頁
- 開本:16
- 作者:李怡
- 出版日期:2008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6030786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跨越時空的自由:郭沫若研究論集》由東方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郭沫若研究叢書》總序
創作論
《女神》與屈騷
中國詩文化的自由形態與自覺形態——郭沫若詩歌的文化闡釋
文化論
面對傳統的兩類中國知識分子——魯迅與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之比較
來自巴蜀的反叛與先鋒——郭沫若與現代四川文學片論之一
青春的詩情與“年輕”的文化人——郭沫若及現代四川作家片論之二
巴蜀文化的20世紀體驗者——郭沫若與四川經典作家札記
郭沫若與中國20世紀學院派文化的分離
研討中國現代作家與鄉土文化的兩個問題——從郭沫若與鄉土文化所想到的
思潮與思維論
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輸入中國的幾個問題——兼及郭沫若與創造社
郭沫若、創造社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
時空的自由與郭沫若的感受方式
學術史論
抗戰文化、抗戰文學與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研究二題
關於郭沫若與四川地域文學研究方法論的兩種思考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問題
二、巴蜀學派與當代批評——與毛迅對話
後記
創作論
《女神》與屈騷
中國詩文化的自由形態與自覺形態——郭沫若詩歌的文化闡釋
文化論
面對傳統的兩類中國知識分子——魯迅與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文化之比較
來自巴蜀的反叛與先鋒——郭沫若與現代四川文學片論之一
青春的詩情與“年輕”的文化人——郭沫若及現代四川作家片論之二
巴蜀文化的20世紀體驗者——郭沫若與四川經典作家札記
郭沫若與中國20世紀學院派文化的分離
研討中國現代作家與鄉土文化的兩個問題——從郭沫若與鄉土文化所想到的
思潮與思維論
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輸入中國的幾個問題——兼及郭沫若與創造社
郭沫若、創造社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
時空的自由與郭沫若的感受方式
學術史論
抗戰文化、抗戰文學與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研究二題
關於郭沫若與四川地域文學研究方法論的兩種思考
一、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問題
二、巴蜀學派與當代批評——與毛迅對話
後記
文摘
《女神》與屈騷
一
《女神》的評析與郭沫若屈原觀的討論歷來都是整個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前者,西方浪漫詩學、個性主義、古今中外的泛神論思想都得到過深入的、全面的和反覆的闡述,對於後者,又顯然主要同一系列的學術研究及歷史劇創作聯繫在一起;相比之下,屈原與郭沫若詩歌創作的關係,特別是屈騷與《女神》的精神聯繫,則始終沒有展開過更細緻更認真的開掘。我認為,這一現象(我稱之為“學術盲點”)的存在有它充分的根據,但也由此而失去了一個解剖《女神》核心的機會。
追溯《女神》研究史我們可以知道,聞一多1923年的兩篇評論提出了《女神》研究中最早的權威性結論:《女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但也顯得缺少“地方色彩”,即民族特色。無論後人對聞一多的這番評論作怎樣的修正,有一個基本的思路是不曾改變的,即都是將《女神》置於引入西方文化、西方詩學以改造中國舊文學、建設中國新詩這一背景上來加以認識,在這樣一個基準上,郭沫若的一些自述也就得到了格外的重視,比如他說:“我短短的做詩經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太戈爾式”,“第二段是惠特曼式”,“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
在中國新詩作為“史”的進步意義上,最充分地開掘《女神》的時代精神、外來影響這絕對無可指責,但是,任何理論性的闡釋在就對象作出更清晰的判斷之時卻也同時意味著某種令人遺憾的“遮蔽”。
一
《女神》的評析與郭沫若屈原觀的討論歷來都是整個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前者,西方浪漫詩學、個性主義、古今中外的泛神論思想都得到過深入的、全面的和反覆的闡述,對於後者,又顯然主要同一系列的學術研究及歷史劇創作聯繫在一起;相比之下,屈原與郭沫若詩歌創作的關係,特別是屈騷與《女神》的精神聯繫,則始終沒有展開過更細緻更認真的開掘。我認為,這一現象(我稱之為“學術盲點”)的存在有它充分的根據,但也由此而失去了一個解剖《女神》核心的機會。
追溯《女神》研究史我們可以知道,聞一多1923年的兩篇評論提出了《女神》研究中最早的權威性結論:《女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但也顯得缺少“地方色彩”,即民族特色。無論後人對聞一多的這番評論作怎樣的修正,有一個基本的思路是不曾改變的,即都是將《女神》置於引入西方文化、西方詩學以改造中國舊文學、建設中國新詩這一背景上來加以認識,在這樣一個基準上,郭沫若的一些自述也就得到了格外的重視,比如他說:“我短短的做詩經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太戈爾式”,“第二段是惠特曼式”,“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
在中國新詩作為“史”的進步意義上,最充分地開掘《女神》的時代精神、外來影響這絕對無可指責,但是,任何理論性的闡釋在就對象作出更清晰的判斷之時卻也同時意味著某種令人遺憾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