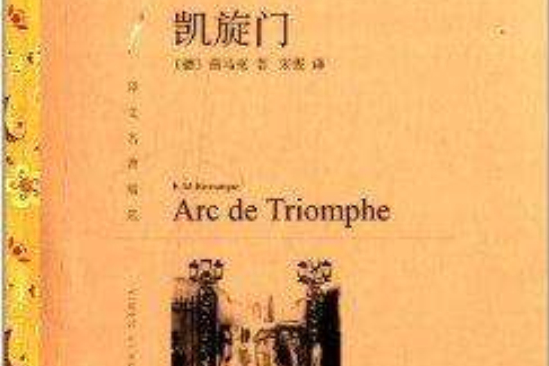小說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敘述一個反法西斯的德國醫生流亡巴黎後的種種遭遇。
基本介紹
- 書名:譯文名著精選:凱旋門
- 作者:雷馬克
-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 頁數:509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譯文出版社
- 外文名:Arc De Triomphe
- 譯者:朱雯
- 出版日期:2012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2757048, 9787532757046
內容簡介,序言,
內容簡介
《譯文名著精選:凱旋門》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序言
埃里希·馬里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於1898年出生在德國威斯特伐利亞的奧斯納布呂克市。祖先是法國人,1789年法蘭西大革命時遷移到了萊茵蘭。家境清貧,父親在當地普雷勒工廠當書籍裝訂工人。他一家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雷馬克青少年時期一直在天主教會學校念書。在當時,窮苦人家子弟的唯一出路是教書,因為進師範學校學習不需要家長在經濟上有什麼負擔;就這樣,從1912年起,雷馬克讀了天主教會辦的師範預備班,1915年正式進入當地的初等師範學校,可是修業未滿兩年,1916年11月就從學校直接應徵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他五次負傷,特別是最後一次在佛蘭德戰役中,他從火線救出一位受傷的戰友時,在英軍的突然襲擊下,自己被好幾顆手榴彈所炸傷,傷勢相當嚴重,經過較長時間的治療,總算只在右腕節上留下一個無法消退的疤痕。大戰結束以後,他回到原來的學校,修畢規定的課程,在靠近荷蘭邊境的一個村子裡當了一年國小教師。但是他對這個工作感到失望,覺得太受約束,而且根據他自身的經驗,教書也不過是為國家培養新一代的士兵,因此他就堅決辭去了教職。二十年代,對戰後德國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時期,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日子很不好過。在那段時間裡,雷馬克自己說是“乾過各種各樣的營生:有時候我到處闖蕩,拿著一隻手提箱,販賣零星什物……後來,我又做過石匠,乾過其他一些事情,還在一家精神病院裡當過風琴手”。之後,他為《大陸回聲報》撰寫廣告稿和評論文章,1922年秋,去漢諾瓦大陸公司正式擔任廣告部主任兼《大陸回聲報》主編,為這個刊物寫了許多作為輪胎、機車、汽車廣告的短小而幽默的文字。由於撰寫這類文字所顯示的才能,他被聘擔任《體育畫報》的編輯,於1925年移居柏林。在這個刊物上,他曾連載過一篇題名為《地平線上的車站》(station am Horizont)的小說,反映了他對汽車和賽車的愛好,但是也像1920年在德勒斯登自費出版的另一本小說《夢之窩》(Die1Yaumbude)一樣,寫得“實在很糟”。後來他自己也說:“早些時候,我完全不是這樣寫作的。我做過種種試驗……為了想創立一種風格,可是所有的東西都顯得沉悶而蒼白,自己一點也不滿意,大概因為我的路子完全走錯了。”
1927年下半年,雷馬克開始寫他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在醞釀、構思的小說《西線無戰事》(In Westen nichts Neues)。完全利用業餘的晚上,他僅僅花了六個星期就把小說寫成了,可是那手稿卻在抽屜里擱置了半年。一家書店不願意出版這部作品,另一家出版社總算將它接受下來了。先在《福斯報》上連載,隨後作了一些修改,印成單行本出版。連載的時候,那份報紙的銷數一下子增加了三倍,人們都說十九世紀英國讀者爭先搶購狄更斯連載小說的盛況,居然重見於今日的德國。1929年1月全書出版以後,更引起了德國以及世界其他許多國家的轟動。僅在德國國內,第一年就銷售了一百二十萬冊。同年3月,首先被譯成英文在英國出版,每冊定價雖高達七先令六便士,但六周之內銷售了二十七萬五千冊。把其他許多語種的譯本一併計算在內,此書總發行量當在五百萬冊以上,這在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種意外的成功,使雷馬克的整個生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原先是個無名小卒的記者,竟然一躍而成為世界聞名的作家。有的人喜歡他,有的人厭惡他,有的人稱頌他,有的人詆毀他,一時間對他本人和這部作品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他一向抱著置身事外的態度,既不願意接見為此而來訪的客人,更不願意參與有關他作品的爭論。而且他從來都以不問世事自居,他也確實從來不參加任何社會運動,不料到了1930年,納粹黨還是找到他頭上來了。他們攻擊他在對待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上採取反對英雄主義的態度,而在他們看來,這種在軍事衝突中表現出來的個人英雄主義,正是錘鍊國家社會主義的鋼鐵精神的熊熊烈火,因此他們決不能寬恕他對這個納粹神話的挑戰。正好那時根據《西線無戰事》改編拍攝的美國影片準備在柏林放映,區的納粹黨魁戈培爾便利用這一時機,唆使一幫希特勒青年團員向那家劇場進行破壞和搗亂,達到了禁演這部影片的目的。這一行動,迫使雷馬克不得不離開柏林,甚至不得不離開德國。他後來說:“1931年,我不得不離開德國,因為我的生命遭受到威脅。我既不是猶太人,而且在政治上也並不左傾。當時的我,也跟今天的我一樣,是個戰鬥的和平主義者。”離開柏林以後,他到了瑞士,定居於馬喬列湖上的龍谷港,納粹政變的訊息他就是在那裡聽到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後,雷馬克的作品跟托馬斯·曼、亨利希·曼、布萊希特等人的作品一起被公開燒毀,隨後又因為他堅決拒絕回國而於1938年被褫奪了德國國籍。翌年,他轉赴美國,到1942年為止,大部分時間都在好萊塢,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銀幕,1947年加入了美國國籍。雷馬克雖然已經流亡國外,但是納粹政權並沒有放鬆對他的迫害。1943年12月,他那仍在德國的妹妹埃爾夫莉德以莫須有的罪名(誣控她不相信德國會取得勝利)被納粹法庭宣判了死刑。從1945年起,雷馬克也常在瑞士居住。六十年代中期,他突然發作了幾次心臟病,健康狀況越來越差,1970年9月25日病逝於瑞士的洛迦諾,終年72歲。
雷馬克一生寫了十一部長篇小說和一個劇本《最後一站》(Dieletae Station,1956年)。十一部小說中,除《西線無戰事》專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其餘幾部,如果按題材來劃分,那么有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以及通貨膨脹年代生活的,如《戰後》(Der Weg zurock,1931年)、《三個戰友》(Drei Kameraden,1937年)、《黑色方尖碑》(Derschwarze Obelisk,1956年)、《上帝沒有寵兒》(Der Himmel kennt keine Gunsflinge,1961年);有寫流亡生活的,如《愛你的鄰人》(Leibe deinen.Nachsten,1953年)、《凱旋門》(Arc de Tfiomphe,1946年)、《里斯本之夜》(Die:Nacht yon Lissabon,1963年);有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如《生命的火花》(Der Funke Leben,1952年)、《生死存亡的年代》(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1954年)。作家逝世後一年,又發表了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天堂里的影子》(Die Schatten im Paradies,1971年)。
雷馬克寫流亡生活的幾部作品中,數《凱旋門》最有影響;除《西線無戰事》以外的十部小說中,也數《凱旋門》最為暢銷。在德文原著發行之前,它的英譯本首先在美國出版,僅在美國國內,銷數就在二百萬冊以上,不久被譯成十五種文字,又銷售了五百萬冊,其盛況與當年《西線無戰事》不相上下。這是因為這部作品的故事情節十分動人,藝術手法也更臻成熟。依我個人看來,《西線無戰事》只能說是雷馬克的成名作,《凱旋門》才是他的代表作。
小說主人公拉維克(直到小說結尾,讀者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是路特維希·佛雷森布格),原來在德國一家大醫院裡當外科主任醫生,受納粹秘密警察迫害和追捕,兩年前流亡到法國,在巴黎為一位醫術並不高明的法國醫生維伯爾和另一位上了年紀的時髦醫生杜蘭特充當“捉刀的”外科醫生。有一天晚上,他在塞納河上的一座橋畔遇到一個漂亮的女人瓊·瑪陀,從而演出一場纏綿悱惻的愛情悲喜劇。有一次,他在街頭搶救一位在事故中受傷的女人,因為沒有身份證件而被法國警察拘捕,並驅逐出境,到了瑞士。幾個月後他潛返巴黎,瓊卻已經跟一個演員住在一起,出於嫉妒,那演員向瓊開了一槍,子彈打在她的頸椎里,不容易取出來。拉維克雖是一位技術高超的外科醫生,對此也無能為力。在瓊和拉維克相互訣別,並明確表示彼此相愛以後,拉維克給瓊注射了解除痛苦的最後一針,從而結束了她無法挽救的生命。
與這個愛情故事交織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復仇的故事。小說主人公拉維克於1933年在德國,曾經幫助兩個朋友逃出了納粹秘密警察的追捕。他和他的女友茜貝爾卻被一個名叫哈克的秘密警察頭目抓去審問,並施以種種酷刑。拉維克給關進了集中營,後來好容易從集中營的醫院裡逃出來。到了巴黎,拉維克又偶然碰上了哈克,這就燃起了他的復仇之火。因為沒有被認出來,拉維克便佯裝跟他交上了朋友,並帶他去冶遊作樂。幾星期後,拉維克終於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他把哈克哄進一座樹林,謊稱那裡有一家高級的幽會場所,可以找上流社會婦女來作樂。就在去樹林的路上,他把哈克用活動扳手猛一下給打死了。
跟雷馬克的大部分作品不同,《凱旋門》的時代背景展示得特別清晰。小說開頭後不久,就寫到“探照燈安裝在凱旋門後面。它們照亮著無名英雄墓。一面巨大的藍、白、紅三色旗,在墓前迎風飄揚。這是1918年停戰的二十周年紀念”。很明顯,這一天是1938年11月11日。在小說的結尾,又寫到“維伯爾指著一張晨報的號外。德軍進占波蘭。‘我從政府方面得到訊息。今天就要宣戰了’”。法國向德國正式宣戰,那是在1939年9月3日。所以小說女主人公瓊在臨死前對拉維克說:“從那個時候起——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不再知道該往哪兒去——是你給我的——這一年。這是時間的禮物。”在這一年裡,歐洲發生了很多重大的政治歷史事件,小說都有所反映或間接提到。拉維克有個富有的女病人凱特·赫格斯特龍,就談起過她的前夫原是一個遊手好閒的浪蕩子,如今已變成一名搖旗吶喊的納粹衝鋒隊頭目。這很可能發生在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軍隊侵占奧地利的前後。小說又多次提到並譴責慕尼黑協定。那是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同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於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舉行會議時簽訂的。協定規定捷克斯洛伐克將蘇台德區和同奧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區割讓給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領土則由英、法、德、意共同“保證”不再受侵犯。捷克政府在德國的軍事威脅和英、法綏靖政策的誘騙下,接受了這個條件。同年10月、11月,德軍占領蘇台德區。不料於1939年3月15日德國違反協定,又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領土;9月1日,甚至還進攻波蘭。至此,英、法才不得不對德國宣戰。幾天之內,所有居留在法國的德國人,都被逮捕,並給關進了拘留營,這中間就有小說主人公拉維克醫生。
作為一個沒有護照、沒有任何證件的難民,拉維克在巴黎過的流亡生活是很不好受的。他無法租用公寓房間,只能借住在一家擠滿了猶太人以及德國、西班牙等國難民的旅館內。他日夜擔心著法國警察的搜查和拘捕。一旦被發現,就要被押送出境,有一回他曾被驅逐到捷克,與他所愛的瓊別離,從而釀成了一出愛情悲劇。但和其他許多流亡在法國的難民相比,他的生活應當說是穩定的。他從未遭受過凍餒的威脅。雖然作為一個醫術高明的“捉刀”醫生,他受到兩位法國同行的剝削是不難想像的,可他畢竟還能過相當優裕的生活,可以和瓊一起去度假勝地里維耶拉談情說愛,演出一幕迥非一般難民所能搬演的愛情劇。所以說,拉維克的痛苦,與其說是物質上的,毋寧說是精神上的。而除了一般難民所共有的精神痛苦以外,他還有隻屬於他一個人的痛苦。那就是他對幾年前在德國集中營里折磨過他、折磨過他的女友的秘密警察頭目哈克懷有深仇大恨,慘痛的往事時刻啃齧著他的心,使他一直無法平靜。後來看見哈克出現在巴黎,他又偵伺追蹤,一心想獵獲這頭嗜血的野獸,結果,終於把這個殺人的魔王消滅了。而同時,他對萍水相逢、橋畔邂逅的瓊·瑪陀則懷著摯愛深情。拉維克原先對人生抱有一種消極、冷漠的態度,有點玩世不恭,自從與瓊相識又相愛以後,他的態度改變了,精神振作起來,生活有了勇氣,有了信心,正像他一再跟瓊說的,“你使我活著,瓊。你使我活著。我本來只是一塊頑石,是你使我活著的”;“沒有了你,我便什麼都完了。你是一切的光明,甜蜜的苦澀——你震撼了我,你給了我你自己和我自己。你使我活著”。正因為愛得真摯,愛得熱烈,他就一直擔憂著會失去她,而事實上,一次生離,一次死別,結果還是失去了。殺死哈克和失去了瓊,使他解除精神上的痛苦,得到了內心的寧靜。作者在小說結尾,以洋溢著詩意的筆觸,描繪了拉維克最後離開巴黎時的心態:
“一切都很好。那些已經過去的和仍然會到來的。這就夠了。即使是結局,這樣也很好。他曾經愛過一個人,卻已經失去了她。他曾經恨過一個人,卻已經殺死了他。這兩件事情,都使他解脫了。一個人復活了他的感情,另一個人消滅了他的過去。沒有一件未了的塵緣。沒有欲望;沒有憎恨,也沒有哀怨。”
瓊是雷馬克筆下最有個性的一位女性形象,瓊和拉維克的瓜葛是最富魅力的一個愛情故事。作者素以善寫對話著稱,而瓊與拉維克的對話,更是一件最為感人的藝術珍品。尤其是他們在瓊臨終前的那一段,各人用各人兒時的語言,瓊用義大利語,拉維克用德語,表達了各人滿腔的積愫,雖然互不通曉,卻進行了最為深邃的心靈交流,讀者掩卷尋思,恐怕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激動。
關於瓊·瑪陀這個人物的原型,評論界頗多揣測,有人認為很可能是雷馬克的好友,好萊塢的著名影星瑪琳·黛德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他們倆正好一起生活在巴黎。小說一開頭,對瓊就有這樣幾句肖像描寫:“只見她臉色蒼白,顴骨高聳,兩隻眼睛間距很寬;容顏呆板,活像一張假面具”;“她那張蒼白的臉上,差不多毫無表情。嘴很飽滿,就是沒有血色,看上去輪廓顯得模糊;唯有頭髮可長得挺美——一種有光澤的、天然的金黃秀髮。”這又正好是瑪琳·黛德麗的寫照。至於拉維克這個人物,很多評論家認為他的原型就是雷馬克自己,因為拉維克的處世態度完全體現了雷馬克的人生哲學。雷馬克自稱是一個“不抱幻想的理想主義者”,他忠於“高尚的個人主義”,視“最普通的人道法則”為自己最高的行為準則,而拉維克正是這些思想的化身。國際旅館中有一個名叫莫羅佐夫的難民,“是第一次大戰的流亡者,近十五年來一直住在巴黎。他是那樣一種俄國人,他們不談自己曾在沙皇的禁衛軍里服過役,也不提自己那貴族的門第”,很明顯,他這個“流亡者”與受納粹法西斯迫害而流亡的巴黎的難民完全屬於不同的類型,而拉維克卻引為最相投合的知己,雷馬克也在小說中把他作為一個僅次於拉維克的重要人物。再說拉維克的殺死哈克,固然是反法西斯的一個具體行動,但從動機到手段,都屬於私人復仇的性質,與當時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運動和反納粹德國的任何組織完全沒有聯繫。雷馬克是拉維克的原型,這一點作者自己也承認,不過拉維克是個醫生,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人的影子。雷馬克有一次在會見布拉格一位記者時說:“拉維克這一形象,包含著三個人的特徵。我自己,還有我的兩個朋友。兩位醫生,他們也像我一樣,隱姓埋名住在巴黎。其中一位,我在心臟病第一次發作時請他來看過病……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學過醫學,小說中有關醫學方面的內容是他幫助我寫下的。”
《凱旋門》是我翻譯雷馬克的第一部作品。1945年秋天,這部小說的英譯稿首先在美國《柯里爾》周刊上發表,我當時就根據連載稿逐期翻譯,逐日發表在上海一家報紙上,自1946年1月20日起至5月7日為止,連載了七十七天,還未刊完,就看到由美國D·阿普爾頓一世紀公司出版的英譯本,才發現連載稿原來只是原著的節譯本,於是又根據全譯本重譯了一遍,於1948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我在當時初版後記中寫道:“在出版方面,我應該特別感謝李先生。假如沒有他對於原著的卓越的鑑賞,以及對譯者的友善的鼓勵,我還不敢相信在物價騰貴的今日,能使這樣一個拙劣的譯本得到出版的機會。”巴金先生不僅把《凱旋門》列入他主編的“譯文叢書”,而且還希望我把雷馬克的所有作品一一介紹過來,彙編成《雷馬克全集》。感謝他的鼓勵,我後來又翻譯了雷馬克的幾部作品,但由於疏懶,我並沒有完成他的期望和我的心愿。我現在已進入耄耋之年,來日無多,看來已不大可能了卻這樁心愿的了,因此對四十多年前翻譯的這本《凱旋門》,特別有一種說不分明的情感。這次上海譯文出版社讓我有一個重排譯文的機會,使我下決心根據原著重譯,可由於近年來衰病侵尋,不能連續持久地工作,竟又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即便如此,仍難免有疏漏紕謬之處,於心深感不安,在此敬請方家和讀者們匡正。
朱雯
1994年6月於病中
1927年下半年,雷馬克開始寫他大戰結束以來一直在醞釀、構思的小說《西線無戰事》(In Westen nichts Neues)。完全利用業餘的晚上,他僅僅花了六個星期就把小說寫成了,可是那手稿卻在抽屜里擱置了半年。一家書店不願意出版這部作品,另一家出版社總算將它接受下來了。先在《福斯報》上連載,隨後作了一些修改,印成單行本出版。連載的時候,那份報紙的銷數一下子增加了三倍,人們都說十九世紀英國讀者爭先搶購狄更斯連載小說的盛況,居然重見於今日的德國。1929年1月全書出版以後,更引起了德國以及世界其他許多國家的轟動。僅在德國國內,第一年就銷售了一百二十萬冊。同年3月,首先被譯成英文在英國出版,每冊定價雖高達七先令六便士,但六周之內銷售了二十七萬五千冊。把其他許多語種的譯本一併計算在內,此書總發行量當在五百萬冊以上,這在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種意外的成功,使雷馬克的整個生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原先是個無名小卒的記者,竟然一躍而成為世界聞名的作家。有的人喜歡他,有的人厭惡他,有的人稱頌他,有的人詆毀他,一時間對他本人和這部作品展開了激烈的論爭。他一向抱著置身事外的態度,既不願意接見為此而來訪的客人,更不願意參與有關他作品的爭論。而且他從來都以不問世事自居,他也確實從來不參加任何社會運動,不料到了1930年,納粹黨還是找到他頭上來了。他們攻擊他在對待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上採取反對英雄主義的態度,而在他們看來,這種在軍事衝突中表現出來的個人英雄主義,正是錘鍊國家社會主義的鋼鐵精神的熊熊烈火,因此他們決不能寬恕他對這個納粹神話的挑戰。正好那時根據《西線無戰事》改編拍攝的美國影片準備在柏林放映,區的納粹黨魁戈培爾便利用這一時機,唆使一幫希特勒青年團員向那家劇場進行破壞和搗亂,達到了禁演這部影片的目的。這一行動,迫使雷馬克不得不離開柏林,甚至不得不離開德國。他後來說:“1931年,我不得不離開德國,因為我的生命遭受到威脅。我既不是猶太人,而且在政治上也並不左傾。當時的我,也跟今天的我一樣,是個戰鬥的和平主義者。”離開柏林以後,他到了瑞士,定居於馬喬列湖上的龍谷港,納粹政變的訊息他就是在那裡聽到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後,雷馬克的作品跟托馬斯·曼、亨利希·曼、布萊希特等人的作品一起被公開燒毀,隨後又因為他堅決拒絕回國而於1938年被褫奪了德國國籍。翌年,他轉赴美國,到1942年為止,大部分時間都在好萊塢,把自己的作品搬上銀幕,1947年加入了美國國籍。雷馬克雖然已經流亡國外,但是納粹政權並沒有放鬆對他的迫害。1943年12月,他那仍在德國的妹妹埃爾夫莉德以莫須有的罪名(誣控她不相信德國會取得勝利)被納粹法庭宣判了死刑。從1945年起,雷馬克也常在瑞士居住。六十年代中期,他突然發作了幾次心臟病,健康狀況越來越差,1970年9月25日病逝於瑞士的洛迦諾,終年72歲。
雷馬克一生寫了十一部長篇小說和一個劇本《最後一站》(Dieletae Station,1956年)。十一部小說中,除《西線無戰事》專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外,其餘幾部,如果按題材來劃分,那么有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以及通貨膨脹年代生活的,如《戰後》(Der Weg zurock,1931年)、《三個戰友》(Drei Kameraden,1937年)、《黑色方尖碑》(Derschwarze Obelisk,1956年)、《上帝沒有寵兒》(Der Himmel kennt keine Gunsflinge,1961年);有寫流亡生活的,如《愛你的鄰人》(Leibe deinen.Nachsten,1953年)、《凱旋門》(Arc de Tfiomphe,1946年)、《里斯本之夜》(Die:Nacht yon Lissabon,1963年);有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如《生命的火花》(Der Funke Leben,1952年)、《生死存亡的年代》(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1954年)。作家逝世後一年,又發表了他的最後一部小說《天堂里的影子》(Die Schatten im Paradies,1971年)。
雷馬克寫流亡生活的幾部作品中,數《凱旋門》最有影響;除《西線無戰事》以外的十部小說中,也數《凱旋門》最為暢銷。在德文原著發行之前,它的英譯本首先在美國出版,僅在美國國內,銷數就在二百萬冊以上,不久被譯成十五種文字,又銷售了五百萬冊,其盛況與當年《西線無戰事》不相上下。這是因為這部作品的故事情節十分動人,藝術手法也更臻成熟。依我個人看來,《西線無戰事》只能說是雷馬克的成名作,《凱旋門》才是他的代表作。
小說主人公拉維克(直到小說結尾,讀者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是路特維希·佛雷森布格),原來在德國一家大醫院裡當外科主任醫生,受納粹秘密警察迫害和追捕,兩年前流亡到法國,在巴黎為一位醫術並不高明的法國醫生維伯爾和另一位上了年紀的時髦醫生杜蘭特充當“捉刀的”外科醫生。有一天晚上,他在塞納河上的一座橋畔遇到一個漂亮的女人瓊·瑪陀,從而演出一場纏綿悱惻的愛情悲喜劇。有一次,他在街頭搶救一位在事故中受傷的女人,因為沒有身份證件而被法國警察拘捕,並驅逐出境,到了瑞士。幾個月後他潛返巴黎,瓊卻已經跟一個演員住在一起,出於嫉妒,那演員向瓊開了一槍,子彈打在她的頸椎里,不容易取出來。拉維克雖是一位技術高超的外科醫生,對此也無能為力。在瓊和拉維克相互訣別,並明確表示彼此相愛以後,拉維克給瓊注射了解除痛苦的最後一針,從而結束了她無法挽救的生命。
與這個愛情故事交織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復仇的故事。小說主人公拉維克於1933年在德國,曾經幫助兩個朋友逃出了納粹秘密警察的追捕。他和他的女友茜貝爾卻被一個名叫哈克的秘密警察頭目抓去審問,並施以種種酷刑。拉維克給關進了集中營,後來好容易從集中營的醫院裡逃出來。到了巴黎,拉維克又偶然碰上了哈克,這就燃起了他的復仇之火。因為沒有被認出來,拉維克便佯裝跟他交上了朋友,並帶他去冶遊作樂。幾星期後,拉維克終於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他把哈克哄進一座樹林,謊稱那裡有一家高級的幽會場所,可以找上流社會婦女來作樂。就在去樹林的路上,他把哈克用活動扳手猛一下給打死了。
跟雷馬克的大部分作品不同,《凱旋門》的時代背景展示得特別清晰。小說開頭後不久,就寫到“探照燈安裝在凱旋門後面。它們照亮著無名英雄墓。一面巨大的藍、白、紅三色旗,在墓前迎風飄揚。這是1918年停戰的二十周年紀念”。很明顯,這一天是1938年11月11日。在小說的結尾,又寫到“維伯爾指著一張晨報的號外。德軍進占波蘭。‘我從政府方面得到訊息。今天就要宣戰了’”。法國向德國正式宣戰,那是在1939年9月3日。所以小說女主人公瓊在臨死前對拉維克說:“從那個時候起——當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不再知道該往哪兒去——是你給我的——這一年。這是時間的禮物。”在這一年裡,歐洲發生了很多重大的政治歷史事件,小說都有所反映或間接提到。拉維克有個富有的女病人凱特·赫格斯特龍,就談起過她的前夫原是一個遊手好閒的浪蕩子,如今已變成一名搖旗吶喊的納粹衝鋒隊頭目。這很可能發生在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軍隊侵占奧地利的前後。小說又多次提到並譴責慕尼黑協定。那是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同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於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舉行會議時簽訂的。協定規定捷克斯洛伐克將蘇台德區和同奧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區割讓給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的其餘領土則由英、法、德、意共同“保證”不再受侵犯。捷克政府在德國的軍事威脅和英、法綏靖政策的誘騙下,接受了這個條件。同年10月、11月,德軍占領蘇台德區。不料於1939年3月15日德國違反協定,又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領土;9月1日,甚至還進攻波蘭。至此,英、法才不得不對德國宣戰。幾天之內,所有居留在法國的德國人,都被逮捕,並給關進了拘留營,這中間就有小說主人公拉維克醫生。
作為一個沒有護照、沒有任何證件的難民,拉維克在巴黎過的流亡生活是很不好受的。他無法租用公寓房間,只能借住在一家擠滿了猶太人以及德國、西班牙等國難民的旅館內。他日夜擔心著法國警察的搜查和拘捕。一旦被發現,就要被押送出境,有一回他曾被驅逐到捷克,與他所愛的瓊別離,從而釀成了一出愛情悲劇。但和其他許多流亡在法國的難民相比,他的生活應當說是穩定的。他從未遭受過凍餒的威脅。雖然作為一個醫術高明的“捉刀”醫生,他受到兩位法國同行的剝削是不難想像的,可他畢竟還能過相當優裕的生活,可以和瓊一起去度假勝地里維耶拉談情說愛,演出一幕迥非一般難民所能搬演的愛情劇。所以說,拉維克的痛苦,與其說是物質上的,毋寧說是精神上的。而除了一般難民所共有的精神痛苦以外,他還有隻屬於他一個人的痛苦。那就是他對幾年前在德國集中營里折磨過他、折磨過他的女友的秘密警察頭目哈克懷有深仇大恨,慘痛的往事時刻啃齧著他的心,使他一直無法平靜。後來看見哈克出現在巴黎,他又偵伺追蹤,一心想獵獲這頭嗜血的野獸,結果,終於把這個殺人的魔王消滅了。而同時,他對萍水相逢、橋畔邂逅的瓊·瑪陀則懷著摯愛深情。拉維克原先對人生抱有一種消極、冷漠的態度,有點玩世不恭,自從與瓊相識又相愛以後,他的態度改變了,精神振作起來,生活有了勇氣,有了信心,正像他一再跟瓊說的,“你使我活著,瓊。你使我活著。我本來只是一塊頑石,是你使我活著的”;“沒有了你,我便什麼都完了。你是一切的光明,甜蜜的苦澀——你震撼了我,你給了我你自己和我自己。你使我活著”。正因為愛得真摯,愛得熱烈,他就一直擔憂著會失去她,而事實上,一次生離,一次死別,結果還是失去了。殺死哈克和失去了瓊,使他解除精神上的痛苦,得到了內心的寧靜。作者在小說結尾,以洋溢著詩意的筆觸,描繪了拉維克最後離開巴黎時的心態:
“一切都很好。那些已經過去的和仍然會到來的。這就夠了。即使是結局,這樣也很好。他曾經愛過一個人,卻已經失去了她。他曾經恨過一個人,卻已經殺死了他。這兩件事情,都使他解脫了。一個人復活了他的感情,另一個人消滅了他的過去。沒有一件未了的塵緣。沒有欲望;沒有憎恨,也沒有哀怨。”
瓊是雷馬克筆下最有個性的一位女性形象,瓊和拉維克的瓜葛是最富魅力的一個愛情故事。作者素以善寫對話著稱,而瓊與拉維克的對話,更是一件最為感人的藝術珍品。尤其是他們在瓊臨終前的那一段,各人用各人兒時的語言,瓊用義大利語,拉維克用德語,表達了各人滿腔的積愫,雖然互不通曉,卻進行了最為深邃的心靈交流,讀者掩卷尋思,恐怕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激動。
關於瓊·瑪陀這個人物的原型,評論界頗多揣測,有人認為很可能是雷馬克的好友,好萊塢的著名影星瑪琳·黛德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他們倆正好一起生活在巴黎。小說一開頭,對瓊就有這樣幾句肖像描寫:“只見她臉色蒼白,顴骨高聳,兩隻眼睛間距很寬;容顏呆板,活像一張假面具”;“她那張蒼白的臉上,差不多毫無表情。嘴很飽滿,就是沒有血色,看上去輪廓顯得模糊;唯有頭髮可長得挺美——一種有光澤的、天然的金黃秀髮。”這又正好是瑪琳·黛德麗的寫照。至於拉維克這個人物,很多評論家認為他的原型就是雷馬克自己,因為拉維克的處世態度完全體現了雷馬克的人生哲學。雷馬克自稱是一個“不抱幻想的理想主義者”,他忠於“高尚的個人主義”,視“最普通的人道法則”為自己最高的行為準則,而拉維克正是這些思想的化身。國際旅館中有一個名叫莫羅佐夫的難民,“是第一次大戰的流亡者,近十五年來一直住在巴黎。他是那樣一種俄國人,他們不談自己曾在沙皇的禁衛軍里服過役,也不提自己那貴族的門第”,很明顯,他這個“流亡者”與受納粹法西斯迫害而流亡的巴黎的難民完全屬於不同的類型,而拉維克卻引為最相投合的知己,雷馬克也在小說中把他作為一個僅次於拉維克的重要人物。再說拉維克的殺死哈克,固然是反法西斯的一個具體行動,但從動機到手段,都屬於私人復仇的性質,與當時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運動和反納粹德國的任何組織完全沒有聯繫。雷馬克是拉維克的原型,這一點作者自己也承認,不過拉維克是個醫生,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人的影子。雷馬克有一次在會見布拉格一位記者時說:“拉維克這一形象,包含著三個人的特徵。我自己,還有我的兩個朋友。兩位醫生,他們也像我一樣,隱姓埋名住在巴黎。其中一位,我在心臟病第一次發作時請他來看過病……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學過醫學,小說中有關醫學方面的內容是他幫助我寫下的。”
《凱旋門》是我翻譯雷馬克的第一部作品。1945年秋天,這部小說的英譯稿首先在美國《柯里爾》周刊上發表,我當時就根據連載稿逐期翻譯,逐日發表在上海一家報紙上,自1946年1月20日起至5月7日為止,連載了七十七天,還未刊完,就看到由美國D·阿普爾頓一世紀公司出版的英譯本,才發現連載稿原來只是原著的節譯本,於是又根據全譯本重譯了一遍,於1948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我在當時初版後記中寫道:“在出版方面,我應該特別感謝李先生。假如沒有他對於原著的卓越的鑑賞,以及對譯者的友善的鼓勵,我還不敢相信在物價騰貴的今日,能使這樣一個拙劣的譯本得到出版的機會。”巴金先生不僅把《凱旋門》列入他主編的“譯文叢書”,而且還希望我把雷馬克的所有作品一一介紹過來,彙編成《雷馬克全集》。感謝他的鼓勵,我後來又翻譯了雷馬克的幾部作品,但由於疏懶,我並沒有完成他的期望和我的心愿。我現在已進入耄耋之年,來日無多,看來已不大可能了卻這樁心愿的了,因此對四十多年前翻譯的這本《凱旋門》,特別有一種說不分明的情感。這次上海譯文出版社讓我有一個重排譯文的機會,使我下決心根據原著重譯,可由於近年來衰病侵尋,不能連續持久地工作,竟又花費了多年的時間,即便如此,仍難免有疏漏紕謬之處,於心深感不安,在此敬請方家和讀者們匡正。
朱雯
1994年6月於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