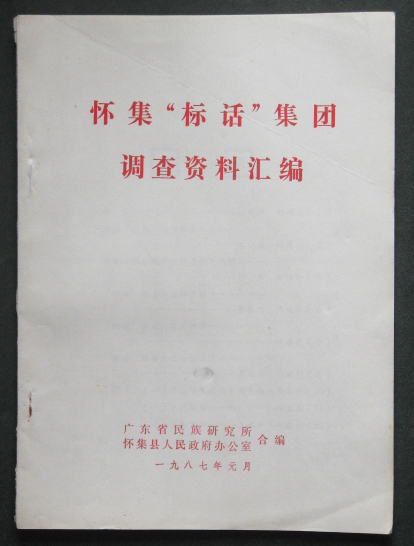概述
“講標人”,據專家初步考證,懷集講標話的漢人祖先是2200多年前戰國時期由中原遷來,這一人群被稱為“講標人”。是南下的華夏部落融合了古越部落人口,從而形成了今天的“講標人”這個獨特的人類群體;而伴隨著文化融合及文化接觸、交往等等,終於發展出現代“講標人”的文化,它是文化交融的結果,其中“標話”本身就是證明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講標人
- 概念:懷集講標話的漢人
- 別名:標話
- 集中地:集中居住在縣北長安鎮
- 性質:是文化交融的結果之一
- 別名:“標話”集團
- 人口:約有7000多人
分布範圍及人口,“標話”,研究結果,
分布範圍及人口
“講標人”又稱“標話”集團,主要居住在廣東省部的懷集、封開兩縣。居住於懷集的“講標人”較多,約15萬人,集中在該縣南部的詩洞、永固、橋頭、大崗等鄉鎮。居於封開的“講標人”人口較少,約有7000多人,集中在縣北長安鎮一帶。以上懷集、封開兩縣的幾個鄉鎮在地理上構成一個以黨山山地為中心的獨特區域,這也就是“講標人”的主要活動區域。
“標話”
“講標人”因操一種屬於漢藏語系侗台語族侗水語支的語言“標話”而得名。經過語言學家的研究,“標語”被認為是一種混合語,與漢語有較大的差別,其標話可以歸入侗台語族中,但其到底應該歸屬於哪一種語,或者說是否可以獨立成語,至今未有定論。
“講標人”自認為來自南雄市珠璣巷,有著漢族的傳統。長安村盧氏族譜中就記載了其祖先與珠璣巷的關係。南下的華夏部落,與嶺南的百越諸部落朝夕相處,互通婚姻,可以說南下的華夏部落和南方百越諸部落是“講標人”共同的祖先。

研究結果
一些學者認識到“講標人”的研究價值,進行相關的研究工作,分別完成若干篇研究論文,或者使用“講標人”的社會文化方面的資料來探討相關問題,從而拓寬了廣東民族學研究的領域。這些學者如廣東民族研究所的練銘志研究員、廣東民族學院(廣東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前身)的姜永興研究員、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客觀瓊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均如研究員,等等。其次,省內一些學者受到民族調查識別工作的影響,關注“講標人”,並利用“講標人”的社會文化資料進行研究,如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的宋長棟教授。再者,還引起了一些年輕學者對“講標人”語言社會歷史文化的興趣,陸續進行調查研究,如顏冰受當年“講標人”民族識別研究的鼓舞,在1988年就以封開縣“講標人”的語言研究完成了中山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到2001年夏天,我們又一起對封開縣長安鎮的“講標人”進行田野人類學的調查研究。
據專家初步考證,懷集講標話的漢人祖先是2200多年前戰國時期由中原遷來,這一人群被稱為“講標人”。 專家們認為,“講標人”是歷史上南方百越諸部落和南下的華夏部落相互影響、混血的結果,其語言社會文化是經過長時間的接觸、交往及多元文化交融的結果,其中在“標話”、宗族組織、宗教信仰、節日、住房、命名等方面的文化交融特點尤其明顯。
封開“講標人”深入調查報告
封開“講標人”集中居住在縣北長安鎮。根據調查統計,長安鎮共有農村戶口的“講標人”6600餘人,約占全鎮人口37000人的18%。至於已經把戶口從農村中遷移到城鎮或者外地的“講標人”的人口則無法進行統計,據當地政府估計約有數百人,新出版的《封開縣誌》介紹“標語”時認為封開“講標人”有7217人,這個數字是比較接近真實狀況的。
當地還有部分人口,原來是講“標話”的,因種種原因不再講“標語”,這些人口並已被當地“講標人”視為異類,列入“不講標”類別。如長安行政村內的樓下墰自然村(林姓),寶山行政村內的下羅柴自然村部分人口(梁姓)、梅花自然村(梁姓)、羅待自然村(褥姓)等等聚落的人口,總數約百人,已不再講“標語”,不再被當地社會承認人“講標人”。但是這些人與各自同一姓氏的“講標人”又保持著密切的同宗關係,仍在一起祭祖。我們在統計“講標人”人口的時候,撇除開了這些已被看成是“講開建話的”人口(開建話為粵語的一支,因歷史上的開建縣而得名)。
近七千人口的“講標人”主要居住在長安鎮長安、寶山、東山三個行政村及下羅境長安墟里,約有40餘個自然聚落。這些聚落分別是:長安行政村的廟後、大街、墰榕、上羅境、大巷街、萬榮寨、長崗、上宅、長遠、銀鋪、城巷、帝兩(又分為軍榮、墰鳳、石坎、大松)、帝木、上墰寺、更樓(長群)、羅仇、鳳寨、安成、羅邁、大園、大棚、水澇、七座、墰田、長安舊墟;寶山行政村的下羅柴、文林、上東、上西、橋頭、宿水、范兩;東山行政村的寨東、寨下、李戶、李宅、白屋、上屋、中南、南屋、花門樓、長江;長安鎮府所在地長安墟,等等。這四十多個自然聚落(聚居地)散布在長安墟周圍,距鎮府最遠的村落亦只在三公里左右。
“講標人”的主要姓氏是褥、梁、仇、盧、陳、林、蘇、李、袁等,個別小姓如唐、葉、朱等人口很少,往往只有幾個人或者十餘人。一般大姓者曾建有宗祠,“文革”時被拆,現在已見不到舊的祠堂。現在能見到的只是寶山樑氏在原址上重建的梁氏宗祠,其亦是剛建起而尚未裝修完畢。其他大姓有的有準備重修宗祠的計畫,有的則對此並無任何準備。一般而言是經濟上的原因,使他們尚無力顧及此事。
部分“講標人”過去亦曾編有族譜,現今均已散失,原因是解放前當地有個土匪頭子,常搶掠燒殺,特別把各姓氏(村落)的炮樓視為眼中釘,常在夜間偷襲炮樓並以火焚之。而各姓的族譜一般是存放在炮樓之上的,故難以倖免。極個別倖存下來的族譜,到“四清”和“文革”時也逃不過厄運,被毀於一炬。這樣,今天人們就無法把自己歷代的來龍去脈及諸先祖的情況講清楚。不過,與重修宗祠行動相一致的是,人們正設法重修族譜。
封開“講標人”的經濟以農業為主,種植水稻、薯類、豆類、玉米等以及經濟作物瓜菜、蓮藕之類,產量較高,但因價格偏低,效益不好。養殖業為養豬、牛、雞、鴨、魚、狗等等。在村寨里房前屋後種有龍眼、黃皮、芭蕉等果樹。由於東部山地(即黨山西麓)多石,居於長安行政村、東山行政村的“講標人”只獲得少量旱地,寶山行政村的情況好些,那裡有些小丘陵山坡地可資利用。總體而言,“講標人”的經濟仍然屬於傳統的農業經濟,商品農業經濟的成分較少,同時在當地從事工商服務業的“講標人”亦很有限。因為外來人口少,封開北部一帶工商業不發達,內需不足,甚至連蔬菜、普通肉類等基本生活品的銷售量都極為有限,所以當地“講標人”在傳統農業之外較難獲得收益。
但是封開“講標人”又並非過著一種傳統式的農民生活,事實上他們難以享受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共享天倫的田園生活。這些年來,外面的世界把年輕的男男女女吸引去了,留在村落內的以老人、中年婦女、小孩為主,農忙季節才能看到幾個回家幫乾農活的青壯年,但即使是農忙季節,田野中幹活的人仍然以婦女、中小學生為主。這就充分說明“講標人”社會已受到外部世界的強烈衝擊。再看看村寨內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水泥鋼筋樓房,可以看出現代化正在影響著“講標人”和他們的社會文化。
封開“講標人”中的文化交融現象 封開“講標人”的人口來自於百越民族及部分南遷華夏族,正是各民族間的相互混血以及文化交往、文化交融、文化認同,形成了今天的“講標人”。因此,在“講標人”社會中,我們可以發現其文化具有明顯的文化交融特點。“講標人”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在“講標人”社會中,文化交融現象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1.“標語”本身是各種語言相互融匯的結果 語言學研究表明,“標話”辭彙中約有一半左右是借用漢語粵方言的,這表明“標語”與漢語之間的聯繫。另據研究,“標語”的基本辭彙,與漢語比較有差距,而在語法上也有與漢語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如修飾詞放在中心詞的後面,如“眼淚”說成“水眼”、“青草”說成“草青”、“糯米”說成“米糯”。這說明“標話”既有漢語成分,又有非漢語成分。因此,可以證明,“標話”是各種語言相互交往而產生的結果,是文化交融的結果之一。
2. “講標人”的宗族組織及其活動體現出文化交融的特點
封開“講標人”的宗族組織,有兩個主要的表現特徵:
第一個是,堅持漢族傳統宗族制度的基本規則,這主要表現在重視血緣關係方面。“講標人”同姓不婚,但若是同姓而不同屬於一個宗族則可以通婚,也可以與非“講標人”中的同姓結婚。這表示其主要是從血緣上來考慮婚配對象的。另外,他們排斥無共同血緣關係者,如對拖油瓶仔,允許其隨姓,允許其在本姓族範圍內耕種土地,但不允許其成年後(18歲之後)仍居住在本姓村寨內或在村寨內建房子,而必須在村寨外面另闢地自立門戶。自然,拖油瓶仔及其後代子孫是不允許參拜本姓宗祠的。
此外,若是異姓養子,雖曾隨姓,同樣愛到輕視甚至欺負,被限制從事某種活動(如在村寨內建房子,祭拜宗祠等),因而養子在娶妻成家並人丁增多時,他和他的子孫都會考慮歸宗問題,即回到與自己同一血緣關係的宗族。事實上後者亦是非常歡迎這部分子弟回歸的。因而在“講標人”這裡,常會出現某個姓氏的某個宗支集體改姓的事,而且又常伴隨搬遷或另闢村落。比如原來更樓有部分盧姓人口,集體性地搬遷到今長群村地建屋成村,並成功恢復為林姓,即其同一血緣祖先的姓氏。這是因為這部分人口原來的祖先來自墰寺林姓,被一盧姓夫妻收為養子並隨父姓盧,但其後代總被盧氏排斥,故只好找機會脫離盧氏另闢新村,這件事說明了“講標人”是多么重視血緣關係。然而,另有一件事又說明了“講標人”雖重視同一血緣關係,但對已改為他姓的有同一血緣關係的人,不管出自何種原因,亦不準其參拜宗祠,修建宗祠時亦不接受其捐助。這又反映“講標人”還講究血緣之外的姓氏這種外在符號的象徵意義。比如歷史上羅柴有一個梁姓男孩,父母雙亡後跟羅境的姑父母長大,並隨姑父姓陳,其後代至今約有幾十人,在羅境寨外闢地自立成村。因其始終不改換姓氏為梁,而被羅柴的同血緣關係者視為異類,自然無法參拜梁氏宗祠。而同時他們又被羅境陳氏視為異類,被稱為“假陳”、“野陳”,亦不準參加陳姓的祭祖活動。因而這部分真正的梁氏後代的陳姓人左右為難,哪兒都不是人。為此他們曾求助於具有同一血緣關係的羅柴梁氏,回答是:“只要改為梁姓便可以重入宗祠,參拜祖先”。羅境村中這部分“假陳真梁”人口的遭遇,最明顯地說明了封開“講標人”既重視同一血緣關係,又講究姓氏這種外在符號的象徵意義。
第二個表現特徵是,堅持南方民族重視地域關係的傳統。我們知道漢族自周代起建立宗法制度,重視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但南方族群普遍較重視地域關係,他們常組成一種相對穩固的地域性聯盟,共同對外。在封開“講標人”這裡,現在能判斷出來具有區域性社會組織意義的是“蘇李祠”所屬範圍和“七聖廟” 所屬範圍。“蘇李祠”雖已被拆除,但其是東山行政村蘇氏和李氏合建的聯族祠,今天仍為人們所知所述。“七聖廟”在“文革”中亦被拆除,這個廟由原居於長安行政村的仇、褥、盧、袁、鐘、賓、黃等姓氏合議合資興建,其祭祀活動範圍僅限於七姓所居住的區域,實際上“七聖廟”這個名稱就是因七姓所建而得,後取粵語“姓”、“聖”同音而定為“七聖廟”。
根據1986年民族學者對懷集縣“標語”集團社會文化的調查,當地“講標人”除有自己族姓的宗祠外,各村寨還有數姓、十多姓甚至二十多姓的聯合祠,以緬懷初到當地的各姓祖先的功勳,這些祖先實際上已上升到神的地位。比如永固鎮的“祝公祠”、詩洞鎮的“九龍廟”、橋頭鎮的“都督廟”等等。這種情況說明,懷集“講標人”文化與封開“講標人”文化一樣,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結果。
3.宗教信仰上表現出來的文化交融特點
封開“講標人”的宗教信仰,從形態上講,有道教、佛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信仰等,這與廣東省內許多地方漢族社會極相似。但是在具體的神的稱呼、神位的安置、神祗分類、神能的認識等方面,也表現其各種文化交融的特徵。
首先,“講標人”供奉灶君,但俗稱其為“灶君太”認為所胃“灶君”是一對夫妻神。同時,“講標人”將供奉的床頭婆稱為“床頭公”賦予其雄性的特徵。
其次,神位的安置上不統一。比如“門口土地財神”神位安置在大門左邊牆壁離地約一米半高的地方。在其傳統住房(俗稱“大屋”)的門樓里,在大門口的左邊牆壁上一米半高位置上供奉的又是“門官神位”,這種多樣性,在封開北部一帶較普遍地存在,反映當地及“講標人”在神位安置方面所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傳統。“講標人”家中的正廳,並不供立神位,而只是掛著“畫符”,是新居落成時由施公貼上去的。與“畫符”同時貼上去的還有司命天官、天皇、歷代宗親、福神、天仙、諸星宿、太陽斗母等的神位,均以紅紙條寫上神名然後貼上上去。這些神靈是被人們請來保佑家門、驅魔降邪的。“講標人”供奉祖先神位一般是在“廳房”(“大屋”的最中心部分),此外其他房子不設祖先神位。
第三,“講標人”還將道佛糅合在一起進行拜祭。如“講標人”參與祭祀活動的梅花自然村的福瀾寺,拜祭的是觀音和北帝,兩神並列在一起。“講標人”認為兩神並列一起並無不妥,都可庇佑鄉親信眾,滿足有心人。另外他們建這個福瀾寺,又是為鎮住梅花河深水潭的邪魔。所以從形式來看,或者從神能來看,“講標人”以及當地講開建話的人都是在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過程中,加進了地方族群的某些文化特質。
第四,“講標人”對鬼神不分,往往連在一起講述,觀念中很少區分鬼和神,更無將鬼和神以善惡分類。他們只是有社神、祖先神、廟神的區分。這說明他們保持的是一種古代越族的宗教觀念。
4.節日活動中體現出來的文化交融
封開“講標人”的節日比較多,基本上是中華傳統農曆的節日,如春節、清明、端午、六月六、七月七、七月十四、八月十五等。但在具體的節日過法上,具有明顯的地方族群的特色。如春節,有“吃初三”的(正月初三日開年,此日最為隆重,出嫁女亦在這天回娘家,以寶山樑氏及東山蘇、李姓為代表),有“吃初六”的(分布在長安行政村“七聖廟”所涉範圍,因“七聖廟”廟誕生紀念日在正月初六),這與其周圍“講開建話”的人在正月初二日開年有明顯不同。又如端午節,過的是初一而非初五。還有如中秋節,連過兩天,即八月十五、十六為節,十五日全家聚餐,要吃魚,十六日為出嫁女回娘家日。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節日文化的形式被“講標人”所堅守,但具體活動內容又具有地方族群的文化特點,這是“講標人”中文化交融的又一個主要表現。
5.其他方面表現出來的文化交融的特點。比如,“講標人”的傳統房子是一種大屋,結構上又分為“正屋”(有一進、三進及五進的)和至少四列附屋(俗稱為“屋仔”,分列在正屋的兩邊)。在兄弟分家之時,按傳統的“左大右小”的原則分配住房,同時又要貫徹“里大外小”的原則。如一個家庭有五個兄弟,剛好建有三進的大屋一座,到分家時,大哥一家可分到“正屋”的最內進的左廂房,二哥一家可分到“正屋”最內進的右廂房,老三一家可分到“正屋”中進的左廂房,四弟一家可分到“正屋”中進的右廂房,老五一家可以分到“正屋”最外進的左廂房,餘下的廂房留給其他家庭成員。“屋仔”的分配與“正屋”的分配一致。這種分家時分割房產的做法,並非完全與中華文化傳統的“左大右小”、“前尊后卑”的作法相同,而是糅合了傳統文化與地方族群文化,是文化交融的結果。
“講標人”一生的名字至少有兩個,一為乳名,二為書名(讀書時使用),三為婚名(結婚時使用的名字,平時不用)。書名與婚名的取法最為傳統、複雜,要通過算卦的看本人命運中欠五行中的哪一行,並依此而取名字,命中缺少哪一行,名字中便要帶這行的字,如認為命中缺水,便取個水字旁的名字,像“洋”、“淼”、“河”、“湖”、“江”等等。這種命名方法反映其有依照傳統五行學說取名字的習慣。但是“講標人”合名中的“排輩”方式,又明顯具有地方族群的特點。比如宗族內沒有統一的字派,都是各個分支內部臨時商定某一代子孫使用哪個字為派輩。同時這個代表輩分高低的字派,是安排在名字中的第二個字還是名字中的第三個字,亦是內部臨時商定,從來就沒有統一過的時候。以盧氏為例,現今健在的男丁分別屬於第18代至第24代,但在第20代前(包括第20代)各個房的排輩是不統一的,只有自第21代起才統一起來,這也就是近十餘年的事。如水澇盧氏,能夠記憶起的祖先的輩分字派自第13代起,為茂、永、際、乾、樹、祥、丕、其、品、相、興、才,而同宗的上宅盧氏自第13代起的字派是居、恩、中、蟾、昌、秉、富、賜、品、相、興、才。同樣不統一的是字派作名字時的用法,水澇盧氏的第13代至第17代及19代至第21代,把輩分字派放在名字的中間,如盧其謙,屬“其”字輩,字派放在名字中第二個字,但第18代“祥”和第25代“才”,做名字的最後一字,如盧天祥,屬“祥”字輩,字派放在名字中第三個字。在這中間,無規律可尋,這是因為是由其宗支內部臨時商定的。
四、“講標人”文化交融的人類學分析
封開“講標人”中的文化交融現象形成有各方面的原因,而這種文化交融最後促成了“講標人”群體及其文化,並對“講標人”的族群認同產生了重要的作用。今天,在外部世界的影響下以及內部各方面因素髮生變化的情況下,“講標人”社會文化變遷亦顯著地表現出來。以下我們將對“講標人”中的文化交融形成的原因、這種文化交融對“講標人”族群認同的意義以及“講標人”的文化變遷進行人類學的分析。
1. “講標人”中文化交融形成的原因
從歷史上看,早在秦漢軍民鑿靈渠經漓、桂、賀等江河南下抵西江流域進行拓殖,並最終開發南海、番禺之前,包括封開縣在內的廣大西江流域諸地區就是百越諸部聚居地。考古學上的發現早就證明了這一點。近二十年來在封開各地發現二三十處青銅文化遺址,普遍出土的的都是越式青銅器,考古學上有“不見中原文化或嶺北楚文化因素,更多地具有南方越文化的特徵”之觀點。秦漢以後南下華夏部落越來越多,華夏-百越雜居、交往。“講標人”中的文化交融,就是在這種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
封開“講標人”中文化交融形成的第二個原因是華夏-百越部落間的通婚,這也是“講標人”形成的必要條件之一,正是因為通婚並伴隨著文化相互采借,使得“標話”得以形成。通婚也反映出當時各地民族間文化價值的相互承認。今天我們在封開長安鎮還能看到族群間相互承認文化價值的現象,如過春節,寶山樑氏是“食初三”,“七聖廟”所涉範圍是“食初六”,而該鎮北部講開建話的人們則“食初二”,這種不同時間過春節的習慣,並不對親戚間的往來造成什麼不便,如出嫁女在丈夫家中不過年時也完全可以回娘家過節。
2.文化交融對“講標人”族群認同的意義
“標話”是文化交融的結果,“講標人”文化亦是文化交融的結果。從人類學來看,文化交融對“講標人”的族群認同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作為文化交融結果之一的“標話”,是“講標人”認同的最重要示志,也是區別於其他族群的標準之一。、
其次,社會文化以及共同文化心理素質的形成,也得益於歷史上的各族文化交融,在“講標人”集體性提出族別識別要求這一點上,體現出經過長期歷史發展與文化交融,他們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
再次,長時期的文化交融,使“講標人”學會了對其他族群文化持開放和包容態度,他們認為在自己社會中的所有文化現象,無不是其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他們並不有意地把自己的文化區分為“是誰的”或者“不是誰的”,“是來自這裡的”或者“是來自那裡的”,他們認同自己社會中的所有文化現象。能夠對文化持這樣一種態度,說明文化交融對這一個群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最後,文化交融是“講標人”地方文化創造的主要方式,而在其地方文化創造過程中,作為大文化傳統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滲透是從不間斷的,並由此使“講標人”認同大傳統文化,使其小文化不斷向大傳統文化靠攏。
3.封開“講標人”的文化變遷
像大多數族群一樣,封開“講標人”的文化亦正在發生變遷,這種文化變遷實際就是一種文化交融,根據研究,“講標人”文化變遷的原因有外部社會的影響、周圍社會與生態環境的變遷、當地政府工作、學校教育、文化活動的宣傳以及來自內部人民的選擇,等等。
“講標人”文化變遷的最主要表現仍然發生在“標話”上。在長安“講標人”群體中,已有若干個村落的人已不講“標話”了,這些人已明確無誤地被“講標人”歸為“不講標”之列,如上述的下羅柴、羅待、樓下、下墰寺等村寨。
對這些村寨放棄“標話”而轉講開建話的原因,當地流傳著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某個祖先娶了個講開建話的媳婦,她不會講標話,於是做丈夫的只好遷就她而在家中講開建話,而他們的孩子因為多數跟著母親活動更是只講開建話,這樣子過了幾代後這個房派的人便不講標話,並被當地視為“不講標”的人。這種說法以下羅柴為代表。
第二種說法是,附近講開建話的人人多勢眾,迫使“講標人”跟著講開建話,到最後終於放棄自己的語言。如羅待褥氏就是迫於附近早已不講“標話”而又人多勢大的梅花村人的壓力而最終放棄“標話”的。
第三種說法帶有傳奇色彩或偶然性,這以樓下林姓放棄“標話”為代表。據說過去樓下村出了個武官,有晚帶兵回家省親,先行兵丁到了樓下村的門樓叫“開門”,寨內守夜人聽說是當了大官的子弟的部下,很高興地大聲吩咐“快來開門”,但因為標話把“開門”說成k o i33t o 33,類似於“開刀”,兵丁聽了以為寨內人要開刀殺自己,於是先下手為強,寨門一開便蜂擁而入,見人就砍。待大官轎子到寨門,已有許多族人丟了性命。痛定思痛之後,村人決定改講開建話。
不管怎么說,封開“標話”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小,而講粵語開建話及封川話(該縣南部的一種粵語)的人越來越多。作為小語種的“標話”的命運似乎早就注定。從人類學角度看,保護小語種的意義類似於保護生物物種,但是,客觀因素以及人民最後的選擇才是最有決定意義的。“標話”的未來如何,我們不妨作不間斷的追蹤研究。
封開“講標人”文化變遷的其他表現是物質文化的快速變遷,這可以視為經濟、社會的一種發展。如衣食住行的變化,確實是向高質量生活方向邁進,這歸因於外界社會的影響、政府工作、學校教育、文化活動等等。同時區域內環境的變化,從另一角度看亦成為發展的一種動力,如當地水質變差,使人們不得不使用地下水,以及準備發展自來水事業等等。
“講標人”社會文化生活變遷亦比較大。過去人們單純生活在宗族組織及區域性組織(如“七聖廟”祭祀圈、長生會等)之中,現在則增加了鄉鎮政治組織、經濟合作單位、企業、醫院、學校等現代社會組織生活。加上在地方社會整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長安墟鎮已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墟鎮生活對當地“講標人”生活已有不小的影響。這種社會生活的變化,是“講標人”及其社會文化變遷的又一個主要方面。
“講標人”精神文化的變遷具有戲劇性。“文革”時破四舊,反迷信,但近十多年來,迷信活動死灰復燃,甚至到了連人們的生老病死、生產、社交,求學、外出均要舉行一些儀式。作為當地的巫婆(俗稱“迷仙婆”)和施公,“生意”興隆,算卦擇日看風水的收入大增。這種在人們精神文化方面發生的變遷,是與今天倡導的科學與人文精神相悖的。因此,在地方文化變遷過程中,繼續加強科學與人文思想的教育宣傳,乃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