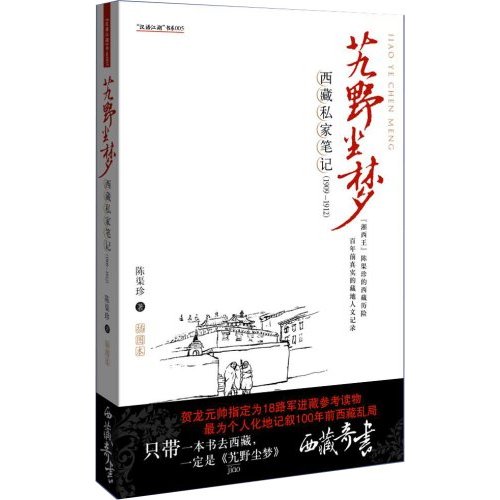《艽野塵夢》,作者取《詩·小雅·小明》“我征租西,至於艽野”之意為書名,含有青藏高原風塵錄的意思;書中詳細敘述了1909年從軍,奉命隨川軍進藏,參加工布、波宓 等戰役,在駐藏期間同當地藏族同胞、官員和喇嘛及藏族姑娘西原的種種故事及經歷;描繪了沿途所見山川景色、人情風俗和社會生活;同時記錄了英、俄帝國主義凱覦和爭奪我國神聖領土西藏的罪惡和陰謀活動,清政府的腐敗,清封疆大吏之間和軍隊內競爭奪權等。從文學的角度看,它不失為一部寫行優美的遊記;從史學的角度來看,它又不失為記錄清末民袂川邊、西藏情況的重要資料。
基本介紹
- 書名:西藏私家筆記:《艽野塵夢》
- 作者:陳渠珍
- ISBN:9787223011174
- 頁數:276 頁
- 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9年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編輯推薦,專業書評,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蒙塵已久的歷險奇書,一部刻骨銘心的愛情經典,一份清末民初西藏實況的珍貴史料。“湘西王”陳渠珍以其戎馬生涯和曠世才情,寫下的最為精才絕艷的回憶文字,誰讀過它,誰將終身銘記。此書寫於1936年,書中所記為作者1909-1912年進出西藏的生死經歷。所娶藏女西原萬里相隨,其堅貞情意催人淚下。今日讀書中所記百餘年前藏地風雲事件和人文習俗,良足使人生髮無限的遐想與感慨。如果說只帶一本書去西藏,這本被譽為“奇人、奇事、奇情、奇文”的《艽野塵夢》一定是首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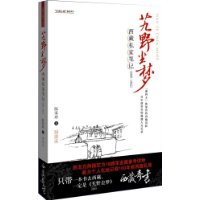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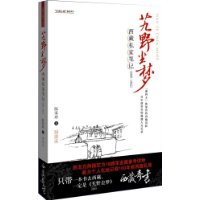
作者簡介
陳渠珍(1882—1952),人稱“湘西王”,是親歷清朝、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不同時代的“振奇之傑”,與熊希齡、沈從文並稱“鳳凰三傑”。1906年參加湖南新軍,後投靠清川邊大臣趙爾豐,入藏平叛。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跋涉萬里回到湘西。其後統一湘西,經營湘西數十年。期間,沈從文曾在其帳下擔任文書,賀龍亦是其舊交。1949年10月赴乾城同解放軍和人民政府進行政權交接。1950年6月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受到毛澤東的接見。1952年病逝於長沙。
媒體推薦
餘一夜讀之竟,寢已雞鳴,不覺其晏,但覺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實,實而復娓娓動人,一切為康藏諸遊記最。
——藏學家 任乃強
此書四十年前曾從陳氏後人借閱一次,為民國年間自印本,因其內容有趣,讀時即深深為之吸引,讀後又久久不能忘記,還不止一次在茶餘飯後當故事講過。
——出版人 鐘叔河
一部奇書,記述了上個世紀初發生在西藏的一個真實故事,非常的時代,非常的場景,非常的人物,非常的經歷,一部愛情經典。曾以手抄本、複印件和內部出版資料形式廣為傳布。誰讀過它,誰將終身銘記。
——作 家 中國藏學出版社總編 馬麗華
在我國的群籍中,死裡逃生於絕地者的追記,又足以驚心動魂的,以此書為第一。
——專欄家 三 七
--------------------------------------------------------------------------------
編輯推薦
沈從文曾是他的文書,而他的才氣毫不遜於沈從文
這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在未來的中國文學史上,一定會有它的地位。
這是一份極為寶貴的關於晚清軍政史的備忘錄。
這是一部精采絕倫的關於西藏民俗風情和青藏高原的人文地理考查報告。
1、 100年前原生態的西藏
“西藏”被稱為當今世界上的最後一塊神秘之地。而100年前的西藏是什麼樣子的呢?每個關注西藏的今天和明天的人,都會樂於了解西藏的過去。對西藏過去的漢語描述是非常罕見的,本書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2、 私家筆記
獨特的個人視角,充沛的個人情感,細膩生動的表達,近百年前一個傳奇人物在你耳邊的“私語”。它衝破了種種宏大敘事留給我們的陳詞濫調的印象,傳達了非常真切的個人感受。
3、 與西原的生死絕戀(愛情故事)
一個藏女對一個漢人不離不棄、生死相隨的故事。讀完本書,一定會記住這個名叫“西原”的女人。這種相濡以沫的感情在今天這樣一個充滿變動的時代更加顯得珍貴。
4、 絕地求生的經歷(歷險)
115人出發,最後僅剩11人生還。在無人區度過的200多天,其艱險程度不讀不足以想像。餓到極點,竟至爭食同伴的屍體。在最殘酷的環境下,對人性底線的拷問,觸目驚心。
5、 “湘西王”陳渠珍
傳奇人物,沈從文曾經的上司,賀龍曾經的上司和對手,湘西的一個傳奇,在這本書中留下了鮮活的面目。
6、 插畫加白話評註(美感與知識性)
這兩者都使書更好讀。插畫增加了書的美感,白話評註使書的知識含量擴充,某種意義上承擔西藏旅遊手冊的功能。
7、“漢語江湖”書系
“漢語江湖”書系已經積累了自己的品牌影響,它致力於在全球化的時代展示最精彩的漢語,收入最能體現漢語神韻的作品。本書納入這一書系,二者相得益彰。
--------------------------------------------------------------------------------
專業書評
鐘叔河:想讀《艽野塵夢》
我喜讀筆記,尤喜尋讀近人和今人的筆記,即使它沒有題名“筆記”,只要是自記自事(不是刻意創作),自說自話(不是奉命而作),便可視為今之《世說》《國史補》,文史價值雖未必能相比,也總能記錄下一些人們活動的真相,勝於空談遠矣。
近見蔣祖烜君文章中提到《艽野塵夢》,此乃民國時期“湘西王”陳渠珍寫的一冊筆記,記其於清朝覆亡前夕進出西藏的經過。“艽野”詞出《小雅》,《毛傳》釋為“遠荒之地”,正指西藏。“塵夢”的意境,則像是在說“往事並不如煙”(這是冰心《追憶吳雷川校長》文中的句子),頗含惜往傷逝的悲愴,因為有一位藏族女子,為了幫助作者逃出西藏,付出了她年輕的生命。
此書四十年前曾從陳氏後人借閱一次,為民國初年自印本,十分難得。因其內容有趣,如今還想再讀,不知蔣君所見是原本還是後來印的?
《艽野塵夢》用的雖是文言,記敘卻能委曲周到,描寫也很注意細節。有些精彩片段,讀時即深深為之吸引,讀後又久久不能忘記,還不止一次在茶餘飯後當故事講過。以下便來複述幾節,全憑記憶,難免出入,也有我故意添減之處,請讀者觀其大略可也。
宣統元年(1909)清軍進藏,陳氏時任某部三營管帶(營長)。過金沙江後,天氣奇冷,宿營的牛皮帳篷夜間凍得硬如鐵板。每日晨起,須先在帳中生火,烤一至二個時辰,待牛皮烤軟,才能拆卸捆載到氂牛背上,這就快到開午飯的時候了。因此部隊總要午後才能出發,只走得三四十里路,天色向晚,又要找宿營地支牛皮帳篷了。
在行軍中,軍官都有馬騎,卻不能一上路就騎馬,而要步行好幾里,待雙腳走得發熱,然後上馬。騎行數里後,腳趾便會發冷,而且越來越冷,決不能等到冷得發病的程度,即須下馬步行。如此走幾里,騎幾里,騎行的時間頂多一半,還得與步行士兵保持同樣的速度,故騎行的路程也頂多一半而已。
營中各隊(排),也為傷病士兵備有馬匹。隊里總有幾個愛耍小聰明愛占小便宜的兵,見馬少兵多,便搶先報告隊長請求騎馬。上馬以後,稍有經驗者知不能久坐,騎些時候就會下馬,沒經驗又貪心不足者,總怕馬被別人騎去,先是裝腳痛不下馬,結果腳真的凍痛凍僵,下不得馬了。營里最後被凍傷凍殘了的,便是各隊最先爭著騎馬的這幾個兵。
進駐拉薩以後,藏官笑臉相迎,還送了個年輕丫頭給陳管帶做小老婆(書中稱之為“藏姬”);但沒舒服幾天,到了辛亥年(1911),這種笑臉就變成凶神惡煞相,要殺漢人了。“藏姬”西林卻站到了男人這邊,幫助陳氏和護兵逃出了拉薩。這時由原路東歸已不可能,只好走藏北無人區,經過青海往西安。他們在無人區一度斷糧,陳氏雖有武器,對天上飛的老鷹、地下跑的羚羊卻毫無辦法,幸虧西林槍法極精,彈無虛發,才不至於餓死。
最後到了西安,那裡正流行麻疹,高寒山區無麻疹病毒,西林沒有病過,沒得免疫力,很快被傳染。別人卻以為成年人不會再“出麻子”,耽誤了治療,西林遂不幸病死,年僅一十九歲。陳氏對她還算有情義,將靈柩運回湘西,建了墓,還留下了這一冊《艽野塵夢》。
《艽野塵夢》中最精彩的故事,也是在無人區中發生的。某次行至有水草處準備安歇,遇上幾個去拉薩的喇嘛也來了,他們的馬多,食物也多,態度卻很友善,應允以一匹馱馬和若干食物相贈。護兵見喇嘛有油水,不知其帶刀槍,便想盡殺其人,盡奪其物,決定翌日整裝待發時動手,以為這樣對方不會防備,事後也無須收拾,最為妥當。陳氏雖以為不可,但寡難阻眾,只得聽之。
第二天一早,喇嘛送來了馱馬食物,還幫助他們將各人坐騎上原帶的物品轉移到馱馬身上,說是輕裝利於快走。整裝已畢,護兵就開了槍,擊傷一個喇嘛。誰知幾個喇嘛(連同傷者)反應極快,立即飛身上馬,並迅速從寬大的藏袍中出槍還擊,護兵應聲倒地,一死一傷,喇嘛們卻絕塵而去。更沒想到的是,剛送來的那匹馱馬也跟著跑去,不僅帶走了禮品,還帶走了他們原有的食物和用品。
食物沒了,護兵也沒了,報應如此之快,真令人驚駭。但作者根本來不及驚駭,因為在無人區中沒了食物,很快便會餓死,如無西林同行,結果就只能是黃沙中又多一堆白骨了。
這幾節故事,略可見清末民初“荒野”情況之一斑,也是邊疆史有價值的資料。
筆記作為一種私人記述,本可補正史之不足,筆墨若能生動傳神,則更有文學的趣味,這便是我喜讀筆記的原因。人們多以為筆記都是古人作品,是一種陳死的體裁,殊不知筆記大家黃秋岳、徐一士、劉禺生等都是近幾十年中人物,陳渠珍則一九五二年去世時還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委員,實在可稱為今人了。
書如今越印越多,古舊書被炒來炒去,能“發掘”的好像都發掘出來了。像《艽野塵夢》這樣原來無名的薄本小冊,因為是私人筆記私家印本,又無關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所以反多湮沒,甚至圖書館的目錄里也查不到。十多年前我箋釋印行過一冊《兒童雜事詩》,幾年前又整理印行過一冊《林屋山人送米圖卷子》,二書的性質,亦與我所說的筆記大略相近,因為孤陋寡聞,至今仍少見有繼續做這種拾遺輯佚事情的人,難道這類著述的命運總是寂寞的么?
藏地奇書《艽野塵夢》
文/ 三 七
曾讀《漢書·李陵傳》,自“陵止營浚稽山”,至“鼙鼓不鳴”,文不滿五百,而轉鬥千里的情狀,已宛然可以想念。李陵是個將軍啊,而自古牽騾負橐,為生計所驅,輾轉於無途之途者,十九為普通百姓,死於道者,又不知有幾百千萬,特無人作傳耳。絕域之通,我們在歷史書中唯讀到一片歡呼之聲,其間垂死的呻吟,枕藉的白骨,早掩沒在西陲的沙雪中;即使我今天所推薦的這一部《艽野塵夢》,作者對一百多名同行者道死的細節,也無詳述。但在我國的群籍中,死裡逃生於絕地者的追記,又足以驚心動魂的,以此書為第一,蓋死者無法開口,生者多不通文墨,所以眾多更慘烈的事實,只有與死者同化了。
《艽野塵夢》的作者陳渠珍後來也是大人物了,沈從文的讀者大概都知道他,所謂“湘西王”,割據一方逾二十年,但在故事開始的1909年,他尚是清軍中的一名管帶。駐藏辦事大臣聯豫與藏方不睦,調川軍入藏欲為挾制,至有達賴出走之事,這些是史家的事,也不去說它;不久武昌事變,駐藏清軍內亂,殺左參贊羅長裿,擁協統鐘穎為首,搶掠拉薩,至被藏兵圍攻繳械,而軍中仇怨糾葛,鐘穎被案誅,諸將仍復相攻,這是後來的事,也不去說它;只說陳渠珍當鼎革之際,懼禍之將至,率了一百一十五名湘西(及滇黔籍)子弟兵,集體地開了小差,於辛亥年十一月間從工布江達出發,北上青海,卻走入了無人的絕域,一行人餐風宿雪,日有死亡,待到第二年六月獲救時,只活下來七人。
中間的一段路線,為本書做注的任乃強先生精熟藏區史地,也不能確考,所繪圖形,終無法得其究竟。大致這一行人出那曲地區後,不久便西偏。他們雇了一名老喇嘛為嚮導,或為彼有意引入死地,也未可知。至通天河該喇嘛就逃掉了,此後更是盲人瞎馬,一腳沙一腳雪地亂走。時當冬季,北風觱發,酷寒可想而知;糧食盡則屠牲口,牲口盡則連行李也不能帶,自然凍餒更甚。中間種種細節,讀來慘怛,如火柴將盡之時:
“每發火時先取乾騾糞,搓揉成細末。再撕貼身衣上之布,捲成小條。八九人順風向,排列成兩行而立,相去一二尺,頭相交,衣相接,不使透風。一人居中,兢兢然括火柴,燃布條,然後開其當風一面,使微風吹入,以助火勢。布條著火後,置地上,覆以騾糞細未。……”
身處絕境,人的本性表露無遺。陳渠珍先既不能約束兵士,後於絕境中遇一小隊蒙古喇嘛,餉以酒食,許以贈糧,而人心無厭,兵士復密議襲殺之以奪其資糧,陳氏聞知其謀,惟空言勸諭而已。次晨兵士果暴起攻擊,交火後陳部死傷六人,喇嘛死三人,四人逃去,“行李財物,既隨駱駝飛去,即許贈糌粑二包亦口惠而實不至,至可痛心也”。陳雲“痛心”,我不得不說他們“活該”啊。
所可歌可泣者,陳渠珍駐德摩時納一藏族女子西原,陳氏原有妻子,娶西原未必非出於軍旅無聊之心,而西原之勇敢高尚,如暗夜之燈,一路之生死與共,亦足鍛造真情。獲救後過西安,西原染天花,一病而逝。陳氏既葬西原,“入室,覺伊不見。室冷幃空,天胡不弔,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長號,淚盡聲嘶也。余述至此,肝腸寸斷矣。余書亦從此輟筆矣”。
此書重慶出版社曾於1982年標點出版。我讀到的是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的版本,前有82年編者序,似乎是舊版的,但任乃強先生已於1989年去世,舊序中“八十六歲高齡的任乃強先生”云云,襲用之已不當,且失校的地方仍多,標點亦多可商,如再版,望能修正。讀此書後一月,即道經那曲一帶,曾動念往追這一行人的舊蹤,左望羌塘,沙天雪地,山巒連綿,衰草掩道,道邊禿鷲,凝立不動,遂栗縮而止。
艽野塵夢,非關愛情
文/聽夏
自來讀史,每遇中國近現代史總是略過。蓋除其中牽扯太多我所不喜之政軍經緯外,更嘆今日之修史人,其文筆往往差如政治課本,委實無法入眼。故YBY問我是否聽說過陳渠珍其人,只愧答不知。及至YBY又道:此人曾有個書童,叫沈從文……聞之不由心驚。
遂於網上搜尋,乃知陳渠珍亦出鳳凰,生於光緒年間,自少隨軍,曾入同盟會,後經國民革命、抗戰等役,功績卓然,名聲顯赫。因曾統治湘西一帶數十載,人稱“湘西王”。然其生平事跡雖不勝枚舉,惟後世褒貶不一。小女子自問不通典史,亦不敢妄下斷言,只得在此就書論書罷。
《艽野塵夢》一書,所敘乃是宣統元年,陳渠珍奉趙爾豐命,隨川軍鐘穎部進藏,復娶藏女西原。歷經工布、波密等役,至武昌起義後,陳因兵變率百餘部出逃。後取道青海,渡哈喇烏蘇河,入絳通沙漠,過通天河,經柴達木盆淖地……歷經七月茹毛飲血之生活,僅七人生還於西安。
而西原萬里從君,竟終以病卒。
陳率餘部抵蘭州時乃1912年,此書卻著於1936年其賦閒之機。時隔24年的追憶,讀來仍激盪人心,宛在目前。為此書做注的藏學專家任乃強先生在弁言中謂:“餘一夜讀之竟。寢已雞鳴,不覺其晏,但覺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實,實而復娓娓動人,一切為康藏諸遊記最。尤以工布波密及絳通沙漠苦征力戰之事實,為西陲難得史料。比之《魯濱孫飄流記》則真切無虛;較以張騫班超等傳,則翔實有致。”實非虛言。我亦因其感慨,或真需得如此歲月沉澱後,對過往人事之記憶,方能如大浪淘沙般,水落而石出。哪怕細節湮沒,情理則昭然。而那些歷時尚新的回憶,怕總是難逃身在此山中的障霧不明之處,無法見得真切了。
只是在網上所搜到不多的幾篇關於此書的感想,竟皆大費筆墨讚嘆陳渠珍與西原之愛情,委實令我難以苟同。陳渠珍後日能成為一代軍閥,叱吒風雲,料非專注兒女心事的多情種子。
且陳入藏前已有妻子,書中描寫他初見西原時,亦只是贊其騎術精湛。“中一女子,年約十五六,貌雖中姿,而矯健敏捷,連拔五竿……”,後於席間初聞第巴提親之語,亦當笑言。及曉其真,也只是“知不可拒,笑應之”。
雖成親當日見西原,有“靚衣明眸,別饒風致。余亦甚愛之”之語,想來不過洞房花燭夜之平常歡喜,殊非愛情。至於為何最後西原離世時,陳竟會“撫屍號哭,幾經皆絕”,後又有“入室,覺伊不見。室冷幃空,天胡不弔,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長號,淚盡聲嘶也。余述至此,肝腸寸斷矣。余書亦從此輟筆矣。”其所為者,在我看來絕非男女之情,而在恩義二字。
復觀《艽野塵夢》,蓋以紀實之筆娓娓道來,雖只萬餘字,細品下卻時有字字珠璣之嘆。且其中所描繪之藏地風土人情,遠比我所讀過當代關於西藏的太多文字都更生動優美,引人入勝。隨便摘錄如下:自成都四日而至雅州,風景與內地同,自是以後,氣象迎殊,山嶺陡峻,鳥道羊腸,險同劍閣,而荒過之。沿途居民寥寥。師行於七月,時方盛暑。身著單服,猶汗流不止。過雅州,則涼似深秋,均著袷衣。愈西愈冷,須著西藏毪子衣矣。過大相、飛越諸嶺,皆重峰疊嶂,高峻極天,俯視白雲,盤旋足下。大相嶺,相傳為諸葛武侯所開鑿,故名。經虎耳崖陡壁懸崖,危坡一線;俯視河水如帶,清碧異常,波濤洶湧,駭目驚心。道寬不及三尺,壁如刀削。余所乘馬,購自成都,良驥也,至是遍身汗流,鞭策不進。蓋內地之馬,至此亦不堪矣。行六日軍瀘定橋,為入藏必經之道,即大渡河下流也。夾岸居民六七百戶,河寬七十餘丈,下臨洪流,其深百丈,奔騰澎湃,聲震山谷。以指粗鐵鏈七根,凌空架設,上覆薄板,人行其上,鹹惴惴焉有戒心。
很難想像陳渠珍行伍出身,筆下卻能如此行雲流水,而其所描繪意象之宏大高遠,同當代眾多遊記相比,二者境界高下立判。
據說沈從文當年在陳幕下任文書時,也曾感慨其“令人嘆服的治軍能力以及長官的自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深夜還不睡覺,年近40也不討姨太太,平時極好讀書,以曾國藩、王守仁自許,看書與治事時間幾乎各占一半。”而其後沈之所以走上文學道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這位文武雙全的長官影響。
讀罷《艽野塵夢》,對陳渠珍其人興趣日盛,又忍不住想要把沈從文相關傳記也找來再研究一遍……
昨天小浪告訴我圖書館的考試要推到7月,不禁又開始蠢蠢欲動,計畫月底出行……
或者,就再去一次湘西,找片安靜的所在,每日散散步讀讀書吧。
讀《艽野塵夢》
文 / 馬普爾
我總覺得,西原的死,是她自己選擇的。
一個藏族女子,16歲時在叔叔家裡見到了一個漢人軍官,為他表演馬上拔竿,一見鐘情。在陳的記憶里,是西原的叔叔為了結交他,將西原送嫁而來。可我總覺得,是西原選了他,為什麼選他?也許是覺得他帥,也許是因為他有權勢,但我更願意相信,她希望這個人帶他離開。她幻想他會給她帶來另一種生活,他滿足了她對英雄的幻想,更多的是對新生活和新天地的幻想。
她跟了這個漢人,卻不料情勢突變,武昌起義發生了,清軍內部突變,陳渠珍率部下東歸,卻不料誤入絳通草原。在書中,那是最驚心動魄的一章,草原茫無邊際,一支人馬迷失其中,數日無糧,一人餓死,還未及被狼吞噬,已被同伴分食。幸得西原有雪域野外生存能力,捕獵野獸,安撫軍心,始終扶佑陳渠珍,歷盡艱苦路途。陳對西原最讚賞的地方,是在這段日子中,她勇敢地出去為大隊覓食,並對他說,沒有她可以,但沒有他不行。
七個月後,這支小分隊最終離開草原時,入草原時的100餘人,僅剩7 人。到達西安後,西原卻染上天花離世,那段寫得百轉千回,催人淚下:
每外出,西原必送出扁門,坐守之。餘一日歸稍遲,西原啟門,余見其面赤色,驚問之。對曰:“自君去後,即周身發熱,頭痛不止。又恐君即歸,故坐此守候也。”是夜,西原臥床不起,次日,又不食。問所嗜。對以:“頗思牛奶。”余入市購鮮牛奶歸,與之飲,亦略吸而罷,不肯再飲。余急延醫診治,醫生曰:“此陰寒內伏,宜清解之。”一劑未終,周身忽現天花。余大駭。襄昔在成都,即聞番女居內地,無不發痘死,百無一生者,乃走詢醫生。醫生曰:“此不足慮。”另主一方,余終疑之。從此藥餌無效,病日加劇,一日早醒,泣告余曰:“吾命不久矣。”余驚問故。對曰:“昨晚夢至家中,老母食我以杯糖,飲我以白嗆,番俗,夢此必死。”言已復泣。余多方慰之,終不釋。是晚,天花忽陷,現黑色。余知不可救,暗中飲泣而已。至夜,漏四下,西原忽呼余醒,硬咽言曰:“萬里從君,相期終始,不圖病入膏肓,中道永訣。然君幸獲濟,我死亦瞑目矣。今家書旦晚可至,願君歸途珍重。”言訖,長吁者再,遂一瞑不視。時冬月OO日也。余撫屍號哭,幾經皆絕。強起,檢視囊中,僅存票錢一千五百文矣,陳屍榻上,何以為殮,不猶傷心大哭,繼念窮途如此,典賣已空,草草裝殮,費亦不少。此間熟識者,惟董禹麓君頗慷慨。姑往告之。時東方漸白,即開門出,見天猶未曉。念此去殊孟浪,又轉身回。見西原瞑然長睡,痛徹肺腑。又大哭。
一切都將好轉時,陪自己走過最艱難的日子的那個人,卻死了;最心愛的女人和親人死了,身邊卻無錢送葬,這足以讓人感到命運的強大和自身的無力。萬念俱灰亦不過如此。
只是對於西原來說,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也許就是在絳通草原上的日子,和在西安每日等他回來的時光,他不再是有權勢的軍官,只是她的男人,要全心依賴她,被她保護,同時也全心保護她的男人。他完全是她的,她也完全是他的。
如果西原不死,情形又會如何?在內地,她不過是個番女,即使那段情份讓她做穩正室的位子,但記憶總會被沖淡,她要適應漢地的他,必然要經過痛苦的改變;而他要讓他周邊的人接受一個番女,費的力氣也不會少。
陳渠珍後來重入軍旅,成為湘西最有勢力的軍閥。年輕時的沈從文曾投身他門下,在沈從文眼中,這位大帥與眾不同,不愛喝酒賭博、縱性殺人,卻愛讀書。不愛女色,四十餘歲仍孤身一人,從不納小,倘若西原不死,不知道陳還會不會不納小。西原死了,正好變成他心中一段傳奇,像度母一樣,和他的青春歲月一起,永遠供他追念懷想。
一個軍閥與一個藏女的愛情故事
文 / 阿細
這樣的一個下午,泡上一杯菊花茶,和我一起來聽聽這個老的故事吧。
遇到他那年,她十五六歲,明眸皓齒、艷若桃李。那天,與往日並不甚不同。天高、雲淡,草原上遍是野花的清香,少女們長長的氈裙如斑斕的蝴蝶在風中翩翩起舞。
那天,她和一群天真爛漫的藏族少女一起為客人表演馬上拔竿。鞭策疾馳、裙袂飄飛,在馬經過立竿的時候俯身,輕盈敏捷的身姿讓眾人大聲叫好,她一氣拉拔五竿,精湛的馬術讓他瞠目結舌,更讓他驚呆的是她燦爛的笑臉。遠遠地,她望著他笑,身上的銀飾在陽光下明亮著她的笑容。瞬間,這個叫西原的藏族女子便深深嵌入了他的靈魂,至此一輩子也不曾離開過。
遇到她那年,他二十餘歲,英武挺拔,是清朝駐藏的一名管帶。受邀去貢覺的營官加瓜彭錯府上飲酒。那天,與往日並不甚不同。依舊是好喝的青稞酒,依舊有大方的藏族少女在草地上跳著鍋莊舞。遠處有人在表演騎術,塵揚草飛、喝聲不斷。初以為是壯漢所為,等馬立身前才知是一群美麗的少女。他詫異地凝望著那個連拔五竿的少女,憨直的模樣讓她忍俊不禁,從沒有男子以這樣的神態打量她。那一刻,少女的心在撲撲地亂跳著。而彼時,她並不知自己的命運已經和這個叫陳渠珍的漢族軍人緊緊系在一起,一直到她生命的終結。
他迎娶了她。
他率兵進攻波密,她騎馬隨征,戰場救他性命。武昌起義後,援藏清軍譁變,他寫紙條與她,期望和他一起東歸,並相約在德摩山下相見。這一次,他經歷了生命中最漫長最痛苦的等待。高原悲鳴的寒風中,她如約而至,金子一樣的笑容照亮著他,溫暖著他。他率領官兵百餘人逃出,她亦跟在其後,懷裡揣的是母親在她臨行前留給她作紀念的珊瑚,而臉上是尚未擦乾的淚痕。寒風中,他們策馬狂奔,髮辮在風中散亂飛舞,如幾近暗涌的命運。
被嚮導喇叭誤導入草原。人馬在一天一天地減少,浩瀚的大漠讓人絕望,更加殘酷地是食糧殫盡,昨日凍死的兄弟,成為今日烹煮的口糧。而她的身體也日漸虛弱,臉色蒼白如枯萎的野花。但她依然愛笑,她的笑,是寒夜中淡亮的火光,微弱,但給他以希望。懷中,藏著一小片乾肉,是她為他節省的。她說自己耐得住餓,而他要指揮隊伍,不可一日不食。況且,她萬里從君,他若無,她還能活下去么?
他的士兵心性大變,欲殺她帶來的藏族少年取食,被她堅毅冷酷地阻擋。俯身拿槍,他亦尾隨,天明時分,獵來野狼拋於雪上。
七個月後,他們抵達丹噶爾廳,始前的百餘人只剩下7個。尋客棧住下,攬銅鏡自照,她號啕大哭,聲音極其慘烈悲鳴,曾經明艷如花的她,已凌裂為慘不忍睹的模樣。
在西安。他們借居於友人的空宅中,一面寫信要家裡匯錢以便回湘西一邊快樂相伴居家過日。生活雖拮据但安定,而這也該是他一生中關於她的最後的一點美好回憶。她穿上了漢族女子的衣服,神情羞澀安詳。他每日出門謀事,她送他至偏門,然後在家中靜靜等待。如同沱江邊吊角樓上臨江遠眺的婦人,期待著男人的歸來。
變賣了隨身攜帶的一切貴重物品,包括她的珊瑚和他作戰用的望遠鏡,而因戰事原因匯款一直未見蹤影。一日夜歸,見她面頰通紅。問,原來他走之後,她便開始渾身發熱,頭痛難忍。她一連燒了幾日,大病,臥床不起。請醫生來看,誤診為寒毒。旅途勞頓加上從小在 潔淨高原長大的她,剛吃了一服藥就現出了天花。
命運是個巨大的圓圈,他們茫然站立其中,不知所措。
終於一天,她眶中噙著淚對他說自己夢見母親餵糖水給自己喝,按照西藏的風俗,夢見這一情景,必死無疑。夜裡,朦朧中他被喚醒,聽見她泣聲道:西原萬里從君,相期終始,不圖病入膏肓,中道永訣。然君幸獲濟,我死亦瞑目矣。今家書旦晚可至,願君歸途珍重。
說罷,瞑然長逝。
抱住她依舊溫熱的身體,巨大的悲痛讓他幾欲昏厥。萬里跟隨,一路相依為命,而他,連給她殮葬的錢都沒有。心如刀絞,號啕大哭。
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將她安葬在西安城外的雁塔寺。在墓前站到夜深,回到居處,室冷幃空,天胡不弔,淚盡聲嘶,禁不住又仰天長號。
書到此戛然而止。因為他“述至此,肝腸寸斷矣。余書亦從此輟筆矣。”
而時至今日,讀來猶可觸當時他肝腸寸斷的痛。
後他返湘,成為湘西最高統領,但從此不近女色。1952年,他逝於長沙。彼時,她已在雁塔寺外沉睡四十年。
--------------------------------------------------------------------------------
目錄
導言
總敘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第二章 臘左探險
第三章 昌都至江達
第四章 收復工布
第五章 進擊波密
第六章 退兵魯朗及反攻
第七章 波密兵變退江達
第八章 入青海
第九章 過通天河
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
第十一章 至柴達木
第十二章 丹噶爾廳至蘭州
附錄:
三七/陳渠珍的《艽野塵夢》
鐘叔河/想讀《艽野塵夢》
阿細/一個軍閥與一個藏女的愛情故事
……
--------------------------------------------------------------------------------
序言
《艽野塵夢》是民國時期的一部奇書。此書寫於1936年,書中所記為清末民初藏地之事,1940-1942年曾在《康導月刊》連載。著名藏學家任乃強先生讀後說:“但覺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實,實而復娓娓動人,一切為康藏諸遊記最。”
《艽野塵夢》的作者是民國一代“湘西王”陳渠珍。晚近中國,湘西鳳凰人才輩出,早年有出任中華民國內閣總理的熊希齡,後來又有作家沈從文、畫家黃永玉,中間就有這個“湘西王”陳渠珍。
陳渠珍(1882—1952),號玉鍪,祖籍湖南麻陽,後遷入鳳凰。16歲入沅水校經堂讀書,1906年畢業於湖南武備學堂,任職於湖南新軍。曾加入同盟會。次年秋,赴武昌投奔湖廣總督趙爾巽,被轉薦到成都川邊大臣趙爾豐處,任新軍六十五標隊官(相當於連長),駐防藏蜀要衝百丈驛。其時,俄國、英國勢力覬覦西藏,外患入侵,西藏局勢動盪不安。宣統元年(1909)7月,陳渠珍所屬部隊奉命援藏。陳渠珍因素有膽略被任命為援藏軍一標三營管帶(相當於營長),參加恩達、江達、工布等平叛戰役,後又遠征波密叛匪,屢建大功。駐藏期間,他同當地藏民、官員和喇嘛來往密切,還與藏族少女西原結婚。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訊息傳到西藏,進藏川軍中的哥老會組織積極回響,並殺死統帥羅長裿。亂軍欲擁戴陳渠珍為首領,而陳渠珍出於多方面的考慮,決定棄職東歸。他偕湖南同鄉士兵及親信共115人,取道青海回中原,途中誤入羌塘大草原,路途輾轉,斷糧數月,茹毛飲雪,僅剩7人生還於蘭州。陳渠珍遣散部眾,與藏女西原抵西安,其時家書未至,窮困不堪,僅賴救濟度日。不久,西原不幸染天花病逝。24年後,陳渠珍追憶這段經歷,寫成《艽野塵夢》一書。1950年陳渠珍受邀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擴大會議,謁見了毛澤東、周恩來,並與舊交賀龍元帥見面,還親手將其所著《艽野塵夢》一冊相贈。那時正好解放軍進藏,賀龍便將此書轉贈給十八軍首長以資參考。
陳渠珍自藏返湘時,已是民國二年(1913年),旋即出任湘西鎮守使署中校參謀。民國七年,陳渠珍任湘西鎮守使田應詔組織的護法軍第一路軍參謀長兼第一梯團長,旋代理第一路軍司令。由此開始其經營“湘西”三十多年的“湘西王”生涯。後成為著名作家的沈從文當時正在陳渠珍身邊當書記,他回憶陳渠珍:“平時極愛讀書,以曾國藩、王守仁自許,看書與治事時間幾乎各占一半。在他的軍部會議室里,放置了五個大楠木櫥櫃,櫃裡藏有百來幅自宋及明清繪畫,幾十件銅器古瓷,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叢刊》。”
期間,1935年春,陳渠珍的部隊被改編,而他以“湖南省政府委員”的空銜移住長沙,第一次結束了他在湘西的割據局面。這段空暇里,他寫成了《艽野塵夢》。作者曾交代說,赴藏之前曾經“搜求前人所著西藏遊記七種讀之……,由藏歸來,復購近人所著西藏政教及遊記八種讀之”,可見寫作之前做了充分的準備。
《艽野塵夢》一書,總敘之外,計有十二章,六萬餘字。作者原序有云:“追憶西藏青海經過事跡,費時兩月,著為《艽野塵夢》一書,取詩人‘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之意。”“我征徂西,至於艽野”出自《詩經·小雅》。艽(jiāo)有“荒遠”之意,還有一種植物叫“秦艽”,生長在海拔三千米之上的高原,此處,作者便是以“艽野”指代青藏高原。現在看來,《艽野塵夢》是一部精采絕倫的傳記小說,還是一份珍貴的清末民初軍政備忘錄,也是關於一百年前西藏風俗民情和青藏高原的人文地理考查報告。此書每章以地名為標題,記錄了從成都起程,至西安為止的這段遊歷,總計有成都、昌都、江達、工布、波密、魯朗、青海無人區、通天河、柴達木、丹噶爾廳、蘭州、西安等大的地名,幾乎每處都有山水風光和人文習俗的描述。書中記錄了英、俄等國覬覦下複雜的西藏局勢,清封疆大吏間和軍隊內部的勾心鬥角,記載了辛亥革命對西藏和川軍的重大影響。其描寫藏女西原,字字感人,描寫荒原求生,更是處處驚心。
《艽野塵夢》曾於1982年和1999年分別由重慶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過兩個版本,均收錄了任乃強先生為該書所做的校注。此次出版,編者對內文重新校訂排版,並參考任乃強先生的校注補充注釋,還請中央美院的王志興老師繪以插圖,以便於讀者理解。任乃強先生是此書最重要的發現者和推廣者,在此特向已經故去的任先生致敬。
一本書有自己的命運。我們深信,《艽野塵夢》將是一本傳世之作。希望編者菲薄的努力沒有玷污它的華彩。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