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於1928年考入
巴黎高等師範學院 從事哲學學習研究。在高師學習期間,她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和工團主義,對社會問題、勞苦工農以及受壓迫的底層人民苦難有著天生的感受。畢業後,她擔任幾所中學的哲學教師,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政治活動並重新反思馬克思主義和勞動壓迫苦難等問題。1934年後她開始從自己的親身經歷與感受出發來思考她的時代問題:貧困、不平等、弱者所受到的屈辱、專制權力與官僚制度對精神的摧殘。[1]為了對苦難有切實和真正的體驗,1934年她辭去了教職,親自到工廠中與工人一起從事重體力勞動。首先到艾士頓的五金廠工作,後來轉到布朗吉的一間工廠,最後轉到巴黎郊外的一家工廠,1936年她志願加入西班牙戰爭,到了巴塞隆納。後來因意外事件不得不退伍,轉而到一間葡萄園工作,在此期間,雖然她的健康一直不好,但他從未中斷從事重體力的苦工勞動。[2]早在1935年,她在葡萄牙的一個海邊小村莊中就曾經歷了精神上的洗禮,在一個夜晚,帶著她自稱“工廠生活在我身上留下了奴役性的永久烙印,正像古羅馬人在最卑賤的奴隸額頭上用燒紅的烙鐵打上的烙印一樣”這樣糟糕的心態和身體狀態,她獨自一人來到海邊,聽著漁夫的妻子兒女手持燭火圍繞著漁船列隊在唱古老的感恩歌曲,被亮得讓人愴然涕下。她心裡猛然體會到:“基督教實在是奴隸們最好的宗教,奴隸們不可能不信基督教,而我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3]但這並沒有標明她皈依基督教信仰,與基督相遇。因此我覺得有些學者把此次心靈的醒悟作為她信仰的開始是不對的。兩年之後,在亞西西的小教堂中,基督又一次召喚了她,“平生第一次感到有某種身不由己的東西迫使我跪倒在地。”但直到1938年,她參加了在索雷姆的修院中復活周所有的宗教禮儀活動,在整個活動中,她感受到了“純潔的歡樂”,同時“更好的理解在不幸中有可能熱愛神聖的愛”。終於在這次活動後“基督受難的思想自然而然的永遠在我腦中紮根”。[4]從此,薇依成為了一名獨特的基督的門徒。
西蒙娜·薇依 在薇依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後,她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她一邊實踐信仰,一邊進行積極的神學思考。從1938年到1943年去世前,她留下了頗為豐厚的著作,在此期間她對以往的勞動、戰鬥、政治參與、社會活動的經歷進行理論總結。在馬賽、在紐約、最後到倫敦,她寫了一本又一本的筆記。內容不僅涉及哲學、宗教、歷史、政治……同時她還寫信給她的神甫朋友貝蘭並與他一起討論和研究,這些信件和寫下的文章後來收集在了《在期待之中》一書中。當然,她的很多文章和心得在生前沒有發表。當她死後,她的作品很多被集結成集出版。如《
重負與神恩 》、《在期待之中》《關於愛上帝的雜談》等等,薇依的全集已經由伽利瑪出版社於1997年全部勘校出版。[5]
1942年6月,薇依離開了
納粹 德國占領下的法蘭西,去了美國,在那裡加入抵抗組織。當年11月,她又去了倫敦。在舒曼(M.Maurice Schumann)領導下的部門工作,她堅持要回到法國去執行任務。但考慮她的特殊身份和種族,她提出的要求無法滿足。她為了和法國人民同受苦難,堅持嚴格自律,只消耗在法國安配給票才能夠領到的很少的粗劣的食物。加上繁重的勞作,她本來就很軟弱的身體很快就垮了下來。1943年8月24日,她終於在英國阿斯福特療養院與世長辭,年僅34歲。
人物生平 1909年2月3日,西蒙娜·薇依出生在巴黎
斯特拉斯堡 街的一所住宅里,如今這幢房子已經拆除,它位於梅茲街上。
西蒙娜·薇依 她的哥哥
安德烈·韋伊 比她年長3歲,在他的幫助下,西蒙娜自幼就獲得了文學和科學方面的知識,6歲時,她就能背誦不少拉辛的詩句。第一次大戰使她的學業經常受挫,儘管如此,1924年6月,16歲時,她終於通過了文科中學畢業會考,成績是“良”。考試委員會主席是一位中世紀前期文學專家,他在口試時給了西蒙娜19分,滿分為20分.。
她在維克多?杜呂依中學學哲學,從師于勒·賽納以後,為進高等師範學校作準備,她在
亨利四世中學 學習兩年,從師
阿蘭 。
阿蘭 發現她有哲學天才,說在她身上具有“罕見的精神力量”,他十分善意地關注著她,但還指出她應當“避免作過於狹窄的用晦澀的語言表達的思考”,並說“她曾經想放棄那種抽象的、深奧莫測的繁瑣探求——這對她來說是一種遊戲,而進行直接的分析”。
她於1928年考入高師,1931年取得大拿和中學哲學教師學銜,隨即被任命為勒浦依市女子中學教師。1931年冬至1932年春,她在那裡明確表態反對政府的壓制政策,向市政府公開表示對該市失業者的同情並以實際行動援助他們。
她對《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社深懷友情,1932年可是同該雜誌合作。這本雜誌使她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述人間疾苦,表達她對勞動者處境的基本看法和感情。
1932年10月她被調到奧塞爾,1933年又調到羅昂。這時,她決定告假一年,以便全心全意地體驗工人生活,夏天在汝拉山區她在乾農活時就想作這種嘗試。
她在雷諾廠找到一份工作,在廠附近租了一間房。儘管她息有頭痛病,身體又虛弱,但她絕不允許自已的生活條件與車間工人有任何不同。
1935年,假期已告結束,她又重操舊業,在布爾日的女子中學任教,直到1936年夏離開那裡。同年8月初,她前往巴塞羅部.她要親自對“赤色分子”與“佛朗哥分子”之間的鬥爭作出判斷.在數周的時間裡,她在卡塔廬西亞前線同共和派軍隊一起飽受磨難,從內心深處感受到真正的戰爭災難。後來,她返回法國。
由於疾病,她再次告假。直至1937年她才去聖康坦女子中學赴任。1938年1月,由於健康狀況不佳,又不得不中斷教學,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40年6月13日,她決定離開巴黎,同年10月在馬賽暫居。
1941年6月,經女友介紹,她認識了Le. R. P貝蘭,當時貝蘭正在馬賽多明我會的修道院,兩年後貝蘭被
蓋世太保 逮捕。貝蘭又介紹她同G.梯蓬相識,她住在梯蓬家裡,在阿爾代什逗留了一段時間。這期間,她經不住農家田間生活的吸引,乾起了體力勞動,她幫助收莊稼或收穫葡萄,與此同時,她並未放棄希臘哲學或印度哲學的研究,擴展梵文知識,並進一步確定了研究神秘主義和上帝這個概念的傾向,這些研究促使她寫下有關天主經和愛上帝的論文,讀者在本書中可讀到這些文章。
她在冬天返回馬賽,繼續同貝蘭討論、研究,在貝蘭的要求下,她在馬賽多明我會修道院地下小教堂的聚會上闡述自己對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看法。
1942年3月,貝蘭被任命為蒙佩利耶修道院院長,他從不曾中斷同薇依的聯繫。他們之間的會面,通信和交流只是在薇依離法時才中斷。
1942年5月15日前後,她在旅途中寫信給貝蘭,她稱這封長信是她的“精神自傳”。輪船於5月17日啟程。她在卡薩布蘭卡逗留了三周,經法國去美國的旅客都滯留在臨時營地里,薇依在那裡修改文章並定稿她把這些文章作為精神遺產寄給貝蘭5月26日她又寫了最後一封告別信,對15日的信的內容進行補充和闡發。
1942年6月底,她抵達紐約法國臨時政府委任她一項任務,她於是在11月10日動身去英國。
她在倫敦負責研究條令;她起草計畫撰寫了一篇有關國家與個人的互相間權利和義務的備忘錄。她執意分擔仍生活在法國本土的人們所經受的磨難,以至拒絕醫生因她過度疲務而特別規定的食品供應,她嚴格地按照國內敵占區的同胞們的食物配給量領取食品。
她的健康狀況嚴重惡化,1943年4月下半月住進了倫敦彌德賽克醫院,8月中,又轉到康特群的阿斯福特療養院。
人們在她的筆記本中發現的最後幾個字是:“教學的最重要方面=對教會的認識(從科學意義上說)。”
薇依的整個一生都包含在這個詞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進阿斯福特療養院後不久,她就與世長辭了。
神學思想 薇依生前寫作涉獵範圍很廣。她自己既是哲學教師也愛好數學,同時還是各種政治運動的參與者,對馬克思主義也有著很獨到的反思。這些在許多關於她的作品和書籍中都有介紹。本文的重點是放在她的神學思想上,特別是和中國教會的神學實踐中有關上帝觀的神學思考和實踐上來獲得對我們的啟發和幫助。
愛中創造一切的上帝
薇依的上帝,不是哲學家和神學家在書齋里皓首窮經研究出來的那個堆砌在一堆玄而又玄的理論背後卻從不顧人間疾苦的不動情的上帝,也不是人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而在塵世間苦心打造出來的如貪官污吏一樣的偶像。關於這兩個方面,都是她盡力拒斥的。她在一篇論及主禱文的文章中寫道:“這就是我們的天父;我們身上沒有任何真實的東西不來自於他。我們屬於他。他愛我們,因為他自愛,因為我們屬於他,但是天父在天上,而不是在別處, 倘若我們以為人世間有天父,那就不是他,那是假的上帝。”[6]的確,從薇依的信主經歷和她的哲學背景出發,我們發現他很注重上帝的超越性,這是和他面對時代的環境而分不開的,她必須回應當時歐洲把社會運動神化、把國家神化、把德意志民族神化的思潮,而且,歐洲的問題就在於取消了基督教傳統中上帝的超越性,取消了神聖與世俗之間的差別,神聖者不再神聖,俗世反成為神聖。所以,他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時代的謬誤乃是由於無超自然的基督教。政教分離論(le laïcisme)是原因——首先是人文主義。”[7]甚至於她把上帝的超越性提高到一個認為上帝是“與超自然無形的隱沒在宇宙中”而且“他們無形的隱沒在靈魂中,是件好事。”[8]因為這避免了吧不是上帝的東西當作上帝來敬拜,也許薇依並沒有想要和什麼思潮作戰,但她很清楚,離開了上帝的超自然性,偶像崇拜必然產生。表面上看起來,薇依的上帝有些如哲學家的形上學中構築的“太一”“絕對理念”等概念,加上薇依的良好哲學素養,有可能使人懷疑這位上帝還是不是那位永活的上帝,那位造物的主宰,薇依是否矯枉過正?但薇依自己就在她的作品中回答了這樣人的提問。她的上帝不是不動情的上帝,相反,她的上帝不僅坐在高天之上,而且還俯視愁苦的群生並自願來到他們中間,與他們同受苦難,這一切都是因為他是愛。薇依寫道:“上帝穿過茫茫塵世來到我們這裡”。[9]而且,這位來到我們中間的上帝是一個“出於愛心,為了愛而創造……只創造愛本身和愛的手段而沒有創造它物”[10]的上帝。
上帝的愛是他屬性的首要,“首先,上帝是愛。首先,上帝在自愛。這種愛,上帝身上的這種友誼,就是三位一體。”[11]這種作為位格與位格之間的聯繫的愛,是薇依上帝觀的出發點。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在基督教悠遠綿長的兩千年歷史中,薇依所屬的神秘主義傳統對上帝聖愛的屬性一貫的強調。顯然,愛不僅是神秘主義傳統的核心概念,也是基督教信仰一貫的核心概念。上帝是愛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從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們的作品中屢屢可見他們特別的強調。如著名的13世紀女神秘主義者哈德薇希認為愛比天地所能包括的一切事物都更為寬闊和遼遠,更為高深恆久。上帝之愛超越一切。[12]而另一位極負盛名的呂斯布魯克則說:“……一切事物在聖靈的溢流中都被聖父和聖子全新的愛著。這就是聖父與聖子的行動著的相遇;我們在其中,在永恆之愛中通過聖靈而被充滿愛意的擁抱著。” [13]薇依繼承了這一神秘主義者們對上帝的認識並有她自己的理解,她把上帝的愛直接和上帝的創造放在了一起:“一切存在之物在其存在當中,也同樣受到上帝創造型的愛的支撐。”同樣,作為上帝的朋友,我們應當“熱愛存在之物,以使他們對塵世間萬物之愛同上帝之愛交融”。 [14]可以說,與我們中某些人想像的相反的是:不把上帝與上帝的創造分割,而是從萬物的美善看到上帝的愛,這是基督教神秘主義的主流。
不幸的意義:基督的十字架
薇依的上帝觀不僅強調上帝的愛,更強調這位愛人的上帝愛人到一個程度,竟然參與了人的受苦。受苦的上帝是20世紀神學思潮的一大主題,許多神學家用頭腦來思考上帝的受苦,以期待給世界的苦難一個答案。而薇依則是身體力行的與這位受苦的上帝站在了一起。從她自己切身體會出發認定受苦的上帝就是那位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在她的神秘經驗中“當基督突然降臨我身時,無論是感官還是想像都不曾有任何參與;我僅僅在苦痛中感到某種愛的降臨,這種愛就像在一位親切的人臉上所看到的微笑。” [15]
在苦痛和不幸中,薇依看到了基督信仰的真實性。我們都知道:自宗教改革後,路德所提出的“十字架神學”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上帝在基督里為我們的緣故承受苦難與不幸這一既舊且新的教義。當路德論到上帝如何分擔基督的苦難時,他明確地用上了“被釘死的上帝”(Deus Crucifixus)一詞。[16]基督的受難與不幸很大程度上就是上帝的不幸與苦難,在不幸與苦難中,上帝的愛以非同尋常的方式臨到了人類。而薇依也說:“,十字架上受難的最崇高時刻的從容,兩邊是何等愛的深淵!”[17]
我們都知道,自從萊布尼茨提出神正論的問題之後,圍繞著全能全愛的上帝為什麼容忍罪惡與不倖存在於世界之上,不知傷透了多少神學家、哲學家的腦筋,反宗教的人士更是以此為藉口來抗議讓人受苦的上帝。可以說,在基督教現代思潮中,神正論問題是一個必須面對而不容迴避的問題。薇依由其神秘主義的立場出發,力圖在基督與人的相遇中,在親身體驗人的不幸與苦痛中尋找答案。
薇依和其他基督教思想家略有不同的一點是她竟然認為不幸是絕對的。作為存在的人的不幸是無法消除的。她說:“不幸:時間把有思維的人,不管其意願如何,帶向她無法承受但卻必然會來臨的東西哪裡。”[18]劉小楓博士對此的解釋是:“這意味著人通過任何手段都無法最終消除生存之不幸……有偶然性導致的不幸育人與生命會共存。悲涼永遠會伴隨著人的存在之偶然性,伴隨著人的遺憾。”[19] 而且,薇依堅決拒斥不幸也會給人帶來益處的這種所謂鍛鍊的學說,她認為罪惡和痛苦如果被人感知到其益處或能引起崇高的光榮的話,那它就不是不幸。不幸之所以是不幸就在於它是對生活的一種徹底否定,是降臨於某人並把它徹底摧垮的事件。[20]最大的不幸,就是上帝的不在場。使一切都變成虛空而無意義。因此薇依從不把基督信仰當作對苦難的逃避或麻醉——正如馬克思所認為的那樣。相反,她認為就是基督也同樣的遭遇不幸,而且是遭遇到人所不能忍受的最大的不幸,上帝在基督里倒空自己,上帝不在場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離棄我!” 但上帝的愛從此就顯明出來了,基督的受難成為了另一種“賜福的不幸”。在這種不幸當中,上帝把自己的存在傾空。這種傾空顯明了上帝在生存破碎中去愛的無限奧秘。[21]這樣,每一個執著最求愛的人應當在不幸中來與上帝站在一起,與十字架上的基督站在一起,直至靈魂和基督發出同樣的呼喊,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會真切的感受到上帝是多末的愛世人,這才是真正的愛上帝的人,而基督徒正是這樣的人。這就是為一所說的“相似於上帝,但是在十字架上受難的上帝……因此,一個愛人的上帝,一個愛上帝的人,應該受苦”的真正含義。[22]
不幸可以說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意味著上帝不在場從而取消了一切生存的意義;但不幸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又被賦予了意義,因為它意味著從極度的十字架被樹起的那一天起,上帝的愛穿越了一切深淵來到了不幸的人之中。“必須在虛無和虛空的苦難中努力找到更為充實的現實,同樣,應當熱愛生活以更加熱愛死亡。”[23]這也許是對薇依和像他一樣千千萬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最好註解。
“滌罪的無神論”與“教外基督徒”
薇依的信仰一直備受爭議。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她一直未接受洗禮並且是主動拒絕接受洗禮,雖然她表明自己很熱愛宗教儀式對此並不感到反感。相反她多次參加彌撒和節期活動。並在其中得到很多精神上的幫助和滿足,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我很懷疑她是否在沒有接受洗禮的情況下去領過聖餐。[24]而且,有的人還不敢肯定薇依是否有“得救的確信”。因為薇依在自己皈依後也曾說過:“真實的矛盾狀況。上帝存在著,上帝並不存在。”並且她還肯定有一種“對上帝這個概念淨化的無神論” [25] 在某些人看來,薇依不僅不是一個基督教的會員,恐怕連是否認信基督都很成問題。她不僅給無神論說話,甚至還替佛教、印度教、希臘神話的眾神來尋找信仰的根據,在她給一位修士的信中這樣寫道:“基督教誕生以來,除在天主教教會之外的那一部分人(“不虔誠的人”“異教徒”“不信教者”)也有對上帝的愛與認識。更廣義地講,認為從基督教誕生以來,在基督教民族中比某些非基督教國家,例如印度對上帝擁有更多的愛與認識,這種說法值得懷疑。”[26]在這封信中,他詳細的比較了各種宗教的學說和思想,深刻地的出了這樣的結論:“如若我們明白了希臘幾何學與基督信仰是從同一源泉噴發出來的,那我們的生活將會發生多末大的變化啊!”[27]來讀薇依的這些文字,也許有的人會憤怒、會瞠目結舌、會反感……但沒有人會否認這些文字下面是一顆跳動的質樸真實的良心。
事實上薇依不是一名傳統意義上的基督教徒,但她絕對是一名跟隨基督的 基督徒。她用自己的聲明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在有形的教會之外,上帝仍然做工。下面我們來看看她的所謂的“無神論”和拒不受洗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不是替他解釋和辯護,乃是要讓我們觸摸這美麗的靈魂。
在一開始我們就必須明了:薇依的認信完全是從其生存的不幸處境中與上帝相遇的,不是任何的教條學說,也不是哲學理念。這就決定了她必然是一個真切的在生命中體會和跟隨基督的人。決定了她必然是一個神秘主義者。
薇依之所以寫出上面那段對上帝的存在似乎不確定的話語,乃是她從人的生存處境出發真實地思考,一方面她知道對於理性的頭腦來講,接受超自然的存在是一件多末困難的事情。“我堅信並無上帝,則是從這種意義講的,即我確信沒有任何實在的東西相似於我說出來的這個名字所可能構想到的東西。”隨後,她更加堅定有力的說出:“但是,我無法構想的東西並不是幻想。”讀到這裡我們就恍然大悟了,可見薇依不是否認上帝的存在,薇依從小受到良好的理智上的訓練,對數學、邏輯、語言、哲學都有很高的素養,她並不是否認理智對人的益處。乃是用理性在說明理性在證明上帝是否存在問題上的無能與無助。靠理性證明上帝,此路不通也。
同時薇依以一種特別開放的態度看待無神論。她這樣寫道:“有兩種無神論,其中之一是對上帝這個概念的淨化(purification)。”“在兩個不曾體驗過上帝的人中間,否認上帝的人也許離上帝最近。”[28]薇依此話不無道理。她又說:“虛假的上帝在各方面類似於真的上帝,除非人們不去觸及他,不然他會永遠阻止人們接近真正的上帝。”[29]其實,薇依的所謂的“滌罪的無神論”並不是指他要拋棄上帝,乃是指他要拋棄那人為的虛假的上帝的概念,比起無神論者,特別是真正肯於在世界上追求公正、良善和一切美好的無神論者,那些虛假的信仰者更加遠離上帝。
薇依拒不接受洗禮,這是來自於她對教會及人為的制度的一種深刻的體會。她在講述她為何不接受洗禮加入教會時說:“我想,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將永不會入教,為的是不因宗教而使自己與普通人相隔。”[30]她認為教會作為塵世間的一個社會組織而存在,就不可避免的具有“濫用權力的天然傾向。”而在教會的歷史上,教會犯下了許多錯誤:以宗教的名義發動政治戰爭,逼害異端,壓迫各社會階層。作為一個局外人,她痛苦的看到在教會當中,參雜了許多人為的因素。“除了純粹的神秘主義外,羅馬的偶像崇拜把一切都弄污了。”[31]
對於教會外的真善和美好,薇依從來不會加以否定。她認為這同樣是來自於上帝的創造。她深刻地指出:“有這樣多的事情是在教會之外,使我所愛和不願意放棄的,這些事情一定是天主所愛的,否則它們不會存在。……這一切常被教會貶低,其實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而這些事情包括了“希臘、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國,世界的美,在科學與藝術中反映的這些純淨樸實的美。……我甚至還可以說得更多。總之,是對表面化的基督宗教之外的這一切之愛,使我停留在教會之外。”[32]但停留在教會之外不意味著在基督之外,薇依以她自己的實踐告訴我們,她一直在愛與不幸當中期待上帝的降臨。
評價 “薇依的生與死是20世紀基督精神的偉大見證,使基督信仰仍然充滿生命力的偉大見證,使基督仍在我們中間、上帝仍然活著的偉大見證。”[33]通過對薇依思想的一些梳理。我們分明可以感受到她信仰的質樸和純真。同時她的思想對於我們來說也有深刻的啟迪意義。
首先,對於基督教的神秘主義傳統,有許多人,特別是教外的人總認為是消極遁世,逃脫現實的一種信仰。薇依用自己的思考和實踐對這種看法的錯誤提供了最好的反駁。她認為上帝讓我們愛這“故土”的世界和世界上的美。[34]薇依自己以身作則,親自參加工廠的勞動,和勞苦民眾同甘苦共患難;在民族淪亡之際,他挺身而出,在國外參與抵抗運動,直至積勞成疾,早逝於貧病交加之中。她的生命和思想,深深的影響著當代的基督教信仰。正如瑪多勒所說:“能夠改變一種生活的數是很少的,薇依的書就屬於這類書之列。在讀了它的書之後,讀者很難保持讀前的情況……”[35]以至於人們把她的《
重負與神恩 》的書與
帕斯卡爾 的《
思想錄 》相比較,並稱她為“當代的
帕斯卡爾 ”。我想是不過分的。
其次,對於我們如何看待痛苦與不幸。薇依的思想使我們得到了更好的啟發。“一個充分和合理的神義論必然要求上帝最終對世界的苦難負責任,而滿足此要求最有力的證明,便是上帝在苦難中有份。”[36]傳統基督教教義堅持上帝不懂情性的觀念,事實上是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20世紀以後,隨著苦罪問題日益成為基督教神學的重要關注。薇依和其他在實踐中經歷上帝與他們一同受苦和戰勝罪惡的思想家們共同得出了上帝在苦難與不幸中與人相遇,並與人一同承當苦難的後果的觀念,使基督教神學在啟示之光的照耀下勇敢地面對和回應苦難對人的威脅和攻擊,並及時給在受苦當中的人以慰藉和希望。在談到十字架神秘主義時,當代神學家猶根.莫爾特曼深刻地指出:“通過基督的受難與死,耶穌認同於那些被奴役的人,分擔他們的受苦。…他們在自己遭受奴役的痛苦中也沒有被拋棄。耶穌與他們在一起。在耶穌中,他們得到解救的希望;耶穌的復活與進入上帝的自由中,為他們帶來自由的希望。在一個剝奪了他們所有希望,剝奪他們所有人性身份,直至它不可再見的世界裡,耶穌使他們認同於上帝。”[37]假如薇依看到這段話,一定會表示非常贊同的。
最後,薇依對待教會之外的真善美的看法。對待所謂的“無神論”的認識,也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當然,自始至終薇依都不是一個無神論者,更不是一個異教徒。她是一個徹底追隨基督的人。他從未否認基督救恩的真實性和獨特性,她說:“沒有重生,沒有內心頓悟,沒有基督和上帝在靈魂中出現,就不會獲救。”[38]但她仍然對這世界上的美好和那些崇高道德的無神論者或其它宗教的信徒抱有崇高的敬意,她相信他們不在上帝的恩典之外。她認為那些擁有超自然的愛和接受上帝所創造世界秩序的人“即使作為無神論者而生而死,他們也是聖人。”[39]在一個周圍幾乎都是非信徒的社會當中,基督徒如何看待他們?如何看待教會之外的真實和美好?是自以為義畫地為牢還是敢於肯定上帝的工作和他在這個世界中默默無聲於那些一直在痛苦中而並不屈服的人們站在一起?無疑薇依會給我們提供一個思索的線路。
當然,薇依的思想豐富異常,可能要繼續講下去的話還會有很多未能發掘出的珍貴閃光之處,但限於時間和篇幅的關係,我們只能討論到這裡。最後我們願意隨著薇依在世時的一次經歷來結束本文,讓我們再一次和這位偉大而美麗的心靈共同去感受那位愛我們的上帝的愛。
他(聖神)帶領我到一間教堂(1942年在馬賽)。教堂很新但很醜陋。他對我說:“跪下。”我回答說:“我尚未領洗。”他說:“帶著愛跪在這塊土地上,就像你跪在一個維繫著真理的地方一樣。”我服從了。[40]
人們在她的筆記本中發現的最後幾個字是:“教學的最重要方面=對教會的認識(從科學意義上說)。”
薇依的整個一生都包含在這個詞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進阿斯福特療養院後不久,她就與世長辭了。
她曾說:“我們生於他人的苦難里,而死於自己的痛苦中。”這也是她精神的寫照。
西蒙娜從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向宗教救世思想的轉變,深刻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痛苦、迷茫、奮鬥和思考。
西蒙娜擁有特立獨行,自甘苦行、永遠站在窮苦人民一邊的“
聖女 ”人格和感人生平,她的思想充滿智慧。
著作
源於期待 前言:論無辜者的不幸
源於期待 01 論無辜者的不幸
02 論必然與順從
03 靈魂朝著上帝
04 注意力的質量
05 最可貴的財富不是尋找得來的
06 只有正義才使意志和諧
07 聆聽一個不幸者的聲音
08 感謝那些並不知把麵包賜予誰的人
09 愛世界的秩序
10 美是世間唯一的合目的性
11 肉體之愛意欲世界之美
12 共同的光明普照眾生
13 愛宗教禮儀活動
14 目光注視著完美的純淨
15 神聖的東西無須費力
16 作為人類之愛的友情
17 內在的愛和外露的愛
18 重負與神恩
19 虛空與報答
20 接受虛空
21 超脫
22 填補虛空的想像
23 棄絕時間
24 無對象的渴望
25 我
26 失去創造
27 隱沒
28 必然與服從
這本書是薇依的一些隨筆。她的文字有一種非同一般的美。這種美讓我們懷疑她的存在是否真實。薇依的思想不同於任何人。是的,她是上帝瘋狂的熱愛者,追隨者……這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理由來解釋她文字中令人無法想像的絕對性和冷漠感。
以下是我摘抄的幾句,希望大家能有所感觸:
1 人們只有在某種距離上看待不幸時才可能接受不幸的存在。
2 愛真理意味著接受空虛,繼之接受虛空,繼之接受死亡。真理是同死亡在一起的。
3 依戀並非他物,只是現實感情中的不足,人們依戀與對事物的擁有,因為人們以為若不再擁有此物,就不再繼續存在。許多人並沒有以全部身心去領會,在一個城市被毀滅和他們一去不復返地遠離這城市之間截然不同。
4 凡是存在的東西絕對不值得愛。
因此,應愛不存在之物。
但是,這個不存在的愛的對象物並不是想像的。因為我們的想像不可能比我們自身——我們自身並不值得愛——更值得愛。
5 美,是一種人們看著它而不向它伸手的水果;
同樣是一種人們看著它而不退卻的不幸。
6 有一種不幸是:人們無力承受它延續下去,也無力從中擺脫出來。
7 限定是上帝愛我們的證明。
……
這本書是令我對薇依感興趣的原因。她不像想成為天使那樣去愛上帝,她對上帝的愛是摒棄。
重負與神恩 有人把薇依的《
重負與神恩 》與
帕斯卡爾 的《
思想錄 》相提並論,並稱薇依為“當代的帕斯卡爾”。這位法國20世紀傑出的宗教思想家,沿循的是
帕斯卡爾 的神秘主義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來炫耀之物,而是艱難、絕非輕鬆的重負。本書不是系統的專門論著,是薇依的朋友、著名宗教學家梯蓬(G .Thibon,1903一)在薇依身後從她大量的手稿、言談記錄中整理成書的。這些閃爍著精神之光的篇章滲透著薇依的深邃思考,顯示了薇依的偉大心靈和崇高的信仰,是20世紀基督神秘主義思想史上一部不容忽視的著作。
重負與神恩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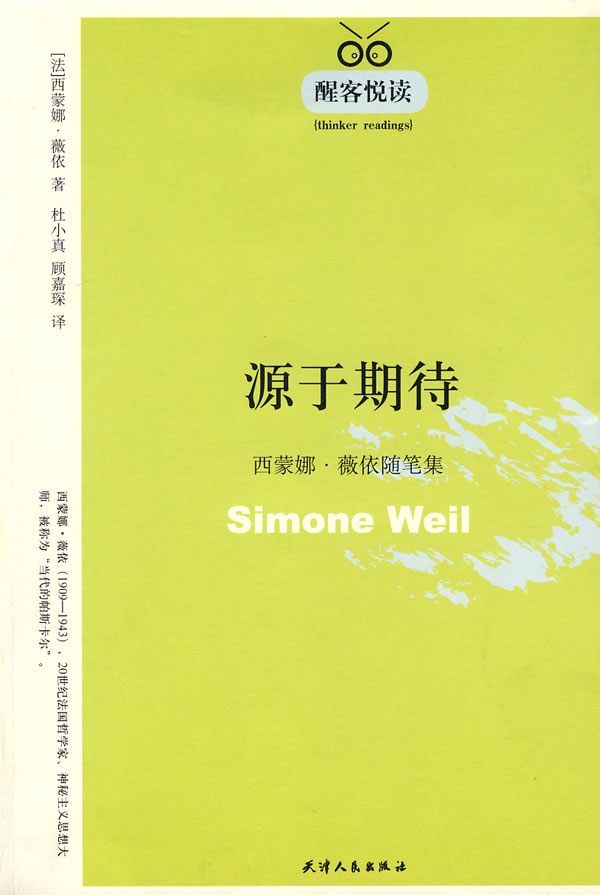 源於期待
源於期待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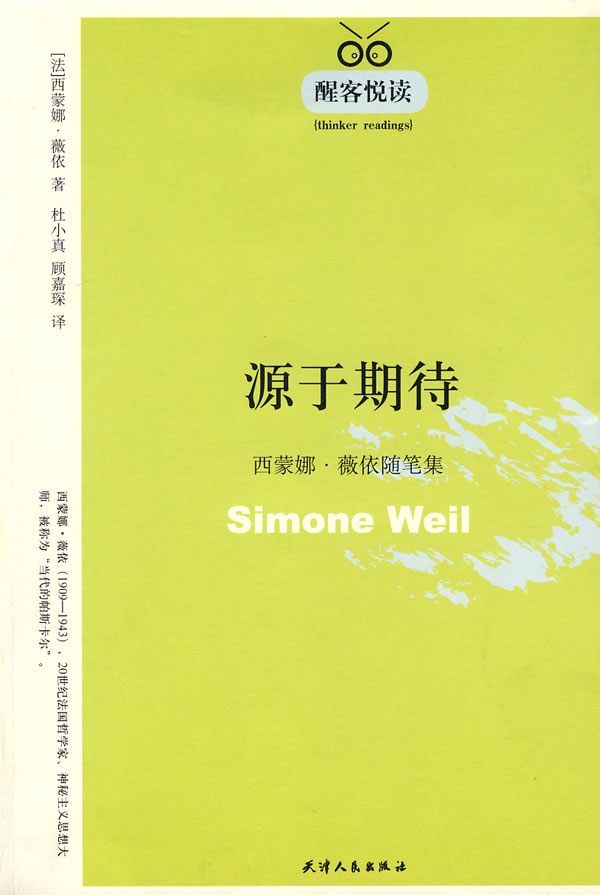 源於期待
源於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