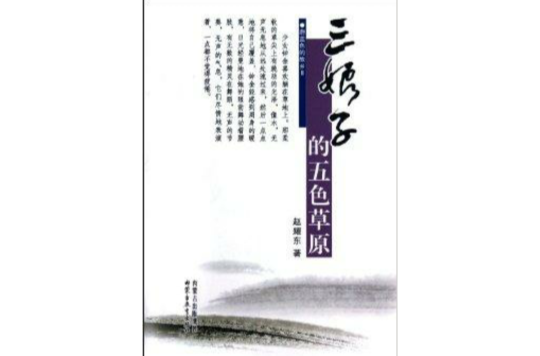趙耀東編著的《三娘子的五色草原》是一部以西部大漠草原為書寫對象的作品。 《三娘子的五色草原》以北方草原歷史文化和當代文明為背景,書寫作家對民族文化的獨特視覺,詮釋了一個民族、一片草原的今天和昨天,表達了作家對民族、家鄉和草原的無限熱愛之情。 《三娘子的五色草原》主要寫了三娘子為了維護民族團結、維護民族利益,處處顧全大局,妥善地處理了許多邊事糾紛等以及其一生的偉大英雄業績。
基本介紹
- 書名:蔚藍色的故鄉:三娘子的五色草原
- 出版社:內蒙古教育出版社
- 頁數:176頁
- 開本:32
- 作者:趙耀東
- 出版日期:2011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118288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趙耀東的長篇小說《三娘子的五色草原》,是一部集兒女情長、民族交融、宗教信仰、國家統一於一體的奇異之作。作品著重表現明代蒙古瓦剌奇喇古特部哲恆阿噶之女三娘子(鐘金哈屯)在北疆草原主政三十年間的功績,但令人記住的還有那一時代分散的蒙古各部落逐漸統一、土默特地區蒙漢雜居牧耕並舉逐漸形成的現實,並由此想到作品背後的歷史。史詩性與傳奇性兼具。
整部作品中大的歷史背景都很真實,力求達到一種真實史實與好看故事的結合。而作家又不為史實所拘囿,在情節的鉤織鋪展中,諸條線索齊頭並進,有對少女鐘金哈屯美麗輕靈、草場放牧的細膩描述,也有對她救護藏僧阿興以及先後被扎拉圖、阿拉坦汗搭救的緊張描寫;有對鐘金哈屯學畫畫、寫漢字、進縣城、見朝吏的有聲有色的描繪,更有對她被親切地稱為“三娘子”以及在孫子巴漢那吉投奔明朝後促成蒙漢通貢和互市的有張有弛的描敘。簡練而豐富,簡潔而深切。豐富的民族文化意蘊與深切的時代精神內涵盡在其中。
整部作品中大的歷史背景都很真實,力求達到一種真實史實與好看故事的結合。而作家又不為史實所拘囿,在情節的鉤織鋪展中,諸條線索齊頭並進,有對少女鐘金哈屯美麗輕靈、草場放牧的細膩描述,也有對她救護藏僧阿興以及先後被扎拉圖、阿拉坦汗搭救的緊張描寫;有對鐘金哈屯學畫畫、寫漢字、進縣城、見朝吏的有聲有色的描繪,更有對她被親切地稱為“三娘子”以及在孫子巴漢那吉投奔明朝後促成蒙漢通貢和互市的有張有弛的描敘。簡練而豐富,簡潔而深切。豐富的民族文化意蘊與深切的時代精神內涵盡在其中。
作者簡介
趙耀東,漢族,七十年代出生於呼和浩特,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呼和浩特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曾在《作品》、《西湖》、《北方文學》、《草原》、《青海湖》等期刊發表小說多篇,多部小說被報刊連載,獲“草原文學獎”,已出版小說集《為誰演奏》、長篇小說《摩撒吉死咒》,被譽為內蒙古最具實力的中堅作家。
文摘
第一章
1
少女鐘金喜歡躺在草地上。那柔軟的草尖上有跳動的光澤,像水,無聲無息地從遠處流過來,然後一點點地將自己覆蓋,鐘金能感到周身的暖意,日光輕曼地在她的眼前舞動著腰肢,有無數的精靈在舞蹈,無聲的節奏,無聲的氣息,它們盡情地表演著,一點都不覺得疲倦。
鐘金看累了,就閉上眼睛,她開始聽唱歌了。她聽見陽坡地上的芨芨草在唱,聽見雲端里的百靈子在唱,就連吃飽了草的牛羊都在唱,它們的歌聲有高亢的,有低沉的,鐘金喜歡昕,她就這樣閉著眼,靜靜地聽,從太陽紅彤彤,一直聽到太陽泛了黃,一點都不累,當她聽見那歌聲變得越來越縹緲的時候,她覺得時間到了。
該回了,她睜開眼,天與地仍是明亮的,一天最明亮的時分,不是中午而是黃昏,在絢麗的光線中,天與地的一切都在翩翩起舞。這片草場是去年夏天找到的,它像一塊寶玉一樣,隱藏著,鐘金趕著羊群穿過一片看不見天的白樺林,才來到這裡。
這片草場就連她的父親阿哈都不知道。
當春天的氣息,從南面吹來時,阿哈一家拉著各種生活的物資,來到這片夏季草場,他們要在這裡待上整整一個夏天,到了草泛黃,牛羊上了膘,才馱著重重的乾草,踏著陣陣秋風,緩慢地返回原來的營地。
太陽像一個火球,帶著燃燒的炙焰,正在一點點接近遠處的山巒,當接近山頂的剎那,烈焰紛飛,化成像水波一樣的晚霞。天說黑就黑,她得趕緊行動,鐘金一邊吆喝著牧羊的“布日”,“布日”是一條忠實的牧羊犬,像鐘金的影子一樣,一時一刻都不離開她:一邊往馬背上放鞍子,她的馬鞍子是哈密草原上最漂亮的,這是當年阿爸娶阿媽的定親物,它用五匹俊美的蒙古馬從哈薩克人手裡換來的,又找了當地最好的手藝人加以修繕,這副工藝馬鞍子,成了奇喇古特部富足的象徵。
天色暗下來了,夜風裹著草地上的水汽,沒走多長時間,皮膚便有了潮膩的感覺,空蕩蕩的草原,即使夏天也是寒冷的。鐘金家的營地離這裡有五六里地,她騎著馬,有點餓了,囊袋裡的肉干已經吃完了,她得趕緊往回趕,她能聞到遠處蒙古包里散發出的美食味道,母親做的羊肉總是很鮮嫩,幾里之外都能聞得到。
“布日”突然狂叫起來,它的叫聲里充滿了警惕。
沒有月亮,眼前黑乎乎的,什麼都看不見,鐘金知道能讓“布日”感到不安,肯定是有什麼情況,在這廣袤的草原上,什麼樣的危險情況都可能發生。鐘金抽出了腰刀,黑夜裡有它就有了力量。“布日”還在叫著,聽聲音它就在離自己馬匹的一步之遙,它的叫聲越來越亮,仿佛一個可怕的野獸就潛伏在不遠處,鐘金屏住呼吸,儘量用耳朵聽得真切一些,除了狗叫什麼都沒有。
“布日”停止了叫聲。黑夜又恢復了寧靜。
鐘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攥著刀柄已經有了汗,她朝“布日”噓了兩聲,仍沒有動靜,她將皮囊里的火鐮子拿出來,點著一隻浸滿松油的火把,天地有了亮光,恐懼在一點點地退縮,這時她看貝,布日”,正在圍著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團團轉著。她看不清那是個什麼東西,她下了馬,同時握緊了馬刀,小心翼翼地一點點朝那個黑乎乎的傢伙走去。現在她擔心那個黑乎乎的東西是一隻狡猾的黑熊,聽營地上的牧民講過,黑熊會裝作睡著的樣子,當人或別的動物靠近,它會一下從地上躍起,一掌將襲擊的目標拍倒。
走近了,並沒有聞到熊的氣息,她把手裡的火把舉高,她看清了,那是個人。一個穿著奇怪袍子的人,躺在草地上,“布日”還在不停地嗅來嗅去。鐘金推了下那個人,沒動,她便用手試探了下那人的鼻息,有絲絲的熱氣,現在她無法斷定這個人的來歷,他為什麼會躺在這裡?四周黑漆漆,她得趕快把他送回營地。
那人的身體很瘦,很輕,鐘金架起他的時候,幾乎沒費什麼力氣。
在草原上,看見了火光,便看見了家。阿爸阿哈已經備好了馬,正準備和五個青年,到牧場上去找鐘金,這么黑的天,他擔心女兒。
看那個人服飾,阿哈一眼就認出了他的身份:“他是一個藏地來的僧人。”阿哈說。對鐘金來說,藏地是一個遙遠得不能再遙遠的地方了。阿爸是個見多識廣的人,他說:“這個僧人還活著,也許是他太餓了,給他餵點奶子,快。”
當那個僧人呼吸變得均勻了,眾人才停止忙乎。
篝火熊熊地燃燒著,快進秋天,草原的夜,漸漸被冷氣一點點包圍、浸透,這沉沉的黑夜只有火和女人的身體是暖的。草原上的女人用身體溫暖完男人,然後起身再侍弄火,她們用火驅走男人身體上的隱冷和黑暗。在火光中,阿哈額頭上的皺紋變深了。他在回憶自己年輕時,到藏區的情景。那次他和他的阿爸,想到西海(現在的青海)去販皮子,結果遇到了’戰爭,土默特部和亦不剌部的軍隊正打得不可開交,在那裡,到處都是散發著臭味的屍首,有人的,有牲畜的。後來,他們遇到了土默特部軍隊,他和他的阿爸不得不放棄三馬車皮子,倉皇地跑進了一家寺院,那裡的僧人,讓他們躲過了劫難。
火焰映掩著阿哈的臉,回憶中的片斷隨著火光閃爍,喇嘛的笑臉,清冷的召廟,光影中游移的壁畫。阿哈嘆了口氣,現在來自強大的土默特部蒙古人幾乎每年都要和瓦刺部的蒙古人打仗,戰爭毀壞了草地,讓這些僧人只能四處流亡。
就在鐘金領著這個陌生的僧人回到營地的第二天,薩滿博扎吉發出了預言,他說鐘金帶回來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危險的野獸,他現在在昏睡,一旦醒來,就會給整個部落帶來危險,這危險像天上的烏雲,籠罩住大地,生活在這裡的人再也看不到晴朗的天空,他們會相信這個僧人,僧人帶有魔咒,控制住他們的大腦。
面對薩滿博的話,哈密草原上的人確實感到了恐慌,他們一直都在聽薩滿的話,這次也不例外。他們當中有的人,去找阿哈,他們想聽一聽首領的話。阿哈一直沉默著,在氈包外圍聚的人越來越多,後來阿哈終於說話了,他說:“現在這個僧人還在昏迷,一切事情等他醒來再說。”
鐘金倒是不關心人們的議論,她從心裡擔心這個瘦弱的僧人會隨時死掉,她就在帳篷里守著,白天放羊的時候,她就到草甸子西面的敖包,默默祈禱,在這裡她許的願都特別靈。有一年,額吉烏日娜得了一種怪病,先是頭疼,然後是全身疼。額吉的病嚇壞了阿爸,他把部落里最好的薩滿叫來,整整折騰了一天,都沒有治好額吉的病。額吉病得越來越厲害,她的眼睛看不見站在面前的人,她的手指又紅又腫,連拳頭都握不住。鐘金跑到了草地西面的敖包前,整整待了一天,她為額吉做著祈願,奇蹟就出現了,當她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營地,看見額吉的眼睛睜開了。第二天,額吉手指間不再紅腫。第三天的時候,額吉就能坐起來和她說話。
這個秘密,只有她自己知道。
跟她期待的一樣,那個瘦弱的僧人是在第三天醒過來的,他醒來,睜大眼睛看了半天四周的環境和人,他不知道這是在哪,隨後他張口說話了,他說的話,誰都聽不懂,在大帳里的人都面面相覷,不知道這個僧人在說什麼?
還是阿哈見多識廣,他說:“他說的是唐古特語,快去,叫查魯來。”
查魯是這裡最老的人,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年齡,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被人扶著走進了大帳。
鐘金並沒有隨著人走進大帳,她靠著蒙古包的門口,布日搖著尾巴盤坐在她的膝下。大帳里很安靜,只有叫查魯的老人和那個僧人有一句沒一句地在說話,她聽不懂,但愛聽。那聲音帶著遙遠而神秘的氣息,每個字和音節都得費些力氣。
P1-4
1
少女鐘金喜歡躺在草地上。那柔軟的草尖上有跳動的光澤,像水,無聲無息地從遠處流過來,然後一點點地將自己覆蓋,鐘金能感到周身的暖意,日光輕曼地在她的眼前舞動著腰肢,有無數的精靈在舞蹈,無聲的節奏,無聲的氣息,它們盡情地表演著,一點都不覺得疲倦。
鐘金看累了,就閉上眼睛,她開始聽唱歌了。她聽見陽坡地上的芨芨草在唱,聽見雲端里的百靈子在唱,就連吃飽了草的牛羊都在唱,它們的歌聲有高亢的,有低沉的,鐘金喜歡昕,她就這樣閉著眼,靜靜地聽,從太陽紅彤彤,一直聽到太陽泛了黃,一點都不累,當她聽見那歌聲變得越來越縹緲的時候,她覺得時間到了。
該回了,她睜開眼,天與地仍是明亮的,一天最明亮的時分,不是中午而是黃昏,在絢麗的光線中,天與地的一切都在翩翩起舞。這片草場是去年夏天找到的,它像一塊寶玉一樣,隱藏著,鐘金趕著羊群穿過一片看不見天的白樺林,才來到這裡。
這片草場就連她的父親阿哈都不知道。
當春天的氣息,從南面吹來時,阿哈一家拉著各種生活的物資,來到這片夏季草場,他們要在這裡待上整整一個夏天,到了草泛黃,牛羊上了膘,才馱著重重的乾草,踏著陣陣秋風,緩慢地返回原來的營地。
太陽像一個火球,帶著燃燒的炙焰,正在一點點接近遠處的山巒,當接近山頂的剎那,烈焰紛飛,化成像水波一樣的晚霞。天說黑就黑,她得趕緊行動,鐘金一邊吆喝著牧羊的“布日”,“布日”是一條忠實的牧羊犬,像鐘金的影子一樣,一時一刻都不離開她:一邊往馬背上放鞍子,她的馬鞍子是哈密草原上最漂亮的,這是當年阿爸娶阿媽的定親物,它用五匹俊美的蒙古馬從哈薩克人手裡換來的,又找了當地最好的手藝人加以修繕,這副工藝馬鞍子,成了奇喇古特部富足的象徵。
天色暗下來了,夜風裹著草地上的水汽,沒走多長時間,皮膚便有了潮膩的感覺,空蕩蕩的草原,即使夏天也是寒冷的。鐘金家的營地離這裡有五六里地,她騎著馬,有點餓了,囊袋裡的肉干已經吃完了,她得趕緊往回趕,她能聞到遠處蒙古包里散發出的美食味道,母親做的羊肉總是很鮮嫩,幾里之外都能聞得到。
“布日”突然狂叫起來,它的叫聲里充滿了警惕。
沒有月亮,眼前黑乎乎的,什麼都看不見,鐘金知道能讓“布日”感到不安,肯定是有什麼情況,在這廣袤的草原上,什麼樣的危險情況都可能發生。鐘金抽出了腰刀,黑夜裡有它就有了力量。“布日”還在叫著,聽聲音它就在離自己馬匹的一步之遙,它的叫聲越來越亮,仿佛一個可怕的野獸就潛伏在不遠處,鐘金屏住呼吸,儘量用耳朵聽得真切一些,除了狗叫什麼都沒有。
“布日”停止了叫聲。黑夜又恢復了寧靜。
鐘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攥著刀柄已經有了汗,她朝“布日”噓了兩聲,仍沒有動靜,她將皮囊里的火鐮子拿出來,點著一隻浸滿松油的火把,天地有了亮光,恐懼在一點點地退縮,這時她看貝,布日”,正在圍著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團團轉著。她看不清那是個什麼東西,她下了馬,同時握緊了馬刀,小心翼翼地一點點朝那個黑乎乎的傢伙走去。現在她擔心那個黑乎乎的東西是一隻狡猾的黑熊,聽營地上的牧民講過,黑熊會裝作睡著的樣子,當人或別的動物靠近,它會一下從地上躍起,一掌將襲擊的目標拍倒。
走近了,並沒有聞到熊的氣息,她把手裡的火把舉高,她看清了,那是個人。一個穿著奇怪袍子的人,躺在草地上,“布日”還在不停地嗅來嗅去。鐘金推了下那個人,沒動,她便用手試探了下那人的鼻息,有絲絲的熱氣,現在她無法斷定這個人的來歷,他為什麼會躺在這裡?四周黑漆漆,她得趕快把他送回營地。
那人的身體很瘦,很輕,鐘金架起他的時候,幾乎沒費什麼力氣。
在草原上,看見了火光,便看見了家。阿爸阿哈已經備好了馬,正準備和五個青年,到牧場上去找鐘金,這么黑的天,他擔心女兒。
看那個人服飾,阿哈一眼就認出了他的身份:“他是一個藏地來的僧人。”阿哈說。對鐘金來說,藏地是一個遙遠得不能再遙遠的地方了。阿爸是個見多識廣的人,他說:“這個僧人還活著,也許是他太餓了,給他餵點奶子,快。”
當那個僧人呼吸變得均勻了,眾人才停止忙乎。
篝火熊熊地燃燒著,快進秋天,草原的夜,漸漸被冷氣一點點包圍、浸透,這沉沉的黑夜只有火和女人的身體是暖的。草原上的女人用身體溫暖完男人,然後起身再侍弄火,她們用火驅走男人身體上的隱冷和黑暗。在火光中,阿哈額頭上的皺紋變深了。他在回憶自己年輕時,到藏區的情景。那次他和他的阿爸,想到西海(現在的青海)去販皮子,結果遇到了’戰爭,土默特部和亦不剌部的軍隊正打得不可開交,在那裡,到處都是散發著臭味的屍首,有人的,有牲畜的。後來,他們遇到了土默特部軍隊,他和他的阿爸不得不放棄三馬車皮子,倉皇地跑進了一家寺院,那裡的僧人,讓他們躲過了劫難。
火焰映掩著阿哈的臉,回憶中的片斷隨著火光閃爍,喇嘛的笑臉,清冷的召廟,光影中游移的壁畫。阿哈嘆了口氣,現在來自強大的土默特部蒙古人幾乎每年都要和瓦刺部的蒙古人打仗,戰爭毀壞了草地,讓這些僧人只能四處流亡。
就在鐘金領著這個陌生的僧人回到營地的第二天,薩滿博扎吉發出了預言,他說鐘金帶回來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危險的野獸,他現在在昏睡,一旦醒來,就會給整個部落帶來危險,這危險像天上的烏雲,籠罩住大地,生活在這裡的人再也看不到晴朗的天空,他們會相信這個僧人,僧人帶有魔咒,控制住他們的大腦。
面對薩滿博的話,哈密草原上的人確實感到了恐慌,他們一直都在聽薩滿的話,這次也不例外。他們當中有的人,去找阿哈,他們想聽一聽首領的話。阿哈一直沉默著,在氈包外圍聚的人越來越多,後來阿哈終於說話了,他說:“現在這個僧人還在昏迷,一切事情等他醒來再說。”
鐘金倒是不關心人們的議論,她從心裡擔心這個瘦弱的僧人會隨時死掉,她就在帳篷里守著,白天放羊的時候,她就到草甸子西面的敖包,默默祈禱,在這裡她許的願都特別靈。有一年,額吉烏日娜得了一種怪病,先是頭疼,然後是全身疼。額吉的病嚇壞了阿爸,他把部落里最好的薩滿叫來,整整折騰了一天,都沒有治好額吉的病。額吉病得越來越厲害,她的眼睛看不見站在面前的人,她的手指又紅又腫,連拳頭都握不住。鐘金跑到了草地西面的敖包前,整整待了一天,她為額吉做著祈願,奇蹟就出現了,當她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營地,看見額吉的眼睛睜開了。第二天,額吉手指間不再紅腫。第三天的時候,額吉就能坐起來和她說話。
這個秘密,只有她自己知道。
跟她期待的一樣,那個瘦弱的僧人是在第三天醒過來的,他醒來,睜大眼睛看了半天四周的環境和人,他不知道這是在哪,隨後他張口說話了,他說的話,誰都聽不懂,在大帳里的人都面面相覷,不知道這個僧人在說什麼?
還是阿哈見多識廣,他說:“他說的是唐古特語,快去,叫查魯來。”
查魯是這裡最老的人,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年齡,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被人扶著走進了大帳。
鐘金並沒有隨著人走進大帳,她靠著蒙古包的門口,布日搖著尾巴盤坐在她的膝下。大帳里很安靜,只有叫查魯的老人和那個僧人有一句沒一句地在說話,她聽不懂,但愛聽。那聲音帶著遙遠而神秘的氣息,每個字和音節都得費些力氣。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