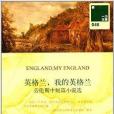《英格蘭,我的英格蘭》是英國著名小說家勞倫斯的中短篇小說選集,收錄10篇經典作品,包括《菊香》《乾草垛里的愛》《普魯士軍官》《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你摸過我》《公主》《太陽》《愛島的男人》《人生之夢》《逃跑的公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英格蘭,我的英格蘭: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集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頁數:595頁
- 開本:16
- 外文名:England,My England
- 譯者:黑馬
- 出版日期:2014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英語
- ISBN:978754264813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健康的愛情需要詩意的滋養
“情色小說家”勞倫斯用充滿陽光和春風的男女
警醒僵化的現代社會
中英文雙語對照,買一贈一
“情色小說家”勞倫斯用充滿陽光和春風的男女
警醒僵化的現代社會
中英文雙語對照,買一贈一
作者簡介
D.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3-1930) 20世紀英國傑出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生於礦工之家,畢業於諾丁漢大學,當過屠戶、會計、工廠職員和國小教師,曾在國外漂泊十幾年,對現實持批判態度。在短短20年的寫作生涯中,出版了12部長篇小說,50多篇中短篇小說,多部詩集及大量散文隨筆。著名作品有《虹》《兒子與情人》《戀愛中的女人》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
黑馬:翻譯、作家、編導。著有長篇小說《孽緣千里》《混在北京》(亦在德國出版),散文隨筆集《情系英倫》和《心靈的故鄉》等。《混在北京》改編成同名電影后獲第19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譯有勞倫斯作品《虹》、《袋鼠》《戀愛中的女人》《勞倫斯散文隨筆集》和《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選》等。2000-2001年英國諾丁漢大學勞倫斯中心訪問學者,美國勒迪希國際寫作之家訪問作家,曾在澳大利亞、德國和捷克的大學開設講座。
黑馬:翻譯、作家、編導。著有長篇小說《孽緣千里》《混在北京》(亦在德國出版),散文隨筆集《情系英倫》和《心靈的故鄉》等。《混在北京》改編成同名電影后獲第19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譯有勞倫斯作品《虹》、《袋鼠》《戀愛中的女人》《勞倫斯散文隨筆集》和《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選》等。2000-2001年英國諾丁漢大學勞倫斯中心訪問學者,美國勒迪希國際寫作之家訪問作家,曾在澳大利亞、德國和捷克的大學開設講座。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我們是不健全的,像一人冬天在游泳池旁逡巡不敢下水,只佩服勞倫斯下水的勇氣而已。
——林語堂
勞倫斯的小說,關於人的動作和心理,原是寫得十分周密的,但同時他對於社會環境與自然背景,也一步都不肯放鬆。所以讀他的小說,每有看色彩鮮艷刻劃明晰的雕刻之感。
——郁達夫
對勞倫斯來說,性就是美,所以他這種性描寫,讀起來也是很愉快的。
——余華
勞倫斯是能於無聲處聽見驚雷的人。人最大的悲劇不在外部世界,不是地震,不是海嘯,而在他的內心。勞倫斯臨死前將自己的一生概括為:A savage enough pilgrimage(殘酷的朝聖之旅)。或許就是這種苦難,這種對自己的心靈絕不放過的苛求,造就了文字的力量。
——馮唐
——林語堂
勞倫斯的小說,關於人的動作和心理,原是寫得十分周密的,但同時他對於社會環境與自然背景,也一步都不肯放鬆。所以讀他的小說,每有看色彩鮮艷刻劃明晰的雕刻之感。
——郁達夫
對勞倫斯來說,性就是美,所以他這種性描寫,讀起來也是很愉快的。
——余華
勞倫斯是能於無聲處聽見驚雷的人。人最大的悲劇不在外部世界,不是地震,不是海嘯,而在他的內心。勞倫斯臨死前將自己的一生概括為:A savage enough pilgrimage(殘酷的朝聖之旅)。或許就是這種苦難,這種對自己的心靈絕不放過的苛求,造就了文字的力量。
——馮唐
名人推薦
他是一個天才,居於英國文學的中心,在世界文學中也有他穩定的位置。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
我們是不健全的,像一人冬天在游泳池旁逡巡不敢下水,只佩服勞倫斯下水的勇氣而已。
——林語堂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
我們是不健全的,像一人冬天在游泳池旁逡巡不敢下水,只佩服勞倫斯下水的勇氣而已。
——林語堂
圖書目錄
序言
菊香
乾草垛里的愛情
普魯士軍官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
你摸過我
公主
太陽
愛島的男人
人生之夢
逃跑的公雞
譯者後記
菊香
乾草垛里的愛情
普魯士軍官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
你摸過我
公主
太陽
愛島的男人
人生之夢
逃跑的公雞
譯者後記
後記
雙語作品的出版這兩年成了流行趨勢,說明隨著中國大陸讀者英文水平的不斷提高,他們閱讀的口味和習慣也在變化。大家都想在讀中文譯文時順便看一眼英文原文,比較著欣賞作者原文的魅力。而對於勞倫斯這位20世紀英國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大家已經不滿足於僅僅讀其中文譯文了,更要識其廬山真面目。出版社順應閱讀趨勢,開始推出雙語版,滿足大家更高的鑑賞需求。作為勞倫斯譯者,我感到很幸運和幸福。拙譯從1986年(那一年末我開始陸續發表出版勞倫斯譯文)開始到現在,能伴隨許多讀者走過不同的歷史階段,從單純的中文版一直走到雙語版,我的譯文因為讀者的新需求而煥發出新的生命活力,這是一個譯者莫大的福分。
感到幸福的同時,責任感和使命感也讓我忐忑,那就是我的譯文要對得起原作者勞倫斯大師,也要對得起中文讀者。而過去的譯文多是弱冠和而立之年的少作,以後再版和選人一些文集時,只是匆忙中把中文捋順一遍,或者是增加些註解,沒有足夠的時間做全面的校正。這兩年開始出雙語選集,就得從頭至尾對照英文梳理一遍方可,一是改正錯誤,二是潤色文體。這個工程應該是艱巨的。好在出版商很寬容,而且不用“時間就是金錢”的時代精神鞭策我,給了我相對寬裕的時間來做。
面對少作,時而汗顏,時而驚艷,百味雜陳。
所謂汗顏,是當初暴虎馮河,不知有漢。
如《菊香》,這是開啟了我的勞倫斯閱讀和研究之門的第一篇小說。那是1980年,我們的國家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大學課堂上剛剛開始適度引入一些外國現代作家作品,那之前我們讀的多是狄更斯時代之前的作品,現代名家裡也唯讀過蕭伯納的喜劇。我所就讀的河北大學英語系請來了第一位外教,是剛剛在普林斯頓獲得博士學位的一位年輕美國學者。他為我們開的英國現代文學課教材里選了四位作家的作品,有伍爾夫夫人、曼斯菲爾德、喬伊斯和勞倫斯,我偏偏喜歡上了入選的勞倫斯小說《菊香》,有一種震撼的感覺。20歲的我不滿足於閱讀,還一定要用中文替勞倫斯表達一遍,這小說讓我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欲望,一種替人傳道當牧師的感覺。後來讀了一本勞倫斯的傳記,書名是《愛的牧師》,意思是勞倫斯通過自己的文學創作充當愛的牧師角色。就想,我翻譯他的作品,不就是要充當勞倫斯作品的牧師嗎?即使只是個小小鄉村教堂里的牧師,只要我認真地領會原文,努力用中文再現其魅力,我就是個小牧師——a priest of Lawrence。
還記得那是1981年,在河北大學老圖書館後面亂石亂瓦堆積的地上,有幾棵參天大槐樹,有陰涼,很僻靜,我就坐在小板凳上,膝蓋當桌,偷偷地翻譯(不敢讓別人知道我有做翻譯家的非分企圖)。然後投稿給了《譯海》還是別的雜誌,從此泥牛人海。當時也沒複印機,稿子丟了也就丟了。後來是憑著第一遍的記憶,重新翻譯一遍,直到出書時才拿出來修改了一些地方。現在對照英文看,裡面有些基本的錯誤令我汗顏,有些幼稚的句式令人發噱,但有些精彩的句子還很讓我“驚艷”,這樣的句子我現在絕對翻譯不出來,那是需要青春的衝動才能搜尋出來的漢語對應詞語。所以我說翻譯與創作一樣,一定要早點開始,文字錯誤可以修改,但熱情與幻想是找補不回來的。現在我在給20歲的我當老師,修改那個時候的修辭和文字,但也欣賞自己那個歲數上的衝動。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一文則是我在福建師大畢業前翻譯的,24歲,剛得了碩士學位,離開學校前大家在忙總結,忙鑑定,忙告別,忙整理行囊。12月的福州陽光很溫暖,日子很悠閒無聊。於是我就趁這段空閒,在長安山上面對波光粼粼的閩江,曬著太陽,在野龍舌蘭叢中把這箇中篇小說的初稿翻譯完了,像勞倫斯一樣,我也是把我的文字寫在橫格本上。後來參加工作後,住辦公室,晚上空空如也的辦公室里只有我一個人,就有了時間抄寫出來拿出去發表了。這個東西我感覺是碩士水平的了,但現在看來還是很幼稚。但那些大段的激情色彩的描寫,看起來還是很舒服,估計是我現在翻譯不出來的。
於是我用現在的學識和理性糾正當初的錯誤,但欣賞地保留了很多當年的句子,那是任何學問所不能替代的與青春和熱情有關的肉身之道。在這一點上,翻譯和創作異曲同工。
研究生畢業後我一直以翻譯和文學創作為“己任”,還不時為《文匯讀書周報》等幾家報紙做訪談記者,採訪一些老翻譯家,沒想過要努力當學者,因此發表了幾篇勞倫斯研究方面的論文就再也沒有嘗試進一步做研究。但又要經常讀一些專論,那是為了加深我對勞倫斯文學文本的理解,幫助我翻譯得更準確。因此不敢貿然作研究性的序言,只談些作為譯者的閱讀經驗,沒有高屋建瓴的答疑解惑功用,有些見解並非獨家,而是多年閱讀他的傳記和評論過程中積累下的被我認可的別人的論點,基本上是二手知識綜合,僅比直接的編譯多了一些自己的“消化”和轉述而已。在此我要向很多英語國家的勞倫斯學者致謝,是他們的研究著作滋養了我,培養了我的文學鑑賞眼光,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翻譯的質量。在勞倫斯研究方面,中國學者的起步已經晚於西方學界半個世紀,西方仍以每年上百部的專著出版速度刷新著紀錄,因此作為中國學者,要拿出完全獨立的見解就難免力有不逮,我們唯一的優勢應該是在勞倫斯與中國文學的比較方面,這似乎是目前西方學者難以企及的,為此我期待著能有新晉學人在這方面推出自己的獨立成果。拙譯如果能為這樣的研究提供參考,則是譯者的莫大榮幸。當然,作為藝術品的翻譯作品,我所期待的是廣大讀者的閱讀和批評。
黑馬
2010年10月27日於 北京楊林居
感到幸福的同時,責任感和使命感也讓我忐忑,那就是我的譯文要對得起原作者勞倫斯大師,也要對得起中文讀者。而過去的譯文多是弱冠和而立之年的少作,以後再版和選人一些文集時,只是匆忙中把中文捋順一遍,或者是增加些註解,沒有足夠的時間做全面的校正。這兩年開始出雙語選集,就得從頭至尾對照英文梳理一遍方可,一是改正錯誤,二是潤色文體。這個工程應該是艱巨的。好在出版商很寬容,而且不用“時間就是金錢”的時代精神鞭策我,給了我相對寬裕的時間來做。
面對少作,時而汗顏,時而驚艷,百味雜陳。
所謂汗顏,是當初暴虎馮河,不知有漢。
如《菊香》,這是開啟了我的勞倫斯閱讀和研究之門的第一篇小說。那是1980年,我們的國家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大學課堂上剛剛開始適度引入一些外國現代作家作品,那之前我們讀的多是狄更斯時代之前的作品,現代名家裡也唯讀過蕭伯納的喜劇。我所就讀的河北大學英語系請來了第一位外教,是剛剛在普林斯頓獲得博士學位的一位年輕美國學者。他為我們開的英國現代文學課教材里選了四位作家的作品,有伍爾夫夫人、曼斯菲爾德、喬伊斯和勞倫斯,我偏偏喜歡上了入選的勞倫斯小說《菊香》,有一種震撼的感覺。20歲的我不滿足於閱讀,還一定要用中文替勞倫斯表達一遍,這小說讓我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欲望,一種替人傳道當牧師的感覺。後來讀了一本勞倫斯的傳記,書名是《愛的牧師》,意思是勞倫斯通過自己的文學創作充當愛的牧師角色。就想,我翻譯他的作品,不就是要充當勞倫斯作品的牧師嗎?即使只是個小小鄉村教堂里的牧師,只要我認真地領會原文,努力用中文再現其魅力,我就是個小牧師——a priest of Lawrence。
還記得那是1981年,在河北大學老圖書館後面亂石亂瓦堆積的地上,有幾棵參天大槐樹,有陰涼,很僻靜,我就坐在小板凳上,膝蓋當桌,偷偷地翻譯(不敢讓別人知道我有做翻譯家的非分企圖)。然後投稿給了《譯海》還是別的雜誌,從此泥牛人海。當時也沒複印機,稿子丟了也就丟了。後來是憑著第一遍的記憶,重新翻譯一遍,直到出書時才拿出來修改了一些地方。現在對照英文看,裡面有些基本的錯誤令我汗顏,有些幼稚的句式令人發噱,但有些精彩的句子還很讓我“驚艷”,這樣的句子我現在絕對翻譯不出來,那是需要青春的衝動才能搜尋出來的漢語對應詞語。所以我說翻譯與創作一樣,一定要早點開始,文字錯誤可以修改,但熱情與幻想是找補不回來的。現在我在給20歲的我當老師,修改那個時候的修辭和文字,但也欣賞自己那個歲數上的衝動。
《英格蘭,我的英格蘭》一文則是我在福建師大畢業前翻譯的,24歲,剛得了碩士學位,離開學校前大家在忙總結,忙鑑定,忙告別,忙整理行囊。12月的福州陽光很溫暖,日子很悠閒無聊。於是我就趁這段空閒,在長安山上面對波光粼粼的閩江,曬著太陽,在野龍舌蘭叢中把這箇中篇小說的初稿翻譯完了,像勞倫斯一樣,我也是把我的文字寫在橫格本上。後來參加工作後,住辦公室,晚上空空如也的辦公室里只有我一個人,就有了時間抄寫出來拿出去發表了。這個東西我感覺是碩士水平的了,但現在看來還是很幼稚。但那些大段的激情色彩的描寫,看起來還是很舒服,估計是我現在翻譯不出來的。
於是我用現在的學識和理性糾正當初的錯誤,但欣賞地保留了很多當年的句子,那是任何學問所不能替代的與青春和熱情有關的肉身之道。在這一點上,翻譯和創作異曲同工。
研究生畢業後我一直以翻譯和文學創作為“己任”,還不時為《文匯讀書周報》等幾家報紙做訪談記者,採訪一些老翻譯家,沒想過要努力當學者,因此發表了幾篇勞倫斯研究方面的論文就再也沒有嘗試進一步做研究。但又要經常讀一些專論,那是為了加深我對勞倫斯文學文本的理解,幫助我翻譯得更準確。因此不敢貿然作研究性的序言,只談些作為譯者的閱讀經驗,沒有高屋建瓴的答疑解惑功用,有些見解並非獨家,而是多年閱讀他的傳記和評論過程中積累下的被我認可的別人的論點,基本上是二手知識綜合,僅比直接的編譯多了一些自己的“消化”和轉述而已。在此我要向很多英語國家的勞倫斯學者致謝,是他們的研究著作滋養了我,培養了我的文學鑑賞眼光,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翻譯的質量。在勞倫斯研究方面,中國學者的起步已經晚於西方學界半個世紀,西方仍以每年上百部的專著出版速度刷新著紀錄,因此作為中國學者,要拿出完全獨立的見解就難免力有不逮,我們唯一的優勢應該是在勞倫斯與中國文學的比較方面,這似乎是目前西方學者難以企及的,為此我期待著能有新晉學人在這方面推出自己的獨立成果。拙譯如果能為這樣的研究提供參考,則是譯者的莫大榮幸。當然,作為藝術品的翻譯作品,我所期待的是廣大讀者的閱讀和批評。
黑馬
2010年10月27日於 北京楊林居
序言
收入本書的10篇中短篇小說,按照一些較為權威的學者理論,分別劃歸勞倫斯的三個創作階段,即早、中、晚三期。
一
《菊香》、《乾草垛中的愛》和《普魯士軍官》屬於1907—1914年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期勞倫斯的長篇小說代表作是((白孔雀》和《兒子與情人》,也就是以寫實和自然主義為特徵的創作時期。這個時期的勞倫斯先是在諾丁漢大學讀師範班時開始練筆,後來是在倫敦郊區的克羅伊頓鎮當國小教師時開始給新興的左派文學刊物《英國評論》投稿,一手詩歌,一手小說(勞倫斯的文學起點十分之高,他是以詩人和長篇小說作家,即novelist為己任的,因此出手就是一部長篇小說《白孔雀》。只是因為《英國評論》看重他的才華,不斷約稿,他才開始較多地涉獵短篇寫作,並高超地發揮出了這種潛能),成為倫敦年輕作家裡的新星,而且作為來自礦工家庭的怍家,他被視為難得的“天才”,其作品的活力對蒼白浮華的小資產階級作家文風來說是一種強有力的滌盪和震撼。
20世紀初葉,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仍是小說寫作的主流,勞倫斯寫作初期繼承的是以哈代和喬治·愛略特為代表的浪漫寫實主義風格,但又有所創新,從一起步就在繼承傳統寫實主義的同時向現代派借鑑,雖然最終並沒有完全成為後來人們推崇的典型的那一批現代派作家,如喬伊斯、普魯斯特、T.S.艾略特和伍爾夫夫人,但卻另闢蹊徑,自成一家。按照寫作時間算,勞倫斯頗具現代主義意義的長篇小說《戀愛中的女人》其實是早於現代主義的代表作《荒原》出版的。多少年後,人們評論勞倫斯時把《戀愛中的女人》說成是小說里的《荒原》,這應該指的是兩者在精神和氣質上的契合,儘管《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從來都睥睨勞倫斯。
《乾草垛中的愛》應該說是老套的寫實主義作品,從中可以看出哈代和喬治·愛略特的影響:一幅幅濃淡相宜的英國鄉村風景畫如瓊漿佳釀般醉人,淳樸幽默的20世紀初英國農民形象躍然紙上。讓我們想到福克斯所言,勞倫斯是“了解英國鄉村和英國土地之美的最後一位作家”。但勞倫斯在這個基礎上有所突破和創新,因為他更與這溫馨風景中的英國勞動者心靈相通、血脈相連。這樣的景物中一個平實溫婉的愛情故事,其高度藝術化的傳達使文本的閱讀享受大大超越了故事本身,成為對英國鄉村審美的親歷和對英國鄉民心靈的造訪。在這個故事裡,勞倫斯已經開始注重揭示人物的潛意識,因此而部分地放棄了嚴密的敘事形式,敘事結構趨於鬆散,情節及其發展並沒有傳統小說里的縝密邏輯和因果關係,一些看似次要的段落反倒成為揭示人物內心的重要線索。恰恰是這種現代敘事形式賦予了這個傳統故事以閱讀的魅力,否則它就流於一般,僅僅是“鄉村和土地之美”的牧歌而已。 ……
如果說《人生之夢》是勞倫斯藉助伊特魯里亞文明的因子對英國生活的建設性表現,《逃跑的公雞》則是他藉助弗雷澤的《金枝》對耶穌基督的顛覆性表現和解構一重塑,復活的耶穌與女神愛茜絲的女祭司的性愛在1928年的人們看來完全是瀆神的筆法。不要忘記,這箇中篇是寫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邊上的小說,可以說與這個長篇交相輝映,相得益彰。一個是人的復活,一個是神的復活;一個是人在大戰後的歐洲廢墟上營造著性愛的天國,一個是耶穌基督拯救人類失敗後走下神壇,還原肉體的男人本身。耶穌基督復活後陷入了沉重的反思:“我試圖強迫他們活,所以他們就強迫我死。總是這樣,強制。退縮毀滅了前進。現在我該獨處了。”
他甚至反思自己前生對人類的愛和被愛:“說了半天,我是想讓他們用死的肉體來愛。如果我是以活生生的愛來親吻猶大,或許他永遠也不會以死來吻我。或許他對我的愛是肉體的愛,可我卻以為這愛跟肉體無關,是殭屍之愛——”
勞倫斯在最後的小說中仍然在扮演“愛的牧師”角色,這一次,他藉助耶穌的復活對正統的基督教精神進行了修正,為它注入血肉,補充肌理,因為它趨於否定肉體生命並迴避“肉體的復活”之說。
勞倫斯二十來歲上以一個短篇小說《序曲》獲得《諾丁漢衛報》徵文獎,並開始在文學上嶄露頭角,以((逃跑的公雞》(又名《死去的人》)落幕,似乎這是上天的刻意安排。以詩人和長篇小說作家為己任的他誤打誤撞進入短篇小說的創作領域,不期亦成大家,同樣領其風騷。其中短篇小說精緻、洗鍊,反倒避免了他在長篇小說里因其篇幅之長而容易出現的大段的人物說教,讀之更賞心悅目,自成風流。其五十多個短篇被認為是從笨拙純潔的寫實主義到精心鋪陳的現代主義到高蹈飄逸的後現代主義的完整歷程。無論什麼主義,都是論者各自的觀點,作為讀者,我們關注的是勞倫斯作品對我們的情感產生的衝擊,關注的是讀了他的作品我們的內里有什麼樣的改變,用文化學大師霍加特的話說:讀了這樣的小說,我們對自己人格潛流的感覺從此變了。它改變了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我們與他人之間關係的方式,看待社會的方式,看待時間與代際、家庭與地域和空間的方式。總之,這樣的小說符合勞倫斯自己給小說下的定義:“閃光的生命之書。”
一
《菊香》、《乾草垛中的愛》和《普魯士軍官》屬於1907—1914年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期勞倫斯的長篇小說代表作是((白孔雀》和《兒子與情人》,也就是以寫實和自然主義為特徵的創作時期。這個時期的勞倫斯先是在諾丁漢大學讀師範班時開始練筆,後來是在倫敦郊區的克羅伊頓鎮當國小教師時開始給新興的左派文學刊物《英國評論》投稿,一手詩歌,一手小說(勞倫斯的文學起點十分之高,他是以詩人和長篇小說作家,即novelist為己任的,因此出手就是一部長篇小說《白孔雀》。只是因為《英國評論》看重他的才華,不斷約稿,他才開始較多地涉獵短篇寫作,並高超地發揮出了這種潛能),成為倫敦年輕作家裡的新星,而且作為來自礦工家庭的怍家,他被視為難得的“天才”,其作品的活力對蒼白浮華的小資產階級作家文風來說是一種強有力的滌盪和震撼。
20世紀初葉,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仍是小說寫作的主流,勞倫斯寫作初期繼承的是以哈代和喬治·愛略特為代表的浪漫寫實主義風格,但又有所創新,從一起步就在繼承傳統寫實主義的同時向現代派借鑑,雖然最終並沒有完全成為後來人們推崇的典型的那一批現代派作家,如喬伊斯、普魯斯特、T.S.艾略特和伍爾夫夫人,但卻另闢蹊徑,自成一家。按照寫作時間算,勞倫斯頗具現代主義意義的長篇小說《戀愛中的女人》其實是早於現代主義的代表作《荒原》出版的。多少年後,人們評論勞倫斯時把《戀愛中的女人》說成是小說里的《荒原》,這應該指的是兩者在精神和氣質上的契合,儘管《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從來都睥睨勞倫斯。
《乾草垛中的愛》應該說是老套的寫實主義作品,從中可以看出哈代和喬治·愛略特的影響:一幅幅濃淡相宜的英國鄉村風景畫如瓊漿佳釀般醉人,淳樸幽默的20世紀初英國農民形象躍然紙上。讓我們想到福克斯所言,勞倫斯是“了解英國鄉村和英國土地之美的最後一位作家”。但勞倫斯在這個基礎上有所突破和創新,因為他更與這溫馨風景中的英國勞動者心靈相通、血脈相連。這樣的景物中一個平實溫婉的愛情故事,其高度藝術化的傳達使文本的閱讀享受大大超越了故事本身,成為對英國鄉村審美的親歷和對英國鄉民心靈的造訪。在這個故事裡,勞倫斯已經開始注重揭示人物的潛意識,因此而部分地放棄了嚴密的敘事形式,敘事結構趨於鬆散,情節及其發展並沒有傳統小說里的縝密邏輯和因果關係,一些看似次要的段落反倒成為揭示人物內心的重要線索。恰恰是這種現代敘事形式賦予了這個傳統故事以閱讀的魅力,否則它就流於一般,僅僅是“鄉村和土地之美”的牧歌而已。 ……
如果說《人生之夢》是勞倫斯藉助伊特魯里亞文明的因子對英國生活的建設性表現,《逃跑的公雞》則是他藉助弗雷澤的《金枝》對耶穌基督的顛覆性表現和解構一重塑,復活的耶穌與女神愛茜絲的女祭司的性愛在1928年的人們看來完全是瀆神的筆法。不要忘記,這箇中篇是寫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邊上的小說,可以說與這個長篇交相輝映,相得益彰。一個是人的復活,一個是神的復活;一個是人在大戰後的歐洲廢墟上營造著性愛的天國,一個是耶穌基督拯救人類失敗後走下神壇,還原肉體的男人本身。耶穌基督復活後陷入了沉重的反思:“我試圖強迫他們活,所以他們就強迫我死。總是這樣,強制。退縮毀滅了前進。現在我該獨處了。”
他甚至反思自己前生對人類的愛和被愛:“說了半天,我是想讓他們用死的肉體來愛。如果我是以活生生的愛來親吻猶大,或許他永遠也不會以死來吻我。或許他對我的愛是肉體的愛,可我卻以為這愛跟肉體無關,是殭屍之愛——”
勞倫斯在最後的小說中仍然在扮演“愛的牧師”角色,這一次,他藉助耶穌的復活對正統的基督教精神進行了修正,為它注入血肉,補充肌理,因為它趨於否定肉體生命並迴避“肉體的復活”之說。
勞倫斯二十來歲上以一個短篇小說《序曲》獲得《諾丁漢衛報》徵文獎,並開始在文學上嶄露頭角,以((逃跑的公雞》(又名《死去的人》)落幕,似乎這是上天的刻意安排。以詩人和長篇小說作家為己任的他誤打誤撞進入短篇小說的創作領域,不期亦成大家,同樣領其風騷。其中短篇小說精緻、洗鍊,反倒避免了他在長篇小說里因其篇幅之長而容易出現的大段的人物說教,讀之更賞心悅目,自成風流。其五十多個短篇被認為是從笨拙純潔的寫實主義到精心鋪陳的現代主義到高蹈飄逸的後現代主義的完整歷程。無論什麼主義,都是論者各自的觀點,作為讀者,我們關注的是勞倫斯作品對我們的情感產生的衝擊,關注的是讀了他的作品我們的內里有什麼樣的改變,用文化學大師霍加特的話說:讀了這樣的小說,我們對自己人格潛流的感覺從此變了。它改變了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我們與他人之間關係的方式,看待社會的方式,看待時間與代際、家庭與地域和空間的方式。總之,這樣的小說符合勞倫斯自己給小說下的定義:“閃光的生命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