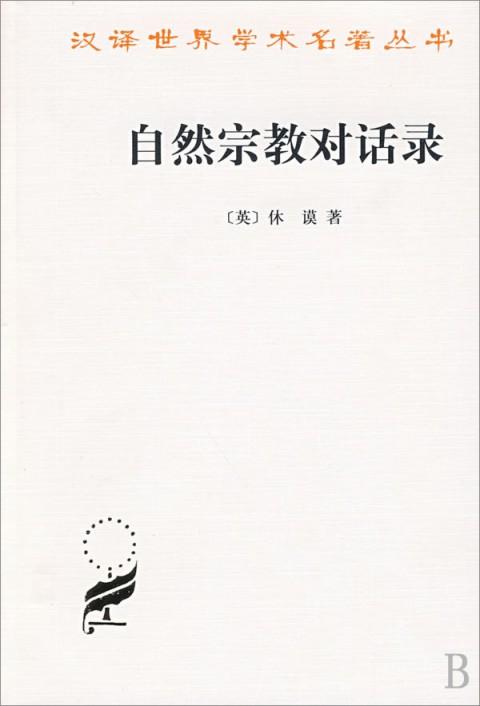《自然宗教對話錄》是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創作的宗教神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779年。
這本書的主題是駁斥當時流行的宗教假設,也就是宇宙設計論,設計論是當時宗教理論的中心支柱。休謨接受了柏克萊的觀點,認為一切知識都以經驗為來源,而經驗是沒有客觀內容的。因此,在心靈面前,除了知覺以外,就再也沒有任何事物了。休謨得出這樣結論: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覺、感覺,此外是否有真實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知道的。休謨的不可知觀點是徹頭徹尾的。他不僅懷疑客觀實體在物質上的存在,同時也懷疑它在精神上的存在。
《自然宗教對話錄》代表休謨晚年較成熟的哲學思想。該書一直是討論有關用來證明上帝存在及其屬性特點的證據的性質的經典作品之一。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自然宗教對話錄
- 外文名稱: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 作者:【英】大衛·休謨
- 類別:宗教神學
- 首版時間:1779年
- 字數:約60000
內容簡介,創作背景,作品思想,後世影響,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自然宗教對話錄》仿效西塞羅論述同一主題的著作《神的本質》,在後面這本書里,一個斯多亞派學者,一個伊壁鳩魯主義者和一個懷疑論者討淪神的本質和存在的各種證明。西塞羅和休謨都認為對話的形式使他們能夠討論這些“危險”的題目而他們個人不必對任何具體的觀點承擔責任。他們可以讓他們的主人翁去攻擊各種為人接受的論證和立場,而他們自己不必贊同或拒絕任何特定的宗教觀點。
休漠《自然宗教對話錄》的開篇是這場討論的旁觀者青年潘斐留斯寫給他的友人赫未柏斯的一封信。潘斐留斯解釋說,對話的形式是極其適合於討論神學的,一方面因為這個題目涉及到上帝存在的學說,後者很顯然不允許任何的質疑,而另一方面它導致關於上帝的性質、他的屬性,命令和計畫的極端晦暗和不定的哲學問題。對話的形式大概能夠既諄諄教誨“明顯的”真理,又揭露了各種困難。
在第一篇里斐羅和克里安提斯爭論了懷疑論的優點之後,休漠描寫斐羅和正統的狄美亞同意人類的理性不適於領會神的真理。他們一致同意下面的觀點:神性的存在是無可懷疑的。斐羅總結了這個情況,他斷言,人們的觀念全部以經驗為基礎,人們沒有任何關於神的屬性和作用的經驗。這樣,最高存在的性質是不可領會的和神秘的。
克里安提斯立刻予以反駁並陳述了休謨在整個《自然宗教對話錄》中詳加分析的理論。克里安提斯堅決認為,人們所具有的關於自然世界的聞識和明證能夠使人們推斷上帝的存在和性質。他然後表述了所謂的“設計論論證”,這種論證在古代和近代的神學討論中十分流行,但是它以伊薩克·牛頓爵士的表述形式變得極端大眾化了。克里安提斯則稱,看著世界,你將會看到,它無非是一架區分為許多小機器的巨大機器。所有的部分都彼此配合,所以這整個巨大的複合體和諧一致地運行著。這種貫穿於全自然之中的手段對於目的的適應與產生於人類設計和理智的適應精確相似。因為自然的對象與人類的產物彼此相似,所以人們根據類比推出其原因也必定是彼此相似的。因此,自然的作者必定與人的心靈是相似的,雖然他必定擁有更為巨大的能力,因為他的產物更為偉大。
在第三篇,克里安提斯堅持認為, 自然作品與人類藝術作品的相似是不證自明的和無可否定的。當人們按照最新的科學知識來考察自然的不同方面時,人們達到的最明白的結論是這些方面必定是設計的結果。通過引證幾個例子,克里安提斯試圖表明設計論論證的巨大的似是性。
斐羅在第六篇至第八篇中堅持認為,除了設計者的解釋外還可提出其他的解釋來說明世界中的秩序,這些另外的替代者也能被證明至少是可能的,他考慮了兩種理論,其中一種理論認為,秩序產生於生殖或生長過程,而另一種理論認為秩序恰好是物質微粒聚集方式的偶然結果。
狄美亞在第九篇極力主張,先天的理性論證不依賴於無論何種經驗的信息,這種論證表明:必定有一個神聖的存在。狄美亞論述說,關於必定有第一因或上帝的經典神學論證說明了發生在這個世界中的原因次序。休謨讓克里安提斯來質疑這個論證,方式是引用休漠在其《人性論》和《人類理智研究》中已提出來的某些關於因果關係的懷疑淪論點和先天論證的非決定性的觀點。而且,休謨指出,即使先天的東西是合法的,即使它實際上證明了必定有一個第一因,或必然實存的存在,它依然不能證明這個存在非得是上帝。或許這個物質的世界自身就是第一因,它自身的原因。
休謨以這個批評結束了他關於旨在於證明上帝存在的論證考察,轉到就上帝的性質或屬性能知道些什麼的問題上面。在第十篇的開頭,斐羅和狄美亞狂熱地談論人的苦難和軟弱,狄美亞把它們描敘為人為什麼必須尋求上帝保護的原因。斐羅用關於人類境況的同樣材料指出,我們無法從正發生在人類世界中的事情里推出神性的道德品質。
克里安提斯在第十一篇論辯道,如果人們回到他關於人和神的類比上去,就能做出一種解釋。如果自然的作者只是有限在完善的,那么這個宇宙中的不完善性就能通過歸於他的限制來說明。斐羅接著論證道,現在的經驗沒有給任何關於神的道德屬性的推論提供任何的基礎,人們愈是認識到人的弱點,人們就愈不能斷然贊成關於這個世界是由一個善的和仁慈的神統治的宗教假設。
當斐羅揭示出四種可能性並廳起來傾向於最後一種可能性時,狄美亞惶恐地認識到他和斐羅並不真正地一致。狄美亞強調上帝的不可理解的性質,強調人類理智慧型力的軟弱,強調人類生活的悲慘是接受正統神學的基礎。斐羅用同樣的觀點導出了不可知論的結論:由於我們的性質和上帝的性質,我們不可能知道他實際上是什麼樣的,我們亦不可能知道是否有關於這個所經驗到的世界特徵的任何說明和正當理由。當狄美亞明白了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多么的寬闊之後,他便退出了討論,斐羅和克里安提斯仍然留在那裡評價他們論證的結論。
在最後一篇,即第十二篇,斐羅提出了被認為是休謨自己的宗教觀點的概要。自然裡面處處都有設計的明證。斐羅指出,“我依然無法獲知設計者的道德特徵。來自這個可觀察的世界的明證是,自然的作品與我們的人工產品而非我們的仁慈的或善的行為更加相似。因此,我們有更充足的理由堅持認為神的自然屬性與我們自己的自然屬性相似,而不是堅持認為他的道德屬性與人類的美德相似。”結果,斐羅贊成一種非道德的,哲學的和理性的宗教。
1776年休謨增加了最後的一段辯論總結“自然神學的全部,……能夠包括在一個簡單的、不過是有些含糊的、至少是界限不明確的命題之內,這命題是,宇宙中秩序的原因或諸原因與人類理智可能有些微的相似。”沒有什麼更多的東西可以說的了,有關原因或者原因的道德特徵尤其如此。
對話以兩段令人迷惑不解的評論作為結束。斐羅發表了他臨別前的意見:“在學術人士之中,做一個哲學的懷疑主義者是做一個健全的,虔信的基督教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
在這篇對話的最後,休謨讓潘斐留斯來評論整個討論,他說:“斐羅的原則比狄美亞的原則更有可能性,而克里安提斯的原則還要更為接近真理。”
創作背景
休漠在他那個時代以“偉大的不信仰宗教者”聞名,他在1751年左右著手寫《自然宗教對話錄》。他把他的手稿給幾個朋友看過,他們因其反宗教的內容而勸他不要出版。在幾年內,他數易其稿,最後,在1776年他去逝之前才改定此稿。他非常掛心於落實此著會在他死後不久出版。休謨最初在他的遺囑中,要求他的朋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安排出版《自然宗教對話錄》。當斯密予以拒絕時,休漠改變了他的遺囑,指示他的外甥,如果出版社在他死後兩年還未出版此著,就由他來處理此事。此著最終於1779年出版。
作品思想
《對話錄》是採取對話的形式寫成的。採取這種形式寫作學術著作,無疑會受到古代柏拉圖等人的影響。從休謨本人來說,在這部有關哲學和宗教問題的,最晚完成的著作中,之所以採取對話的形式,這也由於他後來認識到,這種寫作形式具有自身的優點。這一認識體現在1751年;3月10日致友人埃利奧特的一封信中。在這封信中,他在提到已將寫完的《對話錄》寄給收信人時,還談到他為什麼要採取對話的方式來寫這一著作。他說,他對此的想法是:運用對話的方式,使得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充分陳述自己的觀點,並相互進行駁難,這有助於人們認識,並避免或克服一些“流行的錯誤”。
《對話錄》中的對話人有三位:克里安提斯、狄美亞和斐羅。他們分別代表了宇宙設計論者、天啟論者和休謨本人的觀點。在對話中,休謨的代言人斐羅站在懷疑論立場上,對克里安提斯所代表的宇宙設計論,及狄美亞所代表的天啟論觀點的錯誤,進行了揭露和批判。當然,作為對當時實際情況的反映,狄美亞和克里安提斯之間也進行了一定的鬥爭。
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對“自然宗教”的辯破主要環繞著兩個重要的議題:設計論和神義論。休漠對“設計論”的辯破主要在《自然宗教對話錄》的第二至四篇;對是“神義論”的辯破則主要在《自然宗教對話錄》的第十至十一篇。
一、對宇宙設計論的批判
按照休謨在《對話錄》中的論述,宇宙設計論是這樣一種理論,即主張整個宇宙以及其中的每一個大大小小的部分,都是一些大小不同的機器。“這些各式各樣的機器,甚至它們的最細微的部分;都彼此精確地配合著”。這種大自然中的各種存在物彼此之間精確配合的程度,雖然遠遠超過由人類設計和製造的各種產品相互之間精確配合的程度,但二者之間卻極為“相似”。由此,設計論者便進行推論:自然界中的存在物與人工產品,作為結果既然彼此相似,那么,根據類比的原則,就可推知,產生它們二者的原因,彼此也是相似的。既然人工產品是出於精神性的“心靈和理智”的設計和製造,那么,整個自然界及其中的萬事萬物的存在,也必然是出於類似於人的心靈和理性的精神性的東西的設計與安排。由此也便得出了“神與人相似”的結論。這不但論證了上帝的存在,而且還論證了上帝是類似於人的心靈的精神性的存在物。
為宇宙設計論者所主張的這種最後導向“神與人相似”結論的設計論觀點,在其提出後便遭到了天啟論者的反對。這在《對話錄》第二篇就有反映。天啟論者反對的理由是:設計論者對上帝的存在所作的證明,屬於後天的證明。它依據的是人類後天的不可靠的感覺經驗,而且最後還得出了神與人相似的結論。這就不但不能有力地論證上帝存在的必然性,而且還“隱含著對於至高存在的貶抑”。在他們看來,設計論者的論證方法的不可取還在於:它會被無神論者利用來最終否認至高無上的上帝的存在。
在休漠的“自然宗教”討論中,除了“設計論”外,還有“神義論”。所謂“神義論”是“指為上帝的公正性進行辯護的學說。源於希臘語theos(神)和dike(公正)。其目的是為了協調基督教的上帝全能和仁慈的教義與世間存在的罪惡現實的矛盾。該學說最早由古羅馬奧古斯丁較系統的提出。認為上帝只創造善的東西,惡並非出自上帝。只有當本質上為善的人類濫用了上帝賦予的自由而變得腐
敗和墮落時,世界上才有惡出現。“神義論”的說法主要是維護著人普遍心裡既有宗教傾向的心理,
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狄美亞說:“每個人亦可謂是在他自己的心裡感覺到宗教的真理;是由於他感覺到自己的懦弱和不幸,不是由於任何的推理,才引他去追尋人及萬物所依賴的那個“存在”的保佑。生活中即使是最好的景況也是如此的懊惱和煩厭,所以未來始終是所有我們的希望和畏懼的對象。我們不息地向前瞻望,又用祈禱、禮拜和犧牲,來求解那些我們由經驗得知的,足以折磨和壓迫我們的不知的力量。我們是多么可憐的生物啊!假如宗教不提出些贖罪的方法,並且平服那些不息的刺激和磨難我們的恐怖,那么在這人生的數不清的災難之中,我們有什麼辦法呢?”甚至乎,連一直抱持懷疑主義的斐羅也指出:“我確是相信,使每個人得到確當的宗教感的最好的而且實在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對於人類的悲慘和邪惡作恰當的描述。為著這個目的,一種雄辯和豐富的想像的才能,比起推理和論證的才能來,更為需要。因為不是有必要去證明每個人內心的感覺嗎?有必要的只是使我們,假如可能的話,更親切地和更銳敏地感覺我們內心所感覺到的。”換言之,個人在內心的宗教傾向是緣於從人類面對世事的悲慘與無奈而產生的,“神義論”的說法正好是鞏固宗教中的上帝的神聖性及解釋世間的悲慘問題,為個人在內心的宗教傾向作出了一個既能保存“上帝”的完善性質,又能平衡經驗中的“惡”悲慘之出現。
然而,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卻認為“神義論”的說法也是有問題的。
從觀念來說,“神義論”是荒謬的,即“上帝”既然是完美的,又怎可能容許“惡”與悲慘的出現呢?斐羅說:“我們承認他的力量是無限的,凡是他所意欲的都實現了,但是人類及其他動物都是不幸的,足見他並不意欲人及其他動物的幸福。他的智慧是無限的:他從不會在選擇達到目的的手段中出錯,但是自然的歷程並不傾向於人類或動物的幸福,足見自然的歷程並非為這個目的而設的。在人類知識的全部領域中,再沒有比這些推論更可靠,更無謬誤的了。”“他願意制止罪惡,而不能制止嗎?那么他就是軟弱無力的。他能夠制止,而不願意制止嗎?那么他就是懷有惡意的。他既能夠制止又願意制止嗎?那么罪惡是從那裡來的呢?”這樣看來,“神義論”至少不能為“上帝的屬性”作出恰當的說明。
休謨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通過對設計論、神義論的批判,竭力把道德屬性從“上帝”那裡撤除。而且,休謨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不僅僅是把上帝請出了道德領域,他也把一些重要的原則引入了倫理政治領域。首先,休謨讓自然神論者克里安提斯提出了“真宗教”的標準:“宗教的正當職務在於規範人心,使人的行為人道化。灌輸節制、秩序和服從的精神;由於它的作用是潛移默化,只在於加強道德與正義的動機,它就有被忽略以及和這些其他動機混淆的危險。當它自己獨立一格,作為一個獨立的原則來控制人類,那么它就離開了它的正當範圍,而只變成內亂和野心的掩護了”。其次,休謨讓懷疑論者斐羅在上述標準之外作了一個補充——做一個哲學上的懷疑主義者是做一個虔信的基督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一步,斐羅的意圖,一方面要防止克里安提斯在設計論上得出超出因果聯繫的結論,尤其是把道德屬性賦予上帝;另一方面要防止正統神學中那些傲慢的獨斷論者。
後世影響
《自然宗教對話錄》代表休謨晚年較成熟的哲學思想。這本書的主題是駁斥當時流行的宗教假設,也就是宇宙設計論(簡稱設計論);設計論是當時宗教理論的中心支柱,駁斥了設計論,客觀上就給予宗教本身以一衝沉重的打擊。休謨對宗教的批判既影響了法國啟蒙思想家,為他們所利用和受到他們的重視;也影響了康德,把康德“從獨斷的迷霧中驚醒”,康德也認為上帝的存在與否不能從理性得到證明,它只能是信仰的對象。設計論流行於18世紀,經過休謨的批判,康德的傳播,設計論在學術思想界再也站不住腳,此後也就不再有人以這一類的論證來證明上帝的存在。
作者簡介
大衛·休謨(David Hume),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是經驗主義哲學心理學代表之一,歐洲近代不可知論的主要代表。1711年5月7日生於蘇格蘭愛丁堡,卒於1776年8月25日。11歲進愛丁堡大學。1729年起專攻哲學。1732年剛滿21歲就開始撰寫他的主要哲學著作《人性論》,1734年去法國自修 ,繼續哲學著述。1748年出使維也納和都靈。1749年回家鄉,潛心著述。1751年移居愛丁堡市。1763年任駐法使館秘書;1765年升任使館代辦。1767~1768年任副國務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愛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