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怒濤,四川南川人,1927年8月南京中央軍校第七期,後任國民革命軍成都中央軍校辦公廳副官處少將副處長
生平參加過各種戰役。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羅怒濤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四川南川
- 出生日期:1906
- 職業:國民革命軍成都中央軍校辦公廳副官處少將副處長
- 畢業院校:南京中央軍校
相關信息,人物生平,啟蒙興隆堡,從戎黃埔校,建功古北口,血戰台兒莊,戍邊滇東南,受降赴越南,從職副官處,入編軍政大,退伍陷深潭,屈辱離人世,十一、遲到的緬懷,
相關信息
羅怒濤,四川南川人,1927年8月南京中央軍校第七期,後任國民革命軍成都中央軍校辦公廳副官處少將副處長
人物生平
(1906年—1958年):
1906年出生於四川省南川縣鳴玉鄉興隆堡(今重慶市南川市鳴玉鎮興隆村)。
1928年初春,赴南京報考黃埔軍校,入預科學習和接受訓練。
1929年春,正式編入南京黃埔軍校第七期學生第一總隊步兵大隊第四隊。
1929年12月28日畢業於南京黃埔軍校第七期。隨後在國民革命軍第4師獨立旅相繼擔任排、連長。
1933年擔任第25師第73旅146團9連(即原第4師2團9連)連長,3月在古北口抗日保衛戰中,英勇作戰身負重傷,被送往北平協和醫院醫治療槍傷。
1937年9月參加保定抗日戰役。
1938年3月至4月,參加台兒莊血戰,任第52軍第25師146團營長,指揮戰士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切斷日軍的增援,使其救援台兒莊的計畫落空。
1938年夏秋之交,參加武漢保衛戰。
1939年秋,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取得湘北大捷等。
1941年2月兒子羅翹楚(現名羅橋礎)在湖南省零陵縣(今永州市零陵區)普愛醫院出世。
1941年由湖南經桂入滇,進駐文山,擔負滇東南一帶的邊防任務。任第九集團軍第25師第73團副團長、團長;其間曾一度擔任第九集團軍中校參謀。在雲南駐防期間,曾被派往緬甸邊境的八莫、密支那等處參加中美合辦的軍官培訓班學習,提高軍事指揮素質。
1942年7月女兒羅羨蓉在雲南出世。
1945年7月兒子羅芷村(現名羅喬敏)在雲南蒙自縣芷村火車站出世。
1945年任第九集團軍第2師4團上校團長,9月奉命率部由滇東南開往越南,先後在河內、海防駐守,解除日軍武裝,接受日本侵略軍的投降。
1947年,脫離國民黨正規部隊後,經關麟徵引薦進入成都陸軍軍官學校任副官處少將副處長。
1949年冬,隨成都陸軍軍官學校第一、三總隊參加起義。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教導三隊(原名十八兵團隨校),1950年4月,第十八兵團建制奉命撤銷後,被編入西南軍政大學川西分校。
1952年秋季,退伍復員回三台縣定居。
1954年么女羅小蓉在三台縣出世。
1958年秋,被強制送往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一個月後含冤去世。
1985年5月經三台縣人民政府確認其起義軍人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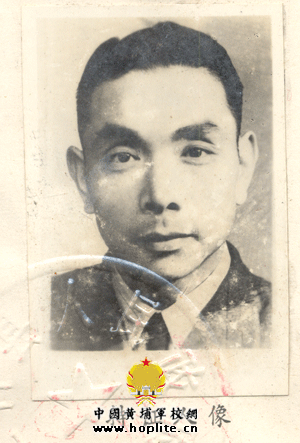
啟蒙興隆堡
父親原名羅德馨,四川省南川縣人。1906年出生在南川縣鳴玉鄉興隆堡。南川縣地處川東南,東接武隆,西靠重慶,北通涪陵,東南及南邊緊靠貴州大山區。從南川縣城往正北方向沿著公路步行大約三十公里,便來到鳴玉鄉(即鳴玉鎮),這是南川通向涪陵最捷近的一條路。
鳴玉鄉置身淺丘山地,屬於窮鄉僻壤。從鳴玉鄉往東翻山越嶺經山間小道徒步幾公里便來到位於溪流旁的一個小村寨-興隆堡,池塘邊有座羅家大院。父親幼年時代在這裡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四書、五經以及《古文觀止》等。辛亥革命成功後,父親被送入鳴玉鄉開辦的新學讀高小,接受新思想的薰陶。不到二十歲,父親遵照父母之命娶王氏為妻,並添一子羅純武(父親離家考入黃埔軍校不久,王氏病故)。隨著年齡的增長,父親帶著渴求新知的欲望,常常徒步到鳴玉場鎮或南川縣城接受社會新思潮。
從戎黃埔校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腐敗的滿清王朝,動搖了封建統治的社會根基,民主救國的新思想開始在全國各地傳播,特別是1919年北京爆發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傳到川東,在年青人心中燃燒起理想的火焰。當時父親正值十多歲的少年,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父親逐漸成長起來。受北伐戰爭洪流的影響,廣州黃埔軍校招生的訊息傳到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青年投筆從戎,紛紛南下廣州報考黃埔軍校立志從軍報國。
1928年1月30日正值農曆正月初八,21歲的父親辭別他的父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以及不滿周歲的兒子(羅純武),毅然投筆從戎。血氣方剛的父親滿懷豪情壯志將羅德馨改名為羅怒濤,誓將自己變為“怒濤”蕩滌封建桎梏和軍閥勢力,足見父親的人生追求和革命氣概。父親冒著嚴寒,從南川步行到涪陵,經涪陵乘船到武漢,準備跋山涉水南下,遠去廣州報考孫中山創辦的“黃埔軍校” 。在武漢一家飯館裡吃飯時,從鄰桌几個年輕人的交談中得知: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形勢發展了變化,黃埔軍校正在遷校到南京,更名為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父親於是改變計畫,繼續搭乘輪船直接趕到南京報考軍校。經過體檢和考試,1928年初被錄取為預科生,在杭州接受入伍訓練,1928年冬預科生開赴南京,於1929年初春正式分科編班成為黃埔第七期學員。黃埔7期分步兵、騎兵、炮兵、工兵4科,父親被編入學生第一總隊步兵大隊第四隊。 從預科開始,前後經過兩年時間,第7期學員總計852人於1929年12月28日畢業。父親時年二十三歲。隨後在國民革命軍第4師獨立旅中相繼擔任排、連長。
父親自告別家鄉投筆從戎之後,一別便是18年,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於1946年帶著我的母親及五歲的我回到南川老家祭祖。離家這段時間父親忙於抗戰抵禦外辱,在他的父母過世之時也未能回家盡孝,只能多次匯錢回家表示孝心。
建功古北口
壯士碧血灑疆場,驍將拚死克日寇。1933年1月,日寇侵占山海關後,直逼平津。緊接著中日之間的戰役在北京東北密雲縣的古北口打響。古北口保衛戰從3月6日交戰以來,中方第107師、第112師和第25師各部與日軍鏖戰一周,牢牢固守住陣地,斃傷敵人2,000人以上,日軍受到沉重打擊。但是由於日軍裝備精良,在侵華戰爭中實戰經驗豐富,又有飛機、坦克及重炮火力的配合,因此,古北口各守軍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父親所在的第25師浴血奮戰3天,師長關麟征、旅長梁愷負傷,團長陣亡負傷各1名,連排長死傷達3/4,全師官兵傷亡總數達4,000餘人,其戰鬥之慘烈可以想見。
在古北口保衛戰中,父親時年26歲,擔任國民革命軍第25師第73旅146團9連連長(即原第4師2團9連),帶著對日寇的深仇大恨,率部擔負第二道防線左邊陣地的守護任務。冒著遭遇日寇飛機轟炸的危險,帶領士兵挖築工事,由於陣地是堅硬的岩石禿山,構築工事難度很大,他用民族危亡的警訓鼓動起士兵抵禦外辱的熱情,安排士兵輪番勞作,同時身先士卒作示範,終於建起了比較牢固的掩體。在拉鋸式的陣地爭奪戰中,他帶領戰士衝刺在前,英勇殺亂,不幸被日軍的榴彈片擊中多處,身負重傷,被送往北平協和醫院治療。
血戰台兒莊
台兒莊大血戰發生於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是中國軍隊和日寇在山東嶧縣台兒莊(今屬棗莊市)一帶進行的一次殘酷的戰役。
在台兒莊抗日浴血大奮戰中,父親在關麟征第52軍的第25師146團擔任營長,在台兒莊外圍東北擔負阻擊任務,打擊從臨沂馳援台兒莊的坂本旅團,切斷日軍的增援,在氣勢洶洶的日軍援敵面前英勇頑強的阻擊,使其救援台兒莊的計畫落空。
台兒莊戰役是中國軍隊取得的一次重大勝利。在歷時半個月的激戰中,中國軍隊付出了巨大犧牲,參戰部隊4.6萬人(包括外圍阻擊戰在內,前後進行了一個多月,投入兵力20多個師計12萬人,其中台兒莊方面6萬人),傷亡、失蹤7,500人,殲滅日軍1萬餘人。它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兇狠氣焰,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畫。它是抗戰初期繼平型關大捷後中國軍隊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堅持抗戰的必勝信心。
在抗擊日寇的戰爭中,父親在關麟征部下還先後於1937年9月參加保定戰役;1938年夏秋之交,參加武漢保衛戰;1939年秋,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取得湘北大捷等等。
我感到欣慰和驕傲的是,在這些輝煌的戰績中都有父親的一份功勞,父親的血沒有白流。
戍邊滇東南
抗戰中,部隊的建制時有變動。比如關麟徵擔任集團軍總司令的第十五集團軍,根據史料記載:武漢會戰前後,1938年夏,陳誠就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其基本部隊第十八軍隨其調至第九戰區,第四軍、第二十五軍也分別調入第九戰區跟其他集團軍一起參加武漢會戰,第十五集團軍番號撤銷。1939年後,第十五集團軍番號在第九戰區恢復,關麟徵任集團軍總司令,下轄其基本部隊張耀明的第五十二軍、陳沛的第三十七軍和夏楚中的第七十九軍,都曾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後關麟徵率第五十二軍組建第九集團軍,第十五集團軍番號撤銷。1941年春,第十五集團軍番號在第一戰區恢復使用並參加中原會戰。1945年初,第十五集團軍劃歸第十戰區指揮管轄。
1940年9月日軍占領越南,進一步切斷了滇越國際交通線,我國西南邊疆形勢緊張。1941年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的關麟征將軍率部由湖南經桂入滇,進駐滇東南重鎮文山。父親先後擔任這個集團軍第25師第73團副團長、團長,駐守中越邊境一帶。
父親一度擔任第九集團軍中校參謀,曾隨關麟征駐紮在文山。父親不吸菸,不飲酒,更不參與賭博,在戍邊軍防的餘暇,他唯一的愛好是讀書,尤其是文史方面的書籍。他從軍之後,一直在關麟征部下任職,隨關出生入死、南征北戰,古北口抗日作戰中父親負傷後被送往北平協和醫院治療,在醫院裡又曾跟關麟征的病房毗鄰。因此跟關的私交甚密。父親曾戲稱關麟征為“文山主人”,其意:一是指關麟征為文山地區最高軍政首腦;二是因為關麟征的“征”,繁體字“徵”字右邊為一個反“文”,中間的上部為“山”,下部為“主”,左邊是一個雙人旁,整個字由“夊、山、主、彳”四部分構成。這也足見父親對文字學的酷愛和跟關麟征關係之密切。
在雲南戍邊期間父親還曾被派往緬甸邊境的八莫、密支那等處參加中美合辦的軍官培訓班學習,提高軍事指揮素質。
在駐守雲南這段時間,母親帶著我們兄妹一同隨軍營調防多次移動。1945年7月弟弟在雲南蒙自縣芷村火車站降生,因此取名為羅芷村(讀中學後改為羅喬敏)。
受降赴越南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全面勝利。根據中、美、英三國首腦1943年12月1日發表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7月美、英、蘇、中簽署的波茨坦公告,越南北緯16度以北由中國軍隊接受日軍投降,16度以南歸英軍受降。
父親時任第九集團軍第2師4團上校團長,奉命率部由滇南開往越南解除日軍武裝,接受日本侵略軍的投降。
日軍投降儀式在河內舉行。
受降儀式結束之後,父親和其它將領均率士兵奔赴各自指定的地區解除日軍武裝,占領各戰備據點,父親率部赴海防駐守。
10月31日,被解除武裝的日軍,全部集中到海防,被遣送回國的日本人(包括日商及日軍家屬)共8萬人左右,前後共分10多次,直到1946年4月才將他們全部遣返回國。
從職副官處
1938年8月,黃埔軍校由南京內遷至成都,改稱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是為黃埔軍校本部。關麟征於1946年任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1947年10月,接任黃埔軍校校長,成為繼蔣介石之後第二任校長,是黃埔軍校在大陸期間三任校長之一,同時是第一位就任校長的黃埔畢業生。
抗日戰爭勝利後,父親脫離國民黨正規部隊,經關麟征引薦進入成都陸軍軍官學校任副官處少將副處長 。此前“副官處”的名稱叫“辦公廳”,自關麟征當校長後更名為副官處。當時副官處處長是黃埔第4期的畢業生吳麗川(少將,河南固始人);副官處下設有三個科室:行政科科長為魯克智(中校),統計室主任為劉振華(軍簡三級),收發科科長為王一士(中校)。跟父親一起在成都陸軍軍官學校同事的好友還有李幫藩及原25師師長姚國俊,原52軍軍長張耀明(1949年秋接任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等。父親此時頗為春風得意,因此取別號“破浪”,喻意人生正“乘風破浪”。
父親在成都陸軍軍官學校任職的幾年,是我們家庭生活最穩定的時期。1946年至1948年母親在其老家四川省三台縣任國小教師,1948年秋季我們遷至成都跟隨父親一起定居。父親一般不管家中事務,家裡的巨細事宜均由母親做主。比如,1945年父親到越南受降,我們隨母親返回三台縣,在縣城東街購買了由七間青瓦平房構成的一個小四合院(1948年我們定居成都後,仍由外公、外婆及三個姨媽及一個未成年的舅舅居住);1948年由於物價飛漲,為了避免貨幣貶值帶來的損失,母親托娘家人幫忙在三台鄉下購置了三十畝土地。
入編軍政大
1949年底,人民解放軍完成對成都及其周圍地區的戰略包圍。此時,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張耀明、教育長吳允周、副官處長吳麗川等飛往台灣。在中共地下黨員的策動之下,成都陸軍軍官學校第一、三總隊10,000多人舉行起義。父親參加起義後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教導三隊(原名十八兵團隨校)。1950年4月,第十八兵團建制奉命撤銷後,改稱為西南軍政大學川西分校。
成都臨近解放,社會秩序混亂,我們兄妹三人跟隨母親回到三台縣居住。父親參加起義後由十八兵團發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家屬證明書,1950年由母親親手遞交三台縣當時的副縣長王棣之,並經王棣之批示縣文教科科長譚善清安排母親繼續作國小教師,母親被安排到心妙鄉國小任教。我們家庭享受軍屬待遇,門前除了懸掛“革命軍屬”的光榮匾之外,逢年過節還有居委會的領導到家慰問,贈送慰問品。
1950年6月15日,在西南軍區大操場舉行成渝鐵路開工典禮,拉開了修建成渝鐵路的序幕。經過10萬軍民兩年的日夜緊張奮戰,全長505公里的成渝鐵路於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車。
在這支修路大軍中,包括西南軍政大學川西分校的全體學員,我父親也在其中。他們在軍政大學裡,一邊學習馬列、毛澤東著作,改造思想,一邊參加鐵路的修建勞動。
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中,在軍政大學裡父親通過學習,寫信動員母親把父親畢生積攢的黃金悉數送交“三台縣增產節約辦公室”。加上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中的退賠,至此,家庭的全部收入只有依靠母親當國小教師的微薄薪金了。
退伍陷深潭
作為職業軍人,父親二十多年一直戎馬倥傯,居無定所;父親的祖籍在南川縣,在考入黃埔軍校之後,父親只在抗戰勝利後1946年祭祖時回過老家一次。1952年秋季人民解放軍開展轉業復員運動,父親拿著西南軍政大學出具的復員退伍證明只好回到母親的原籍三台縣。
居委會當時正在舉辦夜校,組織家庭婦女掃除文盲。鑒於父親有文化,又是西南軍政大學回來的,居委會安排父親作夜校教員,晚上給學員讀報、教學員學文化,還兼管街道黑板報,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中心工作,每周換一次黑板報內容。辦黑板報父親一絲不苟,雖然他不善美工,仍要細心地用彩色粉筆在黑板框線上畫些圖案,在新聞標題處點綴些題花,努力把黑板報辦成精品。這些工作雖然沒有報酬,但受到學員尊敬,也算是一種精神慰藉。但是由於父親當過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在三台縣這種小地方是一件罪惡深重而可怕的事,因此漸漸地他受到一些人仇恨的眼神。為了減少自己在公眾場合的孤寂,父親在辦黑板報時,總會把我帶上,讓我當助手,替他攜帶粉筆、直尺之類的東西。
最初,父親對找到工作充滿信心,積極地進行必要的準備。他用退伍時發的津貼買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書籍,甚至專業性很強的諸如殷周歷史之類的專著。他還將一塊舊木板用釘子和繩子固定在牆壁上,做成一個簡易的書架。
到後來,政治形勢對父親越發不利。他受到巨大的社會壓力,對找到工作逐漸喪失了信心,加之家庭經濟特別困難,他只得將自己珍藏的書籍都廉價變賣掉,包括跟隨他多年的一本厚厚的《辭源》詞典。
為了應對經濟拮据,父親將家中一小塊花圃改為菜圃,自己栽種冬瓜,將舊竹竿纏繞上稻草,把冬瓜秧苗引上房頂,每天細心地照料,冬瓜長得枝繁葉茂,碩果纍纍。冬瓜成熟後,我會滿懷喜悅地登上梯子爬到屋頂,把成熟的冬瓜摘下來。盛夏到來是家裡冬瓜豐收的時節,除了自給自足之外,我們會把多餘的冬瓜放在街邊便賣些錢補貼家用。
隨著幾位姨媽搬出我們家,1957年外公搬到二姨家住,我們三兄妹讀中學吃住在學校,父母只留了兩間自住房,其餘的幾間房子便陸續出租出去,以租金補貼日常需用。
為了進一步緩解家中的經濟窘況,父親曾打算靠賣文筆為生。在街邊父親搭起一張小茶几,擺兩條小凳子,替人代寫書信。等了幾天只有一個人惠顧,得了一毛錢,而得到更多的卻是路人怪異的眼神。父親不堪受人白眼,憤然決定出賣苦力。當時三台縣剛開始引進煤炭作鍋爐的燃料,建立煤炭公司,工廠和一些大一點的機關單位陸續裝備蒸汽鍋爐。煤炭則由木船裝載從涪江上游運送到東河邊的簡易碼頭。煤炭從木船往岸上卸載卻是依靠人力挑下來,這項重體力勞動,既苦又累,一般人是不會去乾的。父親認為碼頭邊認得自己的人不多,自己身體尚無大礙,這個苦能吃下來。父親購買了一根扁擔、一對籮筐,每天早上天剛放亮他便餓著肚子,扛著籮筐到河邊從木船上把煤炭一擔一擔地往岸上挑。八點多鐘回家吃過早飯又往碼頭上趕。
然而更嚴重的打擊卻是政治上的。對父親在政治上的第一次沉重打擊發生在1954年,當時全國進行第一次普選,有選民資格的名單進行三次張榜公布,在人們熟知的歷史背景下,被視為“階級敵人”者將被剝奪選舉權。在選民登記過程中派出所駐街道民警多次調查父親的政歷,由於父親參加了成都起義,又有軍政大學的退伍證明,歷史身份早就是清楚的,因此第一次榜上有父親的名字。但是在張榜後,因為“民眾有意見”,“不該將選舉權給反動軍官”,“人言可畏”,父親的名字很快從榜上被塗掉。既然如此,總得“挖”出理由來,於是在發“選民證”的民眾大會上,將父親揪到台上,公開宣布和批判他當過國民黨軍官的“反動罪行”!。從此,父親便背負沉重的精神負擔,經常遭派出所修整、教訓。當時,外公跟我們住在一起,他是城市貧民出身,擔任居民小組長。因為父親這件事外公受到株連,居民小組長的職務馬上被撤掉。外公在家裡一語雙關地憤憤然嘆息道“這真是牆倒眾人推!”
1958年第二次全國普選時,因為確實沒有找到什麼新的“罪行”,“恩賜”了父親一張“選民證”,重要的是他倖免了一場新的羞辱性的批判。
即使處在最沉悶的日子裡,父親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都積極擁護。他吸取了以前埋頭書齋的教訓,堅持讀報使自己能了解和跟上形勢的變化。在整風“反右”時,有人想把父親打成“右派”,施加壓力要他在街道居民會上“鳴放”,給黨和政府提意見。父親艱難地頂住壓力,沒有落入某些人設定的圈套,只給醫院的護理工作提了意見。這樣,父親總算躲過了人生中又一次新的悲劇。
巨大的政治壓力給予父親沉重的精神負擔,甚至一度使他神情恍惚。當時的物質供應基本都憑票證購買,特別是糧食類的物品。有一次父親到糧站購買大米,發現購糧登記本不在了,急得幾乎暈了過去,那上面可是全家人的命根子,眼看馬上就會斷炊,他急得在家裡團團轉,到處翻箱倒櫃尋找,終無所獲。更為可怕的是,父親擔心被人抓住這件事,以破壞國家統購統銷政策為藉口對他進行批判,終日提心弔膽。當月全家人的口糧只好由外公到處向鄰居借討。後來申請補發新購糧登記本又經歷了若干時日和周折。
這件事的真相,直到父親臨死之前才告訴我:由於當時受到太大的精神壓力,他整日神志不清,一次購糧之後將購糧登記本放在背心的一個衣袋裡,背心脫下後很長一段時間未再穿用,第二次購糧時忘掉這件事,越急越找不著。後來從背心衣袋裡發現這本購糧證時,已補發了新的,父親不敢再提此事,也不敢用這本購糧證購糧。否則,父親又將會大禍臨頭。待到父親被送往勞教隊時,他如實地“坦白”了這件事,並把舊糧證上繳了。
父親自1952年從西南軍政大學復員回三台後,一直奉公守法,戰戰兢兢地夾著尾巴生活,在歷次鎮反、肅反、整風反右運動中規規矩矩沒有越軌行為,故而找不到整他的新材料;但是因為父親擔任過國民黨軍官,因此一直受到社會歧視。他不能找到一份工作,子女的政治前途受到株連,升學、就業長期受到影響。
屈辱離人世
五十年代,我們兄妹四人都未成年,尚在國小或中學讀書。父親擔心自身的政歷對我們的成長造成影響,總是憂心忡忡,始終小心翼翼、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地生活。即使如此,厄運仍然降臨到他的身上,他並因此斷送了性命。
1958年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各地農村不斷大搞高產田,農業生產“創造”出的“衛星”層出不窮。三台縣公安局在蘇河鄉(現紅星鄉)建有一個勞改農場,為了跟上全國的躍進形勢,囿於勞動力缺乏,急需調一批有“政歷問題”的人供作役使。
這年秋天,我和大妹(羅羨蓉)正在三台中學念高中,均在校內食宿,母親在鄉下國小教書,因此平時只有父親一人住在家中。一天晚上八點多鐘大妹把我從教室里找了出去,告訴我:居委會治保委員到學校找到她,告之傍晚時分父親被通知到派出所,現已送往拘押所。臨走時未帶被褥和碗筷,叫我們替父親送去。我和大妹馬上回到家中拿了一雙竹筷子、一個“洋磁碗”,抱著一床破棉被,冒著凜冽的寒風離開東街直奔拘押所。拘押所位於新西街縣政府旁邊,當時靠近拘押所大門的圍牆有部分已坍塌正待重建。我們正向門房走去,突然從斷垣殘壁的圍牆裡衝出一名持槍的士兵,向我們大聲嚷道:“站住!乾什麼?”我們被嚇了一大跳,大妹這時被驚嚇得掉下來了眼淚。我們順從地按照這名士兵的吩咐,寫下父親的姓名,將碗筷、棉被放在門裡。我們未能見到父親的面,父親便在沒有給予任何理由、任何法律手續或法律文書的情況下,被送往公安局辦的勞改農場——蘇河農場去“勞動教養”。
大約一個月之後一個晚上,晚自習已下課了,傳達室工人邱宗榮托人到寢室找到我並通知說,父親從勞改農場被送回城,叫我馬上回家。待我趕到家門口,嚇我一大跳,離家一個月時間,父親的面目已變得難已辨認,骨瘦如柴地躺在一輛滑竿上,右腳赤裸,下肢腫得通紅。他是由兩名勞改隊員用滑竿從蘇河勞改農場抬回城的。這兩名隊員告訴我,在繁重的勞動中父親被鋤頭挖傷腳,感染破傷風,病情惡化仍不予治療,已經生命垂危臨近死亡時才派遣他們倆人抬父親回家。
我們把父親抬到床上,父親已經奄奄一息。年幼的我頓時失去主張。跟我們住在同一個院子裡的阿姨王樹德,她是居委會的治保委員,為人還算正直。她一方面托人到鄉下通知母親,一方面拿出糧票和錢囑咐我到麵館替父親買一碗麵條。買回來後,她看到碗裡無一點油星,特地從她家中舀了一湯匙豬油加在面碗裡(當時我們家中簡直是一無所有)。然而垂危之中的父親已經絲毫無法進食,只能喘著粗氣斷斷續續地告訴我:公安局拘押他到蘇河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教養沒有其它原因,只是因為認定他是2%的反革命。
母親從鄉下趕到家中已是凌晨時分,我們將家裡一塊門板拆卸下來當擔架,將父親抬到縣人民醫院搶救,然而這時早已失去搶救的寶貴時間,醫院已無回天之力,父親終於在醫院含冤去世,這時他才52歲。此時家中早已一貧如洗,一切醫療、掩埋費用只得靠臨時借貸湊集解決。父親被草草掩埋在郊外的一座荒山上。
至今我都不懂這2%的反革命是什麼意思?父親二十多年戎馬生涯,在民族危亡時刻對日英勇作戰並因此負傷,為抵禦外辱做出的貢獻,對國家、對人民、對民族難道有罪嗎!這樣的人難道應當在遭受這般凌辱的情況下去世嗎?
父親被結論定為2%的反革命分子,致使家屬和子女受到嚴重的株連,背著沉重的反革命家屬的包袱,政治上受盡歧視,連生活出路亦幾乎斷絕。
我內心曾對王樹德阿姨產生過怨氣。1958年大搞全民軍事化、共產化,父親被拘押到勞改農場後,我們曾將家裡鎖門的鑰匙拿了一把請她代為保管。居委會大辦公共食堂,她帶人到我們家把廚房裡包括碗筷在內的所有用具全部送到公共食堂,大飯桌、圓凳也通通被拿走,家裡真的算得上是家徒四壁一無所有了。這難道跟她無關嗎?後來細細一想,結合她平時的為人,她並不是一個出賣良心的人,這種“置諸死地而後快”的作法,未必就是她的個人品質。因此,這件事也不能單單怪她,在那種大環境下她也是不得已而遵命為之的。
當然,每當談起那些沉重的往事時,人們總是會說:是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的。誠然,政治氣候是可以決定一切,可是,在同一片天地之間,有人有好生之德、仁愛之心,悲憫善良、同情弱者,有人卻推波助瀾、磨牙吮血,生、末、淨、旦、醜竟在同台之中張顯著人性的差異,展示著不同的嘴臉,這大約就是歷史悲劇能演繹得淋漓盡致、發揮得令人瞠目結舌的原因吧!
十一、遲到的緬懷
1939年“湘北大捷”之後,父親隨關麟征駐軍湖南,我於1941年2月在湖南省零陵縣(今永州市零陵區)出生;隨後,我和母親跟隨父親他們的部隊經廣西、貴州最後駐防在滇東南,妹妹和弟弟也相繼來到人世。
父親給我取名羅翹楚,“翹楚”本意是才能出眾、傑出的人才。《詩-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王勃當眾賦《滕王閣序》,一氣呵成,在座皆驚。故《滕王閣序》被辛棄疾譽為“王郎健筆夸翹楚”,即此之謂。足見父親對我的希望很大,希望我能超越前輩,為社會做出巨大貢獻;大妹1942年7月在雲南出生,取名為羅羨蓉,“蓉”是抗日大後方成都的代稱,“羨蓉”寓意渴望抗戰儘早勝利,國家富強,民族興旺,人民獲得安定的生活;弟弟1945年出生於雲南蒙自縣芷村火車站,父親為了紀念抗戰戍邊滇東南的四年時光,為他取名為羅芷村。最小的妹妹1954年出生於三台縣,父親為她取名為羅小蓉,寓意她是老么。
我們跟父親在一起的時光,在我的記憶里不到八年時間。1948年秋季母親辭去了國小教師的工作,我們從三台遷到成都居住。當時我7歲,讀國小一年級,到1949年冬天我們三兄妹返回三台讀書,在成都前後居住了一年半時間;1952年秋,父親退伍回到三台直到他去世,我們一起相處有六年半的時間。
父親一生不沾菸酒,為人誠懇厚道。他的毛筆字寫得十分漂亮,悉心研讀文史則是他閒暇時的最大愛好。一本厚厚的“辭源”不知翻閱了多少遍。他雖然從軍,書生氣卻十足,一點不懂政治和專營,在內戰紛飛迫近西南之時,他仍潛心於編著“槍械學”一書,沒有考慮時局變遷可能帶來的生存危險。
父親為人總是慈善的,對我們幾兄妹更是如此。他不僅從未打罵過我們,甚至沒有對我們說過重話。我們住在成都的一年多時間裡,父親有時教我們一些繞口令和童謠,給我們講薛濤、紀曉嵐之類的歷史故事,帶我們去望江公園看“薛濤井”,有滋有味地品嘗五香“薛濤豆腐乾”。幼年的我曾站在小凳子上,踮著腳爬在書桌上跟著父親學著查閱“辭源”。
父親回三台時,我們正在國小念書。暑假裡他會牽著我們兄妹逛街,雖然家裡經濟拮据,父親仍會揀最便宜的李子之類的水果給我們嘗,雖然他自己捨不得吃。
父親為自己購買文史書籍的同時,不會忘記為我們買一些適合的讀物,我印象最深的書籍是“動腦筋爺爺”以及葛佩奇著的“自然常識五百題問答”。
父親對我們幾兄妹要求很嚴格,總是鼓勵我們努力學習,跟上時代步伐,看到我們經常從學校里拿回獎狀,他顯得特別高興。
我們家就在三台中學高中部旁邊,有一次我回家時在校門口遇到一名高中女生,她點頭向我打招呼,被父親看見了。回到家中,父親很不高興地盤問我很久。當時我正臨近國小畢業,為了準備升學考試,我跟另外兩名同學約定,每天早晨起床後爬上公園的牛頭山背誦語文。有一次剛好遇到了這幾位高中女生,她們把我們當作小弟弟,關心地詢問我們複習功課的情況。父親顯然過於敏感了,不過也可看出他是不願我們在成長中有一絲閃失。
父親還是一位好女婿,回三台後一直很孝敬他的岳父、岳母;岳父岳母從前承擔的家務他總是自己爭著去做。特別是從糧站背米回家、從一里路外的水井挑水回家等。1954年外婆因心臟病去世,母親當時剛生了小妹妹,外婆唯一的兒子正在北京念大學不能回家奔喪。外婆整個喪事均是父親協助外公操辦的。棺材(當時是土葬)從城內運到郊外的十幾里路,外婆的靈位牌一路都由父親雙手奉祭著。
1957年我國中畢業的時候,升學形勢很嚴峻,在激烈的競爭中我考上了高中,父親很高興。當時家裡已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父親擔心我孱弱的身體抵禦不住嚴寒,毅然將他身上唯一的一件毛衣讓給我作禦寒。
1958年,我正在讀高一下學期。當時,全國處於極度的狂熱之中,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生產大搞人海戰術,實行大兵團作戰,生活搞“一大二公”,砸爛每家每戶的罈罈罐罐,興辦集體食堂。有一次學校按照上級的安排,給我們下達“支農”任務,在班主任蘇XX老師帶領下到黃林鄉拆毀破農舍,推倒舊土牆。一天中午勞動結束後,我肩上扛著鋤頭跟幾名同學一塊回住地吃午飯。走到中途,我突然想起工地上可能還有畚箕,便折身回到工地拾取。待我追上其他同學一塊回到住地時,中午飯已開始了,吃的是紅苕玉米粥。稀粥端在手中,站立在農家屋檐下用餐,感到身上有陣陣涼意,這時我才意識到披在肩上的毛衣不翼而飛。我馬上放下碗筷,急忙奔向剛才走過的道路尋找,可是哪裡還能找到毛衣的蹤影。
在當時的生活條件下,一件毛衣是很貴重的。丟失珍貴之物,心中很不痛快。不過,一想到正在從事的是共產主義崇高事業,為了“大我”,犧牲“小我”,心中的不快也就很快釋然。
我期待著共產主義的早日到來,相信不僅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還會有一件自己的新毛衣。然而,烏托邦的“大躍進”和十年“文革”使我的夢想破滅,在拮据的生活中,我長期依靠一件短小的破棉襖禦寒。直到參加工作領到工資後才攢錢織了一件新毛衣。
在我慢慢懂事之後,一想起這件事,心裡就感到酸楚,對父親產生一種沉痛的愧疚。父親在沒在職業和收入,最困難、最壓抑的情況下,寧願受凍卻把自己身上正穿著的、最值錢的鴨絨毛線衣讓給我,足見他對我的愛心和呵護。我把這件珍貴之物丟失,卻沒有對他說句表示歉意的話,可能我正在丟失他心目中最後的一點希望,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父親雖然參加了成都陸軍軍官學校的起義和軍政大學的學習,但是他的戎馬生涯在年富力強之際便早早結束,厄運接踵而至。在被反覆審查歷史中他惴惴不安地小心度日,不明不白地被送往勞改農場遭受凌辱,並在受傷後得不到及時救治而過早地去世。
在他含冤逝世二十多年之後,經過我們兄妹的奔走,他的起義軍人的身份終於得到承認,他的在天之靈終算可以得到一絲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