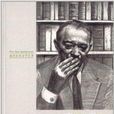基本介紹
- 書名:紐約知識分子叢書:菲利普·拉夫
- 作者:張瑞華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4738088
- 外文名:Philip Rhav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頁數:257頁
- 開本:32
- 品牌:江蘇譯林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1. 菲利普拉夫是紐約知識分子輿論工具《黨派評論》的創始人,是具有深遠影響的社會—文學批評家。
2. 拉夫的批評很具道德責任,反映了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對藝術的審美與政治關懷。
3. 本書系統而詳細地介紹了拉夫的生平、生活,拉夫創辦的重要文學、文化刊物《黨派評論》,以及拉夫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政治及文學思想;是一部國內少有的介紹紐約知識分子重要的人物拉夫的基礎而全面的專著。
2. 拉夫的批評很具道德責任,反映了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對藝術的審美與政治關懷。
3. 本書系統而詳細地介紹了拉夫的生平、生活,拉夫創辦的重要文學、文化刊物《黨派評論》,以及拉夫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政治及文學思想;是一部國內少有的介紹紐約知識分子重要的人物拉夫的基礎而全面的專著。
作者簡介
南京師範大學美國文明方向博士,現為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英美文學與美國文明研究,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國外文學》、《外國文學》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圖書目錄
前言
一拉夫的生活經歷
1.飄泊不定的早期生活
2.激進主義與《黨派評論》
3.《黨派評論》內部的分歧
4.個人感情生活
5.20世紀50年代逐漸“進入”美國
6.20世紀60年代的沉默與“再生”
7.波士頓的最後幾年
二拉夫與《黨派評論》
1.《黨派評論》的編輯宗旨
2.《黨派評論》的編輯原則
3.《黨派評論》的機構化建設
4.《黨派評論》的經濟來源
三拉夫的政治思想
1.激進主義的思想基礎
2.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2.1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2.2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
3.共產主義的墮落與蛻變
3.1反史達林主義
3.2戰後的反共主義
四拉夫的文學思想
1.批評與批評“理論”
1.1批評與批評的目的
1.2批評方法
1.3批評對象與批評手段
1.4批評的基本原則
2.創造性矛盾:對歐洲現代主義作家的批評
3.經驗與思想的對立:美國文學批評之一
4.“第六感”與“時代潮流”:美國文學批評之二
4.1自然主義
4.2無產階級文學
4.3對神話一象徵的獵取
4.4形式主義的新批評
5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品質
五結語
注釋
參考書目
主要譯名英漢對照表
菲利普·拉夫大事年表
後記
一拉夫的生活經歷
1.飄泊不定的早期生活
2.激進主義與《黨派評論》
3.《黨派評論》內部的分歧
4.個人感情生活
5.20世紀50年代逐漸“進入”美國
6.20世紀60年代的沉默與“再生”
7.波士頓的最後幾年
二拉夫與《黨派評論》
1.《黨派評論》的編輯宗旨
2.《黨派評論》的編輯原則
3.《黨派評論》的機構化建設
4.《黨派評論》的經濟來源
三拉夫的政治思想
1.激進主義的思想基礎
2.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2.1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2.2文學的現代主義運動
3.共產主義的墮落與蛻變
3.1反史達林主義
3.2戰後的反共主義
四拉夫的文學思想
1.批評與批評“理論”
1.1批評與批評的目的
1.2批評方法
1.3批評對象與批評手段
1.4批評的基本原則
2.創造性矛盾:對歐洲現代主義作家的批評
3.經驗與思想的對立:美國文學批評之一
4.“第六感”與“時代潮流”:美國文學批評之二
4.1自然主義
4.2無產階級文學
4.3對神話一象徵的獵取
4.4形式主義的新批評
5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品質
五結語
注釋
參考書目
主要譯名英漢對照表
菲利普·拉夫大事年表
後記
後記
開始有意識地閱讀紐約知識分子以及菲利普·拉夫,是在2001年夏。當初基本上是作為院裡的一個“任務”而“接受”菲利普-拉夫的。斗膽“接受”之時,既對文學涉獵不深又對歷史鮮有了解。因此,不得不從當初要求的“三年計畫”拖到“五年計畫”。2006年夏,本書終於成稿。閱讀、寫作中遇到的種種曲折依然歷歷在目,有酸、有苦、有辣,也有甜。
研究是為了學習。進入紐約知識分子這個領域,無論對我個人的視野還是學養,都是一個巨大的飛躍。那些知識分子所散發出的思想智慧與活力、他們對文學與政治的執著,是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但他們的精神卻超越時代,值得我們永遠敬仰與學習。
我走入這一領域,從這一研究中受益匪淺,後來又將學術興趣從文學擴展到美國文明,得感謝錢滿素教授。她將紐約知識分子的研究選題帶入我院,並在我閱讀、寫作的各個階段給予了可貴的指導與鼓勵。她的智慧、學識、寬容令我終生難忘。其次要感謝外院院長張傑教授。他對這套研究叢書的支持、熱情以及執著令我們備感溫馨與鼓舞。還要感謝陳貽夫婦與林華一家,是他們在美國幫我買了一本本參考書,並將它們帶回、郵回國內。當然,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是他們的理解支持著我的寫作。沒有上述所有人的幫助與關懷,這本小小的書無論如何也無法完成。
本書出版之際,我既感高興又感不安。筆者眼界、學識有限,希望廣大讀者、行家不吝批評指正。
張瑞華
2012年7月於南京
研究是為了學習。進入紐約知識分子這個領域,無論對我個人的視野還是學養,都是一個巨大的飛躍。那些知識分子所散發出的思想智慧與活力、他們對文學與政治的執著,是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但他們的精神卻超越時代,值得我們永遠敬仰與學習。
我走入這一領域,從這一研究中受益匪淺,後來又將學術興趣從文學擴展到美國文明,得感謝錢滿素教授。她將紐約知識分子的研究選題帶入我院,並在我閱讀、寫作的各個階段給予了可貴的指導與鼓勵。她的智慧、學識、寬容令我終生難忘。其次要感謝外院院長張傑教授。他對這套研究叢書的支持、熱情以及執著令我們備感溫馨與鼓舞。還要感謝陳貽夫婦與林華一家,是他們在美國幫我買了一本本參考書,並將它們帶回、郵回國內。當然,還要感謝我的家人,是他們的理解支持著我的寫作。沒有上述所有人的幫助與關懷,這本小小的書無論如何也無法完成。
本書出版之際,我既感高興又感不安。筆者眼界、學識有限,希望廣大讀者、行家不吝批評指正。
張瑞華
2012年7月於南京
序言
在美國知識分子歷史中,紐約知識分子赫然在目。作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無疑是20世g30年代到50年代間活躍於美國知識分子舞台上的一支強勁而名字響亮的隊伍。儘管公共知識分子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人們對他們的關注卻始終存在。1987年,拉塞爾·雅各比以啟示錄式的書名、懷舊的口吻,出版了《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在書中,雅各比拋出了紐約知識分子不僅是美國最偉大的公共思想家,也是最後的知識分子的斷言。雅各比通過對當今美國知識分子現狀的分析,指出如今占據知識界的已不再是從前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是各類各派學術專家,即所謂的“私人’知識分子;雅各比嘆息現在“有上千名激進的社會學家,但沒有米爾斯;有三百名好鬥的文藝理論家,但沒有威爾遜”。‘該書一出版就激起了評論界的激烈論辯,但不久之後大家都趨於認同雅各比的觀點:就美國目前的情況而言,公共知識分子的確已不復存在。
人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普遍認識幾乎都與《黨派評論》周圍的社會文化批評家,如菲利普·拉夫、埃德蒙·威爾遜、萊昂內爾·特里林、艾爾弗雷德·卡津、歐文·豪、丹尼爾·貝爾有關。他們也是紐約知識分子這個諾曼·波德霍雷茨所謂的“家族”的三代成員的代表人物。當初面臨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崩潰,這些知識分子深受激進主義思想的吸引,紛紛加入共產主義組織,探尋馬克思主義的種種可能。1936年的莫斯科審判使他們大受震撼,隨後成為揭露史達林極權統治以及蘇聯真相的堅定的反史達林主義者。從此,他們開始偏離大多數左派分子,拒絕無產階級藝術,在反對多種形式的史達林主義的同時,倡導文學的現代主義,成為“反對中產階級市儈勢力,在政治思想與文學實驗上高舉歐洲標準旗幟的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使他們在美國該不該參加戰爭的問題上產生分歧。但無論他們對美國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戰後時局的變化都使他們在調整自己的政治傾向時,“—方面為美國政府提議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對美國社會秩序的批評態度”。他們相信胡克的論斷。“如今……共產主義是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然而,儘管他們認同麥卡錫的共產主義威脅論,他們還是普遍反對麥卡錫迫害共產主義者的極端行為。20世紀60年代,隨著美國社會進一步朝有利於知識分子的方向發展,再加上個人旨趣以及志向的不同,紐約知識分子這個“家族”開始分崩離析,越戰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作為一個統一的“家族”對外說話,之後儘管他們繼續在美國社會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已全然失去往日的內部和諧與統一。
如今,這個主要由作家、政治理論家、社會文化批評家組成的“家族”中老一代成員均已作古,年輕的一代也不再年輕。隨著《黨派評論》於2003年4月停刊以及九十四歲高齡的威廉·菲利普斯於2002年9月離世,紐約知識分子已成歷史,但他們所留下的文學歷史批評巨著、所經歷的輝煌以及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無疑是美國文化歷史上的寶貴遺產。正如歐文·豪與一位文化史學家所總結的:他們在文學上“創造了_一種全新的,對這個國家來說,幾乎是陌生的創作風格:全球性的、博學的且經常富含爭辯的”;在政治上,“在將近三十年間他們代表了美國知識分子的核心,既作為國家之聲音,又作為國家之良知”。
如此重要的政治文化地位無論如何都離不開他們的“家族”輿論工具——《黨派評論》。自雜誌誕生之日起,尤其是自1937年復刊之後,《黨派評論》就一直是他們的機構刊物,幫助確立了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及影響力。它既是“美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家庭喉舌”,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甚至有可能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小型刊物”。‘當然,《黨派評論》的成就離不開雜誌的思想內容,尤其是雜誌對於文學與政治的關注、它所展現的那個歷史時期的經驗模式以及它對知識分子的普遍關懷,也離不開兩位創始人——菲利普·拉夫與威廉·菲利普斯,尤其是拉夫的貢獻。拉夫是公認的雜誌的核心,他起著既是總指揮又是戰略家的作用;他領導雜誌就像指揮戰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編輯個性是壓倒一切的;而與拉夫相比,菲利普斯起的是領班與裁判的作用。詹姆斯-法雷爾戲稱兩人的結合是“內容與形式”的結合。
拉夫個性強悍、善於思辨、言語尖銳。對他的評說總是離不開他一手創辦的雜誌——《黨派評論》。因此,美國知識分子、紐約知識分子、《黨派評論》、拉夫,它們總是鎖鏈一般相互聯結著、相互作用著。如果我們把美國知識分子比作一棵大樹,那么紐約知識分子、《黨派評論》便是這棵大樹上的枝幹與枝權,而拉夫則是枝權上的枝權。這或許是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但本書的目的就是想藉助美國知識分子這棵“大樹”及相關的社會歷史語境,探討拉夫這枝“樹權”:它是如何成長起來的?長什麼樣子?又是如何“一枝獨秀”乃至“獨樹一幟”的?當然,本書藉助這樣一個語境,還有一個無法迴避的原因,那就是:儘管拉夫給讀者留下了不少優秀的,乃至一流的政治、文學批評文章,但他幾乎從來不說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以至於我們對他個人的了解只能依靠別人對他的評說。然而,令人非常遺憾的是,就是這類評說也十分有限,因為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對他的個人生活也知之甚少。他們普遍的印象是:拉夫對別人津津樂道,對自己卻總是三緘其口。“他總是神神秘秘,幾乎不為人所知。”儘管這樣,拉夫的編輯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學思想還是非常透明、非常清晰的。
與其他紐約知識分子一樣,拉夫早期深受激進主義的影響,相信馬克思主義既是他們行動的指南,又是他們政治、文學思想的哲學基礎。在激進氣氛熱烈的20世紀30年代,拉夫加入共產黨,之後又不折不扣地是一位熱情高漲的革命者。1934年的《黨派評論》無疑是這種激進革命熱情的產物。但是,賦予《黨派評論》地位的卻絕不是它對時代潮流的順應,而在很大程度上,與拉夫一樣,是對時代潮流的反對或者說是抵制。回顧《黨派評論》的歷史,儘管《黨派評論》初刊時是共產黨旗下的革命刊物,但第二年,拉夫就敏感地發現無產階級文學有問題,例如:共產黨對文學的操縱、文學質量的普遍下降、批評的黨性化傾向,等等。第三年,再加上財政問題以及共產黨政策的轉向,《黨派評論》宣布停刊。莫斯科審判堅定了拉夫與共產黨脫離的決心,使他毅然走上反史達林主義的道路。因此,1937年復刊時,拉夫堅持《黨派評論》與任何黨派和黨性分離,雜誌的關注中心從無產階級轉向了知識分子.從高爾基與反叛詩人轉向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T.S.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這種編輯思想與立場深深吸引了-一大批具有類似傾向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是猶太知識分子,且很快形成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群體。有人將這個瀰漫著猶太氣氛的圈子稱作美國的“布盧姆斯伯里團體”。威廉·巴勒特曾提到,他在那些猶太知識分子中間幾乎忘記了自己根本就不是個猶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隨著知識分子對美國以及戰爭的態度逐漸分化,《黨派評論》成為了論爭美國該不該加入歐洲戰爭的前沿陣地。拉夫的態度從最初的不介入戰爭轉變為“在某種意義上,這場戰爭便是我們的戰爭”。這種態度的轉變使德懷特·麥克唐納等一些堅決的反戰成員離開《黨派評論》。20世紀50年代,拉夫引領《黨派評論》率先揭露了蘇聯共產主義的極權性質。儘管在對待麥卡錫極端迫害共產主義者的問題上.《黨派評論》沒有成為批評麥卡錫主義的領頭羊.但拉夫本人還是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對麥卡錫的譴責。除了政治上的成就,或許《黨派評論》最大的成就在於它發現並培養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作家與批評家,他們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索爾·貝婁、蘇珊·桑塔格、萊昂內爾·特里林、瑪麗·麥卡錫、歐文·豪、艾爾弗雷德·卡津、德懷特·麥克唐納、邁耶·夏皮羅、克萊門特·格林伯格、哈羅德·羅森堡等。據歐文·豪說,《黨派評論》“不僅幫助創立了美國文學中的新流派,即城市‘疏離’小說以及猶太小說,而且還幫助形成了美國文學批評中的獨特流派.即所謂的紐約社會批評家”。當然,《黨派評論》能成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雜誌,也離不開這些作家與批評家的貢獻。
在那群個性迥異、成就卓著的紐約知識分子中,拉夫是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拉夫早年輾轉數國,飽嘗生活的艱辛,因此除了,20世紀50年代在政治上沉默了一段時間外,拉夫基本上一直是位共產主義者。他留下的政治文章是他所經歷的共產主義歷程的最好體現,其中包括:20世紀30年代在《新民眾》、《工人日報》、《反叛詩人》等共產主義雜誌上發表的宣揚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文學的、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文章;20世紀30年代末與40年代初對與共產主義相對的史達林主義的揭露與批評;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對共產主義成為一種實際的政治教條的質疑;以及最後幾年他向20世紀30年代的激進馬克思主義的回歸等。這些文章體現了拉夫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的政治使命感與責任感:大蕭條之前,他著意向美國人介紹馬克思、列寧;莫斯科審判之後,介紹史達林、托洛茨基,介紹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墮落以及史達林主義的真相;之後,介紹凱斯特勒、馬爾羅、薩特等一些歐洲激進知識分子,同時觀照美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意識,提醒戰後美國知識分子注意普遍的“資產階級化”傾向。事實上,拉夫的這些思想都得到了延伸,成了《黨派評論》的部分政治使命。
然而,拉夫畢竟是位熱愛文學的文學批評家,他首要關心的還是政治世界中文學的存在。20世紀40和50年代是拉夫的政治保守時期,但卻是他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最繁榮時期。隨著激進主義逐漸消退,拉夫對文學的興趣越來越濃。他的批評視野基本上落在對現代美國文學、歐洲現代主義作家的闡釋以及對時代潮流,例如新批評、形式主義、宗教回歸、神話一象徵崇拜等的反擊上。那段時間,拉夫創作出了一批極富洞察力與思辨性的批評作品。這些,再加上後期的一些作品,具體體現了拉夫所一貫堅持的批評思想與批評原則。
拉夫頭腦清醒、思想具體、道德意識強烈。他認為批評是周旋於生活與藝術間極具責任感的活動;批評家的職責是恢復文學事件中參與者的角色。可以說,拉夫的批評代表著一種道德姿態。拉夫提倡文學過程的自律,蔑視任何以意識形態評判作品的批評家,如馬克斯韋爾·蓋斯馬、格蘭維爾·希克斯、伯納德·德·沃托等;但拉夫又不同於絕對“審美”的批評家,他還注重藝術的政治含義。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之所以能在拉夫身上融合,主要是因為對拉夫來說,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的現代主義是對付絕望處境的兩大激進力量。拉夫還尋找“有用的過去”,視歷史為機會的區域,作家確立自我的重要因素。這種“第六感”賦予了拉夫辨別歐洲經典作家與美國作家的能力,使他能夠與他的批評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並能客觀、公正地評說他們的功過、優劣。
拉夫的文學批評方法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他強調文學的社會決定因素以及藝術客體在時間維度中的存在,但拉夫同時義吸收了存在主義、心理分析、社會學中的一些概念。我們欣賞拉夫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能夠恰到好處地運用這些現代批評資源,不同於某一方法或技巧。
與他比較歐洲化的政治思想一致的是。拉夫的文學思想也非常歐洲化。在《黨派評論》復刊之後,拉夫有感於美國文學的不足.曾號召進行“美國文學的歐洲化”。拉夫的這種文學的歐洲化思想是在並不丟棄本國特色的基礎上提出的,拉夫堅持“美國文學的歐洲化”不是對歐洲文學的單純模仿或再現,而是拓寬民族文化,繪美國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更加國際化。這種文學前景具體要求美國文學能創造出一種在思想上是世界性的、在具體內涵上是民族性的文學,正像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所創造的那樣。在拉夫的思想中,美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就像倫道夫·伯恩所言的不同種族的文化與美國文化的關係。拉夫本人也是歐洲現代主義大師的仰慕者,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儘管拉夫與他無論在脾性上還是在觀念上都差異甚大,但卻發現了他對現代危機所作的種種思考及其作品中所蘊涵的多重矛盾衝突與對立差異。拉夫認為,在所有現代小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與現代經歷的關係最為密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無論是在人物塑造還是在經驗與思想、生活與文學、傳統與創新等一系列辯證關係的演繹方面,都蘊涵著“創造性矛盾”。“創造性矛盾”是拉夫批評思想中的最高文學價值的體現。以歐洲文學為參照,拉夫在閱讀美國文學時發現美國文學存在著嚴重的對立與分裂,即以納撒尼爾·霍桑與亨利·詹姆斯為代表的“蒼白臉”和以惠特曼與馬克·吐溫為代表的“紅皮膚”兩種傳統之間的對立與分裂。然而拉夫義提出,儘管這兩種傳統之間存在著許多方面的對立,但兩者在對於經驗的態度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共同之處。拉夫希望在美國生活得到深入的同時,美國文學中對經驗的崇拜能在與思想的融合中減弱,美國文化能最終走出兩極分裂的死胡同。
拉夫還對批評家提出了看法。他指出批評家永遠不能成為任何偏見或狹隘的奴僕;他必須了解國家的傳統偏見,必須以世界文學的最高標準審視作品。他既不能戴著任何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去評判作品,又不能將作家的意識形態等同於作品的意識形態。一位優秀的批評家應該能夠判斷什麼是世界級的珍品,什麼是民族層次上的優秀作品。他必須公正、客觀、嚴謹、清醒,而且還需要道德意識、批評智慧、審美力、鑑賞力、評判力等多種才能。事實上,拉夫的批評就是他所堅持的這些才能與意識相結合的典範。如果我們相信卡津所言:拉夫“本質上是位辯論家,而不是作家……是知識分子司儀與主帥……是他那群激進知識分子的詹森博士”,那么我們無疑是在低估乃至忽視拉夫的文學與批評才能。儘管拉夫一生沒有留下任何宏篇巨著,但拉夫對美國文學中存在的嚴重分裂、對美國文學對經驗的崇拜以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剖析與洞見不能不說是引人深思。
這位烏克蘭出生,畢生致力於將全球意識帶入美國的歐洲移民,與其他紐約知識分子一樣夢想著在美國取得成功、得到承認,但他同時又是那群知識分子中最邊緣的人物。在逐漸認識美國、接受美國,將它接納為“我們的國家與我們的文化”,並於1957年進入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的整個過程中,拉夫似乎在,並且也想與美國、與自己達成妥協。然而,他最終還是無法妥協,在失去了抗擊時代潮流的最後一個陣地——《現代時刻》之後,他徹底崩潰了。無論說他如威廉·巴勒特所言.“越是成功.就越是抨擊給他帶來成功的那個制度”,是位很不明智的頑固分子;還是說他是位贏弱老人,最終被時代潮流所擊潰;還是說他如瑪麗·麥卡錫在著名悼詞中所說.“從未學會游泳”,具有那種反抗時代潮流的精神;還是說他至死還在守望著自己的那塊“麥田”,是位不經世事、頑固不化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拉夫的確是個矛盾的多面體,在他身上存在著許多互相衝突,乃至令人不解的矛盾。瑪麗·麥卡錫提到:“正如那些認識他的人所看到的,在拉夫身上存在著兩個人物.他們長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衝突。說一個是政治的、陽剛的以及進攻性強的,而另一個是藝術的、陰柔的以及夢幻的可能過於簡單,但這些對立就是組成部分。”“的確.這是拉夫眾多矛盾中最明顯的,或許也是最具意義的一對矛盾,因為這兩個拉夫的融合形成了第三個拉夫,即作為編輯的拉夫。他能夠以不同的面孔處理不同的人和事,能夠或強或弱、或硬或軟地周旋在政治與文學之間。但除此之外,或許還存在著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拉夫。例如,拉夫熱愛生活。但似乎生活對他過於吝嗇:早年離開父母.被迫獨自謀生;經歷過兩次離異;遭遇過感情的背叛以及第三任妻子葬身火海的打擊;後來又因第四任妻子脾性、教養的問題,他最終陷入崩潰境地。拉夫生前對自己的猶太性諱莫如深,但卻把價值一百多萬美元的遺產留給了以色列。拉夫政治思想激進,寫有不少政治評論,但在他的三大批評文集中卻沒有那些政治文章的一席之地……這些拉夫與前三個相比無疑隱蔽得多,但它們卻是使拉夫這位人物豐滿起來的具體因素。指出拉夫身上存在著這些矛盾並不是說拉夫是位個性分裂的人物,相反,各個方面的對立在拉夫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調合,讓人覺得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充滿矛盾、困惑與苦惱的典型的現代人物。
作為社會一文化批評家,拉夫與威爾遜和特里林相比並不多產.但事實上,無論是在批評種類還是在批評質量上,拉夫並不遜色。威廉·巴勒特認為:
如果從另一角度進行比較……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以及在某一段時期內,他或許比威爾遜更具影響力。的確,相比之下,他的作品徽乎其微,他的讀者也僅有威爾遜的一小部分那么多,但他的影響更多地體現在年輕的知識分子身上。他們在繼續教授文學或者從事文學創作,儘管他們可能沒有完全追隨他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採取了相反的立場,但他們都以自己的思維方式從拉夫那兒得到了某種教導,並擴大了他的影響力。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拉夫最有意義的,也最公正的總結與評判。
人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普遍認識幾乎都與《黨派評論》周圍的社會文化批評家,如菲利普·拉夫、埃德蒙·威爾遜、萊昂內爾·特里林、艾爾弗雷德·卡津、歐文·豪、丹尼爾·貝爾有關。他們也是紐約知識分子這個諾曼·波德霍雷茨所謂的“家族”的三代成員的代表人物。當初面臨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崩潰,這些知識分子深受激進主義思想的吸引,紛紛加入共產主義組織,探尋馬克思主義的種種可能。1936年的莫斯科審判使他們大受震撼,隨後成為揭露史達林極權統治以及蘇聯真相的堅定的反史達林主義者。從此,他們開始偏離大多數左派分子,拒絕無產階級藝術,在反對多種形式的史達林主義的同時,倡導文學的現代主義,成為“反對中產階級市儈勢力,在政治思想與文學實驗上高舉歐洲標準旗幟的人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使他們在美國該不該參加戰爭的問題上產生分歧。但無論他們對美國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戰後時局的變化都使他們在調整自己的政治傾向時,“—方面為美國政府提議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對美國社會秩序的批評態度”。他們相信胡克的論斷。“如今……共產主義是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然而,儘管他們認同麥卡錫的共產主義威脅論,他們還是普遍反對麥卡錫迫害共產主義者的極端行為。20世紀60年代,隨著美國社會進一步朝有利於知識分子的方向發展,再加上個人旨趣以及志向的不同,紐約知識分子這個“家族”開始分崩離析,越戰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作為一個統一的“家族”對外說話,之後儘管他們繼續在美國社會中起著重要作用,但已全然失去往日的內部和諧與統一。
如今,這個主要由作家、政治理論家、社會文化批評家組成的“家族”中老一代成員均已作古,年輕的一代也不再年輕。隨著《黨派評論》於2003年4月停刊以及九十四歲高齡的威廉·菲利普斯於2002年9月離世,紐約知識分子已成歷史,但他們所留下的文學歷史批評巨著、所經歷的輝煌以及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無疑是美國文化歷史上的寶貴遺產。正如歐文·豪與一位文化史學家所總結的:他們在文學上“創造了_一種全新的,對這個國家來說,幾乎是陌生的創作風格:全球性的、博學的且經常富含爭辯的”;在政治上,“在將近三十年間他們代表了美國知識分子的核心,既作為國家之聲音,又作為國家之良知”。
如此重要的政治文化地位無論如何都離不開他們的“家族”輿論工具——《黨派評論》。自雜誌誕生之日起,尤其是自1937年復刊之後,《黨派評論》就一直是他們的機構刊物,幫助確立了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及影響力。它既是“美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家庭喉舌”,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甚至有可能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小型刊物”。‘當然,《黨派評論》的成就離不開雜誌的思想內容,尤其是雜誌對於文學與政治的關注、它所展現的那個歷史時期的經驗模式以及它對知識分子的普遍關懷,也離不開兩位創始人——菲利普·拉夫與威廉·菲利普斯,尤其是拉夫的貢獻。拉夫是公認的雜誌的核心,他起著既是總指揮又是戰略家的作用;他領導雜誌就像指揮戰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編輯個性是壓倒一切的;而與拉夫相比,菲利普斯起的是領班與裁判的作用。詹姆斯-法雷爾戲稱兩人的結合是“內容與形式”的結合。
拉夫個性強悍、善於思辨、言語尖銳。對他的評說總是離不開他一手創辦的雜誌——《黨派評論》。因此,美國知識分子、紐約知識分子、《黨派評論》、拉夫,它們總是鎖鏈一般相互聯結著、相互作用著。如果我們把美國知識分子比作一棵大樹,那么紐約知識分子、《黨派評論》便是這棵大樹上的枝幹與枝權,而拉夫則是枝權上的枝權。這或許是個不太貼切的比喻,但本書的目的就是想藉助美國知識分子這棵“大樹”及相關的社會歷史語境,探討拉夫這枝“樹權”:它是如何成長起來的?長什麼樣子?又是如何“一枝獨秀”乃至“獨樹一幟”的?當然,本書藉助這樣一個語境,還有一個無法迴避的原因,那就是:儘管拉夫給讀者留下了不少優秀的,乃至一流的政治、文學批評文章,但他幾乎從來不說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以至於我們對他個人的了解只能依靠別人對他的評說。然而,令人非常遺憾的是,就是這類評說也十分有限,因為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對他的個人生活也知之甚少。他們普遍的印象是:拉夫對別人津津樂道,對自己卻總是三緘其口。“他總是神神秘秘,幾乎不為人所知。”儘管這樣,拉夫的編輯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學思想還是非常透明、非常清晰的。
與其他紐約知識分子一樣,拉夫早期深受激進主義的影響,相信馬克思主義既是他們行動的指南,又是他們政治、文學思想的哲學基礎。在激進氣氛熱烈的20世紀30年代,拉夫加入共產黨,之後又不折不扣地是一位熱情高漲的革命者。1934年的《黨派評論》無疑是這種激進革命熱情的產物。但是,賦予《黨派評論》地位的卻絕不是它對時代潮流的順應,而在很大程度上,與拉夫一樣,是對時代潮流的反對或者說是抵制。回顧《黨派評論》的歷史,儘管《黨派評論》初刊時是共產黨旗下的革命刊物,但第二年,拉夫就敏感地發現無產階級文學有問題,例如:共產黨對文學的操縱、文學質量的普遍下降、批評的黨性化傾向,等等。第三年,再加上財政問題以及共產黨政策的轉向,《黨派評論》宣布停刊。莫斯科審判堅定了拉夫與共產黨脫離的決心,使他毅然走上反史達林主義的道路。因此,1937年復刊時,拉夫堅持《黨派評論》與任何黨派和黨性分離,雜誌的關注中心從無產階級轉向了知識分子.從高爾基與反叛詩人轉向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T.S.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這種編輯思想與立場深深吸引了-一大批具有類似傾向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是猶太知識分子,且很快形成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群體。有人將這個瀰漫著猶太氣氛的圈子稱作美國的“布盧姆斯伯里團體”。威廉·巴勒特曾提到,他在那些猶太知識分子中間幾乎忘記了自己根本就不是個猶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隨著知識分子對美國以及戰爭的態度逐漸分化,《黨派評論》成為了論爭美國該不該加入歐洲戰爭的前沿陣地。拉夫的態度從最初的不介入戰爭轉變為“在某種意義上,這場戰爭便是我們的戰爭”。這種態度的轉變使德懷特·麥克唐納等一些堅決的反戰成員離開《黨派評論》。20世紀50年代,拉夫引領《黨派評論》率先揭露了蘇聯共產主義的極權性質。儘管在對待麥卡錫極端迫害共產主義者的問題上.《黨派評論》沒有成為批評麥卡錫主義的領頭羊.但拉夫本人還是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對麥卡錫的譴責。除了政治上的成就,或許《黨派評論》最大的成就在於它發現並培養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作家與批評家,他們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索爾·貝婁、蘇珊·桑塔格、萊昂內爾·特里林、瑪麗·麥卡錫、歐文·豪、艾爾弗雷德·卡津、德懷特·麥克唐納、邁耶·夏皮羅、克萊門特·格林伯格、哈羅德·羅森堡等。據歐文·豪說,《黨派評論》“不僅幫助創立了美國文學中的新流派,即城市‘疏離’小說以及猶太小說,而且還幫助形成了美國文學批評中的獨特流派.即所謂的紐約社會批評家”。當然,《黨派評論》能成為國內最具影響力的雜誌,也離不開這些作家與批評家的貢獻。
在那群個性迥異、成就卓著的紐約知識分子中,拉夫是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拉夫早年輾轉數國,飽嘗生活的艱辛,因此除了,20世紀50年代在政治上沉默了一段時間外,拉夫基本上一直是位共產主義者。他留下的政治文章是他所經歷的共產主義歷程的最好體現,其中包括:20世紀30年代在《新民眾》、《工人日報》、《反叛詩人》等共產主義雜誌上發表的宣揚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文學的、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文章;20世紀30年代末與40年代初對與共產主義相對的史達林主義的揭露與批評;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對共產主義成為一種實際的政治教條的質疑;以及最後幾年他向20世紀30年代的激進馬克思主義的回歸等。這些文章體現了拉夫作為一名共產主義者的政治使命感與責任感:大蕭條之前,他著意向美國人介紹馬克思、列寧;莫斯科審判之後,介紹史達林、托洛茨基,介紹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墮落以及史達林主義的真相;之後,介紹凱斯特勒、馬爾羅、薩特等一些歐洲激進知識分子,同時觀照美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意識,提醒戰後美國知識分子注意普遍的“資產階級化”傾向。事實上,拉夫的這些思想都得到了延伸,成了《黨派評論》的部分政治使命。
然而,拉夫畢竟是位熱愛文學的文學批評家,他首要關心的還是政治世界中文學的存在。20世紀40和50年代是拉夫的政治保守時期,但卻是他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最繁榮時期。隨著激進主義逐漸消退,拉夫對文學的興趣越來越濃。他的批評視野基本上落在對現代美國文學、歐洲現代主義作家的闡釋以及對時代潮流,例如新批評、形式主義、宗教回歸、神話一象徵崇拜等的反擊上。那段時間,拉夫創作出了一批極富洞察力與思辨性的批評作品。這些,再加上後期的一些作品,具體體現了拉夫所一貫堅持的批評思想與批評原則。
拉夫頭腦清醒、思想具體、道德意識強烈。他認為批評是周旋於生活與藝術間極具責任感的活動;批評家的職責是恢復文學事件中參與者的角色。可以說,拉夫的批評代表著一種道德姿態。拉夫提倡文學過程的自律,蔑視任何以意識形態評判作品的批評家,如馬克斯韋爾·蓋斯馬、格蘭維爾·希克斯、伯納德·德·沃托等;但拉夫又不同於絕對“審美”的批評家,他還注重藝術的政治含義。馬克思主義與現代主義之所以能在拉夫身上融合,主要是因為對拉夫來說,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的現代主義是對付絕望處境的兩大激進力量。拉夫還尋找“有用的過去”,視歷史為機會的區域,作家確立自我的重要因素。這種“第六感”賦予了拉夫辨別歐洲經典作家與美國作家的能力,使他能夠與他的批評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並能客觀、公正地評說他們的功過、優劣。
拉夫的文學批評方法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的,他強調文學的社會決定因素以及藝術客體在時間維度中的存在,但拉夫同時義吸收了存在主義、心理分析、社會學中的一些概念。我們欣賞拉夫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能夠恰到好處地運用這些現代批評資源,不同於某一方法或技巧。
與他比較歐洲化的政治思想一致的是。拉夫的文學思想也非常歐洲化。在《黨派評論》復刊之後,拉夫有感於美國文學的不足.曾號召進行“美國文學的歐洲化”。拉夫的這種文學的歐洲化思想是在並不丟棄本國特色的基礎上提出的,拉夫堅持“美國文學的歐洲化”不是對歐洲文學的單純模仿或再現,而是拓寬民族文化,繪美國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更加國際化。這種文學前景具體要求美國文學能創造出一種在思想上是世界性的、在具體內涵上是民族性的文學,正像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所創造的那樣。在拉夫的思想中,美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就像倫道夫·伯恩所言的不同種族的文化與美國文化的關係。拉夫本人也是歐洲現代主義大師的仰慕者,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儘管拉夫與他無論在脾性上還是在觀念上都差異甚大,但卻發現了他對現代危機所作的種種思考及其作品中所蘊涵的多重矛盾衝突與對立差異。拉夫認為,在所有現代小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與現代經歷的關係最為密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無論是在人物塑造還是在經驗與思想、生活與文學、傳統與創新等一系列辯證關係的演繹方面,都蘊涵著“創造性矛盾”。“創造性矛盾”是拉夫批評思想中的最高文學價值的體現。以歐洲文學為參照,拉夫在閱讀美國文學時發現美國文學存在著嚴重的對立與分裂,即以納撒尼爾·霍桑與亨利·詹姆斯為代表的“蒼白臉”和以惠特曼與馬克·吐溫為代表的“紅皮膚”兩種傳統之間的對立與分裂。然而拉夫義提出,儘管這兩種傳統之間存在著許多方面的對立,但兩者在對於經驗的態度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共同之處。拉夫希望在美國生活得到深入的同時,美國文學中對經驗的崇拜能在與思想的融合中減弱,美國文化能最終走出兩極分裂的死胡同。
拉夫還對批評家提出了看法。他指出批評家永遠不能成為任何偏見或狹隘的奴僕;他必須了解國家的傳統偏見,必須以世界文學的最高標準審視作品。他既不能戴著任何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去評判作品,又不能將作家的意識形態等同於作品的意識形態。一位優秀的批評家應該能夠判斷什麼是世界級的珍品,什麼是民族層次上的優秀作品。他必須公正、客觀、嚴謹、清醒,而且還需要道德意識、批評智慧、審美力、鑑賞力、評判力等多種才能。事實上,拉夫的批評就是他所堅持的這些才能與意識相結合的典範。如果我們相信卡津所言:拉夫“本質上是位辯論家,而不是作家……是知識分子司儀與主帥……是他那群激進知識分子的詹森博士”,那么我們無疑是在低估乃至忽視拉夫的文學與批評才能。儘管拉夫一生沒有留下任何宏篇巨著,但拉夫對美國文學中存在的嚴重分裂、對美國文學對經驗的崇拜以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剖析與洞見不能不說是引人深思。
這位烏克蘭出生,畢生致力於將全球意識帶入美國的歐洲移民,與其他紐約知識分子一樣夢想著在美國取得成功、得到承認,但他同時又是那群知識分子中最邊緣的人物。在逐漸認識美國、接受美國,將它接納為“我們的國家與我們的文化”,並於1957年進入美國布蘭迪斯大學的整個過程中,拉夫似乎在,並且也想與美國、與自己達成妥協。然而,他最終還是無法妥協,在失去了抗擊時代潮流的最後一個陣地——《現代時刻》之後,他徹底崩潰了。無論說他如威廉·巴勒特所言.“越是成功.就越是抨擊給他帶來成功的那個制度”,是位很不明智的頑固分子;還是說他是位贏弱老人,最終被時代潮流所擊潰;還是說他如瑪麗·麥卡錫在著名悼詞中所說.“從未學會游泳”,具有那種反抗時代潮流的精神;還是說他至死還在守望著自己的那塊“麥田”,是位不經世事、頑固不化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拉夫的確是個矛盾的多面體,在他身上存在著許多互相衝突,乃至令人不解的矛盾。瑪麗·麥卡錫提到:“正如那些認識他的人所看到的,在拉夫身上存在著兩個人物.他們長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沒有衝突。說一個是政治的、陽剛的以及進攻性強的,而另一個是藝術的、陰柔的以及夢幻的可能過於簡單,但這些對立就是組成部分。”“的確.這是拉夫眾多矛盾中最明顯的,或許也是最具意義的一對矛盾,因為這兩個拉夫的融合形成了第三個拉夫,即作為編輯的拉夫。他能夠以不同的面孔處理不同的人和事,能夠或強或弱、或硬或軟地周旋在政治與文學之間。但除此之外,或許還存在著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拉夫。例如,拉夫熱愛生活。但似乎生活對他過於吝嗇:早年離開父母.被迫獨自謀生;經歷過兩次離異;遭遇過感情的背叛以及第三任妻子葬身火海的打擊;後來又因第四任妻子脾性、教養的問題,他最終陷入崩潰境地。拉夫生前對自己的猶太性諱莫如深,但卻把價值一百多萬美元的遺產留給了以色列。拉夫政治思想激進,寫有不少政治評論,但在他的三大批評文集中卻沒有那些政治文章的一席之地……這些拉夫與前三個相比無疑隱蔽得多,但它們卻是使拉夫這位人物豐滿起來的具體因素。指出拉夫身上存在著這些矛盾並不是說拉夫是位個性分裂的人物,相反,各個方面的對立在拉夫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調合,讓人覺得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充滿矛盾、困惑與苦惱的典型的現代人物。
作為社會一文化批評家,拉夫與威爾遜和特里林相比並不多產.但事實上,無論是在批評種類還是在批評質量上,拉夫並不遜色。威廉·巴勒特認為:
如果從另一角度進行比較……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以及在某一段時期內,他或許比威爾遜更具影響力。的確,相比之下,他的作品徽乎其微,他的讀者也僅有威爾遜的一小部分那么多,但他的影響更多地體現在年輕的知識分子身上。他們在繼續教授文學或者從事文學創作,儘管他們可能沒有完全追隨他的思想,甚至有可能採取了相反的立場,但他們都以自己的思維方式從拉夫那兒得到了某種教導,並擴大了他的影響力。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拉夫最有意義的,也最公正的總結與評判。
名人推薦
拉夫是《黨派評論》的統帥,他“經營雜誌就像黨的領袖或議會領袖……雜誌是他個性,或者說,他身體的延伸。——歐文·豪 拉夫的離去,加上同時期威爾遜和W.H.奧登的離去,標誌著一個文化時代的結束,一個有質量的批評時代的結束。——艾倫·萊查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