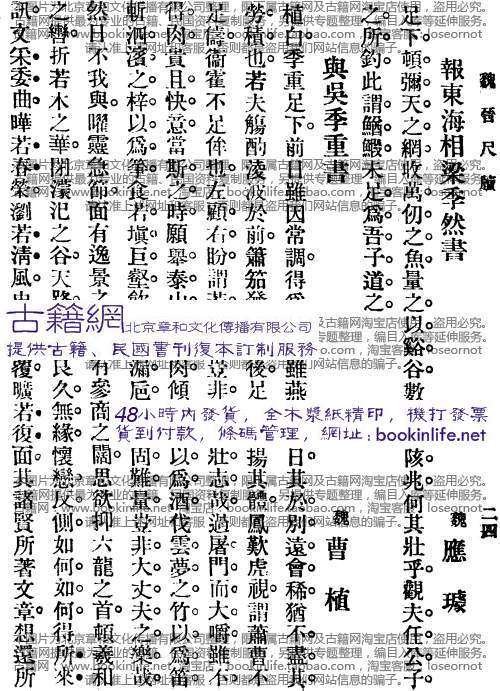陳琳《為曹洪與魏太子書》 。按顯然代筆,而首則申稱: “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速以為懽,故自竭老夫之思” ;結又揚言: “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邱,謂為‘倩人’ ,是何言歟! ”欲蓋彌彰,文之俳也。用意如螢焰蜂針,寓於尾句: “恐猶未信邱言,必大噱也” ;言凡此皆所以資嗢噱。明知人之不己信,而故使人覩己之作張致以求取信,明知人識己語之不誠,而仍陽示以修詞立誠;己雖弄巧而人不為愚,則適成己之拙而愈形人之智;於是誑非見欺,詐適貢諂,莫逆相視,同聲一笑。告人以不可信之事,而先關其口曰: “說來恐君不信” ,此復後世小說家伎倆,具見《太平廣記》卷論卷四五九《舒州人》 。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為曹洪與魏太子書
- 創作年代:東漢
- 文學體裁:小說
- 作者:陳琳
作品原文,作品詮釋,
作品原文
作者:東漢·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爽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談笑。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岳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雲王者之師,有徵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嘆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敘王師曠盪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徵,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有星流景集,飈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
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絀,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年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雎渙者,學藻繪之彩。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埛,鴻雀戢翼於污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揮勁融,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文選》)
作品詮釋
東漢·陳琳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最有意思的是開頭和結尾。
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第三冊中論及陳琳《為曹洪與魏太子書》時寫道:
趙毅衡這樣引申到:
錢锺書是形式論方面的專家,他在論陳琳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中指出:“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懽,故自竭老夫之思。”曹洪明知道曹丕不會相信他這個武夫會寫文詞如此漂亮的信,偏偏讓陳琳寫上:“這次不讓陳琳寫,我自己來出醜讓你開心一番吧。”錢锺書認為這是,“欲蓋彌彰,文之俳也。”
曹洪知道曹丕不會相信這封信出自他手,曹丕也明白他話中有話。曹丕覺得自己足以和陳琳比一番聰明。所以這是雙方的共謀,是假話假聽中的真話真聽,曹丕不會笨到去戳穿他的“謊言”;曹丕覺得這族叔,還有他的書記官,真能逗人。這實際上是一個默契的遊戲。
錢锺書進一步指出:這是講述虛構故事的必然框架:“告人以不可信之事,而先關其口:‘說來恐君不信’。”也就是說,我說出來你不相信,我接下來說的你肯定不會相信。所有的小說實際上都具有這樣的框架,而這種框架其實是一種文化契約。傳送者(作家)知道自己是在作戲,而接受者(讀者)
知道自己看的是假戲,也知道不必當真,這就是假戲假看——所有的小說家都享受了可以自由作假這個條件,接受者在此時則只要去欣賞作家的生花妙筆、演員的唱功和畫家的筆法就行了。這就是說,在假戲假看這個類型中,傳送者知道對方沒有要求他有“事實性”的誠信,他反而可以自由地作假;發出的符號文本是一種虛構,不必對“事實性”負責。接收者看到文本之假,也明白他不必當真,他在文本中欣賞傳送者“作假”的技巧。修辭不是立其誠,而是以巧悅人,所有的小說家都分享這個契約。
當然,有時在虛構的文本中也可能包括正義的或真的東西,前者如《洛麗塔》,監獄長看了這篇小說後,認為男主人公的懺悔好,對教育下一代有益;後者如《格列佛遊記》,假話之中也夾雜著真話。此時,接收者可能看出作者的意圖作偽,但是認為小說文本在虛假表意中也具有認知價值,因而將計就計坦然地接收,以偽為偽。
無論是誰講一個故事,聽者如果願意聽下去,就必須擱置對虛假的挑戰。信息傳送者假扮一個人格,你聽的時候不必當真,你可以分裂出一個人格,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你就不能順利地聽。此時,敘事就變成了一個撒謊的問題。不言而喻,最好的撒謊就是虛構,就是藝術想像。撒謊在不同的文化中有巨大的差距,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存在虛構,而虛構必須有假話的框架。中國人很會玩計策,我們把這一些謀略都稱之為智慧,因為這種作為謀略的謊言通常是在目的高尚、道德宏大的前提下進行的。比如說孫臏、諸葛亮,他們撒謊的目的是為了達到某種崇高的目標。在這方面,藝術也許過於小道,所以論想像力,可以說阿拉伯人的想像力最好,讓歐洲人都覺得阿拉伯人最會撒謊,這個說法當然不很恰當,但阿拉伯人的想像力的確是很豐富。
符號到底說的是真相還是假象?符號應該是能說真相才能說假象。按虛構性/事實性標準,敘述可以分成:(1)事實性敘述:新聞、歷史、法庭辯詞等;(2)虛構性敘述:小說、戲劇、電影、電子遊戲等;(3)擬事實性敘述:廣告、宣傳、預言等;(4)擬虛構性敘述:夢境、白日夢、幻想等。這個分類捲入一個更加根本性的問題:虛構性敘述,本質上就是謊言,因而不能以真假論之。各種逆時形式的敘述,實際上已經承諾敘述者所說的都是真的。這就是以假當真的情況,麥克尤恩的小說《贖罪》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以假當假和以假當真是藝術欣賞的兩種不同的境界。多數人看電視的時候,忘記了是電視,隨之而哭,隨之而笑,忘記了各種假的痕跡。假的痕跡消失,就出現了逼真性——就是你忘掉它是藝術,把它當成是真的。這種情況,反而是大部分人欣賞藝術或者是解讀符號所達到的境界。以假當假就是我剛才所舉的例子中,就是曹丕的境界,就是陳琳、曹洪的境界,就是我演假戲,你也把它當作假戲去看;當然,這裡面也有真的:在戲中,在小說中,你看作者的文字多巧、多妙,而其敘事技巧又是多么的高超,這是一個默契遊戲,但事實上達到這個默契遊戲的還不多——你看了《少年維特之煩惱》去自殺,這肯定是假戲真看!(引自《敘事·圖像·符號——當代文化景觀三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