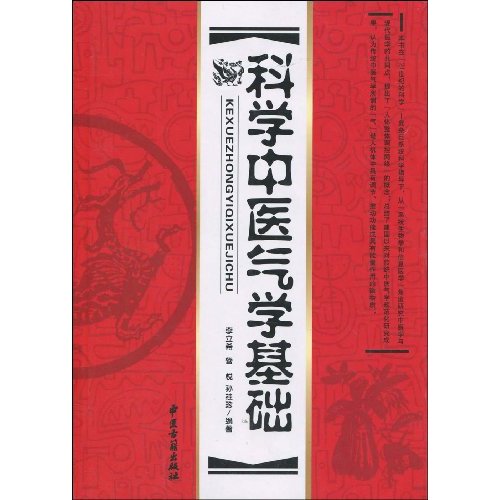張載提出了以“氣”為核心的宇宙結構說,發揮了孟子學說中的浩然之氣,尤其是闡發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二者是相助相成的 。其學說被稱為氣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氣學
- 提出者:張載
- 簡介:以“氣”為核心的宇宙結構說
張載的氣學,個人簡介,理論學說,氣學全文,目錄,全文,
張載的氣學
個人簡介
關於氣的學說或者學術
張載,字子厚,人稱橫渠先生,其學被稱為氣學,有《橫渠易學》、《正蒙》、《經學理崫》、《張子語錄》,收入《張載集》。
理論學說
他認為世界是由兩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看得見的萬物,一部分是看不見的,而兩部分都是由"氣"組成的。"氣"有兩種存在方式,一種是凝聚,一種是消散。消散也不是消失得沒有此物,只不過是人們的肉眼看不到而已。他用“太虛”表示“氣”的消散狀態,這是本來的原始狀態,"氣"是"太虛"與萬物的合稱。張載又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
羅欽順認為“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認為“氣”是宇宙萬物的根本,“理”是“氣”運動變化的條理秩序;“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不同意朱熹“理與氣是二物”的見解。
王夫之批評程朱理學的唯心主義傾向。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又用“絪蘊生化”說明“氣”變化日新的性質。
氣學全文
目錄
第一章:氣學的概念
第二章:氣學的形成和發展
第三章:氣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1: 中醫學
2: 風水學
3: 文學
第四章:氣學存在的意義
全文
第一章 氣學的概念
“氣”的概念由先秦思想家提出。 他們 把“氣”做為一種範疇來加以研究和探討旳。如“氣貫長虹”“長虹”,說明氣運的空間之大之闊,是一個無限的空間,沒有距離的限制;而“氣呑萬里如虎”(辛棄疾)這個空間顯然是有限的,“萬里”是一段距離,有距離的限制;如“怒髮衝冠”(岳飛),“發”在這裡轉變成一種氣,成了達到了極限的“怒氣”,直把帽子都頂起來了。而“怎一個愁字了得”(李清照)“愁”在這裡也轉變成一種氣,一種達到極限的愁氣”。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把宇宙之“氣”(即雲氣)《說文》說:“氣,雲氣也。”加以發揮,提出了“萬物歸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這是中國古代哲人獨到的智慧。
綜觀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經典文獻中就有關“氣”的概念有以下八種涵義:
一:氣是指雲氣、風氣或大氣。如《說文》說:“氣,雲氣也。”《莊子·知北游》說:“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但需要指出,氣與“氣”不同:氣為雲氣、風氣,無形而運行不息;氣為“氣廩”之氣,指精米,與“餼”義同。如《說文》說:“氣,饋客芻米也,從米,氣聲。”這是天子待諸侯之禮,如《左傳·桓公十年》說:“齊人來氣諸侯。”
二:氣是指“六氣”。《左傳》以六氣論氣,如該書《昭公元年》說:“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三:氣是指天地陰陽之氣。氣是自然存在於天地之間的陰陽之氣,如《國語·周語上》說:“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荀子·禮論》說:“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
四:氣是指沖氣。沖氣即陰陽沖和之氣,是宇宙萬物的生長發育之原。如《老子。四十二章》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五:氣是指浩然之氣。《孟子》認為氣是充塞於天地之間並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浩然之氣。
六:氣是指精氣。如上述的《易傳》、《管子》等皆將氣規定為精或精氣。
七:氣是指陰陽五行之氣。《白虎通》認為陰陽五行之氣由宇宙中的“渾沌”一氣所分,如該書《天地》說:“渾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
通過對氣的各種涵義的分析,將氣的基本內涵一般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氣是構成宇宙(萬物)本原戓本體。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宇宙又稱天地、天下、太虛、寰宇、乾坤、宇空等等。古代唯物主義哲學家認為“氣”是世界的物質本原。東漢·王充謂“天地合氣,萬物自生”(《論衡·自然》)。北宋·張載認為“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正蒙·太和》)。氣是一種肉眼難以相及的至精至微的物質。氣和物是統一的,故曰:“善言氣者,必彰於物”(《素問·氣交變大論》)。氣是世界的本原,是構成宇宙的元初物質,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基本元素。“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摁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日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鹹章”(《素問·天元紀大論》引《太始天元冊》語)。《內經》稱宇宙為太虛,在廣闊無垠的宇宙虛空中,充滿著無窮無盡具有生化能力的元氣。元氣(即具有本原意義之氣)敷布宇空,統攝大地,天道以資始,地道以資生。一切有形之體皆賴元氣生化而生成。元氣是宇宙的始基,是世界萬物的淵源和歸宿。氣是構成宇宙的本始物質,氣本為一,分為陰陽,氣是陰陽二氣的矛盾統一體。“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天氣”是自然界的清陽之氣,“地氣”是自然界的濁陰之氣。陰氣濁重,降而凝聚成為有形的物體,構成了五彩繽紛的大地;陽氣清輕,升而化散為無形的太虛,形成了蒼莽的天宇。天地陰陽之氣上升下降,彼此交感而形成天地間的萬事萬物。“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素問·至真要大論》)。先秦和秦漢時期的道家提出了以“道”為宇宙本原的宇宙觀,並創立了“道-氣-物”和“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萬物”的宇宙發生模式,將氣作為“道”或“太易”化生宇宙萬物的中間環節。《老子》、《莊子》、《管子》、《淮南子》等皆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產生的最初本原或本體。如《淮南子。泰族訓》說:“夫道者,有形者皆生焉。”《列子·天瑞》則說:“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沌。”至兩漢,元氣說盛行。《春秋繁露》認為,“元者,始也”,“元者,為萬物之本”,並產生於“天地之前”。《論衡》認為元氣自然存在,產生天地萬物和人的道德精神。該書《自然》說:“天地合氣,萬物自生。”《論死》說:“氣之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氣為萬物之本原,故稱為“元氣”。元氣是構成宇宙萬物和人類的形體與道德精神的唯一本原,其上沒有“道”或“太易”等,因而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最高範疇,後世稱為“元氣-元論”或“氣-元論”或“氣本原論”。所以說,氣是構成宇宙的本原,是宇宙統一性的物質基礎。氣是構成宇宙最基本的物質要素,宇宙是氣可以感知的有形存在形式。氣規定宇宙的本質,氣的內涵揭示了氣的物質性和普遍性、無限性和永恆性。
二:氣是宇宙(萬物)運動的根本屬性。原始混沌的氣因清濁不同而出現陰陽二氣。陰陽為固有的兩種對立要素,即“陰陽有定性而無定質’’(《張子正蒙注·卷一》)。陰陽矛盾對立形成了氣的永恆的有規律的運動變化。氣始終處於運動變化之中,或動靜、聚散,或絪緼;清濁,或升降、屈伸,以運動變化作為自己存在的條件或形式。天地運動一氣,轂萬物而生。《內經》稱氣的運動為“變”、“化”,“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素問·天元紀大論》)。“物之生,從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素問·六微旨大論》)。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變化,不論是動植物的生育繁衍,還是無生命物體的生化聚散,天地萬物的生成、發展和變更、凋亡,無不根源於氣的運動。“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素問·六微旨大論》)。氣有勝復作用,即氣本身具有克制與反克制的能力。氣這種勝與復、克制與反克制的作用,是氣自身運動的根源。氣分陰陽,陰陽相錯,而變由生。陰陽相錯,又稱陰陽交錯、陰陽交感,即陰陽的相互作用。陰陽相錯是氣運動變化的根本原因。換言之,陰陽的對立統一是氣運動變化的根源和宇宙總規律,故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氣的陰陽對立統一運動,表現為天地上下、升降、出入、動靜、聚散、清濁的相互交感,這是氣運動的具體表現形式。《內經》以“升降出入”四字概之,故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素問·六微旨大論》)。
氣的運動促使人們也持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事物,如宋人張載認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6]這就把由氣衍生的萬物歸結為氣,即氣不僅化生萬物,而且萬物也因此體現出氣的運動變化的屬性。再進一步說,人也是由氣的聚散所致,人的生死、善惡、榮辱等都可用“氣”來說明終級原因,因此在氣的運動中,人一方面必須順其自然,另一方面也可適度調養,孟子的“養氣”說,黃老思想中的調氣等學說除了具有我們現在所說的調整精神、身體的意思外,還包括將已之一身與天地萬物溝通,以天地四時調順來養育已之一身的意思。這樣,人生活在運動著的世界,並且可以通過得“道”來參與運動著的宇宙。“氣”的運動這一觀點使中國古代思想對於事物的相對性有所認識,由於運動,事物會發生由此向彼的轉化,彼和此並不是不能逾越的鴻溝,同時在評判事物時,由於人這一評判相位變化運動之中的,萬物以人為尺度的評判前提因人的評判相位變化而發生變化,如《老子·四十二章》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氣由道生,無形而運行於天地之間,聚合而生萬物,故《老子·四十章》又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認為氣存在於宇宙之中,“通天下一氣耳”,而人類也由此氣聚合而成,如該書《知北游》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列子》則認為“有形者生於無形”,而氣生於“太易”,無形無狀,“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此氣“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列子·天瑞》)。
因此,氣的運動決定了宇宙間的運動和變化。
三:氣是宇宙(萬物)之間聯繫的中介。氣充塞於宇宙萬物之中,使它們之間相互貫通,相互影響,處於和諧有序的運動之中。如《易傳·乾·文言》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呂氏春秋·召類》說:“類同則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
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著宇宙萬物的發生髮展與變化。氣分為陰陽二氣或五行之氣,陰陽二氣的升降交感、氤氳合和,五行之氣的運動攙和,產生了宇宙萬物並推動著它們的發展與變化。如《易傳·繫辭上》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易傳·鹹》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管子·乘馬》說:“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呂氏春秋·大樂》說:“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
氣是陰陽的對立統一體,是一切運動變化的根源。氣之陰陽兩端相互感應而產生了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繫。有差異就有統一,有異同就有感應。“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正蒙·乾稱》)。相互感應和普遍聯繫是宇宙萬物的普遍規律。“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或以異相應”,“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感如影響,無復先後,有動必藏,鹹感而應,故曰鹹速也”(《橫渠易說·下經·鹹》)。陰陽二氣的相互感應產生了天地萬物之間的普遍聯繫,使物質世界不斷地運動變化。這種陰陽二氣相互感應的思想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把人與自然、社會視為一個具有普遍聯繫的有機整體。
氣是人的一種道德境界。如《孟子》認為,存在於人體內的氣為“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浩然之氣”是一種道德精神,受人的意志的支配,人的意志堅定,則成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大丈夫。 氣又是推動和調控人體生命活動的動力源泉。人的壽夭,與氣密切相關。氣的運動停止,則標誌著人體生命活動的終止。人要長壽,則必須珍惜、保養運行於人體中的氣。如《管子·樞言》說:“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
綜上所述,宇宙是氣的本原,天地是氣分離後的生成物,人是氣的特殊的聚散方式,因此,天地之氣與人之氣可以互相轉化。人與宇宙(萬物)、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對象的兩極對立的思維法則被消解了,人對宇宙的認識,不是以人的實踐來探究宇宙的方方面面,而是人以內省的方式來追詢自我的意識,因為在“氣”的觀點看來人與世界是同質同性的,不直接問諸內心而去探求外界是捨近求遠,捨本逐末。再說作為萬物的根本“氣”,根源就是回到氣的存在狀態,所以說中國古代哲人把“氣”作為哲學範疇,只是重視它整體的綜合,而輕視其具體的分析。從而導致了“氣”的哲學概念與命題上出現的偏差顯而易見。“氣”的哲學範疇,在中國道家學說、宋代程朱理學、清代戴震等人的學說中都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並且內化為一種氣的思想。既是客觀的實在,又是主觀的道德精神。所以說,氣學是一門研究氣的基本內涵,揭示氣所涵蓋自然、社會、人生的獨立學科。
第二章 氣學的形成和氣學派主要代表人物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立位而成章。”(《說卦》)。所說天道為“陰與陽”,是就天之氣而說的,是指陰陽之氣。聖人作《易》時之所以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為了順從人的本性與自然現象的必然性。換言之,這也就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其所以要窮盡物之理與窮盡人之性,乃是為了使人最終能夠達到與自然規律相一致。
《易經》的出現給中國本土文化的發展大致確定了方向,即整個宇宙只有天地人與氣陰陽學說(包括五行和八卦)間兩個方面的互動,整體上顯得籠統和模糊。是中國古代哲人(即先秦儒學)對哲學理論研究探討無法細緻深入下去的主要原因。這樣造成了周孔儒學只有倫理道德的說教,卻不能給這種倫理道德以本體上、實用上的說明。這無疑是儒家文化在理論上的一個無比重大缺陷。 氣一元論認為,氣是宇宙中自然存在的一種極細微物質,它自身的升降聚散運動推動著宇宙萬物的發生髮展和變化。古代哲學的氣學說,是研究氣的概念、結構和運動規律,並用以解釋宇宙萬物發生、發展、變化的一種古代宇宙觀和方法論。 古代哲學的“元氣說”始於西漢時期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該書《重政》說:“元者,為萬物之本。”東漢張衡、《古微書》、《易緯 . 乾鑿度》等有所發展,但他們認為元氣由“玄”或“道”或“太易”產生,是玄、道或太易生萬物的中間環節,還未發展到“氣本原論”。王充的《論衡》認為氣即元氣,自然存在,沒有任何東西在元氣之前,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支配元氣,元氣是宇宙的最初本原,因而確立了“元氣本原論”,標誌著“氣一元論”的形成。兩漢以前有關氣的各種思想、各種學說,至此也大多被“元氣一元論”所同化。
從“元氣一元論”的形成過程可見,兩漢時期對宇宙本原的探討,基本上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發展先秦道家的“道—氣—物”的宇宙生成模式,提出了“玄—元氣—萬物”和“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萬物”的宇宙發生模式,把元氣作為“玄”和“太易”化生宇宙萬物的中間環節和質料;二是以王充的《論衡》為代表,明確提出了“元氣”為宇宙萬物之本原的思想,開“氣本論”哲學之先河。北宋張載的《正蒙》指出的“太虛無形,氣之本體”的“氣本體論”,是以氣為最高範疇的“氣一元論”哲學發展的最高峰。可以說理學思潮中的氣學流派由北宋張載所開創並成為其理論代表,中間經過南宋、元代的沉寂,至明代又重新崛起,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王夫之是明代氣學的重 要人物。明代氣學深受張載思想的影響,繼承了張載的氣本論哲學,並對張載思想加以發揮,把道、理、性建立在氣本論哲學的基礎之上。這是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修正,在宋明理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亦是氣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儒家氣學派代表主要有張載、羅欽順、王廷相、吳廷翰與王夫之,以及清代的戴震等。
一:張載的氣學
(一)張載的生平與著述
(1)張載簡介
張載(1020-1077),北宋大儒,哲學家,理學創始人之一,理學支脈“關學”創始人,封先賢,奉祀孔廟西廡第38位。字子厚,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徙家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進士,授祁州司法參軍,調丹州雲岩令。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神宗熙寧二年(1069),除崇文院校書。次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同年冬告歸,十二月乙亥卒於道,年五十八。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賜謚明公。
事見《張子全書》卷一五附宋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宋史》卷四二七有傳。
(2)張載生平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常對西部邊境侵擾,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西夏入侵,慶曆四年(1044)十月議和。朝廷向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這些國家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年僅二十一歲的張載刺激極大,他就向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邊議九條》,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演(郴縣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為國家建功立業,博取功名。范在延州(今延安)軍府召見了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鄉,收復失地的打算得到了范的熱情讚揚,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他道:“儒家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意思是說你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而勉勵他去讀《中庸》,在儒學上下功夫。張載聽從了范的勸告,回家刻苦攻讀《中庸》,仍感不滿意。於是遍讀佛學、道家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家學說上來,經過十多年的攻讀,終於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繫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系。
慶曆二年(1042)范仲淹為防禦西夏南侵,在安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築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仁宗嘉祐二年(1057)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文彥博宰相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一天晚上,遇洛陽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的見解,感到自己學得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今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橫渠先生行狀》)。於是撤席罷講,但又對二程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橫渠先生行狀》,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積極開拓精神,他的《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張載中進士後,先後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雲岩縣令(今陝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簽書謂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作雲岩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里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覆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使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經略使蔡挺的關係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諮詢。他曾說服蔡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並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在此時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他的軍事政治才能。
神宗熙寧二年(1069)御史中丞呂公著(晦叔)向神宗推薦張載,稱讚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為政的方法,張載“皆以漸復三代(即夏、商、周)為對”。神宗聽了非常滿意,高興地說:“你先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作些事,以後我還要重用你。”張載認為自己剛調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了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後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持。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勝任,想請你幫忙,你願意嗎?”張載回答說:“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與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家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絕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擬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准。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污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衝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於是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後,依靠家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制兩項實踐。為了訓誡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著遺蹟,至今這一帶還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熙寧十年(1077)秦風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以“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為由,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說:“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辭,庶幾有遇焉。”意思是說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辭,藉此機會可施行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便帶病入京。神宗讓他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向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制。唯張載認為可行,並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路經洛陽見到二程時說:“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當年農曆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舍,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臨終時只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的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後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才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三月,將張載葬於橫渠大振谷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宋寧宗賜謚“明公”,淳祐元年(1241),賜封郿伯,從祀孔廟,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改稱先儒張子。
(3)張載思想
張載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關學的創始人,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其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以後的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兩代政府視為哲學的代表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張載認為,宇宙的本原是氣。他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有聚散而無生天,氣聚則有形而見形成萬物,氣散則無形可見化為太虛。他認為宇宙是一個無始無終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滿浮與沉、升與降、動與靜等矛盾的對立運動。他還把事物的矛盾變化概括為“兩與一”的關係,說:“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認為兩與一互相聯繫、互相依存,“有兩則有一”,“若一則有兩”。在認識論方面,他提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區別,見聞之知是由感覺經驗得來的,德性之知是由修養獲得的精神境界,進入這種境界的人就能“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在社會倫理方面,他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主張通過道德修養和認識能力的擴充去“盡性”。他主張溫和的社會變革,實行井田制,實現均平,“富者不失其富”貧者“不失其貧”。
張載還提倡“民胞物與”思想。他在《西銘》中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無與也。”乾坤是天地的代稱,天地是萬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混合,處於宇宙之中,因為三者都是“氣”聚而成的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因此人類是我的同胞,萬物是我的朋友,萬物與人的本性是一致的。
(4)張載著作
張載著有《崇文集》十卷(已佚),《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等,明嘉靖間呂柟編有《張子鈔釋》,清乾隆間刊有《張子全書》,後世編為《張載集》。
(二):張載對後世氣家的影響。
張載是氣學的開創者和理論代表,他對氣學流派及整個宋明理學均有重要影響。他提出“太虛即氣”[1]《正蒙·太和》的氣本論宇宙觀,認為無形的太虛是氣的本然狀態,氣聚成形而為萬物,形散返原而復歸於太虛。他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1]《正蒙·太和》指出無形的太虛與有形的萬物是氣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態,宇宙萬物均以氣為存在的根據。在張載氣本論的哲學體系里,氣是最高範疇,道和理統一於氣,體現了氣運動變化的過程和規律。他說:“由氣化,有道之名。”[1]《正蒙·太和》認為道是“氣化”,即物質性的氣運動變化的過程,離開了氣和氣的運動變化,則無所謂道。張載並指出:“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1]《正蒙·太和》把氣在聚散變化中“順而不妄”的條理即規律稱之為理,可見道和理均不能離開氣而獨立存在。張載所謂性,是由虛與氣結合而構成。他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1]《正蒙·太和》所謂虛,即太虛,它是氣的本然狀態。“太虛者,氣之體。”[1]《正蒙·乾稱》張載認為,太虛是天地萬物的本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1]《張子語錄中》;指出“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1]《張子語錄下》,而天地萬物均出自於太虛,以虛為祖,即是以虛為天地萬物產生的本原。張載以物質性的虛與氣作為構成性的要素,其性便以虛和氣作為存在的根據,認為氣是宇宙的本體,性不具本體的意義,性不過是氣“虛而神”的屬性。“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1]《正蒙·乾稱》。在這裡,張載強調性只是“氣之性”,性則因氣而存在,性是氣“固有”的本質屬性,而從屬於氣。
雖然張載把道、理、性作為氣運動變化的過程和規律及屬性,但他以為道、理、性均具有儒家倫理的內涵和屬性。他說:“人倫,道之大原。”[1]《張子語錄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1]《張子語錄下》。主張“變化氣質”,“製得習俗之氣”[1]《經學理窟·學大原上》,以符合天理的原則。強調“守禮”、“持性”而不違道,“由窮理而盡性”[1]《正蒙·誠明》。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相分的理論,更重要的是他主張變化氣質,克服氣質的偏差,通過學習,復歸天地之性。並提出“立天理”[1]《經學理窟·義理》的命題,反對“今之人滅天理而窮人慾”[1]《經學理窟·義理》。這是對宋明理學的理論貢獻。張載提出的“心統性情”的命題也被朱熹譽為“顛撲不破”的理學原理。可見,張載雖提出氣一元論的哲學思想,而與程(指程顥和程頤)朱(指朱熹)的理本論和陸(指陸九淵)王(指王守仁)的心本論不同,但他思想體系中的一系列命題和理論均表明他是一位重要的理學奠基人,對後世理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故不可因其具有氣本論思想就把他排除在理學之外。
二:羅欽順的氣學
(一)羅欽順的生平與著述
羅欽順早年曾鑽研過佛學,“既悟其非,乃力排之”。晚年批判地改造了朱熹的理學,建立了氣本論的自然哲學。《困知記》一書是他的主要哲學著作, 此外還有《整庵存稿》20卷、《整庵續稿》13卷。
羅欽順是從程朱理學中分化出來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在理學演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哲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在理氣關係問題上提出了理在氣中的觀點,用氣本論代替了朱熹的理本論。他認為,氣是世界萬物的本原,“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理只是氣之理,並不是“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更不是“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他否定理是離氣而獨立存在的主宰,批評朱熹所謂理“墮”在氣中、“泊”在氣上,以及理氣“不離不雜”等說法是“將理氣作二物看”。
他認為,氣產生了天地萬物,萬物變化千條萬緒,紛紜??,而“雜不克亂”,其間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事物變化的規律性、必然性便是理。理須從氣的聚散、往來的“轉折處”去看。
羅欽順認為理氣不是二物。但並不認為理等於氣。“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理作為物質運動變化的規律,同氣不可分離,但它又是和事物有區別的。
他討論理和物的關係, 認為 “有此物即有此理”,“無此物即無此理”,但他認為整個宇宙是不生不滅的,“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
羅欽順對朱熹的“理一分殊”說,作了自己的解釋,指出“理一”是一氣運動的總規律,“分殊”是萬物具有的特殊規律,二者都根源於氣,不是先於氣而存在的。“氣本一也”,氣分為陰陽、產生萬物,一理即散為萬理,這就叫“一本萬殊”。太極雖是眾理的總名,但以氣為體。分陰分陽之氣是太極之體,一陰一陽之道是太極之用。否定了太極之理先於陰陽而存在以及太極生陰陽、理生氣的說法。把朱熹的唯心主義理氣體用說顛倒了過來。
在羅欽順看來,理一和分殊的關係是一般和個別的關係,分殊來源於氣化流行,理一即“在分殊之中”。個別不離一般,一般在個別中。人的認識也必須先從個別開始,然後達到一般,即由具體到抽象。他把朱熹哲學中關於一般和個別的辯證法思想,從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中剝離出來,置於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
在心物問題上,羅欽順批判了以心法起滅天地,以萬物為虛幻的佛學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說,唯物地解決了主觀同客觀的關係問題,提出了初步的反映論學說。他肯定,“盈天地之間此惟萬物”,人也是萬物中的一物。心作為認識器官,雖有靈明,但也是一物。心之官則思,能“推見事物之數,究知事物之理”,認識其客觀規律,因此具有很大能動性。但是,如果“認精神以為道”,那就根本錯了。批評心學認為心“可以範圍天地”的觀點,說它竟“私造化以為已物”,顛倒了主客關係。
他批判地改造、繼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指出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是格此心;窮理是窮天下事物之理,不是窮心中之理。他反對“反觀內省”的認識方法,主張“資於外求”,就天地萬物上講求其理。認為只要運用“推知”、“統會”等思維方法,就能認識萬物之理,達到“通徹無間”、內外合一的境界。
在理學演變中,羅欽順最早批判了“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提出了理欲統一的觀點。他不同意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的區分,認為性只有一個,即氣之理。如果區分天命、氣質,就是一性而兩名。他認為人慾出於天性,人之有欲,是無可非議的,正如喜怒哀樂之情不是惡一樣,欲同樣不是惡,也不可“去”。只有恣情縱慾,才會流於惡。他主張以理節慾,反對存理滅欲,承認人的物質欲望的合理性。
羅欽順沒有完全擺脫程朱的影響,在認識論上,他接受了朱熹“理具於心”的觀點,承認事物之理即心中所具之理,窮理窮到極處,就能“一以貫之”,這叫合內外之道。在人性論上,他接受了“性即理”的觀點,承認心中所具之理,也就是仁義禮智之性。故窮理和盡心知性是一回事。這些都是羅欽順思想的局限性。
(二)羅欽順復興氣學的理論意義和對張載思想的發揮。
羅欽順提出“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2]卷下的思想,認為氣是理的基礎,須從氣中認識理,指出:“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2]卷下認為理是氣聚散變化的條理,有氣才有理。這是對張載思想的繼承,也是對程朱理本論的否定。
受張載氣本論哲學的影響,羅欽順從心本於氣的思想出發,根本否定心學宇宙觀。他說:“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困知記]續卷上佛教以心法起滅天地的心本論思想遭到張載的批判,羅欽順對此十分贊成,他藉此來批判以心為宇宙本原的思想,認為佛教不識陰陽之氣,不懂心的來源,所以陷入以心為本的謬誤。他說:“佛氏初不識陰陽為何物,固無由知所謂道,所謂神。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為空寂;推其用而偏於陰界入,則以為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為性,萬無是處。”[困知記]續卷上羅欽順以氣本論思想批駁了佛教以心為空寂、以心為物、以心為性的理論。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抽掉了佛教心本論的基礎。
羅欽順並把楊簡心學與佛教心學聯繫起來加以批判,指出楊簡所說的“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這句話與佛教心學的觀點無異,“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2]續卷下通過否定楊簡的觀點來否定心學宇宙觀,並反對心學家所謂的“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困知記]續卷下的心學觀點,認為人心的變化不過是反映了天地人物的變化,批評把天地萬物的產生歸於吾心的思想。羅欽順站在氣學立場,否定心學宇宙觀,在明代心學興起之際具有獨特的理論意義。
羅欽順站在氣學的立場,提出性為陰陽之理的思想,否定心學宇宙觀,把人慾納入性的範疇,反對理學去人慾的觀念;在氣本論的前提下,提出性體心用論;以《尚書·大禹謨》、《論語》、《孟子》等經書為依據,論述其心性有別的思想,強調心性的區分,據此以批判佛教與陸王心學,從時代的高度清算了程朱的理本論、陸王以及佛教心性論的弊端。
羅欽順提出性為陰陽之理的思想,認為性是人之生理,最終從屬於氣;性成於夫婦居室的生化之中;性必有欲,性包括了欲,欲為天性而不可去。他說:“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為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2]續卷上認為凡天地間的萬物均以陰陽之氣為自身存在的根據,萬物由陰陽之氣而成形;由陰陽之理而為性,性即陰陽之理,陰陽之理即陰陽之氣的規律和屬性。也就是說,性是由陰陽之氣所產生的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及規律。由此,羅欽順把性概括為人之生理。他說:“性者,人之生理。”[2]卷上所謂人之生理,指在告子“生之謂性”的基礎上,以生之理為性。他認為,只講生還不是性,生之理才是性。其生源於氣,其“理須就氣上認取”[2]卷下,故其性最終從屬於氣。羅欽順所謂的“理”,乃是“氣”的聚散變化之理。由於“理”通過“氣”的聚散得以表現,所以在羅欽順的哲學裡,“氣”是最根本的,“理”則從屬於“氣”,這與朱熹的理氣說形成對照,反映出氣本論與理本論哲學的差異。在羅欽順看來,“理”作為“氣”的聚散之理,“理須就氣上認取”;“性”作為“人之生理”,其生源於氣,最終“性”、“理”均從屬於“氣”。這是他與理學思潮中程朱理本論一派和胡宏、張?木式性本論一派的區別,也是對張載性論的發揮。在這個問題上,羅欽順汲取張載“飲食男女皆性也”[1]《橫渠易說·繫辭上》的觀點,明確提出“性必有欲”的思想,體現了氣學家性論的特點。他把欲望作為性的內涵和固有的本能,指出:“夫性必有欲,非人也,天也。”[2]三續認為欲望即是天性,是人人自然具有而不可避免的,所以不應去人慾。這是對程朱“存天理,去人慾”思想的修正。由此他對宋儒過分壓抑人慾的主張提出批評:“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姿情縱慾而不知反,斯為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慾’、‘遏人慾’為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2]卷下認為性的善與惡取決於對欲的調節如何,使欲符合“當然之則”即為善,姿情縱慾則為惡。既反對過分“去人慾”,又反對縱慾,而主張在肯定人慾的基礎上加以節慾。他說:“既曰天矣,其可去乎!欲之有節無節,非天也,人也。既曰人矣,其可縱乎!”[2]三續指出欲既然是人的天性,就不能去掉,只能加以節制。羅欽順“性必有欲”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和喜怒哀樂之情,這是對張載思想的發揮,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和學術價值。
在認識論上,羅欽順汲取張載“人本無心,因物為心”[1]《張子語錄下》,即人的主觀認知之心以物為根據的思想,並加以發揮,提出人心對事物及其規律的認識,須與客觀事物相吻合而無二致,才能獲得對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認識。因此應遵循《大學》先格物後致知之序,並由此批評了王陽明的良知說。他說:
須就天地萬物上講求其理,……人固萬物中之一物爾,須灼然見得此理之在天地者與其在人心者無二,在人心者與其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二,在鳥獸草木金石者與其在天地者無二,方可謂之物格知至,方可謂之知性知天,不然只是揣摩臆度而已。……今以良知為天理,即不知天地萬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驟窺,山河大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萬物眾多,未易遍舉,草木金石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邪!……以此觀之,良知之非天理,豈不明甚矣乎![2]附錄《答歐陽少司成崇一》乙未春
強調須從天地萬物上講求其理,即理是客觀事物的規律,人心之理不過是對事物之理的反映,通過認識事物而得到。故人心之理須與天地萬物之理相符合,而不得有二,人的認識達到了這種程度,才算是做到了“物格知至”。這反映了羅欽順的格物致知論是建立在對客觀事物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其知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不是主觀自生的。由此,羅欽順批評了王陽明的以良知為天理說,指出萬物之中並未有良知,良知只在人心,不在天地萬物;而事物之理則具有普遍性,它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故良知與理不同,不能把良知作為天理。由於良知並不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所以羅欽順將良知“置之度外”,也就是否定了良知的本體地位。這是對當時方興未艾的王陽明良知說展開的批評,表現出羅欽順思想的時代特色及對張載認識論的發展。
三:王廷相的氣學
(一)王廷相的生平和著述
1504年任兵部給事中,因忤中官劉瑾、廖鏜,被誣下獄,謫贛榆縣丞。當時正遇上北方大同邊境告急,王廷相上書陳述採取權宜振刷之策,初步展露在軍事上進行改革的宏圖大志及非凡的才能,後來逐步遷升為山東提軍副史、湖廣按察使、四川巡撫右副御史、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太子太保等職。
嘉靖二十年(1541)因受郭勛一案牽連,革職為民,被罷免官職回歸故里。
1544年病逝,年七十一,埋葬於儀封城東二里許(即今儀封鄉老君營村南),謚肅敏。
王廷相以經術稱於世,對天文、音律、輿圖、農業亦有成就,又擅長詩、詞、文。曾三督學政:北畿學政、四川按察使提學僉事、山東提學副使,對地方教育尤多貢獻。時人稱“自舉進士至歷宮保中、兩任郡邑、三督學校,以禮范海內者,四十餘年”(《喪禮備纂·張鹵序》)。學術上宗張載“氣一元”論,認為“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無道、無理” (《雅述》上)。否定佛道兩家“有”生於“空”和“無”的說法,反對程朱學派“理在氣先”的觀點。認為“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橫渠理氣辨》)。主張“性生於氣”,兩者互相依存,不可分離,“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 (《答薛君采論性書》)。重視 “見聞之知”,否定先天的“德性之知”和“良知”,強調知識是“思”和“見聞”相結合的產物,在實踐中練習才是“真知”。提倡“知行並舉”,反對“泛講以求知”。認為“學以濟世”,故在學習方法上,強調“致知”和“履事”。道德修養上,反對“虛靜以養心”,主張內外交參,動靜結合,心虛氣和,因時制宜等方法。
一生著作甚豐,有《慎言》、《雅述》、《橫渠理氣辨》、《喪禮備纂》等,編入《王氏家藏集》、《王浚川所著書》中。
受張載氣本論哲學的影響,王廷相認為,氣既是宇宙的本體,又是構成萬物的材料。他說:“元氣化為萬物,萬物各受元氣而生。”[3]《雅述》上篇氣是一種無形而實有的客觀實在。“氣雖無形可見,卻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3]《內台集》卷4《答何柏齋造化論十四首》氣無形,物有形,然而氣並非虛寂空冥一無所有,無形之氣即是有形之物的根源。“是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也。”[3]《內台集》卷4《答何柏齋造化論十四首》氣為虛,形為實,虛實是指氣本體與氣所產生的有形之物的形態。氣是形之種,所謂種,即種子、根源,指有形之物由無形之氣產生;形是氣之化,即有形之物是氣化的產物,氣在運動變化中產生萬物。王廷相認為,萬物的產生是一個由虛到實、從無形到有形的過程,虛與無形是指氣本體而言,實與有形是指氣化生物而言,但無論虛與實、無形與有形都統一於氣,是氣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態。王廷相以“無形”和“實有”言氣,既把氣本體與氣化之物區別開,又把二者統一於氣。這是對張載太虛無形、萬物有形思想的繼承和發揮。
王廷相根本否定當時流行的以觀念性的理(道)為宇宙本體的程朱理本論哲學。他指出:“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為道之本。”[3]《雅述》上篇在王廷相氣一元論的哲學體系里,元氣為最高範疇,作為宇宙本原的元氣是道的本體,離開了元氣則無道,道不過是元氣產生人、物之後,存在於人和物之中的道理。在理氣關係上,王廷相提出“理生於氣”的命題。他說:“理生於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故曰‘神與性皆氣所固有。’”[3]《王氏家藏集》卷33《橫渠理氣辯》王廷相在對張載理氣思想的闡釋中,論證了“理生於氣”的觀點。他認為,理作為事物的規律,由作為萬物之本原的氣所產生,有氣才有理,無氣則無理,理根源於氣,不能離氣而獨存,正如性是氣“固有”的屬性一樣,理、性均不離氣而存在。王廷相針對程朱的理本論批評說:“萬理皆出於氣,無懸空獨立之理。”[3]《王氏家藏集》卷33《太極辯》指出理出於氣,而非理生氣,把被程朱顛倒的理氣關係重新加以扶正。
王廷相哲學中的心是一個認識論的哲學範疇,而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這是他與心學家的原則區別。其心緣於外物,是對客觀事物的反映。他從“由外以觸內”的認識路線出發,批評了心學“先內以操外”、由心到物的認識方法,從而堅持了反映論的原則。其心論是在氣一元論哲學的前提下,對以往認識論的清理和揚棄發展。
王廷相的認識論以心物結合、心緣外物而起為特徵,他認為心作為認知主體,本身無內容,是靜而虛的,然而它具有反映外物的功能。他說:“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靜而未感也,人心與造化之體皆然。使無外感,何有於動?故動者緣外而起者也。應在靜也,機在外也。已應矣,靜自如。故謂動以擾靜則可,謂動生於靜則不可,而況靜生於動乎?”[3]《雅述》上篇指出當心未感知外物時,它處於靜的狀態;當外物被心感知,心便處於動的狀態。心之動是緣外物而起,有了外界事物的運動,才有心對外物的反映。可見客觀事物的存在是第一性的,心感知外物是第二性的。由此他反對“動生於靜”,即外物的運動變化產生於心的觀點,而認為心的感應源於外物,並強調“人心有物,則以所物為主。”[3]《慎言》卷6《潛心篇》心物結合,是以物為主,而不是以心為主。這是對心本論哲學的否定,亦是對張載“人本無心,因物為心”思想的汲取。
王廷相從心反映外物、心緣外物而起的思想出發,對佛教和陸王心學作了批判。在批判中他提出“由外以觸內”,即由物到心的反映論的認識方法,以圖糾正當時出現的先內後外、“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的先驗的認識理論。王廷相批判了佛教以天地為幻妄、只講“禪定而無應”[3]《雅述》上篇、心中無物的思想。他說:“異端之學無物,靜而寂,寂而滅;吾儒之學有主,靜而感,感而應。”[3]《慎言》卷6《潛心篇》佛教雖以心法起滅天地,但終究不承認物的真實存在,心雖靜但物不存。王廷相則認為,心靜而有感,外物的存在是真實客觀的,心緣外物,感而應之,把心與外物相結合,批判佛教求靜而不動、言心而無物的?觀點。
王廷相對心學“先內以操外”觀點的批評尤具時代意義。王廷相之世,心學盛行,王陽明倡“是內非外”之說,遭到了王廷相的批評:“先內以操外,此謂之動心,動心不可有;由外以觸內,此謂之應心,應心不可無,非不可無,不能無也。……動心何有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應心之不能無也。”[3]《雅述》上篇王陽明心學認為,意念是心的發動處,意念所指,便是事物。這就是王廷相所批評的“先內以操外”的所謂“動心”。心學關於“動心”的觀點把外物看做是內心的產物,而與心緣外物而起的反映論原則相違,故遭到王廷相的批評。在對心學的批評中,他提出了“由外以觸內”,即由物到心的反映論原則,並把它稱之為“應心”,認為“應心”不可無,從認識路線上劃清了與王陽明“致良知”說的原則界限,亦是對張載認識論的發揮。
四:吳廷翰的氣學
(一) 吳廷翰 的生平和著述
吳廷翰(1491-1559),字嵩柏,號蘇原。明無為州人。正德十四年(1519)中舉,十六年(1521)取進士。歷官兵主事、戶部主事,至吏部文選司郎中。在吏部銓選中,推薦直言的諫官,忤上司之意,調任廣東僉事,轉任嶺南分巡道兼督學政。因彈劾權貴,改任浙江參議、山西參議。山西年荒,力請賑濟。出庫金,救活饑民十萬人,經手數萬兩金銀,一文不名。曾奉命采端溪硯,不持一硯歸。40餘歲辭官歸里,
代表作
專事著述,著有:《吉齋漫錄》、《櫝記》、《瓮記》、《叢言》、《志略考》、《湖山小稿》、《洞雲清響》等。以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反對客觀唯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在人性論上,主張只有氣質之性,別無他性。在天理、人慾問題上,主張天理在人慾之中。在形神問題上,批駁靈魂不滅,死後輪迴的見解。在認識上,堅持“德性之知”必須由於“聞見之知”肯定認識與學習和鍛鍊的關係。在知行關係問題上,認為知和行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知指導行,行非有知指導不可。他早年受外祖父張綸的啟迪,不贊同宋儒把性和氣區別開來作為善惡相對的劃分。中年以後,受樸素唯物論者王廷相(1474-1544)的影響,反對一些人認為深山大澤有鬼神的見解。他的哲學著作,深受日本學術界歡迎。1984年2月中華書局出版了由容肇祖點校的《吳廷翰集》。
第三章:氣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1: 中醫學
2: 風水學
3: 文學
第四章:氣學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