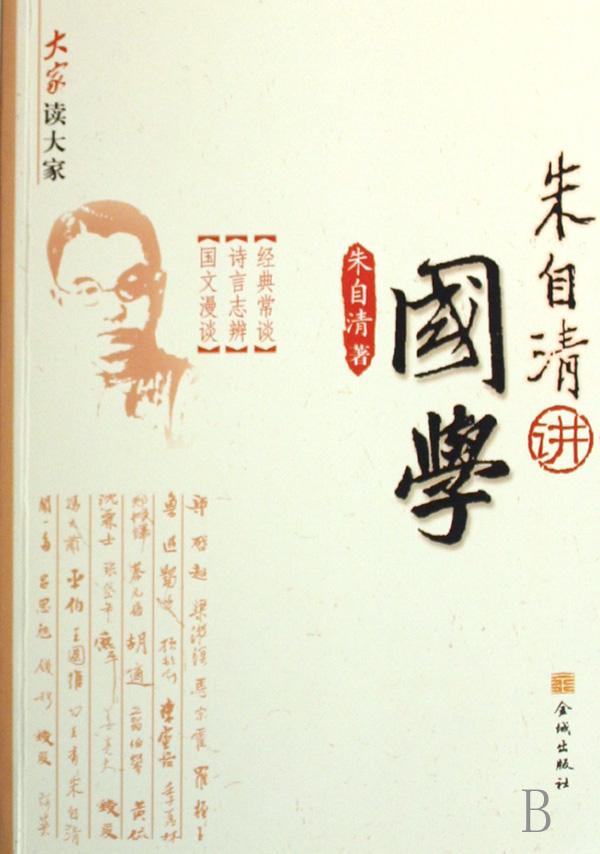《朱自清卷·大家國學》是朱自清大師的國學修為,今日大眾的國學養分也。 在“國學熱”經由電視講壇進入百姓視野、傳統文化過度娛樂化。 而國學常識卻明顯匱乏的當下,聽聽昨天的大師怎么說,是一種補課,更是一種參照。 《朱自清卷·大家國學》選自朱自清作品全集,包括經典常談、詩言志辨、文學論著(含晚期說理性的散文、雜文、語文教學、讀書指導方面的論文,和對文學創作、文學作品、學術論著的評論,以及少量小說、讀書筆記與譯文),詩歌部分(含新詩與舊體詩詞),學術論著部分,日記、書信部分等。通過《朱自清卷·大家國學》,讀者能了解朱自清先生作為我國現代文學家、學者和愛國民主戰士的一生,了解他的文學創作成就和對我國現代文學所作的傑出貢獻,以及他由狷者到鬥士的思想歷程。同時,日記、書信也為讀者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
基本介紹
- 書名:朱自清卷•大家國學
-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 頁數:333頁
- 開本:16
- 定價:30.00
- 作者:商金林 朱自清
- 出版日期:2008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105830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朱自清卷·大家國學》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 ——朱自清
作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家,朱自清說,我們非打破‘正統國學’的觀念不可”,“認識經史以外的材料的學術價值,認識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多讀新文藝作品。
《朱自清卷·大家國學》收專著《經典常談》和《詩言志辨》二種,以及單篇論文十篇,凸顯了朱先生的學術風範,也是後世學人的“經典讀本”。
《說文解字》第一,《史記》、《漢書》第九,六藝之教,風雅正變,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論雅俗共賞。
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
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 ——朱自清
作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家,朱自清說,我們非打破‘正統國學’的觀念不可”,“認識經史以外的材料的學術價值,認識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多讀新文藝作品。
《朱自清卷·大家國學》收專著《經典常談》和《詩言志辨》二種,以及單篇論文十篇,凸顯了朱先生的學術風範,也是後世學人的“經典讀本”。
《說文解字》第一,《史記》、《漢書》第九,六藝之教,風雅正變,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論雅俗共賞。
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
作者簡介
《朱自清卷·大家國學》選自朱自清作品全集,包括經典常談、詩言志辨、文學論著(含晚期說理性的散文、雜文、語文教學、讀書指導方面的論文,和對文學創作、文學作品、學術論著的評論,以及少量小說、讀書筆記與譯文),詩歌部分(含新詩與舊體詩詞),學術論著部分,日記、書信部分等。通過《朱自清卷·大家國學》,讀者能了解朱自清先生作為我國現代文學家、學者和愛國民主戰士的一生,了解他的文學創作成就和對我國現代文學所作的傑出貢獻,以及他由狷者到鬥士的思想歷程。同時,日記、書信也為讀者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
《大家國學》者,朱自清大師的國學修為,今日大眾的國學養分也。 在“國學熱”經由電視講壇進入百姓視野、傳統文化過度娛樂化。 而國學常識卻明顯匱乏的當下,聽聽昨天的大師怎么說,是一種補課,更是一種參照。
《大家國學》者,朱自清大師的國學修為,今日大眾的國學養分也。 在“國學熱”經由電視講壇進入百姓視野、傳統文化過度娛樂化。 而國學常識卻明顯匱乏的當下,聽聽昨天的大師怎么說,是一種補課,更是一種參照。
圖書目錄
總序
前言
經典常談
序
《說文解字》第一
《周易》第二
《尚書》第三
《詩經》第四
三《禮》第五
《春秋》三傳第六(《國語》附)
“四書”第七
《戰國策》第八
《史記》、《漢書》第九
諸子第十
辭賦第十一
詩第十二
文第十三
詩言志辨
序
詩言志
一 獻詩陳志
二 賦詩言志
三 教詩明志
四 作詩言
比興
一 毛詩鄭箋釋興
二 興義溯源
三 賦比興通釋
四 比興論詩
詩教
一 六藝之教
二 著述引詩
三 溫柔敦厚
正變
一 風雅正變
二 詩體正變
文學論著
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論詩學門徑
中國文評流別述略
詩多義舉例
陶詩的深度——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層冰堂五種》之三)
什麼是宋詩的精華——評石遺老人(陳衍)評點《宋詩精華錄》(商務印書館出版)
詩文評的發展——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二、三分冊:《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與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
論雅俗共賞
《文選序》“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說
前言
經典常談
序
《說文解字》第一
《周易》第二
《尚書》第三
《詩經》第四
三《禮》第五
《春秋》三傳第六(《國語》附)
“四書”第七
《戰國策》第八
《史記》、《漢書》第九
諸子第十
辭賦第十一
詩第十二
文第十三
詩言志辨
序
詩言志
一 獻詩陳志
二 賦詩言志
三 教詩明志
四 作詩言
比興
一 毛詩鄭箋釋興
二 興義溯源
三 賦比興通釋
四 比興論詩
詩教
一 六藝之教
二 著述引詩
三 溫柔敦厚
正變
一 風雅正變
二 詩體正變
文學論著
現代生活的學術價值
論詩學門徑
中國文評流別述略
詩多義舉例
陶詩的深度——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層冰堂五種》之三)
什麼是宋詩的精華——評石遺老人(陳衍)評點《宋詩精華錄》(商務印書館出版)
詩文評的發展——評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二、三分冊:《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商務印書館)與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
論雅俗共賞
《文選序》“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說
文摘
經典常談
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國小”,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我國舊日的教育,可以說整個兒是讀經的教育。經典訓練成為教育的唯一的項目,自然偏枯失調;況且從幼童時代就開始,學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殘了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後,讀經漸漸廢止。民國以來雖然還有一兩回中國小讀經運動,可是都失敗了,大家認為是開倒車。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國中國文課程標準里卻有“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話,高中的標準是更有“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的話。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典選錄的也不少。可見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經典訓練不但沒有廢止,而且擴大了範圍,不以經為限,又按著學生程度選材,可以免掉他們囫圇吞棗的弊病。這實在是一種進步。
我國經典,未經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果是敬而遠之。朱子似乎見到了這個,他注“四書”,一種作用就是使“四書”普及於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書”注後來成了國小教科書。又如清初人選注的《史記菁華錄》,價值和影響雖然遠在“四書”注之下,可是也風行了幾百年,幫助初學不少。但到了現在這時代,這些書都不適用了。我們知道清代“漢學家”對於經典的校勘和訓詁貢獻極大。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只該是選本、節本——應該儘可能的採取他們的結論:一面將本文分段,仔細地標點,並用白話文作簡要的注釋,每種讀本還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這需要見解、學力和經驗,不是一個人一個時期所能成就的。商務印書館編印的一些《學生國學叢書》,似乎就是這番用意,但離我們理想的標準還遠著呢。理想的經典讀本既然一時不容易出現,有些人便想著先從治標下手。顧頡剛先生用淺明的白話文譯《尚書》,又用同樣的文體寫《漢代學術史略》,用意便在這裡。這樣辦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典,卻能啟發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這部小書也只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讀者能把它當做一隻船,航到經典的海里去,編撰者將自己慶幸,在經典訓練上,盡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兒。可是如果讀者念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受到了經典訓練,不再想去見識經典,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辜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這部書不是“國學概論”一類。照編撰者現在的意見,“概論”這名字容易教讀者感到自己滿足;“概論”里好像什麼都有了,再用不著別的——其實什麼都只有一點兒!“國學”這名字,和西洋人所謂“漢學”一般,都未免有籠統的毛病。國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分別標明歷史和語言,不再渾稱“國學”,確是正辨。這部書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不以“經學”、“史學”、“諸子學”等作綱領。但《詩》、《文》兩篇,卻還只能敘述源流;因為書太多了,沒法子一一詳論,而集部書的問題,也不像經、史、子的那樣重要,在這兒也無須詳論。書中各篇的排列,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順序,並照傳統的意見,將“國小”書放在最前頭。各篇的討論,儘量採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確_撰罷了。全篇的參考資料,開列在各篇後面;局部的,隨處分別註明。也有襲用成說而沒有注出的,那是為了節省讀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讀物和考據的著作不同,是無須乎那樣嚴格的。末了兒,編撰者得謝謝雷海宗先生允許引用他還沒有正式印行的《中國通史選讀》講義,陳夢家先生允許引用他的《中國文字學》稿本。還得謝謝董庶先生,他給我抄了全份清稿,讓排印時不致有太多的錯字。
《說文解字》第一
中國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叫倉頡的造的。這倉頡據說有四隻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蹄兒、鳥爪兒印著的痕跡,靈感湧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泄露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會變機靈了,會爭著去作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著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制他們,所以夜裡嚎哭;文字原是有巫術的作用的。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國末期才有,那時人並不都相信,如《易·繫辭》里就只說文字是“後世聖人”造出來的。這“後世聖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不斷地在演變著;說是一人獨創,是不可能的。《繫辭》的話自然合理得多。
“倉頡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生與演化的時代,字型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系統相承,民間書卻極為龐雜。到了戰國末期,政治方面,學術方面,都感到統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抬出一個造字的聖人,實在是為統一文字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聖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只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並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什麼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於“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可能因為這點聯繫,商契便被傳為造字的聖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是這個傳說卻暗示著文字起於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於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於《說文序》。“倉頡造字說”大概凝定於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後來加添的枝葉了。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人國小,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型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只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他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秘書)等官兒,都只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逸去,但許慎《說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為“大篆”,字型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在相信這只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
始皇為了統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爰歷》篇六章,胡毋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里的,但字型以當地通用的小篆為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為一書,單稱《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在殘存著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還存留著。《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後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後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事類而言。這些一面供教授學童用,一面供民眾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典和別的字書里的字,他都搜羅在他的書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型,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典的注文的體例。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並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後人可以溯源沿流,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型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國小”,現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於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國小人手;現在學問的範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人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里也搜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里還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金”是銅器,銅器的銘文稱為金文。銅器里鐘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為鐘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現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現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鑽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記錄。這稱為甲骨文,又稱為卜辭,是盤庚(約公元前一三○○)以後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里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在統統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書”用筆,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國才有帛,紙是漢代才有的。筆出現於商代,卻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蕩然無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為“六書”。“六書”這個總名初見於《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里才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二”(上)“=”(下)兩個字,短畫和長畫都是抽象的符號,各代表著一個物類。“二”是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這“上”和“下”兩種關係便是無形的事類。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為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等。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是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為聲;但水小為“淺”,金小為“錢”,貝小為“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五是“轉注”,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注字,也可以叫做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後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注”。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六是“假借”,語言裡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做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於”、“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號”,借為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為縣長的“長”。“縣令”、“縣長”是“令”、“長”的引申義。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後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申義的多,一字數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才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平聲,“縣長”的“長”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國小”,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我國舊日的教育,可以說整個兒是讀經的教育。經典訓練成為教育的唯一的項目,自然偏枯失調;況且從幼童時代就開始,學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殘了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後,讀經漸漸廢止。民國以來雖然還有一兩回中國小讀經運動,可是都失敗了,大家認為是開倒車。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國中國文課程標準里卻有“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話,高中的標準是更有“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的話。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典選錄的也不少。可見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經典訓練不但沒有廢止,而且擴大了範圍,不以經為限,又按著學生程度選材,可以免掉他們囫圇吞棗的弊病。這實在是一種進步。
我國經典,未經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果是敬而遠之。朱子似乎見到了這個,他注“四書”,一種作用就是使“四書”普及於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書”注後來成了國小教科書。又如清初人選注的《史記菁華錄》,價值和影響雖然遠在“四書”注之下,可是也風行了幾百年,幫助初學不少。但到了現在這時代,這些書都不適用了。我們知道清代“漢學家”對於經典的校勘和訓詁貢獻極大。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只該是選本、節本——應該儘可能的採取他們的結論:一面將本文分段,仔細地標點,並用白話文作簡要的注釋,每種讀本還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這需要見解、學力和經驗,不是一個人一個時期所能成就的。商務印書館編印的一些《學生國學叢書》,似乎就是這番用意,但離我們理想的標準還遠著呢。理想的經典讀本既然一時不容易出現,有些人便想著先從治標下手。顧頡剛先生用淺明的白話文譯《尚書》,又用同樣的文體寫《漢代學術史略》,用意便在這裡。這樣辦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典,卻能啟發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這部小書也只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讀者能把它當做一隻船,航到經典的海里去,編撰者將自己慶幸,在經典訓練上,盡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兒。可是如果讀者念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受到了經典訓練,不再想去見識經典,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辜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這部書不是“國學概論”一類。照編撰者現在的意見,“概論”這名字容易教讀者感到自己滿足;“概論”里好像什麼都有了,再用不著別的——其實什麼都只有一點兒!“國學”這名字,和西洋人所謂“漢學”一般,都未免有籠統的毛病。國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分別標明歷史和語言,不再渾稱“國學”,確是正辨。這部書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不以“經學”、“史學”、“諸子學”等作綱領。但《詩》、《文》兩篇,卻還只能敘述源流;因為書太多了,沒法子一一詳論,而集部書的問題,也不像經、史、子的那樣重要,在這兒也無須詳論。書中各篇的排列,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順序,並照傳統的意見,將“國小”書放在最前頭。各篇的討論,儘量採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確_撰罷了。全篇的參考資料,開列在各篇後面;局部的,隨處分別註明。也有襲用成說而沒有注出的,那是為了節省讀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讀物和考據的著作不同,是無須乎那樣嚴格的。末了兒,編撰者得謝謝雷海宗先生允許引用他還沒有正式印行的《中國通史選讀》講義,陳夢家先生允許引用他的《中國文字學》稿本。還得謝謝董庶先生,他給我抄了全份清稿,讓排印時不致有太多的錯字。
《說文解字》第一
中國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叫倉頡的造的。這倉頡據說有四隻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蹄兒、鳥爪兒印著的痕跡,靈感湧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泄露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會變機靈了,會爭著去作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著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制他們,所以夜裡嚎哭;文字原是有巫術的作用的。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國末期才有,那時人並不都相信,如《易·繫辭》里就只說文字是“後世聖人”造出來的。這“後世聖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不斷地在演變著;說是一人獨創,是不可能的。《繫辭》的話自然合理得多。
“倉頡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生與演化的時代,字型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系統相承,民間書卻極為龐雜。到了戰國末期,政治方面,學術方面,都感到統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抬出一個造字的聖人,實在是為統一文字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聖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只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並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什麼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於“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可能因為這點聯繫,商契便被傳為造字的聖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是這個傳說卻暗示著文字起於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於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於《說文序》。“倉頡造字說”大概凝定於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後來加添的枝葉了。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人國小,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型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只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他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秘書)等官兒,都只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逸去,但許慎《說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為“大篆”,字型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在相信這只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
始皇為了統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爰歷》篇六章,胡毋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里的,但字型以當地通用的小篆為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為一書,單稱《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在殘存著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還存留著。《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後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後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事類而言。這些一面供教授學童用,一面供民眾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典和別的字書里的字,他都搜羅在他的書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型,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典的注文的體例。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並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後人可以溯源沿流,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型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國小”,現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於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國小人手;現在學問的範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人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里也搜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里還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金”是銅器,銅器的銘文稱為金文。銅器里鐘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為鐘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現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現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鑽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記錄。這稱為甲骨文,又稱為卜辭,是盤庚(約公元前一三○○)以後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里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在統統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書”用筆,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國才有帛,紙是漢代才有的。筆出現於商代,卻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蕩然無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為“六書”。“六書”這個總名初見於《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里才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二”(上)“=”(下)兩個字,短畫和長畫都是抽象的符號,各代表著一個物類。“二”是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這“上”和“下”兩種關係便是無形的事類。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為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等。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是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為聲;但水小為“淺”,金小為“錢”,貝小為“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五是“轉注”,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注字,也可以叫做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後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注”。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六是“假借”,語言裡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做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於”、“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號”,借為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為縣長的“長”。“縣令”、“縣長”是“令”、“長”的引申義。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後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申義的多,一字數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才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平聲,“縣長”的“長”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序言
《大家國學》這套叢書,是在“國學熱”持續升溫的氛圍中問世的。承編者要我寫幾句話,考慮了一下,想有這樣幾點可說。
第一,我要講的是,“國學”並不是“一陣風”式暫時流行的話題。
“國學”和“國學熱”,現在已經成為媒體習見的熱門名詞。上海的《學術月刊》與《文匯讀書周報》,曾將國學評選為“2005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之一。《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2006》,在歷史學部分專設“國學熱的挑戰”一節,描述國學怎樣“得到學者和媒體的強烈關注,引發了如何重新評價傳統學術文化和傳統文化在現代中國的地位及作用,當代中國是否需要‘重振國學’、‘重振國學’是要‘接續文脈’還是‘復辟返古’等問題的爭論”。剛剛出版的《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2007》,又設有“國學熱的反響”一節,於敘說“國學熱仍在持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注意”之餘,著重介紹了一些論作對這一潮流的批評討論。不難預料,明年的《發展報告》還會把國學列為重點內容。
國學之所以熱,決不是出於偶然,也非少數人炒作能致,應該說,這是歷史必然趨勢的一種體現。中國的振興,正在國內外造成強烈的震撼。身歷祖國由積弱轉趨盛強的中國人,不會忘記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傳統,希望以其精華貢獻於世界。外國人面對崛起的中國,也一定會更加關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這又增加了中國人探討研究傳統文化即國學的責任。這樣看來,國學之熱當前僅僅是開始,其高潮尚遠在後面。
第二,我想說,“國學”是一個具有自身特色的學術範疇。
現在有了成熟的文學、史學、哲學等等學科,為什麼還要談什麼“國學”?這樣的問題,很早就有學者提出過了。前些時,我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和《光明日報》國學版合編的《年度國學2006》寫了一篇題為《國學的存立》的小文,涉及這個問題。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國維先生給《國學叢刊》撰序,主張“學無中西”,他說:“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到上世紀二十年代,錢穆先生在江南授課,其講義《國學概論》弁言也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需要指出王國維講“學無中西”,其“學”是“專以知言”,即具體的知識,不能說中西的文化學術彼此一樣,錢穆的“學術本無國界”,也應作如是觀。
不僅文史,科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這樣。二○○五年,我在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開幕式上說過:科學作為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和認識,本身確無所謂中西,但作為科學產生和發展背景的社會、文化是無法擺脫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實上,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學的形成、發展有著不一樣的途徑和過程,在社會、文化中科學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國的學術文化有著非常明顯的獨特之處,從而“國學”終不可廢。
第三,我還想建議,大家通過學術史的角度來認識國學。
“國學”一詞,本由與“西學”區別而出現,通行既久,其涵義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話說的“較起真來”,究竟什麼是國學,國學的內涵、外延如何,多少年來不知有多少爭論。今天要求一下子講清楚,實際是做不到的事。
經常有朋友、同學問我,要了解國學,初識門徑,應該從哪些書人手,我總是推薦兩本書,一本是章太炎的《國學講演錄》、一本便是上面提到過的錢穆《國學概論》。章書從國小談到經、史、子、集,是橫的分類介紹,錢書自孔子下及民國,’是縱的歷史敘述。兩書體例不同,但和其他類似著作一樣,貫穿著作者本人的見解。如欲比較全面地知道國學的範圍與內容,特別是學者各家的異同,還必須博覽種種重要論著,即所謂原典。
當然,國學歷代論著浩如煙海,絕非有限時間所能涉獵,這便需要選擇與我們最關緊要的優先閱讀。前輩學者為我們樹有典範,重視學術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學術史的研究。例如梁啓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引導促進當時學術進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因為民國前期的學術文化是直接從清代延續變革而來。我們距離清朝已遠,要接觸學術文化傳統,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紀的國學諸家。認識國學,最好先來閱讀二十世紀諸家的作品。
《大家國學》叢書,正是為此設計的。編者就二十世紀名家學者,“選擇其關於國學、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學術等概論性、常識性的文字成一選本”,“以便於引導讀者進一步了解、把握學者最基本的國學修養與學術思想”,這確是便利一般讀者的創意。相信這套書會繼續編印下去,對國學的普及和中國優秀文化的闡揚,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李學勤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第一,我要講的是,“國學”並不是“一陣風”式暫時流行的話題。
“國學”和“國學熱”,現在已經成為媒體習見的熱門名詞。上海的《學術月刊》與《文匯讀書周報》,曾將國學評選為“2005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之一。《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2006》,在歷史學部分專設“國學熱的挑戰”一節,描述國學怎樣“得到學者和媒體的強烈關注,引發了如何重新評價傳統學術文化和傳統文化在現代中國的地位及作用,當代中國是否需要‘重振國學’、‘重振國學’是要‘接續文脈’還是‘復辟返古’等問題的爭論”。剛剛出版的《中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報告2007》,又設有“國學熱的反響”一節,於敘說“國學熱仍在持續,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注意”之餘,著重介紹了一些論作對這一潮流的批評討論。不難預料,明年的《發展報告》還會把國學列為重點內容。
國學之所以熱,決不是出於偶然,也非少數人炒作能致,應該說,這是歷史必然趨勢的一種體現。中國的振興,正在國內外造成強烈的震撼。身歷祖國由積弱轉趨盛強的中國人,不會忘記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傳統,希望以其精華貢獻於世界。外國人面對崛起的中國,也一定會更加關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這又增加了中國人探討研究傳統文化即國學的責任。這樣看來,國學之熱當前僅僅是開始,其高潮尚遠在後面。
第二,我想說,“國學”是一個具有自身特色的學術範疇。
現在有了成熟的文學、史學、哲學等等學科,為什麼還要談什麼“國學”?這樣的問題,很早就有學者提出過了。前些時,我在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和《光明日報》國學版合編的《年度國學2006》寫了一篇題為《國學的存立》的小文,涉及這個問題。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國維先生給《國學叢刊》撰序,主張“學無中西”,他說:“何以言學無中西也?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到上世紀二十年代,錢穆先生在江南授課,其講義《國學概論》弁言也說:“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需要指出王國維講“學無中西”,其“學”是“專以知言”,即具體的知識,不能說中西的文化學術彼此一樣,錢穆的“學術本無國界”,也應作如是觀。
不僅文史,科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這樣。二○○五年,我在第22屆國際科學史大會開幕式上說過:科學作為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和認識,本身確無所謂中西,但作為科學產生和發展背景的社會、文化是無法擺脫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實上,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學的形成、發展有著不一樣的途徑和過程,在社會、文化中科學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國的學術文化有著非常明顯的獨特之處,從而“國學”終不可廢。
第三,我還想建議,大家通過學術史的角度來認識國學。
“國學”一詞,本由與“西學”區別而出現,通行既久,其涵義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話說的“較起真來”,究竟什麼是國學,國學的內涵、外延如何,多少年來不知有多少爭論。今天要求一下子講清楚,實際是做不到的事。
經常有朋友、同學問我,要了解國學,初識門徑,應該從哪些書人手,我總是推薦兩本書,一本是章太炎的《國學講演錄》、一本便是上面提到過的錢穆《國學概論》。章書從國小談到經、史、子、集,是橫的分類介紹,錢書自孔子下及民國,’是縱的歷史敘述。兩書體例不同,但和其他類似著作一樣,貫穿著作者本人的見解。如欲比較全面地知道國學的範圍與內容,特別是學者各家的異同,還必須博覽種種重要論著,即所謂原典。
當然,國學歷代論著浩如煙海,絕非有限時間所能涉獵,這便需要選擇與我們最關緊要的優先閱讀。前輩學者為我們樹有典範,重視學術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學術史的研究。例如梁啓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引導促進當時學術進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因為民國前期的學術文化是直接從清代延續變革而來。我們距離清朝已遠,要接觸學術文化傳統,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紀的國學諸家。認識國學,最好先來閱讀二十世紀諸家的作品。
《大家國學》叢書,正是為此設計的。編者就二十世紀名家學者,“選擇其關於國學、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學術等概論性、常識性的文字成一選本”,“以便於引導讀者進一步了解、把握學者最基本的國學修養與學術思想”,這確是便利一般讀者的創意。相信這套書會繼續編印下去,對國學的普及和中國優秀文化的闡揚,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李學勤
二○○七年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