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2009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副標題: 一本為所有人又不為任何人所寫之書(叢書名: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尼采註疏集),作為尼采註疏集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採用最新的中譯本版本,在KSA版、PÜTZ版和GALLIMARD法文版注釋的同時,為適合漢語學術語境以及讀者更好理解行文,主編劉小楓教授對譯文作了體察入微的精心修訂,每一處細微的改動都從內容(哲學方面)和形式(詩的韻律方面)更貼切地傳達了尼采的大義,而且還特意對涉及經文處加了【中譯編者注】,這都將使本書成為國內學術界最完備的研究本《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基本介紹
讀者對象,作者簡介,目錄,
讀者對象
此書完全值得每一位關注並熱愛尼采的學內外人士重新閱讀。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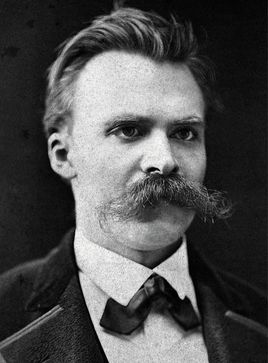
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中譯本前言
尼采的扎拉圖斯特拉在山頂孤獨地生活了10年,隨後下山,這時扎拉圖斯特拉40歲;尼采寫作《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時也將近40;古希臘人把40歲稱為壯年,而柏拉圖海外遊歷,返回雅典的時候,恰好也是40歲。這不是偶然的巧合——海德格爾講,對思想家,沒有偶然的巧合。對尼采而言,經由《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他至少奠定起自己哲學的前廳(致Overbeck,1884年3月8日及同年4月7日;致von Meysenbug,1884年3月末及4月初——這一年,尼采恰好四十),按照書中“論三種變形”里的說法,“一種神聖的肯定(Ja-sagen)”開始了。
柏拉圖40歲之前的漫遊生涯里, 去過許多地方,但是,根據拉爾修的記載,在埃及求學之後,唯獨有一個地方,柏拉圖沒有涉足:“……此還去過埃及求見那些先知(προφήτας)……柏拉圖還打算交往(συμμῐξαι)祆教僧侶(Μάγοις),可亞洲的戰爭令其卻步。返回雅典後,他就住在阿卡德米(即學園所在地)……”(《名哲言行錄》,III.7 )。所謂祆教僧侶(Μάγοις),即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創立的波斯拜火教僧侶, 據說他們都擁有某些魔法(西文magic詞源),德國人尼采的扎拉圖斯特拉,在希臘人那裡名為瑣羅亞斯德,拉爾修在《名哲言行錄》開篇的序言就介紹了瑣羅亞斯德的歷史:“自波斯人瑣羅亞斯德開始的祆教僧侶活動時間,是特洛伊淪陷前5000年”(Ⅰ.2)。偶然的戰爭中斷了柏拉圖的旅程,於是,尼採回溯這段往事的時候,就說:
這個雅典人曾在埃及人那裡上過學(或者是埃及的猶太人那裡?……),為此人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偶像的黃昏》,“我感謝古人什麼”2,參衛茂平譯本,上海:華東師大,2007年)
由於這種“高昂的代價”,所以,尼採在“我感謝古人什麼”這一節不停抨擊柏拉圖,一會用羅馬風格抑制柏拉圖,一會用修昔底德療救柏拉圖的軟弱,可是,這些療救豈不都還是在希臘的傳統里嗎?尼采真認為這些就可以真正解決柏拉圖(和柏拉圖主義)帶來的問題?而不是一種更深刻的反諷?
“我感謝古人什麼”共5小節。第一小節講羅馬對抗希臘:這就是扎拉圖斯特拉風格的來源(注意:僅僅是風格);上文援引的第二小節用修昔底德的“絕對意志”克服柏拉圖;到了第四小節,尼采自稱是第一個還能夠理解古老的狄奧尼索斯的人——在被柏拉圖敗壞的人當中,於是他又試圖用狄奧尼索斯最根本的“生命意志”克服柏拉圖的疾病,所以,到了第五小節,尼采說,“我,這位哲學家狄奧尼索斯的最後信徒”,狄奧尼索斯之所以是哲學家,就因為只有這位酒神的狀態,才能表達永恆的生命意志和永恆的輪迴。但是,緊接著這個稱呼後,尼采寫下了這一節的最後一句話:“——我,這位永恆輪迴的教師……”這一自稱表明,尼采之為哲人狄奧尼索斯的信徒,不是因為狄奧尼索斯的希臘特徵,而是因為其對權力意志和永恆輪迴的領悟。
“我感謝古人什麼”之前一節是 “一個不合時宜者的漫遊”,尼採在其中這樣收尾:“我已經給了人類所擁有的最深沉的(tiefste)書,這就是我的《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不久,我就要給他們那本最具獨立性的書。——”這本最獨立的書就是《重估一切價值》(《偶像的黃昏》,“前言”)。不過,我們首先需要關注的,恰恰是這兩次對《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或隱或顯的提及,因為從結構上看,正是這兩處包裹了整個“我感謝古人什麼”一節。而且,在這層包裹之中,還有一根沉默的金線。
如果對比一下拉爾修和尼采對柏拉圖漫遊經歷的描述,我們就會發現一樁奇怪的事情——尼采完全省略了拉爾修的後半句:“柏拉圖還打算交往祆教僧侶”。按照尼采原文的脈絡,似乎由於柏拉圖在埃及受了那些先知的影響,所以貽害後代。可是,尼采加了一個括弧,括弧里說,“或者在埃及的猶太人那裡”?與其說這裡是一次順帶的諷刺,不如說,尼采暗示了,柏拉圖在埃及所受何種影響,這並不確定。因為,隨後對“柏拉圖還打算交往祆教僧侶”這句的完全沉默,大概就在那個省略號里,而這或許就是尼采未加言明的東西:人們所以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並不是因為柏拉圖在埃及學到了什麼,正相反,是因為柏拉圖沒有去過波斯。尼采通過一句疑問句,一個省略號,還有他的沉默,傳達出的信息在於:如果以希臘方式解決希臘人柏拉圖帶來的問題,無論如何都不是真正的解決,所以,尼采如果要遠離柏拉圖之後的古人們,他就要踏上一條和柏拉圖相反的道路——於是,尼采來到波斯,並且請出波斯宗教的奠基人瑣羅亞斯德/扎拉圖斯特拉。如是,尼采感謝古人之所在,就在於,他認清了他們和柏拉圖的關係——那么,他必須走上另外一條道路。
事實上,在希臘人自己的目光里,波斯人一直是一個偉大的競爭對手,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與後世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劇的區別就在於,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波斯人是真正的對手,而不僅僅是敵人。在希羅多德《原史》開篇,他一再列舉波斯和希臘的對立,大概不僅僅是為希波戰爭鋪墊,也是要說明,波斯人是與希臘人不同的一類人(卷一,1-5;131-140)——對於這些,古典語文學家尼采自然十分熟悉。而且,尼采尤其熟悉《名哲言行錄》,還專門做過這方面的研究(Beiträge zur Quellenkunde und Kritik des Laertius Diogenes,1870年;參《瞧這個人》,“為什麼我如此聰明”,3),拉爾修在《名哲言行錄》序言裡說到哲學起源時,明確高舉希臘。但是,全書開頭的第一句話卻是:有人說,哲學研究始於野蠻人,他們極力列舉,波斯人有他們的祆教僧侶(Μάγοις)……讀到這裡的時候,尼采一定竊笑不已。
希臘人認為,Zoroaster是ζωρός和ἄστηρ的結合體,意為“純潔的星球”(《名哲言行錄》Ⅰ.8),而尼采的扎拉圖斯特拉甫一開口,第一句話就是:“你這偉大的星球啊”,這不僅僅是巧合,毋寧是一種暗示,暗示了扎拉圖斯特拉與柏拉圖(或蘇格拉底)的關係,因為,熟悉柏拉圖的人,都會立刻想起曾對太陽祈禱的蘇格拉底(《會飲》220d);而且,蘇格拉底這一行為由突然闖入的阿爾喀比亞德說出,巧合的是,正是在以阿爾喀比亞德命名的一篇對話里,柏拉圖讓蘇格拉底提到了瑣羅亞斯德(《阿爾喀比亞德前篇》122a處)。
在古典時代,《阿爾喀比亞德前篇》向來被當作柏拉圖對話的入門(前廳),比如奧林匹俄多羅斯(Olympiodorus)、揚布里科(Ιamblichus)、普羅克洛斯(Proclus)和普盧塔克這些解經大家, 他們都認為,這是閱讀柏拉圖對話的第一站,換言之,它預示了其他對話錄的主要方式和主要內容,阿爾-法拉比就說:“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在他名為《阿爾喀比亞德前篇》(‘阿爾喀比亞德’就是榜樣的意思)的書中找到。” 阿爾-法拉比所說的“這一切”,指的是柏拉圖的思考過程:人自身稟有的美是否能帶來最終的幸福?但無論是外表的美貌、高貴的出身、富裕的家產還是統治城邦,都不是幸福本身,而只有某種知識和某種生活方式,才能獲得幸福。 這就是《阿爾喀比亞德前篇》談論的主要問題——也是柏拉圖對話探討的主要問題:選擇怎樣的生活方式(105a);何為正義(109b-117a);知識是否可教(109d-112e);善惡和幸福(115a);認識自己(124a-b)等。 在柏拉圖的所有對話里,這是出現瑣羅亞斯德的地方,而且,恰恰是在《阿爾喀比亞德前篇》這個“前廳”里。
我們仔細看看蘇格拉底這段話:
當他14歲的時候,就會到人們稱為“王室教師”的人那裡受教,這是所有波斯成年人中遴選出的最佳者:最明智的人、最正義的人、最自製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位老師要教導他們敬拜諸神,學習霍羅馬澤之子瑣羅亞斯德的教義,學習一個王者應該知道的東西。最正義的人教他要終身恪守真道。最自製的人教他不要受制於任何一種快樂,這樣才能成為一個自由的人和一個真正的王者,王者首先就當統治自己,而不是成為自己的奴隸。最勇敢的人教他無懼無畏,因為恐懼即是受到奴役。(《阿爾喀比亞德前篇》122a)
蘇格拉底這段話出現的部分,是蘇格拉底對阿爾喀比亞德最長的一段說辭(121a-124b),或者是一個故事:一個王室故事(royal tale)。 這個故事隸屬的對話進程,可以大抵劃歸至第二部分。第一部分里(103a-119c),蘇格拉底使阿爾喀比亞德明白,欲求富裕和有權勢的生活所必需的要素,必須要在一個人自身中探求,而且,他還讓阿爾喀比亞德知道了自己的無知(118b)。最後一部分的內容,則是在這個王室故事的啟發下,引導阿爾喀比亞德如何自我完善,或者追求美德,這就是最終認識自己的靈魂(124b以下)。
在這段王室故事的說辭之前,阿爾喀比亞德說,他的家族可以溯至宙斯。蘇格拉底說,他的家族也同樣可以溯至宙斯,而且,宙斯是世間每一個王的先祖:包括斯巴達和波斯。隨後,蘇格拉底詳述了斯巴達王和波斯王的財富和權勢,也就是說,在雅典視野里,只有這兩者才是可以對堪的目標——是他們的敵人和對手,“必須要擊敗的人”。阿爾喀比亞德想擁有統治雅典的權勢,但蘇格拉底說,你認為波斯的王后們會認為你可與真正的波斯王相比嗎?斯巴達的王后也會同樣震驚:“這個年輕人究竟能憑藉什麼達到目的呢”(123e)?——換言之,他必須具備和波斯王者和斯巴達王者同樣的能力,才有擊敗他們的可能。所以,蘇格拉底特彆強調了阿爾喀比亞德的一種特徵:沒有經過教育;先前,蘇格拉底就已經指責阿爾喀比亞德沒有接受教育便匆匆從政(118c)。
於是,蘇格拉底提到這段波斯王的教育,以便教育阿爾喀比亞德,也就是說,如果要把阿爾喀比亞德教育為堪與波斯王比肩的人物,那么,蘇格拉底一個人就得身兼最明智的人、最正義的人、最自製的人和最勇敢的人四種身份。在第一項美德里,蘇格拉底提到了瑣羅亞斯德。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對這一明智美德的描述有三層意蘊:敬神、習得瑣羅亞斯德的教義,然後是王政的知識。這裡的等序倒頗為清楚。瑣羅亞斯德作為先知,被包裹在敬神和王的知識之間,而且“霍羅馬澤之子”的稱呼,隱含這樣的暗示:瑣羅亞斯德並不能作為一種更高的開始。只有具備這四種美德才是合格的王者,可是,作為波斯宗教(禮教)的奠基者,瑣羅亞斯德與後三種美德並無關聯,所以在第一種美德中提及瑣羅亞斯德,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為了忽略。更大的反諷在於:一個明智、正義、自製並且勇敢的人,會汲汲於世間奢華的財富、衣飾和役使他人?這不由使人生疑。
此外,蘇格拉底並沒有提到斯巴達王的教育,而只是提到波斯王的教育,這是否在暗示,斯巴達的教育其實和雅典一樣:都是希臘式的教育?關鍵之處在於:波斯王這四重美德的教育豈不太希臘式了,這不正是傳統希臘的四德么? 如果按照蘇格拉底這種說法,那么,教育出來的就是希臘人,而不是波斯人了。因為,波斯人對美德的看法,與蘇格拉底的描述似乎並不相同。
希羅多德《原史》卷一145提到:“子嗣繁多,在他們(指波斯人)眼中看來乃是男性僅次於勇武的一項美德”(王以鑄譯文)。希羅多德也提到了波斯人的其他禮俗,如果那些不是直接與“美德”相關的話,那么,這一句就是探究波斯美德最關鍵的一句話。第一美德無疑是勇武,也就是希臘人的勇敢,但那是他們的第四種美德;第二種美德是子嗣繁多,希臘人卻並不認為這是一種美德。從他對其他風俗的描繪,還可以看出,波斯人不知自製,或不以自制為美德(I.134),這至少可以表明,通過希羅多德這樣的希臘人看來,波斯美德與希臘美德之間有著重大的差異。
所以,真正的波斯王教育,一定不是這種蘇格拉底描繪的希臘式教育。柏拉圖實際上是把希臘的特徵籠罩在一切探究的根基上,一切教育的根基上。而同時具有四種美德的蘇格拉底,更是超越于波斯人之上,是一個美德教育的典範。且以敬神這種明智的美德為例。在對話的結尾,阿爾喀比亞德想當然地認為,蘇格拉底能夠教他如何認識自己的靈魂,但蘇格拉底斷然否認,而是只有神才可以(135d);在對話開端,蘇格拉底表示,自己一直不敢對阿爾喀比亞德表露心跡,是由於某種神意的阻止,如今開口,則是神意解除了阻止(103a);而在蘇格拉底最長的這段講辭里,他首先提到了阿爾喀比亞德和自己的神聖先祖。以這種實際的言辭教育,蘇格拉底希望阿爾喀比亞德懂得敬神,而這是所有美德教化中的第一條。
蘇格拉底就此敉平了波斯人和希臘人美德的差異,偷偷地把波斯人置換為希臘人。不過,這未必就表示蘇格拉底就持有這樣的看法,毋寧說,他在教育阿爾喀比亞德時,偷偷地進行了這樣的置換。在這段講辭結尾,蘇格拉底暗示,阿爾喀比亞德是一個極有愛欲的人,所以,必須激發起他的愛欲才可以教育。這種激發一個最明顯的特徵是,蘇格拉底藉助波斯王后和斯巴達王后之口,對阿爾喀比亞德表示輕蔑,以圖更加激發其愛欲:“這個年輕人究竟能憑藉什麼達到目的呢”?波斯和斯巴達的權勢財富、王后們(女人們)正是足以激發阿爾喀比亞德愛欲的初端。但是,蘇格拉底暗中強調,波斯王所以是希臘人偉大的對手,是因為他具有希臘式的美德。蘇格拉底的置換是為了提升阿爾喀比亞德的愛欲,在這種敵對的層面之上,還有一個更為偉大的愛欲“形式”:某種希臘式的美德。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就是希臘人之為希臘人的本質:對存在的本真領悟。蘇格拉底的教育有無成效?在這段講辭結束之後,阿爾喀比亞德立刻主動發問:“我應該踐行怎樣的自我教化呢?”於是,蘇格拉底微微頷首:“嗯”。
我們無法斷言,在這個關鍵的戲劇場景里,柏拉圖貌似輕描淡寫地提到瑣羅亞斯德,更深的用意究竟何在。但是至少可以肯定,柏拉圖當然知道希臘傳統里波斯和希臘的競爭,但他的筆下,蘇格拉底以一種更高的東西超越了這種競爭——“隨著蘇格拉底,希臘人的鑑賞力驟然轉向辯證法”《偶像的黃昏》,“蘇格拉底問題”,所以,柏拉圖的蘇格拉底提到的瑣羅亞斯德,其實籠罩於希臘的外衣之下。他的面目變得模糊不清。一切都服務於蘇格拉底的辯證法,服務於蘇格拉底的教育。
尼采不知道其中的情形?《善惡的彼岸》前言直接攻擊柏拉圖的根本錯誤,並且以“假如真理是一位女人”開篇,這不正是蘇格拉底引誘阿爾喀比亞德的方式么?這本書的核心一章是第五章,其中格言200把阿爾喀比亞德和凱撒並舉,稱為那種天生(自然本性)渴望統治、“為了勝利”的人。這更接近修昔底德的阿爾喀比亞德(《戰爭志》,卷五,卷六),而不是受到蘇格拉底教育的那位——修昔底德卻也是尼採用來療救柏拉圖流弊的藥方之一。
看來,尼採選擇扎拉圖斯特拉,若加以源流考究,其中深意在焉,尤其是在他面對柏拉圖的競爭時。如果要揭開蘇格拉底裹上的外衣,那么,還有什麼比讓包裹里的人物說話更好的方式呢?海德格爾試圖回歸前蘇格拉底的自然哲人,以克服柏拉圖帶來的形上學弊病,不過,早在他之前,尼采就已經發現,希臘如何能夠解決“希臘”本身的問題呢?柏拉圖在自己哲學的“前廳”里遮掩了瑣羅亞斯德和波斯,相反,尼採在自己的哲學“前廳”直接讓瑣羅亞斯德說話,而且,不用希臘人的稱呼,而是德國人的稱呼: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尼采漢譯最多的著作——足見漢語知識界對這本書喜愛有加。最早的中譯出自魯迅之手,名為《察羅堵斯德羅緒言》,顧名思義,只譯出前言10篇。《扎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第一個全譯本出自蕭贛之手,以文言翻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36年3月出版,不過,被施蟄存譏為“笑掉牙床”,隨後各種譯本不斷。本譯本倒無心添湊這個熱鬧,只是,尼采說過,“要領悟別人的鮮血殊非易易:我憎恨懶散的讀者”(“論閱讀和寫作”),所以,藉助西人學術註疏的成果,我們希望能夠勤快一些,荷西俄德很久以前就教導過,要“勤於耕耘”,兼之黃明嘉先生譯辭流暢,譯本亦因之增色。
目錄
尼采註疏集出版說明(劉小楓)
中譯本前言(婁林)
KSA版編者說明
Pntz版編者說明
第一卷
扎拉圖斯特拉前言
扎拉圖斯特拉的演說島
論三種變形
論道德講席
論信仰彼岸世界的人
論蔑視肉體者
論快樂和激情
論蒼白的罪犯
論閱讀和寫作
扎拉圖斯特拉如
論山旁之樹
論死之說教者
論戰爭和戰士
論新偶像
論市場的蒼蠅
論貞潔
論朋友
論一千零一個目標
論愛鄰人
論創造者的道路
論老嫗和少婦
論毒蛇的咬齧
論孩子和婚姻
論自由地死
論饋贈的道德
第二卷
持鏡的小孩
在幸福島上
論同情者
論牧師
論道德家
論烏合之眾
論毒蜘蛛
論著名的智慧者
夜歌
舞蹈之歌
……
第三卷
第四卷
尼采年表(佩特爾·普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