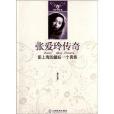《張愛玲傳奇:舊上海的最後一個貴族》由胡辛著。本事一經敘述就成了文學。張愛玲說過:“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胡辛的傳記文學,是傳記小說。傳記可以說是一種懷舊,一種追憶逝水年華,一種人類對人無長久的無可奈何的哀悼!傳記就像一張沉人歲月的河裡的網,到得一定的時機,便迅猛地將它扯上岸,作一檢點,作一總結,以為網住的都是精華,都是最實質的,其實天曉得。網眼有大有小,再說適中的也並不一定是最本質的。
基本介紹
- 書名:張愛玲傳奇:舊上海的最後一個貴族
-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 頁數:368頁
- 開本:16
- 定價:34.00
- 作者:胡辛
- 出版日期:2012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926215X, 9787539262154
- 品牌:江西教育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編輯推薦,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張愛玲傳奇:舊上海的最後一個貴族》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胡辛,原名胡清,中國作家。江西南昌人,祖籍安徽黃山太平。現為南昌大學影視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廣播電視藝術學、現當代文學碩士生導師。1983年以處女作《四個四十歲的女人》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即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後一發不可收,涉小說、傳記、影視文學、散文隨筆和理論研究等多種形式。至今已出版書30本。其作品翻譯成英文、日文,兩次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美國、馬來西亞。三部傳記在海峽兩岸出版,在世界華人區中有較大的影響。作為—個充滿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學者型作家,胡辛以獨立的女性意識、深厚的文化底蘊、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富有激情的藝術頓悟創造了真誠、鮮活的人間情致和靈活不拘的藝術表達形式。
圖書目錄
總序
引子
第一部 覓
出名要趁早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
傾城之戀
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人世間沒有愛
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
香港的回憶
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留下一段真情
人生中總有厚實的、靠得住的東西。
蠻荒·女人·玫瑰
女人把人類飛越太空的靈智拴在踏實的根樁上。
第二部 惑
兩地錯緣
傻就傻吧,人生只有這么一回!
杜鵑花·罌栗花·創世紀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愛的萎謝
愛是熱,被愛是光。
不了情多少恨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我有迷魂招不得
火車的行駛像是轟轟烈烈通過一個時代……
又見香港
恩怨之間本來是微妙的,很容易就一翻身倒了個過。
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讓生命來到你這裡
對於這世界他的愛不是愛,而是疼惜。
鄉戀·怨女·傷逝
隨著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
紅樓夢海上花
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
情到深處是孤獨
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後記
引子
第一部 覓
出名要趁早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
傾城之戀
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
人世間沒有愛
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
香港的回憶
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留下一段真情
人生中總有厚實的、靠得住的東西。
蠻荒·女人·玫瑰
女人把人類飛越太空的靈智拴在踏實的根樁上。
第二部 惑
兩地錯緣
傻就傻吧,人生只有這么一回!
杜鵑花·罌栗花·創世紀
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愛的萎謝
愛是熱,被愛是光。
不了情多少恨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我有迷魂招不得
火車的行駛像是轟轟烈烈通過一個時代……
又見香港
恩怨之間本來是微妙的,很容易就一翻身倒了個過。
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已經想家了。
讓生命來到你這裡
對於這世界他的愛不是愛,而是疼惜。
鄉戀·怨女·傷逝
隨著我生長的,我想起我從前的家了。
紅樓夢海上花
十年一覺迷考據,贏得紅樓夢魘名。
情到深處是孤獨
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後記
後記
還原一個真正的張愛玲!
然而,談何易!
不言而喻,傳記文學是紀實的,它不同於以虛構為生命的小說。然而,傳記又往往是傳記作家用文學手筆去還原且凸現傳主的歷史,這似乎又應了張愛玲的一句話:“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燼餘錄》)傳記作者便注定了在紀實與虛構中突圍糾纏不已。如若作者既寫傳記更寫小說,那就真正是難解難分了。
惠特曼說過:“我恨許多傳記,因為它們是不真實的。我國許多偉人,都被他們寫壞了。上帝造人,但是傳記家偏要替上帝修改,這裡添一點,那裡補一點,再添再補,一直寫到大家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了。”說得真好,這對傳記作者一針見血的批評,卻又分明點出了傳記作者的勃勃野心和異想天開。傳記作者正是膽大包天,敢與上帝比試比試,再捏一個人的人。也許惟妙惟肖,也許一塌糊塗;也許形神兼備,也許有形無神,也許走形走神,也許已經脫胎換骨……但不管怎樣,這個再捏出的人與上帝造的人終歸是有差距的。
胡適認為:“傳記的最重要的條件是紀實傳真。”也就是“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份,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尚友其人。”(《胡適文存·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郁達夫認為新的傳記:“是在記述一個活潑潑的人的一生,記述他的思想與言行,記述他與時代的關係。他的美點,自然應當寫出,但他的缺點和特點,因為要傳述一個活潑潑而且整個的人,尤其不可不書。所以若要寫新的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我們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儘量來寫,才可以見得真,說得像。”(郁達夫《什麼是傳記文學》)
所謂紀實,是資料的蒐集、整理、發掘,辨真偽虛實等等,這很重要,可以說,是傳記成功與否的基礎。相對而言,資料占有愈真實愈完整愈豐富愈翔實愈細緻,成功的可能就愈大。但是,即便所有的零件都具備了,要“組裝”成可傳神的傳主,應該說,還有漫長的道路。這一點,做小說的,多有所認識;而做傳記的,卻往往掉以輕心。有的就將採訪手記刊出,且自鳴得意為原汁原湯,可說到底,那還只不過是原料,至多是半成品;匆匆拋出,日後再加工,怕是會夾生的。
所謂“傳真”,所謂“活潑潑”,關鍵的關鍵還是傳記作者。
一個傳記作者為傳主所作的傳,只是他個人對傳主歷經的歷史事件、傳主的個性、人格等等的一種理解和注釋;況且每一個人只能是生活在他的境況之中,各有各的一定的視角視野,你在與傳主的資料或更直接與傳主本人打交道時,你起初只是一個讀者、一個觀者,不知不覺中你進入了狀態。或許你身不由己,被感動被魅惑;你的視野心甘情願地與傳主的“視野融合”;或許你清醒得冷竣,以一副公正的純客觀的姿態,可是,你在選擇這一個作為你要書寫的傳主時,正是你的感情在左右你。而且愈是遮蔽自我的傳記作者,其實愈是主觀性強,因為他(她)決不人云亦云,且將自己的情感隱蔽得很深;你理直氣壯地讓傳主的視野融合進你的視野。自然,兩種融合併不經緯分明。一不小心,就會出現視域受阻或是盲視!
傳主還是那個傳主,資料還是那些資料,可是作者的切入的視角、取捨及排列組合,體現的是作者主體的眼光;同時傾斜了作者太多的個人情感!如果說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那么,十個傳記作家同寫一個傳主,一定會塑造出十個不同的傳主!所以傳記文學中,傳主已不再是純粹的傳主,雖然是史實的記錄,但是傳記作者獨特的認識和把握,以及感情的或裸露或隱匿的澆鑄,傳記中的傳主便既籠罩著作者的身影,又融匯著作者的靈魂。它是傳記作者對傳主的人格、性格、大的所作所為小的細枝未節乃至所想的自己的理解和解釋。傳記作者的這種有言或無言的理解和解釋是作者本人對人性的把握。
傳記可以說是一種懷舊,一種追憶逝水年華,一種人類對人無長久的無可奈何的哀悼!傳記就像一張沉人歲月的河裡的網,到得一定的時機,便迅猛地將它扯上岸,作一檢點,作一總結,以為網住的都是精華,都是最實質的,其實天曉得。網眼有大有小,再說適中的也並不一定是最本質的。麥芒說得好:“人和藝術一樣,與歷史總是存在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當人先於他的藝術變成歷史,僵化也就開始了。”當今社會,為活人作傳似已成為一種時尚。大而言之,也許是為了社會發展的需求;小而言之,也許是傳主或傳記作者的需求;但怎么看似都涌動著種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快,快,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出名要趁早呵!晚了即使出名了,也不那么痛快了。
當然,認識人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每個人與自己的心距離最遠,跟別人的心也決不會距離太近。
張愛玲和張愛玲的心距離最遠。
張愛玲透徹地斷言:人總是髒的,沾著人就沾著髒。於是,只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她才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偏偏就是這個張愛玲,直言不諱她對世俗名利的追慕和渴求!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實踐作家的天才夢,她總是催著自己: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張愛玲悲涼地感悟:人世間沒有愛。家裡對她,是沒有恩情可言的。外面男子的愛呢?從《金鎖記》中的姜季澤到《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從《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到《十八春》中的沈世鈞,無論遺少洋少、傳統的還是新派的知識男性,張愛玲的筆端烙刻著對他們深深的失望!可偏偏就是這個張愛玲,不顧一切不可思議地與胡蘭成墜進大火大水般的狂戀之中。一個是冰清玉潔的大家閨秀,一個是山地農家的叛逆之子:一個是情竇晚開的生命初戀,一個是有名無名八次婚戀的插曲;曠世才女與文化漢奸是怎樣地緣起情生又絕情滅緣?雖有多少恨,卻總留著不了情,漫漫半世紀!張愛玲是徹悟還是混沌?誰說得清呢?
張愛玲理直氣壯地宣稱:她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是的,她在上海淪陷區的輝煌,雖被人譽為廢墟上的罌粟花,但她的筆觸的確只限於男女糾葛人性情慾,這是明白無誤的。可偏偏就是這個張愛玲,在中國解放的歡慶鑼鼓聲中,加進了《十八春》、《小艾》的真誠的頌歌;墨跡未乾去到香港的她,卻又大唱了《秧歌》、《赤地之戀》反調;痛定思痛之後,她對她的這些極端之作只有採取遺忘或塗改的下策。自命清高的張愛玲又如何能徹底遠離塵世呢?
張愛玲是天才,張愛玲更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關於張愛玲及家族的資料並非豐富與翔實,好在張愛玲自己說過:“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離。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並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里,也成為自身的一次經驗。”張愛玲還說過:“寫小說的間或把自己的經驗用進去,是常有的事。至於細節套用實事,往往是這種地方最顯出作者對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實感。作者的個性滲入書中主角的,也是幾乎不可避免的,因為作者大都需要與主角多少有點認同。”
張愛玲還感嘆過:中國語言文字的魅力無處不在!好的文字、好的句子,有時可以叫你感動一生一世。語言的感召、感悟,其力量是巨大的。如果說攝影是用圖像留住原本已逝去的故事的話,那么傳記文學則是用語言留下原本已逝去的故事的藝術。從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中尋覓真正的張愛玲的語境,也許事倍功半,吃力不討好,但我寧願僅當編寫者,也不願撕碎張愛玲語言的纖維,不願攪混原狀汁的人生況昧。也許太傻,可傻就傻吧,人生能有幾回心甘情願的傻呢。
《張愛玲傳奇——舊上海的最後一個貴族》(原著《最後的貴族·張愛玲》)殺青於1992年,原本應張秋林先生之約,為海峽兩岸出版社所撰寫的。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收為《胡辛自選集》四卷本之一。跨越千年,2005年暮春雨時節,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又將此書作為六卷本選集之一推出,可稱周而復始;2012年薔薇雨中江西教育出版社亦將該書作為新的六卷本自選集之一推出,終天地有情。在此,向傅偉中先生和熊侃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
原後記寫於1993年10月5日
補充於2004年10月8日
再補充於2012年1月22日
然而,談何易!
不言而喻,傳記文學是紀實的,它不同於以虛構為生命的小說。然而,傳記又往往是傳記作家用文學手筆去還原且凸現傳主的歷史,這似乎又應了張愛玲的一句話:“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燼餘錄》)傳記作者便注定了在紀實與虛構中突圍糾纏不已。如若作者既寫傳記更寫小說,那就真正是難解難分了。
惠特曼說過:“我恨許多傳記,因為它們是不真實的。我國許多偉人,都被他們寫壞了。上帝造人,但是傳記家偏要替上帝修改,這裡添一點,那裡補一點,再添再補,一直寫到大家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了。”說得真好,這對傳記作者一針見血的批評,卻又分明點出了傳記作者的勃勃野心和異想天開。傳記作者正是膽大包天,敢與上帝比試比試,再捏一個人的人。也許惟妙惟肖,也許一塌糊塗;也許形神兼備,也許有形無神,也許走形走神,也許已經脫胎換骨……但不管怎樣,這個再捏出的人與上帝造的人終歸是有差距的。
胡適認為:“傳記的最重要的條件是紀實傳真。”也就是“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份,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尚友其人。”(《胡適文存·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郁達夫認為新的傳記:“是在記述一個活潑潑的人的一生,記述他的思想與言行,記述他與時代的關係。他的美點,自然應當寫出,但他的缺點和特點,因為要傳述一個活潑潑而且整個的人,尤其不可不書。所以若要寫新的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我們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儘量來寫,才可以見得真,說得像。”(郁達夫《什麼是傳記文學》)
所謂紀實,是資料的蒐集、整理、發掘,辨真偽虛實等等,這很重要,可以說,是傳記成功與否的基礎。相對而言,資料占有愈真實愈完整愈豐富愈翔實愈細緻,成功的可能就愈大。但是,即便所有的零件都具備了,要“組裝”成可傳神的傳主,應該說,還有漫長的道路。這一點,做小說的,多有所認識;而做傳記的,卻往往掉以輕心。有的就將採訪手記刊出,且自鳴得意為原汁原湯,可說到底,那還只不過是原料,至多是半成品;匆匆拋出,日後再加工,怕是會夾生的。
所謂“傳真”,所謂“活潑潑”,關鍵的關鍵還是傳記作者。
一個傳記作者為傳主所作的傳,只是他個人對傳主歷經的歷史事件、傳主的個性、人格等等的一種理解和注釋;況且每一個人只能是生活在他的境況之中,各有各的一定的視角視野,你在與傳主的資料或更直接與傳主本人打交道時,你起初只是一個讀者、一個觀者,不知不覺中你進入了狀態。或許你身不由己,被感動被魅惑;你的視野心甘情願地與傳主的“視野融合”;或許你清醒得冷竣,以一副公正的純客觀的姿態,可是,你在選擇這一個作為你要書寫的傳主時,正是你的感情在左右你。而且愈是遮蔽自我的傳記作者,其實愈是主觀性強,因為他(她)決不人云亦云,且將自己的情感隱蔽得很深;你理直氣壯地讓傳主的視野融合進你的視野。自然,兩種融合併不經緯分明。一不小心,就會出現視域受阻或是盲視!
傳主還是那個傳主,資料還是那些資料,可是作者的切入的視角、取捨及排列組合,體現的是作者主體的眼光;同時傾斜了作者太多的個人情感!如果說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那么,十個傳記作家同寫一個傳主,一定會塑造出十個不同的傳主!所以傳記文學中,傳主已不再是純粹的傳主,雖然是史實的記錄,但是傳記作者獨特的認識和把握,以及感情的或裸露或隱匿的澆鑄,傳記中的傳主便既籠罩著作者的身影,又融匯著作者的靈魂。它是傳記作者對傳主的人格、性格、大的所作所為小的細枝未節乃至所想的自己的理解和解釋。傳記作者的這種有言或無言的理解和解釋是作者本人對人性的把握。
傳記可以說是一種懷舊,一種追憶逝水年華,一種人類對人無長久的無可奈何的哀悼!傳記就像一張沉人歲月的河裡的網,到得一定的時機,便迅猛地將它扯上岸,作一檢點,作一總結,以為網住的都是精華,都是最實質的,其實天曉得。網眼有大有小,再說適中的也並不一定是最本質的。麥芒說得好:“人和藝術一樣,與歷史總是存在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當人先於他的藝術變成歷史,僵化也就開始了。”當今社會,為活人作傳似已成為一種時尚。大而言之,也許是為了社會發展的需求;小而言之,也許是傳主或傳記作者的需求;但怎么看似都涌動著種種急功近利的浮躁。快,快,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出名要趁早呵!晚了即使出名了,也不那么痛快了。
當然,認識人的確是一件困難的事。每個人與自己的心距離最遠,跟別人的心也決不會距離太近。
張愛玲和張愛玲的心距離最遠。
張愛玲透徹地斷言:人總是髒的,沾著人就沾著髒。於是,只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她才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偏偏就是這個張愛玲,直言不諱她對世俗名利的追慕和渴求!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實踐作家的天才夢,她總是催著自己: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張愛玲悲涼地感悟:人世間沒有愛。家裡對她,是沒有恩情可言的。外面男子的愛呢?從《金鎖記》中的姜季澤到《傾城之戀》中的范柳原,從《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到《十八春》中的沈世鈞,無論遺少洋少、傳統的還是新派的知識男性,張愛玲的筆端烙刻著對他們深深的失望!可偏偏就是這個張愛玲,不顧一切不可思議地與胡蘭成墜進大火大水般的狂戀之中。一個是冰清玉潔的大家閨秀,一個是山地農家的叛逆之子:一個是情竇晚開的生命初戀,一個是有名無名八次婚戀的插曲;曠世才女與文化漢奸是怎樣地緣起情生又絕情滅緣?雖有多少恨,卻總留著不了情,漫漫半世紀!張愛玲是徹悟還是混沌?誰說得清呢?
張愛玲理直氣壯地宣稱:她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是的,她在上海淪陷區的輝煌,雖被人譽為廢墟上的罌粟花,但她的筆觸的確只限於男女糾葛人性情慾,這是明白無誤的。可偏偏就是這個張愛玲,在中國解放的歡慶鑼鼓聲中,加進了《十八春》、《小艾》的真誠的頌歌;墨跡未乾去到香港的她,卻又大唱了《秧歌》、《赤地之戀》反調;痛定思痛之後,她對她的這些極端之作只有採取遺忘或塗改的下策。自命清高的張愛玲又如何能徹底遠離塵世呢?
張愛玲是天才,張愛玲更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關於張愛玲及家族的資料並非豐富與翔實,好在張愛玲自己說過:“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離。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並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里,也成為自身的一次經驗。”張愛玲還說過:“寫小說的間或把自己的經驗用進去,是常有的事。至於細節套用實事,往往是這種地方最顯出作者對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實感。作者的個性滲入書中主角的,也是幾乎不可避免的,因為作者大都需要與主角多少有點認同。”
張愛玲還感嘆過:中國語言文字的魅力無處不在!好的文字、好的句子,有時可以叫你感動一生一世。語言的感召、感悟,其力量是巨大的。如果說攝影是用圖像留住原本已逝去的故事的話,那么傳記文學則是用語言留下原本已逝去的故事的藝術。從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中尋覓真正的張愛玲的語境,也許事倍功半,吃力不討好,但我寧願僅當編寫者,也不願撕碎張愛玲語言的纖維,不願攪混原狀汁的人生況昧。也許太傻,可傻就傻吧,人生能有幾回心甘情願的傻呢。
《張愛玲傳奇——舊上海的最後一個貴族》(原著《最後的貴族·張愛玲》)殺青於1992年,原本應張秋林先生之約,為海峽兩岸出版社所撰寫的。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收為《胡辛自選集》四卷本之一。跨越千年,2005年暮春雨時節,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又將此書作為六卷本選集之一推出,可稱周而復始;2012年薔薇雨中江西教育出版社亦將該書作為新的六卷本自選集之一推出,終天地有情。在此,向傅偉中先生和熊侃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
原後記寫於1993年10月5日
補充於2004年10月8日
再補充於2012年1月22日
序言
我喜愛薔薇雨。
如果女性注定與花有緣,那么開在暮春的最後的薔薇恐怕該屬於我。過了盛期,不見繽紛,卻有兀傲;不見嬌柔,卻有單瓣野薔薇的清芬與野氣;自然,還少不了也能刺痛人的不算少的刺兒。
而滋潤薔薇又凋零薔薇的雨,則交疊著繁華與荒涼,濃縮著生命與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無法透徹的人生的滋味。
我跟薔薇雨有緣。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自選集四卷本,含長篇小說《薔薇雨》和三部傳記——《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張愛玲傳》、《陳香梅傳》。2005年晚春,我的自選集六卷本又由21世紀出版社再次推出,像是生命的二度春,前四本之外,加了長篇小說《懷念瓷香》與論著《我論女性》。有意思的是,2012年薔薇花開時,我的自選集六卷本將第三次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這回,將論著《我論女性》換成《贛地·贛味·贛風——在流變與永恆中的地域文學藝術創作》,這部近80萬字贅著曾讓責編先生莫展一籌,可最終還是沒有割捨某部分而讓她整體誕生,算是勉為其難了。
其實,還是16年前的那句話:我鐘情的是小說,而不是傳記。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國評論家的話:小說是蒸餾過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餾技術如何,《薔薇雨》、《懷念瓷香》畢竟將我半生對古城南昌、瓷都景德鎮的種種積澱,苦痛又歡暢地蒸餾出來。因了歲月的滄桑,更因了現代化都市模型的誘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對準摩天大樓立交橋的暈眩,我願我的《薔薇雨》和《懷念瓷香》,以我這個女人的眼睛,為這方水土這方女人留下一點文字的攝影、筆墨的錄相。有人嘆說《薔薇雨》“儼然一部現代《紅樓夢》”,有人則俯瞰日“不過一市井小說耳”,或假或真,在我來說,很是珍惜這兩句,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昧”!1991年6月我曾應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之約將其改編成30集電視連續劇,並於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萬字的劇本列印本數十套,歷經花謝花開幾春秋,終於1997年冬由上海永樂影視集團求索製作社和江西電視台聯合攝製成28集電視連續劇,1998年暮春季節,熱播於大江南北,頗獲好評。都說當代題材的電視劇如女人般經不起老,《薔薇雨》與我的處女作《四個四十歲的女人》一樣,可是扛住了歲月的滄桑!
《懷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語》,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讀者的摯愛,與其說寫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說還是女人的故事。因為陶瓷的燒煉,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與水,在火的煉膛里,揉合撕擄、愛恨交加、難解難分,當天地歸於平寂時,結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的藝術峰巔,還可能是次品,乃至廢品,但不論結晶成什麼,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與水了,永遠不再!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經不起碰撞,你千萬別以為烈火的考驗能鑄就鋼筋鐵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輕輕一碰,它就摔得粉粉碎!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懷念瓷香》將我從22歲到30歲在瓷都景德鎮的人生閱歷傷懷其問,是走過歲月仍難以忘懷的追夢。1991年我作為4集撰稿的9集電視系列片《瓷都景德鎮》是中國第一部關於瓷都的大型專題片,獲得了中國電視二等獎;2004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個廣播電視藝術學碩士點首屆研究生拍攝的9集電視系列片《瓷都名流》,於2005年元旦始在江西衛視播放,被瓷都陶藝家稱為:“格調最高、藝術性最強。”“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實,且感人。觀人多日:好看!太短了!還沒看夠!”的確,瓷都景德鎮,溶入了我太多的摯愛。當然,在《懷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實的,故事是虛構的。但不管怎么說,陶瓷給人的總是永恆的驚艷。
我的傳記,其實也應該稱為傳記小說。《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創作於上世紀80年代末,因種種原因捱至90年代初才分別在海峽兩岸出版。該長篇傳記源於童年聽來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傳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1927年參加南昌八一起義的主席團成員——工商界的代表,他並沒有隨軍南下,吃了些苦頭後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證婚人劉己達正是大姑爹請來的,這個劉己達便是1939年早春在信豐挨過打的贛南專員,蔣經國後來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在南昌時則於一偶然的機緣,搭救過兵變中的軍閥朱培德,後來外公開了錢莊,但席捲全球的墨西哥白銀暴跌風浪中,他也一頭栽到底。1938年我父、母兩家族皆逃難到贛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蓮的外婆強撐門戶。外婆家在南昌時的女傭蓉媽,到贛州後曾在章亞若母親家幫傭,她沒有割斷與外婆的走往。這兩位都愛抽水煙的主僕,綿長而隱秘的談評話題之一便是章亞若神秘的死,這話題一直延伸到勝利後兩家族回歸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發現托著腮幫偷聽得人神的我們姊妹時,外婆會駭然告誡:別瞎傳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為何主僕年年月月愛聽愛說?在贛南時,我的父親胡江非從事音樂事業,我的二舅吳石希就是話劇《沉淵》的主角,《沉淵》公演之際正值章亞若猝死,蔣經國狂暴無理地禁演該劇,那時正是我表舅吳識滄領著他們不知深淺地與蔣經國抗爭了一番。固然我開筆寫這部書時,又尋訪了一些有關的人物並參閱了有關史料,但這故事已在我心中積澱了許久許久。我想,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愴的江西女人的故事。2011年10月20日,蔣孝嚴先生在台北親口對我言:“你的這本書是最早的、第一部全面深刻寫我母親的書,我從頭至尾、從頭至尾讀了,很感動。”該書原名《章江長恨歌》,後海峽兩岸出版人都改為現名,大概是從“名人效應”考慮吧。
《最後的貴族·張愛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選集時更名為《張愛玲傳》,現恢復原貌)殺青於1992年,因種種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別在海峽兩岸出版。仿佛是張愛玲在成全此書,據說解放日報刊出書評《“看張”的新文本/讀(最後的貴族·張愛玲)》的當天傍晚,新民晚報即登出張愛玲去世的悲訊。我想此書被評為華東地區優秀暢銷書,十幾家報刊發訊息發評論連載等跟這不無關聯。生命是緣,從某種視角看這算小奇緣吧。但我的心並不狂喜。想張愛玲人生,肉身處於繁華熱鬧中,靈魂卻寂寞荒涼;張愛玲辭世之時肉身極至荒涼,靈魂卻無法拒絕熱鬧。也許,荒涼與熱鬧的種種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傳奇?
關於《陳香梅傳》創作的前前後後,我已在該書的後記中作了冗長的描述,在此無須贅言。從認識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學形象,頭尾不過兩年,雖是有意識地走近她,但不能說是走進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美訪問時,未能見著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應紐約大學之邀,再次赴美作學術交流時,非常遺憾,又未能聯繫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寫出了一個真實的她?我只求在廣袤深邃的歷史背景中,勾勒出這一個女人尋尋覓覓的人生軌跡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瀾而已。
本事一經敘述就成了文學。張愛玲說過:“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我的傳記文學,是傳記小說。傳記可以說是一種懷舊,一種追憶逝水年華,一種人類對人無長久的無可奈何的哀悼!傳記就像一張沉人歲月的河裡的網,到得一定的時機,便迅猛地將它扯上岸,作一檢點,作一總結,以為網住的都是精華,都是最實質的,其實天曉得。網眼有大有小,再說適中的也並不一定是最本質的。
如果說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部長篇小說,我的人生近不惑時才與編小說糾葛在一起。只是我述說我的人生時人們說我在編小說,我編出小說時人們卻說那是我的人生!我的真實人生不乏傳奇,我的虛構小說卻編不出傳奇。
在數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選集,傳記壓倒了小說;2005年、2012年的自選集,都力圖打個平手,《我論女性》的前半部為論說,後半部附錄我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贛地·贛味·贛風——在流變與永恆中的地域文學藝術創作》前面為論說,後面是我創作的影視文本;仿佛想作個見證,贛地老女子我就是這樣看女性寫女性的。也像是猶在鏡中,雖然紅顏早已老去,但自己仍自在地久久地又細細地端詳自己。當然,心並不滿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頭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寫,寫女人”,我心依舊。
薔薇雨中的女人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會像“流言”般撒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謝作家出版社和責編李玉英女士,因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這么一套齊楚可觀的自選集,他們對我的確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薔薇雨中,在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和老朋友張秋林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六卷本的胡辛自選集又自信面世。2012年薔薇雨中,六卷本胡辛自選集三度登場,仿佛總也沒過氣,總也不見老似的,怎么說都是件高興的事。感謝江西出版集團副總傅偉中先生,感謝責編熊侃先生,他們始終尊稱我為老師,其實,我與他們亦屬忘年交。感謝南昌大學的扶植。我信:清泉汩汩,真誠如一,定會滋潤一方青翠田園的。
我自信我留著一份懵懂的真誠,對人對己。
愛讀惠特曼的詩:“我願意走到林邊的河岸上/去掉一切人為的虛飾/赤裸了全身/我瘋狂地渴望能這樣接觸到我自己。”
胡辛於南昌大學
原序寫於1995年12月27日
補充於2004年10月8日自紐約大學歸來
再補充於2012年2月2日
如果女性注定與花有緣,那么開在暮春的最後的薔薇恐怕該屬於我。過了盛期,不見繽紛,卻有兀傲;不見嬌柔,卻有單瓣野薔薇的清芬與野氣;自然,還少不了也能刺痛人的不算少的刺兒。
而滋潤薔薇又凋零薔薇的雨,則交疊著繁華與荒涼,濃縮著生命與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無法透徹的人生的滋味。
我跟薔薇雨有緣。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自選集四卷本,含長篇小說《薔薇雨》和三部傳記——《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張愛玲傳》、《陳香梅傳》。2005年晚春,我的自選集六卷本又由21世紀出版社再次推出,像是生命的二度春,前四本之外,加了長篇小說《懷念瓷香》與論著《我論女性》。有意思的是,2012年薔薇花開時,我的自選集六卷本將第三次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這回,將論著《我論女性》換成《贛地·贛味·贛風——在流變與永恆中的地域文學藝術創作》,這部近80萬字贅著曾讓責編先生莫展一籌,可最終還是沒有割捨某部分而讓她整體誕生,算是勉為其難了。
其實,還是16年前的那句話:我鐘情的是小說,而不是傳記。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國評論家的話:小說是蒸餾過的人生。不管我的蒸餾技術如何,《薔薇雨》、《懷念瓷香》畢竟將我半生對古城南昌、瓷都景德鎮的種種積澱,苦痛又歡暢地蒸餾出來。因了歲月的滄桑,更因了現代化都市模型的誘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對準摩天大樓立交橋的暈眩,我願我的《薔薇雨》和《懷念瓷香》,以我這個女人的眼睛,為這方水土這方女人留下一點文字的攝影、筆墨的錄相。有人嘆說《薔薇雨》“儼然一部現代《紅樓夢》”,有人則俯瞰日“不過一市井小說耳”,或假或真,在我來說,很是珍惜這兩句,這是我夢寐以求的“昧”!1991年6月我曾應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之約將其改編成30集電視連續劇,並於1992年10月由“中心”出了65萬字的劇本列印本數十套,歷經花謝花開幾春秋,終於1997年冬由上海永樂影視集團求索製作社和江西電視台聯合攝製成28集電視連續劇,1998年暮春季節,熱播於大江南北,頗獲好評。都說當代題材的電視劇如女人般經不起老,《薔薇雨》與我的處女作《四個四十歲的女人》一樣,可是扛住了歲月的滄桑!
《懷念瓷香》原名《陶瓷物語》,2000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也得到不少讀者的摯愛,與其說寫的是陶瓷的故事,不如說還是女人的故事。因為陶瓷的燒煉,太像人生,尤其是女人的人生!土與水,在火的煉膛里,揉合撕擄、愛恨交加、難解難分,當天地歸於平寂時,結晶出的,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的藝術峰巔,還可能是次品,乃至廢品,但不論結晶成什麼,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與水了,永遠不再!這就是人生。而愈是精美的瓷,愈經不起碰撞,你千萬別以為烈火的考驗能鑄就鋼筋鐵骨,非也,只要不小心輕輕一碰,它就摔得粉粉碎!這太像人的感情,尤其是女人的感情。《懷念瓷香》將我從22歲到30歲在瓷都景德鎮的人生閱歷傷懷其問,是走過歲月仍難以忘懷的追夢。1991年我作為4集撰稿的9集電視系列片《瓷都景德鎮》是中國第一部關於瓷都的大型專題片,獲得了中國電視二等獎;2004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個廣播電視藝術學碩士點首屆研究生拍攝的9集電視系列片《瓷都名流》,於2005年元旦始在江西衛視播放,被瓷都陶藝家稱為:“格調最高、藝術性最強。”“出乎意料的美、自然、真實,且感人。觀人多日:好看!太短了!還沒看夠!”的確,瓷都景德鎮,溶入了我太多的摯愛。當然,在《懷念瓷香》中,陶瓷是真實的,故事是虛構的。但不管怎么說,陶瓷給人的總是永恆的驚艷。
我的傳記,其實也應該稱為傳記小說。《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創作於上世紀80年代末,因種種原因捱至90年代初才分別在海峽兩岸出版。該長篇傳記源於童年聽來的故事。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傳奇色彩。我的大姑爹李郁是1927年參加南昌八一起義的主席團成員——工商界的代表,他並沒有隨軍南下,吃了些苦頭後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我的父母的證婚人劉己達正是大姑爹請來的,這個劉己達便是1939年早春在信豐挨過打的贛南專員,蔣經國後來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我的外祖父在南昌時則於一偶然的機緣,搭救過兵變中的軍閥朱培德,後來外公開了錢莊,但席捲全球的墨西哥白銀暴跌風浪中,他也一頭栽到底。1938年我父、母兩家族皆逃難到贛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蓮的外婆強撐門戶。外婆家在南昌時的女傭蓉媽,到贛州後曾在章亞若母親家幫傭,她沒有割斷與外婆的走往。這兩位都愛抽水煙的主僕,綿長而隱秘的談評話題之一便是章亞若神秘的死,這話題一直延伸到勝利後兩家族回歸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一旦發現托著腮幫偷聽得人神的我們姊妹時,外婆會駭然告誡:別瞎傳啊,要命的事。既然是要命的事,為何主僕年年月月愛聽愛說?在贛南時,我的父親胡江非從事音樂事業,我的二舅吳石希就是話劇《沉淵》的主角,《沉淵》公演之際正值章亞若猝死,蔣經國狂暴無理地禁演該劇,那時正是我表舅吳識滄領著他們不知深淺地與蔣經國抗爭了一番。固然我開筆寫這部書時,又尋訪了一些有關的人物並參閱了有關史料,但這故事已在我心中積澱了許久許久。我想,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愴的江西女人的故事。2011年10月20日,蔣孝嚴先生在台北親口對我言:“你的這本書是最早的、第一部全面深刻寫我母親的書,我從頭至尾、從頭至尾讀了,很感動。”該書原名《章江長恨歌》,後海峽兩岸出版人都改為現名,大概是從“名人效應”考慮吧。
《最後的貴族·張愛玲》(1996年收入我的自選集時更名為《張愛玲傳》,現恢復原貌)殺青於1992年,因種種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別在海峽兩岸出版。仿佛是張愛玲在成全此書,據說解放日報刊出書評《“看張”的新文本/讀(最後的貴族·張愛玲)》的當天傍晚,新民晚報即登出張愛玲去世的悲訊。我想此書被評為華東地區優秀暢銷書,十幾家報刊發訊息發評論連載等跟這不無關聯。生命是緣,從某種視角看這算小奇緣吧。但我的心並不狂喜。想張愛玲人生,肉身處於繁華熱鬧中,靈魂卻寂寞荒涼;張愛玲辭世之時肉身極至荒涼,靈魂卻無法拒絕熱鬧。也許,荒涼與熱鬧的種種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傳奇?
關於《陳香梅傳》創作的前前後後,我已在該書的後記中作了冗長的描述,在此無須贅言。從認識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學形象,頭尾不過兩年,雖是有意識地走近她,但不能說是走進了她的心扉。1997年7月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美訪問時,未能見著她;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我應紐約大學之邀,再次赴美作學術交流時,非常遺憾,又未能聯繫上她。我不知道,我是否寫出了一個真實的她?我只求在廣袤深邃的歷史背景中,勾勒出這一個女人尋尋覓覓的人生軌跡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瀾而已。
本事一經敘述就成了文學。張愛玲說過:“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為小說了。”我的傳記文學,是傳記小說。傳記可以說是一種懷舊,一種追憶逝水年華,一種人類對人無長久的無可奈何的哀悼!傳記就像一張沉人歲月的河裡的網,到得一定的時機,便迅猛地將它扯上岸,作一檢點,作一總結,以為網住的都是精華,都是最實質的,其實天曉得。網眼有大有小,再說適中的也並不一定是最本質的。
如果說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部長篇小說,我的人生近不惑時才與編小說糾葛在一起。只是我述說我的人生時人們說我在編小說,我編出小說時人們卻說那是我的人生!我的真實人生不乏傳奇,我的虛構小說卻編不出傳奇。
在數量和重量上,1996年的自選集,傳記壓倒了小說;2005年、2012年的自選集,都力圖打個平手,《我論女性》的前半部為論說,後半部附錄我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贛地·贛味·贛風——在流變與永恆中的地域文學藝術創作》前面為論說,後面是我創作的影視文本;仿佛想作個見證,贛地老女子我就是這樣看女性寫女性的。也像是猶在鏡中,雖然紅顏早已老去,但自己仍自在地久久地又細細地端詳自己。當然,心並不滿足,仍有失落,走了很久很久,回頭看看,幸而仍是“女人寫,寫女人”,我心依舊。
薔薇雨中的女人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會像“流言”般撒播么?
1996年的暮春,我致謝作家出版社和責編李玉英女士,因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這么一套齊楚可觀的自選集,他們對我的確是鼎力扶植。2005年的薔薇雨中,在二十一世紀出版社和老朋友張秋林先生的鼎力相助下,六卷本的胡辛自選集又自信面世。2012年薔薇雨中,六卷本胡辛自選集三度登場,仿佛總也沒過氣,總也不見老似的,怎么說都是件高興的事。感謝江西出版集團副總傅偉中先生,感謝責編熊侃先生,他們始終尊稱我為老師,其實,我與他們亦屬忘年交。感謝南昌大學的扶植。我信:清泉汩汩,真誠如一,定會滋潤一方青翠田園的。
我自信我留著一份懵懂的真誠,對人對己。
愛讀惠特曼的詩:“我願意走到林邊的河岸上/去掉一切人為的虛飾/赤裸了全身/我瘋狂地渴望能這樣接觸到我自己。”
胡辛於南昌大學
原序寫於1995年12月27日
補充於2004年10月8日自紐約大學歸來
再補充於2012年2月2日
編輯推薦
漫漫半世紀,張愛玲仍是誘惑人們釋讀卻難解的謎。寫張愛玲的書很多,可在還原張愛玲的語境上,《張愛玲傳奇:舊上海的最後一個貴族》則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文摘
書摘
月亮,是人生大舞台上永恆的場景呵。
“小姐,儂看中了啥書!”攤主湊上來問。
“喔。”她反剪雙手,微微俯下身,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這本《傳奇
》,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么貴,真還有人買嗎?”
“喔喲,兩百塊,真勿算貴。這本書阿拉還真勿想賣,留一本自家看看
。勿瞞儂講,四天裡相,就賣光哉!老派新派格人都愛看《傳奇》。”攤主
邊說邊收起這扇夜藍色的窗。
她仍裝著不相干的樣子:“真的嗎?真的賣光了?真的這本你要留給自家
看?”那聲音卻微微發顫。
“啥人騙儂?儂到別家書攤看看,哪裡還有《傳奇》?”攤主小心地收起
了這扇夜藍色的窗,繼而收攤。
痛快。痛快。
她發了瘋似的高興著。
她喜歡這藍綠色。
空曠的藍綠色的天,藍得一點渣子都沒有——有是有的,沉澱在底下,
黑漆漆、亮閃閃、煙烘烘、鬧嚷嚷的一片——這就是上海。
她生在這座都市。剛滿周歲就離開了這都市。都市沒印象。
八歲時,她第一次回到了這都市。坐在馬車上,粉紅底子的洋紗衫褲上
就飛著藍色蝴蝶——藍蝴蝶!侉氣而快樂的她做著藍色的夢。
在這都市的藍色的天空下,她連帶喜歡上了“英格蘭”,以為那裡藍格
盈盈的天下有著許多的小紅房子!儘管母親糾正她,英國多霧多雨,可她固
執地不改變這一個又一個藍色的夢想。她要去英格蘭圓夢。
因為戰爭她沒去成英格蘭,而是去了香港求學。大紅桔紅粉紅的廣告牌
倒映進藍綠的海水裡,雖犯沖,但畢竟富有刺激,18歲的青春和廣告牌的色
彩一塊溶進藍色的夢裡。
因為戰爭她沒有完成學業,三年後乘船回上海,夜過台灣海峽,從船艙
圓窗戶洞裡望出去,夜的海灣是藍灰色的,靜靜的一隻小漁船,點一盞紅燈
籠……真是如醉如痴地喜歡著呀。
藍色,是她的生命藍。
藍色有著古中國的敦厚含蓄,卻又分明洋溢著西方文明的鮮活;藍綠色
是年輕人的沒有邊的天,讓年輕的心飛到很遠很遠;藍紫色卻蘊積了太多太
多的憂怨,像鈍刀一點一點傷著你珍貴的感情……
天近黃昏。8月南方的黃昏是漫長的。這邊,太陽還沒有下去,熱氣灼
灼蒸人;那邊,月亮已漸漸升起,清冷傲視人間。被高大尖頂的建築切割過
的都市天空,日月共存。
她,並沒有走。她依舊反剪雙手,卻挺直了腰,仰起臉,微眯著眼,凝
眸這輝煌的瞬間。
收了攤的攤主不禁打量起她來,陡地,給震住了——
這是一個上頂天下立地的奇女子!
儘管她奇裝炫人,可在這摩登都市,她並不是那種望一眼就攝魂的漂亮
女子。在南方女子多嬌俏中,她的個頭略顯大,始終留著一點北方人的侉味
;在肥白如瓠的都市女孩中,她的膚色顯黃,卻是那種象牙黃的色澤;她的
髮型倒很隨便,燙過後長長了,披在肩上翹成兩鉤,像老式床幔上的兩隻掛
鉤,襯著標準的鵝蛋臉;五官極其端正,表情卻稍嫌缺乏,但惟其這呆滯,
才顯出那溫柔敦厚的古中國情調,惟其這缺乏,才透出一種森森然赫赫然的
皇室貴族之氣。
P12-14
月亮,是人生大舞台上永恆的場景呵。
“小姐,儂看中了啥書!”攤主湊上來問。
“喔。”她反剪雙手,微微俯下身,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這本《傳奇
》,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么貴,真還有人買嗎?”
“喔喲,兩百塊,真勿算貴。這本書阿拉還真勿想賣,留一本自家看看
。勿瞞儂講,四天裡相,就賣光哉!老派新派格人都愛看《傳奇》。”攤主
邊說邊收起這扇夜藍色的窗。
她仍裝著不相干的樣子:“真的嗎?真的賣光了?真的這本你要留給自家
看?”那聲音卻微微發顫。
“啥人騙儂?儂到別家書攤看看,哪裡還有《傳奇》?”攤主小心地收起
了這扇夜藍色的窗,繼而收攤。
痛快。痛快。
她發了瘋似的高興著。
她喜歡這藍綠色。
空曠的藍綠色的天,藍得一點渣子都沒有——有是有的,沉澱在底下,
黑漆漆、亮閃閃、煙烘烘、鬧嚷嚷的一片——這就是上海。
她生在這座都市。剛滿周歲就離開了這都市。都市沒印象。
八歲時,她第一次回到了這都市。坐在馬車上,粉紅底子的洋紗衫褲上
就飛著藍色蝴蝶——藍蝴蝶!侉氣而快樂的她做著藍色的夢。
在這都市的藍色的天空下,她連帶喜歡上了“英格蘭”,以為那裡藍格
盈盈的天下有著許多的小紅房子!儘管母親糾正她,英國多霧多雨,可她固
執地不改變這一個又一個藍色的夢想。她要去英格蘭圓夢。
因為戰爭她沒去成英格蘭,而是去了香港求學。大紅桔紅粉紅的廣告牌
倒映進藍綠的海水裡,雖犯沖,但畢竟富有刺激,18歲的青春和廣告牌的色
彩一塊溶進藍色的夢裡。
因為戰爭她沒有完成學業,三年後乘船回上海,夜過台灣海峽,從船艙
圓窗戶洞裡望出去,夜的海灣是藍灰色的,靜靜的一隻小漁船,點一盞紅燈
籠……真是如醉如痴地喜歡著呀。
藍色,是她的生命藍。
藍色有著古中國的敦厚含蓄,卻又分明洋溢著西方文明的鮮活;藍綠色
是年輕人的沒有邊的天,讓年輕的心飛到很遠很遠;藍紫色卻蘊積了太多太
多的憂怨,像鈍刀一點一點傷著你珍貴的感情……
天近黃昏。8月南方的黃昏是漫長的。這邊,太陽還沒有下去,熱氣灼
灼蒸人;那邊,月亮已漸漸升起,清冷傲視人間。被高大尖頂的建築切割過
的都市天空,日月共存。
她,並沒有走。她依舊反剪雙手,卻挺直了腰,仰起臉,微眯著眼,凝
眸這輝煌的瞬間。
收了攤的攤主不禁打量起她來,陡地,給震住了——
這是一個上頂天下立地的奇女子!
儘管她奇裝炫人,可在這摩登都市,她並不是那種望一眼就攝魂的漂亮
女子。在南方女子多嬌俏中,她的個頭略顯大,始終留著一點北方人的侉味
;在肥白如瓠的都市女孩中,她的膚色顯黃,卻是那種象牙黃的色澤;她的
髮型倒很隨便,燙過後長長了,披在肩上翹成兩鉤,像老式床幔上的兩隻掛
鉤,襯著標準的鵝蛋臉;五官極其端正,表情卻稍嫌缺乏,但惟其這呆滯,
才顯出那溫柔敦厚的古中國情調,惟其這缺乏,才透出一種森森然赫赫然的
皇室貴族之氣。
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