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作者簡·古道爾 (Jane Goodall)、菲利普·伯曼 (Phillip Berman),簡·古道爾博士著述的《希望的理由》是一部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傳”。在這部鮮活生動、發人深省的著作中,她詳細回顧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經歷乃至個人精神上的漫漫旅途,自己的母親、兒子和已故的丈夫,以及貢貝黑猩猩故事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
- 開本:32
- 類型:傳記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2760235
- 作者:簡·古道爾、菲利普·伯曼
-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 頁數:228頁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簡·古道爾(Jane Goodall) (英國)菲利普·伯曼(Phillip Berman) 譯者:祁阿紅
簡·古道爾(Jane Goodall),生於倫敦。自幼即對動物行為極感興趣。18歲離開學校,到赴非洲為止,她曾先後擔任過秘書以及影片製作助理。此後,她在非洲擔任古生物學家路易斯·利基的助手,與利基的合作經驗使她能於1960年在貢貝動物保護區設立一個營區,得以觀察該地黑猩猩的行為。1965年獲劍橋大學動物行為學博士學位。1977年她建立了“簡·古道爾人、動物與環境研究所”。1991年,她倡議並成立了“根與芽”組織,目的是使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年輕一代都能夠行動起來,為了環境、動物和他們自己的社區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1995年,被英國女王授予勳爵。簡·古道爾撰有許多書籍和論文,最著名的是《生活在人類的陰影中》(1971)、《貢貝的黑猩猩:行為模式》(1986)以及《透過視窗:對貢貝黑猩猩的觀察》(1990),此著作已被翻譯成15種文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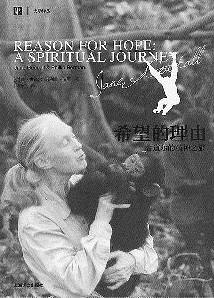 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
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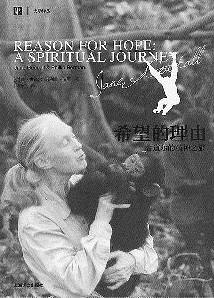 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
希望的理由:古道爾的精神之旅菲利普·伯曼(Phillip Berman),具有哈佛大學神學院比較宗教學學位。他的獲獎作品有《信念的勇氣》、《探索意義》和《回家的旅程》。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與簡-古道爾在一起,就像與聖雄甘地一起漫步。
——《波士頓環球報》
行為科學中的愛因斯坦。
——《洛杉礬時報》
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婦女之一。
——普利茲獎獲得者溫迪·沃瑟斯坦
簡·古道爾對黑猩猩的研究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
——史蒂芬-傑伊·古爾德
毫無疑問,她是對我們的知識世界最有影響的貢獻者之一。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在缺少英雄的時代中的一位女英雄。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波士頓環球報》
行為科學中的愛因斯坦。
——《洛杉礬時報》
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婦女之一。
——普利茲獎獲得者溫迪·沃瑟斯坦
簡·古道爾對黑猩猩的研究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
——史蒂芬-傑伊·古爾德
毫無疑問,她是對我們的知識世界最有影響的貢獻者之一。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在缺少英雄的時代中的一位女英雄。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名人推薦
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婦女之一。
——普利茲獎獲得者溫迪·沃瑟斯坦
簡·古道爾對黑猩猩的研究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
——史蒂芬·傑伊·古爾德
——普利茲獎獲得者溫迪·沃瑟斯坦
簡·古道爾對黑猩猩的研究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
——史蒂芬·傑伊·古爾德
圖書目錄
譯者的話
鳴謝
前言
第一章童年生活
第二章初涉世事
第三章非洲之行
第四章貢貝印象
第五章孤身一人
第六章十年變遷
第七章失落之園
第八章罪惡之源
第九章戰爭前兆
第十章同情關愛
第十一章生離死別
第十二章走出陰影
第十三章道德進化
第十四章皈依之路
第十五章希望之光
第十六章劫後餘生
第十七章新的起點
後記
關於簡·古道爾人,動物與環境研究所
鳴謝
前言
第一章童年生活
第二章初涉世事
第三章非洲之行
第四章貢貝印象
第五章孤身一人
第六章十年變遷
第七章失落之園
第八章罪惡之源
第九章戰爭前兆
第十章同情關愛
第十一章生離死別
第十二章走出陰影
第十三章道德進化
第十四章皈依之路
第十五章希望之光
第十六章劫後餘生
第十七章新的起點
後記
關於簡·古道爾人,動物與環境研究所
後記
1984年,菲利普·伯曼問我,是否能為他當時正在編的《信念的勇氣》一書提供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可不好寫,但我盡了最大的努力。
12年之後,菲利普又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合作,把我那篇文章中的觀點展開來談。我對他說我沒有時間。可是他卻提出我們出一本訪談錄——以神學家與人類學家對話的形式出現。我只要提供答案部分就行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在編寫過程中,書的範圍和重點發生了變化。原先構想的範圍廣泛的訪談錄變成了帶有更多個人觀點的書,變成了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傳”。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命題,而且我知道這意味著長時間的思考和寫作。
在初期階段,菲利普對我的採訪有時候是在美國,有時候在我英國的家裡,也有的時候在坦尚尼亞的三蘭港或者貢貝。他還採訪了許多在我的生活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接下來他就要著手對數英里長的磁帶進行整理和編排。
寫這樣一本書的確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又是一種挑戰。我對自己說,這也許是人生中的機會之一,是抓住它還是放棄它,全在於我們自己。
根據菲利普所提供的結構框架和他對訪談的闡述,我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如果我當時知道寫這本書要花多少時間,有時候要深深觸及自己的靈魂,進行那樣痛苦的思考,我想我就不會接受這樣的挑戰了。當時除了每年300來天在外講學,其餘所有時間我都在伯恩茅斯的家中寫這本書——那是是我惟一可以潛心寫作的地方。為寫這本書,我起早貪黑,將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統統放在一邊。就這樣,所花的時問也比我預期的要長得多。謝謝你萬妮,你犧牲了那么多我們原本可以在一起的時問。
在這本書里的有些段落是我從其他書里逐字逐句摘錄的。我盡力爭取用最佳方式通過語言來表達思想,或者描述特別有意義的體驗,有時候我所寫出的字句似乎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發揮。
現在這本書稿已經完成,照片也都已選定,書名也經商談確定。
可是這個旅程卻是永無止境的。
12年之後,菲利普又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合作,把我那篇文章中的觀點展開來談。我對他說我沒有時間。可是他卻提出我們出一本訪談錄——以神學家與人類學家對話的形式出現。我只要提供答案部分就行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在編寫過程中,書的範圍和重點發生了變化。原先構想的範圍廣泛的訪談錄變成了帶有更多個人觀點的書,變成了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傳”。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命題,而且我知道這意味著長時間的思考和寫作。
在初期階段,菲利普對我的採訪有時候是在美國,有時候在我英國的家裡,也有的時候在坦尚尼亞的三蘭港或者貢貝。他還採訪了許多在我的生活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接下來他就要著手對數英里長的磁帶進行整理和編排。
寫這樣一本書的確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又是一種挑戰。我對自己說,這也許是人生中的機會之一,是抓住它還是放棄它,全在於我們自己。
根據菲利普所提供的結構框架和他對訪談的闡述,我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如果我當時知道寫這本書要花多少時間,有時候要深深觸及自己的靈魂,進行那樣痛苦的思考,我想我就不會接受這樣的挑戰了。當時除了每年300來天在外講學,其餘所有時間我都在伯恩茅斯的家中寫這本書——那是是我惟一可以潛心寫作的地方。為寫這本書,我起早貪黑,將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統統放在一邊。就這樣,所花的時問也比我預期的要長得多。謝謝你萬妮,你犧牲了那么多我們原本可以在一起的時問。
在這本書里的有些段落是我從其他書里逐字逐句摘錄的。我盡力爭取用最佳方式通過語言來表達思想,或者描述特別有意義的體驗,有時候我所寫出的字句似乎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發揮。
現在這本書稿已經完成,照片也都已選定,書名也經商談確定。
可是這個旅程卻是永無止境的。
序言
許多年前,也就是1974年舂,我遊覽了巴黎聖母院。當時遊人不多,大教堂里肅穆恬靜。碩大的圓花窗在早晨陽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輝。我默默看在眼裡,心中暗暗稱奇。突然,教堂里響起風琴聲:是教堂一隅在舉行婚禮,演奏的樂曲是巴赫的《D小調托卡塔與賦格》。樂曲開頭的主題曲,我一直比較喜歡。這美妙樂曲在教堂巨大的空間裡迴蕩,仿佛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仿佛進入並占據了我的整個心靈。
一時之下,我突然感受到一種永恆。它也許是我體驗最深的如痴如醉狀態,一種對神秘世界的陶醉。高高聳立的大教堂;教堂建設者們的集體靈感和信念;巴赫的出現;他那把真理變成音樂的大腦;能理解那無法解釋的進化進程的大腦——當時的我就能理解——這一切都起始於原始塵埃的偶然旋轉,這叫我怎么能相信呢?既然我不能相信這是偶然的結果,那我就得承認反偶然。我必須承認宇宙中存在一種引導力量——換句話說,我必須相信有上帝。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所受到的教育是,要進行邏輯的、經驗的思維,而不是直覺的、精神的思維。就我所知,我60年代初在劍橋上大學的時候,在動物學系工作和學習的大多數師生都是不可知論者,甚至是無神論者。那些信上帝的人都秘而不宣,不讓同伴們知道。
所幸的是,我上劍橋大學時已27歲,信仰已經形成,所以沒受當時各種思想的影響。我信仰基督教,相信神的力量,我將其稱之為上帝。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對各種信仰的接觸,我逐漸認識到上帝只有一個,-不過人們使用的名稱不同罷了:真主、道、造物主等等。在我看,上帝是我們藉以“生存、活動和修身養性的偉大精神”。在人生道路上,我的信仰動搖過,對上帝的存在懷疑、甚至否認過。對如何擺脫人類給自己和地球上其他生物所造成的諸多環境和社會問題,我也曾絕望過。人類為什麼有那么大的破壞性?為什麼那么自私和貪婪?為什麼有時候還那么邪惡?每到這時候,我就覺得地球上出現生命並無重要意義可言。如果沒有什麼意義,那豈不正如紐約一個憤世嫉俗的光頭仔說的,人類只是一個“進化的東西”呢?
不過,我產生懷疑的時候相對較少,情況也各不相同——比如:我第二個丈夫死於癌症的時候;在蒲隆地那樣的小國爆發種族仇恨的時候(我聽說發生了殘酷的折磨和大規模屠殺,這就使我想起慘絕人寰的納粹大屠殺中令人髮指的種種罪行);我們在坦尚尼亞貢貝國家公園進行研究工作的4名學生被綁票並遭勒索贖金的時候。每到這種時候,我就問自己:面對如此可怕的苦難、如此深重的仇恨、如此巨大的破壞,我怎么能相信什麼命運天定呢?可是我終究擺脫了這些懷疑,而且大多數情況下,我對未來還是樂觀的。然而,如今很多人已經失去了對上帝、對人類命運所抱的信念和希望。 1986年以來,我幾乎一直在四處奔波。我這樣做是為簡·古道爾研究所的環境和教育項目募集資金,並與儘可能多的人共享我感悟到的一個重要信息。這個信息涉及到人類的本性以及人類與在這個星球上生活的其他動物的關係。這是希望的信息—對地球上未來生命的希望。這些奔波令人精疲力竭。比如我最近在北美為時7個星期的旅行就很典型。我總共到了27座城市,上下32次飛機(而且在飛機上還要處理大量積壓的文字工作),做了71場學術報告,直接聽眾達32500人。此外,我還接受了170次媒體採訪,參加了許多業務會議、午宴、晚宴——甚至還有早餐宴。我其他所有外出講學的日程安排也幾乎都這么密集。
在我的行程中,有一件事成了我與他人愉快交往的障礙。這個令人尷尬、莫名其妙的障礙,在醫學上稱之為“面容失認症”,用普通語言來解釋,就是識別面孔的能力較差。我一度認為這是思想懶惰造成的,於是就儘量去記我見過的那些人的面孔,為的是下次再見到他們的時候能把他們認出來。那些具有明顯外形特徵的人,比如面部骨骼與眾不同、長著鷹鉤鼻子、相貌特別俊或者特別醜的,都不難辨認。不幸的是,對其他面孔,我就認不出來了。我知道,有時候如果我沒有立即認出某個人,他就會感到惱火,我自己感到惱火自不消說。由於感到很尷尬,我就只好暗暗恨自己。
最近我跟一個朋友交談時偶然發現,他也有跟我一樣的問題。我簡直不敢相信。後來我發現我妹妹朱迪也有過類似的尷尬。也許其他人也有過。我給著名神經科大夫奧利弗·薩克斯博士寫信,問他是否聽說過這種與眾不同的情況。他豈止聽說過——他本人也是如此!他的情況比我還厲害。他給我寄來一篇克里斯廷·坦普爾的文章,標題是“發展式記憶損傷:面孔和圖案”。
雖然我知道自己不必感到內疚,但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我總不能見到一個人就跟他解釋說,下次再見到他的時候,我也許壓根兒就認不出他了!也許我應當這么做?這是很沒面子的事,因為多數人會以為我這是故意替自己找藉口,顯然是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裡——所以他們感情上受了傷害。我只好盡力而為——通常是假裝個個都認識!雖然這樣也有很尷尬的時候,但總比那樣好。
人們(無論我認識與否!)總是問我的精力是從哪兒來的。他們總是說我顯得非常平靜。他們想知道的是:我怎么能這么平靜?我沉思嗎?我信教嗎?我祈禱嗎?他們問得最多的還是:面對環境遭到如此的破壞,人類遭受如此的苦難,面對人口太多,消費過頭,污染、毀林、沙漠化、貧窮、饑荒、殘酷、仇恨、貪婪、暴力、戰爭,我怎么還這么樂觀?她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他們似乎在懷疑。她的內心深處究竟是怎么想的?她對人生有什麼看法?她的樂觀、她的希望里有什麼秘密? 我寫此書就是想回答這些問題,因為我的回答也許對人們有所助益。這就需要我對生活中許多不堪回首、想來痛心的往事進行大量觸及心靈、重新認識的反思。但我還是儘量實事求是地去寫,否則還有什麼必要動筆呢?作為讀者,如果你走在自己獨特的人生道路上的時候,發現我的思想和信念的某些方面對你還有所幫助,那我的一番勞動就沒有白費。
一時之下,我突然感受到一種永恆。它也許是我體驗最深的如痴如醉狀態,一種對神秘世界的陶醉。高高聳立的大教堂;教堂建設者們的集體靈感和信念;巴赫的出現;他那把真理變成音樂的大腦;能理解那無法解釋的進化進程的大腦——當時的我就能理解——這一切都起始於原始塵埃的偶然旋轉,這叫我怎么能相信呢?既然我不能相信這是偶然的結果,那我就得承認反偶然。我必須承認宇宙中存在一種引導力量——換句話說,我必須相信有上帝。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所受到的教育是,要進行邏輯的、經驗的思維,而不是直覺的、精神的思維。就我所知,我60年代初在劍橋上大學的時候,在動物學系工作和學習的大多數師生都是不可知論者,甚至是無神論者。那些信上帝的人都秘而不宣,不讓同伴們知道。
所幸的是,我上劍橋大學時已27歲,信仰已經形成,所以沒受當時各種思想的影響。我信仰基督教,相信神的力量,我將其稱之為上帝。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對各種信仰的接觸,我逐漸認識到上帝只有一個,-不過人們使用的名稱不同罷了:真主、道、造物主等等。在我看,上帝是我們藉以“生存、活動和修身養性的偉大精神”。在人生道路上,我的信仰動搖過,對上帝的存在懷疑、甚至否認過。對如何擺脫人類給自己和地球上其他生物所造成的諸多環境和社會問題,我也曾絕望過。人類為什麼有那么大的破壞性?為什麼那么自私和貪婪?為什麼有時候還那么邪惡?每到這時候,我就覺得地球上出現生命並無重要意義可言。如果沒有什麼意義,那豈不正如紐約一個憤世嫉俗的光頭仔說的,人類只是一個“進化的東西”呢?
不過,我產生懷疑的時候相對較少,情況也各不相同——比如:我第二個丈夫死於癌症的時候;在蒲隆地那樣的小國爆發種族仇恨的時候(我聽說發生了殘酷的折磨和大規模屠殺,這就使我想起慘絕人寰的納粹大屠殺中令人髮指的種種罪行);我們在坦尚尼亞貢貝國家公園進行研究工作的4名學生被綁票並遭勒索贖金的時候。每到這種時候,我就問自己:面對如此可怕的苦難、如此深重的仇恨、如此巨大的破壞,我怎么能相信什麼命運天定呢?可是我終究擺脫了這些懷疑,而且大多數情況下,我對未來還是樂觀的。然而,如今很多人已經失去了對上帝、對人類命運所抱的信念和希望。 1986年以來,我幾乎一直在四處奔波。我這樣做是為簡·古道爾研究所的環境和教育項目募集資金,並與儘可能多的人共享我感悟到的一個重要信息。這個信息涉及到人類的本性以及人類與在這個星球上生活的其他動物的關係。這是希望的信息—對地球上未來生命的希望。這些奔波令人精疲力竭。比如我最近在北美為時7個星期的旅行就很典型。我總共到了27座城市,上下32次飛機(而且在飛機上還要處理大量積壓的文字工作),做了71場學術報告,直接聽眾達32500人。此外,我還接受了170次媒體採訪,參加了許多業務會議、午宴、晚宴——甚至還有早餐宴。我其他所有外出講學的日程安排也幾乎都這么密集。
在我的行程中,有一件事成了我與他人愉快交往的障礙。這個令人尷尬、莫名其妙的障礙,在醫學上稱之為“面容失認症”,用普通語言來解釋,就是識別面孔的能力較差。我一度認為這是思想懶惰造成的,於是就儘量去記我見過的那些人的面孔,為的是下次再見到他們的時候能把他們認出來。那些具有明顯外形特徵的人,比如面部骨骼與眾不同、長著鷹鉤鼻子、相貌特別俊或者特別醜的,都不難辨認。不幸的是,對其他面孔,我就認不出來了。我知道,有時候如果我沒有立即認出某個人,他就會感到惱火,我自己感到惱火自不消說。由於感到很尷尬,我就只好暗暗恨自己。
最近我跟一個朋友交談時偶然發現,他也有跟我一樣的問題。我簡直不敢相信。後來我發現我妹妹朱迪也有過類似的尷尬。也許其他人也有過。我給著名神經科大夫奧利弗·薩克斯博士寫信,問他是否聽說過這種與眾不同的情況。他豈止聽說過——他本人也是如此!他的情況比我還厲害。他給我寄來一篇克里斯廷·坦普爾的文章,標題是“發展式記憶損傷:面孔和圖案”。
雖然我知道自己不必感到內疚,但仍然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我總不能見到一個人就跟他解釋說,下次再見到他的時候,我也許壓根兒就認不出他了!也許我應當這么做?這是很沒面子的事,因為多數人會以為我這是故意替自己找藉口,顯然是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裡——所以他們感情上受了傷害。我只好盡力而為——通常是假裝個個都認識!雖然這樣也有很尷尬的時候,但總比那樣好。
人們(無論我認識與否!)總是問我的精力是從哪兒來的。他們總是說我顯得非常平靜。他們想知道的是:我怎么能這么平靜?我沉思嗎?我信教嗎?我祈禱嗎?他們問得最多的還是:面對環境遭到如此的破壞,人類遭受如此的苦難,面對人口太多,消費過頭,污染、毀林、沙漠化、貧窮、饑荒、殘酷、仇恨、貪婪、暴力、戰爭,我怎么還這么樂觀?她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他們似乎在懷疑。她的內心深處究竟是怎么想的?她對人生有什麼看法?她的樂觀、她的希望里有什麼秘密? 我寫此書就是想回答這些問題,因為我的回答也許對人們有所助益。這就需要我對生活中許多不堪回首、想來痛心的往事進行大量觸及心靈、重新認識的反思。但我還是儘量實事求是地去寫,否則還有什麼必要動筆呢?作為讀者,如果你走在自己獨特的人生道路上的時候,發現我的思想和信念的某些方面對你還有所幫助,那我的一番勞動就沒有白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