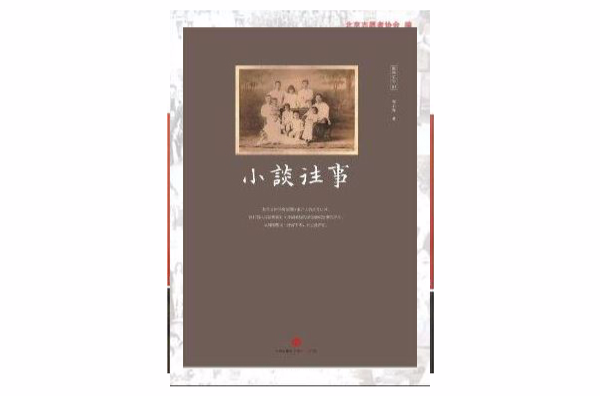《小談往事》內容簡介:權力對歷史給定的解釋是粗線條的、單色調的,但我們都想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口述史以更細緻、更豐富的內容瞻望社會名流、關注平民百姓,還原歷史的真實寫照。本書中,知名學者邢小群採訪了昔日望族建德周家的後人周啟博、著名教育家黃炎培的孫女黃且圓、前國務院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等人,重新記錄那些被塵封的家國往事。
基本介紹
- 書名:小談往事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244頁
- 開本:16
- 作者:邢小群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圖書目錄
第一篇 周家往事
第二篇 祖父黃炎培
第三篇 灰娃的國小中學和大學
第四篇 新中國水電的起步
第五篇 聽父親紀登查談往事
第六篇 為了兩岸夭空的安寧
第七篇 黃藥眠的跌宕人生
第八篇 我接觸的風雲人物
文摘
丁:這些年媒體不時提起您的祖父黃炎培先生與毛澤東在延安的那段對話,而對您祖父其他方面介紹不多。您是黃炎培的長孫女,能不能談談和他的接觸?
黃:關於我祖父,我覺得公眾有一些錯誤的印象。他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大家都認為他代表資本家,甚至說他是中國最大的資本家。其實,他沒有任何資本,他只是一個教育家。1949年以前,中國有3位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一位是陶行知,一位是晏陽初,一位是我祖父黃炎培。他一生最主要的事情是辦教育,他是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的開創者。
1958年,祖父80歲,寫了一本自述《八十年來》。他的父親是個知識分子,沒有土地,沒有房屋,終其一生都是租房居住。他的個性是得錢即使。先是做家塾教師,後漫遊河南、廣東、湖南,當督撫的秘書。祖父的父親在30幾歲時就去世了,他的母親死得更早。祖父十三四歲就沒了雙親,跟著自己的祖母生活,在外祖父家的私塾學經史。他祖母姓沈,出身川沙縣一個鄉紳大戶,家裡書比較多。祖母帶著他和他的兩個妹妹,就寄住在沈家。現在上海黃炎培故居,實際上是沈家的房子。沈家和黃家都是大家族,他們之間的通婚比較多。祖父的一個姑父也是沈家子弟,對他影響和幫助比較大。祖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後,經濟條件比以前好多了。他的姑父到了上海,對他說,你不要在鄉下待著了,應該到上海來學習,他就投考了上海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特班。外祖父受姑夫、舅舅、表伯父等親族資助進了南洋公學後,師從蔡元培。這個班有不少名人,比如李叔同、邵力子、章士釗。李叔同跟我祖父關係特別好,祖父受他影響比較大。祖父原來不會講國語,是李叔同教了他國語。李叔同不是北京人,祖父的國語學得也不好,聽不出跟他的家鄉話浦東話有什麼區別。蔡元培的教課方式是,交給學生一張清單,上列哲學、文學、政治、外交、經濟、教育等。讓每個人自己選擇,你想學什麼,認定一門之後,蔡元培就給他們開出應讀的主要書目、次要書目,讓他們到圖書館借書,閱讀,每天寫讀書筆記送老師批閱。祖父選擇了外交。蔡元培給他開出《國際公法》和外交文牘幾種。他在公學上到一半時,發生了學潮。不知道誰將墨水瓶打到老師身上,老師要開除學生;全班學生反對,學校就把全班開除;全年級反對,就把全年級開除;後來發展到把全校一千多學生都開除,從此公學解散。
還有一件比較有意思的事。祖父在公學上到一半的時候,他姑父說南京要舉行鄉試,祖父又去參加鄉試。鄉試正好考的是外交方面的問題:如何收回治外法權?他把學到的萬國公法用上了;當時清朝要改革,把八股文改成策論,好些人只會做八股文,祖父因上了南洋公學,會寫策論,所以他考得特別好,中了舉人。
從南洋公學出來,蔡元培鼓勵他們辦教育,說:“必須辦學校來喚醒民眾。”清政府簽了《辛丑條約》後,命令各省縣辦國小。祖父和幾個同道商量,認為只有教育能救國,就聯名上書縣府,把川沙的觀瀾書院改辦成國小堂。他知道川沙縣的縣官不敢批覆,就去找省里的頭頭,頭頭正好是張之洞,他對張說我們要辦個國小,張之洞就批准了。書院有田產,充當國小基金。祖父被聘為總理,親自授課,但只是盡義務,不拿薪水,還自膳。他還要做點其他事掙錢貼補家用。後又在老家辦了一個開群女學,也去授課。辦學的費用,主要是請上海實業家楊斯盛資助。通過祖父的遊說,楊斯盛先是慷慨捐銀300元,後來楊老先生髮展到毀家興學的程度。祖父因演說毀謗了皇太后、皇上,被拘捕,楊斯盛出錢為他請律師,又出錢資助他逃亡日本。回國後又是這位楊先生請他出面辦學。祖父先後創辦廣明國小、浦東中學、廣明師範講習所,月薪40元。當時,中學校長月薪100元。但祖父和他的同道感念楊先生的辦學熱情,都領薪極少。祖父還說服了當時江蘇省的一個頭兒,讓他們拿出一部分稅收辦教育。這樣一來,教育經費就比較充裕了,教育發展得也比較快。祖父在江蘇的時候,江蘇教育特別發達,主因祖父在江蘇的努力。
1905年,在蔡元培的家裡,祖父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後來,祖父在江蘇學務會(後改名江蘇省教育會)被推為幹事,成了江蘇教育界的名人。
1909年清廷籌備立憲,各省設咨議局,祖父當選為江蘇咨議局議員。後在全省120人的議員中當選為常駐議員。在辛亥革命中,他是教育界推動革命的主力。
祖父擔任江蘇教育會常任調查幹事時,發現中學生畢業後,只有少數人能升學,大多數苦於就不了業。他就在1918年發起創辦了中華職業教育社。思路還是走實業救國的路。辦社、辦校、買機器、造房子的錢,一方面向國內社會募,一方面到南洋的新加坡等地募集。那時華僑領袖之一陳嘉庚就答應每年給他們社1000元。他們也通過銀行擔保,發行了教育債券。
祖父也參與創辦過大學,像東南大學。我父親跟我說,他當時為了集資辦學,必須跟資本家接觸,向他們要募捐,所以認識了很多上海大資本家,和這些人有比較深的交往。父親說,有人認為祖父黃炎培是資產階級代表,或者說在全國是個人物,因為南洋那些最有名的資本家他都比較熟悉,抗戰的時候他也向他們要過募捐,但祖父自己根本沒有任何資產。
1931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祖父在上海參與發起成立抗日救國研究會。第二年淞滬戰事,他們還從軍需方面支援了十九路軍。抗戰爆發,他帶領職教社和學校去了四川。這時,職教社下屬和委託設計的職業學校、補習學校已有幾百所,成為三四十年代的一種風尚。
1940年,為了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他們組織了民主政團同盟,職教社是組成單位之一。同盟就是民盟的前身。祖父是第一任中央主席。此後,他才較多參與一些政治活動。
和其他弟妹相比,我接觸祖父多一些。記憶中第一次看見他,是在抗戰勝利後的重慶。當時寄居在重慶的人都想從後方往南京、上海那邊走。祖父原來就是上海人,也要回去,但堵在重慶的人太多了,只好等。抗戰時期,祖父家在重慶,我們家在成都。抗戰勝利後,我家也到了重慶,從那時起,我才有了對祖父的印象。
邢:您當時幾歲?
黃:我是1939年生的,大概6歲吧。
我印象里,祖父住的房子沒有我們家好。抗戰中,父親所在的水利局發不出工資。他辦公司,參加投標,修美軍軍用機場,賺了一些錢。父親到了重慶,在巴蜀學校附近買了一所別墅式的房子,巴蜀國小就在旁邊,家裡挺寬敞。我父親的觀點是:花了的錢才是你自己的。結果新房子住了半年,我們就回南京了。他把房子又賣了。我祖父當時住在附近山坡上一個很舊很破的二層樓房裡。因我母親先回江蘇,父親就帶著我和弟弟,搬到祖父那裡住了些天。祖父好像沒有什麼固定的收入,幫人家做一件什麼事,或者促成一件什麼事,有人就給他一筆錢。後來中華職教社會給他發一些錢。聽我母親說,在抗戰勝利的那一段時間,父親還接濟過祖父。祖父當時沒有太多收入。參政員好像只算是社會工作。我大伯父是武漢大學教授,在樂山。當時大學教授特別窮,吃不飽飯,大伯母是個美國人,就自己做一些糖果糕點,讓孩子出去賣,1943年或1944年,我大伯父去世了,家裡生活艱難,祖父就讓我父親和其他子女,每個人接濟我伯父一些錢,他自己是拿不出什麼錢的。其實,祖父生活最好的時候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比較安定,而且住的條件比新中國成立前好到不知道哪去了。
另外,我覺得祖父在婚姻問題上,也接受了新的思想,他特別倡導男女平等。他辦了國小,就讓妻子和兩個妹妹去上學,以自己當教師的工資抵三人學費。他又特別恪守舊道德。祖父曾向自己留洋過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你們是先結婚後戀愛還是先戀愛後結婚的?祖父說自己是先結婚後戀愛的,有人說是先戀愛後結婚的。祖父對我的祖母特別尊重,且讓自己的孩子都要尊重自己的母親。上海管母親叫“姆媽”,川沙叫“姆娘”,祖父就把方言的“姆”字改成恩愛的“恩”,讓他的子女叫母親“恩娘”,即對子女有恩的意思。我父親讓我們對母親也叫“恩娘”。父親在美國時給家裡寫信,祖父在回信中細心地說,你的字太草,又寫得比較小,以後要把字寫得大些、工整一些,這樣你母親才能看得清楚。可見他對妻子的體貼和尊重。
有一年我去美國,看到大伯父兒子家有一個祖父寫的條幅。前面四句是描寫峨眉,最後四句說:“功名期望皆身外,天地莊嚴在眼前,此體此心都付汝,母心純善體純堅。”這是他對一個母親的讚美,是對一個心地善良和身體健康婦女的讚美,表現了他的婦女觀,這種思想觀念在當時也是比較新潮的。現在的電視劇總是瞎編一氣,給我祖父身邊編出像小蜜一樣的人,似乎和我祖父有什麼特殊關係。連我表妹都被搞糊塗了,還問過我,到底祖父有沒有緋聞。我說沒聽說過。祖父是一個很嚴謹的人。其實,他在上海那么多年,二三十年代,上海有那么多小報,真有小蜜早就傳遍了。有個朋友對我開玩笑地說,在那個年代,如果他要找第二個太太,他那么有名,要找早就找了,不必弄個小蜜什麼的。現在一些人不好好去研究歷史,研究那個時代人的道德追求和操守,編的東西一看就假。
我的親祖母是1940年或1941年去世的,她本來已經到了四川,可能對一些瓶瓶罐罐放心不下,非要回到老家看一看,一回老家,就高血壓發作去世了。繼祖母跟我的父親年齡差不多。我祖母走的時候,我弟弟剛出生不久,我才一歲多快兩歲,所以那些小叔叔、姑姑(繼祖母的子女)都比我小一些。
邢:您祖父兄弟幾個?
黃:我祖父家就他和兩個妹妹。我祖父的父親也是單傳。到我祖父,孩子就比較多了。
在北京
黃:我們家是1953年1月搬到北京,以後跟我祖父交往就多了,過節時都要到祖父家。那時候他住在安兒胡同,有一個比較大的四合院,生活比從前好得多了。
那個四合院還是比較講究的。一進門往右拐,是一個較小的院子,警衛員就住那裡。南邊有幾間大的屋子是他對外的會客室,家裡人一般不到那裡去。再進一個門,才是正式的套院。套院雖大,但不算奢華。後頭有鍋爐房等附屬設施,院裡也住了10幾個人,像祖父的秘書,還有廚師、 兩個保姆等,都是國家工作人員。
到北京後,聽說祖父“五一”、“十一”的時候可以上天安門觀禮,我和弟弟都想跟他去。父親讓我們自己去說。我們先找了繼祖母,她和祖父商量後說,我們倆可以去。1953年的“五一”,我和弟弟,連同小姑姑、小叔叔擠在小汽車裡,和祖父去了一次天安門城樓,晚上看焰火。在小車上祖父興奮地對我們說,新中國成立了,中國多么好,毛主席多么英明偉大。他說得挺真心。現在的年輕人不太理解那時老人們的想法。祖父年輕的時候講演,被逮起來要殺頭,講演的內容都是帝國主義怎么欺負我們,瓜分中國。現在終於把帝國主義趕跑了,是個特別值得驕傲的事。我記得在汽車上祖父和我們說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話。
毛主席來以前,我們已先到了,就坐在天安門檢閱台,那裡擺了好些椅子,我記得當時旁邊坐著包爾漢夫婦,他們好像也帶了倆孩子。祖父坐在比較中間的位置,是隨便坐的,沒有排位。毛主席來了,走到我們面前,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問我祖父:這都是你的娃兒啊?祖父說是。我們就跑上去跟毛主席握手,毛主席高興地跟我們一大群小孩握手。毛主席的手很大,又很軟,我特別興奮,握完了又去握了一次。但是,我對劉少奇沒什麼好印象。他在毛主席之前上來,我們小孩都躍躍欲試想跟他握手,他根本不理,就從我們面前過去了,也沒有和我祖父說任何話。不像毛主席還跟我祖父打招呼。20世紀60年代我上了大學。快到“餓肚子”的時候,我們正下工廠。工廠在城裡,放假我就去了祖父家裡,又跟他上了一次天安門,看見了毛主席,又握了一次手。是“五一”還是“十一”記不清了。那一次好像有一些蘇聯領導人來,我們與赫魯雪夫已經發生分歧。記得布爾加寧穿著藍的軍裝,特別耀眼,特別漂亮。我看見林彪獨自坐在一個藤椅上,不理人,臉孔煞白,我們也沒敢前去握手,只想去跟毛主席握手。毛主席走的時候,我又跟著去看了看,他從城樓走下去的時候,有6個警衛圍著他一起走下去,都是高個子,前後各一,左右側各二。
序言
口述歷史的工作,我們已經做了十幾年,深知其中的甘苦。
首先,尋找合適的採訪對象並非易事。固然,口述歷史既可以瞻望社會名流,也可以關注平民百姓。但雜誌是公共平台,希望展示的內容有較高的文化歷史含量。完全民間的家長里短,不足以吸引讀者。與重大歷史相關的人事,才是讀者的興趣所在。
正好,當時周啟博先生從美國回來探親。我們和他聯繫,請他講述周家的往事。天津周家,上溯五代,出現過許多影響歷史的重要人物。第一代周馥官至兩江總督、兩廣總督。第二代周學熙當過北洋政府的財政部長,是山東大學的創始人,也是中國近代工業的先驅。周啟博的爺爺周叔嫂是第三代,是民族工商業的領袖人物,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啟博的父親周一良是第四代,以史學家著名。周家這一代還出了許多著名的學者教授。周啟博先生的本職工作雖然是工程師,對歷史卻有很深的研究。請他口述“周家往事”作為欄目的開場戲,可能是恰當的選擇。此文在2012年第一期《信睿》刊出以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接著,我們又採訪了黃且圓,她是黃炎培的孫女、黃萬里的長女、楊樂的夫人,我們請她回憶祖父和父親。當時她已經身患癌症,還是接受了我們採訪,並校訂了文稿。2叭2年3月10日,文章還沒有刊出,她就與世長辭,年僅73歲。這篇口述的發表,成了對她的紀念。
接著我們又採訪了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先生。紀登奎65歲便溘然長逝,帶走了太多的歷史秘密。好在晚年和兒子有所交談。聆聽紀坡民的轉述,多少能夠彌補一些遺憾。 對李銳的採訪,是十年前進行的,早已整理成文,但李老一直無暇審訂。主要原因是李老離休後仍然十分繁忙,各地客人登門拜訪,川流不息。他每天寫日記都要利用清晨時間。他的寫字檯每天都有新收的信件、材料,有人請他作序,有人請他題字,有人送他新書和文章,他的案頭堆積如山。他寫了一輩子文章,不願意草率應對,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認真修改。經他的女兒李南央出面促進,終於讓李老在九五高齡,完成了對口述往事的校訂。
我們採訪的鄰居劉心儉先生,本人並非高官,也不是國家領導人的秘書、子女。但他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也曾參與推動了一項政策的改革。當代中國的歷史轉型,輿論往往將功歸於政治領袖。其實,歷史的進步是合力作用的結果。領導人的決策固然重要,但一些小人物的促進也不應當忽略、湮沒。我們在生活中會遇到曾在歷史變遷中起過作用,又不被歷史所重視的人,他們可能僅僅提過一次建議,表達過一次意見,參與過一次行動,卻為一個舊制度的終結和一個新制度的開始提供了契機。如實記錄下他們的聲音,是史學工作者不應推卸的責任。
最近幾年,內地讀者對黨史國史的興趣持續升溫。口述史尤其受到歡迎。箇中原因,其實並不神秘。是人,都想知道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權力對歷史給定的解釋,是粗線條、單色調的,往往經不起人們與自己的生活體驗對照。於是,人們就希望得到更細緻、更豐富、更切近生活真實的歷史信息。不論是回憶錄、口述史,還是專題研究,只要在更細緻、更豐富、更真實方面確有補益,就能得到讀者的青睞。我們的心愿,就是把這樣的信息奉獻給讀者。
丁東,邢小群
201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