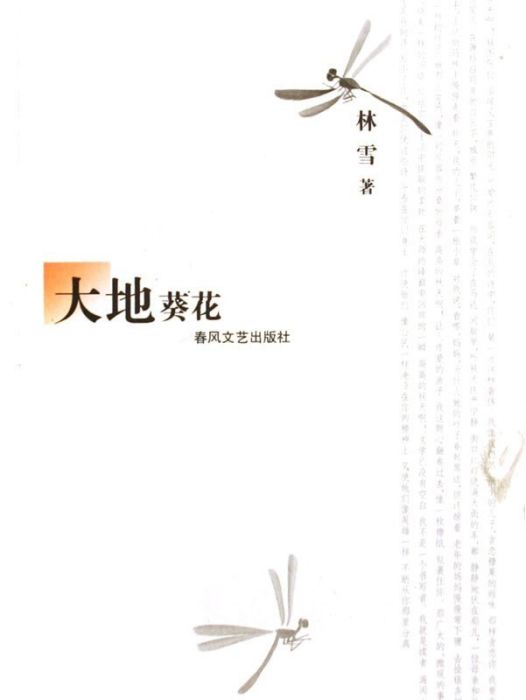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大地葵花
- 作者:林雪
- 創作年代:當代
- 文學體裁:詩集
- 字數:105千字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作品鑑賞,作品影響,作品評價,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大地葵花》是後工業時代尋求心靈突破的一部詩歌地理。它是一部詩歌的地方志,詩人以還鄉人的視角,打量一座時間的廢墟。在歷史遺落的細節中,發現民間個體身上閃爍的黃金品質;在悲愴的現實新聞場景中,放進一顆樸素的平民心腸。詩集試圖依託民間的本土資源,建立與後工業時代強大背景相抗衡的綠色信仰。對後工業時代的批判鋒芒,溶解在詩人對平民境遇的深切悲憫之中,折射出時代的命運。
作品目錄
《大地葵花》初版自序 1 大地篇 岩石上的那個人 在蓋牟城 睡吧,木底 關嶺的少女 午後的死亡 陶街 柳條邊 我歌唱塵埃里深積的人民 放牛老人 我的馬車帶走了哪些詞? 一個農民在田裡直起身 生活就是活著 有生之日 風中的少年 我們窮困悲苦,無人知曉歌頌 星星一樣的好人 憤怒的蕨 那個人荷鋤而歸 在小鳥叫聲里金子出現 風把我從詩歌中吹醒 死亡風景 從最簡單的事情開始 我愛上了山谷 一個句子有多少條命 在大地上風不為人知地吹著 高坡玉米 詩意秧苗 土豆田 我用第三個靈魂歌唱 落日光芒 在一切高於詩歌的地方 渾北人家 我從歸來的村莊出發 那些我還沒遇見的人 朝著赫圖阿拉方向 車程 在一棵馬齒莧旁小心地躺下 我用泥土寫出一整本詩集 | 蘇子河邊的女人 一首詩中的赫圖阿拉 河水曾漫過水源地以西 下一首:苦難。下一首:自由 東州藍 炊煙小鳥 永恆的黃金和人民 一片終結者的時間 給孩子們 在通什的谷地停下 人民深深地種植 高高的秋天啊 有一個早晨下起了雪 來自塌陷區第N個新聞 樹林之詩 新的一天正慢慢越過永陵山嶺 一首詩有沒有前世? 在早上最純真的時分 遙遠的鶴 在一個叫赫圖阿拉的地方 那個清晨 在站前快餐店要白開水的父親 語音提示 給孩子們 坐在場院裡瞌睡的老祖母 河水安靜而緩慢地寫詩 再過永安橋 2 葵花篇 鄉村客車 外省方式 在大風中追趕汽車的媽媽 公交站牌下的南方小孩 平遙報童 你是誰啊?我的兄弟 令聞街186號轉角處地攤上的糜子 蹲著 陳紅彥之死 對一個河南少年的詩歌練習(三首) 詩:平庸而破碎的心靈之禱(代跋) |
作品鑑賞
- 赫圖阿拉情結
展讀詩集,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關鍵字是“赫圖阿拉”,它在女詩人筆下的反覆出現,堪稱是虔誠般的信奉。“赫圖阿拉”是滿語,漢意為“橫崗”,即平頂的山崗。在東北大地上,即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蘇子河南岸,有一座古城依山而建,這是三百多年前後金時代的第一都城“赫圖阿拉城”。在這本詩集中,“我曾經努力想寫出一些平凡的、感人的句子,寫出平凡而悲傷的真理,寫出自己悄無聲息的、低聲部的熱愛”。於是,“這種愛有了一個象徵,一個載體,由赫圖阿拉山地,到撫順的丘陵,到遼瀋平原,到整個祖國”。這是詩人在詩集“初版自序”中的表白。其可貴之處在於詩人意識到自己的詩已經不是青春年代那些超越或激烈的幻影,那些介於現實生存與子虛烏有的迷茫;而是生活中樸素、深刻而又充滿思考的細節,抑或是對於生活(本源)的追問。由是,詩人在詩歌文化版圖上尋找到一個堅實而可靠的坐標點——赫圖阿拉。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情結既是詩人立足於大地之上用詩歌跟歷史與自然對話,又是《在一切高於詩歌的地方》,讓“那些玉米之上的/蒼穹,玉米之下的面孔/在回憶中一一醒來”。可以從女詩人對於一個詞的反覆敘寫中感受到其寫作的韌性和執拗,那種全新的解讀所帶來的可能是持久不斷的、秘不可宣的愉悅。這是女詩人對詩的本質的親近和深入,是最貼近生活本質的原始奧秘。“我注定被生下來。注定寫下這首詩/今天是我結業的日子,撫順的地理學/是我血液里的課程。一個情結/在我神經上扎駐,我愛那些地名/愛我生前和死後的那些人。遠古的鬼魂”(《睡吧,木底》)。
讀林雪的作品,可以從她有意釋明的事物中,聆聽她給詩歌閱讀者指示的方向,這方向並非是一塊路標,而是一種暗示,它可能是聲音、光芒,是潮水般漲滿了整個道路的腳踏車隊,是一條縱橫南北的主幹道,抑或是一棵小心地躺下的馬齒莧,一隻飛向火的蛾,總之這些都是具象的、觸物的,在其詩中出現,仿佛是靈魂的極光飛揚著集束的力量,導引人們進入到詩中所敘述的倫理世界。“赫圖阿拉!我,一個/漢族的女兒,不是尋找/你對一個女人的隱語,而是尋找/命運里樸素而深遠的象徵”(《高坡玉米》),“赫圖阿拉!那些我們無力知道的命運/背後,風兒吹起的地方/生活一如既往等著我們/現實即是魔幻,魔幻即是現實/那種對迷宮的模仿和質疑/使感覺越過了自己的本能/怎么還原到我們內心”(《詩意秧苗》),這種如縷絮語似乎是關於靈魂的探尋與照射,更是對命運、本真人生揪心的體驗和詰問,這不再是青春的夢幻投影,而是以思考的行為哲學為背景的精神現實和內在渴求。“赫圖阿拉!我書寫著你,一直寫到/靈魂里開出玫瑰。一個女人/邊向前走,邊從心靈里摘下刺荊/自我的碎片!絕處的生機!在知識和肉體消散/至無限的地方,詩歌和詞語又一次出現了”(《我從歸來的村莊出發》)。作為一個現實中的生活場景,或者“經驗中”的世界,詩人自言她也未嘗想到,因為一次尋常的短途旅行,竟能讓她在後來的10年間,陸續回到那裡,寫出了這些詩篇。於是乎,“那個出生時,曾在內心分裂成/無數自我的女人,那個隨時都在內心中/死去的女人,通過詩歌完成了/她自己的詩意或愛情”(《生活就是活著》)。一個詞,就是一條探秘生命和靈魂出口的通道。越過永陵的山嶺,越過生活的廣闊無邊,驅動著詩人在語言內外書寫,在“內心分裂”的生存境遇中徐緩而優雅地展開。對一個詞的深刻體驗和反覆詠嘆成了穿越經驗或歷史的某種催化劑,成了強化詩歌生命和力量的維生素。並且,“與我的現在來一次哲學意義上的相遇”(林雪語)。
- 憂鬱的詩意
從林雪詩歌文本中不難窺見一種情調,那是一種憂鬱的詩意。儘管她的詩如大地上生長出來的“葵花”,其間布滿了岩石、陶街、炊煙、玉米、秧苗、河流、山嶺、樹林、村莊等可感的自然意象,也映現了相互關聯的靈魂、愛情、命運、時間、死亡等相對抽象的思想意象;然而,“你的心,在這個世界上/一個叫赫圖阿拉的地方/靜靜地感恩、哭泣”(《在一個叫赫圖阿拉的地方》),“而我為什麼憂鬱妥協?今天早上,在孩子的哭聲中/我摘下衫領上的一根頭髮/我的嘴角又多了一絲皺紋”(《朝著赫圖阿拉方向》),“赫圖阿拉,只有這樣時間和憎恨才能從我身體/內外同時開始。我在詩歌中/感覺憂鬱,沒有確定所指”(《風把我從詩歌中吹醒》),“我的眼睛在天空和牲畜的複眼中/看著大地的歡樂悲苦。赫圖阿拉!/我的一部分血管盤旋在你的礦脈里/我的手,一部分的頭髮和指甲/沉積成鈣,混在你的塵埃里”(《在大地上風不為人知地吹著》)。無論是對時光流逝的喟嘆,還是閱覽大地上的悲欣交集;無論是看到“土路上的每一寸都鋪滿悲傷”之後《我用第三個靈魂歌唱》,還是“駐紮在記憶久久縈迴的地方”的《一首詩中的赫圖阿拉》;無論是“她變白還是變藍”的生活就是要先生出再活下去的《生活就是活著》,還是坐回到清晨光線里看到《一個農民在田裡直起身》如看到了“他精神上的起伏和大地詩句”……這些總是凝聚著一種憂鬱的人生況味,一股對於自然生命流程的感傷詩意,含蘊著詩人的思想、心靈和情感等方面所積淤的矛盾與憂思。誠然,這種憂鬱的詩意生成並非一時心情上的憂愁或傷感,而是一個有思想、極敏感且情感豐富的創作主體面對個人、群體,甚至人類的遭遇與命運的不幸所形成並表現出來的一種沉湎於痛苦的思索之中的心態。
林雪詩歌同樣關注“死亡”,她筆下的《午後的死亡》特別深刻、悽美而動人。“死亡啊這是大街上去年冬天的雪這是我/被河流/沖刷後的身體從指紋一樣的細沙到最後/的辭彙我們/之間的默契如同一張玻璃在粉碎保持/住唯美”,貫穿其中的那種精神與現實感,“那么美,為什麼啊,只是/為了等待,為了被敲碎”(《死亡風景》)。這些意象和情感經驗的不斷復現和瀰漫,在無形之中強化了憂鬱的詩意氛圍。難得的是,她把筆觸延伸到生活底層的不幸者中,在慘叫聲里斷送青春生命的《陳紅彥之死》,讓詩人作為一個“倖存者”,在與命運玩一種“賭博遊戲”的同時,頓悟到“一些人死了。另一些人活著/一生是一次深長的葬禮/我們活著。倖存者/只是對死亡證明”。詩人深深的憂鬱融入了人物悲劇性的“死亡事件”中,這是對於生存價值的肯定和認同,對於至高無上的生命存在的無奈與嘆息。林雪這份關注和傷感是別樣的,那是置身於特定境遇中所感知的屬於生命與時間的憂鬱,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憂鬱的沉思。
- 平靜而開闊的敘事
讀詩集《大地葵花》,呈現的仿佛是另外一個林雪。這樣說,其意是指這部詩集的作品比之她早期的以抒情為主的詩境而言,有明顯的不同,但這肯定是一種突破。她似乎變得更為寧靜、自如和開闊了,儘管依然帶有激情。前期詩作中那種注重“詩眼”語句的特點,在這裡已轉換成滲透於整個詩作的一種意味,既深沉又圓融,妙不在句而在句與句之間。就句式來說,又非追求詩化的警策,顯得素樸而細微。那些平靜自然的敘述,洗盡鉛華的清新,令人回味深長。詩集裡大部分詩作,尤其在第二輯“葵花篇”中,她常從具體而富有質感的人物和事件出發,去尋找合適而可靠的意象外衣,藉助敘述性甚至對話式語境的配合,營設整體情緒氛圍,抒寫節制而從容。即便是表現那種具有哲理意味的作品,也顯得相當冷靜。她筆下那些富有歷史感的詩篇,如《岩石上的那個人》《在蓋牟城》《睡吧,木底》《陶街》等,無法把握的輕佻的時間、一杯水的命運、越來越淡的愛情、生活的薄脆、人情的冷暖,是如此的令人格外動情,但在字面上是平靜的,甚而是寧靜致遠的。
林雪詩歌除了有著一般女性詩人靈動細膩、瀰漫性強的特點外,還有強烈的懸浮感和暗示性。但她不像一般女性詩寫者擺脫不了的那種自戀性或泛性化,這使得她的詩更經得起品讀。她認為好的詩人有能力追求獨立和自由的生活。她不憑恃對兩性世界的關係書寫來表現自己,她希望看到自己的精神在平常事物損耗中,仍然沒有喪失詩意和耐心以及生髮出光亮的東西,非常靈慧地完成了從經驗世界向著生命意識與哲學思考的超越。即便是寫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她也能別出心裁。這是因為她變得更加睿智了,而這種獨特同樣離不開她的靈慧和感覺。與同為六十年代出生者關注或偏重於對宏大敘事主題的抒情的路數有別,她的感覺來源於普通生活中的人和事物,來源於習慣的甚至瑣碎的“重複”的東西,從而律動出某種寧靜的詩情,並努力做到適度把握和自如操控。於是,詩緒就在這種日常化的感覺背後,悄無聲息地產生了深化的效果。《渾北人家》中通過對那個生活在陰影里又在陽光下“已沒有身段”的坐在自家農舍大門外的女人的描述,詩人觸發出了“一個過路女人茫然若失,向你遙望”的感受及體驗。《在小鳥叫聲里金子出現》一詩,從平常的一間草屋,屋頂茅草飛動感覺到“夢一樣升高了樓頂/我有了詩和生活這兩種文本”,並感受到“進入一首詩/離棄的時間越久,靈魂越自由”,這就像身後的村莊“在小鳥不停的叫聲里/漸顯現出金”,對此,詩人沒有大動情感之“干戈”,而是在平靜敘述中讓人們傾聽到自己靈魂深層的悸動。生命與內心的自然律動,與她富有非同尋常的敘事能力,即那種出色而練達的、近乎大面積敘事,構成了林雪個性化的敘事方式:有時敘事與抒情相結合,有時敘事即是抒情。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敘事方式更能讓心靈世界巧妙地獲得某種充沛的釋放。哪怕是某些看似與她無關的東西,在她的心目中也能產生一種自在的感覺,甚至給人一種哲學的意義。毫無疑問,那是一個閱盡愛恨冷暖與人生世相者對於生命的感悟與洞徹。
- 命名、語言及其他
對於林雪而言,“詩人不只是詩歌的祭品,寫詩也從來不僅僅意味著對語言的實踐,不僅為了背叛古典的詩歌布道”,她以為至關重要的是,在寫詩過程中,是否能做到自覺探索於持續而堅持的反抗中的可能,並隨著技藝發展成熟而創造出詩歌新的意義。由是對新發現的命名她常常會通過可以觸摸的鮮明的喻體加以呈現,如生活像“箭鏃”(向四下飛射),陽光(尖銳)是“街道橫陳著1000把刀”,整個山坡的“玉米都是女人”(都懷著孕啊!)。《在一個叫赫圖阿拉的地方》一詩最為典型,詩人通過多重的喻體如:“正在眼前的事物”“一場生活本身”“已經死去很多次又重新復活”“幸福總是可能”“一部國產電影”等等或可感或可思的喻體來為“一個叫赫圖阿拉的地方”命名,一個令人“靜靜地感恩、哭泣”的地方便如此立體而多維地顯現。類似以上這些帶有詩意的命名,在林雪的這部詩集中俯拾皆是。
林雪對文字的驅遣能力的確令人驚嘆,她的詩歌語言充滿著一種自由生長的色素,那是“能使黑暗減輕的真理,和飛翔著的,詩歌的語言”(《我的馬車帶走了哪些詞?》),仿佛是大地上那些旺盛而開放的植物和花朵,搖曳多姿而又絢麗多彩。在詩人的精心駕馭下,如同“這么美妙的鷓鴣的叫聲,無以復加的/幸福。一直叫到生活深處/叫到你我內心和本質”(《我歌唱塵埃里深積的人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詩人把握語言的力度。一方面,她詩中所展現的色彩、氣味、氛圍,常常有一種感性彌真的情感濃度,看似尋常卻別有風致,是真正意義上的返樸歸真。另一方面,對語言的認知和運用達到相當理解和放達的林雪,在題材、詩意對象的探索與變化之中臻達某種難以剝離的美學境界,構成她詩歌語言頗具特色的基本語境和主要風格。
《新的一天正慢慢越過永陵山嶺》這首詩的外部結構相對而言是短促而簡潔的,按理應當產生緊張而急迫的語言效果,但由於詩人把強烈的情緒藏匿於敘述之中,因而獲得的語感卻顯得舒緩而深長,似乎是娓娓道來且又親切自然。而這,恰好與那種特有的“赫圖阿拉情結”相對應,就像《河水安靜而緩慢地寫詩》,這就是詩人心律搏動的曲線。仔細解讀會發現,這首僅21行的短詩,除了“慈悲”“降落”“沉默”“憂傷”等富有深幽色調語詞的使用外,整首詩的聲調在“慢慢地越過”那種不絕如縷的句式中瀰漫,如是便奇蹟般地使長短錯落不一的外部語言結構轉化為舒緩、安靜、和諧的內在語感了。可以說,林雪這部詩集中的大多數詩篇都有這個特點,這同時顯示了她的語言功力和獲得持續的再生、活力和詩意生長的可能。
林雪是“一隻手握住平凡而普通的生存之憂,握住形而下的心靈之碎,另一隻手攀越重巒疊嶂,以期到達人性光芒的山頂”(《大地葵花》代跋)。誠然,詩人的內在意識在某種意義上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反之亦然。畢竟,詩歌(文學)藝術並非是真實世界的傀儡,又純非想像世界的附庸,更多的時候應該是這兩個世界的落差或交媾生髮的“寧馨兒”。林雪深諳其中三昧,認為偉大詩人應無一例外地具有這樣能力:“從日常生活中的平庸出發,到達高尚的精神和理想。這是兩個世界的節奏。”或許,值得林雪引以思考的是另一種“神諭”,即如何從詩歌人本走向詩歌神本,仿如將一片詩意從大地和心底飛升,去接通更為遼闊高遠的茫茫宇宙,去接近一種帶有地域色彩的人神一體的複合視角,力求無限地逼近自身的“元型”,逼近超驗世界,逼近生命極地。如是,可能會獲得某種更大的能量,並進入到另一種新的提升和超越。
作品影響
- 榮譽表彰
2007年,《大地葵花》獲得第五屆遼寧文學獎·詩歌獎;10月25日,該詩集獲得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優秀詩歌獎。
2008年7月4日,該作品被遼寧省作家協會評為遼寧省2007年度優秀文藝作品。
- 研討會
2007年11月13日上午,由遼寧省作家協會、遼寧省新詩學會、《詩潮》雜誌社聯合主辦的魯迅文學獎獲獎詩集《大地葵花》研討會在遼寧省作家協會召開。
作品評價
“林雪這部對故鄉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人民的歌吟詩集,讓我們感受到女詩人詩風變革中的一系列關鍵字:我、熱愛、大地、人民、時間、靈感、命運、生活、死亡、虔誠、謙卑、感知、心靈、無言、驚愕、詩!”(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詩歌獎獲獎作品評語)
出版信息
書名 | 作者 | 出版地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ISBN |
|---|---|---|---|---|---|
大地葵花 | 林雪 | 瀋陽 | 春風文藝出版社 | 2006年10月 | 7-5313-3111-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