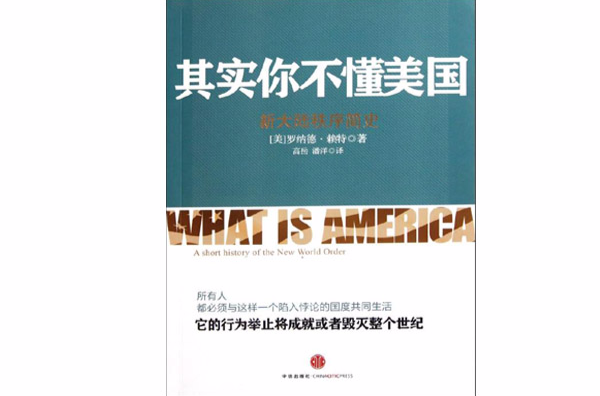《其實你不懂美國:新大陸秩序簡史》是中信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羅納德·賴特。本書向我們展示了新大陸是何創造了現代世界,以及如何威脅現代社會。
基本介紹
- 書名:其實你不懂美國:新大陸秩序簡史
- 作者:[美] 羅納德·賴特
- ISBN:7508629655, 9787508629650
- 頁數:317頁
- 定價:42元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1年12月16日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目錄,精彩書評,精彩書摘,
內容簡介
為何我們關於民主、繁榮、公民權利等偉大成就的危害,往往來自內部?
如賴特所說,由於美國在征服、擴張、和無限邊界等問題上的獨特理念,它也許比我們所知道的美國更為真實。他從那些古老的地方揭開影響社會進步的面紗,宗教極端主義、軍國主義、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以及美國無所不在的“使命感”。
作者簡介
羅納德·賴特是罕有的小說及非小說雙棲作家,從小在英國長大,於劍橋大學受完人類學訓練後,前往加拿大進行深造,就此定居加拿大。
作為人類學家的賴特的第一本小說《科學羅曼史》,榮獲了英國戴維海姆文學獎(David Higham Prize),《紐約時報》年度好書、英國《周日泰晤士報》年度好書、加拿大《環球郵報》年度好書。第二本小說《韓德森的矛》則在這主題上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和模擬。在此同時,賴特的非文學著作《被竊取的大陸》獲選英國《獨立報》和《周日泰晤士報》的年度好書。其著作《失控的進步》更是引起國際震動。
目錄
第一章 新世界秩序
第二章 戰利品、勞動力和土地
第三章 人口稠密的城鎮
第四章 宗教與利益齊頭並進
第五章 白皮膚的野蠻人
第六章 天定命運
第七章 一種帝國
第八章 恐懼之風
第九章 這個世界的最大希望
精彩書評
在最近一次由加拿大廣播電視公司進行的民意測驗中,52%被調查者認為美國是“在世界上起消極作用的國家”。美國的聲望從未如此之低,然而,不管我們喜歡與否,美國就是這樣的一個軍事、經濟強國,她做的事情與每個人都相關。我們所有人,不論是美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必須與這樣一個陷入悖論的國度共同生活:被神權和財閥束縛的民主制,在四百年間一直忙於戰爭的“愛好和平”的國家,一個既持有善意又貪婪、既開放又多疑、既虔誠又崇尚物質、既友好又令人恐懼、既單純又腐化、既尊崇自由主義又帶有壓迫性、既個人主義又墨守成規、既慷慨又善於攫取、既是帝國主義又具有地方觀念、既現代又陳舊的國家。
——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
精彩書摘
人,是在印第安人人口銳減的災難之後的事情,而印第安人的削弱直接促成了白人美國的崛起。在本書中上下文語境清晰的情況下,我將“美洲人”一詞的含義復原為1776年美國革命之前的原始含義。然而,我發現在行文中很難避免使用“印第安人”這個辭彙——尤其是這個辭彙已經牢牢根植於歷史資料、歷史條約以及國會議案的文字記載中。所以,我在此向對“印第安人”這個辭彙感到不快的讀者表示歉意。
任何以第三視角所做的關於美國的描述,都無法避免地被置於25歲的法國貴族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陰影之下。他自稱“信鴿”,其著作《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作為一部外國人對於美國特性和發展前景的研究之作,無人能出其右。 我在本書中也引用了一些托克維爾的個人旅行筆記和採訪,這些筆記和採訪曾經以《美洲之旅》(Journey to America)的名字集結出版。雖然這本書並沒有《論美國的民主》知名,但是其中的內容卻比《論美國的民主》更具揭示性。
1831年-1832年,法國政府資助托克維爾考察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監獄系統。他藉此遊歷了美國全境,但是他的興趣並沒有僅僅局限於這項任務。他讚揚了在這片新大陸上展現出的現代的“改革思想以及嚴懲罪犯的原則”,但是同時他也補充道:“我在這裡看到了地牢……這讓人想起野蠻殘忍的中世紀。”今天,托克維爾看到的景象或許仍然在關塔那摩監獄(Guantánamo)、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或者是一些美國國內的監獄裡再現。(譯註:關塔那摩監獄位於古巴東南端關塔那摩省。北緯19.54度,西經75.9度。灣中設有一座屬於美國海軍的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占地116平方千米。近年來由於該基地被美軍用於拘留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等地區的戰事中捕獲的戰犯,而再度受到媒體與民間的關注。阿布格萊布監獄始建於20世紀 70 年代,當年薩達姆政府在這所監獄內肆意折磨和殺害無辜平民,這裡在薩達姆統治時期曾是“死亡與摧殘”的象徵。美軍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後,在此大量關押、審訊和虐待囚犯。 2004 年 4 月,美國 CBS 電視台公布了美軍虐囚的首批照片後,爆發了舉世震驚的美軍虐囚醜聞,布希總統被迫為美國軍人的非法野蠻行為向伊拉克人民公開道歉。2004 年 5 月開始審判第一名被控犯下虐囚罪行的美軍士兵。現在已有 11 名美軍官兵因虐囚案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最嚴厲的處罰是美軍士兵格拉納被判處 10 年監禁。阿布格萊布監獄於 2006 年 7 月關閉。)
雖然托克維爾不愧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家,並且能夠根據所蒐集的資料和數據對未來做出創見性的判斷和預測,但是他並不是一位歷史學家。我在此提及這一點,並非要揪住托克維爾的某些錯誤不放,而是要駁倒這些錯誤,還原歷史的真相。他這樣寫道:“因為美國沒有鄰居,所以他們不存在大型戰爭的可能性,或者是財政危機、他國侵犯,甚至是可怕的征服的威脅;……沒有什麼災禍可以讓他們感到恐懼——實際上這對於共和國來說比上述所有邪惡(贏取軍事上的榮光)全部加起來還要糟糕……沒有什麼比巨大的帝國更能對個人的自由和福利造成威脅了。”
沒有鄰居?當然,托克維爾在這裡指的是美國沒有白人的鄰居。在托克維爾的時代,以他的階層角度出發,只有白人才算得上是全球事件的真正角色。由於他並未將美洲的原住民,或者稱“印第安人”看作美國歷史的主要參與者,因此托克維爾也就沒有意識到美國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帝國——全副武裝、充滿侵略性,在崇尚武力的安德魯·傑克遜將軍(General Andrew Jackson)的領導下,就在托克維爾的眼皮底下展開了殘暴的擴張行動。傑克遜總統是那個時代的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被蒙蔽的大眾愛戴他,有見解的知識界憎恨他,而托克維爾本人則忽視他。托克維爾對傑克遜總統的評價“是一個非常平庸的人”。年輕的法國人是一位謹慎的樂觀主義者,他深信讓這位粗魯殘暴的將軍擔任總統職位,並非美國模式的常態,純屬錯誤的意外。因此,托克維爾並未深入研究傑克遜其人其事,對於傑克遜在擔任將軍職務時期屠殺印第安人,進行我們今日稱為“種族清洗”的駭人暴行——19世紀30年代的印第安大遷徙——也未加重視。
托克維爾對於過往歷史的忽略與他仍處於年輕氣盛的時期有一定的關係。如同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一樣,托克維爾也將眼光投向了未來。事實上,美國脫離英國成立獨立的合眾國,不過發生在托克維爾來訪前五十年。但是托克維爾對於美國殖民地時期歷史的描述和評論,僅僅參照了一些新英格蘭地區早期清教徒移民所記錄的“歷史”和後來在這些記載之上撰寫而成的書籍,同時他與之交談採訪的美國人也閱讀這些書籍。與地處阿爾斯特(Ulster)和南非的其他極端新教徒類似,來到北美洲的清教徒將自己視為上帝的選民,通過《聖經》的指引,來到了應許之地。托克維爾引用這些描述的時候往往取其字面含義,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描述不過是為了模糊北美洲原住民的真實狀況,以及原住民與白人之間的關係而進行的宗教和種族宣傳。
因此,托克維爾並沒有理解“邊疆”(frontier)這一關鍵性概念——自從17世紀初便開始的種族戰爭和文化衝突在地域上的不斷西進——在塑造這個移民國家過程中的重要性;直到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發現並揭示了美國歷史上的邊疆理論。特納認為邊疆拓殖“扯開了文明的外衣”,是理解美國文化方式如何漂離了歐洲主流文化的關鍵。1893年,特納在芝加哥舉辦的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宣讀了著名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曠野征服了殖民者。不久以後,他就開始種植印第安人的玉米,用尖銳的爬犁耕種莊稼;他大聲宣戰,並戰勝了傳統的印第安方式。”
雖然托克維爾不具備特納那樣敏銳的洞察力,但是他對白人如何在新大陸站穩腳跟並發展出一片天地的過程也提出了疑問:新移民如何做到征服了內陸地區,同時又沒有喪失自己的好名聲呢?托克維爾辛辣地指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的西班牙人沒能完全消滅當地土著,或者說沒能抹去土著的權利。然而美國人顯然“完成了這雙重目的……在世人心中,他們的所作所為又並未違反任何一條道德原則。”
如同當前社會一樣,當年這套狡猾的詭計以崇高的理想和希望作為掩護,實則隱藏著罪惡的真相。美國是未來之國,赦免了自己在過往歷史中犯下的罪:這是一片良好意願鋪就的樂土。正如劉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在最近發表於《哈潑斯》的《恐怖警告》(Terror Alerts)中諷刺的那樣:“我們是好人,從歷史的監獄中釋放出來,因此可以自由想像屬於我們的時代永遠不會結束。”
任何以第三視角所做的關於美國的描述,都無法避免地被置於25歲的法國貴族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陰影之下。他自稱“信鴿”,其著作《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作為一部外國人對於美國特性和發展前景的研究之作,無人能出其右。 我在本書中也引用了一些托克維爾的個人旅行筆記和採訪,這些筆記和採訪曾經以《美洲之旅》(Journey to America)的名字集結出版。雖然這本書並沒有《論美國的民主》知名,但是其中的內容卻比《論美國的民主》更具揭示性。
1831年-1832年,法國政府資助托克維爾考察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的監獄系統。他藉此遊歷了美國全境,但是他的興趣並沒有僅僅局限於這項任務。他讚揚了在這片新大陸上展現出的現代的“改革思想以及嚴懲罪犯的原則”,但是同時他也補充道:“我在這裡看到了地牢……這讓人想起野蠻殘忍的中世紀。”今天,托克維爾看到的景象或許仍然在關塔那摩監獄(Guantánamo)、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或者是一些美國國內的監獄裡再現。(譯註:關塔那摩監獄位於古巴東南端關塔那摩省。北緯19.54度,西經75.9度。灣中設有一座屬於美國海軍的關塔那摩灣海軍基地,占地116平方千米。近年來由於該基地被美軍用於拘留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等地區的戰事中捕獲的戰犯,而再度受到媒體與民間的關注。阿布格萊布監獄始建於20世紀 70 年代,當年薩達姆政府在這所監獄內肆意折磨和殺害無辜平民,這裡在薩達姆統治時期曾是“死亡與摧殘”的象徵。美軍入侵和占領伊拉克後,在此大量關押、審訊和虐待囚犯。 2004 年 4 月,美國 CBS 電視台公布了美軍虐囚的首批照片後,爆發了舉世震驚的美軍虐囚醜聞,布希總統被迫為美國軍人的非法野蠻行為向伊拉克人民公開道歉。2004 年 5 月開始審判第一名被控犯下虐囚罪行的美軍士兵。現在已有 11 名美軍官兵因虐囚案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最嚴厲的處罰是美軍士兵格拉納被判處 10 年監禁。阿布格萊布監獄於 2006 年 7 月關閉。)
雖然托克維爾不愧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家,並且能夠根據所蒐集的資料和數據對未來做出創見性的判斷和預測,但是他並不是一位歷史學家。我在此提及這一點,並非要揪住托克維爾的某些錯誤不放,而是要駁倒這些錯誤,還原歷史的真相。他這樣寫道:“因為美國沒有鄰居,所以他們不存在大型戰爭的可能性,或者是財政危機、他國侵犯,甚至是可怕的征服的威脅;……沒有什麼災禍可以讓他們感到恐懼——實際上這對於共和國來說比上述所有邪惡(贏取軍事上的榮光)全部加起來還要糟糕……沒有什麼比巨大的帝國更能對個人的自由和福利造成威脅了。”
沒有鄰居?當然,托克維爾在這裡指的是美國沒有白人的鄰居。在托克維爾的時代,以他的階層角度出發,只有白人才算得上是全球事件的真正角色。由於他並未將美洲的原住民,或者稱“印第安人”看作美國歷史的主要參與者,因此托克維爾也就沒有意識到美國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帝國——全副武裝、充滿侵略性,在崇尚武力的安德魯·傑克遜將軍(General Andrew Jackson)的領導下,就在托克維爾的眼皮底下展開了殘暴的擴張行動。傑克遜總統是那個時代的喬治·W·布希(George W. Bush),被蒙蔽的大眾愛戴他,有見解的知識界憎恨他,而托克維爾本人則忽視他。托克維爾對傑克遜總統的評價“是一個非常平庸的人”。年輕的法國人是一位謹慎的樂觀主義者,他深信讓這位粗魯殘暴的將軍擔任總統職位,並非美國模式的常態,純屬錯誤的意外。因此,托克維爾並未深入研究傑克遜其人其事,對於傑克遜在擔任將軍職務時期屠殺印第安人,進行我們今日稱為“種族清洗”的駭人暴行——19世紀30年代的印第安大遷徙——也未加重視。
托克維爾對於過往歷史的忽略與他仍處於年輕氣盛的時期有一定的關係。如同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一樣,托克維爾也將眼光投向了未來。事實上,美國脫離英國成立獨立的合眾國,不過發生在托克維爾來訪前五十年。但是托克維爾對於美國殖民地時期歷史的描述和評論,僅僅參照了一些新英格蘭地區早期清教徒移民所記錄的“歷史”和後來在這些記載之上撰寫而成的書籍,同時他與之交談採訪的美國人也閱讀這些書籍。與地處阿爾斯特(Ulster)和南非的其他極端新教徒類似,來到北美洲的清教徒將自己視為上帝的選民,通過《聖經》的指引,來到了應許之地。托克維爾引用這些描述的時候往往取其字面含義,並沒有意識到這些描述不過是為了模糊北美洲原住民的真實狀況,以及原住民與白人之間的關係而進行的宗教和種族宣傳。
因此,托克維爾並沒有理解“邊疆”(frontier)這一關鍵性概念——自從17世紀初便開始的種族戰爭和文化衝突在地域上的不斷西進——在塑造這個移民國家過程中的重要性;直到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發現並揭示了美國歷史上的邊疆理論。特納認為邊疆拓殖“扯開了文明的外衣”,是理解美國文化方式如何漂離了歐洲主流文化的關鍵。1893年,特納在芝加哥舉辦的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宣讀了著名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曠野征服了殖民者。不久以後,他就開始種植印第安人的玉米,用尖銳的爬犁耕種莊稼;他大聲宣戰,並戰勝了傳統的印第安方式。”
雖然托克維爾不具備特納那樣敏銳的洞察力,但是他對白人如何在新大陸站穩腳跟並發展出一片天地的過程也提出了疑問:新移民如何做到征服了內陸地區,同時又沒有喪失自己的好名聲呢?托克維爾辛辣地指出,征服墨西哥和秘魯的西班牙人沒能完全消滅當地土著,或者說沒能抹去土著的權利。然而美國人顯然“完成了這雙重目的……在世人心中,他們的所作所為又並未違反任何一條道德原則。”
如同當前社會一樣,當年這套狡猾的詭計以崇高的理想和希望作為掩護,實則隱藏著罪惡的真相。美國是未來之國,赦免了自己在過往歷史中犯下的罪:這是一片良好意願鋪就的樂土。正如劉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在最近發表於《哈潑斯》的《恐怖警告》(Terror Alerts)中諷刺的那樣:“我們是好人,從歷史的監獄中釋放出來,因此可以自由想像屬於我們的時代永遠不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