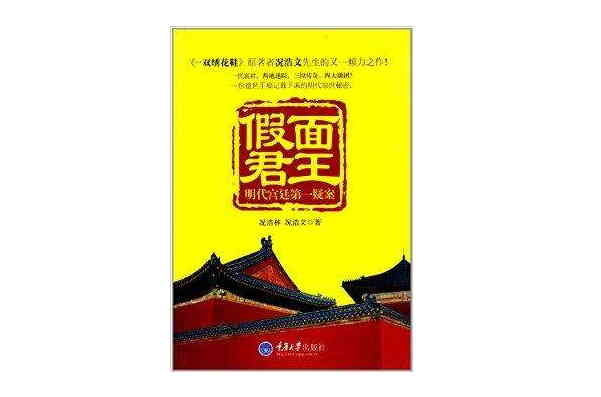《假面君王:明代宮廷第一疑案》是由重慶知名作家況浩文與其妹妹況浩林合作完成的一部歷史題材小說。“文化大革命”初期大破“四舊”,貴州安順地區一座千年古剎遭到瘋狂破壞。一個因被“陪斗”而去該寺的“弼馬溫”級的“走資派”,偶然在一尊地藏王菩薩身首異處的佛像胸腔內,發現了一卷黃緞包紮、保存完好的陳年手稿。它記述了中國明代歷史上一件十分傳奇的宮廷疑案和一場極為聰慧的政治“騙局”。遂行這一“騙局”的孿生兄弟,既經歷了血雨腥風的刀劍搏殺,也曾有啼笑皆非的難逃艷福,最終雙雙獲得成功。“騙局”的實施,不僅改變了一代哀君幾近死亡的命運,促進了蒙漢民族團結;還使這對孿生兄弟分別獲得了純真的愛情,巨額的財富,稀世的名駒。通覽《假面君王:明代宮廷第一疑案》,也許您能了解中國明代歷史上四大疑團的謎底,即:建文皇帝失蹤之謎,鄭和七下西洋之謎,朱棣四征漠北之謎,傳國玉璽下落之謎。還能解讀五百多年來讓中國文人困惑不解、神秘難懂的“紅崖天書”。
基本介紹
- 書名:假面君王:明代宮廷第一疑案
- 出版社:重慶大學出版社
- 頁數:269頁
- 開本:32
- 品牌:重慶大學出版社
- 作者:況浩文 況浩林
-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62470294, 978756247029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假面君王:明代宮廷第一疑案》是《一雙繡花鞋》原著者況浩文先生的又一傾力之作!一代哀君,兩地迷蹤,三段傳奇,四大疑團!一份遺世手稿記載下來的明代驚世秘密。
作者簡介
況浩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解放後在西南公安部五處及西南軍區公安部隊司令部偵察處工作。轉業到重慶工業部門,“文革”中長期遭受迫害,平反後相繼擔任重慶市外貿局長、重慶市外經委主任、重慶長發集團公司董事長等職務。業餘時問斷續寫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南嶺之鷹》《一雙繡花鞋》《企業家》《寶笈疑雲》《麒麟花》等中、長篇小說及電影文學劇本。《一雙繡花鞋》在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風靡海內外。
況浩林,女,原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師。寫作出版有《簡明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少數民族經濟史稿》等學術作品。
況浩林,女,原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師。寫作出版有《簡明中國近代經濟史》《中國近代少數民族經濟史稿》等學術作品。
圖書目錄
前言第三神殿佛肚藏書
第一章鬼門餘生秦淮夜渡
第二章全廬涉險密謀解圍
第三章風雲突變汗血忠魂
第四章八閩驚艷神龍點睛
第五章臥底中原諜影古觀
第六章泉州設疑閹奴吞鉤
第七章血戰倭船情殉南洋
第八章亡命天涯魂系渝州
第九章榆關定計虎穴保胎
第十章弄鬼三皇火焚祭壇
第十一章大漠疑冢拱璧歸漢
第十二章午夜魅影魔窟除妖
第十三章九重驚夢荒島餘生
第十四章溫陵風雨血洗倭穴
第十五章百代存疑千年遺恨
第一章鬼門餘生秦淮夜渡
第二章全廬涉險密謀解圍
第三章風雲突變汗血忠魂
第四章八閩驚艷神龍點睛
第五章臥底中原諜影古觀
第六章泉州設疑閹奴吞鉤
第七章血戰倭船情殉南洋
第八章亡命天涯魂系渝州
第九章榆關定計虎穴保胎
第十章弄鬼三皇火焚祭壇
第十一章大漠疑冢拱璧歸漢
第十二章午夜魅影魔窟除妖
第十三章九重驚夢荒島餘生
第十四章溫陵風雨血洗倭穴
第十五章百代存疑千年遺恨
序言
動盪不安的一九六七年。
夏秋之間,為了躲避重慶急劇升級的武鬥,我們一家逃到了當時相對平靜的貴陽,住在三妹家裡。我沒事成天逛街,一個下午在冷冷清清的黔靈山前,偶然碰上了二十多年沒有見面的老同學徐亦瑞,國中、高中我們都是同班同桌,算得上莫逆之交,相逢讓大家都很高興,便一起溜進了遊人稀少的黔靈公園,邊逛邊聊別後情況。我當時因為寫了倒霉的《一雙繡花鞋》被劃成“預備敵人”,前途吉凶難料。徐亦瑞的境遇也不比我好,他在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貴州一個縣的文化館,辛苦工作十幾年才混了個副館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他這號“弼馬溫”級的當權派也被打倒“奪權”。因為官卑職小,除偶爾為了湊數把他拉去陪斗之外,平日裡就被監督著為造反派刷大標語,抄大字報,身份逐漸上升為“候補人民”。這次徐亦瑞就是跟隨造反派頭子來到省城,有選擇地抄寫滿街的“北京來電”,然後寄回縣裡轉抄,用以壯大本派聲勢、嚇唬對立派。
“知道嗎,為什麼永樂皇帝四征漠北、三寶太監又七下西洋?”徐亦瑞瞪大了他那雙高度近視的眼睛,緊盯著我。
猝不及想,無言以對,我發覺這位老同學還像兒時一樣,思維是跳躍式的。我們正談到山城武鬥的慘烈狀況,他卻突然提出了十五世紀明代永樂年間的問題。
徐亦瑞從我驚訝的表情中得到滿足,他扶了扶自己那副像玻璃瓶底般厚的眼鏡,又問:“聽說過貴州安順關索嶺上的‘紅崖天書’嗎?知道它和明代宮廷第一疑案——建文皇帝失蹤之謎的關係嗎?”
我的好奇心真正被調動起來了,便叫著他在學校時的諢名說:“瞎猴兒,你就給我來個竹筒倒豆子,別老在這裡賣關子。”
徐亦瑞“吧嗒、吧嗒”地狠狠吸了幾口我從重慶帶去的八分錢一包的“勁松牌”香菸,衝著我嘻嘻一笑:“行呀,不過今夜的晚飯得由你請客。”
我們在公園內的弘福寺側邊找了一條石礅坐下,徐亦瑞這才細細講了開來。
“今年春末,我和縣委宣傳系統的‘走資派’們,被一大群造反派押去深山裡的雲峰禪寺,在‘破四舊’的現場上挨斗。造反派的‘革命行動’從下午一直持續到深夜,在這座唐代修建、明初重修的廟宇里,佛像全被拉下神壇砸爛,匾額楹聯也都被摘下焚燒。大雄寶殿前的壩子上燃起一堆熊熊大火,無數的佛教典籍、神幔、幡引都被投進火里燒。造反派的男男女女圍著這堆大火手舞足蹈、聲嘶力竭地唱著‘造反有理’,那情景活像原始部落在燒吃俘虜人肉以前的瘋狂模樣。我這個‘黑爪牙’只被陪鬥了一會兒,就被安排去後面第三重神殿掃集經典書籍,裝來焚燒。我只好背著背篼,拿著掃帚,打著火把,向著黑咕隆咚的地藏王菩薩神殿里走去。
“我媽生前信佛,每月逢二、六、九都要吃齋念經。我小時候經常跟媽上廟禮佛,因此對菩薩一直懷著幾分崇敬。看見造反派把一座千年古剎糟蹋得一塌糊塗,心裡實在不是滋味。我慢慢走著,剛跨進鬼氣森森的地藏王殿,忽然,腳下碰著一個圓鼓鼓的東西倏地往旁邊一滾,嚇了我一大跳。支著火把一看,卻是地藏王菩薩那顆莊嚴的佛頭——斷離頸項滾落在地。我再仔細看看,它的法身也撲倒在地,左手托著的紅色如意寶珠已被砸得粉碎,右手持的錫杖也斷成了幾節。我心裡好生不忍,一時衝動,放下掃帚與火把,用力將撲倒的佛像翻過身來,準備將佛頭正面安裝在它的頸項上面,還地藏王菩薩佛像一個全身。當我剛剛把佛像翻轉過來時……”說到這裡,徐亦瑞壓低了嗓音,好像在訴說一個重大機密而又擔心泄漏似的。“我突然發現摔開裂口的地藏王胸腔內,藏著一包亮黃黃的東西。這使我大為驚訝,便把這包東西從佛像的胸腔內硬扒了出來,支著火把一看,卻是一個用明黃綢緞包裹、再用黃色絲絛緊緊拴住的筒卷。”
“快講呀,什麼東西?莫非我還會當‘汪精衛’去告密!”
徐亦瑞又要過一支香菸,再“吧嗒、吧嗒”猛吸幾口提了提神方才說道:“我三把兩把扯開絲絛,卻見黃緞上面用工楷寫著:
翰林院編修 臣程濟謹遵
聖命恭錄後封存
皇明丁亥年仲春吉日
包裹裡面是一大卷扎得十分緊實的文稿。我憑直覺知道,這卷在五百多年前寫成的文稿,不管內容如何,都是珍貴文物,丟進造反派的火堆里燒掉實在可惜,應該想法收藏起來。但咋藏呢?揣進自己懷裡吧,文卷太大,鼓鼓囊囊好大一坨,明眼人一看就會穿幫。我想先在廟裡找個地方藏著,以後再找機會來取。於是又用黃緞包好文卷,匆匆忙忙走到殿後,在一棵大樹下刨開野草將它藏了進去,但野草枯淺,根本遮不住文卷。我也管不了許多,又馬上跑進殿內,將佛頭合上佛身,然後掃集碎落滿地的爛匾額、破佛幔,裝一背篼送去火場。”
“當我重新紮了一支火把拿去廚房浸油時,突然看見路邊一堆東西,猛地想到一個危險而又新奇的主意。原來縣裡造反派‘奪權’後,給‘走資派’每人做了一頂鐵絲骨架的絹面高帽子,發給本人保管,每次挨斗時要求自動戴帽到場,損害者還要挨揍。我‘沾光’也有一頂,帽子上面在紅筆勾抹下寫了六個黑字‘小爬蟲徐亦瑞’。這次要到廟裡挨斗,我當然就自動戴帽到場。這時所有高帽子都集中放在大雄寶殿右側的石條礅上,我路過時順手拿起自己那頂,飛快向地藏王殿跑去,從枯草里找出那捲文稿,實實貼貼塞進高帽子內,再扯下一條經幡飄帶,牢牢將它在帽內鐵絲架上栓緊。我又才拿著火把東尋西找,在神台後面找到一個書櫥,裡面裝滿了經卷,什麼《地藏本願經》《蓮華三昧經》等,我心裡暗暗叫了一聲‘菩薩,得罪了!’便一背篼將這些經典統統背走,送到前面火場,算是交差。
“月上中天之時,造反派押著我們,唱著‘集中火力打黑幫’的歌曲班師回城。我生怕高帽子裡面的那捲文稿掉出露餡兒,便雙手將高帽子捧在胸前走路。回城的路剛走一半,忽然,‘押解’我們的造反派頭子大叫一聲:‘隊伍停下!’行進中的一二百人猛然停了下來,發愣地望著他。造反頭兒是個粘上毛比猴還精的人物,他順手奪過一支火把,忽地照到我的面前,‘大家看,徐亦瑞十分愛惜這頂高帽子嘛!’馬上,百十雙眼光刷地投向我的身上。我心裡‘咯噔’一響,全身冷汗突冒,‘糟糕,露餡兒了!’這時,造反頭兒卻又將火把支向隊伍中的其他‘走資派’,只見他們有的將高帽子夾在腋下,有的倒提在手上,還有人橫掛在肩上,總之,表現出的都是敵視與不屑。只有我一個人,活像舊社會出喪時孝子端靈牌那樣,恭恭敬敬地將高帽子雙手捧在胸前。‘完了,準備挨揍,坐牢吧!’我正這樣想時,造反頭兒發問了:‘徐亦瑞,你為什麼如此愛惜這頂高帽子?說,大聲說!’我一時福至心靈,急中生智答道:‘這是革命戰士用來幫助我們改造思想、觸及靈魂的工具,當然應該愛惜。’看來,那造反派頭子聽了這話十分受用,便大聲武氣吼叫道:‘你們這些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在這一點上都應該向徐亦瑞學習,他算有點進步了。’這時,我聽到身後的縣委宣傳部長輕輕罵了一句:‘軟骨頭,馬屁精!’接著又對著我的小腿狠狠踹了一腳,我只有苦笑。當晚,打著火把走了十多里山路,我總算平安地把那捲裝在高帽子內的文稿捧回了宿舍,撬開護牆的木板,連夜藏了起來。”
徐亦瑞講到此時,天色已近黃昏,我挽著他到公園附近一個小食店,買了半斤高價包穀酒,就著一盆鹽煮素瓜豆,痛快地吃喝了起來。最後每人還吃了兩碗光面,酒醉面飽才走出小店,沿著大街邊逛邊聊。我首先提出了一個心中存疑已久的問題:“那捲文稿如是寫於明代永樂年間,經歷五百多年歲月,怎么還沒腐朽?”
“這——你就外行了嘛!常言道‘紙壽千年’,它藏在地藏王菩薩的胸腔里,不受風雨侵蝕,又與空氣隔絕,當然不容易壞了啊。”徐亦瑞又點燃一支我遞給他的“勁松”香菸,清清嗓子,接著講了開來。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用被單擋上窗戶,這才取出那捲《程濟遺稿》細細研讀。文稿字跡工整,寫的雖是古體散文,但行文十分流暢,全無生僻晦澀詞句,讀來毫不費事。喔!我還忘了問你,知道程濟是什麼人嗎?”
我老實地搖了搖頭。
“估計你也不知道,他原是明初四川岳池縣一名教諭,後來到南京考進翰林院做了編修。建文帝自宮中出逃以後他一直隨侍左右,是朱允炆一個大大的忠臣。”
“慢著,你說建文帝朱允炆在他叔父朱棣——也就是後來的永樂皇帝——攻破南京之時,沒有投入宮中大火自焚而死,而是出逃在外?”
“是的,《程濟遺稿》對此作了明白無誤的翔實記述。他還寫了永樂皇帝為什麼會四次親征漠北,又命鄭和幾下西洋,從而使建文帝一行能平安地流亡於外,直至終老。”
我聽了大感興趣,非要徐亦瑞系統講述不可。他的記憶力也真好,又是學歷史的,便從建文君臣的倉皇出逃一直講到貴州安順的“紅崖天書”;從刀光劍影的大漠征戰一直講到怒濤翻湧的海上搏殺。他一支接一支抽著我的“勁松”香菸,一口氣講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將《程濟遺稿》的梗概講完。我真佩服他對明初歷史的熟悉和地域知識的廣博。
聽完以後,我十分感慨地說:“一部明史,太多問號。”
“明史背後,又太多驚嘆號!”
天色早已斷黑,徐亦瑞要回招待所了。我們乍相逢,又別離,彼此都很悵惘,長久黯然無語。快到招待所時,徐亦瑞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說:“老同學,我們現在的境遇都很不好,天涯淪落,前路茫茫,還不知道這輩子能不能再見?你的文字功底遠比我強,將來如有機會,我們合作,以《程濟遺稿》為素材,寫它一部長篇小說。這裡面一定要把‘紅崖天書’寫上,因為它牽涉到中國歷史上一個百代之謎,那就是歷代皇帝都視為命根子的傳國玉璽的下落!” “什——么!?”我驚訝得半天合不攏嘴,“你說的是那方用‘和氏璧’雕成的金鑲玉印?”
“是的。”徐亦瑞平靜地點了點頭。
“野史上說,它被元順帝擄回大漠以後,從此就失蹤了嘛。”
“不,不!《程濟遺稿》上清楚地寫著,這方傳國玉璽被一位中州俠士歷經乾難萬險從漠北奪回,送到當時匿居在貴州的建文帝手中。但朱允炆此時萬念俱灰,再無召集勤王兵馬以圖復國的大志,反而認為這方玉璽是‘不祥之物’,硬要將它扔下山澗砸碎。幸虧程濟手快,搶了過來,才保全了這件國寶。”
“後來它的下落呢?”
“遺稿中沒有明寫,但有暗示。程濟最後在文稿上記錄了朱允炆四句類似偈語的竹枝詞,第一句就是‘白雲深處隱不祥’。建文帝不是說傳國玉璽是‘不祥之物’嗎!而在川黔一帶,‘深’與‘僧’同一讀音,這句竹枝詞就可讀作‘白雲僧處隱不祥’。僧的住處能是什麼?廟唄!偏偏與雲峰禪寺相距不遠的長順縣,又有一座白雲山。如果那山上有和尚廟,可不就是‘白雲僧處’,正好去找那‘不祥之物’嘛!”
我聽了覺得有點牽強,但他越講越來勁:“據說離白雲山不遠還有一座高峰山,上有高峰寺,廟對面的石壁上鐫刻有‘西來面壁’四個大字,傳說是建文帝的手筆。‘西’與‘璽’、‘壁’與‘璧’都是諧音,這是不是對傳國玉璽下落的又一暗示呢?”這時,我們快要走到他住的那家寒磣的招待所了,徐亦瑞不要我進去,“造反派的勤務員和我住在一起,見我接觸生人,總要盤問半天。老夥計,我們就在這裡分手吧,為了以後的合作,彼此都要保重。”說完他就轉身,我一直目送徐亦瑞那佝僂瘦小的身影消失在黑洞洞的招待所門裡。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這位老同學。“文化大革命”過去後的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幾次去信探問,都被退回。後來又托貴陽的三妹專程到徐亦瑞工作過的那個縣文化館打探,才確實知道,原來他早就患有嚴重的肺結核,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又被反覆折磨,終於口噴鮮血而亡。徐亦瑞至死都是無家無室的“光棍”,遺物無人受領。造反派生怕肺癆病傳染人,便將他的衣籠帳被、書籍文具和著他的遺體一併推進了焚屍爐,燒得乾乾淨淨,未留半點東西。
這個訊息使我的心情長期處於憤懣之中,暗自決定要將他轉述過的《程濟遺稿》整理加工成書,以祭奠這位老同學的在天之靈。但那些年我的工作實在太忙,只得找我在民族大學執教的妹妹況浩林,向她詳細轉述了《程濟遺稿》的內容,希望她能動筆。我妹妹聽了也感興趣,在她講授民族經濟學的同時,擠了幾年業餘時間,對這個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歷史淵源、人文風物進行了翔實的蒐集梳理,比較鑑別,去粗取精,棄蕪存菁,以《程濟遺稿》為重要素材,又極大地豐富了它的內容。我們兄妹合作,重新構思並創作出了這部作品——述說中國歷史上最費解最傳奇的疑案——《假面君王》。
夏秋之間,為了躲避重慶急劇升級的武鬥,我們一家逃到了當時相對平靜的貴陽,住在三妹家裡。我沒事成天逛街,一個下午在冷冷清清的黔靈山前,偶然碰上了二十多年沒有見面的老同學徐亦瑞,國中、高中我們都是同班同桌,算得上莫逆之交,相逢讓大家都很高興,便一起溜進了遊人稀少的黔靈公園,邊逛邊聊別後情況。我當時因為寫了倒霉的《一雙繡花鞋》被劃成“預備敵人”,前途吉凶難料。徐亦瑞的境遇也不比我好,他在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貴州一個縣的文化館,辛苦工作十幾年才混了個副館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他這號“弼馬溫”級的當權派也被打倒“奪權”。因為官卑職小,除偶爾為了湊數把他拉去陪斗之外,平日裡就被監督著為造反派刷大標語,抄大字報,身份逐漸上升為“候補人民”。這次徐亦瑞就是跟隨造反派頭子來到省城,有選擇地抄寫滿街的“北京來電”,然後寄回縣裡轉抄,用以壯大本派聲勢、嚇唬對立派。
“知道嗎,為什麼永樂皇帝四征漠北、三寶太監又七下西洋?”徐亦瑞瞪大了他那雙高度近視的眼睛,緊盯著我。
猝不及想,無言以對,我發覺這位老同學還像兒時一樣,思維是跳躍式的。我們正談到山城武鬥的慘烈狀況,他卻突然提出了十五世紀明代永樂年間的問題。
徐亦瑞從我驚訝的表情中得到滿足,他扶了扶自己那副像玻璃瓶底般厚的眼鏡,又問:“聽說過貴州安順關索嶺上的‘紅崖天書’嗎?知道它和明代宮廷第一疑案——建文皇帝失蹤之謎的關係嗎?”
我的好奇心真正被調動起來了,便叫著他在學校時的諢名說:“瞎猴兒,你就給我來個竹筒倒豆子,別老在這裡賣關子。”
徐亦瑞“吧嗒、吧嗒”地狠狠吸了幾口我從重慶帶去的八分錢一包的“勁松牌”香菸,衝著我嘻嘻一笑:“行呀,不過今夜的晚飯得由你請客。”
我們在公園內的弘福寺側邊找了一條石礅坐下,徐亦瑞這才細細講了開來。
“今年春末,我和縣委宣傳系統的‘走資派’們,被一大群造反派押去深山裡的雲峰禪寺,在‘破四舊’的現場上挨斗。造反派的‘革命行動’從下午一直持續到深夜,在這座唐代修建、明初重修的廟宇里,佛像全被拉下神壇砸爛,匾額楹聯也都被摘下焚燒。大雄寶殿前的壩子上燃起一堆熊熊大火,無數的佛教典籍、神幔、幡引都被投進火里燒。造反派的男男女女圍著這堆大火手舞足蹈、聲嘶力竭地唱著‘造反有理’,那情景活像原始部落在燒吃俘虜人肉以前的瘋狂模樣。我這個‘黑爪牙’只被陪鬥了一會兒,就被安排去後面第三重神殿掃集經典書籍,裝來焚燒。我只好背著背篼,拿著掃帚,打著火把,向著黑咕隆咚的地藏王菩薩神殿里走去。
“我媽生前信佛,每月逢二、六、九都要吃齋念經。我小時候經常跟媽上廟禮佛,因此對菩薩一直懷著幾分崇敬。看見造反派把一座千年古剎糟蹋得一塌糊塗,心裡實在不是滋味。我慢慢走著,剛跨進鬼氣森森的地藏王殿,忽然,腳下碰著一個圓鼓鼓的東西倏地往旁邊一滾,嚇了我一大跳。支著火把一看,卻是地藏王菩薩那顆莊嚴的佛頭——斷離頸項滾落在地。我再仔細看看,它的法身也撲倒在地,左手托著的紅色如意寶珠已被砸得粉碎,右手持的錫杖也斷成了幾節。我心裡好生不忍,一時衝動,放下掃帚與火把,用力將撲倒的佛像翻過身來,準備將佛頭正面安裝在它的頸項上面,還地藏王菩薩佛像一個全身。當我剛剛把佛像翻轉過來時……”說到這裡,徐亦瑞壓低了嗓音,好像在訴說一個重大機密而又擔心泄漏似的。“我突然發現摔開裂口的地藏王胸腔內,藏著一包亮黃黃的東西。這使我大為驚訝,便把這包東西從佛像的胸腔內硬扒了出來,支著火把一看,卻是一個用明黃綢緞包裹、再用黃色絲絛緊緊拴住的筒卷。”
“快講呀,什麼東西?莫非我還會當‘汪精衛’去告密!”
徐亦瑞又要過一支香菸,再“吧嗒、吧嗒”猛吸幾口提了提神方才說道:“我三把兩把扯開絲絛,卻見黃緞上面用工楷寫著:
翰林院編修 臣程濟謹遵
聖命恭錄後封存
皇明丁亥年仲春吉日
包裹裡面是一大卷扎得十分緊實的文稿。我憑直覺知道,這卷在五百多年前寫成的文稿,不管內容如何,都是珍貴文物,丟進造反派的火堆里燒掉實在可惜,應該想法收藏起來。但咋藏呢?揣進自己懷裡吧,文卷太大,鼓鼓囊囊好大一坨,明眼人一看就會穿幫。我想先在廟裡找個地方藏著,以後再找機會來取。於是又用黃緞包好文卷,匆匆忙忙走到殿後,在一棵大樹下刨開野草將它藏了進去,但野草枯淺,根本遮不住文卷。我也管不了許多,又馬上跑進殿內,將佛頭合上佛身,然後掃集碎落滿地的爛匾額、破佛幔,裝一背篼送去火場。”
“當我重新紮了一支火把拿去廚房浸油時,突然看見路邊一堆東西,猛地想到一個危險而又新奇的主意。原來縣裡造反派‘奪權’後,給‘走資派’每人做了一頂鐵絲骨架的絹面高帽子,發給本人保管,每次挨斗時要求自動戴帽到場,損害者還要挨揍。我‘沾光’也有一頂,帽子上面在紅筆勾抹下寫了六個黑字‘小爬蟲徐亦瑞’。這次要到廟裡挨斗,我當然就自動戴帽到場。這時所有高帽子都集中放在大雄寶殿右側的石條礅上,我路過時順手拿起自己那頂,飛快向地藏王殿跑去,從枯草里找出那捲文稿,實實貼貼塞進高帽子內,再扯下一條經幡飄帶,牢牢將它在帽內鐵絲架上栓緊。我又才拿著火把東尋西找,在神台後面找到一個書櫥,裡面裝滿了經卷,什麼《地藏本願經》《蓮華三昧經》等,我心裡暗暗叫了一聲‘菩薩,得罪了!’便一背篼將這些經典統統背走,送到前面火場,算是交差。
“月上中天之時,造反派押著我們,唱著‘集中火力打黑幫’的歌曲班師回城。我生怕高帽子裡面的那捲文稿掉出露餡兒,便雙手將高帽子捧在胸前走路。回城的路剛走一半,忽然,‘押解’我們的造反派頭子大叫一聲:‘隊伍停下!’行進中的一二百人猛然停了下來,發愣地望著他。造反頭兒是個粘上毛比猴還精的人物,他順手奪過一支火把,忽地照到我的面前,‘大家看,徐亦瑞十分愛惜這頂高帽子嘛!’馬上,百十雙眼光刷地投向我的身上。我心裡‘咯噔’一響,全身冷汗突冒,‘糟糕,露餡兒了!’這時,造反頭兒卻又將火把支向隊伍中的其他‘走資派’,只見他們有的將高帽子夾在腋下,有的倒提在手上,還有人橫掛在肩上,總之,表現出的都是敵視與不屑。只有我一個人,活像舊社會出喪時孝子端靈牌那樣,恭恭敬敬地將高帽子雙手捧在胸前。‘完了,準備挨揍,坐牢吧!’我正這樣想時,造反頭兒發問了:‘徐亦瑞,你為什麼如此愛惜這頂高帽子?說,大聲說!’我一時福至心靈,急中生智答道:‘這是革命戰士用來幫助我們改造思想、觸及靈魂的工具,當然應該愛惜。’看來,那造反派頭子聽了這話十分受用,便大聲武氣吼叫道:‘你們這些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在這一點上都應該向徐亦瑞學習,他算有點進步了。’這時,我聽到身後的縣委宣傳部長輕輕罵了一句:‘軟骨頭,馬屁精!’接著又對著我的小腿狠狠踹了一腳,我只有苦笑。當晚,打著火把走了十多里山路,我總算平安地把那捲裝在高帽子內的文稿捧回了宿舍,撬開護牆的木板,連夜藏了起來。”
徐亦瑞講到此時,天色已近黃昏,我挽著他到公園附近一個小食店,買了半斤高價包穀酒,就著一盆鹽煮素瓜豆,痛快地吃喝了起來。最後每人還吃了兩碗光面,酒醉面飽才走出小店,沿著大街邊逛邊聊。我首先提出了一個心中存疑已久的問題:“那捲文稿如是寫於明代永樂年間,經歷五百多年歲月,怎么還沒腐朽?”
“這——你就外行了嘛!常言道‘紙壽千年’,它藏在地藏王菩薩的胸腔里,不受風雨侵蝕,又與空氣隔絕,當然不容易壞了啊。”徐亦瑞又點燃一支我遞給他的“勁松”香菸,清清嗓子,接著講了開來。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用被單擋上窗戶,這才取出那捲《程濟遺稿》細細研讀。文稿字跡工整,寫的雖是古體散文,但行文十分流暢,全無生僻晦澀詞句,讀來毫不費事。喔!我還忘了問你,知道程濟是什麼人嗎?”
我老實地搖了搖頭。
“估計你也不知道,他原是明初四川岳池縣一名教諭,後來到南京考進翰林院做了編修。建文帝自宮中出逃以後他一直隨侍左右,是朱允炆一個大大的忠臣。”
“慢著,你說建文帝朱允炆在他叔父朱棣——也就是後來的永樂皇帝——攻破南京之時,沒有投入宮中大火自焚而死,而是出逃在外?”
“是的,《程濟遺稿》對此作了明白無誤的翔實記述。他還寫了永樂皇帝為什麼會四次親征漠北,又命鄭和幾下西洋,從而使建文帝一行能平安地流亡於外,直至終老。”
我聽了大感興趣,非要徐亦瑞系統講述不可。他的記憶力也真好,又是學歷史的,便從建文君臣的倉皇出逃一直講到貴州安順的“紅崖天書”;從刀光劍影的大漠征戰一直講到怒濤翻湧的海上搏殺。他一支接一支抽著我的“勁松”香菸,一口氣講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將《程濟遺稿》的梗概講完。我真佩服他對明初歷史的熟悉和地域知識的廣博。
聽完以後,我十分感慨地說:“一部明史,太多問號。”
“明史背後,又太多驚嘆號!”
天色早已斷黑,徐亦瑞要回招待所了。我們乍相逢,又別離,彼此都很悵惘,長久黯然無語。快到招待所時,徐亦瑞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說:“老同學,我們現在的境遇都很不好,天涯淪落,前路茫茫,還不知道這輩子能不能再見?你的文字功底遠比我強,將來如有機會,我們合作,以《程濟遺稿》為素材,寫它一部長篇小說。這裡面一定要把‘紅崖天書’寫上,因為它牽涉到中國歷史上一個百代之謎,那就是歷代皇帝都視為命根子的傳國玉璽的下落!” “什——么!?”我驚訝得半天合不攏嘴,“你說的是那方用‘和氏璧’雕成的金鑲玉印?”
“是的。”徐亦瑞平靜地點了點頭。
“野史上說,它被元順帝擄回大漠以後,從此就失蹤了嘛。”
“不,不!《程濟遺稿》上清楚地寫著,這方傳國玉璽被一位中州俠士歷經乾難萬險從漠北奪回,送到當時匿居在貴州的建文帝手中。但朱允炆此時萬念俱灰,再無召集勤王兵馬以圖復國的大志,反而認為這方玉璽是‘不祥之物’,硬要將它扔下山澗砸碎。幸虧程濟手快,搶了過來,才保全了這件國寶。”
“後來它的下落呢?”
“遺稿中沒有明寫,但有暗示。程濟最後在文稿上記錄了朱允炆四句類似偈語的竹枝詞,第一句就是‘白雲深處隱不祥’。建文帝不是說傳國玉璽是‘不祥之物’嗎!而在川黔一帶,‘深’與‘僧’同一讀音,這句竹枝詞就可讀作‘白雲僧處隱不祥’。僧的住處能是什麼?廟唄!偏偏與雲峰禪寺相距不遠的長順縣,又有一座白雲山。如果那山上有和尚廟,可不就是‘白雲僧處’,正好去找那‘不祥之物’嘛!”
我聽了覺得有點牽強,但他越講越來勁:“據說離白雲山不遠還有一座高峰山,上有高峰寺,廟對面的石壁上鐫刻有‘西來面壁’四個大字,傳說是建文帝的手筆。‘西’與‘璽’、‘壁’與‘璧’都是諧音,這是不是對傳國玉璽下落的又一暗示呢?”這時,我們快要走到他住的那家寒磣的招待所了,徐亦瑞不要我進去,“造反派的勤務員和我住在一起,見我接觸生人,總要盤問半天。老夥計,我們就在這裡分手吧,為了以後的合作,彼此都要保重。”說完他就轉身,我一直目送徐亦瑞那佝僂瘦小的身影消失在黑洞洞的招待所門裡。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這位老同學。“文化大革命”過去後的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幾次去信探問,都被退回。後來又托貴陽的三妹專程到徐亦瑞工作過的那個縣文化館打探,才確實知道,原來他早就患有嚴重的肺結核,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又被反覆折磨,終於口噴鮮血而亡。徐亦瑞至死都是無家無室的“光棍”,遺物無人受領。造反派生怕肺癆病傳染人,便將他的衣籠帳被、書籍文具和著他的遺體一併推進了焚屍爐,燒得乾乾淨淨,未留半點東西。
這個訊息使我的心情長期處於憤懣之中,暗自決定要將他轉述過的《程濟遺稿》整理加工成書,以祭奠這位老同學的在天之靈。但那些年我的工作實在太忙,只得找我在民族大學執教的妹妹況浩林,向她詳細轉述了《程濟遺稿》的內容,希望她能動筆。我妹妹聽了也感興趣,在她講授民族經濟學的同時,擠了幾年業餘時間,對這個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歷史淵源、人文風物進行了翔實的蒐集梳理,比較鑑別,去粗取精,棄蕪存菁,以《程濟遺稿》為重要素材,又極大地豐富了它的內容。我們兄妹合作,重新構思並創作出了這部作品——述說中國歷史上最費解最傳奇的疑案——《假面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