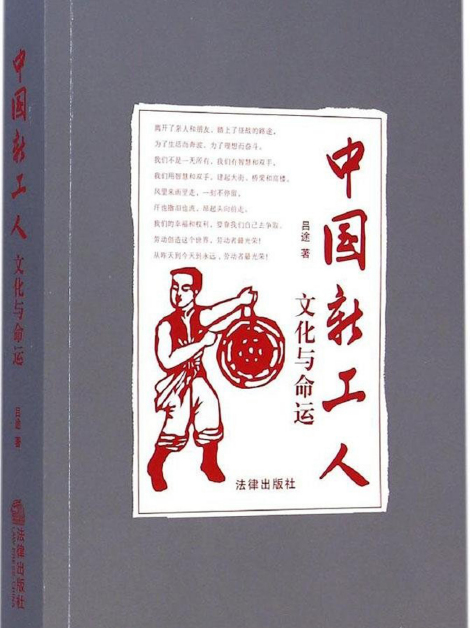票子
從1998年到2015年,王佳的17年幾乎都在東莞度過。
王佳老家在貴州遵義的農村。國中一畢業,她就瞞著家人,和5個同學一起來東莞打工,一直在東莞各個區鎮間輾轉。
“剛開始什麼都不懂,每個月拿250元就很高興了。”剛到東莞的王佳沒有經驗和學歷,等待她的只有低回報的體力活。從1998年到2003年,王佳先後在印刷廠、塑膠廠、電子廠工作過,月工資也從最初的250元慢慢升到1500元。
2003年,她用打工攢下的錢遠赴黑龍江學日語,之後又回到了東莞。“因為我對東莞最熟悉,找工作也不再局限於體力活。”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現在,她當上了車間小組長,月工資3500元,扣掉住房公積金和社保之後,還能剩下約3200元。
王佳的收入沒有“拖後腿”。據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今年2月發布數據,外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離開老家河南、到江蘇打工的 張占波,則在平均線上下“掙扎”。
這個生於1983年、曾在礦山拿3000元月薪的青年,現在在蘇州的電器廠拿1900元月薪。他租的房間約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覺一個月存上200元就不錯了,壓力太大了。”
“相對於這樣的收入水平,80後和90後的打工者的消費欲望,是非常高的。”長期研究打工者群體的NGO“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志願者、《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作者呂途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她印象最深的是張占波的夢想:“別人開寶馬,我們也可以努力有錢去開寶馬。我說不上來怎么樣才能掙到錢開寶馬,但是我覺得有可能。”
“他不吃不喝幾十年,也不一定能買上寶馬車。為什麼一份更高的工資不是夢想?為什麼建設一個健康的家庭不是夢想?”呂途分析,“對
青年一代打工者來說,寶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輛汽車,還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會認同等等符號。在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眼裡,消費已經不止是為了滿足需求,還是為了滿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房子
“成家”,是蘇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現在面臨的最大困難。
蘇浩民來自湖南新化縣,現在蘇州的一家模具廠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後在東莞、深圳、北京工作過。離開北京時,他和當時的女友分手。
“結不了婚讓我很苦惱。”蘇浩民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我將來想回老家生活,但是在蘇州和老家都還沒找到合適的對象。”
他認為打工過的這些城市只適合工作,不適合生活。“因為房價太高,買不起房子。”
面對大城市的高房價,蘇浩民的選擇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樣——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攢的錢、父親的資助,加上借外債,蓋起了新房。“這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成就。”從此,他的工資要用來為房還債。
呂途分析,對於正在存錢蓋房的打工者來說,其他的消費都要被壓到最低。“雖然有的工友的月結餘比例比較高,但是他或她一旦蓋房,就立刻進入負債狀況。”
呂途認為,這種“打工者在老家買房、自己長期漂泊在外”的現狀相當常見,是一種“加和為零”的遊戲:“當房子和居住地長期分離的時候,房子存在的意義大打折扣。城鎮化在大步推進,在農村蓋房子的人後悔了,在鎮上買房的人又趕不上時代的發展了,想在縣上買,卻已經買不起了,一輩子辛苦掙錢,就是為了買跟不上時代步伐的房子?”
一些“80後”青年打工者告訴記者,傳統上,買房子是為養老,但是,因為自己的子女將來必定不會在老家謀生,等老了以後,也許仍會面臨“無法養老”的問題。
對於回老家之後的生活,蘇浩民還沒有明確的規劃。“如果40歲之前能回去,就在老家找點別的事做;如果50歲才回去,就打算學一門手藝,用手藝謀生吧。”
買房問題,也折射著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費觀。
呂途認識一位“90後”打工者小尹,他在一家汽車製造廠工作,工資一個月2000元左右。他在網上申請搖號,入住了重慶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區,租金加水電費合計約每月600元。
呂途曾去過他家裡參觀:“印象很不錯,約30平方米。廚房和廁所都是原本就裝修好的,他自己買了家具、裝了木地板,花了2萬多元。”
按照政策,租滿5年後,小尹就可以購買這間房。在旁人眼中的“幸運”,卻被這名“90後”棄如敝履。“我問他:‘將來是否會把這個房子買下來?’他很吃驚地看著我說:‘我如果買房子就表示我要結婚了,我怎么可能滿意這樣的房子?別人都住別墅了,我卻住廉租房。太沒有面子了。’”呂途回憶。
孩子
每近年關,當今
青年一代在網路上宣洩“過年回家遭長輩逼婚”帶來的苦惱,已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王佳的上一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帶來的。
2007年時,她26歲,“家裡人已經非常著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經朋友介紹,她和上一任丈夫開始了用簡訊、電話撐起的“異地相親”。
2個月後,介紹人就帶男方去見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憶是:“大家都覺得可以。我父母說我們年齡也差不多,兩家離得也不是很遠,回雙方家庭都蠻方便的。”但直到此時,兩人還沒見過面,甚至都沒視頻聊過天。
在雙方家庭的催促下,他們於2008年10月“閃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長期工作在東莞,丈夫在遵義市里工作,孩子成了
農村留守兒童。生活在三地的他們,組成了“沒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對此很苦惱,又無法放棄城市的打工生活:“當時如果我回去帶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資,也就夠房租、水電和基本生活費,再過三年五載,還是沒錢。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幾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來。”
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最終,自己還是選擇了離婚,留在城市。現在,她也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兩人都在東莞打工。
對於王佳這樣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問題,呂途認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會屈從於父母‘以愛的名義’的強迫,不取決於子女對父母的愛有多深,而是取決於青年對自己未來定位的認識。”
她分析:“如果農村青年未來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戀愛、結婚對象是否來自同村或者鄰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從於父母的強迫,大多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把握和自信。當自己都很迷茫時,聽了父母的話,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錯誤決策可能帶來的責備,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這個‘最後的庇護所’。”
王佳現在確定,自己要在東莞定居。“這裡工作機會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東莞,回去之後,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倆沒有把孩子留在身邊,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個新的“留守幼童”,由爺爺奶奶照顧。
“如果將來條件允許,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邊。”這是千千萬萬個王佳的夢想。但是,已被父母帶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後”們,會比留守兒童更幸福嗎?
2014年,呂途對北京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皮村同心實驗學校5年級的學生做了社會調查。在學生的煩惱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調查問卷的字裡行間,彰顯著青年農民工初為父母的諸多壓力。學生們的原話有:“爸爸媽媽脾氣不好”,“我讓爸爸戒菸,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媽媽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壞”
戶籍
“來北京有十幾年了,一直沒再離開過。”出生在遼寧本溪的姜國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1992年,姜國良就離開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著家鄉的劇團四處奔波,去過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來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國良有兩個兒子。“我不是重視物質的人,未來最大的困難就是孩子的教育,將來考中學,非京籍的孩子會面臨種種困難。”
他也在未雨綢繆,一方面想給孩子入北京電子戶籍,另一方面也在打聽老家的學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適,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學,這也是沒辦法的。”
在京十幾年,姜國良依然不認為自己已經在北京紮下了根。“這個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較適合小鄉鎮裡安逸的生活。未來是不是會回家,我也說不好。”
同樣的心態,出現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軍身上。
1988年出生於山東農村的他,已經在一家江蘇的德資企業站穩了腳跟。2014年,他在打工的城市付了房子首付,今年準備和女友結婚。“我個人最大的成就,就是這幾年沒有像好多人一樣‘吃家裡的’。我自己努力攢出了首付,這是親手勞動所得,我很滿足。”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但他依然沒信心從此留在打工的城市。“家鄉的親人、朋友,都離蘇州太遠。雖然自己在這裡工作,但朋友圈子還是比較單調的。將來小孩上學,戶口問題也很麻煩。現在已經沒有信心說,未來幾十年一定都在這裡。”
呂途分析,“過客心態”是打工群體最顯著的心理特徵之一。她曾家訪過一對在廣州番禺新橋村的打工者夫妻:“他們已經在番禺住了十多年,兩個兒子都是在這裡出生的。但家裡面除了兩張並在一起的雙人床,沒有任何家具,所有的東西,都放在各種紙殼箱裡。”
“從農村到城市,青年打工者的生活、思想、消費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他們適應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後,下一步就是實現在城市發展的夢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目前,他們還迷茫在城鄉之間。”
“也許大家認為,打工者本來就是過客,這不完全符合事實。”這名曾去德國探訪土耳其移民的學者說,“從居住地的穩定性來說,打工者傾向於在一個地方落腳的趨勢是明顯的。移民人口總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回不去老家了。”
現在,姜國良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們這群從農村到城市裡來的人,能夠生活得更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我們打工的城市,從弱勢群體變為更有影響力、更有自信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