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佑禪師(771——853),唐代高僧,俗姓趙,福州長溪(在今福建)人,禪宗溈仰宗初祖。
年十五歲從建善寺法常律師出家,於杭州龍興寺受具足戒,究大小乘教。後到江西參百丈懷海。有一次,懷海讓他撥爐灰,看有火沒有,他撥後說沒有,懷海往深處撥,找到火星,責備他說沒有,於是大悟。唐憲宗元和末年,至溈山弘揚禪風,村民感德,群集共建同慶寺。相國裴休前來聞道,聲譽大揚,學僧雲集,遂於此敷揚宗風達四十年之久,世稱溈山靈佑。
溈山靈佑的基本禪法是“三種生”說,即把主客觀世界分為“想生”、“相生”、“流注生”,這也是他為接引學人證得大圓鏡智(佛智),達到自由無礙境地而設的三種機法。
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示寂,世壽八十三歲,謚“大圓禪師”。有《潭州溈山靈祐禪師語錄》、《溈山警策》各一卷傳世。
基本介紹
- 別稱:靈祐禪師
- 字號:大圓禪師
- 所處時代:唐朝中後期
- 民族族群:漢人
- 出生地:福州長溪
- 出生時間:西元771年
- 去世時間:西元853年
- 主要作品:潭州溈山靈佑禪師語錄
- 主要成就:開創禪宗溈仰宗
人物簡介
 五燈會元 卷九
五燈會元 卷九人物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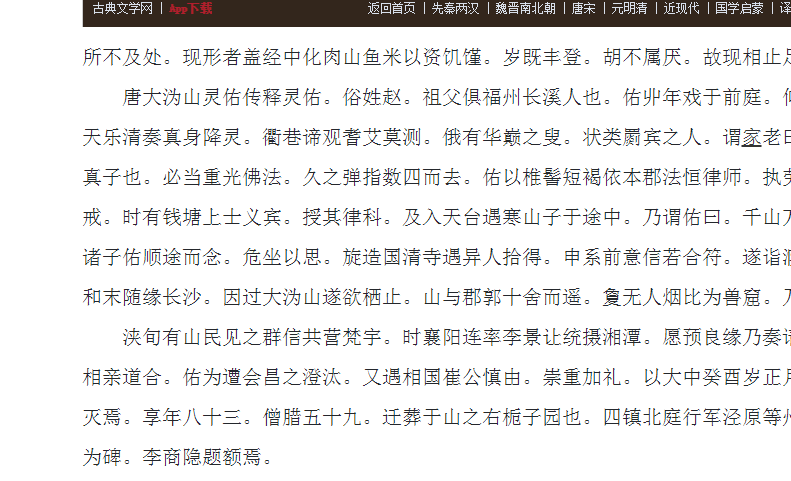 唐高僧傳 卷十一
唐高僧傳 卷十一 溈山道場
溈山道場 密印寺
密印寺弟子門人
禪法思想
從現有文獻看,靈佑與歷代的眾多大禪師一樣,行雲流水,隨緣參禪隨機弘教,並沒有親自著述什麼禪法主張。然而,中國佛教是一個文教,重視師承關係的國度,靈佑作為開宗立派的祖師,他隨緣任運的言傳身教,在當時被弟子們當成指導修行實踐的珍貴法寶,記錄下來。現存記述靈佑生平和禪法的資料主要有《祖堂集》卷十六 、《景德傳燈錄》卷九 、《五燈會元》卷九、《宋高僧傳》卷十一、《佛祖歷代通載》卷十六 以及《潭州溈山靈佑禪師語錄》等 所載靈祐的傳記和語錄。此外,在《全唐文》卷820中還載有唐鄭愚撰寫的《潭州大溈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並序》。至於見錄於《禪門日誦》中的《溈山大圓禪師警策》一卷,乃是靈佑為了警策學人珍惜現有生命,好好修行,不要懈怠懶惰,不要浪費光陰而作的。它雖然影響大,“自古即被視為禪林初學者必讀書籍之一,與《四十二章經》、《遺教經》並稱為佛祖三經。”(參見電子版《佛光大詞典·靈祐》)但畢竟是一種對學人修行態度的勸勉與鞭策,與禪法思想關係不大。
在此,筆者主要依據上述原始資料,參考《唐五代禪宗史》 、《禪宗宗派源流》 、《中國禪宗通史》 、《分燈禪》 等相關的研究,對靈祐的生平、歷史地位及主要禪法思想略加考察介紹。
1、主張直心
《景德傳燈錄》載,靈祐上堂說: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為,澹寧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
直心是道場,這是大乘佛教的一貫說法,《維摩詰經》、《楞嚴經》等大乘經論中都有明確的教導。因為按照佛法看來,正道與直心相應,不與諂曲、虛偽之心相合。一顆斜曲的心,必然是為凡情俗欲的煩惱所覆蓋的心,是執著的、染污了的無明之心,是自已不健康的同時還會給他人給自然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的心,這是與正道與真理南轅北轍的虛妄識心。相反,只有以直心來生活,來為人處事,才是促成自己與真理與正道最終相契合的保證,也才能真正地開啟人人本有的“真心”的巨大潛能,達到消除一切自尋的煩惱、還生命以自在無礙的健康真面目、成就自利利他的無量功德善果的目的。當然,直心是有凡聖的層次分別的,光是凡夫層面的直爽、坦率和不欺詐是不夠的,必須要達到離諸相待,中道不偏,無所執著的所謂“情不附物”,於一切時一切地逢緣對境的當下又不沾不滯,如鳥飛空中,無跡可尋一樣,才是真正的“直心”。
南宗禪特彆強調開啟人人本有的真心自性。真心是與妄心相對的,只要常行直心,去除種種的凡情俗意,去除種種的煩惱污濁的心行,真心自性的光明自然顯現,在此之外,無需再苦苦尋覓什麼真心,所以靈祐禪師讓人以質直無偽之心來臻達最終的清淨無為的解脫之境,如此一來,自然水到渠成地成為一個任運逍遙的“無事真人”,清淨無為,如秋水般的澄渟明潔。
2、“理事不二”
《祖堂集》載,慧寂在溈山時,曾向靈祐請教:“如何是佛?”靈祐回答:“以思無思之妙,返靈焰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如如佛。”理是體或是性,事是用或外相。理事關係是中國佛教經常提到的,像法相宗、華嚴宗對此都有所探討。特別是華嚴宗,以“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和“事事無礙法界”的四法界來充分闡述了重重無盡的法界圓融無礙的緣起觀,境界特別的高超圓滿。禪宗里,早在靈祐之前的唐代著名禪師石頭希遷在《參同契》中便有理事相依相待,不一不二,不可呆板地偏執一面的“回互”思想。
溈山靈祐在這裡明確提倡“理事不二”的理念,但作為禪師,他不會作出特別精細嚴密的論證與闡述,而更在於直截了當地指點學人來把握理事圓融的關係,從而教人不要逃避現實生活中的人事,不要將出世間與世間打成兩截。道就在日常的生活與工作之中,就在點點滴滴的人事裡,清淨的出世間其實就是從污濁的世間中得到的超越,萬法本自如如,唯人自鬧,只要你換一個看法,換一種生活態度,就能獲得自由自在,故此一切時中,無論面對的是怎樣的花花世界,身處其中的你都無須閉目塞聽,只要你具有一顆與中道相應的無著之心,那么你就是端坐紫金蓮台的“真如如佛”,行住坐臥儘是道,儘是般若風光。實際上,“理事不二”的思想,也是暗合慧能大師的思想的,因為如果離開世間去另外追求什麼出世間,拋開事相去追求什麼真性,恰恰就是六祖慧能大師所批評的猶如求兔角一樣的子虛烏有了。
《祖堂集》又載:有一天,靈祐與慧寂一起游山。靈祐說:“見色便見心。”慧寂問:“樹子是色,阿那個是和尚色上見底心?”靈祐回答:“汝若見心,云何見色?見色即是汝心。”
靈祐主張見到外在的色,也就是見到內在的心,也即是肯定自已的心與色身與周圍的物質環境,都是渾然一體,不可分離的。對此,應該說在大乘佛教看來,心色是不一不二的,兩者都可以統攝於本體意義的“一心”中。也就是說,從相上看兩者是有區別的,然而從體性上看,卻是無二無別,而且我們平常所謂的精神性的“心”與物質性的“色”,其實都是“真心”第二層面上的兩分而已。既然如此,一個真正的修行人,剛開始入手時,也許應該著重於向內觀察自已的起心動念,仔細地加以防護,然而最終卻不應該僅僅停留於關注內心,實際上,當你正確地面對環境,善巧地處理事務之時,就是心的妙用,也才是完美地把握了你的心。因此,像《維摩詰經》心淨則國土淨的意思,並不是說停留於自我內心的工夫而對外在的人事漠不關心,如果這樣的話,那僅僅是一種自受用的狹小的清淨,並沒有真正地把握到圓滿的清淨心。圓滿的清淨心,應該不僅僅局限於內心的純美莊嚴,同時也應該積極於淨化外在的世間環境,做到內外一如,將內在的真善美外化成對人間淨土的建設中,這才是心淨則國土淨的圓滿之義。而靈祐禪師心色不二,見色即見心的說法,筆者認為正是與此相應的中道圓融理念。
3、頓漸圓融的修行觀
《景德傳燈錄》載,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靈祐回答說:
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趨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頓超直入,不落階層的修行成就觀,是南宗禪法所標榜的,但這並非像一般人所誤解的那樣,以為南宗禪就是完全的否定漸修,完全否定傳統佛教的持戒、禪定乃至對經論的學習等等。事實上,南宗禪師雖然無一例外地強調直截了當地頓悟去,但多持有頓漸相結合的圓融修行觀,譬如神會、玄沙師備等。
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到,靈祐禪師就是明確提倡頓悟漸修不相偏廢的人。他大概認為,從究竟來講,說修或不修都是多餘的,都是因為沒有真正體悟到無得中道而來的世俗思維方式以及表達方式。而對於我們這個世間的人來講,普遍的,即便根機較好,能夠在當下一念中明白至理。然而多生累劫所薰染的習氣毛病,污垢重重,卻是難以隨著理上的頓悟而當下轉化清淨的。所以必須不斷地藉著對真理的把握來清除煩惱眾多的凡俗虛妄心識,修正不合正理的世俗言行,這才是腳踏實地的修行功夫,於人於已才會有實質性的受用。也就是說,從一般人來講,必須做好頓悟之後的漸修功夫,這當然並不排除頓悟的當下理事都清淨圓滿的可能性,只是這種可能性實在太過於稀有難得。不過,靈祐禪師畢竟是南宗禪師,故此頓悟成就仍然是其禪法的主體精神,所以在這一段開示中,他開宗明義便說“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最後結束時,又再一次強調:“若也單刀趨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歷史地位
除了本法系的禪僧之外,歷代其他的大禪師如雪峰義存、玄沙師備等對其禪法也都有所舉揚。禪林中對靈佑禪師的推崇程度,無過於鄭愚的讚美所說:“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大圓禪師碑銘並序》)評價是非常高的。
除此之外,據傳為靈祐禪師親撰的《溈山大圓禪師警策》,雖然不屬於禪法著作,但對於後學僧格的養成極有意義,“自古即被視為禪林初學者必讀書籍之一,與《四十二章經》、《遺教經》並稱為佛祖三經”。與廣為流傳的著名佛典並稱為“三經”,足見人們對它的推崇程度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自然的,著作者溈山靈祐禪師的鼎鼎大名,也是千古流芳,感動了一代代的有緣人。
靈佑非凡的影響力是不用置疑的,不過,對他的禪法思想,忽滑谷快天說:“靈祐根本思想與百丈所見不異,作為溈仰門風者,賓主對揚之手段而已。而其手段多出自慧寂”。 大概是認為靈祐的禪法思想不出其師懷海,並認為接機手法即所謂的“門風”,是各宗特色的所在,而作為禪門五宗之一溈仰宗的接機教化手段,卻多出自他的弟子慧寂,故靈佑本人似乎貢獻不多。
對此,筆者淺見認為,禪門五宗本來一脈相承,皆為六祖南宗禪系,其根本禪法思想本來就是相通的,只過大家在表達上有時會有自已的特色而已。而作為禪師,只要他真正把握了禪法的精髓,具備了佛法的真智慧與悲天憫人的情懷,任運自在,隨緣對機地給眾生以恰如其分的教導,達到開啟大家的真心的目的,那么,他便是眾生真正的依歸處,是值得肯定與讚嘆的,而用不著為了區別於他人而特意標新立異,這就猶如,只要對症下藥使人儘快恢復健康即是最好的,而不在於花樣的新舊與否。換一句話說,接機手法本來就是一種手段,若為了手段而忘了目的,反而是顛倒了。故《楞嚴經》批評愚痴的人執指忘月,執著於手段而迷失了目的,佛說如此一來,兩者都會被迷失了真義。
另外,以溈山靈佑為開山祖師的溈仰宗,雖然在中國佛教界和社會上都曾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但它在禪宗五葉中成立最早,衰亡也最早,大概在唐末轉入宋初時即告絕傳,然而這是不能做為論斷溈仰宗優劣的依據的。溈仰宗的衰亡,若探究其原因,除了本身的接機手法、歷史偶然性等之外,應該說能否得到傳承法脈的優秀人才是最為關鍵的了,故此北宋契嵩說:“然其盛衰者,豈法有強弱也?蓋後世傳承,得人與不得人耳。” 這也正是佛門常說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