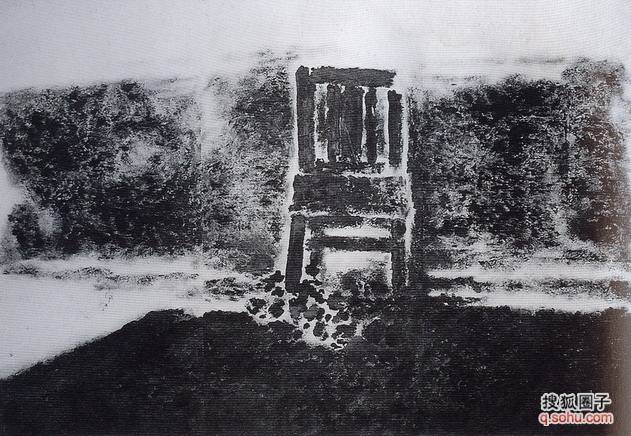基本介紹
- 中文名:閻秉會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天津
- 職業:書法家,美術家
作品展,個展,群展,閻秉會的詩,評價,梵志體,特點,意義,秉會上當,
作品展
個展
1993年 天津美術學院《閻秉會書法展覽》
群展
1985年 湖北武漢《國畫新作邀請展》
北京中國美術館畫廊《現代書法首展》
1987年 日本東京都美術館《中國現代書法展》
1989年 北京中國美術館《中國現代藝術展》
1990年 日本東京《中國現代水墨畫展覽》
1996年 美國舊金山《重返家園——中國當代實驗水墨藝術聯展》
1997年 上海《中國藝術大展——當代中國畫展》
1998年 “中國現代水墨藝術”歐洲巡迴展
收藏、日本東京大田區美術館、丹麥利斯威列森博物館
閻秉會的詩
評價
( 文/寒碧 ) 白話詩從民眾中來,又到百姓中去,我一向對之情有深衷。
記得數年前,讀王維的詩集,曾有兩首排律引起我特別的興趣。其實詩寫得很一般,內容不過宣揚佛教義理,也沒有王維詩風慣常的空靈逸韻。令我矚目的是詩題下面的小註:“梵志體”。“梵志”是何許人?其詩竟能稱“體”?且竟使大名鼎鼎的王摩詰效法?這些如今看來純屬知識性的問題,當時卻一直困擾著我。
梵志體
後來讀到范攄的《雲溪友議》和馮翊的《桂苑叢談》,才對所謂的“梵志體”有了些初步印象:梵志王姓,生活於隋末唐初;是一位“甚有意旨”的白話詩人。他用詩諷人戒世,文辭淺近通俗,因此深得大眾的喜愛。像下面幾句:
工匠莫學巧,巧被他人使。
身是自來奴,妻亦官人俾。
——《工匠莫學巧》
黃昏到家裡,無米也無柴。
男女空餓肚,狀似一食齋。
——《貧窮田舍漢》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
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
——《城外土饅頭》
特點
中國詩歌一向有著文雅的傳統,得意的詩人“雅”出了貴族氣派,失意的詩人“雅’’出了儒酸味道,油膩膩甜滋滋讓人不好消化。對於我這個久溺其中但尚能自警——感情未全麻木的年青人來說,看到上面那幾句詩,就仿佛在燕窩魚翅之外發現了一碗豆腐腦,它自然端不到星級飯店裡,也盛不進金銀美器中,卻自有它親切可口的色香味。也就在此前後,我又從宋人的一些筆記和詩話(如《梁溪漫志》、《庚溪詩話》、《苕溪漁隱叢話》等)里陸續蒐集到一些片斷資料,才知除王摩詰之外,大詩人黃山谷竟也是“梵志體”的推揚者。我喜歡梵志的單純、樸素,所謂“其言雖鄙,其理歸真”,“言之不文,行之‘必’遠”!於是興沖衝去檢索《全唐詩》,想系統地看個究竟。但結果大出逆料,《全唐詩》竟一字未收這位了不起的詩人之作!
胡適曾把中國古代詩歌史的發展概括為兩條線索:“通俗化”的和“文人化”的,他認為前者的趨勢最終沒有抵住後者。魯迅也曾指出:歌詩詞曲原是民間物,一到文人手中,跟著就是滅亡;他們把“竹枝”改成了“文言”,譬如把“小家碧玉”變成了“姨太太”。
意義
——“梵志體”即屬通俗的“民間物”,在文人統緒的詩壇里,其“滅亡”是理宜固然的事。宋以後漸漸無人提及梵志,《全唐詩》竟然不收梵志,就是鑿證。也許有人會問:“唐宋時的王摩詰、黃山谷不是文人嗎?他們不是對‘梵志體’推崇有加嗎?”這怎么解釋呢?其實道理很簡單,你稍加分析就會察覺,摩詰和山谷從來就沒看重過梵志詩的“通俗化”,他們都只是在闡揚佛理一端上覺得梵志是“大修行人”,在這個意義上才認同了他。他們理解的“梵志體”和梵志所作的白話詩是毫不相干的兩回事。
梵志之後,中唐的寒山、拾得都是白話詩的大手筆。下面所引寒山的幾句,可以看成這一類詩人的自識:
有個王秀才,笑我語多失。
雲不識蜂腰,又不會鶴膝。
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詩,如盲童詠日。
不調平仄,出言不文,故難免招致秀才文人的嘲笑。因此寒山老實不客氣地闡明立場,予以回擊。 當然,他的力量畢竟微弱。他的詩歌命運,並不比梵志強出多少,連同拾得,他們的作品始終流布於民間而上不了文壇。
白話詩無法與文人詩相抗衡,最終在文人主宰的詩壇上銷聲匿跡,宋以後迄於清,中國詩壇上再沒出現過盛名的白話詩人。
我的朋友閻秉會,是一位著名書畫家,餘事為詩,不事采藻。他對古典詩歌有獨到的理解和好尚,認為白話詩不該有滅亡的命運,因此乃有振衰踵後之志。他斷斷以爭:有文人之詩,有常人之詩,兩者的藝術趣尚不同,各自的價值標準相左,宏通的理解應是不作軒輊,不能用文人詩的標準評判常人詩,就比如不能拿踢足球的規則來裁判桌球。他更主張文人要多讀白話詩,以救雕饋虛浮之弊,這同我一向所持的觀點略同。我曾多次講過:“雅”與“不雅”絕非衡量詩歌的價值標準,並且詩人的所謂“逃俗”,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應理解為“近俗”’而不是簡單地求“雅”;太雅了就不真了,而虛假和媚俗本差不太遠。因此,我特別鼓勵秉會多寫這些不雅之作,也特別喜歡他這類詩:
一歲即喪父,三十又失母,
自幼少人愛,今日知母苦。
——《自況》
人人都在走,人人不等候。
究竟去何方,可問林中獸。
——《走》
浪跡天涯何所尋,
青山頂上看白雲。
千山萬山無今古,
白雲深處即我心。
——《心》
這些詩都寫得坦易平實,不乖真情,明白如話,也許那些 “雅人”們看了“不屑”,但我相信他們也不能。
秉會幾年來一直喔吟不輟,作品已有了極可觀的數量,並且有著比較高的質量。日前他費了很大力量進行整理刪存,精選近百首滿意的作品,擬壽之梨棗,他向我征徇意見並命我為序。我對他說,作為一個文人,你能如此特立獨行,在秀才們嗤之以鼻的白話詩上下功夫,這需要有怎樣的勇氣和毅力,忍受多大的寂寞呀。你的創作不必強說成功,甚至也不必非說成熟,僅你的態度就夠了。我希望你將這些作品高自標置,因為它們本來就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力。秉會頗有會心地說:“結廬在人境,我手寫我心”。
有一種詩是絕艷的花,開在花瓶里,擺在窗台上;有一種詩是無花的果,長在原野中,生在泥土裡。親愛的讀者,你更喜歡哪一種呢?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