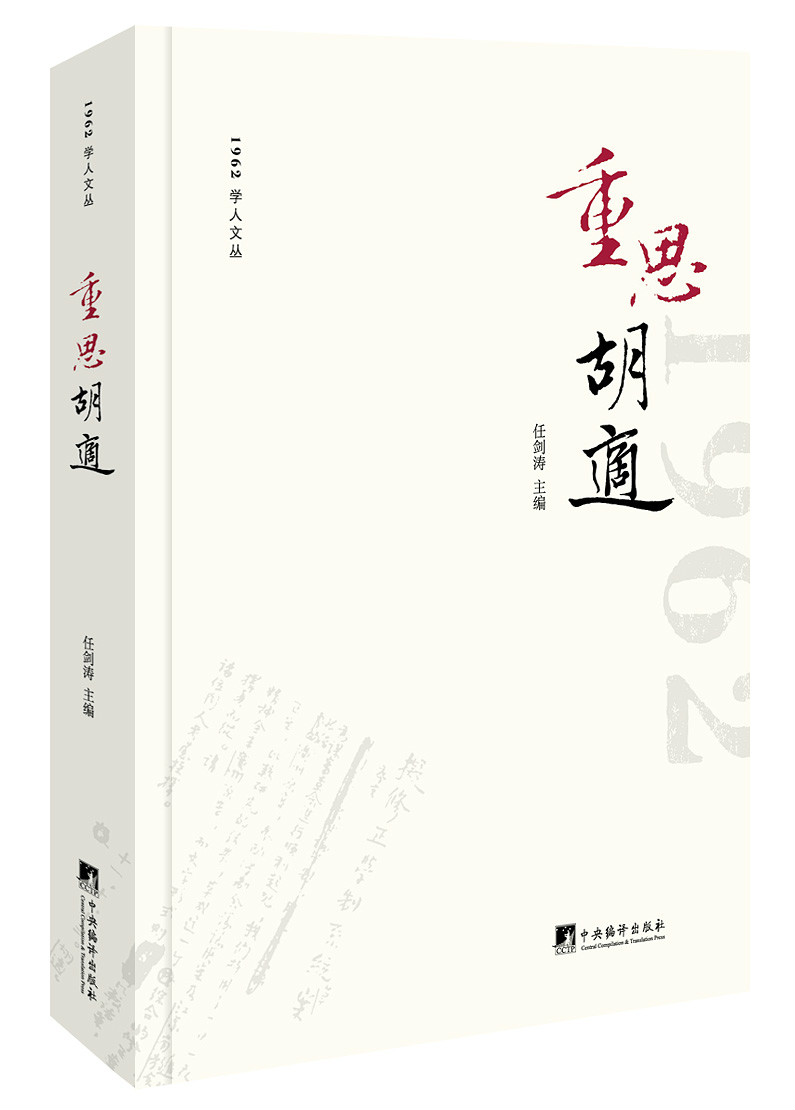胡適是啟動中國現代轉軌的一代思想重鎮。他的思想貢獻是多方面的。以其社會影響而言,他對新文化運動、尤其是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既廣泛深刻、又持續久遠;以其對政治轉型的作用而言,胡適是以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載入史冊的。前者,似乎可以說是完全竟功,今天中國的文化形態已經轉進到現代的結構;後者,就其所期待的政制建構來講,言之成功,則遠未可期。但胡適所指示的方向,絕對是正確無誤的。在古今中西的強烈碰撞中,胡適為轉型中國刻畫的藍圖,究竟是不是可以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變成現實,自然是一個歷史過程才能顯示答案的問題。
1962年,胡適去世。本書是在胡適去世那年出生的幾位學人茶聚的基礎上形成的論文。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胡適思想的再認知”,包括高全喜、許章潤、單世聯、陳明和任劍濤5篇論文,下編“胡適話題的再探究”,包括歐陽哲生、燕繼榮、陳志武和胡傳勝4篇論文。正文後附錄“胡適思想的當代考察——紀念胡適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實錄”。
基本介紹
- 書名:重思胡適
- 作者:任劍濤 主編
- 原版名稱: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 譯者:秦傳安
- ISBN:9787511723710
- 頁數:400
- 定價:88.00元
-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11月
- 裝幀:精裝
- 開本:16
主編,目錄,導言,
主編
任劍濤,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近期主要從事政治哲學、政治思想史、中國政治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從自在到自覺——中國國民性探討》(1992),《倫理政治研究——從早期儒學視角的理論透視》(1999)、《道德理想主義與倫理中心主義——儒家倫理及其現代處境》(2003)、《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2004)、《權利的召喚》(2005)、《後革命時代的公共政治文化》(2008)、《政治哲學講演錄》(2008)、《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
目錄
導 言 /01
上編 胡適思想的再認知 /001
胡適:新舊之“中庸”(高全喜) /002
基於庸見的法意——胡適之先生關於憲政與法制的看法(許章潤) /025
信念與錯覺——評說胡適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的一些觀點(單世聯) /053
重建儒家視野里的胡適——論胡適與儒家(陳明) /096
胡適與國家認同(任劍濤) /129
下編 胡適話題的再探究 /181
胡適與司徒雷登:兩個跨文化人的歷史命運(歐陽哲生) /182
胡適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兼論中國國家發展歷程(燕繼榮) /216
胡適“自由夢”的經濟基礎(陳志武) /247
中國的復興與自由主義的理論難題(胡傳勝) /272
附 錄 /313
胡適思想的當代考察——紀念胡適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實錄 /314
後 記 /385
上編 胡適思想的再認知 /001
胡適:新舊之“中庸”(高全喜) /002
基於庸見的法意——胡適之先生關於憲政與法制的看法(許章潤) /025
信念與錯覺——評說胡適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的一些觀點(單世聯) /053
重建儒家視野里的胡適——論胡適與儒家(陳明) /096
胡適與國家認同(任劍濤) /129
下編 胡適話題的再探究 /181
胡適與司徒雷登:兩個跨文化人的歷史命運(歐陽哲生) /182
胡適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兼論中國國家發展歷程(燕繼榮) /216
胡適“自由夢”的經濟基礎(陳志武) /247
中國的復興與自由主義的理論難題(胡傳勝) /272
附 錄 /313
胡適思想的當代考察——紀念胡適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實錄 /314
後 記 /385
導言
1962年,胡適去世;1962年,我們出生。
這當然是生命長河中偶然碰巧出現的兩件事情。但無巧不成書。往往正是偶然出現、且不大相關的事情,一經關聯性思考,就出現了某些令人驚異的內在契合。
在2012 年,1962年出生的幾位學人茶聚,說起這一年中國的種種大事小事,總覺得跟“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我們沒什麼關係,於是大家想做一二件事情,以志我們在這一年活過。說來說去,胡適1962年的仙逝,成了大家的共同話題。議論來議論去,大家覺得不論是就我們恰好這一年出生的偶然巧遇而言,還是就中國的現代轉變來說,都值得為胡適召開一個專門學術會議,以便以一個較為正式的形式,表達我們對胡適的深刻紀念,也自我提醒知天命之年的我們,得為國家的發展思考一些更為重要的問題。由於2012年的中國處在一個特殊政治年份,因此,是次會議不得不放到接近年尾的時間舉辦。好在會議開得非常熱烈,學術上也有一定收穫。於是,在會議上,與會者達成共識,將提交會議的發言稿修訂成正式論文,並交付出版,以便將這一次富有意義的胡適紀念會記載下來。
胡適是啟動中國現代轉軌的一代思想重鎮。他的思想貢獻是多方面的。以其社會影響而言,他對新文化運動,尤其是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既廣泛深刻又持續久遠;以其對政治轉型的作用而言,胡適是以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載入史冊的。前者,似乎可以說是完全竟功,今天中國的文化形態已經轉進到現代的結構;後者,就其所期待的政制建構來講,言之成功,則遠未可期。但胡適所指示的方向,絕對是正確無誤的。在古今中西的強烈碰撞中,胡適為轉型中國刻畫的藍圖,究竟是不是可以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變成現實,自然是一個歷史過程才能顯示答案的問題。不過,一切關心中國現代轉型話題的人們,試圖繞開胡適去申論相關主張,那卻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胡適的思想有一種不溫不火的性格。不是說胡適沒有激進的主張,支持全盤西化,就至今為人所詬病;也不是說胡適就沒有維護傳統的一面,他使美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辯護,甚至顯得有些迂腐。但總體上說來,在中國文化急遽轉型的歷史劇痛階段,他並沒有走向偏執和極端。他深切感到中國傳統文化已經不適應現代轉變之需,因此呼籲轉型中國接受西方文化。但他並未因此提倡“不讀中國書”。他自覺意識到中國接受現代西方文化的必要與重要,但並未走向一偏,即使提倡自由,但更強調“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是因為如此,胡適的思想給人們一種矛盾重重的感覺:說他開懷擁抱現代,他一生卻又花費了巨大精力,致力於整理“國故”;講他潛心整理國故,卻又對西方現代學術推崇有加。這不僅矛盾,而且有點兩頭不著岸的尷尬:整理國故,人們並沒有將他視為與傳統親和的保守人士;引進西學,人們也沒有將他看作現代學術的創製人物。這是他去世時被人認定為“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最重要的緣由之所在。在中國需要作別傳統、進入現代的情況下,胡適缺乏決絕的態度,自然處在一種吃力不討好的爭論漩渦之中:親和傳統的人士,對胡適切齒痛恨;支持現代的人士,對胡適缺乏創造備感遺憾。但不得不承認,現代學術的引入,缺乏胡適的努力,可能會出現巨大的缺失;傳統的整理,缺乏胡適的倡導,可能會喪失現代生機。這就是胡適具有不可替代的現代思想史地位的紮實理由所在。
百餘年來,中國的現代轉變總是處在一種進退失據的狀態。歷經晚清、民國與人民共和國三個階段,但中國完成現代轉型的歷史任務,似乎仍處在艱難困苦的境地。在三個不同階段上,人們對這一困擾中國人的處境,充滿憤懣之情。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狀況。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多少身懷振興國家雄心的志士,生髮浩嘆、痛心疾首,不斷發出慘痛的批判之聲,決絕地斥責現實,絕望地看待未來。魯迅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痛切診斷、對中國現實的絕望觀察、對傳統文化弊端的深刻指正、對現代中國發展的痛心疾首,躍然紙上,活生生顯示出一個“新舊雜陳、方生未死”的中國那種無望的精神狀態。與胡適相比較,魯迅的精神氣質與其相差何止千里。這是今人祭出“要胡適,還是要魯迅”話題的動力所在。
其實,胡適與魯迅並不那么對立。如果把魯迅看作是中國人不得不“送舊”的代言人的話,他那種決然而然的批判態度,對傳統、對現實的決不妥協,以匕首和投槍戰鬥的姿態,恰好凸顯了中國作別傳統的艱辛狀態。如果把胡適視為中國人進入現代不得不“迎新”的傳聲筒的話,他那種試圖混合古今中西精粹以逼進現代的取向,也恰好顯示出中國進入現代的曲折複雜。魯迅與胡適之所以作為中國現代文化的兩面旗幟,不存在要誰不要誰的客觀理由,只存在偏重哪個面相的主觀偏好。對此,只有那種深刻領會了對中國轉型之難而引發的憤恨的人,才能理解魯迅;也只有那些領悟了中國轉型中理性的絕對重要性的人,才能與胡適相契。基於此,人們就有了平情對待魯迅與胡適的理由。正是基於這樣的理性態度,我們也才在死與生的偶然繼起性中,發現了我們紀念胡適的特殊價值。
胡適,以及魯迅,總是站在國家轉軌的十字路口,提點人們。他們是觀察、論述中國現代轉軌的智者。在那個時代,他們以自由的心靈,觸碰嚴酷的現實。不論是對現實強烈不滿引發的憤慨,還是對未來發展的充滿期待,他們都沒有被現實所摧折、被壓力所彎曲、被挫折所屈服,他們對國家和未來懷抱深切的期望。這正是表明他們心靈自由的最可貴的地方,也是今天的我們與他們在精神深處相契合的地方。
魯迅對現實的極端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無法模仿的。他那種決絕的姿態、入木三分的文辭、終生不妥協的作為,不是一般人所可以習得的。相比之下,胡適的可學性較強。胡適較為平實的人生取向、寬容待人的態度、中庸的為學方式,比較符合常人的思維與行動進路。當然,胡適也不是一般人即學即成的。他是大師,是一般人敬仰的對象。不過就一般人來講,面對胡適,有一種相對親切的感覺,“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與胡適那種自由而寬容的心靈相交,自然也就親和很多。
探究胡適的思想,自然不是我們的直接目的。因為我們這群學者,除開一位公認的胡適專家外,其他人從未專門處理過關係到胡適的學術話題。幾乎是一群胡適研究的門外漢,卻要來專門論道胡適,也許會引起人們的訕笑。但我們也自有論說胡適的切實理由:不僅是因為他逝世的時候,我們剛好出生,似乎有一種人生—精神繼起的稟賦。但這完全是不成理由的理由。關鍵是因為,胡適一直是我們各自所從事的專業研究的重要參照人物。儘管大多數論者沒有專門研究胡適,但胡適未嘗完全離開我們的關注視野。只不過此前缺少一個契機,讓我們來專門整理自己對胡適相關論說的看法或學術見解。而這次,確乎有了一個申述各自關於胡適與自己專業研究關聯性的機會。自然,由於參會者各自的專業視角和關注點的不同,切入胡適論題的角度便大為不同。不過從總體上講,最後參會者提交的論文,可以切分為兩個視角:一是論述胡適本人的思想,二是分析胡適開啟的相關論題。
前一部分有五篇論文。
高全喜的論文“胡適:新舊之‘中庸’”,致力勾畫胡適的思想性格。文章從蔣介石在胡適逝世撰寫的輓聯說起,解析胡適何以成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胡適與蔣介石一生多相交集。胡對蔣,有尊重,有批評,有苛責;蔣對胡,有憤懣、有嘉許、有期待。彼此還算是一種君子之交。但蔣胡之間似乎總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所以胡對蔣有微詞,但總還護著蔣;蔣對胡有不滿,但總還是能夠容忍。蔣對胡適一生的概括,確實比較準確地勾畫了胡適的思想與人生特質。蔣胡有君臣之名,更有敵友複雜關係。雙方能夠相容,而沒有走向一種決然的敵對狀態,不能不說與胡適、當然也與蔣介石的中庸性格相關。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古今中西”風雲際會之際,這也是一種被時代所約定的精神品質。這種“不顯山不露水”所顯現的“極高明而道中庸”,呈現出一種現代中國人的獨特風骨。
許章潤的論文“基於庸見的法意——胡適之先生關於憲政與法制的看法”,著重指出,胡適先生對於法制和政制、立國與立憲以及約法與人權,都發表過相當數量的文論,不僅旨在接應當日的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而且觸及到了法律的政治、社會、道德和歷史稟性。通過討論立憲與建國的一元進程,人權與約法的內在機理及其政治理想,人民及其守法的共和主義,以及經由法制賦予民主以肉身的結構-功能主義,胡適思想展示出國家觀念和自由理想、強有力的政府和立憲民主、統一的政制與多元政治理想、賦權的法律與守法的美德之間的緊張,以及法律的合法性與它的文化-歷史正當性之間的對應性互動,等等。其以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視角,對於一個轉型時代的法制難題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答案,而呈現出一種基於庸見和常識的法意。
單世聯的論文“信念與錯覺——評說胡適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的一些觀點”,對20世紀30年代那場關乎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大爭論進行了回顧和評價。1934到1937年的“民主與獨裁”論戰,具有全國性的規模,僅就發生在胡適等人編輯的《獨立評論》上的文章而言,第一階段的主題是中國如何統一,第二階段的中心是中國應取何種政制。論戰主要發生在知識界,對中國實際政治生活並無明顯影響,但其言論所涉,卻是百年中國文化始終難以迴避的艱難選擇,而其中的有些觀點,我們現在也不難聽到。胡適在論戰中寫了不少文字,其根本主張是中國搞不了新式獨裁,搞“新式獨裁”的後果只能是“舊式專制”。胡適對“現代式獨裁”的獨特解釋包含著若干依然有效的問題,比如複雜社會中政府權力的擴張、技術專家的參政、民主的訓練等等。重溫古典自由理念,我們依然需要正視民主在當代世界的種種“新形式”。回顧胡適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的觀點,不但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有助於澄清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若干問題。
陳明的論文“重建儒家視野里的胡適——論胡適與儒家”,強調指出,胡適出身徽州儒學世家,自幼受正統的儒家教育,留學美國期間也長期以孔孟和朱子之徒自居,就是在新文化運動的激烈期,也從未對孔孟口出惡語,更是精思十多年作成平生得意之作《說儒》,胡適晚年的秘書胡頌平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多處記錄了晚年胡適對孔子和儒家的稱道。可見,一般印象中胡適是全盤西化論者、全盤反傳統主義者,實際是片面的。研究胡適與儒家的關係,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他所伸張的“充分的世界化”,其實是一個文化政治問題。胡適將充分世界化和天下觀真正的重建兩相聯繫,正是基於此,胡適對儒家的消解太過頭,對重建儒家的現實重要性認識不足。反思胡適與儒家的關係,在重新認識胡適的同時,也要重新認識儒家,重新思考重建儒家的意義。
任劍濤的論文“胡適與國家認同”,明確指出,在中國從古典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人們必須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認同。胡適也處在這樣的狀況中。對於胡適而言,古典帝國時代的中國文化,始終是他要表達忠誠和傾慕的對象。但在文化意義上的“祖國”與政治上正在建構之中的現代“中國”之間,胡適的國家認同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紊亂。對於祖國的傳統文化,胡適一直是尊重和自豪的。但對於建構中的現代“中國”這一政治實體,由於沒有坐實在他所理想的憲政民主平台上,因此他的認同態度是複雜的:對於20世紀中國建構的兩個政黨國家而言,胡適均不太認同,但對兩者的具體認同態度又有明顯差異。而在中國與美國的國家建構與認同差別的體認上,胡適確定了自己國家認同的典範形式——憲政民主國家,並期待中國的國家建構能夠落定在這樣的國家平台上。
後一部分有四篇論文。
歐陽哲生的論文“胡適與司徒雷登:兩個跨文化人的歷史命運”,首先確認,胡適與司徒雷登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兩位重量級歷史人物。胡適日記為人們找尋他與司徒雷登、燕京大學交往提供了諸多線索,司徒雷登回憶錄等材料則可顯現他對胡適、北京大學的看法。胡適與司徒雷登在教育、外交方面相似的經歷為他們的交誼奠定了基礎;而對基督教的不同立場又預示了他倆之間的矛盾。胡適與司徒雷登之間的對話,為處理世俗與宗教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樣板,是我們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值得解析的典型案例。司徒雷登站在宗教立場上、胡適站在世俗立場上看待相關問題。胡適與司徒雷登在種種問題上表現的立場和調整,不過是中西矛盾發展到新階段的典型表現。他們之間既對話、爭論,又彼此容忍,這就為處理世俗與宗教的對話提供了新的樣板,也為中美文化交流展示了取長補短、求同存異、互相適應這一新的趨向。
燕繼榮的論文“胡適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兼論中國國家發展歷程”,基於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古老的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指出中國的表面變局是中國經歷“喪權辱國”到“民族復興”的演變;實質變局是,中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清醒過來,試圖實現傳統“天下型”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轉變。在這種古今之變、中西相遇的變化中,中國遭遇了嚴峻的“國家性危機”(stateness crisis)。晚清覆亡,舊的政治秩序解體。如何建立起一個對外能夠維護國家主權、對內能夠實施有效統治的現代國家,成為中國最為急迫的任務。面對危機,國共兩黨都沿用蘇俄革命的經驗,通過黨治國家形式,實現建立現代國家、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胡適對國共兩黨都持批評態度,這既是其自由主義的思想基底使然,也是其漸進改良“實驗主義”哲學觀念之必然。跳出簡單的革命與反革命、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維模式,從“國家性危機”以及“以政黨挽救國家”的危機應對方式的視野來考察中國近代歷史,能夠更好地體認和闡發胡適思想的時代價值。
陳志武的論文“胡適‘自由夢’的經濟基礎”,在綜合考察五四以來中國思想界的思想傾向後,指出:五四時期與之前的中國社會運動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於其旗幟鮮明地以個人自由為目標,以知識啟蒙和新文化為具體手段。那場啟蒙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它決定了過去近一個世紀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命運,其中也不乏因認知盲點帶來的災難。當然,回頭看,那次啟蒙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從激進民主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到改良自由主義的胡適,存在著共同的知識結構缺陷,即都以人文哲學為主,對現代經濟學了解甚少,以至於他們雖然都號稱追求自由夢,但對自由夢所需要的基礎制度只有模糊的理解,不清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是個人自由的基石條件。這些認知缺陷使他們除了熱衷自由的價值取向外,沒能為這一價值追求找到成功的具體實現手段。在我們今天研究五四思想史的時候,有必要避免同樣的認知盲點,最好能用現代經濟學以及其它社會科學範式去審視胡適等知識分子的思想世界,從而為“自由夢”夯實經濟基礎。
胡傳勝的論文“中國的復興與自由主義的理論難題”,首先指出了一個悖謬的現象,一方面中國的復興是21世紀世界歷史的最重要現象之一。最敏銳的中國問題專家甚至也沒有預料到這個現象。另一方面,1989年以後至少十年時間,不少人認定,中國的崩潰似乎指日可待。在西方的意識形態中,中國的崩潰似乎是國際共產主義或全球專制政體的最後亦是最大的失敗。至今,中國崩潰與中國威脅仍然成為關於中國的兩個最生動的想像。其次,作者對這樣的悖謬進行了分析,強調指出,一方面,中國的復興或富強並不全是虛構。不承認這點並不明智。中國的復興遵循的是中國文化原有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國的復興不僅是自由主義解釋不了的、與自由主義無關的,甚至是根本反自由主義的。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自由主義話語是屬於富強或民族尊嚴重建這個更大的話語的,而一旦中國的富強通過非自由主義的手段獲得,這就為自由主義提出一個理論難題,尤其是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思想的構成性因素時。
論文之後,附上了1962學人紀念胡適逝世5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會議發言實錄。本來,發言中的大多數話語,已經為發言者寫入了論文中,似乎沒有必要收入本書。但讀者閱讀發言實錄後可以發現,在會議進程中各位發言人的發言,不僅比書面語言顯得活潑,而且因為是在嚴肅的學術對話中申述自己見解的,因此更增加了一種相互攻錯的論辯性,這無疑有助於發言者甚至是閱讀者在不同意見中有效整理自己的思緒。因此,將之收入書中,似乎不為多餘。
這些論文,凝聚了寫作者的深入思考和專業見解。其中,有若干論題是以往的胡適研究中較少提起或重視不夠的。水平如何,得由讀者評價。但我們的態度非常誠懇。這種誠懇的態度,不唯是對先賢胡適的,也是對我們自己1962學人所在的學術群體的,更是對轉型中國需要深入剖析的理論問題的,自然還是對讀者諸君的。經由現代先驅探究中國轉型問題,是我們共同確立的群體研究志向,願與同道和讀者一起付諸實踐。
1962學人以紀念胡適為契機的學術聚會,只是這批學人學術聚會的一個起點。這樣的聚會會不會有些許學術創穫?難說。一切望諸將來吧!時間,才是量度一切的剛性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