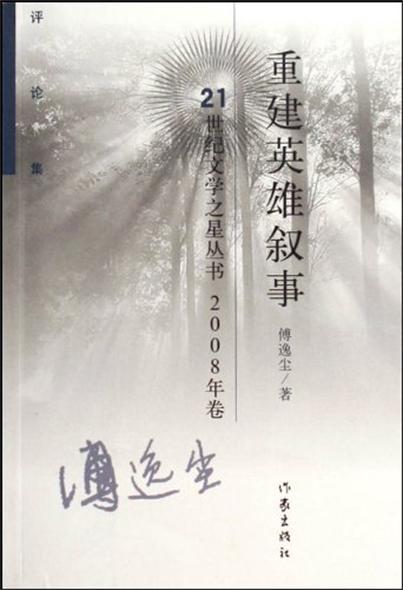《重建英雄敘事(2008年卷評論集)》為“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是中國作家協會、中華文學基金會主辦,中華文學基金會策劃,由專門的編審委員會經過嚴格程式編選的青年作家作品集。本叢書意在扶植文學新人,年齡在40歲以下,具有創作成績和潛力,尚未出版過文學專集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均可列入備選範圍。本叢書已出版10卷,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2、2004、2005、2006、2007年卷已分別由百花文藝出版社、華夏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本卷為2008年卷,收錄了傅逸塵的評論文章。主要包括《當代軍旅文學的現實主義主潮》、《守望生活“現場”的“有難度的寫作”》、《新世紀小說研究》等。這些內容充分顯示了作者豐富而細膩的生活。具有較高的文學性、藝術性和可讀性。
基本介紹
- 書名:重建英雄敘事:2008年卷評論集
-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 頁數:242頁
- 開本:32
- 定價:22.00
- 作者:傅逸塵
- 出版日期:2009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6347181
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作者簡介
傅逸塵,男,本名傅強。1983年生於遼寧鞍山,2002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現役軍人。參與多項國家級課題研究,現為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文藝學專業06級碩士研究生。
2003年以來,在《文藝報》、《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山花》、《芙蓉》、《小說評論》、《當代文壇》等報刊發表文學理論批評文章五十餘篇,計二十餘萬字,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等轉載。
2003年以來,在《文藝報》、《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山花》、《芙蓉》、《小說評論》、《當代文壇》等報刊發表文學理論批評文章五十餘篇,計二十餘萬字,多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等轉載。
圖書目錄
總序:
序:重整山河待後生
第一輯 當代軍旅文學的現實主義主潮
裂變與生長
“強健而充分”的現實主義
愛國主義、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宏偉交響
軍旅文學八十年:“三個階段”與“四次浪潮”
新世紀軍旅文學:堅守與突圍
直面現實與呼喚英雄
軍旅小說要警惕快餐化
第二輯 守望生活“現場”的“有難度的寫作”
軍旅文學:精神立場的執著堅守者
守望生活“現場”的“有難度的寫作”
顛覆“高雅”與“通俗”二元對立模式的軍旅長篇小說
戰爭題材文學:重新回到正面描寫戰爭中來
換一種調式,唱出大真之美
在超越中建構軍旅文學批評
對峙:在傾斜的棋盤上
《長征》:史詩精神的回歸與重建
英雄話語的重建與悲劇精神的燭照
為軍旅生活的“存在”作證
第三輯 新世紀小說研究
城鄉二元對立背景下的人性探索
蒼白的寫意與病態的知識分子私語
詩意的現實主義與頹敗的精神家園
虛偽而矯情的“泛私語化寫作”
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還是作者的權利?
“超越性”的歷史敘事
危險的欲望化敘事
輯外篇
並不遙遠的絕響
序:重整山河待後生
第一輯 當代軍旅文學的現實主義主潮
裂變與生長
“強健而充分”的現實主義
愛國主義、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宏偉交響
軍旅文學八十年:“三個階段”與“四次浪潮”
新世紀軍旅文學:堅守與突圍
直面現實與呼喚英雄
軍旅小說要警惕快餐化
第二輯 守望生活“現場”的“有難度的寫作”
軍旅文學:精神立場的執著堅守者
守望生活“現場”的“有難度的寫作”
顛覆“高雅”與“通俗”二元對立模式的軍旅長篇小說
戰爭題材文學:重新回到正面描寫戰爭中來
換一種調式,唱出大真之美
在超越中建構軍旅文學批評
對峙:在傾斜的棋盤上
《長征》:史詩精神的回歸與重建
英雄話語的重建與悲劇精神的燭照
為軍旅生活的“存在”作證
第三輯 新世紀小說研究
城鄉二元對立背景下的人性探索
蒼白的寫意與病態的知識分子私語
詩意的現實主義與頹敗的精神家園
虛偽而矯情的“泛私語化寫作”
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還是作者的權利?
“超越性”的歷史敘事
危險的欲望化敘事
輯外篇
並不遙遠的絕響
文摘
一、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的文體自覺和技術創新
中國當代軍旅長篇小說與“現實主義”有著太多的聯繫與錯綜複雜的矛盾糾葛。建國後,“毛澤東同志提倡我們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兩結合”理論強力影響、規約了建國後,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創作,並在其後相當長的時期里持續發揮著作用。進入新時期的軍旅文學是以人道主義的張揚和現實主義的恢復為基本特徵的。急切的表達和說教欲望使得“主題先行,思想大於形象”成為這一時期軍旅文學的集體症候。陳舊的文學觀念、傳統的思維定式及審美心理積澱,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軍旅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力量與藝術感染力。進入90年代,“作家們力圖遵循著現實主義文學嚴格地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表現生活的原則,以豐富、細膩的筆觸表現生活中的各種形態,並不斷地向著人物的心靈深處拓展;但是,過於強烈的‘主題意向’又使得作家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意識到的思想內容生硬地灌注到作品中,而沒有能夠融會到藝術形象的塑造中”。總體而言,軍旅文學與現實主義的關係始終處於一種焦慮和緊張的狀態。在軍旅文學史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創作領域裡,現實主義成為了一個被數度改寫並隱含了多種似是而非的文學觀念的模糊概念,但“寫真實”的原則與對現實生活的熱情追求始終被軍旅長篇小說寫作奉為圭臬。現實主義在表現和再現歷史的深廣度上,揭示歷史本質方面確實有著其他文學流派所不具備的優勢,然而,隨著時代和文學的發展,現實主義文學自身也要尋求更新換代。而此種自我完善並不是簡單的由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觀念顛覆和消解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就能夠完成的。我以為現實主義與其他文學思潮和流派之間本來就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作為藝術地關照並反映世界的方式,現實主義對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文學思潮並不具備天然的拒斥力,相反倒是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和性。而當代軍旅文學,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之所以長期處於對現實主義的困惑與焦慮之中,我想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在於“道”與“技”的疏離。藝術觀念、藝術思維的僵化落後,技術素養的偏低和語言能力的欠缺束縛著軍旅長篇小說作家,使得他們無法展開靈動的翅膀向現實主義的浩瀚天空飛翔。然而,在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中我驚喜地發現,隨著現實主義和技術主義的雙重祛魅,現實主義的“道”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技”正在發生自然的融合,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向我們展示了“兼技並道”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突出地表現為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作家對長篇小說文體的自覺和進行技術“創新”的努力。
“在西方文體學家看來,文體其實就是語言,文體的本質不過是一個表達方式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言說的問題。就長篇小說的文體而言,問題可能遠非這么簡單,在語言背後其實還隱藏著許多深層的藝術問題。作家的思維與藝術觀念、時代的審美風尚等等都會對長篇小說的文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文體絕不是一個平面的‘語言’問題。而是一個深邃、複雜、立體、多維的系統結構,它牽涉到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結構、修辭、敘述、描寫等幾乎所有方面。”。作為一種重型文體,追求思想和意義的“深度”自然是軍旅長篇小說題中應有之義。20世紀90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作家已經主動而自覺地完成了思想主體從集體性的、階級性的“大我”向個體性的“自我”的轉化。作家們在作品中儘管依然表達著對社會、人生、歷史……等生活形態的“史詩”性追求,但卻更加注重尋求獨特的視角對思想進行個人化的表述,進而“實現了從歷史的‘判斷性’向歷史的‘體驗性’、歷史的‘事件性’向歷史的‘過程性’,以及歷史的‘抽象性’向歷史的‘豐富性’的轉變。作家們沒有採取整體性的宏大‘歷史’視角,而是從微觀的個人化‘視點’切入,以點寫面,把歷史改寫成了零碎的、具體可感的人生片斷與人生經驗。這樣,宏大的政治歷史場景被處理成了具體的生命境遇與生存境遇,這既賦予了‘歷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還原了歷史的原生態”。
項小米的《英雄無語》以孫女“我”的主觀視角來追尋爺爺和奶奶各自的生命軌跡和情感歷程,通過對爺爺、奶奶各自生活和內心隱秘的探尋營造了一段波瀾壯闊、奇崛弔詭的歷史;而通過“我”對歷史材料的發掘,對爺爺、奶奶各自情感和人格的想像性重構,又勾勒出了一幅幾近完整的、極富傳奇色彩的紅色革命歷史。這種對歷史的個人性、限制性、想像性的重構徹底顛覆了以往軍旅長篇小說對革命歷史客觀性、全景性、確定性的敘事,顯露出現實語境下新一代軍旅長篇小說作家視野中,革命歷史的奇幻瑰麗和變化莫測。《英雄無語》的故事結構極具形式美感,三條線索穿插並行:現實時空中,獨居女人“我”和申建、喬納圍繞著對一首客家歌謠的考證而產生的情感糾葛;“我”對於家族史,對於爺爺、奶奶的悲歡離合的興趣和追蹤,發掘和敘述;“我”對客家文化的研究和闡釋。現實時空中“我”的生活和感情經歷與歷史時空中爺爺奶奶的命運遭際形成了關照和同構關係,對爺爺、奶奶人生命運的想像性敘述因為融人了“我”的情緒和感情而顯得鮮活而生動,爺爺、奶奶悲喜命運的逐步清晰也對“我”的現實生活和心靈世界構成了某種刺激和壓抑。在歷史和現實故事線索之間躁動不安的客家文化的闡釋,則穿越了父輩們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阻隔,在祖輩和孫輩之間架起了一座精神和文化彌合的橋樑。《英雄無語》各自獨立的故事線索看似破碎,“我”的限制性視角看似單薄,但“我”與爺爺奶奶及“每”對話性關係的形成,極大地擴展了小說的時空容量,而歷史與現實時空的平等敘事更使得小說的復調特性得以確立。作品沒有設定一種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而是存在著多重互動作用的思想立場:作者並沒有對爺爺進行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將“我”與其他人物一起置入真切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下,探索人性的豐富與駁雜,從而更加切近歷史的本質和真實。一、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的文體自覺和技術創新
中國當代軍旅長篇小說與“現實主義”有著太多的聯繫與錯綜複雜的矛盾糾葛。建國後,“毛澤東同志提倡我們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兩結合”理論強力影響、規約了建國後,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創作,並在其後相當長的時期里持續發揮著作用。進入新時期的軍旅文學是以人道主義的張揚和現實主義的恢復為基本特徵的。急切的表達和說教欲望使得“主題先行,思想大於形象”成為這一時期軍旅文學的集體症候。陳舊的文學觀念、傳統的思維定式及審美心理積澱,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軍旅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力量與藝術感染力。進入90年代,“作家們力圖遵循著現實主義文學嚴格地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表現生活的原則,以豐富、細膩的筆觸表現生活中的各種形態,並不斷地向著人物的心靈深處拓展;但是,過於強烈的‘主題意向’又使得作家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意識到的思想內容生硬地灌注到作品中,而沒有能夠融會到藝術形象的塑造中”。總體而言,軍旅文學與現實主義的關係始終處於一種焦慮和緊張的狀態。在軍旅文學史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創作領域裡,現實主義成為了一個被數度改寫並隱含了多種似是而非的文學觀念的模糊概念,但“寫真實”的原則與對現實生活的熱情追求始終被軍旅長篇小說寫作奉為圭臬。現實主義在表現和再現歷史的深廣度上,揭示歷史本質方面確實有著其他文學流派所不具備的優勢,然而,隨著時代和文學的發展,現實主義文學自身也要尋求更新換代。而此種自我完善並不是簡單的由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觀念顛覆和消解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就能夠完成的。我以為現實主義與其他文學思潮和流派之間本來就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作為藝術地關照並反映世界的方式,現實主義對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文學思潮並不具備天然的拒斥力,相反倒是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和性。而當代軍旅文學,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之所以長期處於對現實主義的困惑與焦慮之中,我想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在於“道”與“技”的疏離。藝術觀念、藝術思維的僵化落後,技術素養的偏低和語言能力的欠缺束縛著軍旅長篇小說作家,使得他們無法展開靈動的翅膀向現實主義的浩瀚天空飛翔。然而,在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中我驚喜地發現,隨著現實主義和技術主義的雙重祛魅,現實主義的“道”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技”正在發生自然的融合,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向我們展示了“兼技並道”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突出地表現為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作家對長篇小說文體的自覺和進行技術“創新”的努力。
“在西方文體學家看來,文體其實就是語言,文體的本質不過是一個表達方式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言說的問題。就長篇小說的文體而言,問題可能遠非這么簡單,在語言背後其實還隱藏著許多深層的藝術問題。作家的思維與藝術觀念、時代的審美風尚等等都會對長篇小說的文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文體絕不是一個平面的‘語言’問題。而是一個深邃、複雜、立體、多維的系統結構,它牽涉到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結構、修辭、敘述、描寫等幾乎所有方面。”。作為一種重型文體,追求思想和意義的“深度”自然是軍旅長篇小說題中應有之義。20世紀90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作家已經主動而自覺地完成了思想主體從集體性的、階級性的“大我”向個體性的“自我”的轉化。作家們在作品中儘管依然表達著對社會、人生、歷史……等生活形態的“史詩”性追求,但卻更加注重尋求獨特的視角對思想進行個人化的表述,進而“實現了從歷史的‘判斷性’向歷史的‘體驗性’、歷史的‘事件性’向歷史的‘過程性’,以及歷史的‘抽象性’向歷史的‘豐富性’的轉變。作家們沒有採取整體性的宏大‘歷史’視角,而是從微觀的個人化‘視點’切入,以點寫面,把歷史改寫成了零碎的、具體可感的人生片斷與人生經驗。這樣,宏大的政治歷史場景被處理成了具體的生命境遇與生存境遇,這既賦予了‘歷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還原了歷史的原生態”。
項小米的《英雄無語》以孫女“我”的主觀視角來追尋爺爺和奶奶各自的生命軌跡和情感歷程,通過對爺爺、奶奶各自生活和內心隱秘的探尋營造了一段波瀾壯闊、奇崛弔詭的歷史;而通過“我”對歷史材料的發掘,對爺爺、奶奶各自情感和人格的想像性重構,又勾勒出了一幅幾近完整的、極富傳奇色彩的紅色革命歷史。這種對歷史的個人性、限制性、想像性的重構徹底顛覆了以往軍旅長篇小說對革命歷史客觀性、全景性、確定性的敘事,顯露出現實語境下新一代軍旅長篇小說作家視野中,革命歷史的奇幻瑰麗和變化莫測。《英雄無語》的故事結構極具形式美感,三條線索穿插並行:現實時空中,獨居女人“我”和申建、喬納圍繞著對一首客家歌謠的考證而產生的情感糾葛;“我”對於家族史,對於爺爺、奶奶的悲歡離合的興趣和追蹤,發掘和敘述;“我”對客家文化的研究和闡釋。現實時空中“我”的生活和感情經歷與歷史時空中爺爺奶奶的命運遭際形成了關照和同構關係,對爺爺、奶奶人生命運的想像性敘述因為融人了“我”的情緒和感情而顯得鮮活而生動,爺爺、奶奶悲喜命運的逐步清晰也對“我”的現實生活和心靈世界構成了某種刺激和壓抑。在歷史和現實故事線索之間躁動不安的客家文化的闡釋,則穿越了父輩們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阻隔,在祖輩和孫輩之間架起了一座精神和文化彌合的橋樑。《英雄無語》各自獨立的故事線索看似破碎,“我”的限制性視角看似單薄,但“我”與爺爺奶奶及“每”對話性關係的形成,極大地擴展了小說的時空容量,而歷史與現實時空的平等敘事更使得小說的復調特性得以確立。作品沒有設定一種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而是存在著多重互動作用的思想立場:作者並沒有對爺爺進行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將“我”與其他人物一起置入真切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下,探索人性的豐富與駁雜,從而更加切近歷史的本質和真實。
中國當代軍旅長篇小說與“現實主義”有著太多的聯繫與錯綜複雜的矛盾糾葛。建國後,“毛澤東同志提倡我們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兩結合”理論強力影響、規約了建國後,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創作,並在其後相當長的時期里持續發揮著作用。進入新時期的軍旅文學是以人道主義的張揚和現實主義的恢復為基本特徵的。急切的表達和說教欲望使得“主題先行,思想大於形象”成為這一時期軍旅文學的集體症候。陳舊的文學觀念、傳統的思維定式及審美心理積澱,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軍旅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力量與藝術感染力。進入90年代,“作家們力圖遵循著現實主義文學嚴格地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表現生活的原則,以豐富、細膩的筆觸表現生活中的各種形態,並不斷地向著人物的心靈深處拓展;但是,過於強烈的‘主題意向’又使得作家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意識到的思想內容生硬地灌注到作品中,而沒有能夠融會到藝術形象的塑造中”。總體而言,軍旅文學與現實主義的關係始終處於一種焦慮和緊張的狀態。在軍旅文學史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創作領域裡,現實主義成為了一個被數度改寫並隱含了多種似是而非的文學觀念的模糊概念,但“寫真實”的原則與對現實生活的熱情追求始終被軍旅長篇小說寫作奉為圭臬。現實主義在表現和再現歷史的深廣度上,揭示歷史本質方面確實有著其他文學流派所不具備的優勢,然而,隨著時代和文學的發展,現實主義文學自身也要尋求更新換代。而此種自我完善並不是簡單的由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觀念顛覆和消解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就能夠完成的。我以為現實主義與其他文學思潮和流派之間本來就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作為藝術地關照並反映世界的方式,現實主義對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文學思潮並不具備天然的拒斥力,相反倒是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和性。而當代軍旅文學,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之所以長期處於對現實主義的困惑與焦慮之中,我想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在於“道”與“技”的疏離。藝術觀念、藝術思維的僵化落後,技術素養的偏低和語言能力的欠缺束縛著軍旅長篇小說作家,使得他們無法展開靈動的翅膀向現實主義的浩瀚天空飛翔。然而,在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中我驚喜地發現,隨著現實主義和技術主義的雙重祛魅,現實主義的“道”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技”正在發生自然的融合,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向我們展示了“兼技並道”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突出地表現為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作家對長篇小說文體的自覺和進行技術“創新”的努力。
“在西方文體學家看來,文體其實就是語言,文體的本質不過是一個表達方式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言說的問題。就長篇小說的文體而言,問題可能遠非這么簡單,在語言背後其實還隱藏著許多深層的藝術問題。作家的思維與藝術觀念、時代的審美風尚等等都會對長篇小說的文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文體絕不是一個平面的‘語言’問題。而是一個深邃、複雜、立體、多維的系統結構,它牽涉到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結構、修辭、敘述、描寫等幾乎所有方面。”。作為一種重型文體,追求思想和意義的“深度”自然是軍旅長篇小說題中應有之義。20世紀90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作家已經主動而自覺地完成了思想主體從集體性的、階級性的“大我”向個體性的“自我”的轉化。作家們在作品中儘管依然表達著對社會、人生、歷史……等生活形態的“史詩”性追求,但卻更加注重尋求獨特的視角對思想進行個人化的表述,進而“實現了從歷史的‘判斷性’向歷史的‘體驗性’、歷史的‘事件性’向歷史的‘過程性’,以及歷史的‘抽象性’向歷史的‘豐富性’的轉變。作家們沒有採取整體性的宏大‘歷史’視角,而是從微觀的個人化‘視點’切入,以點寫面,把歷史改寫成了零碎的、具體可感的人生片斷與人生經驗。這樣,宏大的政治歷史場景被處理成了具體的生命境遇與生存境遇,這既賦予了‘歷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還原了歷史的原生態”。
項小米的《英雄無語》以孫女“我”的主觀視角來追尋爺爺和奶奶各自的生命軌跡和情感歷程,通過對爺爺、奶奶各自生活和內心隱秘的探尋營造了一段波瀾壯闊、奇崛弔詭的歷史;而通過“我”對歷史材料的發掘,對爺爺、奶奶各自情感和人格的想像性重構,又勾勒出了一幅幾近完整的、極富傳奇色彩的紅色革命歷史。這種對歷史的個人性、限制性、想像性的重構徹底顛覆了以往軍旅長篇小說對革命歷史客觀性、全景性、確定性的敘事,顯露出現實語境下新一代軍旅長篇小說作家視野中,革命歷史的奇幻瑰麗和變化莫測。《英雄無語》的故事結構極具形式美感,三條線索穿插並行:現實時空中,獨居女人“我”和申建、喬納圍繞著對一首客家歌謠的考證而產生的情感糾葛;“我”對於家族史,對於爺爺、奶奶的悲歡離合的興趣和追蹤,發掘和敘述;“我”對客家文化的研究和闡釋。現實時空中“我”的生活和感情經歷與歷史時空中爺爺奶奶的命運遭際形成了關照和同構關係,對爺爺、奶奶人生命運的想像性敘述因為融人了“我”的情緒和感情而顯得鮮活而生動,爺爺、奶奶悲喜命運的逐步清晰也對“我”的現實生活和心靈世界構成了某種刺激和壓抑。在歷史和現實故事線索之間躁動不安的客家文化的闡釋,則穿越了父輩們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阻隔,在祖輩和孫輩之間架起了一座精神和文化彌合的橋樑。《英雄無語》各自獨立的故事線索看似破碎,“我”的限制性視角看似單薄,但“我”與爺爺奶奶及“每”對話性關係的形成,極大地擴展了小說的時空容量,而歷史與現實時空的平等敘事更使得小說的復調特性得以確立。作品沒有設定一種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而是存在著多重互動作用的思想立場:作者並沒有對爺爺進行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將“我”與其他人物一起置入真切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下,探索人性的豐富與駁雜,從而更加切近歷史的本質和真實。一、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的文體自覺和技術創新
中國當代軍旅長篇小說與“現實主義”有著太多的聯繫與錯綜複雜的矛盾糾葛。建國後,“毛澤東同志提倡我們的文學應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兩結合”理論強力影響、規約了建國後,特別是五六十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創作,並在其後相當長的時期里持續發揮著作用。進入新時期的軍旅文學是以人道主義的張揚和現實主義的恢復為基本特徵的。急切的表達和說教欲望使得“主題先行,思想大於形象”成為這一時期軍旅文學的集體症候。陳舊的文學觀念、傳統的思維定式及審美心理積澱,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軍旅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力量與藝術感染力。進入90年代,“作家們力圖遵循著現實主義文學嚴格地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表現生活的原則,以豐富、細膩的筆觸表現生活中的各種形態,並不斷地向著人物的心靈深處拓展;但是,過於強烈的‘主題意向’又使得作家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意識到的思想內容生硬地灌注到作品中,而沒有能夠融會到藝術形象的塑造中”。總體而言,軍旅文學與現實主義的關係始終處於一種焦慮和緊張的狀態。在軍旅文學史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創作領域裡,現實主義成為了一個被數度改寫並隱含了多種似是而非的文學觀念的模糊概念,但“寫真實”的原則與對現實生活的熱情追求始終被軍旅長篇小說寫作奉為圭臬。現實主義在表現和再現歷史的深廣度上,揭示歷史本質方面確實有著其他文學流派所不具備的優勢,然而,隨著時代和文學的發展,現實主義文學自身也要尋求更新換代。而此種自我完善並不是簡單的由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觀念顛覆和消解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就能夠完成的。我以為現實主義與其他文學思潮和流派之間本來就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作為藝術地關照並反映世界的方式,現實主義對浪漫主義、自然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等文學思潮並不具備天然的拒斥力,相反倒是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和性。而當代軍旅文學,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之所以長期處於對現實主義的困惑與焦慮之中,我想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在於“道”與“技”的疏離。藝術觀念、藝術思維的僵化落後,技術素養的偏低和語言能力的欠缺束縛著軍旅長篇小說作家,使得他們無法展開靈動的翅膀向現實主義的浩瀚天空飛翔。然而,在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中我驚喜地發現,隨著現實主義和技術主義的雙重祛魅,現實主義的“道”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技”正在發生自然的融合,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向我們展示了“兼技並道”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突出地表現為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說作家對長篇小說文體的自覺和進行技術“創新”的努力。
“在西方文體學家看來,文體其實就是語言,文體的本質不過是一個表達方式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言說的問題。就長篇小說的文體而言,問題可能遠非這么簡單,在語言背後其實還隱藏著許多深層的藝術問題。作家的思維與藝術觀念、時代的審美風尚等等都會對長篇小說的文體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文體絕不是一個平面的‘語言’問題。而是一個深邃、複雜、立體、多維的系統結構,它牽涉到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結構、修辭、敘述、描寫等幾乎所有方面。”。作為一種重型文體,追求思想和意義的“深度”自然是軍旅長篇小說題中應有之義。20世紀90年代的軍旅長篇小說作家已經主動而自覺地完成了思想主體從集體性的、階級性的“大我”向個體性的“自我”的轉化。作家們在作品中儘管依然表達著對社會、人生、歷史……等生活形態的“史詩”性追求,但卻更加注重尋求獨特的視角對思想進行個人化的表述,進而“實現了從歷史的‘判斷性’向歷史的‘體驗性’、歷史的‘事件性’向歷史的‘過程性’,以及歷史的‘抽象性’向歷史的‘豐富性’的轉變。作家們沒有採取整體性的宏大‘歷史’視角,而是從微觀的個人化‘視點’切入,以點寫面,把歷史改寫成了零碎的、具體可感的人生片斷與人生經驗。這樣,宏大的政治歷史場景被處理成了具體的生命境遇與生存境遇,這既賦予了‘歷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還原了歷史的原生態”。
項小米的《英雄無語》以孫女“我”的主觀視角來追尋爺爺和奶奶各自的生命軌跡和情感歷程,通過對爺爺、奶奶各自生活和內心隱秘的探尋營造了一段波瀾壯闊、奇崛弔詭的歷史;而通過“我”對歷史材料的發掘,對爺爺、奶奶各自情感和人格的想像性重構,又勾勒出了一幅幾近完整的、極富傳奇色彩的紅色革命歷史。這種對歷史的個人性、限制性、想像性的重構徹底顛覆了以往軍旅長篇小說對革命歷史客觀性、全景性、確定性的敘事,顯露出現實語境下新一代軍旅長篇小說作家視野中,革命歷史的奇幻瑰麗和變化莫測。《英雄無語》的故事結構極具形式美感,三條線索穿插並行:現實時空中,獨居女人“我”和申建、喬納圍繞著對一首客家歌謠的考證而產生的情感糾葛;“我”對於家族史,對於爺爺、奶奶的悲歡離合的興趣和追蹤,發掘和敘述;“我”對客家文化的研究和闡釋。現實時空中“我”的生活和感情經歷與歷史時空中爺爺奶奶的命運遭際形成了關照和同構關係,對爺爺、奶奶人生命運的想像性敘述因為融人了“我”的情緒和感情而顯得鮮活而生動,爺爺、奶奶悲喜命運的逐步清晰也對“我”的現實生活和心靈世界構成了某種刺激和壓抑。在歷史和現實故事線索之間躁動不安的客家文化的闡釋,則穿越了父輩們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阻隔,在祖輩和孫輩之間架起了一座精神和文化彌合的橋樑。《英雄無語》各自獨立的故事線索看似破碎,“我”的限制性視角看似單薄,但“我”與爺爺奶奶及“每”對話性關係的形成,極大地擴展了小說的時空容量,而歷史與現實時空的平等敘事更使得小說的復調特性得以確立。作品沒有設定一種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而是存在著多重互動作用的思想立場:作者並沒有對爺爺進行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將“我”與其他人物一起置入真切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下,探索人性的豐富與駁雜,從而更加切近歷史的本質和真實。
序言
中國現代文學發軔於本世紀初葉,同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共命運,在內憂外患,雷電風霜,刀兵血火中寫下完全不同於過去的嶄新篇章。現代文學繼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長豐厚的文學遺產,順乎20世紀的歷史潮流和時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內涵和全新的文體(無論是小說、散文、詩歌、劇本以至評論)建立起全新的文學。將近一百年來,經由幾代作家揮灑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後繼,披荊斬棘,以艱難的實踐辛勤澆灌、耕耘、開拓、奉獻,文學的萬里蒼穹中繁星熠熠,雲蒸霞蔚,名家輩出,佳作如潮,構成前所未有的世紀輝煌,並且躋身於世界文學之林。80年代以來,以改革開放為主要標誌的歷史新時期,推動文學又一次春潮洶湧,駿馬奔騰。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斕的新作,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畫廊最後增添了濃筆重彩的畫卷。當此即將告別本世紀跨入新世紀之時,回首百年,不免五味雜陳,萬感交集,卻也從內心湧起一陣陣欣喜和自豪。我們的文學事業在歷經風雨坎坷之後,終於進入呈露無限生機、無窮希望的天地,儘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鋪滿鮮花的康莊大道。
綠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帶著滿身朝露的新人嶄露頭角,自然是我們希冀而且高興的景象。然而,我們也看到,由於種種未曾預料、而且主要並非來自作者本身的因由,還有為數不少的年輕作者不一定都有順利地脫穎而出的機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為出書艱難所阻滯。出版渠道不順,文化市場不善,使他們失去許多機遇。儘管他們發表過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還獲了獎,顯示了自己的文學才能和創作潛力,卻仍然無緣出第一本書。也許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和體制轉換期中不可避免的暫時缺陷,卻也不能不對文學事業的健康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因而也不能不使許多關懷文學的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嘆息,焦慮不安。固然,出第一本書時間的遲早,對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長不會也不應該成為關鍵的或決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及早地跨過這一步呢?
於是,遂有這套“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構想和舉措。
中華文學基金會有志於發展文學事業、為青年作者服務,已有多時。如今幸有熱心人士贊助,得以圓了這個夢。瞻望21世紀,漫漫長途,上下求索,路還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也許可以看作是文學上的“希望工程”。但它與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貧濟困,也並非照顧“老少邊窮”地區,而是著眼於為取得優異成績的青年文學作者搭橋鋪路。有助於他們順利前行,在未來的歲月中寫出更多的好作品,我們想起本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魯迅先生先後編印《未名叢刊》和“奴隸叢書”,扶攜一些青年小說家和翻譯家登上文壇;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學叢刊》,更是不間斷地連續出了一百餘本,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當時青年作家的處女作,而他們在其後數十年中都成為文學大軍中的中堅人物;茅盾、葉聖陶等先生,都曾為青年作者的出現和成長花費心血,不遺餘力。前輩們關懷培育文壇新人為促進現代文學的繁榮所作出的業績,是永遠不能抹煞的。當年得到過他們雨露恩澤的後輩作家,直到鬢髮蒼蒼,還深深銘記著難忘的隆情厚誼。六十年後,我們今天依然以他們為光輝的楷模,努力遵循他們的腳印往前走去。
開始為叢書定名的時候,我們再三斟酌過。我們明確地認識到這項文學事業的“希望工程”是屬於未來世紀的。它也許還顯稚嫩,卻是前程無限。但是不是稱之為“文學之星”,且是tt21世紀文學之星”?不免有些躊躇。近些年來,明星太多太濫,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無一不可稱星。星光閃爍,五彩繽紛,變幻莫測,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憑風翻雲卷,光芒依舊;但也有為時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閃即逝,或許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來、炒出來的。在人們心目中,明星漸漸跌價,以至成為嘲諷調侃的對象。我們這項嚴肅認真的事業是否還要擠進繁雜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這一批青年作家,他們真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星嗎?
當我們陸續讀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協及其他方面推薦的新人作品,反覆閱讀、醞釀、評議、爭論,最後從中慎重遴選出叢書入選作品之後,忐忑的心終於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輕快愉悅之感。“他們真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星嗎?”能的!我們可以肯定地、並不誇張地回答:這些作者,儘管有的目前還處在走向成熟的階段,但他們完全可以接受文學之星的稱號而無愧色。他們有的來自市井,有的來自鄉村,有的來自邊陲山野,有的來自城市底層。他們的筆下,蕩漾著多姿多彩、雲譎波詭的現實浪潮,涌動著新時期芸芸眾生的喜怒哀傷,也流淌著作者自己的心靈悸動、幻夢、煩惱和憧憬。他們都不曾出過書,但是他們的生活底蘊、文學才華和寫作功力,可以媲美當年“奴隸叢書”的年輕小說家和《文學叢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當今某些已經出書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兩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們是文學之星。這一批青年作家,同當代不少傑出的青年作家一樣,都可能成為21世紀文學的啟明星,升起在世紀之初。啟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東方天空出現時,人們稱它為啟明星,黃昏時候在西方天空出現時,人們稱它為長庚星。兩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對遙遠的天體賦予美好的傳說,寄託綺思遐想,但對現實中的星,卻是完全可以預期洞見的。本叢書將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長江潮湧,奔流不息。其中出現趕上並且超過前人的文學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嗎?
歲月悠悠,銀河燦燦。仰望星空,心緒難平!
綠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帶著滿身朝露的新人嶄露頭角,自然是我們希冀而且高興的景象。然而,我們也看到,由於種種未曾預料、而且主要並非來自作者本身的因由,還有為數不少的年輕作者不一定都有順利地脫穎而出的機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為出書艱難所阻滯。出版渠道不順,文化市場不善,使他們失去許多機遇。儘管他們發表過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還獲了獎,顯示了自己的文學才能和創作潛力,卻仍然無緣出第一本書。也許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和體制轉換期中不可避免的暫時缺陷,卻也不能不對文學事業的健康發展產生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因而也不能不使許多關懷文學的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嘆息,焦慮不安。固然,出第一本書時間的遲早,對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長不會也不應該成為關鍵的或決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現象也屢見不鮮,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及早地跨過這一步呢?
於是,遂有這套“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構想和舉措。
中華文學基金會有志於發展文學事業、為青年作者服務,已有多時。如今幸有熱心人士贊助,得以圓了這個夢。瞻望21世紀,漫漫長途,上下求索,路還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也許可以看作是文學上的“希望工程”。但它與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貧濟困,也並非照顧“老少邊窮”地區,而是著眼於為取得優異成績的青年文學作者搭橋鋪路。有助於他們順利前行,在未來的歲月中寫出更多的好作品,我們想起本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魯迅先生先後編印《未名叢刊》和“奴隸叢書”,扶攜一些青年小說家和翻譯家登上文壇;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學叢刊》,更是不間斷地連續出了一百餘本,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當時青年作家的處女作,而他們在其後數十年中都成為文學大軍中的中堅人物;茅盾、葉聖陶等先生,都曾為青年作者的出現和成長花費心血,不遺餘力。前輩們關懷培育文壇新人為促進現代文學的繁榮所作出的業績,是永遠不能抹煞的。當年得到過他們雨露恩澤的後輩作家,直到鬢髮蒼蒼,還深深銘記著難忘的隆情厚誼。六十年後,我們今天依然以他們為光輝的楷模,努力遵循他們的腳印往前走去。
開始為叢書定名的時候,我們再三斟酌過。我們明確地認識到這項文學事業的“希望工程”是屬於未來世紀的。它也許還顯稚嫩,卻是前程無限。但是不是稱之為“文學之星”,且是tt21世紀文學之星”?不免有些躊躇。近些年來,明星太多太濫,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無一不可稱星。星光閃爍,五彩繽紛,變幻莫測,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憑風翻雲卷,光芒依舊;但也有為時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閃即逝,或許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來、炒出來的。在人們心目中,明星漸漸跌價,以至成為嘲諷調侃的對象。我們這項嚴肅認真的事業是否還要擠進繁雜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這一批青年作家,他們真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星嗎?
當我們陸續讀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協及其他方面推薦的新人作品,反覆閱讀、醞釀、評議、爭論,最後從中慎重遴選出叢書入選作品之後,忐忑的心終於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輕快愉悅之感。“他們真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星嗎?”能的!我們可以肯定地、並不誇張地回答:這些作者,儘管有的目前還處在走向成熟的階段,但他們完全可以接受文學之星的稱號而無愧色。他們有的來自市井,有的來自鄉村,有的來自邊陲山野,有的來自城市底層。他們的筆下,蕩漾著多姿多彩、雲譎波詭的現實浪潮,涌動著新時期芸芸眾生的喜怒哀傷,也流淌著作者自己的心靈悸動、幻夢、煩惱和憧憬。他們都不曾出過書,但是他們的生活底蘊、文學才華和寫作功力,可以媲美當年“奴隸叢書”的年輕小說家和《文學叢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當今某些已經出書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兩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們是文學之星。這一批青年作家,同當代不少傑出的青年作家一樣,都可能成為21世紀文學的啟明星,升起在世紀之初。啟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東方天空出現時,人們稱它為啟明星,黃昏時候在西方天空出現時,人們稱它為長庚星。兩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對遙遠的天體賦予美好的傳說,寄託綺思遐想,但對現實中的星,卻是完全可以預期洞見的。本叢書將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長江潮湧,奔流不息。其中出現趕上並且超過前人的文學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嗎?
歲月悠悠,銀河燦燦。仰望星空,心緒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