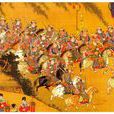基本介紹
作品原文,注釋譯文,詞語注釋,作品譯文,作品鑑賞,作品解讀一,作品解讀二,
作品原文
酒泉子①
每見惶惶,隊隊雄軍驚御輦。②
驀街穿巷犯皇宮,只擬奪九重。③
長槍短劍如亂麻,爭奈失計無投竄。④
金箱玉印自攜將,任他亂芬芳。⑤
注釋譯文
詞語注釋
②此句“每見惶惶,隊隊雄軍驚御輦”一作“每見惶惶隊隊,雄軍驚御輦”。
句中“惶惶”,猶“煌煌”。鮮明,明亮貌。詞中指起義軍衣甲鮮明。“御輦”,指皇帝的車駕;
③句中“驀”,原意為突然,詞中做超越講;“驀街穿巷”即過街穿巷。
④句中“九重”,即九重城闕,是帝王所居之處;“爭奈”,怎奈;
⑤句中“將”,音jiāng,攜帶。“芬芳”,指皇室貴族的子女們,或言指繁華的京城皇宮。
作品譯文
只見那一隊隊義軍衣甲鮮明, 雄壯的軍威使皇帝膽顫心驚。
過大街穿小巷直衝禁城皇宮,
一心要奪帝位推到昏庸朝廷。
長槍短劍亂紛紛干戈多如林,
天子無良策倉皇逃竄出皇宮。
攜帶著金箱玉印匆匆去逃命,
聽任他把金枝玉葉踏為灰塵。
作品鑑賞
作品解讀一
《酒泉子·每見惶惶》上片著重寫農民起義軍揭竿而起,大軍挺進京城長安時的威武雄壯氣勢。百萬雄軍長驅直入,勢如破竹,一直打進京城長安,驚亂了宮中養尊處優、驕奢淫逸的皇帝的平靜生活,使王公貴族惶惶不可終日。但見支支雄壯的隊伍,越過大街,穿過小巷,直逼皇家的宮牆。他們捨得一身剮,定要把無道的昏君拉下馬。 黃巢起義入長安
黃巢起義入長安
 黃巢起義入長安
黃巢起義入長安下片側重表現在神勇的義軍面前,唐朝官僚大臣與封建皇帝驚慌失措的狼狽相,從而反襯出義軍的勇猛頑強以及洋洋自得的情狀。在槍舞劍揮之中,唐朝君臣膽戰心驚,紛亂如麻。情急之下,更是沒個主張,惶惶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四處潰竄,狼狽不堪。義軍終於攻占了長安,贓銀細軟全帶上,金箱玉印都拿走。作者立場堅定,愛憎分明,以“隊隊雄軍”讚頌義軍,以對“御輦”的“驚”,對“皇宮”的“犯”,對“九重”的“奪”,熱情地肯定了義軍的正義行動。而對唐朝的豪門望族、王公大臣及其主子皇帝,作者則表現出明顯的貶抑與憎恨,書寫其見義軍的心理狀態,用的是“惶惶”;描摹官僚潰竄,用的是“失計”、“無投竄”。通過這些詞句,作者頌揚起義軍的強大聲勢,嘲笑官僚貴族的慌亂狼狽。正是在這鮮明的對比之中,顯示出作者鮮明的政治傾向。
用詞的形式來寫農民起義的內容,是較為少見的。民間文學是一個豐富的寶庫,其中就珍藏著類似這樣的寶貴遺產。詞作語言凝練,文字樸實,風格豪壯,具有史詩的價值。
作品解讀二
這闋詞高國藩教授在他的《敦煌曲子詞欣賞》中說:“這首詞通篇以一個旁邊觀者的身份讚揚了農民起義的行為,字裡行間對農民起義軍表示同情,並對起義的最終失敗表示無比惋惜。”這完全錯會了詞意!高教授在上片說得很對。他說:“首句表現整個封建王朝惶惶不可終日,繼則以‘驚御輦’、‘犯皇宮’、奪九重”,表現一層高過一層的起義巨大的力量,從‘惶’到‘驚’,再從‘犯’最終到‘奪’,此四字精煉地表現了農民起義從暴動到勝利的全過程。”這一段說得完全對。但是他說:“下片,寫農民起義的失敗。”則是又推翻了他自己所說的“從暴動到勝利”的論斷,反而為失敗了!他是如何將此詞腰斬而又自圓其說的呢?他得出“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歸結為一個字,即‘亂’。”殊不知下闋是離不開上闋的。上闋所表現的既是農民起義軍已“犯皇宮,只擬奪九重”了。“九重”,指皇位,“擬奪”也就是說目的是如此,但尚未奪到。雖未奪到,但那“長槍短劍如麻”其氣勢之威武,也就足夠使那些皇子王孫、公侯將相們“無投竄”的了,則整個皇城又焉得不亂!但這“亂”說是起義軍造成的可,若說是起義軍之亂,則似乎於詞無據!“長槍短劍如麻”,只是言其長槍短劍之多,俗語說:“麻在林中,不扶自直。”“直”則不亂。所以義軍尚“長槍短劍”其聚也“如麻”,則這個“亂”,就肯定不是起義軍的亂,而是整個皇室以至皇城之亂了。
高教授說“失敗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失計’,即起義的計畫欠妥當。……所以下片次句的全意為:怎奈計畫欠妥當,不知道應去向何方?”“向何方”?義軍的方向不是很明確的么?即“驀街穿巷犯皇宮,只擬奪九重”。而且已造成了京師的大“亂”!“無投竄”是說沒有地方逃命!那么這裡“無投竄”到底指的是誰?若說是義軍則為不通,因為義軍是攻進來的,“驀街穿巷犯皇宮,只擬奪九重”,且“隊隊雄軍驚御輦”,整飭而又威武,不存在“無投竄”。即令是如高教授說的是失敗了,進攻不成,退卻而已,也與“無投竄”無關。“無投竄”者,如沒頭之蒼蠅,難道義軍攻不進城,也不會“鳴金收兵”,照原路退回的嗎?可見這句實指守城的官兵,以其無計退敵,及待城破了,義軍攻了進來,這才慌得不知往哪裡躲的了。
最妙的是高教授解釋“金箱玉印自攜將”說:“‘金箱’指皇宮裡的金銀財寶,‘玉印’指皇帝的玉印,即玉璽。……‘自’指自然。……‘攜將’即意為拿走,意思是皇宮裡的金銀財寶和代表王朝的印把子,都給拿走了。……現在印把子從皇帝之手轉到了農民起義軍之手,”顯然,高教授認為“金箱玉印自攜將”中的“自”是“自然”,即(農民起義軍)自然地拿著。這種解釋既勉強,又不通。其實這句中的“自”就是本義:自己、親自之意。即在慌亂之中,誰的財物,誰的印信,只有自己抱著跑;因為,一來沒了親信,慌亂中,都各顧各的逃命去了,無人可使,二來縱有親信也不能信,這些“金箱玉印”原是比自己的命還要貴重的,更不能給了別人拿著,怕他抱跑了,所以只有“自攜將”,即是說只有自己抱著跑。這其實是很淺白的句子,用不著去將“自”字曲解為什麼“自然”。之所以不得不如此用心的,蓋不如此,便說不通(如此了也沒有說通)是起義軍的失敗!為了自圓其說,也就顧不得字義之不通了!
最後“任他亂芬芳。”高教授說:“意思就是:管它亂紛紛成個啥模樣!這是進一步為農民起義軍奪了印把子叫好!……反正印把子已到手,金鑾殿已奪下,管它封建王朝亂成什麼樣子!”既說“下片,寫農民起義的失敗”,這裡又說農民起義“印把子已到手,金鑾殿已奪下”,則是皇朝業已推翻了,自己登基作皇帝了,其為成功也,孰莫大焉,何敗之有?這完全是前言不對後語,自相矛盾!高教授在這裡完全脫離了詞的文本亂說詞。上闋說得非常清楚:人家是“只擬奪九重”,“擬”者,打算、準備之辭也。而且也不過是“驚御輦”,即俗話說的“驚駕”而已,他何嘗說“印把子已到手,金鑾殿已奪下”?這又可證明所謂“自攜將”者,實在是印把子還是攜在人家的手上,並不在義軍的手中。至於這裡說的“任他亂芬芳”,則完全是指責皇室以及大臣們,這些有守土之責的官家老爺們,都自顧逃命去了,管不得他治下的城池及百姓們如何的。若說這指的是起義軍,則無異是說農民起義軍只顧了搶“金箱玉印”,只管自己發財,而對於人民,則“管它亂紛紛成個啥模樣!”,這豈非連土匪也不如的嘛,哪裡還是如高教授說的是什麼“總之,這是一曲農民起義的讚歌”?
其實這闋詞,上下非常一致,都是在歌頌農民起義軍:上闋寫的是寫起義軍的軍威,下闋寫的是在起義軍的攻打下,皇城一片混亂的情景!詞境非常一致而又愛憎分明。高教授之所以弄不清對象而將上下兩闋割裂了開來而又不能自圓其說的,主要還是沒有讀通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