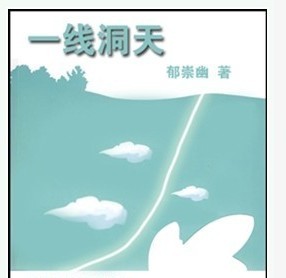郁崇幽,筆名,原名高艷飛,河南永城人。生於1987年,作家、時評人。現居北京,作品《一線洞天》等。郁崇幽小說作品情調憂鬱色彩濃厚,浪子情懷濃郁,現實意義不強,可讀性落了下乘。文句乾脆利落,造句頗有美感,亦多匠心獨運妙手偶得之筆,尚值讚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郁崇幽
- 出生地:河南永城
- 出生日期:1987年
- 原名:高艷飛
介紹,簡歷,代表作品,圖片,
介紹

例《一線洞天》第二十五章中:“我突然想起來念雲,在我找到洋曉影並且勸服她跟我一起回去的時候,洋曉影央我帶上念雲先回上海。念雲問我:“上海有很多的海是不是?”我說:“是的,很多很多海。””
據作者本人所說,《一線洞天》寫於2006年與2007年,仿安妮寶貝的痕跡較重,自己也不甚滿意,故而未版。大多數作品零散見於報端,迄今未出完整作品集。
簡歷
1987年生於河南省永城市,父為新疆建設兵團退役軍官,現歸鄉。2007年考入洛陽理工學院,主動退學去美。2010年出任北京某青春文學雜誌執行副主編,目前已離職,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低調生存。
代表作品
長篇小說:一線洞天
我在南京又待了兩個禮拜,終於說動了洋曉影,她答應跟我一起回去。但是她預定了兩張去上海的車票,要我帶著念雲先去徐家匯她的父母那裡。我問她為什麼不同去,她先是不說話,後來才指了指破敗的樓房說得處理了它們。
我欣喜的點了點頭,帶著念雲先行離開南京。離開之時,大雨依舊。
我抱著念雲登上大巴車,跟因從沾了水的玻璃窗看去顯得有些模糊的洋曉影揮手告別。洋曉影跟著大巴車慢慢的走著,接著小跑了起來。她的身影漸漸小了,終於消失不見。車子駛離南京市區,大雨打在樓房上的煙霧迅速把整個南京城喇糊習元隱沒,一切完結。
念雲趴在我的身旁,親吻我的臉,說:“叔叔,上海大嗎?”
我捏著她的臉,笑著說:“大,比南京大。”
“上海有很多海,是嗎?”
“嗯,是的,有很多很多海。”——第十一章《煙鎖重樓》
“念雲,我們回一趟南京好不好整芝笑項?”吃晚飯的時候,她在看一本兒童讀物,我這樣子問她。
“回南京?”念雲說,“去找媽媽?”
“是的,”我點點頭,“是去找媽媽。”
“你自己去好了。”念雲扔下書,鑽到沙發上。
“你也去,我們一起去。”我稍微的提高了一些聲音。
“不,我不回去。”念雲背對著我,斬釘截鐵的說。
“為什麼?我們是去找你媽媽,你媽媽!”我有些生氣了。
念雲坐起來,直勾勾的看著我,說:“我知道媽媽已經死了,你以為我真的什麼事情都不明白嗎?”
我低下頭,喃喃的說:“我……”
“你為什麼非要活在媽媽的夢裡面?”念雲咄咄逼人的質問我。
我跌坐在地板上。“好了,”我說,“好了,念雲,你別說了,你讓我感到害怕了。”
念雲甜甜的一笑,說:“叔叔別怕,你還有念雲呢。”——第十七章《阿soul的悲情》
詩集:天山下的木房子
在天山下,
我有一座木房子,
以森林為友,
以草原為鄰。
在乃戒嬸歷史行走之前,
我在這裡蓋下了這座木房子。
用我的骨,搭成支架,
用我的毛髮,搭成肯去料屋蓬。
在旬葛羅漫山的懷抱里,
草和木斷囑戰,樹和花,鳥和獸,
是安詳生存的居民,
挺拔的白樺和雲杉,是守衛的士兵。
我從第四紀冰川前的七月來,
在天邊尋找失散的情人。
那清澈幽深的天池,
那旖旎的青山雪峰,
那隆起的古冰磧壠,
那細碎的冰川漂礫,
那化名雪海的博格達,
而你,而你,悄悄的駐足在哪裡?
我建一座木房子,
用盡一生的精力和魂靈,
卻不曾有一個凡間的人居住。
采一朵塔格依力斯,
戴在麋鹿的頭上;
采一朵野薔薇,
戴在猞猁的頭上;
采一朵定痛的天仙子,
在我踏過雪線之前,
輕輕的插在鬢髮之後。
另有多篇時事評論及散文發表於《新京報》、《齊魯晚報》、《牡丹》等報刊雜誌。其中《小樓一夜聽春雨》一文,清新雋永,於樸素中見灑脫超然,是一篇難得的散文佳作。
“這深情是不為人知的,萬物皆有情,情到濃時卻轉薄。秋雨下的不緊不慢,像一個慢性子的人,自顧自在自己的世界裡遊蕩,全然不知別人心裡的感受。晚起的居民站在自家屋檐下,踮著腳尖往天上看,看雨是否會停下來。從他們的面目上,是看不出結果的,不過大致可以推算出來。若瞧得他們面上沒有什麼表情,或者略有欣喜,便知秋雨正慢慢止歇;反之,只消站在原處片刻,就會看到原本踮腳看天的人披著蓑衣穿著高底的鞋子急匆匆出門去。
所以諒灶趨,假若急著辦事的話,是不宜等待秋雨止歇的。秋雨最是連綿,由著它的性子,怕是要下滿整個秋季方肯罷休。最讓人著惱的是,眼看著停了,不多時卻復又淅淅瀝瀝下起來了。街道的路面很平,雨水落在上面,往往不能即時流入泥土裡。略略匯聚半刻鐘,就成了一面晶瑩剔透的鏡子,像鏡泊湖的湖面一般。三五雨滴落下,盪起幾圈漣漪,雨落的聲音,就隨著水波的紋路,一點點泛開去,到青石板路的邊緣而止了。
梧桐是尤為欣喜秋雨的。枝幹被洗刷一新,枯黃的葉落一地,預兆的便是來年的新生。生命如是周而復始,已經成了諸如早晚功課一般的慣例,是不會因著人世間的變幻而改變的。
秋雨下到不過半晌,霧氣便徹底消散殆盡了。街道遠處的青磚紅瓦,廊檐低回,一覽無遺。雖然舉目處能夠看得清晰,但有了雨幕的遮擋,總不能夠盡心如意。便是冒著雨走到近前,卻又失了一目了然的韻味。想來古人所說,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箇中味道恐怕只有當局者方能體會了。
霧雖然盡了,天空里又升起了裊裊炊煙,但不知是誰家庭院。設若這個場景,是在大漠荒原,便能給人落寞到極致的孤獨感。然而在此處,一切就有了改觀。瞑目處,雨聲仿似流水潺潺,又似鐘鼓輕響,更似琴瑟同鳴,冷清的氛圍里頓時便有了溫馨的味道。這個時候大抵上是沒有人肯打破這喧囂中的寂靜的,哪怕鄰里相見,也只是一個會意的神情,各自去忙各自的事。
炊煙散盡,雨也便悄悄的止歇了。可人心裡,並不曾因著雨的停歇而歡快,反倒潮潮的,一如青石板的路面。小樓一夜聽春雨,固然會使人繾綣萬千,但秋雨也不遑多讓。春雨來則來了,去便去了,過後一片生機,萬物復甦,帶來的總是希望。而秋雨來便來了,卻不會再去了。它給人帶來的,除了濕冷,便只有陰冷,連帶內心裡,都有了憂鬱的感傷。這尚不是最使人黯然的,秋去不過三五日,便是霜降雪落,迎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小樓一夜聽春雨》 2012第四期《牡丹》
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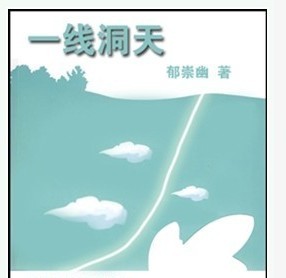

在歷史行走之前,
我在這裡蓋下了這座木房子。
用我的骨,搭成支架,
用我的毛髮,搭成屋蓬。
在羅漫山的懷抱里,
草和木,樹和花,鳥和獸,
是安詳生存的居民,
挺拔的白樺和雲杉,是守衛的士兵。
我從第四紀冰川前的七月來,
在天邊尋找失散的情人。
那清澈幽深的天池,
那旖旎的青山雪峰,
那隆起的古冰磧壠,
那細碎的冰川漂礫,
那化名雪海的博格達,
而你,而你,悄悄的駐足在哪裡?
我建一座木房子,
用盡一生的精力和魂靈,
卻不曾有一個凡間的人居住。
采一朵塔格依力斯,
戴在麋鹿的頭上;
采一朵野薔薇,
戴在猞猁的頭上;
采一朵定痛的天仙子,
在我踏過雪線之前,
輕輕的插在鬢髮之後。
另有多篇時事評論及散文發表於《新京報》、《齊魯晚報》、《牡丹》等報刊雜誌。其中《小樓一夜聽春雨》一文,清新雋永,於樸素中見灑脫超然,是一篇難得的散文佳作。
“這深情是不為人知的,萬物皆有情,情到濃時卻轉薄。秋雨下的不緊不慢,像一個慢性子的人,自顧自在自己的世界裡遊蕩,全然不知別人心裡的感受。晚起的居民站在自家屋檐下,踮著腳尖往天上看,看雨是否會停下來。從他們的面目上,是看不出結果的,不過大致可以推算出來。若瞧得他們面上沒有什麼表情,或者略有欣喜,便知秋雨正慢慢止歇;反之,只消站在原處片刻,就會看到原本踮腳看天的人披著蓑衣穿著高底的鞋子急匆匆出門去。
所以,假若急著辦事的話,是不宜等待秋雨止歇的。秋雨最是連綿,由著它的性子,怕是要下滿整個秋季方肯罷休。最讓人著惱的是,眼看著停了,不多時卻復又淅淅瀝瀝下起來了。街道的路面很平,雨水落在上面,往往不能即時流入泥土裡。略略匯聚半刻鐘,就成了一面晶瑩剔透的鏡子,像鏡泊湖的湖面一般。三五雨滴落下,盪起幾圈漣漪,雨落的聲音,就隨著水波的紋路,一點點泛開去,到青石板路的邊緣而止了。
梧桐是尤為欣喜秋雨的。枝幹被洗刷一新,枯黃的葉落一地,預兆的便是來年的新生。生命如是周而復始,已經成了諸如早晚功課一般的慣例,是不會因著人世間的變幻而改變的。
秋雨下到不過半晌,霧氣便徹底消散殆盡了。街道遠處的青磚紅瓦,廊檐低回,一覽無遺。雖然舉目處能夠看得清晰,但有了雨幕的遮擋,總不能夠盡心如意。便是冒著雨走到近前,卻又失了一目了然的韻味。想來古人所說,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箇中味道恐怕只有當局者方能體會了。
霧雖然盡了,天空里又升起了裊裊炊煙,但不知是誰家庭院。設若這個場景,是在大漠荒原,便能給人落寞到極致的孤獨感。然而在此處,一切就有了改觀。瞑目處,雨聲仿似流水潺潺,又似鐘鼓輕響,更似琴瑟同鳴,冷清的氛圍里頓時便有了溫馨的味道。這個時候大抵上是沒有人肯打破這喧囂中的寂靜的,哪怕鄰里相見,也只是一個會意的神情,各自去忙各自的事。
炊煙散盡,雨也便悄悄的止歇了。可人心裡,並不曾因著雨的停歇而歡快,反倒潮潮的,一如青石板的路面。小樓一夜聽春雨,固然會使人繾綣萬千,但秋雨也不遑多讓。春雨來則來了,去便去了,過後一片生機,萬物復甦,帶來的總是希望。而秋雨來便來了,卻不會再去了。它給人帶來的,除了濕冷,便只有陰冷,連帶內心裡,都有了憂鬱的感傷。這尚不是最使人黯然的,秋去不過三五日,便是霜降雪落,迎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小樓一夜聽春雨》 2012第四期《牡丹》
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