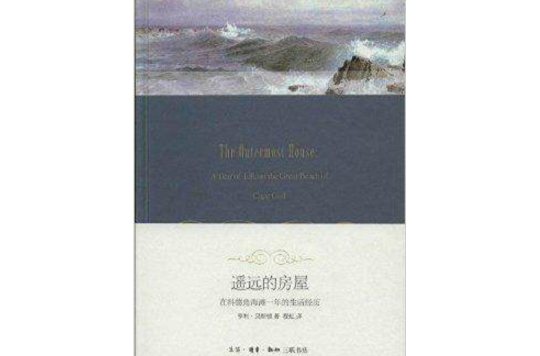《遙遠的房屋:在科德角海灘1年的生活經歷》是美國著名的自然文學作家亨利·貝斯頓於20世紀20年代寫的一本散文集。它描述了作者隻身一人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瀕臨大西洋那片遼闊孤寂的海灘生活一年的經歷。全書由十章組成,依據大自然的節奏展開,從秋季開始,以秋季結束,形成了一個圓滿的循環。作者以散文詩般的語言分別描述了他所居住的小屋,他所在的海灘、沙丘,他觀察到的各種鳥類、海灘及沙丘地帶的植物,海灘及大海四季的景色以及零零星星的海灘上的過客。其中既讚美了自然的壯麗,也揭示了自然的冷酷。
基本介紹
- 書名:遙遠的房屋:在科德角海灘1年的生活經歷
- 作者:亨利•貝斯頓
- 類型:小說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08041135, 7108041138
- 外文名:The Outermost House:A Year of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 譯者:程虹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頁數:163頁
- 開本:32
- 品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遙遠的房屋:在科德角海灘1年的生活經歷》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亨利·貝斯頓 譯者:程虹
圖書目錄
譯序
中文版序
導讀
1949年版作者序
第一章 海灘
第二章 秋天,大海及鳥類
第三章 拍岸巨浪
第四章 仲冬
第五章 冬季來客
第六章 海灘上的燈火
第七章 漫步於內陸的春光中
第八章 大海灘的夜晚
第九章 年之高潮
第十章 獵戶星在沙丘升起
中文版序
導讀
1949年版作者序
第一章 海灘
第二章 秋天,大海及鳥類
第三章 拍岸巨浪
第四章 仲冬
第五章 冬季來客
第六章 海灘上的燈火
第七章 漫步於內陸的春光中
第八章 大海灘的夜晚
第九章 年之高潮
第十章 獵戶星在沙丘升起
序言
2004年秋,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我來到《遙遠的房屋》的原址——位於科德角的那片瀕臨大西洋外海、我在書中讀過無數次的海灘。此時,秋色正濃。一所紅磚白窗的房子,老海岸警衛站,孤零零地矗立在長滿荒草及沙地植物的沙丘頂上。離警衛站不遠處,立著一塊介紹亨利·貝斯頓及其《遙遠的房屋》的牌子。“遙遠的房屋”已不復存在,它在1978年2月的一場冬季風暴中被捲入了大海,葬身於我眼前約一英里處的海底。我環顧四周,尋找著書中讀到的那些景物:內側是長滿齊腰的茅草及沙地植物的沙丘,再往裡是一池池映出岸邊秋色的碧水,那是海水積成的瀉湖;外側,是孤寂的海灘,濤聲陣陣,海浪滾滾。我走下沙丘,沿著遊人稀少的海灘漫步,體驗著八十多年前,貝斯頓肩背生活必需品,從諾塞特海岸警衛站,沿著海灘,踏著浪花返回他那“遙遠的房屋”的感覺,想像著若干年前的一個秋日,貝斯頓“、漫步于海灘”,“從變幻莫測的雲朵中解讀到冬季的來臨”的詩情畫意。我在一處泛白的流木上坐下,觀望著大海潮起潮落,看著“風把海浪像殉葬者一樣送上不歸之路”,最終“粉碎於這孤寂無人的海灘”。我將目光投向眼前約一英里處的海面上,知道那裡便是“遙遠的房屋”的原址或葬身之地。從貝斯頓離開“遙遠的房屋”到後者葬身於海底,僅僅幾十年的時間,大海就向這片狹窄的陸地侵入了一英里,或許,用不了很久,我坐的這片海灘也會被大海所吞沒。然而,此時物質的東西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貝斯頓已經將“遙遠的房屋”的魂魄以及它的詩意留在了人間。我們不妨說,此時無形勝有形。“遙遠的房屋”不是作為一種物質的形式,而是作為一種對遠古自然的崇敬,對一種簡樸而又充滿詩意的生活之豐富的想像留存於我們的記憶之中。儘管在造訪“遙遠的房屋”的原址時,我已經開始翻譯此書,但是這次親臨其境的經歷,畢竟給了我對那片陌生的土地所產生的親切感,給了我將一種文字轉變成另一種文字時的自如。或者說,我從科德角的自然中,獲取了貝斯頓當年得到的那幾許詩意及激情。
《遙遠的房屋——在科德角海灘一年的生活經歷》是美國著名的自然文學作家亨利·貝斯頓於20世紀20年代寫的一本散文集。它描述了作者隻身一人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瀕臨大西洋那片遼闊孤寂的海灘生活一年的經歷。
1925年,人到中年的貝斯頓在靠近科德角的那片海灘買下一塊地並自己設計草圖,請人在臨海的沙丘上建了一所簡陋的小屋。起初,他只是想在翌年秋季到那裡住上一兩周,並無意將它作為長久的居所。然而,當兩周結束後,貝斯頓卻遲遲沒有離去。因為,那片土地及外海的美麗和神秘感令他心醉神迷。他在那裡生活了整整一年並記錄下大自然栩栩如生的影像:大海的潮起潮落,湧向海灘的層層波濤,紛至沓來的各種鳥類,海上的過客,冬季的風暴,秋季的壯觀,春季的神聖,夏季的繁茂。他發現,那裡常年舉行著無可比擬的自然的盛會。
全書由十章組成,依據大自然的節奏展開,從秋季開始,以秋季結束,形成了一個圓滿的循環。作者以散文詩般的語言分別描述了他所居住的小屋,他所在的海灘、沙丘,他觀察到的各種鳥類、海灘及沙丘地帶的植物,海灘及大海四季的景色以及零零星星的海灘上的過客。其中既讚美了自然的壯麗,也揭示了自然的冷酷。當然,更令人感動的是作者在孤寂的海灘獨自享受自然,與大自然進行心靈溝通的那種精神的震撼與感悟。貝斯頓一生曾著有多部自然文學作品,但《遙遠的房屋》是他作者生涯的巔峰。誠如他的遺孀伊莉莎白所述:“沙丘可以生成或崩潰,人也有生老病死,但是他(貝斯頓)感到他的作品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此生無憾。”
作者建在沙丘上的那所孤零零的小屋,雖然簡陋,卻不失浪漫色彩:它的壁板及窗框被漆成淡淡的黃褐色,那種典型的水手艙的顏色。作者稱它為“水手艙”,因為房子建在延伸進海洋的沙丘上,恰似漂在海上的一葉小舟,一間遙遠的、給人以幻覺的小房子。而且,多窗是這房子的特點。如作者所述:“一間有七個窗子的房屋,位於沙丘之上,海上的陽光之下,僅此,便可想像出流光四射的情景,一種令人不安的光的把戲。”因此,他便有了一個近似戶外的居所,陽光湧進他的屋內,大海湧向他的房門。他本人則靠在枕頭上便可看到大海,觀望海上升起的繁星,停泊漁船搖曳的燈光,還有溢出的白色浪花,並聽著悠長的浪濤聲在寧靜的沙丘問迴蕩。
作者筆下的自然,有著一種史詩般的壯麗。科德角是以一幅氣勢磅礴的畫卷展示於眾的:“位於北美海岸線東部的前沿,距麻薩諸塞州內海岸約三十多英里處,在浩瀚的大西洋上屹立著最後一抹古老的、漸漸消失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卻始終進行著大海與土地之戰。“年復一年,大海試圖侵吞土地;年復一年,土地為捍衛自己而戰,盡其精力及創造力,令其植物悄然地沿海灘滋長蔓延,組成了草與蔓編織的網,攏住了前沿的沙石,任憑風吹雨打。”海浪這種自然現象在書中含有某種感人的悲壯:“秋天,響徹於沙丘中的海濤聲無休無止。這也是反覆無窮的充滿與聚集、成就與破滅、再生與死亡的聲音。”隨後,我們跟隨作者一次次地觀看著海浪一個接一個地從大西洋的外海扑打過來。它們越過層層阻礙,經過破碎和重組,一波接一波地構成巨浪,以其最後的精力及美麗映出藍天,再將自己粉碎於孤寂無人的海灘。從海浪這種反覆無窮的充滿與聚集、成就與破滅、再生與死亡的運作中,我們深切感受到了人類歷史生生不息,前仆後繼的宏偉進程,當然,還有伴隨這個進程的悲壯與詩意。
……
我們通常知道鳥類的遷徙,貝斯頓在書中則詳細地描述了鮮為人知的魚類的遷徙,並從中看到了動物所具有的某種我們人類無法理解的能力。他仔細地觀察到,每年四月份,一種灰鯡魚就會離開大海,游到位於麻薩諸塞州葦茅斯的一條小溪中,在一個淡水池塘中產卵。然後,產卵的雌魚與雄魚一起越過堤壩,游回大海。在池塘里出生的小鯡魚在十個月或一年之後追隨它們而去,並於來年春季再回來。於是,便留下一個令人百思不解的謎。在茫茫大海的某片水域,每一條產自當地葦茅斯的魚都記得它出生的那個池塘,並且穿越沒有航標的漫漫海路抵達此地。貝斯頓不禁發問:“是什麼在那一個個冷淡遲鈍的小腦子中激起了靈感?當新的曙光灑在潮水形成的河面時,是何等召喚在吸引著它們?這些小生靈憑藉著什麼找到了它們的航線?鳥類可依據景物、河流以及海角來認路,魚又是靠什麼認路呢?”然而,這些魚很快就“來到”了葦茅斯,並隨著漲滿的春水,到了初生地的池塘。從貝斯頓對灰鯡魚往返於大海及出生地的遷徙的描述中,不僅使我們對動物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的好奇與敬意,而且開始思索大自然到處傳播生命的渴望與激情。讓生命充滿世界的每一處角落,讓大地、天空及海洋都聚集著生命。我們知道,貝斯頓生活的年代,正值艾略特的《荒原》出版,自然已死的悲觀論調充斥著人間。然而,從《遙遠的房屋》中,我們讀到的卻是一種樂觀。總結在科德角一年的收穫時,貝斯頓寫道:“有些人問我這如此奇特的一年生活使我對大自然有何種理解?我會答覆道,最首要的理解是一種強烈的感受,即創造依然在繼續,如今的創造力像自古以來的創造力一樣強大,明天的創造力會像世界上任何的創造力那樣氣吞山河。創造就發生在此時此地。”我們從他的書中得知,在每一處空蕩的角落,在所有那些被遺忘的地方,大自然拚命地注入生命,讓死者煥發新生,讓生者更加生機勃勃。大自然激活生命的熱忱,無窮無盡,勢不可當,而又毫不留情。貝斯頓感嘆道:“所有這些她(大自然)的造物,即便是像這些受挫的小‘鯡魚’,為了成就大地的意圖,它們要忍受何等的艱難困苦、飢餓寒冷,經受何種不惜遍體鱗傷的廝殺搏鬥?又有哪種人類有意識的決心比得上它們沒有意識的共同意願,寧可委屈自我而服從於整個宇宙生命的意志?”這段話令人深思。人類只不過是整個生態體系中的一部分,我們是否應當從動物的這種集體意識中學會重新確立我們的位置,調整我們的行為方式,從而服從整個宇宙生命的意志?
當然,最令人心動的當是貝斯頓語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種當今社會久違了的“精耕細作”。他的遺孀伊莉莎白·貝斯頓回憶他寫《遙遠的房屋》時的情景:“他總是用鉛筆或鋼筆寫,幾乎從不用打字機,唯恐打字的聲音擾亂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韻律。有時他花整個上午的時間來推敲一個句子。”在充斥著“文化快餐”的現代社會中,或許,我們應當給諸如《遙遠的房屋》這樣為數不多的文學經典留下一片園地。
程虹
2007年4月
《遙遠的房屋——在科德角海灘一年的生活經歷》是美國著名的自然文學作家亨利·貝斯頓於20世紀20年代寫的一本散文集。它描述了作者隻身一人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瀕臨大西洋那片遼闊孤寂的海灘生活一年的經歷。
1925年,人到中年的貝斯頓在靠近科德角的那片海灘買下一塊地並自己設計草圖,請人在臨海的沙丘上建了一所簡陋的小屋。起初,他只是想在翌年秋季到那裡住上一兩周,並無意將它作為長久的居所。然而,當兩周結束後,貝斯頓卻遲遲沒有離去。因為,那片土地及外海的美麗和神秘感令他心醉神迷。他在那裡生活了整整一年並記錄下大自然栩栩如生的影像:大海的潮起潮落,湧向海灘的層層波濤,紛至沓來的各種鳥類,海上的過客,冬季的風暴,秋季的壯觀,春季的神聖,夏季的繁茂。他發現,那裡常年舉行著無可比擬的自然的盛會。
全書由十章組成,依據大自然的節奏展開,從秋季開始,以秋季結束,形成了一個圓滿的循環。作者以散文詩般的語言分別描述了他所居住的小屋,他所在的海灘、沙丘,他觀察到的各種鳥類、海灘及沙丘地帶的植物,海灘及大海四季的景色以及零零星星的海灘上的過客。其中既讚美了自然的壯麗,也揭示了自然的冷酷。當然,更令人感動的是作者在孤寂的海灘獨自享受自然,與大自然進行心靈溝通的那種精神的震撼與感悟。貝斯頓一生曾著有多部自然文學作品,但《遙遠的房屋》是他作者生涯的巔峰。誠如他的遺孀伊莉莎白所述:“沙丘可以生成或崩潰,人也有生老病死,但是他(貝斯頓)感到他的作品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位,此生無憾。”
作者建在沙丘上的那所孤零零的小屋,雖然簡陋,卻不失浪漫色彩:它的壁板及窗框被漆成淡淡的黃褐色,那種典型的水手艙的顏色。作者稱它為“水手艙”,因為房子建在延伸進海洋的沙丘上,恰似漂在海上的一葉小舟,一間遙遠的、給人以幻覺的小房子。而且,多窗是這房子的特點。如作者所述:“一間有七個窗子的房屋,位於沙丘之上,海上的陽光之下,僅此,便可想像出流光四射的情景,一種令人不安的光的把戲。”因此,他便有了一個近似戶外的居所,陽光湧進他的屋內,大海湧向他的房門。他本人則靠在枕頭上便可看到大海,觀望海上升起的繁星,停泊漁船搖曳的燈光,還有溢出的白色浪花,並聽著悠長的浪濤聲在寧靜的沙丘問迴蕩。
作者筆下的自然,有著一種史詩般的壯麗。科德角是以一幅氣勢磅礴的畫卷展示於眾的:“位於北美海岸線東部的前沿,距麻薩諸塞州內海岸約三十多英里處,在浩瀚的大西洋上屹立著最後一抹古老的、漸漸消失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卻始終進行著大海與土地之戰。“年復一年,大海試圖侵吞土地;年復一年,土地為捍衛自己而戰,盡其精力及創造力,令其植物悄然地沿海灘滋長蔓延,組成了草與蔓編織的網,攏住了前沿的沙石,任憑風吹雨打。”海浪這種自然現象在書中含有某種感人的悲壯:“秋天,響徹於沙丘中的海濤聲無休無止。這也是反覆無窮的充滿與聚集、成就與破滅、再生與死亡的聲音。”隨後,我們跟隨作者一次次地觀看著海浪一個接一個地從大西洋的外海扑打過來。它們越過層層阻礙,經過破碎和重組,一波接一波地構成巨浪,以其最後的精力及美麗映出藍天,再將自己粉碎於孤寂無人的海灘。從海浪這種反覆無窮的充滿與聚集、成就與破滅、再生與死亡的運作中,我們深切感受到了人類歷史生生不息,前仆後繼的宏偉進程,當然,還有伴隨這個進程的悲壯與詩意。
……
我們通常知道鳥類的遷徙,貝斯頓在書中則詳細地描述了鮮為人知的魚類的遷徙,並從中看到了動物所具有的某種我們人類無法理解的能力。他仔細地觀察到,每年四月份,一種灰鯡魚就會離開大海,游到位於麻薩諸塞州葦茅斯的一條小溪中,在一個淡水池塘中產卵。然後,產卵的雌魚與雄魚一起越過堤壩,游回大海。在池塘里出生的小鯡魚在十個月或一年之後追隨它們而去,並於來年春季再回來。於是,便留下一個令人百思不解的謎。在茫茫大海的某片水域,每一條產自當地葦茅斯的魚都記得它出生的那個池塘,並且穿越沒有航標的漫漫海路抵達此地。貝斯頓不禁發問:“是什麼在那一個個冷淡遲鈍的小腦子中激起了靈感?當新的曙光灑在潮水形成的河面時,是何等召喚在吸引著它們?這些小生靈憑藉著什麼找到了它們的航線?鳥類可依據景物、河流以及海角來認路,魚又是靠什麼認路呢?”然而,這些魚很快就“來到”了葦茅斯,並隨著漲滿的春水,到了初生地的池塘。從貝斯頓對灰鯡魚往返於大海及出生地的遷徙的描述中,不僅使我們對動物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的好奇與敬意,而且開始思索大自然到處傳播生命的渴望與激情。讓生命充滿世界的每一處角落,讓大地、天空及海洋都聚集著生命。我們知道,貝斯頓生活的年代,正值艾略特的《荒原》出版,自然已死的悲觀論調充斥著人間。然而,從《遙遠的房屋》中,我們讀到的卻是一種樂觀。總結在科德角一年的收穫時,貝斯頓寫道:“有些人問我這如此奇特的一年生活使我對大自然有何種理解?我會答覆道,最首要的理解是一種強烈的感受,即創造依然在繼續,如今的創造力像自古以來的創造力一樣強大,明天的創造力會像世界上任何的創造力那樣氣吞山河。創造就發生在此時此地。”我們從他的書中得知,在每一處空蕩的角落,在所有那些被遺忘的地方,大自然拚命地注入生命,讓死者煥發新生,讓生者更加生機勃勃。大自然激活生命的熱忱,無窮無盡,勢不可當,而又毫不留情。貝斯頓感嘆道:“所有這些她(大自然)的造物,即便是像這些受挫的小‘鯡魚’,為了成就大地的意圖,它們要忍受何等的艱難困苦、飢餓寒冷,經受何種不惜遍體鱗傷的廝殺搏鬥?又有哪種人類有意識的決心比得上它們沒有意識的共同意願,寧可委屈自我而服從於整個宇宙生命的意志?”這段話令人深思。人類只不過是整個生態體系中的一部分,我們是否應當從動物的這種集體意識中學會重新確立我們的位置,調整我們的行為方式,從而服從整個宇宙生命的意志?
當然,最令人心動的當是貝斯頓語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種當今社會久違了的“精耕細作”。他的遺孀伊莉莎白·貝斯頓回憶他寫《遙遠的房屋》時的情景:“他總是用鉛筆或鋼筆寫,幾乎從不用打字機,唯恐打字的聲音擾亂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韻律。有時他花整個上午的時間來推敲一個句子。”在充斥著“文化快餐”的現代社會中,或許,我們應當給諸如《遙遠的房屋》這樣為數不多的文學經典留下一片園地。
程虹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