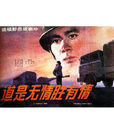劇情簡介
山谷中,炮兵某部三連正在進行實彈打靶。瞄準手馬衛東看錯了火炮上的瞄準線,致使炮彈偏離方向,還炸傷了一位老大娘。團長看三連軍事素質如此差,心中十分憂慮,擔心一連也會如此。不僅別人心裡沒底,就是一連自己也沒把握,因為連長袁翰回京探親,超假已半個月,至今未歸。團長命令打靶時由指揮排長代理連長指揮。翌日凌晨,一連在前往射擊陳地的路上,碰上袁翰探親歸來,官兵們都很高興,但團長卻命令袁翰等候處理,仍由指揮排長指揮射擊。出乎意料的是,一連在連長不在的情況下,射擊成績依然優秀,團長認為這是與連長帶兵有方分不開。袁翰因妻子生了雙胞胎,家中無人照顧,而延誤歸期。沉重的家庭負擔使他產生了離隊思想。他向團長坦率地講了自己的想法,團長認為他是個有強烈責任感和犧牲精神的優秀軍事幹部,告訴他團里已決定他去三連任連長。背著超假處分的袁翰到任後,發現了許多問題,他決心從抓軍事訓練入手,改變三連的落後面貌。他和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使連隊軍事素質很快得到提高。這時,他接到兩個女兒病危、要他速歸的電報。他將身邊僅有的13元錢寄回家,自己仍然狠抓軍事訓練。雖然團里派軍醫前往,但雙胞胎中的一個仍然死去了。在袁翰的領導下,三連發生了可喜的變化,袁翰為此立了功,為功勞包括了他的妻子和只活了一個多月的小女兒。對越反擊戰前,袁翰升任營長,處分也取消了。軍車隆隆向前線開去,袁翰忽然發現路邊走過來抱著孩子的婦女正是他的妻子。他毅然下達了加速前進的命令,決心待到勝利歸來時,再與親人相見。迎著絢麗的朝霞,炮車載著人民的重託、親人的期望、駛向遠方。
演職員表
演員表
| 角色 | 演員 | 配音 |
|---|
| 袁翰 | 朱時茂 | ---- |
| 團長 | 牛千 | ---- |
| 羅懷牧 | 楊同順 | ---- |
| 袁翰妻 | 牛翠敏 | ---- |
| 三班長 | 孫海英 | ---- |
| 司務長 | 張曉春 | ---- |
| 周鳴天 | 郭剛 | ---- |
| 副連長 | 朱劍平 | ---- |
| 馬衛東 | 高健 | ---- |
| 駕駛班長 | 吳少增 | ---- |
| 三班戰士 | 段飛宇 | ---- |
| 三班戰士 | 馬明昌 | ---- |
角色演員介紹參考資料
音樂原聲
幕後花絮
獲獎記錄
| 獲獎時間 | 獲獎獎項 | 獲獎方 | 備註 |
|---|
1984年 | 第四屆中國電影金雞獎 | 最佳故事片 | 《道是無情勝有情》 | 提名 |
1983年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獎 | 優秀故事片二等獎 | 《道是無情勝有情》 | 獲獎 |
1988年 | 新時期十年電影獎 | 最佳處女作導演榮譽獎 | 韋廉(《道是無情勝有情》) | 獲獎 |
幕後製作
劇本改編
小說《射天狼》發表後,《解放軍文藝》編輯部約洪柱國寫一篇評論文章。為此,洪柱國在發高燒的情況下一口氣讀完了小說。小說的主題和筆觸使他產生了強烈的改編欲望。洪柱國雖然是軍隊編劇,但不了解炮兵的生活,為了改編好《射天狼》,他特意到原作者朱蘇進當戰士時所在的連隊體驗生活,對小說中所描寫的環境以及各類人物的原型都盡力查訪。在改編時他還加入了自己在炮兵連生活時的感受,比如為了保持食堂地板乾淨以迎接衛生檢查,戰士們在露天吃了七八天的飯,這種形式主義幹部、戰士都滿腹牢騷,洪就把這個細節加入劇本中,讓袁翰擔負起抵制形式主義的重擔。
影片主旨
原小說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編劇把影片的背景改為“十年動亂”剛結束的1977至1979年。那一時期,動亂所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並沒有馬上消除,在“極左”思潮影響下,部隊軍事責質下降,幹部隊伍老化,幹部待遇低,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干擾部隊建設。導演韋廉認為電影工作者有責任大膽、深刻地反映部隊的現實矛盾,有義務提出問題,更重要的是通過揭示這些矛盾,讓人們感到軍人的內心,蘊藏著巨大的力量,認識到它的力度足克服軍隊、軍人自身的弱點,糾正前進道路上出現的錯誤和偏差。他希望通過該片能引發人們探討:當兵為什麼光榮,軍人為什麼應該受到尊重。在他看來,比起戰爭時期的英雄主義,和平時期的英雄主義更需要堅毅、頑強、持久和耐力。
演員選擇
在選演員時,韋廉特彆強調要有“兵味”,要求演員穿上軍裝是兵,脫了軍裝也是兵,從內心到外表都要透著“兵味”。他還注意誇大生活中人與人在臉型、體型上差別,但又對所有演員有一個共同要求:黑、瘦,因為這是長期風吹日曬緊張軍營生活的標誌。選用牛千演團長,除了他當過多年兵,氣質對路外,就是因為他外形精瘦。
影片評價
該片裡有一種為同時期軍事題材影片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軍人生活於其中的軍營訓練場的生活實感,可聞可感的、能令觀眾相信其真實存在的軍人們的日常勞動、訓練、事業心、獻身精神及他們的歡樂與苦惱、失落與慰安等真實的情感。該片的拍攝成功同原著所提供的文學基礎是分不開的,但原作沒有什麼引人入勝的戲劇情節,次要人物大多一掠而過,如果電影藝術家把握不住它的藝術美的精華,會變成單調乏味的“舊”聞紀錄。因此,更應該對成功地進行了藝術再創造的電影藝術家刮目相看。導演在物色演員和對演員總譜設計時,著意誇大了角色間在臉型和體型上的差別,所以不僅袁翰、顏子鵠的銀幕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幾位次要人物無論在全景、中景、近景出現,觀眾一眼就能認他出來。與原作相比,電影為袁翰性格提供的自然環境是有所豐富和發展的,而在社會環境方面則有所削弱,還弱化了原小說關於連隊幹部之間的思想衝突線,藝術處理上有失著之處。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副編審陳適存評) 袁翰演員:朱時茂有文化知識、懂科學技術的炮兵連長,農民出身,環境和職務養成了性格憨厚而又果斷的一面,長期以來沉重的家庭包袱和經濟拮据,以及十年內亂在部隊造成的軍事素養差等劣境又形成了他性格直爽而又急躁甚至有些暴躁的一面。雖不能完全掙脫個人的苦惱,但為著連隊建設、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默默做著貢獻、承受著種種犧牲。
袁翰演員:朱時茂有文化知識、懂科學技術的炮兵連長,農民出身,環境和職務養成了性格憨厚而又果斷的一面,長期以來沉重的家庭包袱和經濟拮据,以及十年內亂在部隊造成的軍事素養差等劣境又形成了他性格直爽而又急躁甚至有些暴躁的一面。雖不能完全掙脫個人的苦惱,但為著連隊建設、反侵略戰爭的準備默默做著貢獻、承受著種種犧牲。 團長演員:牛千性格內向,有一定文化素養,精明強幹,對部隊教育訓練搞不上去的現狀十分焦急。他嚴格要求部屬,對人民負責,對部隊負責,雖然非常喜歡袁翰,但表出來的卻是一個“嚴”字。
團長演員:牛千性格內向,有一定文化素養,精明強幹,對部隊教育訓練搞不上去的現狀十分焦急。他嚴格要求部屬,對人民負責,對部隊負責,雖然非常喜歡袁翰,但表出來的卻是一個“嚴”字。 羅懷牧演員:楊同順原三連連長,想搞好連隊,但缺乏自信,是一個稱職的司務長,但沒有能力當好炮兵連長。他厭惡社會上的一些壞風氣,懂得搞形式主義,但沒有能力抵制,甚至自己也去照著辦。
羅懷牧演員:楊同順原三連連長,想搞好連隊,但缺乏自信,是一個稱職的司務長,但沒有能力當好炮兵連長。他厭惡社會上的一些壞風氣,懂得搞形式主義,但沒有能力抵制,甚至自己也去照著辦。 袁翰妻演員:牛翠敏作為軍人的妻子,她深知丈夫家庭、工作壓力很大,不想再給他增添一點負擔和痛苦,但月子裡沒人照顧,一人侍候不了兩個嬰兒的實際困難又使她不得不向袁翰訴苦,明知無濟於事,但還是控制不了自己。
袁翰妻演員:牛翠敏作為軍人的妻子,她深知丈夫家庭、工作壓力很大,不想再給他增添一點負擔和痛苦,但月子裡沒人照顧,一人侍候不了兩個嬰兒的實際困難又使她不得不向袁翰訴苦,明知無濟於事,但還是控制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