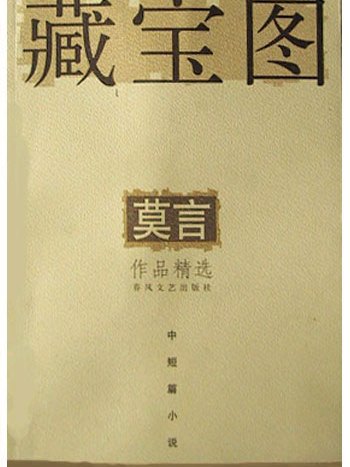基本介紹
- 書名:藏寶圖:中短篇小說
- 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
- 頁數:379頁
- 開本:32開
- 品牌:春風文藝
- 作者:莫言
- 出版日期:2003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1322056
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媒體推薦
代序
在路上尋找故鄉(代序)
一、 “高密東北鄉”是我的發明
記者:小說家以故鄉為寫作背景,古往今來不乏其人,因此而獲得成功的也大有人在,如馬爾克斯、福克納等。但似乎並無人像您那樣走得徹底,所有的小說都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
莫言:小說家筆下的故鄉當然不能與真正的故鄉畫等號,故鄉高密在我的創作世界中,剛開始還有現實的意義,越往後越變得像一個虛幻的遙遠的夢境,實際上它只是我每次想像的出發點或歸宿。最早使用“高密東北鄉”這個概念是一九八五年在軍藝念書時,當時也沒有十分明確的想法,就在《白狗鞦韆架》這篇小說里,幾乎是無意識地寫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幾個字。後來成了一種創作慣性,即使故事與高密東北鄉毫無關係,還是希望把它納入整個體系中。但我也覺悟到一個問題:一個作家故鄉素材的積累畢竟是有限的,無論在其中生活多久,假如要不斷用故鄉為背景來寫作,那么這個故鄉就必須不斷擴展,不能抱殘守缺炒剩飯。應該把通過各種途徑得到的故事、細節、人物等都納入到故鄉的範圍里來。後來我給故鄉下了一個定義:故鄉就是一種想像,一種無邊的,不是地理意義上而是文學意義上的故鄉。
記者: 自二十一歲離開故鄉後,當兵、創作、走南闖北,如此豐富的人生經歷卻似乎很少直接進入到您的小說中,這些經歷對於您的故鄉寫作有怎樣的關聯?
莫言:海明威說過,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當然,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資源。一個人的童年時期,正是世界觀、思想的形成發展時期,求知慾旺盛,記憶力最好,如果童年不幸,有可能獲得一些獨特的感受和經驗,而這些獨特的東西,恰好是最富有文學意義的。至於當兵以後的生活,則變得趨同化、政治化、格式化、整齊劃一,單凋,好像後來的生活與文學足斷電的。
在中國寫農村題材有悠久的傳統,遊子返鄉式的寫作,從“五四”以來一直是創作的重要主題,每個作家都有類似的寫作。沈從文更典型,離開湘西就無東西可寫,或根本寫不好,但一寫湘西,立時在文壇上顯得非同凡響。而他當了教授後,寫起大學生活就缺少個性,一般化了。他寫湘西,寫船上的船夫、吊腳樓的妓女,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呼之欲出,讓我們眼前立刻想像出自己的湘西,感到一種水汽,一種泥土氣息,吊腳樓的顏色、形狀都可想像出來,這樣的作家就是找到了故鄉,找到了自我、找到了童年、找到了根。
為什麼作家都要用作品尋找故鄉?因為他們離開了故鄉。試想,如果沈從文不離開湘西,可能也寫得不錯,但肯定形成不了一種居高臨下的目光.他不會用一種比較的態度來看故鄉。他背井離鄉在上海、北京闖蕩,接受了現代文明的薰陶,再回頭來觀照過去的生活,眼界就比原來高得多。
《透明的紅蘿蔔》是以我當時生活的經歷、感受為基礎生髮的一部小說,記憶中那個涵洞非常高大,但後來我帶著電視台的記者去拍這個涵洞時,才發現它原來那么矮小,一方面可能是人長高了,一方面在城市裡,我看到的都是高樓大廈,再回頭比較農村的草房、童年記憶中高大的涵洞,馬上就覺得過去的記憶很不真實,童年的東西類似夢幻。
……
在路上尋找故鄉(代序)
一、 “高密東北鄉”是我的發明
記者:小說家以故鄉為寫作背景,古往今來不乏其人,因此而獲得成功的也大有人在,如馬爾克斯、福克納等。但似乎並無人像您那樣走得徹底,所有的小說都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
莫言:小說家筆下的故鄉當然不能與真正的故鄉畫等號,故鄉高密在我的創作世界中,剛開始還有現實的意義,越往後越變得像一個虛幻的遙遠的夢境,實際上它只是我每次想像的出發點或歸宿。最早使用“高密東北鄉”這個概念是一九八五年在軍藝念書時,當時也沒有十分明確的想法,就在《白狗鞦韆架》這篇小說里,幾乎是無意識地寫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幾個字。後來成了一種創作慣性,即使故事與高密東北鄉毫無關係,還是希望把它納入整個體系中。但我也覺悟到一個問題:一個作家故鄉素材的積累畢竟是有限的,無論在其中生活多久,假如要不斷用故鄉為背景來寫作,那么這個故鄉就必須不斷擴展,不能抱殘守缺炒剩飯。應該把通過各種途徑得到的故事、細節、人物等都納入到故鄉的範圍里來。後來我給故鄉下了一個定義:故鄉就是一種想像,一種無邊的,不是地理意義上而是文學意義上的故鄉。
記者: 自二十一歲離開故鄉後,當兵、創作、走南闖北,如此豐富的人生經歷卻似乎很少直接進入到您的小說中,這些經歷對於您的故鄉寫作有怎樣的關聯?
莫言:海明威說過,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當然,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資源。一個人的童年時期,正是世界觀、思想的形成發展時期,求知慾旺盛,記憶力最好,如果童年不幸,有可能獲得一些獨特的感受和經驗,而這些獨特的東西,恰好是最富有文學意義的。至於當兵以後的生活,則變得趨同化、政治化、格式化、整齊劃一,單凋,好像後來的生活與文學足斷電的。
在中國寫農村題材有悠久的傳統,遊子返鄉式的寫作,從“五四”以來一直是創作的重要主題,每個作家都有類似的寫作。沈從文更典型,離開湘西就無東西可寫,或根本寫不好,但一寫湘西,立時在文壇上顯得非同凡響。而他當了教授後,寫起大學生活就缺少個性,一般化了。他寫湘西,寫船上的船夫、吊腳樓的妓女,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呼之欲出,讓我們眼前立刻想像出自己的湘西,感到一種水汽,一種泥土氣息,吊腳樓的顏色、形狀都可想像出來,這樣的作家就是找到了故鄉,找到了自我、找到了童年、找到了根。
為什麼作家都要用作品尋找故鄉?因為他們離開了故鄉。試想,如果沈從文不離開湘西,可能也寫得不錯,但肯定形成不了一種居高臨下的目光.他不會用一種比較的態度來看故鄉。他背井離鄉在上海、北京闖蕩,接受了現代文明的薰陶,再回頭來觀照過去的生活,眼界就比原來高得多。
《透明的紅蘿蔔》是以我當時生活的經歷、感受為基礎生髮的一部小說,記憶中那個涵洞非常高大,但後來我帶著電視台的記者去拍這個涵洞時,才發現它原來那么矮小,一方面可能是人長高了,一方面在城市裡,我看到的都是高樓大廈,再回頭比較農村的草房、童年記憶中高大的涵洞,馬上就覺得過去的記憶很不真實,童年的東西類似夢幻。
……
圖書目錄
在路上尋找故鄉(代序)
大風
秋水
嗅味族
一匹誤入民宅的狼
長安大道上的騎驢美人
冰雪美人
爆炸
野種
牛
我們的七叔
藏寶圖
大風
秋水
嗅味族
一匹誤入民宅的狼
長安大道上的騎驢美人
冰雪美人
爆炸
野種
牛
我們的七叔
藏寶圖
文摘
書摘
沒有撒謊,更不敢造謠,我實事求是地說:
“我跟於進寶到井裡去了。”
“什麼?”父親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我的圍著飯桌喝菜湯的兄弟姐妹們也用嘲笑的眼光看著我,我知道這些傢伙把我當成傻瓜,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我到井裡去乾什麼,當然也不能怨他們,因為這件事情的確離奇,如果我不是親身經歷,寧丁死我我也不會相信天底下竟然會存在著這樣的事。
“我跟著於進寶到他家後園那眼井裡去了。”我對他們儘量詳盡地說著:“昨天下午,我去找於進寶玩耍,玩了一會兒,口渴得很,於進寶家沒有水,於進寶就帶我到他家後園裡去找水喝,地家後園裡有一口很深的井……”
母親打斷我的話,問我,又像是自言自語:
“雜種,雜種,你一夜沒回來?你在哪裡睡的?”
“抬來吧,”叔叔說,“我可是從來不出診。”
“就來了,”孫七姑說,“我頭前跑來,先給您報個信兒。”
這時,從大街上傳來一個女人誇張的尖叫聲:
“痛死啦……親娘啊……痛死啦……”
孫七姑的弟弟孫大和孫二,用一扇門板將他們的母親抬到了醫院門前,放在了雪地上。他們的母親,一個瘦長的、與她的女兒形成了鮮明對照的、花白頭髮的女人,在門板上不斷地將身體折起來,然後又猛地倒下去。她的兩個兒子,將手抄在棉襖的袖筒里,目光茫然,果然像木頭一樣。叔叔惱怒地說:
“什麼東西!抬進來啊,放在外邊晾著,難道還怕臭了嗎?”
孫大和孫二將門板抬起來,別彆扭扭地想往門裡擠。叔叔說:
“放下門板,抬人!”
兄弟兩個一個抱腿,一個抱頭,終於把他們的母親抬到了診斷床上。叔叔喝了幾口茶水,搓搓手,上前給她診斷。老女人喊著:
“痛死了,痛死了,老頭子啊,你顯現神靈,把我叫了去吧……”
叔叔說:
“死不了,你這樣的,閻王爺怎么敢收!”
叔叔用手摸摸老女人烏黑的肚皮,說:
“化膿性闌尾炎。”
“還有治嗎?”孫七姑焦急地問。
“開一刀,切去就好了。”叔叔輕描淡寫地說。
“要多少錢……”孫大磕磕巴巴地問。
“五百。”叔叔說。
“五百……”孫二嘬著牙花子說。
這隻也許早就失去了煉丹走火本領的狐狸孑遺從我和妻子面前,流水落花般跑過,它的秀麗的腳趾抓得我心臟緊縮。妻子的指甲掐得我肉痛。在跑動中,它側著狹長的臉,用綠色的眼睛,鄙夷地瞄了我一眼。狐狸瞧我不起,它高傲得可以,它冷漠得要命。這隻偉大的狐狸,像一尊移動的紀念碑,從路上飄然而過,像一道紅色閃電,堅硬而滋潤。我無意中叫了一聲,長而恐怖,嘴巴張著不合,舌頭凍結,目光如線一樣粘在狐狸那條老練地道的雪尖尾巴上,狐狸跑到哪兒,就把線帶到哪兒。
狗和人雜沓地追來,狗無表情,人卻惡狠狠地罵我:你他媽的怎么站著不動!你腿有毛病?他們不敢戀罵,撇下我不管,急如星火地追下去,人跑成狗樣,狗跑成人狀,狐狸躍上河堤,
在那道壁立的白光上,投下一個邊緣朦朧的影子,狐狸的影子,使柳樹立刻綠得厲害。
這隻狐狸臉上的傲慢神情刺激著我的神經,它蔑視我,它使我把從前積累的關於狐狸的印象全部曝光。我在動物園見過鐵籠子裡一群紅狐狸,它們臭氣熏天,懶洋洋地蹲在陰暗潮濕的石洞裡,尖削的下巴使它們滿臉荒誕愚蠢。那次我跟那個單眼皮大眼睛的姑娘去看狐狸,奶油冰棍把她的嘴巴弄得黏乎乎的。她問:你為什麼像狐狸一樣陰沉?我說:我怕這鐵籠子。她吃驚地看著我憂傷的臉,我憂傷地看著她吃驚的臉。她說:遺憾嗎?我說:你聞得慣狐狸的味道嗎?她說:我有慢性鼻炎。我說:我們去看老虎吧。
狐狸翻過河堤,跳到枯燥滾燙的河沙上,宛若進了白色沙漠。它柔軟的爪子踩出一朵朵梅花,天上的金光,沙上的白光,把它夾成一個金銀狐狸。兩岸墨綠的垂柳排比而下,河堤的漫坡上一團團連續著荊條、紅柳、酸棗棵子,枯河之沙曲曲折折向前流著,沙子熱脹,摩擦有聲。狐狸在沙上跑,尾巴拖出一條痕跡。它鑽進叢生的灌木,不見了。那群漢子也下了河,低頭辨認著沙上的花紋。狗把鼻子觸到花紋上,可恥地對著人叫。三架飛機壓著狗頭飛過去。飛行訓練繼續進行。駕駛員都是面孔冷峻的小伙子,都不會眨眼睛。飛機有時飛得很高,有時飛得很低,飛低時,麥茬地里它們金黃色的大影子像河水一樣流動,機翼激起的硬風把野草按倒,枝桿強硬、葉子邊緣上生滿硬刺可以做止血藥用的大薊在伏地的野草中昂揚著紫紅色的花朵,
安護士從牆角拐出來,我認為她是為我走得如此風姿綽約雄赳赳氣昂昂,像個燙髮的紅衛兵小將。飛機成排地低飛過去,巨大的轟鳴聲把梧桐葉子都震翻了。
安護士說:老師,老師讓我問問你們,是流還是不流?
我說:流,堅決流。
安護士響亮地笑起來,我看她,她立刻把笑容斂起來,說:其實,這不算什麼大事,我們每天都給人流產,半個小時就完事。她用眼斜看著我,嘴對我妻子說:大嫂,老師是搞藝術的,你應該支持他。
妻子說:什麼狗屁藝術,嫁給他是我前輩子幹了缺德事。
安護士說:哎喲我的大嫂!全縣裡的女人也比不上你幸福。
妻子說:你知道我遭了多少罪?等他等老了,和我一般大的女伴都兩三個孩子了我才結婚,還是我拉著他去登的記。
安護士說:拉郎配。
妻子說:他像個小孩一樣,能把人氣死。
我說:行了。
麻嬸說:“杜大哥,您吃塊嘗嘗吧,也許吃到嘴裡就不臊了。”
麻叔罵麻嬸道:“這樣的髒東西,你也好意思讓杜大哥嘗?杜大哥家大魚大肉都放臭了,還喜吃這!”
杜大爺把那塊牛蛋子放到盤子裡,將筷子摔到老董同志面前,說:“說我家把大魚大肉放臭了是胡說,但你要說咱老杜沒斷了吃肉,這是真的,孬好咱還有一個乾屠宰組的女婿嘛!”
老董同志說:“老杜,您是我見到的最有福氣的老頭,公社書記的爹也享不到您這樣的福!”
“托您的福,”杜大爺說著,往外走,走了兩步,又回頭道,“隊長,我年紀大了,熬不了夜,前半夜我頂著,後半夜我可就不管了。”
麻叔說:“你不管誰管?你是飼養員!”
杜大爺說:“飼養員是餵牛的,不是遛牛的。”
麻叔說:“我不管你這些,反正牛出了毛病我就找你。”
杜大爺說:“你這是欺負老實人!”
杜大爺罵罵咧咧地走出來了。我生怕被他發現,一矮身蹲在了窗前。但他從燈下剛出來,眼前一摸黑,根本看不到我。我看到他頭重腳輕地走了出去。我趁機溜到灶間,掀開鍋,伸手往裡一摸,果然摸到一個碗。再一摸,碗裡果然有東西。我一下子就聞到了炒牛蛋子的味道。麻嬸真是個重契約守信用的好人。我端著碗就躥到院子裡。這時,我聽到杜大爺在大門外喊叫起來:“隊長,毀了!隊長,毀了!牛都趴下了!”
我可顧不了那么多了。我蹲在草垛後邊的黑影里,抓起牛蛋子就往嘴裡塞。我看到麻叔和老董同志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我聽到麻叔大聲喊叫:“羅漢!羅漢!你這個小兔崽子,跑到哪
里去了?”我抓緊時間,將那些牛蛋子吞下去,當然根本就顧不上咀嚼,當然我也顧不上品嘗牛蛋子是臊還是不臊。吃完了牛蛋子,我放下碗,打了一個嗝,從草垛後慢悠悠地轉出來。他們在門外喊成一片,我心中暗暗得意。老杜,老杜,你這個老狐狸,今天敗在我的手下了。
我一走出大門,就被麻叔捏著脖子提起來:“兔崽子,你到哪裡去下蛋啦?”
我坦率地說:“我沒去下蛋,我去吃牛蛋子了!”
“什麼?你吃了牛蛋子?”杜大爺驚訝地說。
我說:“我當然吃了牛蛋子,我吃了滿滿一碗牛蛋子!”
杜大爺說:“看看吧,隊長,你們是一家人,都姓管,我讓他看著牛,他卻去吃了一碗牛蛋子,讓這些牛全都趴在了地上,不死牛便罷,死了牛我一點責任都沒有!老董同志您可要給我作證。”
老董同志焦急地說:“別說了,趕快把牛抬起來。”
我看著他們哼哼哈哈地抬牛。抬起魯西,趴下雙脊;拉起雙脊,趴下魯西。折騰了好久,才把它們全都弄起來。
……
沒有撒謊,更不敢造謠,我實事求是地說:
“我跟於進寶到井裡去了。”
“什麼?”父親驚訝地睜大了眼睛。
我的圍著飯桌喝菜湯的兄弟姐妹們也用嘲笑的眼光看著我,我知道這些傢伙把我當成傻瓜,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我到井裡去乾什麼,當然也不能怨他們,因為這件事情的確離奇,如果我不是親身經歷,寧丁死我我也不會相信天底下竟然會存在著這樣的事。
“我跟著於進寶到他家後園那眼井裡去了。”我對他們儘量詳盡地說著:“昨天下午,我去找於進寶玩耍,玩了一會兒,口渴得很,於進寶家沒有水,於進寶就帶我到他家後園裡去找水喝,地家後園裡有一口很深的井……”
母親打斷我的話,問我,又像是自言自語:
“雜種,雜種,你一夜沒回來?你在哪裡睡的?”
“抬來吧,”叔叔說,“我可是從來不出診。”
“就來了,”孫七姑說,“我頭前跑來,先給您報個信兒。”
這時,從大街上傳來一個女人誇張的尖叫聲:
“痛死啦……親娘啊……痛死啦……”
孫七姑的弟弟孫大和孫二,用一扇門板將他們的母親抬到了醫院門前,放在了雪地上。他們的母親,一個瘦長的、與她的女兒形成了鮮明對照的、花白頭髮的女人,在門板上不斷地將身體折起來,然後又猛地倒下去。她的兩個兒子,將手抄在棉襖的袖筒里,目光茫然,果然像木頭一樣。叔叔惱怒地說:
“什麼東西!抬進來啊,放在外邊晾著,難道還怕臭了嗎?”
孫大和孫二將門板抬起來,別彆扭扭地想往門裡擠。叔叔說:
“放下門板,抬人!”
兄弟兩個一個抱腿,一個抱頭,終於把他們的母親抬到了診斷床上。叔叔喝了幾口茶水,搓搓手,上前給她診斷。老女人喊著:
“痛死了,痛死了,老頭子啊,你顯現神靈,把我叫了去吧……”
叔叔說:
“死不了,你這樣的,閻王爺怎么敢收!”
叔叔用手摸摸老女人烏黑的肚皮,說:
“化膿性闌尾炎。”
“還有治嗎?”孫七姑焦急地問。
“開一刀,切去就好了。”叔叔輕描淡寫地說。
“要多少錢……”孫大磕磕巴巴地問。
“五百。”叔叔說。
“五百……”孫二嘬著牙花子說。
這隻也許早就失去了煉丹走火本領的狐狸孑遺從我和妻子面前,流水落花般跑過,它的秀麗的腳趾抓得我心臟緊縮。妻子的指甲掐得我肉痛。在跑動中,它側著狹長的臉,用綠色的眼睛,鄙夷地瞄了我一眼。狐狸瞧我不起,它高傲得可以,它冷漠得要命。這隻偉大的狐狸,像一尊移動的紀念碑,從路上飄然而過,像一道紅色閃電,堅硬而滋潤。我無意中叫了一聲,長而恐怖,嘴巴張著不合,舌頭凍結,目光如線一樣粘在狐狸那條老練地道的雪尖尾巴上,狐狸跑到哪兒,就把線帶到哪兒。
狗和人雜沓地追來,狗無表情,人卻惡狠狠地罵我:你他媽的怎么站著不動!你腿有毛病?他們不敢戀罵,撇下我不管,急如星火地追下去,人跑成狗樣,狗跑成人狀,狐狸躍上河堤,
在那道壁立的白光上,投下一個邊緣朦朧的影子,狐狸的影子,使柳樹立刻綠得厲害。
這隻狐狸臉上的傲慢神情刺激著我的神經,它蔑視我,它使我把從前積累的關於狐狸的印象全部曝光。我在動物園見過鐵籠子裡一群紅狐狸,它們臭氣熏天,懶洋洋地蹲在陰暗潮濕的石洞裡,尖削的下巴使它們滿臉荒誕愚蠢。那次我跟那個單眼皮大眼睛的姑娘去看狐狸,奶油冰棍把她的嘴巴弄得黏乎乎的。她問:你為什麼像狐狸一樣陰沉?我說:我怕這鐵籠子。她吃驚地看著我憂傷的臉,我憂傷地看著她吃驚的臉。她說:遺憾嗎?我說:你聞得慣狐狸的味道嗎?她說:我有慢性鼻炎。我說:我們去看老虎吧。
狐狸翻過河堤,跳到枯燥滾燙的河沙上,宛若進了白色沙漠。它柔軟的爪子踩出一朵朵梅花,天上的金光,沙上的白光,把它夾成一個金銀狐狸。兩岸墨綠的垂柳排比而下,河堤的漫坡上一團團連續著荊條、紅柳、酸棗棵子,枯河之沙曲曲折折向前流著,沙子熱脹,摩擦有聲。狐狸在沙上跑,尾巴拖出一條痕跡。它鑽進叢生的灌木,不見了。那群漢子也下了河,低頭辨認著沙上的花紋。狗把鼻子觸到花紋上,可恥地對著人叫。三架飛機壓著狗頭飛過去。飛行訓練繼續進行。駕駛員都是面孔冷峻的小伙子,都不會眨眼睛。飛機有時飛得很高,有時飛得很低,飛低時,麥茬地里它們金黃色的大影子像河水一樣流動,機翼激起的硬風把野草按倒,枝桿強硬、葉子邊緣上生滿硬刺可以做止血藥用的大薊在伏地的野草中昂揚著紫紅色的花朵,
安護士從牆角拐出來,我認為她是為我走得如此風姿綽約雄赳赳氣昂昂,像個燙髮的紅衛兵小將。飛機成排地低飛過去,巨大的轟鳴聲把梧桐葉子都震翻了。
安護士說:老師,老師讓我問問你們,是流還是不流?
我說:流,堅決流。
安護士響亮地笑起來,我看她,她立刻把笑容斂起來,說:其實,這不算什麼大事,我們每天都給人流產,半個小時就完事。她用眼斜看著我,嘴對我妻子說:大嫂,老師是搞藝術的,你應該支持他。
妻子說:什麼狗屁藝術,嫁給他是我前輩子幹了缺德事。
安護士說:哎喲我的大嫂!全縣裡的女人也比不上你幸福。
妻子說:你知道我遭了多少罪?等他等老了,和我一般大的女伴都兩三個孩子了我才結婚,還是我拉著他去登的記。
安護士說:拉郎配。
妻子說:他像個小孩一樣,能把人氣死。
我說:行了。
麻嬸說:“杜大哥,您吃塊嘗嘗吧,也許吃到嘴裡就不臊了。”
麻叔罵麻嬸道:“這樣的髒東西,你也好意思讓杜大哥嘗?杜大哥家大魚大肉都放臭了,還喜吃這!”
杜大爺把那塊牛蛋子放到盤子裡,將筷子摔到老董同志面前,說:“說我家把大魚大肉放臭了是胡說,但你要說咱老杜沒斷了吃肉,這是真的,孬好咱還有一個乾屠宰組的女婿嘛!”
老董同志說:“老杜,您是我見到的最有福氣的老頭,公社書記的爹也享不到您這樣的福!”
“托您的福,”杜大爺說著,往外走,走了兩步,又回頭道,“隊長,我年紀大了,熬不了夜,前半夜我頂著,後半夜我可就不管了。”
麻叔說:“你不管誰管?你是飼養員!”
杜大爺說:“飼養員是餵牛的,不是遛牛的。”
麻叔說:“我不管你這些,反正牛出了毛病我就找你。”
杜大爺說:“你這是欺負老實人!”
杜大爺罵罵咧咧地走出來了。我生怕被他發現,一矮身蹲在了窗前。但他從燈下剛出來,眼前一摸黑,根本看不到我。我看到他頭重腳輕地走了出去。我趁機溜到灶間,掀開鍋,伸手往裡一摸,果然摸到一個碗。再一摸,碗裡果然有東西。我一下子就聞到了炒牛蛋子的味道。麻嬸真是個重契約守信用的好人。我端著碗就躥到院子裡。這時,我聽到杜大爺在大門外喊叫起來:“隊長,毀了!隊長,毀了!牛都趴下了!”
我可顧不了那么多了。我蹲在草垛後邊的黑影里,抓起牛蛋子就往嘴裡塞。我看到麻叔和老董同志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我聽到麻叔大聲喊叫:“羅漢!羅漢!你這個小兔崽子,跑到哪
里去了?”我抓緊時間,將那些牛蛋子吞下去,當然根本就顧不上咀嚼,當然我也顧不上品嘗牛蛋子是臊還是不臊。吃完了牛蛋子,我放下碗,打了一個嗝,從草垛後慢悠悠地轉出來。他們在門外喊成一片,我心中暗暗得意。老杜,老杜,你這個老狐狸,今天敗在我的手下了。
我一走出大門,就被麻叔捏著脖子提起來:“兔崽子,你到哪裡去下蛋啦?”
我坦率地說:“我沒去下蛋,我去吃牛蛋子了!”
“什麼?你吃了牛蛋子?”杜大爺驚訝地說。
我說:“我當然吃了牛蛋子,我吃了滿滿一碗牛蛋子!”
杜大爺說:“看看吧,隊長,你們是一家人,都姓管,我讓他看著牛,他卻去吃了一碗牛蛋子,讓這些牛全都趴在了地上,不死牛便罷,死了牛我一點責任都沒有!老董同志您可要給我作證。”
老董同志焦急地說:“別說了,趕快把牛抬起來。”
我看著他們哼哼哈哈地抬牛。抬起魯西,趴下雙脊;拉起雙脊,趴下魯西。折騰了好久,才把它們全都弄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