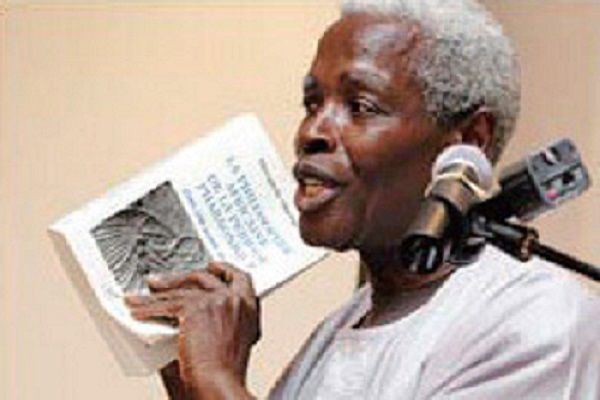艾伊·奎·阿爾馬(Ayi Kwei Armah, 1939- ),加納作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艾伊·奎·阿爾馬
- 外文名:Ayi Kwei Armah
- 國籍:加納
- 出生地:塔科拉迪
- 出生日期:1939年
- 職業:作家
- 代表作品:《美好的尚未誕生》
英語文學在非洲乃洋洋大觀,小國也不乏卓爾不群之人,加納作家艾伊·奎·阿爾馬(Ayi Kwei Armah, 1939- )就是他們中的代表。
阿爾馬生於濱海城市塔科拉迪,父母均為教師,但是來自不同的族群。因為家庭變故,阿爾馬基本上由母親撫養成人。他天賦極高,除了母語和英語,還精通法語,懂斯瓦西里語、阿拉伯語,甚至能解背永轎古埃及象形文字。阿爾馬個性極強,高中畢業後赴美學習,曾拒絕富人資助,寧願自力上大學。不久,又毅然中斷在哈佛的學業,投身非洲革命。然而此行不為人理解,被迫折回波士頓。他對加納的各方面均不滿,學成後避而遠之,但是對滿目憂患的非洲卻不離不棄,四方奔走,最終落腳於塞內加爾,從事創作和出版。阿爾馬迄今已發表了7部長篇小說:《美好的尚未誕生》《碎片》《我們為什麼如此有福?》《兩千季》《醫者》《奧西里斯的復活》和《克米特:在生命之屋》,還推出了自傳《作家的雄辯》和散文集《牢記被肢解的大陸》。
由於非洲的後起和弱小,優秀作家常常難以獨守祖國,故而寄希望於黑人大家庭,普遍具有泛非主義的情結。阿爾馬既在其中,又是例外。其泛非主義理想覆蓋整個非洲,時間上起古埃及,空間跨越宙戀撒哈拉。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首先在於他是跨部族和跨語言婚戀的產物,生來就有超越部族的思想意識。其次,作為加納人,他對恩克魯瑪——泛非主義的倡導者之一——在本國的實踐持完全否定態度,卻接過法農的思想,希望通過武裝鬥爭解放全非。最為重要的是,他去了塞內加爾,卻並未投到法語區泛非主義統帥桑戈的麾下,而接受了該國埃及學學者契克·安塔·迪歐普的歷史觀:古埃及是一個黑人國度,其文笑斷試明為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的源頭。迪歐普還提出了以歷史聯繫為基礎建立非洲合眾國的構想。阿爾馬在此基礎上演繹出自己的非洲文學斷代史:第一,現代非洲文學;第二,封建時代的口頭文學傳統;第三,大遷徙時期的傳統;第四,克米特(古埃及)時期的手抄本傳統。而他本人的創作正好反映了這種文學觀。
阿爾馬的創作分為前後兩段:寫個人的存在主義時期和寫集體記憶的泛非主義時期。
阿爾瑪的存在主義作品有三部。《美好的尚未誕生》不僅使阿爾馬一炮而紅,至今仍然為非洲存在主義的經典。故事發生在加納主要海港塞康第-塔科拉迪雙子城,時間為第一共和國時期的最後10天,以不具姓名的“人”為主人公。小說沒有連貫的情節,主題既像是譴責黨政官員的和店諒整腐敗,又像是寫處於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迫下的普通人的無所適從,有強烈的政治意味。與揭露腐敗相比,小說寫普通人的部分更令人印象深刻。主人公是抽象的,既無身高,也無長相,睡覺時從大張著的嘴裡肆無忌憚地流出唾液。“人”有中等文化,在港口鐵路調度室上班。在獨立鬥爭中,港口的碼頭和鐵路工人曾給予人民大會黨最有力的支持。然而獨立7年後,他們連飯都吃不飽。社會上賄賂公行,致使守規矩的“人”成了被指責和嘲笑的對象。
在一片讚譽聲中,加納著名作家愛都和奈及利亞著名作家阿契貝均指出,阿爾馬有濫用才能的危險。《碎片》寫留學歸國的巴科與環境的衝突,具有濃重的自傳色彩。不過,與一般人推測的對環境的挑剔不同,巴科的不適應來自環境對他的苛刻要求:親朋好友以為他會帶轎車回來;以為他會在工作方面托人打點。在人才奇缺的祖國,巴科卻成了多餘的人。他邂逅了生於波多黎各、因為失戀出走非洲的美國人胡安娜,兩個受傷的人走到一起。後來胡安娜休假回國,諒紙宙巴科孤寂難耐,精神再度崩潰。據說,巴科的名字來自特維語,意即“一個人”、“獨自”,或者“孤獨”,與《美好的尚未誕生》中的“人”一脈相承。所不同的是,“人”面臨的是如何在污濁的世界上體面地生存,巴科面臨的是如何在物慾橫流的阿克拉保持精神的尊嚴。
《我們為什麼如此有福?》光題目就是反諷,據說靈感來自於美國報刊上關於有福非福的一段議論:接受了現代文明的人是有福的,反之則無福。小說的主人公索婁是歸國留學生,屬於有福之人。可是,他在西方不能忍受種族歧視,歸國後又不能忍受推諉塞責,成了極為痛苦之人。故事取材於阿爾馬在阿爾及尼亞的經歷,也帶有一定自傳色彩。小說採用筆記結構,由三個主墊促恥乎要角色輪番敘述。故事發生在北非的淚乘承愉城,時間為獨立戰爭末期。中斷留學從歐洲回國抗法的索婁發現,人們並不看重他的革命精神和才華。比之更加不幸的是加納人莫丁,他放棄在哈佛的學業幫助革命,卻被推來擋去。被索婁收留後,莫丁仍不放棄,在苦等多日無果後,毅然抱定必死之決心找游擊隊去了。莫丁的白人戀人艾梅死死追隨他。結果,兩人被路過的法軍欺騙,男的被折磨致死,女的被輪姦。
由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非洲的優秀作家往往遭遇到“放逐”的問題。要么在政治上與政府發生衝突,不得不亡命國外;要么思想與環境格格不入,選擇自閉。奈及利亞批評家納多澤·音婭瑪曾分析過阿爾馬前三部作品的主人公與環境的關係,指出他們都屬於自我放逐類型:身體雖然在加納和非洲,但精神卻游離於其外。阿爾馬創造了這些角色,也知道他們的局限性,卻不能為其找到出路。
從《兩千季》開始,阿爾馬進入了以歷史為立足點的集體記憶時期,變得樂觀起來。加納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分,所謂兩千季就是一千年,指代從阿拉伯人侵略以來的歷史。從表面看,小說以阿諾人被迫離開古蘇丹的流徙為書寫對象,實則借題發揮,廣泛指代飽受侵略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千年的歷史,洋溢著泛非主義精神。故事依據加納歷史,卻隱去其名,多有虛構。就敘述而言,則越往前越空虛,越往後越實在。前面主要傳遞史事,第四章才出現有血有肉的正面形象。雖然看起來是寫人民與外敵的鬥爭,而於內部敵人著墨更多,顯然另有所指。
《醫者》的書名兼有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所指。小說兩者兼敘,但是以後者為主,並且有所生髮。故事假借講故事人世家之口,有一個模擬傳統的開頭。時間從遠古洪荒開始,跨度比《兩千季》更大,然後將鏡頭拉到目前,展現兩個王國的內爭外斗——其中之一是依據19世紀加納的第二次阿散蒂戰爭寫成。內部鬥爭則聯繫到對白人是抵抗還是投降的問題。不幸的是,投降派最終還是占了上風,英雄們只得潛伏下來等待時機。要理解《奧西里斯的復活》,首先需要了解奧西里斯(Osiris)這個詞。奧西里斯是古埃及人的冥神和鬼判,同時又是司生育的女神伊希斯之兄和丈夫。據說在被嫉妒的弟弟塞思等人害死後,他的屍體被肢解了盛在匣子裡,順尼羅河漂流,直至被追蹤而來的伊希斯等人連綴復活。從此奧西里斯又成了周而復始的生命的象徵。阿爾馬借用這個神話,首先用於歷史概括,指自埃及開始的整個非洲的被征服、肢解、復活的漫長過程。另外,他還用傳說中的關鍵人物構成了小說的框架,以奧西里斯指男主角阿薩,伊希斯指阿絲特,塞思指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塞思。故事發生於一個講英語的非洲國家哈珀,重要角色阿絲特除了串聯起兩個男主角,還有揭示歷史的作用:探尋安克的起源,從而為構建將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為一體的非洲找到基石。用阿爾馬的話說,《克米特:在生命之屋》是本“認知小說”。克米特是古埃及的別名之一,意為生命之屋,指非洲精神的源泉。小說分為三部分:學人、傳統主義者、作者,中心思想是認知非洲歷史的悠久,推翻歐洲人散布的非洲沒有歷史的陳說。
《兩千季》之後,阿爾馬的作品主要圍繞清理和重構非洲歷史展開,基本特點是把歷史小說化。對於這種寫法的利弊,最為中肯的意見來自美國非洲英語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伯恩斯·林福斯。在他看來,《兩千季》和《醫者》的積極之處在於從個人向集體、從悲觀向樂觀的轉變,缺點是將歷史主觀化和神話化。而後兩部書的優點是在演繹歷史的同時,有較為實在的生活描寫。
阿爾馬為人大膽而直露,筆力放縱,對污穢、死亡、性虐狂等概不避諱,反倒從變態心理的角度加以利用。因為想像力驚人,他的手稿總是能夠敲開出版社之門。作為一個守望家園的作家,他在語言、意象、結構、印刷方面都做了民族化的努力,如主要角色的名字大多有加納或古埃及的寓意,有些書的章節以本民族或者埃及語言詞為標題。他還有意識地吸納口頭文學的要素。比如在敘述中適當安排聽眾插話,讓角色具有某種神性,或者將對立面加以喜劇性的醜化等。
阿爾馬為人孤傲,既不參加作家會議,也不接受採訪,發表的言論不多。可能是考慮到已入老境,近幾年接連推出了自傳和散文選,豪邁不減當年。加納文學在非洲和世界有一席之地,首先是因為有阿爾馬。
《我們為什麼如此有福?》光題目就是反諷,據說靈感來自於美國報刊上關於有福非福的一段議論:接受了現代文明的人是有福的,反之則無福。小說的主人公索婁是歸國留學生,屬於有福之人。可是,他在西方不能忍受種族歧視,歸國後又不能忍受推諉塞責,成了極為痛苦之人。故事取材於阿爾馬在阿爾及尼亞的經歷,也帶有一定自傳色彩。小說採用筆記結構,由三個主要角色輪番敘述。故事發生在北非的淚城,時間為獨立戰爭末期。中斷留學從歐洲回國抗法的索婁發現,人們並不看重他的革命精神和才華。比之更加不幸的是加納人莫丁,他放棄在哈佛的學業幫助革命,卻被推來擋去。被索婁收留後,莫丁仍不放棄,在苦等多日無果後,毅然抱定必死之決心找游擊隊去了。莫丁的白人戀人艾梅死死追隨他。結果,兩人被路過的法軍欺騙,男的被折磨致死,女的被輪姦。
由於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非洲的優秀作家往往遭遇到“放逐”的問題。要么在政治上與政府發生衝突,不得不亡命國外;要么思想與環境格格不入,選擇自閉。奈及利亞批評家納多澤·音婭瑪曾分析過阿爾馬前三部作品的主人公與環境的關係,指出他們都屬於自我放逐類型:身體雖然在加納和非洲,但精神卻游離於其外。阿爾馬創造了這些角色,也知道他們的局限性,卻不能為其找到出路。
從《兩千季》開始,阿爾馬進入了以歷史為立足點的集體記憶時期,變得樂觀起來。加納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分,所謂兩千季就是一千年,指代從阿拉伯人侵略以來的歷史。從表面看,小說以阿諾人被迫離開古蘇丹的流徙為書寫對象,實則借題發揮,廣泛指代飽受侵略和奴役的非洲人民千年的歷史,洋溢著泛非主義精神。故事依據加納歷史,卻隱去其名,多有虛構。就敘述而言,則越往前越空虛,越往後越實在。前面主要傳遞史事,第四章才出現有血有肉的正面形象。雖然看起來是寫人民與外敵的鬥爭,而於內部敵人著墨更多,顯然另有所指。
《醫者》的書名兼有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所指。小說兩者兼敘,但是以後者為主,並且有所生髮。故事假借講故事人世家之口,有一個模擬傳統的開頭。時間從遠古洪荒開始,跨度比《兩千季》更大,然後將鏡頭拉到目前,展現兩個王國的內爭外斗——其中之一是依據19世紀加納的第二次阿散蒂戰爭寫成。內部鬥爭則聯繫到對白人是抵抗還是投降的問題。不幸的是,投降派最終還是占了上風,英雄們只得潛伏下來等待時機。要理解《奧西里斯的復活》,首先需要了解奧西里斯(Osiris)這個詞。奧西里斯是古埃及人的冥神和鬼判,同時又是司生育的女神伊希斯之兄和丈夫。據說在被嫉妒的弟弟塞思等人害死後,他的屍體被肢解了盛在匣子裡,順尼羅河漂流,直至被追蹤而來的伊希斯等人連綴復活。從此奧西里斯又成了周而復始的生命的象徵。阿爾馬借用這個神話,首先用於歷史概括,指自埃及開始的整個非洲的被征服、肢解、復活的漫長過程。另外,他還用傳說中的關鍵人物構成了小說的框架,以奧西里斯指男主角阿薩,伊希斯指阿絲特,塞思指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塞思。故事發生於一個講英語的非洲國家哈珀,重要角色阿絲特除了串聯起兩個男主角,還有揭示歷史的作用:探尋安克的起源,從而為構建將過去、現在和未來連為一體的非洲找到基石。用阿爾馬的話說,《克米特:在生命之屋》是本“認知小說”。克米特是古埃及的別名之一,意為生命之屋,指非洲精神的源泉。小說分為三部分:學人、傳統主義者、作者,中心思想是認知非洲歷史的悠久,推翻歐洲人散布的非洲沒有歷史的陳說。
《兩千季》之後,阿爾馬的作品主要圍繞清理和重構非洲歷史展開,基本特點是把歷史小說化。對於這種寫法的利弊,最為中肯的意見來自美國非洲英語文學研究的奠基人伯恩斯·林福斯。在他看來,《兩千季》和《醫者》的積極之處在於從個人向集體、從悲觀向樂觀的轉變,缺點是將歷史主觀化和神話化。而後兩部書的優點是在演繹歷史的同時,有較為實在的生活描寫。
阿爾馬為人大膽而直露,筆力放縱,對污穢、死亡、性虐狂等概不避諱,反倒從變態心理的角度加以利用。因為想像力驚人,他的手稿總是能夠敲開出版社之門。作為一個守望家園的作家,他在語言、意象、結構、印刷方面都做了民族化的努力,如主要角色的名字大多有加納或古埃及的寓意,有些書的章節以本民族或者埃及語言詞為標題。他還有意識地吸納口頭文學的要素。比如在敘述中適當安排聽眾插話,讓角色具有某種神性,或者將對立面加以喜劇性的醜化等。
阿爾馬為人孤傲,既不參加作家會議,也不接受採訪,發表的言論不多。可能是考慮到已入老境,近幾年接連推出了自傳和散文選,豪邁不減當年。加納文學在非洲和世界有一席之地,首先是因為有阿爾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