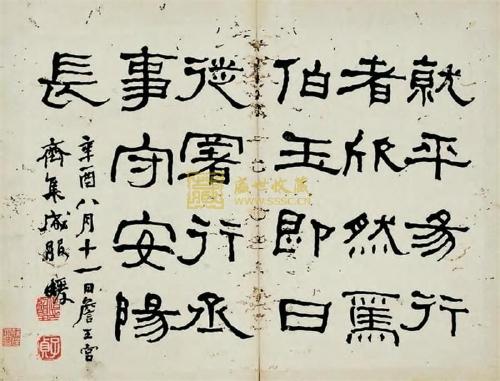《與汪菊士論詩》是清代何紹基寫的一篇論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與汪菊士論詩
- 創作年代:清代
- 作者:何紹基
- 類型:論文
正文
凡學詩者,無不知要有真性情,卻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詩時方去打算也。平日明理養氣,於孝悌忠信大節,從日用起居及外間應務,平平實實,自家體貼得真性情,時時培護,時時持守,不為外物搖奪。久之,則真性情方才固結到身心上,即一言語,一文字,這個真性情時刻流露出來。然雖時刻流露,以之作詩作文,尚不能就算成家者。以此真性情雖偶然流露,而不能處處發現,因作詩文自有多少法度,多少工夫,方能將真性情搬運到筆墨上。又性情是渾然之物,若到文與詩上頭,便要有聲情氣韻,波瀾推盪,方得真性情發現充滿,使天下後世見其所作,如見其人,如見其性情。若平日知持養,臨提筆時要他有真性情,何嘗沒得幾句驚心動魄的,可知道這性情不是暫時撐支門面的,就是從人借來的,算不得自己真性情岜。
詩是自家做的,便要說自家的話,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話頭,都與自己無涉。如說山水,便有高深的閒話;說古蹟,便有感慨陳跡的閒話;說朋友,便有投分相思惜別的閒話,爾也用得,我也用得,其實大家用不著。疑者曰:“焉知彼此不同要說這句話?”豈知偶然間同一句兩句,是不能無的,然合上下看來,總要各出各意,句同意必不同,才是各人自家的話,斷無公共用得的。我常教子弟以不誠無物,若不是自家實心做出來,即入孝出悌,只算應酬。若是實心出來,即作揖問候,亦是自家的實事。試看誠心恭敬的君子,其作揖問候,氣象亦與人不同,況語言文字乎!
落筆要面面圓,字字圓。所謂圓者,非專講格調也,一在理,一在氣。理何以圓?文以載道,或大悖於理,或微礙於理,便於理不圓。讀書人落筆,謂其悖理礙理,似未必有其事,豈知動筆用心,稍偏即理不圓,稍隔即理不圓,此病作家中尚時時有之,況初學乎?試言其略:如方仕進,向上動輒雲歸隱;本事未必能應變,動輒見危難而作旁觀之太息;居親喪而吟詠,賦悼亡而過傷。此悖與礙也。悼亡既如此痛,則以不續弦為是。泛泛友朋,即作摯交語,則除此友朋外,更不相與他人為是。以此類推,要理圓是極難了,非平日平心積理,凡事到前銖兩斟酌,下筆時又銖兩斟酌,安得理無滯礙乎?氣何以圓?用筆如鑄元精,耿耿貫當中,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萬折可也,一戛即止可也,氣貫其中則圓。如寫字用中鋒然,一筆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韻,安得不雄渾,安得不淡遠?這事切要握筆時提起丹田,高著眼光,盤曲縱送,自運神明,方得此氣。當真圓,大難大難。
余嘗謂山谷云:“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此說“不俗”兩字最精確。“俗”,不是壞字眼,流俗污世,到處相習成風,謂之“俗”。人如此,我亦如此,不能離開一步,謂之“俗”。做人如此,焉能臨大節而不奪乎?現在做何事,便盡現在之理,故預先籌畫到大節的,往往臨時不濟;惟素位而行者,利害私見,本不存於中,臨大節也只是素位而行,如何可奪。行文之理,與做人一樣,不粘皮帶肉則潔,不強加粉飾則健,不設心好名則朴,不橫使才氣則定。要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傍前人,不將就俗目。有時遇題即有詩則做,有時遇題而無詩則且不做。然道理熟,功夫熟,未有遇題而無詩者。道一本而萬殊,遇題無詩,到底是理之萬殊者,未看得博、想得穿耳。古詩家、書家能不俗者,都是此法。惟山谷此語說得確,惟余體會山谷此語到文字上見得通透,是否,是否?
昔人云:詩必有為而作,方為不苟。此語不易解。如遇忠孝節烈有關風教者,樂得做一篇,然此等題,作者或百人,佳篇不得三四,除此三四篇外,雖有為而作,仍無關係了。有時小題乘興、而所見者遠大,則不必有為而作,而理足詞文,字句之外,大有關係。故大家之集,題目大小雜出,而未有無正經性情道理寄託者,此之謂有為而作,非必盡要在重正大題也。惟冶遊之題,必無有關係語,古人亦有存者,偶不經意,非後人所當效也。且詩文先要使子弟看得去,為要做詩方讀書,如何來得及,然細心打量,亦無來不及者。人可一日不讀書乎!當讀者何書?經史而已。六經之義,高大如天,方廣如地,潛心玩索,極意考究,性道處固啟發性靈,即器數文物,那一件不從大本原出來。考據之學、往往於文筆有妨,因不從道理識見上用心,而徒務鉤稽瑣碎,索前人瘢垢,用心既隘且刻,則聖賢真意不出,自家靈光亦閉矣。故讀經不可不考據,而門徑宜自審處。恃孔、賈之符,倚程、朱之勢,互相誹薄者,皆無與於聖經者也。子史百家皆以博其識而長其氣,但論古人宜寬厚,不宜刻責,非故為仁慈也、養此胸中春氣,方能含孕太和。若論史務刻,則讀經書難得力.蓋聖人用心,未有不從其厚者。知此意則經寞之學可做成一貫矣。積理養氣,皆從此為依據。至於作詩,則吾嘗謂天下吝嗇人、刻薄人、狹隘人、粘滯人俱不會作詩,由先不會讀書也。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
詩無佳句則馨逸之致不出;然務求佳句,尚非詩之正路。詩以意為主,韻為輔。句之佳者,乃時至氣化,自然流出;若勉強求之,則往往有椎鑿痕跡。如草木氣茂,開出好花,誠為可觀;亦有枝幹節葉勃勃有致而不開花者,其勁氣秀色,自不可掩也。
今人通籍或成人後,即不肯高聲讀書,此最是大病。古人之書固以義理為主,然非文章無以發之,非音節無以醒之。即六經之文,童年誦習時,知道什麼文字,壯後見道有得,再一吟諷,神理音節之妙,可以涵養性情,振盪血氣,心頭領會,舌底回甘,有許多消受。至於二史諸子百家集,本是做出底文章,若不高聲讀之,如何能得其推敲激昂之勢?至古人作詩,原為被之管弦,播之樂府,後來樂府與詩家分路,然試取兩京、六朝、唐、宋大家詩篇讀之,無不音節同足,聲情茂美;間有近於木拙者,然細繹低諷之,亦自有朱弦三嘆之妙。近代詩家,每一大集中,可以擊節高歌者,不得幾篇。漁洋、竹垞詩無可讀,以有藻色無精意,一讀則淺;愚山、荔裳有邊幅無雄氣,一讀則窘;梅村歌行兼學少陵、香山,然杜、白之作,愈唱愈高,而梅村愈唱愈低,徒覺詞煩而不殺,以無真理真識真氣也。顧亭林詩多可讀,經史味深也;高江村詩多可誦,儒雅道在也;然顧、高之詩,罕有人傳者,由今人不肯高聲瀆前人之詩,故黑白不分耳。至於自家作詩,必須高聲讀之。理不足讀不下去,氣不盛讀不下去,情不真讀不下去,詞不雅讀不下去,起處無用意瀆不起來,篇終不混茫瀆不了結。真箇可讀,即可管弦樂府矣,可管弦樂府方是詩:略舉一二。要之本朝詩可擊節讀者極少,仲則、心餘可矣而少餘昧,簡齋淺,夢樓陋,覃溪拙,稚存、船山客氣。
正經用功,只有閉戶之一法。逢人開口談學問,其學問可知;逢人開口談詩文,其詩文可知。今人但求人知,不務自家心得,有人誇他是名士,是才子,便寵耀十分,真是可鄙。對客揮亳,動輒累紙,間出奇語,喧然傳誦,比如飛蚊一響,豈百年安身立命之地乎。苦吟一宵,難得佳篇,即前人大家集中,罕有百篇傑出者,咄嗟而辦,果誰欺耶!況功夫內斂,則愈做愈深。道理靜求,則愈揮愈密。世間居積致富者,終年營營籌算,暗布潛謀,唯恐妻子知覺,一旦成就,則買田開市,氣象勃然,而此本人仍然樸陋如窶人子,如此方是真致富人。此法甚佳,學者當效之。
地盤最要打得大,如有一塊大地,則室屋樓台,聽其所為,若先只方丈地,則一亭已無可布置矣。苟且之見,動雲學陶、韋,不知陶、韋胸中多少道理,人品多少高冷,而果能陶、韋乎?好高者動雲兩京,不知兩京時所見所聞皆周、秦,家世傳衍皆周、秦,其人並不必為詩也,一篇一句,偶然傳後,而吾乃以多篇多句者效之,與《法言》文中僭擬聖經何異?即使真肖,亦優孟衣冠耳。做人要做今日當做之人,即做詩要做今日當做之詩,必須書卷議論,山水色相,聚之務多,貫之務通,恢之務廣,煉之務重,卓之務特,寬作丈量,堅作築畚,使此中無所不有,而以大氣力包而舉之。然未嘗無短篇也,尺幅千里矣;未嘗無淡旨也,清潭百丈矣。譬如一所大院,正房客屋,幽亭曲榭,林鳥池魚,茂草荒林,要無所不有,才好才好。
是道理精神都從天地到人身上,此身一日不與天地之氣相通,其身必病;此心一日不與天地之氣相通,其心獨無病乎?病其身則知之,病其心則不知,由私意物慾蒙蔽所致耳。今想不受其蒙蔽,除卻明理,更無別說。雖然,亦有二說焉:讀書閱事,看到事物之所以然與天地相通,是一境;清明之氣,生於寂處,心光一片,自然照澈通明,亦是一境。此二境者,相為表里。離此二境,非靜非動時,但提起此心,要它刻刻與天地通尤要。請問談詩何為談到這裡?曰:此正是談詩。
聖人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說《三百篇》也。學詩不學《三百篇》可乎?作詩不可以興觀群怨可乎?興觀群怨四字,蘊藉深厚之至矣,猶曰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者,聖人之深於詩也。“不學詩,無以言。”
自《易》、 《書》、 《禮》,聖人所以教世型後者,無不至矣。所以彌縫缺漏,長善救失,在於無形,而《詩》作焉。故《詩》者,聖人教人盡頭方法也。《詩》所不能救,而《春秋》作焉,聖人所大不得已也。聖人務在教人為良民,為賢士臣,《春秋》誅賞,非所願筆之於書也。千萬世來,所以防民情偽者,法無不具,其實惟詩教為多,但人不覺耳。《春秋》經之支流,遂為編年紀事。歷代之史,徒冗且雜,有關懲勸者亦僅矣,而詩歌亦因之衰敝,此則聖人所不及料也。學詩者不可不知此意。
詩貴有奇趣,卻不是說怪話。正須得至理,理到至處,發以仄徑,乃成奇趣。詩貴有閒情,不是懶散。心會不可言傳,又意境到那裡,不肯使人不知,又不肯使人遽知,故有此閒情。
聖人且說“好古敏以求之”,後人敢說不師古。然試看聖人學古是怎樣學的,學一個人罷了,乃合堯、舜、禹、文、周公、老彭、左丘明、郯子、師襄而無不學之,可見聖人學古,直以自己本事貫道三古,看是因,全是創也。後儒去聖人遠矣,其學古也,奈何曰與聖人一樣。何也?學周公像周公,學老子像老子,無論必無此事,即有之,亦優孟而已。學詩要學古大家,只是借為入手,到得獨出手眼時,須當與古人並驅。若生在老杜前,老杜還當學我。此狂論乎?曰:非也。松柏之下,其草不植,小草為大樹所掩也,不能與天地氣相通也;否則小草與松柏各自有立命處,豈假生氣之於松柏乎?記得隨園有云:“與其做總督衙門的門上,自然不如典史衙門的官主。”此語卻有理,只是小小官主,也不是容易做的。古人詩文集,往往從其子弟門人輯錄傳世,然如杜、韓、權、陸等巨集,豈能徒靠他人存錄乎?蓋雖手自存稿而不肯明言,即自命必傳,到此時便亦自有蘊藉含蓄之法,所以養文章之福,存羞恥之界也。《三百篇》何嘗自著姓名乎?兩京、六朝始有最錄之集,然零星墜散,亦賴後人收拾。唐人存集,亦不矜矜自鳴,必須傳後。白香山自藏詩本於廬山,乃偶然別致事,如羊叔子沉碑之意,只是風雅佳話耳。宋人多自定集,去古遠矣。元、明以來,乃有年年訂集,每數十百篇即題一集名,勢不能不綴輯湊衍充其篇幅,又動輒要人作序,要人題詞誇詡。嗚呼!廉恥道喪,尚雲詩乎!願與學者共戒之也。
凡事看立志何如,若所志不過眼前名士,當世詩翁,借圖聲譽,則但取古詩唐詩選本,揣摩幾篇,近人詩集,涉獵幾部,只要肯做,不怕不翁。若要自走一路,自名一家,或冷淡,或兀傲,或博雅,或風韻秀婉,或山水模寫清妙,須自己要學這一路,看這一路,不雜不間,是不容易的。若想做個一代有數的詩人之詩,則砥行積學,兼該眾理,任重致遠,充擴性情之量,則天地古今相際。而用筆之法,行氣之準,如何得厚得重得空得實得精得大。此志最高,能到不能到,自有氣數管著;而真立此志者,蓋亦不多也。
天天起來題圖和韻,誠屬無味。然作家又有一種習氣,說生平不喜題圖,不愛次韻,如此便算高乎?詩人不詩人,全不在此:只是題圖,看是什麼圖,有故實有道理,可藉以發攄自己才情見識,才好與它題;若人人想的行樂圖,其人不自亮,我又從而文采之,豈不增醜?和韻至坡、谷為極盛,然如和陶詩,許多理趣,山谷和韻,奇致層出,何曾不自見胸次,無庸高論也。
立身應世為學大要,不外一藏字,於詩道尤要尤要。說不盡,寫不盡,時時領略此理而已。
凡做一事,必兼做別事,此一事方得好。專做詩,詩不能工也。隨時隨事都不是詩,都是詩之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