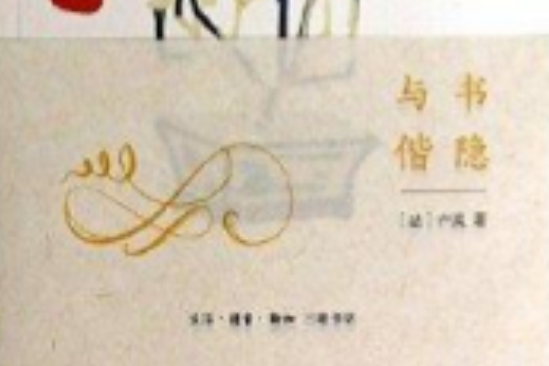《與書偕隱》是盧嵐女士近年發表在《作家》雜誌上的專欄文字的結集。書中所談作家、新書、文壇動態、文藝思潮之類話題,一是有豐富的本土資訊和第一手資料,不隔,二是行文經營不是率爾出手,似可見出頗費沉吟的慎重,文字講究,不像有些專欄那么水,那么淺,那么粗糙。
基本介紹
- 書名:與書偕隱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頁數:309頁
- 開本:32
- 作者:盧嵐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08047410, 710804741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與書偕隱》作者以優美、舒緩、細緻的筆觸,介紹法國文化全貌。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盧嵐
盧嵐,旅法作家,1962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外語系,著名學者梁宗岱先生的高足。曾任教於中山大學、廣州外國語學院,20世紀70年代赴法深造於巴黎大學法國文學系。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把水留給我》、散文集《凡爾賽的噴泉》《巴黎讀書記》,譯有《故夢》《山丘之水》,整理《熱愛生命:蒙田試筆》等梁宗岱著譯精華六種。
盧嵐,旅法作家,1962年畢業於中山大學外語系,著名學者梁宗岱先生的高足。曾任教於中山大學、廣州外國語學院,20世紀70年代赴法深造於巴黎大學法國文學系。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把水留給我》、散文集《凡爾賽的噴泉》《巴黎讀書記》,譯有《故夢》《山丘之水》,整理《熱愛生命:蒙田試筆》等梁宗岱著譯精華六種。
圖書目錄
第一編帕斯捷爾納克的幸福歷程
隨風起舞
海明威,以人生灌溉作品
當里爾克遇上羅丹
解讀福樓拜
勒克萊齊奧的浪子三弦
格里耶和“新小說”
與歷史開玩笑
當鬥牛進入鬥獸場
一頭習慣了冬天的熊
大仲馬,從現實到神話
落入水中的樹幹
與身世捉迷藏
薩特總值的遞減
地面地下,情人敵人
梁宗岱的審美世界
獨立市橋人不識
當《一無所知》返回巴黎
阿拉不承擔責任
我走了
戈多來也不來
思想是一種聲音
第二編伊斯坦堡的憂鬱
普希金放逐敖德薩
契訶夫,希望的殺手或深沉的悲憫
詩後的藍波
《基督山伯爵》的三生三世
福樓拜與迦太基
蕭邦與喬治桑的冬日奏鳴曲
特洛伊,從傳奇故事還原為歷史
竇西泛海來
作家手稿,再見!
第三編作家的榮譽與困惑
走過“紅色天堂”
是“海燕”還是“金絲雀”
歷史與精神分析法
莫失我,莫失你
一張照片,一本書
隨心所欲柯列特
薩岡的多彩人生
隨風起舞
海明威,以人生灌溉作品
當里爾克遇上羅丹
解讀福樓拜
勒克萊齊奧的浪子三弦
格里耶和“新小說”
與歷史開玩笑
當鬥牛進入鬥獸場
一頭習慣了冬天的熊
大仲馬,從現實到神話
落入水中的樹幹
與身世捉迷藏
薩特總值的遞減
地面地下,情人敵人
梁宗岱的審美世界
獨立市橋人不識
當《一無所知》返回巴黎
阿拉不承擔責任
我走了
戈多來也不來
思想是一種聲音
第二編伊斯坦堡的憂鬱
普希金放逐敖德薩
契訶夫,希望的殺手或深沉的悲憫
詩後的藍波
《基督山伯爵》的三生三世
福樓拜與迦太基
蕭邦與喬治桑的冬日奏鳴曲
特洛伊,從傳奇故事還原為歷史
竇西泛海來
作家手稿,再見!
第三編作家的榮譽與困惑
走過“紅色天堂”
是“海燕”還是“金絲雀”
歷史與精神分析法
莫失我,莫失你
一張照片,一本書
隨心所欲柯列特
薩岡的多彩人生
序言
如果人家告訴你,說他買了一本好書,乍聽下,你抓不準要處,什麼書?小說?哲學?歷史?科幻?好在哪裡?內容豐富?角度殊眾?別具風格?要是人家說買了一本暢銷書,你馬上就明白了,大抵是一本出版商賺了錢,作者也賺了錢的流行書。這類書經常是《廊橋》之類,一男一女,床上床下;也可能是大明星、社會名流的羅曼史,尤其是新鮮揭秘。暢銷也會忽然掉到童話、科幻作品頭上,如哈利·波特,但像皇上的寵幸,不可多得;保健、食療、傳記會有一定銷路;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偶然會走俏,但較少聽說;至於文學作品,不說也罷。
每年書展的交易數字龐大,說明書的健康狀況尚可,但文學作品就不可同日而語,它對書商的成交數字不再起大作用。出版社要賺錢,就指望非文學作品,賺了錢,才回過頭去出幾本名家著作,作為招牌貨,算是一種交代。在銀角子的大前提下,商業價值的標準代替了文學價值的標準。文學雜誌銷量不走俏,品種越來越少,報紙上的文學版被縮小或砍掉,出版商遇上文學書稿,先皺眉頭。
另一方面,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可成為作家,法國就有超過一百四十萬人已經寫了一部手稿。在被調查的人當中,有32%已經寫成或者想寫一本書,也就是說,法國有三分之一人想成為作家。然則,芸芸眾多的作家當中,有多少人能夠成得了一個小氣候的?總是狹隘的個人意識多於普遍意識。以三分之一時間來照鏡,三分之一看肚臍,三分之一來回味。總是讓我來談談我,讓大家來談談我,我只對我感興趣。評論一個作家的角度,從韻事,尤其風流韻事出發的多,從作品出發的少。過去作家是多題材創作,天上地下,人神野獸,道德罪罰,精神肉體,現在的寫作題材總帶有目的性,著重銷路,不惜討好。獲得一定成就的當代作家,著眼的題材跟過去也不一樣,在法國,大抵致力於精神分析,或開拓某一世俗專題,如紀德的精神探索,薩特的存在主義,西蒙·德·波伏瓦對女權的呼籲。
文學所面臨的局面,是內容與手法都不再引起讀者共鳴?是讀者對社會新聞,對“八卦”現象更感興趣?或者,是迅速發展的科技和資訊社會,要求更多的是智力、推理、知識,而非文學?事實上,學校寧可急於教會學生使用電腦,而不急於教他們怎樣欣賞普魯斯特,你能夠說學校盲目或差錯?新科學,新技術,人文科學,的確將文學擠到牆角去了。作家為尋求出路,只好逆流而上,學會給文學拌上醬料。於是偵探、科幻、言情、心理分析、世俗專題、揭自己內幕或別人內幕的作品越來越多。離奇怪誕的非正統文學作品,紛紛登上書店的書架。暢銷書,往往就藏在這些書籍當中。
早在1947年,穆尼耶(E.Moullier)已宣告文學的輝煌時代的過去,文學經歷了它的燦爛時期後,不再給人帶來新火花:“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絢麗奪目,盛極一時的文學時代……這個煙花回落到自己身上。”
不管從事文學,或醉心文學的人如何不甘心,文學的大時代,大作家的時代也許已結束,一如偉人時代的結束。我們不需要喧天嘩地的偉人,只要好人,要與民眾共呼吸的正直人。“聖人恆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就是說,國君沒有自己的喜惡,以百姓的喜惡為自己的喜惡;大作家一時沒有也罷,可以要些好作家,要說真話,具深度,有責任心的作家。文學是證明人的存在的方法,它以愛,以恨,以喜,以怒,以幽默來闡釋人生。文學可以道出人的生存困境,但不可能改變世界,唯其不可能,還要不斷地道出,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它的立足點。都說實用書籍有市場;有關文化現象的,如繪畫、雕塑、電影等也有一定讀者,但這類作品,如果使用的語言不足以表達其概念或觀念,不一定是一本成功的書。要觸動人的感覺、直覺和審美,文學語言是唯一的手段。它從細節深入事物的內部,以捕得正著的字眼,把敘述者的意願、動機和感受傳遞給讀者。尤其,如果沒有文學的陶冶,又怎能指望有審美的判斷和鑑賞能力?
文學的狀態不好,但文學的明天還在唱。一種藝術永遠不會安樂死。不管非文學書籍氣勢如何迫人,一本好書會按照它本身的價值,最後回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實用書自有它的實用處;暢銷書只標誌某一時期讀者的情緒,不一定代表本身有什麼價值。而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就像人擁有生命,會在大浪淘沙中存活下去,人物會家喻戶曉,名氣比真人更大。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文學家,寧可保衛文學的純度,對“暢銷作家”這頂桂冠反而迴避。他們有道理,因為大文學家的作品,最初大抵不暢銷,古今中外如是。
曹雪芹是誰給他酒肉就為誰寫,《紅樓夢》是依靠手抄流傳下來的。就某些著名的文學作品的初版印數而言,風靡至今的《愛麗斯漫遊記》,只印了四十八冊;被尊為法國散文典範的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憶》,印了一千二百冊;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是一千冊,該書出版引起社會軒然大波,在它的影響下,托爾斯泰寫了《安娜·卡列尼娜》,易卜生寫了《玩偶之家》;《印第安納》使喬治桑一夜成名,只印了七百冊;現在還不斷重版,不斷搬上銀幕的《巴黎聖母院》,是一千一百冊;巴爾扎克的《幽谷百合》一千二百冊,《朱安黨人》三百冊;司湯達的《紅與黑》七百五十冊;拉博爾的《柱廊》一百冊,他是當時的著名作家,在《新法蘭西評論》撰寫專欄,與瓦菜里一起編文學雜誌《交流》;梁宗岱的法譯《陶潛詩選》印了二百七十冊;紀德的《地糧》二百一十五冊;博爾赫斯第一部著作《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狂熱》印了三百冊;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百二十五冊。
盧梭的《社會契約》引起法國大革命,影響了法國人以至全人類的思想,以當時印刷業的不發達,印數肯定極少,但不影響其思想的廣泛傳播。都說眼下文學書籍出版不容易,其實過去也大抵如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由於出版條件沒有與出版商達成共識,初版自費印刷;雨果第一部文集《頌歌與詩》,自費印了五百冊,出版社沒有給他發出去,讓他全部搬回家,他就堆放在壁爐周圍。普魯斯特的《在少女們的身邊》,自費印了一千七百五十冊;藍波的《地獄一季》,到處籌款出版不遂,最後由他母親資助。但這些都是日後傳世的作品。文學盛世時期的作家比起當代作家,境遇好不了多少。被公認為20世紀法國文學泰斗的普魯斯特,當初出版商看到他的作品就皺眉頭,避之則吉。所以,書的價值又怎能以交易數字來衡量?如果有人問,文學何價?回答是,文學無價。
為《文匯讀書周報》和《作家》雜誌撰寫專欄的十多年以來,筆者跟蹤著文壇的林林總總,而文學危機的叫聲,就在耳邊不斷。你一腳深一腳淺走著,卻欲罷不能。你發現國內文壇對外邊某些文學現象了解不足,為兩種不同文化的差距,或者因為在特定時期的誤導,產生了誤解。你因著近水樓台的方便,了解得更多更全面,就有將較為準確的訊息傳遞迴去的迫切感,對所謂文學危機,感覺就遲鈍了。心想,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戰爭危機發生過多少回?還有道德危機。1950年代,法國高級時裝危機就嚷開了,到1970年至1977年問,叫聲尤烈。但時裝大師們像啥事也沒有發生,充耳不聞,只一心一意做他們的針線活,到現在,高級時裝依然大行其道。對所謂文學危機,最好也像啥事都沒有發生,做你喜歡做、應該做的事。
眼下世界正在經歷著一場大變革,因著科技的高速發展,一個從未經歷過的世紀說來就來了。單是你日常使用的電腦、電話、網路的日新月異,就讓你趕得上氣不接下氣。大量的訊息,大量的構想,大量的商品,大量的物質,見識的爆炸,一切知識都被無限制地推向前,你不知道哪裡才是不可知的邊界。不少過去的事物被翻倒,世界的進程加速了。然則,新鮮事物從來就不斷發生,且每時每刻都在變,但根植於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審美,一種物質以外的精神活動,從來就沒有被淹沒,被帶走。人必須通過文學來認識自己以及自己的世界;也認識別人以及別人的世界。文學是人的夢想和精神世界的反映,只要有人類,就有夢想。有夢想,就有審美,有文學。如果重複前人講過的故事在所難免,但高度的攀升是無止境的,表現的手法也可以乾變萬化;一張臉龐能有多大?但可以是西施,或鐘無鹽;是耶穌,或猶大。而生活和歷史皺褶中所隱藏的故事無窮無盡,人的深淺也難以測量。據說一生離不開海洋的美國作家梅爾維爾(Melville),有一回把聲波發向海底,以探測其深度,但沒有了回聲,看來某些地方是莫測其深的。人心也一樣。人間既有天堂,也有地獄,作家就有話可說了。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無論繪畫、雕塑、音樂或電影,都不可能像文學那樣,將喜怒哀樂,將人的精神、思想和價值觀闡釋得如此透徹。
不過,文學也像人,需要不時閉目養神。19世紀的法國文壇星光燦爛,如今是相對沉寂了些。某一時期的文學現象也大抵如是。如果老瞪著一雙眼,很快會發現,世界沒有太多好東西看。筆者好歹繞著書架走了一圈,也繞自己走了一圈,推動心頭馬達的那團火也旺盛過,需要閉目養神一下了,就有《與書偕隱》的意思。拿一本自己喜歡的書,躲到一角地方,不為別人,只為自己消閒受用。如果寫作是欲望,閱讀則是樂趣。而敝帚自珍,以前寫下的文字必須集起來。雖說已經結集過幾種小冊子,但拉拉扯扯,還有一兩種要拼湊起來。想起蒙田將自己的《試筆》稱為“滷肉片”,藍波把自己的詩比作“洗碗水”,你能夠將自己的成品比作什麼?且不管它。在這裡只感謝仁發先生在百忙中撥冗為我聯絡出版社,也慶幸自己煮下的“夾生飯”有了著落。
這本小冊子大抵都是些卷帙訊息,新書,舊書,古典,現代,形形色色的作家,都放作一處。那個海明威,你不必驚詫於他給自己的那一槍了,他的孫女遞給我們一把鑰匙,原來三生石上自有因由;利特爾一個漂亮的滾翻,就穿越了猶太人被屠殺的禁區,給我們描繪了一個人類社會鬥獸場的故事,成就了21世紀的一部大書;傳說福樓拜有個兒子,但福樓拜不讓他姓福樓拜,卻使他以另一種方式誕生,成了莫泊桑;特洛伊再不是瞎子荷馬胡扯出來的故事,已經具有充分的實物證據,證明這是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費加羅報》的專欄作家揚·穆瓦認為,生活的美,是女性向我們展示的,大抵是歌德的“永恆的女性引導我們上升”。但事實上,像引導但丁暢遊上界天堂那類貝亞特麗彩,其本身的歷程,總是既華彩又沉重,像全球偶像瑪莉蓮·夢露。藍波說“生活在別處”,只有別處才有他的生活,所以,他逃離故國,有多遠走多遠,最後在亞丁港和阿拉爾生活。須知那邊的氣溫終年在三十攝氏度到四十五攝氏度之間,生活條件落後,風俗野蠻,男士外出都必須帶上刀槍,但他在那裡度過了最後十一個年頭;當年喬治桑和蕭邦跑到海外去藏愛,還有比這更風流、更浪漫的故事嗎?然則,當你跟蹤過他們的腳印,才知道他們的實際經歷跟你的想像差了一大截。還有中國作家巴金、孔羅蓀、吳祖光等在開放初期訪問法國,是1970年代末與80年代初的事了,現在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已經作古,在法國的短期活動亦已成為歷史。你姑且在這裡複述一下。
二○一二年四月
每年書展的交易數字龐大,說明書的健康狀況尚可,但文學作品就不可同日而語,它對書商的成交數字不再起大作用。出版社要賺錢,就指望非文學作品,賺了錢,才回過頭去出幾本名家著作,作為招牌貨,算是一種交代。在銀角子的大前提下,商業價值的標準代替了文學價值的標準。文學雜誌銷量不走俏,品種越來越少,報紙上的文學版被縮小或砍掉,出版商遇上文學書稿,先皺眉頭。
另一方面,我們這個時代人人皆可成為作家,法國就有超過一百四十萬人已經寫了一部手稿。在被調查的人當中,有32%已經寫成或者想寫一本書,也就是說,法國有三分之一人想成為作家。然則,芸芸眾多的作家當中,有多少人能夠成得了一個小氣候的?總是狹隘的個人意識多於普遍意識。以三分之一時間來照鏡,三分之一看肚臍,三分之一來回味。總是讓我來談談我,讓大家來談談我,我只對我感興趣。評論一個作家的角度,從韻事,尤其風流韻事出發的多,從作品出發的少。過去作家是多題材創作,天上地下,人神野獸,道德罪罰,精神肉體,現在的寫作題材總帶有目的性,著重銷路,不惜討好。獲得一定成就的當代作家,著眼的題材跟過去也不一樣,在法國,大抵致力於精神分析,或開拓某一世俗專題,如紀德的精神探索,薩特的存在主義,西蒙·德·波伏瓦對女權的呼籲。
文學所面臨的局面,是內容與手法都不再引起讀者共鳴?是讀者對社會新聞,對“八卦”現象更感興趣?或者,是迅速發展的科技和資訊社會,要求更多的是智力、推理、知識,而非文學?事實上,學校寧可急於教會學生使用電腦,而不急於教他們怎樣欣賞普魯斯特,你能夠說學校盲目或差錯?新科學,新技術,人文科學,的確將文學擠到牆角去了。作家為尋求出路,只好逆流而上,學會給文學拌上醬料。於是偵探、科幻、言情、心理分析、世俗專題、揭自己內幕或別人內幕的作品越來越多。離奇怪誕的非正統文學作品,紛紛登上書店的書架。暢銷書,往往就藏在這些書籍當中。
早在1947年,穆尼耶(E.Moullier)已宣告文學的輝煌時代的過去,文學經歷了它的燦爛時期後,不再給人帶來新火花:“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絢麗奪目,盛極一時的文學時代……這個煙花回落到自己身上。”
不管從事文學,或醉心文學的人如何不甘心,文學的大時代,大作家的時代也許已結束,一如偉人時代的結束。我們不需要喧天嘩地的偉人,只要好人,要與民眾共呼吸的正直人。“聖人恆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就是說,國君沒有自己的喜惡,以百姓的喜惡為自己的喜惡;大作家一時沒有也罷,可以要些好作家,要說真話,具深度,有責任心的作家。文學是證明人的存在的方法,它以愛,以恨,以喜,以怒,以幽默來闡釋人生。文學可以道出人的生存困境,但不可能改變世界,唯其不可能,還要不斷地道出,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它的立足點。都說實用書籍有市場;有關文化現象的,如繪畫、雕塑、電影等也有一定讀者,但這類作品,如果使用的語言不足以表達其概念或觀念,不一定是一本成功的書。要觸動人的感覺、直覺和審美,文學語言是唯一的手段。它從細節深入事物的內部,以捕得正著的字眼,把敘述者的意願、動機和感受傳遞給讀者。尤其,如果沒有文學的陶冶,又怎能指望有審美的判斷和鑑賞能力?
文學的狀態不好,但文學的明天還在唱。一種藝術永遠不會安樂死。不管非文學書籍氣勢如何迫人,一本好書會按照它本身的價值,最後回到它應有的位置上。實用書自有它的實用處;暢銷書只標誌某一時期讀者的情緒,不一定代表本身有什麼價值。而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就像人擁有生命,會在大浪淘沙中存活下去,人物會家喻戶曉,名氣比真人更大。這就是為什麼真正的文學家,寧可保衛文學的純度,對“暢銷作家”這頂桂冠反而迴避。他們有道理,因為大文學家的作品,最初大抵不暢銷,古今中外如是。
曹雪芹是誰給他酒肉就為誰寫,《紅樓夢》是依靠手抄流傳下來的。就某些著名的文學作品的初版印數而言,風靡至今的《愛麗斯漫遊記》,只印了四十八冊;被尊為法國散文典範的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憶》,印了一千二百冊;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是一千冊,該書出版引起社會軒然大波,在它的影響下,托爾斯泰寫了《安娜·卡列尼娜》,易卜生寫了《玩偶之家》;《印第安納》使喬治桑一夜成名,只印了七百冊;現在還不斷重版,不斷搬上銀幕的《巴黎聖母院》,是一千一百冊;巴爾扎克的《幽谷百合》一千二百冊,《朱安黨人》三百冊;司湯達的《紅與黑》七百五十冊;拉博爾的《柱廊》一百冊,他是當時的著名作家,在《新法蘭西評論》撰寫專欄,與瓦菜里一起編文學雜誌《交流》;梁宗岱的法譯《陶潛詩選》印了二百七十冊;紀德的《地糧》二百一十五冊;博爾赫斯第一部著作《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狂熱》印了三百冊;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百二十五冊。
盧梭的《社會契約》引起法國大革命,影響了法國人以至全人類的思想,以當時印刷業的不發達,印數肯定極少,但不影響其思想的廣泛傳播。都說眼下文學書籍出版不容易,其實過去也大抵如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由於出版條件沒有與出版商達成共識,初版自費印刷;雨果第一部文集《頌歌與詩》,自費印了五百冊,出版社沒有給他發出去,讓他全部搬回家,他就堆放在壁爐周圍。普魯斯特的《在少女們的身邊》,自費印了一千七百五十冊;藍波的《地獄一季》,到處籌款出版不遂,最後由他母親資助。但這些都是日後傳世的作品。文學盛世時期的作家比起當代作家,境遇好不了多少。被公認為20世紀法國文學泰斗的普魯斯特,當初出版商看到他的作品就皺眉頭,避之則吉。所以,書的價值又怎能以交易數字來衡量?如果有人問,文學何價?回答是,文學無價。
為《文匯讀書周報》和《作家》雜誌撰寫專欄的十多年以來,筆者跟蹤著文壇的林林總總,而文學危機的叫聲,就在耳邊不斷。你一腳深一腳淺走著,卻欲罷不能。你發現國內文壇對外邊某些文學現象了解不足,為兩種不同文化的差距,或者因為在特定時期的誤導,產生了誤解。你因著近水樓台的方便,了解得更多更全面,就有將較為準確的訊息傳遞迴去的迫切感,對所謂文學危機,感覺就遲鈍了。心想,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戰爭危機發生過多少回?還有道德危機。1950年代,法國高級時裝危機就嚷開了,到1970年至1977年問,叫聲尤烈。但時裝大師們像啥事也沒有發生,充耳不聞,只一心一意做他們的針線活,到現在,高級時裝依然大行其道。對所謂文學危機,最好也像啥事都沒有發生,做你喜歡做、應該做的事。
眼下世界正在經歷著一場大變革,因著科技的高速發展,一個從未經歷過的世紀說來就來了。單是你日常使用的電腦、電話、網路的日新月異,就讓你趕得上氣不接下氣。大量的訊息,大量的構想,大量的商品,大量的物質,見識的爆炸,一切知識都被無限制地推向前,你不知道哪裡才是不可知的邊界。不少過去的事物被翻倒,世界的進程加速了。然則,新鮮事物從來就不斷發生,且每時每刻都在變,但根植於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審美,一種物質以外的精神活動,從來就沒有被淹沒,被帶走。人必須通過文學來認識自己以及自己的世界;也認識別人以及別人的世界。文學是人的夢想和精神世界的反映,只要有人類,就有夢想。有夢想,就有審美,有文學。如果重複前人講過的故事在所難免,但高度的攀升是無止境的,表現的手法也可以乾變萬化;一張臉龐能有多大?但可以是西施,或鐘無鹽;是耶穌,或猶大。而生活和歷史皺褶中所隱藏的故事無窮無盡,人的深淺也難以測量。據說一生離不開海洋的美國作家梅爾維爾(Melville),有一回把聲波發向海底,以探測其深度,但沒有了回聲,看來某些地方是莫測其深的。人心也一樣。人間既有天堂,也有地獄,作家就有話可說了。任何一種藝術形式,無論繪畫、雕塑、音樂或電影,都不可能像文學那樣,將喜怒哀樂,將人的精神、思想和價值觀闡釋得如此透徹。
不過,文學也像人,需要不時閉目養神。19世紀的法國文壇星光燦爛,如今是相對沉寂了些。某一時期的文學現象也大抵如是。如果老瞪著一雙眼,很快會發現,世界沒有太多好東西看。筆者好歹繞著書架走了一圈,也繞自己走了一圈,推動心頭馬達的那團火也旺盛過,需要閉目養神一下了,就有《與書偕隱》的意思。拿一本自己喜歡的書,躲到一角地方,不為別人,只為自己消閒受用。如果寫作是欲望,閱讀則是樂趣。而敝帚自珍,以前寫下的文字必須集起來。雖說已經結集過幾種小冊子,但拉拉扯扯,還有一兩種要拼湊起來。想起蒙田將自己的《試筆》稱為“滷肉片”,藍波把自己的詩比作“洗碗水”,你能夠將自己的成品比作什麼?且不管它。在這裡只感謝仁發先生在百忙中撥冗為我聯絡出版社,也慶幸自己煮下的“夾生飯”有了著落。
這本小冊子大抵都是些卷帙訊息,新書,舊書,古典,現代,形形色色的作家,都放作一處。那個海明威,你不必驚詫於他給自己的那一槍了,他的孫女遞給我們一把鑰匙,原來三生石上自有因由;利特爾一個漂亮的滾翻,就穿越了猶太人被屠殺的禁區,給我們描繪了一個人類社會鬥獸場的故事,成就了21世紀的一部大書;傳說福樓拜有個兒子,但福樓拜不讓他姓福樓拜,卻使他以另一種方式誕生,成了莫泊桑;特洛伊再不是瞎子荷馬胡扯出來的故事,已經具有充分的實物證據,證明這是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費加羅報》的專欄作家揚·穆瓦認為,生活的美,是女性向我們展示的,大抵是歌德的“永恆的女性引導我們上升”。但事實上,像引導但丁暢遊上界天堂那類貝亞特麗彩,其本身的歷程,總是既華彩又沉重,像全球偶像瑪莉蓮·夢露。藍波說“生活在別處”,只有別處才有他的生活,所以,他逃離故國,有多遠走多遠,最後在亞丁港和阿拉爾生活。須知那邊的氣溫終年在三十攝氏度到四十五攝氏度之間,生活條件落後,風俗野蠻,男士外出都必須帶上刀槍,但他在那裡度過了最後十一個年頭;當年喬治桑和蕭邦跑到海外去藏愛,還有比這更風流、更浪漫的故事嗎?然則,當你跟蹤過他們的腳印,才知道他們的實際經歷跟你的想像差了一大截。還有中國作家巴金、孔羅蓀、吳祖光等在開放初期訪問法國,是1970年代末與80年代初的事了,現在他們當中絕大部分人已經作古,在法國的短期活動亦已成為歷史。你姑且在這裡複述一下。
二○一二年四月
名人推薦
一切偉大的詩都是直接訴諸我們的整體,靈與肉,心靈與官能的。它不獨使我們感到美感的悅樂,並且要指引我們去參悟宇宙和人生的奧義。而所謂參悟,又不獨間接解釋給我們的理智而已,並且要直接訴諸我們的感覺和想像,使我們全人格都受它感化與陶熔。譬如食果,我們只感到甘芳與鮮美,但同時也得到了營養與滋補。
——梁宗岱
——梁宗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