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信的歷史背景
背景
1848年德國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背叛而失敗了。
革命者們在思考和總結革命經驗和教訓,聯繫到發生在16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運動,它是多次歐洲革命的起點。拉薩爾創作《濟金根》也是借古諷今,因為政治自由和國家統一,是那場革命沒有完成的目標,300年之後德國人民仍然在為這個目標奮鬥。50年代後期,又出現了新的革命形式,即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運動的發展,要求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有兩條道路,拉薩爾倒向資產階級自由派一邊,他的作品表現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學藝術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在批評中表述了關於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歷史悲劇、現實主義和批評標準的文藝學、美學觀點。
拉薩爾生平
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國早期工人運動活動家,機會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全德工人聯合會創始人,主席。
1825年4月11日生於布雷斯勞(現弗羅茨瓦夫),1864年8月31日卒於瑞士日內瓦。在柏林大學攻讀哲學、語言和歷史。1848年歐洲革命期間,參加杜塞道夫民主派的革命活動,並與K.馬克思、F.恩格斯結識。1859年出版的歷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反對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統一德國,反映了唯心主義的歷史觀。革命失敗後,他繼續從事律師工作,完成了為哈茨費爾特伯爵夫人辦理離婚案的工作,伸張了正義,獲取了良好的名聲。當沉寂了一個時期的國際工人運動在六十代年初開始復甦的時候,拉薩爾積極參加了德國工人運動,於1862年和1863年先後發表了《工人綱領》、《公開答覆》等小冊子。1863年5月擔任了當時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國工人組織――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主席。而此時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遠離德國的英國,主要從事理論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拉薩爾在德國工人中的名聲和影響,自然要超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當時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人物。
同馬克思相比,這個小七歲的理論家和革命家,有著嚴重的不足和弱點。馬克思從一開始,對拉薩爾的活動就持有批評態度。後因向馬克思向拉薩爾“借債” 等種種原因,馬克思認為拉薩爾已“無可救藥”,以致斷絕了來往。
馬克思致斐迪南·拉薩爾
全文
親愛的拉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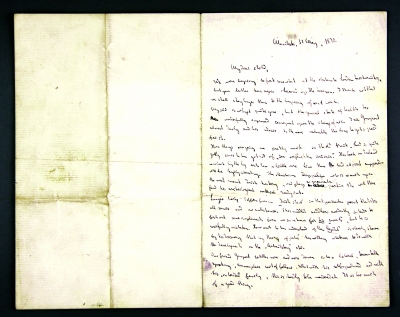 馬克思手稿
馬克思手稿至今沒有接到敦克爾先生收到的收件回執,我還不能肯定,手稿(此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手稿)是否已經脫離當局之手。你從信中附去的收據可以看出,它是由倫敦寄出的。
關於戰爭的問題:這裡一致認為,戰爭在義大利是不可避免的[320]。毫無疑問:艾曼努爾先生(維克多-艾曼努爾二世)真心想打,而波拿巴先生也曾真心想打。決定後者行動的是:
(1)害怕義大利的匕首。自從奧爾西尼死後,他就不斷暗地裡對燒炭黨人進行欺詐,“克洛蒂爾達”的丈夫普隆-普隆則充當中間人。[470]
(2)極端嚴重的財政困難;在“和平時期”再繼續供養法國軍隊,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倫巴第是塊肥肉。此外,戰爭一爆發,也就又有可能發行“戰時公債”了。其他任何公債都是“不可能”發行的。
(3)波拿巴在法國各政黨中已日益失去威信,他的外交活動也同樣是一連串的失敗。因此,必須做點什麼事來挽回他的聲望。甚至在農村里,也由於糧價慘跌而怨聲載道,波拿巴先生企圖通過他的關於糧食庫存的法令來人為地提高小麥價格,但是徒勞無功。[471]
(4)俄國推動了土伊勒里宮的暴發戶。藉助于波希米亞[註:捷克。——編者注]、莫拉維亞、加里西亞以及匈牙利南部、北部、東部和伊利里亞等地的泛斯拉夫主義運動,藉助於在義大利的一次戰爭,俄國就幾乎肯定能摧毀奧地利還在不斷地對它進行的反抗。(俄國驚恐地面臨著一次國內土地革命,而對外戰爭,單就轉移視線這一點來說,也許就會受到政府的歡迎,更不用說一切外交目的了。)
(5)前威斯特伐里亞國王[註:日羅姆·波拿巴。——編者注]的兒子普隆-普隆先生及其黨羽(以日拉丹為首的一幫匈牙利、波蘭、義大利的形形色色的冒牌革命家)盡一切努力來使事情有個結局。
(6)在義大利進行的對奧戰爭,是不能直接出面擁護教皇等人和反對所謂自由的英國將在其中保持中立的唯一的戰爭,至少在最初是這樣。假如普魯士在戰鬥開始的時候就想進行干預的話(但是我相信不會這樣),它會受到俄國的威脅。
另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先生對真正的嚴重的戰爭毫無疑問地是害怕得要命的。(1)這個人總是疑慮重重,並且象所有的賭徒一樣,不可能果斷。他經常爬到盧比康河邊,然而總是必須靠站在他背後的人把他推下去。在布倫附近、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在1851年12月,每次他都是最後被迫認真地執行了他的計畫。[41](2)在法國,人們對他的計畫採取極端冷淡的態度,這當然不是使他感到鼓舞的事情。民眾表示無所謂。但是大金融資本家、工業家、商人、僧侶的黨派,以及高級將領(例如佩利西埃和康羅貝爾)都直接而嚴肅地提出反對。事實上,軍事方面的前景並不是光明的。即使把《立憲主義者報》上的吹牛當做實話看待,情況也還是如此。[306]如果法國總共能湊足七十萬人,那末其中適合服兵役的最多不過五十八萬人。這些人當中還要減去駐阿爾及利亞的五萬人,憲兵等等四萬九千人,防守法國的城市(巴黎等地)和要塞的十萬人(最低限度),駐紮在靠近瑞士、德國、比利時的邊界上的監視軍至少十八萬一千人。剩下的只有二十萬人,即使把皮蒙特的那一點點軍隊加進去,對於在明喬河和阿迪傑河設有堅固陣地的奧地利人來說,這也決不能算是優勢力量。
無論如何,如果波拿巴先生退卻,那他就會在法國士兵民眾當中徹底垮台;這可能就是使他終於向前挺進的原因。
你似乎認為匈牙利會在這樣一種戰爭中起義。我對這一點非常懷疑。奧地利當然會派遣一支監視軍到加里西亞—匈牙利邊界上去對付俄國,而這同時也會使匈牙利受到威脅。匈牙利的團隊(只要它們不象在大多數情況下那樣,分散在它們的敵人,如捷克人、塞爾維亞人、斯洛維尼亞人等等當中),將會被派往德意志人居住的省份去。
戰爭自然會引起嚴重的後果,而且最後肯定會引起革命的後果。但是,在最初,它將在法國保持波拿巴主義,在英國和俄國削弱國內的運動,在德國重新喚起極端狹隘的民族熱情,等等,因此,據我看來,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將起反革命的作用。
不管怎樣,我對這裡的流亡者不抱任何希望。除了至少是個狂信者的馬志尼之外,他們全都是十足的冒險家,他們的全部野心就是騙取英國人的錢。科蘇特先生完全墮落了,變成了一個巡迴講演者,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各地區散布同一套謬論,把它奉獻給一批一批的新聽眾。
這些狗已經成為十足的保守派,實際上應當得到赦免。例如,哥特弗利德·金克爾先生在這裡出版名叫《海爾曼》的周報,就連《科倫日報》同它相比,都算得上是勇敢機智的報紙。(據說,這位可愛的善於做戲的牧師由於向富於美感的猶太女人獻殷勤使他妻子跳樓喪命。在悲痛萬狀的表演的感動下,弗萊里格拉特出於慈悲心腸竟然寫了一首悼念死去的約翰娜·莫克爾的詩[註:斐·弗萊里格拉特《約翰娜·金克爾安葬之後》(見本卷第359—360頁)。——編者注],但是過了幾天,他確信,悲痛是假的,哥特弗利德先生從來沒有感到象他妻子死後這樣“輕鬆和自由”。)這個傢伙鼓吹催眠的、獻媚的和軟綿綿的“樂觀主義”。這家報紙應當叫《哥特弗利德》。至於我,我寧願在“曼托伊費爾”[註:文字遊戲:哥特弗利德(《Gottfried》)是金克爾的名字(《Gott——“上帝”,《Friede》——“和平”),曼托伊費爾(《Manteufel》)是反動大臣的姓(《Mann》——“人”,《Teufel》——“鬼”)——編者注]的束縛下寫東西,也不願意在倫敦西蒂區的德國庸人的束縛下寫東西。而對金克爾來說,這種束縛倒更覺輕鬆和愜意,因為從性格和觀點來說,他同這些庸人毫無區別。“列伐爾特”(又叫“施塔爾”)關於已故的莫克爾夫人的廢話使後者在這裡更加名聲掃地。[472]
祝好。
你的 卡·馬
如果你能在布勒斯勞(弗羅茨拉夫)打聽到一個叫馮·保拉-克雷歇爾的女人的底細並儘快地告訴我就好了,這對我非常重要。
注釋
[41]政治流放犯人塔西利埃在法國民主派報紙《人》上發表的信,是馬克思寫《小波拿巴法國》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5—671頁)的材料來源。馬克思在這篇文章里揭露了法國政治犯在流放地凱恩(在南美法屬蓋亞那)的生活條件。這個流放地,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熱帶氣候造成大量死亡,被稱為“不流血的斷頭台”。
這封信的譯文由馬克思寄給憲章派機關報《人民報》,於1856年4月12日在該報發表。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綽號,由布倫、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個城市名稱的第一個音節組成;這個綽號暗指他曾經企圖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布倫(1840年8月6日)舉行波拿巴主義的暴亂,也指1851年12月2日的巴黎政變,這次政變在法國確立了波拿巴的專政。——第37、557頁。
[306]指1859年1月30日《立憲主義者報》上發表的、由法國記者路·博尼法斯署名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一旦發生戰爭,法國可以向國外派出五十萬軍隊。1月31日恩格斯寫了《法國軍隊》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00—206頁),作出自己的估計並指出,法國在戰時派到義大利與奧地利作戰的軍隊將只有二十萬人。恩格斯在文章中援引了巴黎的訊息,指出,《立憲主義者報》上的材料和它所依據的數字都來自路易-拿破崙。因此,馬克思於2月1日把恩格斯的文章寄給《紐約每日論壇報》以後,認為有必要把2月2日《泰晤士報》上的材料告訴恩格斯:《立憲主義者報》上發表的上述文章的作者就是路易-拿破崙本人。——第374、558頁。
[320]指法國和撒丁王國(皮蒙特)為一方與奧地利為另一方之間在這個時期已經迫近的戰爭。這次戰爭(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是拿破崙第三發動的,他力圖在“解放”義大利的幌子下掠奪土地並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戰爭在法國鞏固波拿巴政體。義大利大資產階級和自由貴族則指望依靠戰爭使義大利在沒有人民民眾參加的情況下統一於統治皮蒙特的薩瓦王朝的政權之下。然而拿破崙第三懾於廣泛開展起來的反對義大利壓迫者——奧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運動,力圖保持義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擔心戰爭繼續打下去會招致軍事上的困難,所以在法國—皮蒙特軍隊獲得幾次勝利後,於7月11日背著撒丁單獨和奧地利締結了維拉弗蘭卡和約。戰爭的結果是,法國得到了薩瓦和尼斯,倫巴第歸併於撒丁,威尼斯地區仍歸奧地利人管轄。——第391、556、565、591頁。
[470]謀刺路易-拿破崙的奧爾西尼被處死後,路易-拿破崙對發誓要殺死他的義大利燒炭黨人的報復提心弔膽,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歐洲的金融恐慌》一文談到了這一點。這篇文章以及卡·馬克思的文章《路易-拿破崙的處境》和弗·恩格斯的文章《法國軍隊》闡述了這封信所涉及的許多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9—194、195—199、200—206頁)。並見注305。——第556頁。
[471]路易-拿破崙規定調整糧食價格和為此目的建立公共倉庫保管糧食的法令,見馬克思的文章《法國調整糧食價格的方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85—689頁)。——第557頁。
[472]從馬克思1860年3月3日給拉薩爾的信中可以看出,馬克思這裡指的是倫敦報紙《每日電訊》上發表的一篇關於哥特弗利德·金克爾的妻子約翰娜·莫克爾去世的通訊。這篇通訊出自德國女作家芬尼·列伐爾特(按夫姓是施塔爾)的手筆。——第559頁。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
全文
親愛的拉薩爾:
我這樣久沒有寫信給您,特別是我還沒有把我對您的《濟金根》[註:斐·拉薩爾《弗蘭茨·馮·濟金根》。——編者注]的評價告訴您,您一定覺得有些奇怪吧。但是這正是我延遲了這樣久才寫信的原因。由於缺乏美的文學,我難得讀到這類的作品,而且我幾年來都沒有這樣讀這類作品:在讀了之後提出詳細的評價、明確的意見。沒有價值的東西是不值得這樣費力的。甚至我間或還讀一讀的幾本比較好的英國小說,例如薩克雷的小說,儘管有其不可辯駁的文學和文化歷史的意義,也從來沒有能夠引起我的這樣的興趣。但是我的判斷能力,由於這樣久沒有運用,已經變得很遲鈍了,所以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我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和那些東西相比,您的《濟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對它不吝惜時間。第一二次讀您這部從題材上看,從處理上看都是德國民族的戲劇,使我在情緒上這樣地激動,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擱一些時候,特別是因為在這個貧乏的時期里,我的鑑賞力遲鈍到了這樣的地步(雖然慚愧,我還是不得不說):有時甚至很少有價值的東西,在我第一次讀時也不會不給我留下一些印象。為了有一個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態度,所以我把《濟金根》往後放了一放,就是說,把它借給了幾個相識的人(這裡還有幾個多少有些文學修養的德國人)。但是,“書有自己的命運”[註:忒倫底烏斯·摩爾《論賀雷西的用詞、音節和韻律》。——編者注]——如果把它們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們,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濟金根》奪了回來。我可以告訴您,在讀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時候,印象仍舊是一樣的,並且深知您的《濟金根》經得住批評,所以我就把我的意見告訴您。
當我說任何一個現代的德國官方詩人都遠遠不能寫出這樣一個劇本時,我知道我對您並沒有作過分的恭維。同時,這正好是事實,而且是我們文學中非常突出的,因而不能不談論的一個事實。如果首先談形式的話,那末,情節的巧妙的安排和劇本的從頭到尾的戲劇性使我驚嘆不已。在韻律方面您確實給了自己一些自由,這給讀時帶來的麻煩比給上演時帶來的麻煩還要大。我很想讀一讀舞台腳本;就眼前的這個劇本看來,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這裡來了一個德國青年詩人(卡爾·濟貝耳),他是我的同鄉和遠親,在戲劇方面做過相當多的工作;他作為普魯士近衛軍的後備兵也許要到柏林去,那時我也許冒昧叫他帶給您幾行字。他對您的劇本評價很高,但是認為,由於道白很長,根本不能上演,在做這些長道白時,只有一個演員做戲,其餘的人為了不致作為不講話的配角盡站在那裡,只好三番兩次地儘量做各種表情。最後兩幕充分證明,您能夠輕易地把對話寫得生動活潑,我覺得,除了幾場以外(這是每個劇本都有的情況),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懷疑,您在為這個劇本上演加工的時候會考慮到這一點。當然,思想內容必然因此受損失,但是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無根據地認為德國戲劇具有的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486]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將來才能達到,而且也許根本不是由德國人來達到的。無論如何,我認為這種融合正是戲劇的未來。您的《濟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慾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但是還應該改進的就是要更多地通過劇情本身的進程使這些動機生動地、積極地、也就是說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論證性的辯論(不過,我很高興在這些辯論中又看到了您曾經在陪審法庭和民眾大會上表現出來的老練的雄辯才能[487])逐漸成為不必要的東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認這個標準是區分舞台劇和文學劇的界限;我相信,在這個意義上《濟金根》是能夠變成一個舞台劇的,即使確實有困難(因為達到完美的確絕不是簡單的事)。與此相關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繪。您完全正確地反對了現在流行的惡劣的個性化,這種個性化總而言之是一種純粹低賤的自作聰明,並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學的一個本質的標記。此外,我覺得一個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麼,而且表現在他怎樣做;從這方面看來,我相信,如果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劇本的思想內容是不會受到損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在今天是不再夠用了,而在這裡,我認為您原可以毫無害處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意義。然而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們僅僅是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劇本的形式方面也用過一些心思而已。
至於談到歷史內容,那末您以鮮明的筆調和對以後的發展的正確提示描述了您最關心的當時的運動的兩個方面:濟金根所代表的貴族的國民運動和人道主義理論運動及其在神學和教會領域中的進一步發展,即宗教改革。在這裡我最喜歡濟金根和皇帝之間,教皇使節和特利爾大主教之間的幾場戲(在這裡,您把世俗的受過美學和古典文學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論上有遠見的使節同目光短淺的德國僧侶諸侯加以對比,從而成功地直接根據這兩個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了卓越的個性刻畫);在濟金根和查理的那場戲中對性格的描繪也是很動人的。您對胡登的自傳(您公正地承認它的內容是本質的東西)的確採取了一種令人失望的做法,您把這種內容放到劇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爾塔扎爾和弗蘭茨的對話也非常重要,在這段對話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說明他應當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這裡,真正悲劇的因素出現了;而且正是由於這種意義,我認為在第三幕里應當對這方面更強調一些,在那裡是有很多機會這樣做的。但是,我又回到次要問題上來了。——那個時期的城市和諸侯的態度在許多場合都是描寫得非常清楚的,因此那時的運動中的所謂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寫得淋漓盡致了。但是,我認為對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農民分子,以及他們的隨之而來的理論上的代表人物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農民運動象貴族運動一樣,也是一種國民運動,也是反對諸侯的運動,遭到了失敗的農民運動的那種鬥爭的巨大規模,與拋棄了濟金根的貴族甘心扮演宮廷侍臣的歷史角色的那種輕率舉動,正是一個鮮明的對照。因此,在我看來,即使就您對戲劇的觀點(您大概已經知道,您的觀點在我看來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夠現實的)而言,農民運動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那個有約斯·弗里茨出現的農民場面的確有它的獨到之處,而且這個“蠱惑者”的個性也描繪得很正確,只是同貴族運動比起來,它卻沒有充分表現出農民運動在當時已經達到的高潮。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根據我對戲劇的這種看法,介紹那時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會,會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劇本生動起來,會給在前台表演的貴族的國民運動提供一幅十分寶貴的背景,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使這個運動本身顯出本來的面目。在這個封建關係解體的時期,我們從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國王、無衣無食的僱傭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險家身上,什麼驚人的獨特的形象不能發現呢!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這種類型的歷史劇中必然會比在莎士比亞那裡有更大的效果。此外,我覺得,由於您把農民運動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個方面對貴族的國民運動作了不正確的描寫,同時也就忽視了在濟金根命運中的真正悲劇的因素。據我看來,當時廣大的皇室貴族並沒有想到要同農民結成聯盟;他們必須壓榨農民才能獲得收入這樣一種情況,不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同城市結成聯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這種聯盟並沒有出現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現了。而貴族的國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農民結成聯盟,特別是同後者結成聯盟才能實現;據我看來,悲劇的因素正是在於:同農民結成聯盟這個基本條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貴族的政策必然是無足輕重的;當貴族想取得國民運動的領導權的時候,國民大眾即農民,就起來反對他們的領導,於是他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濟金根和農民確實有某種聯繫,這究竟有多少歷史根據,我無法判斷,而這個問題也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此外,就我的記憶所及,在向農民呼籲的檔案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觸及這個和貴族有關的麻煩問題,而且企圖把農民的憤怒都特別集中到僧侶身上去。但是我絲毫不想否認您有權把濟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農民的。但這樣一來馬上就產生了這樣一個悲劇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堅決反對過解放農民的貴族,另一方面是農民,而這兩個人卻被置於這兩方面之間。在我看來,這就構成了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衝突。您忽略了這一因素,而把這個悲劇性的衝突縮小到極其有限的範圍之內:使濟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國宣戰,而只向一個諸侯宣戰(這裡雖然您也非常恰當地把農民引進來),並且使他僅僅由於貴族的冷漠和膽怯就遭到了滅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比較有力地強調了氣勢兇猛的農民運動以及由於先前的“鞋會”和“窮康拉德”[488]而必然變得更加保守的貴族的心情,那末這一點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論證。然而這一切都不過是可以把農民運動和平民運動寫入戲劇的一種方法而已;此外至少還有十種同樣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的方法。
您看,我是從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來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對意見,這對您來說正是我推崇這篇作品的最好證明。是的,幾年來,在我們中間,為了黨本身的利益,批評必然是最坦率的;此外,每出現一個新的例證,證明我們的黨不論在什麼領域中出現,它總是顯出自己的優越性時,這始終使我和我們大家感到高興。而您這次也提供了這個例證。
此外,世界局勢似乎要向一個十分令人喜悅的方向發展。未必能夠構想,還有什麼比法俄同盟能為徹底的德國革命提供更好的基礎。我們德國人只有水淹到脖子時,才會全都發起條頓狂來;這一次淹死的危險似乎十分逼近了。這倒更好些。在這樣一個危機中,一切現存的勢力都必然要滅亡,一切政黨都必然要一個跟一個地復滅,從《十字報》到哥特弗利德·金克爾,從萊希堡伯爵到“黑克爾、司徒盧威、布倫克爾、齊茨和勃魯姆”[489]。在這樣一個鬥爭中,必然出現一個時刻,那時只有最不顧一切的、最堅決的黨才能拯救民族,同時必然會出現一些條件,只是在那些條件下,才有可能徹底清除一切舊的垃圾,即內部的分裂以及波蘭和義大利附屬於奧地利的情況。我們不能放棄普魯士波蘭的一寸土地,而且……(後面現已遺失)
注釋
[486]在這裡和以後恩格斯談到舞台劇本和文學劇本之間的區別和其他藝術創作問題的地方,實際上都是針對拉薩爾在《弗蘭茨·馮·濟金根》劇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論點同拉薩爾進行論戰。——第583頁。
[487]恩格斯指1849年5月3—4日對拉薩爾的審判。當時他被控的罪名是1848年11月22日在諾伊斯(杜塞道夫附近)舉行的民眾大會上的演說中號召武裝起來反對國家政權。拉薩爾發表演說後當天被捕並被審前羈押。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標題《拉薩爾》在《新萊茵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當局和監獄當局對拉薩爾的暴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16—321、531—533、543—548、553—558頁)。恩格斯也可能指1848年9月18日拉薩爾在沃林根(科倫附近)民眾大會上的講話。恩格斯親自參加了這次民眾大會並當選為大會書記(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95—596頁)。——第583頁。
[488]“鞋會”和“窮康拉德”都是農民秘密團體,它們的活動為德國1525年農民戰爭作了準備。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這一著作(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23—435頁)中闡述了這兩個團體的活動。——第586頁。
[489]指德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848—1849年革命時期在南德意志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中提到他們的首領。這首歌曲的副歌是:
“黑克爾、司徒盧威、布倫克爾、勃魯姆和齊茨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殺死!”
恩格斯的著作《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就是以這首歌曲的副歌開始的。這部著作批評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時期的行動(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9頁)。——第587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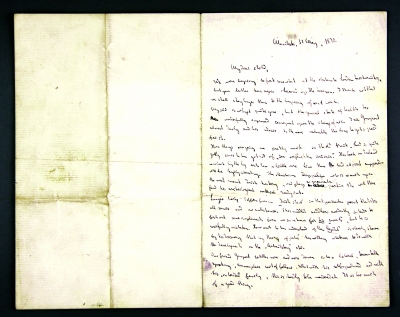 馬克思手稿
馬克思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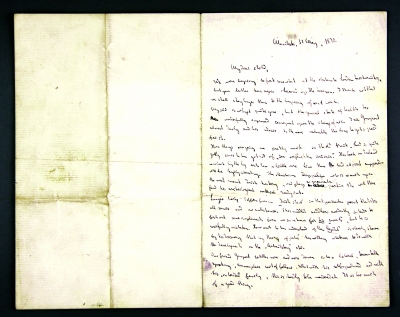 馬克思手稿
馬克思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