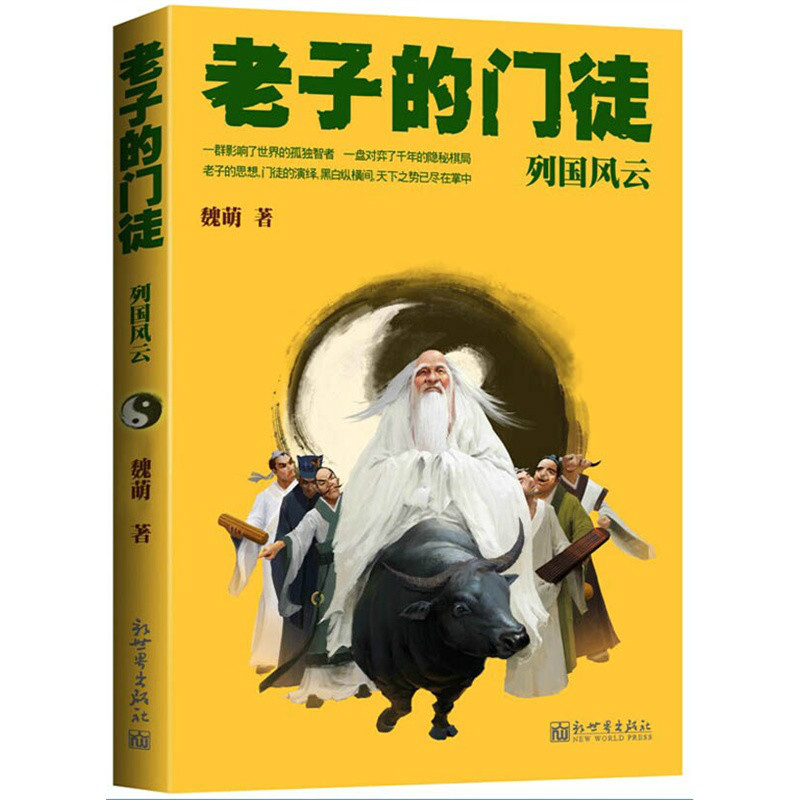基本介紹
- 書名:《老子的門徒:列國風雲》
- 又名:《老子的門徒》
- 作者:魏萌
- ISBN:9787510449499
- 類別:歷史普及讀物,中國古代史
- 頁數:223
- 定價:29.8
-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6-1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編輯推薦,作品目錄,線上試讀,
編輯推薦
老子的一生虛無縹緲,宛若游龍,歷史上關於他的傳說數不勝數,可是直到今天,人們甚至還在為究竟有無此人而爭論不休。他和他的五千言《道德經》一樣,留給後人解不盡的謎題。老子的門徒遍布天下,但除了“玄門十子”確有記載之外,其餘眾人皆因仰慕其學識、思想、人格、品行而自投門下,古往今來,絡繹不絕。老子和他的門徒,在兩千多年前便布下了一盤棋局。黑白縱橫間,天下之勢已盡在掌中……
作品目錄
第一章 撲朔迷離的身世
第二章 齊國局中局
第三章 內亂殺出來的千里良緣
第四章 王城腳下的人禍天災
第五章 任人擺布的天下共主
第六章 棋枰之上初露鋒芒
第七章 從藏書吏到柱下史
第八章 大國弭兵小國變法
第九章 霸權之花的凋零
第十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第十一章 變法還是鬥法
第十二章 成也公卿敗也公卿
第十三章 一場曠日持久的內訌
第十四章 塵埃落定出函谷
線上試讀
第一章 撲朔迷離的身世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遭遇犬戎之亂,西周滅亡。在諸侯的拱衛下,原太子宜臼即位周王,史稱周平王。平王為躲避戎兵的鋒芒,將都城從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西北)遷往雒邑。自此,王室衰,春秋始,其結果就是諸侯做大,周室日萎,大國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要挾天子,小國則在大國實力的此起彼伏間搖擺不定。
宋國是黃河下游的一個二流國家,四面皆為平原,易攻難守,東南地區還有蠻夷之患。和它的鄰居衛國一樣,不論是哪個諸侯國想要借刀殺人或炫耀武力,都會首先拿它們開刀。
當年,晉文公重耳流亡在外的時候,宋國的國君曾有恩於他。宋國正是憑藉與晉國的這點恩情,為自己找到了一個自認為堅不可摧的靠山。然而宋國的統治者們始終沒有明白這樣一個道理:亂世之中,自勝者強。
死死依附晉國,並沒能給宋國帶來安寧太平的日子,就在晉楚爭霸的短短几十年間,發生在宋國境內的大小戰役就有近百次之多。長期的戰亂與上國的盤剝,使宋國的大地上滿目瘡痍,許多原本富庶肥沃的土地都因為民生的凋敝而變成了貧瘠的荒地。百姓們敢怒不敢言,始終於一片水深火熱之中任人宰割,任人拋棄……
周靈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五月,在宋國大夫向戌的努力撮合下,晉、楚、齊、魯、宋、衛、鄭、許、陳、蔡、曹、宋等十三個諸侯國決定在宋國的國都商丘再次舉行“弭兵大會”,以消弭綿延不絕的戰火,還百姓以休養生息的機會。這個訊息很快傳遍了中原大地,聞之者無不歡欣鼓舞,尤其是那些飽受戰亂之苦的宋國百姓。
有關“弭兵大會”的訊息同樣也在第一時間傳到了宋國的相邑(今安徽渦陽)。
這一天日光和煦,幾個赤腳的孩子在村口的一棵銀杏樹下奔跑嬉戲。已成合抱之勢的銀杏樹旁是一進樸素得有些簡陋的院落。很多年前,一位精通殷商古禮的老先生遊學至此,住進了這進院子。
老先生一身仙風道骨,超然物外,與世無爭,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來歷,只是都尊稱他為商先生。商先生博古通今,知書達理,清心寡欲,平易近人,方圓數百里內的年輕人紛紛慕名而來,投於其門下。
“先生,先生!出大事了!”一個目光炯炯,身材魁梧的少年從門外跌跌撞撞地闖將進來,臉上油光膩膩,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文甦,如此大驚小怪,所為何事?”說話之人正是商容商先生,被稱作文甦的少年是他的學生秦佚。
“喜訊,喜訊呀!您大概還不知道吧?兩個月後,中原的十三個諸侯國將會在我們宋地召開弭兵大會。戰火一熄,還愁過不上好日子嗎?宋侯總算是聰明了一回。”秦佚神采奕奕地將剛剛得到的訊息悉數道來。
商先生輕拂長髯,望著身旁正襟危坐的一位年輕人微笑不語。此時此刻,屋外又傳來了孩童們嬉笑的聲音。五月的南風兀自灌入,堂前頓時花香盈室……
“佚天生愚鈍,不知先生為何發笑?”秦佚被商先生的笑而不答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伯陽,你最了解為師的心意,你來說給文甦一聞,如何?”
“弟子豈敢在先生面前造次。”被喚作伯陽的年輕人謙虛道。
“你我之間亦師亦友,何須拘於世俗之禮,但說無妨。”
伯陽不便推脫,於是起身執禮道:“我聽聞有道之君,從不依靠武力霸凌於天下。這是因為武力只會激起人們的怨恨,戰端一起便如離弦之箭,一發不可收拾。人心若被欲望所遮蔽,就會不擇手段地與人爭,與人搶。然而物壯則老,盛極必衰,逞一時之勇得來的勝利怎么會長久呢?個人如此,天下之勢也是如此。人與人相爭,國與國相侵,霸主的寶座頻頻易主,戰爭也因此總是周而復始。軍隊所到之處,流血漂櫓,白骨遍野,且大戰之後,必遇荒年,最終還是苦了百姓。”
“那么通過會盟的方式將戰火消弭於無形,不正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嗎?”秦佚反問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伯陽的話顯然只說了一半,“穿衣不是為了穿衣而穿,而是為了取暖,為了遮羞,戰爭同樣不是為戰而戰,不過是一種表象罷了,所以消弭戰火絕沒有你想像的那么簡單。《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你難道忘記了嗎?三十多年前,晉楚兩國的大夫就曾在宋都西門外的高台上會盟弭兵,他們信誓旦旦地說再不以兵戎相見,然而不到兩年時間,兩國便鏖戰於鄢陵。”
秦佚眉頭緊蹙,沉默不語,因為伯陽所說的都是事實。
“連年征戰,縱是萬乘大國也吃不消呀。齊桓勢衰之後,晉楚兩國為了爭奪中原霸權,幾十年里大小百戰,如今早已是人困馬乏,民怨沸騰,這就是輕言戰事的報應。如今楚國受困於晉人一手扶植的吳越諸國,而晉國內部士族大夫鼎立而起,內亂堪憂。一南一北兩個大國皆為守勢,它們需要以消弭戰禍為幌子,以便集中力量解決內部問題。這弭兵大會名為弭兵,實為緩兵。風雨欲來,必先寧靜,更加劇烈的戰禍恐怕離我們不遠了。”說罷,伯陽重新跪坐於案幾之前,並為商先生沏了一杯清茶。
“伯陽大哥的話,真是令我茅塞頓開啊。”秦佚所說的確是心裡話,他這一生中最佩服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德高望重的商先生,一個就是他的這位伯陽大哥。
秦佚是個孤兒,從記事起便一直跟隨在商先生左右,先生教他讀書識字,並將畢生所學悉數傳授。在伯陽前來拜師之前,秦佚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商先生最得意的門生。
伯陽前來拜師的時候也就二十歲上下的樣子,恰逢先生在為營造學館的事情積極奔走,兩人相談甚歡,一見如故。秦佚一度覺得先生因為伯陽的到來而冷落了自己,他與先生情同父子,所以在心底對伯陽產生了些許的隔閡。
秦佚負責先生的日常起居,一日,先生留伯陽於家中吃飯。秦佚在給伯陽盛取肉羹的時候,故意將湯水灑在了伯陽的新衣之上。伯陽對此不以為意,還主動幫秦佚舀取飯食。商先生明察秋毫,卻沒有責怪秦佚的無禮,而是在事後為他講述了一個故事。
“文甦,你來。”待伯陽離去以後,商先生將秦佚喚到了自己的近旁,“我知道,你對為師偏愛伯陽心有不滿。可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秦佚心頭一緊,原來自己的那點小心思早已被先生所洞穿,他慚愧不已,面頰滾燙無比。
“我問你,你是哪裡人?緣何在此?”
商先生這不是明知故問嗎,可秦佚還是畢恭畢敬地答道:“弟子乃秦國鹹陽人,母親難產而亡,父親從軍後便沒了訊息。幸而先生遊學到秦地,收留了弟子,否則弟子恐怕早已為虎狼食肉寢皮了。”
“那你可知伯陽的來歷?”
“弟子只知他姓李名耳,字伯陽,喔,對了,與他一同來的鄉友好像都管他叫老聃。”
“就只有這些嗎?”
“他平日沉默寡言,和我們這些師兄、師弟交往不多。”
“既然如此,就讓為師給你講一個故事吧。”商先生嘆了一口氣,他的面容忽然變得異常凝重,仿佛一下子衰老了許多,這讓秦佚感到十分詫異。
“在靈王即位為周王的那一年,為師在陳國的苦縣附近遇到了一位經年未見的老朋友,老友相見自然要小敘一番,於是便在那裡盤桓了數日。就是在那個時候,苦縣厲鄉的曲仁里出了一件怪事。為師的那位老友是本地人,平素最愛網羅散逸民間的各種奇談怪聞,他告訴為師,曲仁里的鄉村之中住著一位遭人拋棄的老婦人,她原本是宋國貴族,但不知何故流落民間,成了一位默默無聞的農婦。”
商先生略微停頓了一下,似乎在考慮如何繼續:“這位農婦本已是八十一歲的高齡,但她竟然還懷有身孕,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後來,又有人告訴為師,她在自己剛剛出生的時候便已經身懷六甲,如此說來,那腹中之子也應是八十一歲的高齡了。”
秦佚驚訝地睜大了眼睛:“這怎么可能?後來呢?”
“為師向來不信鬼神怪事,於是便親自去拜訪了那位農婦。”
“先生,您真的見到她了?”
“你猜得沒錯。”商先生話鋒一轉,“不過,她並沒有傳說中那么蒼老。”
“弟子有些糊塗了。”
“你不要著急,容為師慢慢道來。這位婦人乃理氏之女,顓頊帝高陽氏的後裔。她並不是什麼耄耋老婦,看上去正值桃李年華。”
“這么說,她出生時便懷有身孕的傳聞也是以訛傳訛的吧?”
“不錯。雖然她的確懷有身孕,卻並非像人們所謠傳的那樣。她告訴為師,在去年七月里的一天早晨,她正在河邊清洗衣物,上游竟莫名其妙地漂來許多黃燦燦的李子,起初她並沒在意,可後來終於還是禁不住好奇,沿著河流一路向上。只是,她沒有找到李子的來源,卻在河邊遇到了一位‘故人’。”
“喔?是什麼樣的故人?”
“一個身披鎧甲,渾身血污的男人。那人筋疲力盡地倒於河邊,臉上那道深可見骨的傷疤還在向外淌著膿血。可即便如此,理氏還是一眼認出,這就是自己失散多日的丈夫。”
“什麼?丈夫?理氏的丈夫是位軍士?”
“不錯,而且還是一位地位很高的‘軍士’。”
“弟子明白了,這一定又是一個始亂終棄的故事。”
“不錯,不過事情可沒有你想的那么簡單。”
“先生,這亂世之中,禮崩樂壞,人心難測,所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原來也不過是鏡花水月,空如一夢!為了不負他人,亦不教他人負我,看來弟子將來還是孑然一身的好。”
“莫說蠢話!兒女情長,在所難免。只是莫要輕言許諾,一切順其自然就好。人生天地之間,但凡有所希冀,必會有所失望,若問如何不失望,唯有不去希冀。”
“弟子謹記先生教誨。那後來呢?”
“‘軍士’甦醒後就悄悄地離開了。”
“哼!這樣的男人隨他去吧,只是要苦了那可憐的理氏。”
“為師初至苦地的時候,她已經有二十三個月的身孕了,村裡的風言風語俯拾即是,說她和男人野合,懷上了怪胎,結果把那個野男人也給嚇跑了。你看,人言可畏,更可恨啊!”商先生平生最恨流言蜚語和始亂終棄,所以在講到這一段時竟也不禁有些咬牙切齒。
“謠言固然可恨,但先生,懷胎二十三個月仍未生產,這,這恐怕確實不祥啊。”
“祥與不祥全在人心,為師看那理氏的眼神中分明已知天命。她行動不便,卻還要操持農活、家務,忍受他人的白眼。柔弱而被人欺凌,雖說是人生的不幸,但上天總是會眷顧弱者的。強弱之勢,只能定一時成敗,強非強,弱非弱,乾坤扭轉,以弱克強。成者常以弱為道,理氏雖弱,卻是生命之承載,這才是宇宙間最強大的力量啊!文甦,這些道理你慢慢就會明白了。”
“強非強……弱非弱……弟子愚鈍,還請先生明示。”
“自然有輪迴,人事有代謝。草木在生長的時候,柔軟而富有彈性,死去之後,才變得乾燥堅硬;人在活著的時候,身體柔韌,死去之後,才變得異常堅硬。這說明什麼呢?柔弱是生命的本質啊,而堅硬逞強乃死的象徵。女子柔弱卻往往長壽,男子剛強卻容易早夭,這就是關於生死的自然之道。”
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苦縣的上空突然出現了一團盤旋不去的紫氣,商先生自然也看到了,但在講給秦佚的那個故事裡卻對此隻字未提。村裡的老人家都說,紫氣沖天乃祥瑞之兆,理氏的這個孩子將來必定會有一番大作為。
楚人好鬼神,上至楚王,下至百姓,皆篤信神明。楚人生病之後,往往不像中原國家那般求醫問藥,而是先請大儺做法,憑藉神力驅除病魔。苦縣原是陳國的一個小縣,由於地鄰楚地,所以楚風頗盛。後來,楚國索性滅了陳國,將苦縣直接納入到自己的地界裡。
商先生不明就裡,他厭惡巫醫大儺,於是只為理氏請來了村上的穩婆。穩婆只看了一眼,便知大事不妙,立即表示自己對理氏的情況無能為力。她告訴商先生,這是難產的徵兆,弄不好會母子雙亡,況且懷胎過久乃是鬼怪作祟,唯一的辦法只有去請大儺來做一場法事,才有可能消災弭禍,保母子平安。
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商先生勉為其難地請穩婆出面去請大儺。
穩婆請來的這位大儺非常神秘,自從他定居苦縣之日起就沒有人見識過他的真實面容。於外人面前,他總是佩戴著一副古怪的面具,其家中的戶牖亦蒙以黑布,森森然有幾分鬼氣。
商先生與大儺打了一個照面,雖然看不清面具下的那張面孔,可心底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先生望著大儺踱門進屋的背影,想要說些什麼,卻欲言又止。
大儺來到理氏的床前,仔細察看了她的眼皮和瞳仁,然後從身後的褡褳里取出一柄象牙短劍。只見他劍尖輕輕一挑,手中的畫符與置於案上的香篆竟自行焚燒起來。畫符的黑煙與香篆的白煙裊娜纏繞,如兩條游龍般宛轉升騰,不一會就將整間屋子都籠罩在一種撲朔迷離的神秘氣氛里。
站在一旁的穩婆被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驚呆了,直到大儺請她借一步說話的時候,她才猛然間回過神來。大儺告訴她:“從方才的香篆上看,這位婦人腹中的孩子非同一般,只是其命雖清貴,但初生便逢劫難。此乃天意不可違,這母子二人我只能保一人性命無虞。”
這時,商先生恰好走進屋來,大儺的一番話在他的內心深處攪動起一波洶湧的暗潮,他感到一種難以抉擇的痛苦,雖然這個艱難的抉擇並不需要由他來做定奪。
言語之際,商先生無意間瞥了瞥大儺那雙文以彩繪的手掌。那是一雙厚重粗糙的大手,手背上青筋暴突,大大小小的傷疤猙獰可怖,給人一種孔武有力的感覺。
“大師不是本地人吧?”商先生很有禮貌地垂問道。
“喔?先生何以見得?”大儺愣了一下,停下了正要邁出的步子。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大師乃行伍出身,官銜卻是文官大夫。”
大儺顯然吃了一驚,他死死地盯著商先生的眼睛,似乎想從那瞳仁里看出些什麼端倪,然而那雙眼睛實在是太深邃了,深邃得讓他有些難以承受。大儺強作鎮定道:“先生誤會了,在下的確不是本地人,但卻不是什麼行伍、大夫之流,不過一介山野村夫罷了。”
商先生開懷大笑,並上前攤開大儺的雙手:“恕老夫無禮,掌中之繭如此厚重,手臂多有創痕,身形魁梧矯健而又不失清朗之氣,大師雖是習武之人,但又絕非莽夫,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你不是文官大夫便是公子貴胄。要知道,面具和彩繪可以遮蔽一個人的身形,可是卻掩飾不了他的談吐與氣度。”
“先生真乃高人也!”大儺對商先生的眼力深表佩服,“實不相瞞,在下確為行伍出身,為避禍亂,不得已而隱姓埋名,苟且於此。至於那些裝神弄鬼的伎倆,實在是讓先生見笑了。”
“無礙,無礙,亂世之中,自有全身之道,棄世隱去也不失為一種上策。只是你和老夫的一位朋友頗為相似……也許是老夫的錯覺吧,也讓你見笑了。”
“先生不妨說來聽聽,或許在下有所耳聞。”
“老夫的那位朋友不是別人,正是宋國的左司馬——老佐。”商先生意味深長地瞥了那面具一眼。
大儺又是一驚,他的周身微微顫抖,如牲牛般觳觫不止,而這一切自然都逃不過商先生的眼睛……
“這可如何是好,這可如何是好啊?先生你都聽到了吧,不行,俺得趕快告訴理氏妹子,讓她早作打算。”穩婆薄嘴唇,杏仁眼,一看就是個急性子。
商先生本欲阻攔,可穩婆的小碎步速率驚人,眨眼工夫已經躥到了理氏的身旁。大儺對此倒是不置可否,仿佛在他看來,生老病死都是過眼雲煙,冥冥之中已有定數。
穩婆心直口快,說著就抹起了眼淚。理氏顯得異常平靜,還反倒安慰起穩婆來:“媯嫂子,你不要為難,我已經想好了,孩子……孩子一定要保住。還有,孩子以後就隨我理氏吧……不,不,還是讓他姓李吧,對,就是李子的李。”理氏的眼神是那么的空靈而篤定,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她悄悄摸出藏於枕下的一把匕首,輕輕地劃破了自己的小腹。
“妹子,你這是,這是何苦哩……”穩婆接生無數,面對淋漓的鮮血連眼都沒眨過一下,可是這一次她卻不知如何是好,雙手顫抖著愣在那裡。
“媯……媯嫂子,你……孩子……就拜託你了……快……”望著理氏漸漸失去血色的臉頰,穩婆狠了狠心,顫顫巍巍地將理氏腹中的孩子取了出來……
“咦?這孩子的相貌好生奇怪。”穩婆拭淨孩子身上的血污,仔細地端詳了起來,只見初生的小傢伙生得耳長過腮,白髮虬髯,乍一看,竟宛如一位童顏老翁。穩婆用一條布單蓋住了理氏的身體——這位可憐的母親甚至沒有來得及看上孩子一眼,便永遠地睡去了。
“把孩子交給我吧。”商先生主動提出要收養這個孩子。站在他身後的大儺並沒有離去,而是目不轉睛地盯著穩婆懷裡的孩子,沉默不語。
“這,這事俺可做不了主,要不,要不俺去把比長(與鄰長相似,只不過比長設於國都地區,鄰長設於國都以外的地區。春秋戰國時,一里分五鄰,每鄰分為五家,每鄰都設有負責治安糾舉與收容安置之事的鄰長)請來,咱們聽聽他的意見咋樣?”穩婆見商先生沒有反對,便匆匆忙忙地請來了比長。
比長在了解了商先生的心意之後,不好意思地搓手道:“這位先生,你看,俺們都是鄉下人,這娃生得可憐,俺們作為鄉親父老的也不好將他託付給外人不是?況且將來葉落歸根,他總還是要回到這裡不是?外邊這兵荒馬亂的……”
“不!他本來就不屬於這裡,將來也不應回到這裡。”商先生面無表情,不怒自威。
“先生咋這么說呢?娃的親娘就是俺們村的,這娃咋就不屬於這裡咧?”比長似乎有些不高興。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孩子的母親也並非本地人士。”
比長心中暗驚,因為他很清楚,這理氏是被一夥楚軍逼得走投無路,投河自盡,結果大難不死,被村里人給救起來的。
“而且我還知道,她在這裡定居也不過就是兩年前的事情。”
“你究竟是什麼人?”比長那兩隻冒著精光的小眼睛警惕地盯著商先生,他擔心面前的這個老傢伙是來向理氏尋仇的仇家。
“這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孩子的父親是宋國人就可以了。現在,你還堅持說這孩子是本地人嗎?”
“啥?你說他爹是宋國人?你憑啥在這瞎咧咧?俺們四鄰五舍這么多口子都沒見過他爹,咋的,難不成你認識那個野漢子?”
“不錯。”
村民們大吃一驚,比長壓抑著心中的不快繼續問道:“那你倒是給俺說說,那野漢子究竟是誰?”
“不可說。老夫只能告訴你,這個孩子姓老。”
“放屁!娃他娘生前說了,娃姓李,李子的李,知道不?”
商先生微微一笑,並沒有因為比長的無禮而有所慍怒,他幽幽地說道:“老夫對這孩子的身世了如指掌,如有妄言願遭天譴。只不過老夫受人所託,要永遠保守這個秘密,所以只能向各位有所隱瞞了。”
比長暗想:“看來這老傢伙沒有騙人。”於是他又轉陰為晴,強堆起笑臉對商先生說道:“這位先生,你看,俺是個粗人,說話可能不太中聽,不過俺也是個講理的人。這樣吧,孩子呢還是由我們來撫養,您是讀書人,有文化,就給這孩子起個名字吧。”
“髭發皆白,耳長而墜……不如就叫他老聃如何?”
“好,好,老聃好。”
商先生似乎忽然想到了什麼,於是又繼續說道:“既然理氏執意要孩子姓李,那就兩姓並存,姓李名耳號老聃好了。”
“這個好,這個好,李耳,這個好,嘿嘿。”比長憨憨地笑了,比起那個拗口的“老聃”,他顯然更喜歡這個通俗易懂的“李耳”,至於號不號的那些文縐縐的東西他向來是漠不關心的。
比長將村里人召集起來,在他的主持下,孩子最終過繼給當地的一戶富農。商先生雖然有些不捨,但見苦縣清幽寧靜,民風淳樸,便尊重了當地百姓的意願。
“好吧,那就勞煩各位好生照顧這個孩子了,商某就此別過。”商先生起身告辭,最後又望了一眼襁褓中的嬰兒,“以後若是有什麼困難,可以隨時讓他來找我,在下宋人商容。”
正午的日光熾熱而刺眼,屋子裡卻伸手不見五指。一陣輕輕的嘆息打破了這令人窒息的死寂,黑暗中忽然亮起了一絲微弱的燭光,精緻的漆木案幾漸漸地變得清晰起來,案幾之上端放著一張詭異的面具,一個英俊而疲憊的身影投射在北面的牆壁上。
“老淵啊老淵,白日點燈,你意欲何為?”
“白即是黑,日即是夜,白日即為黑夜,我於黑夜點燈,有何不可?”
“老淵啊老淵,拋棄妻子,你該下地獄!”
“我已在地獄,何有再下之理?”
“老淵啊老淵,你是要苦了那孩子!”
“與其讓他跟著我東躲西藏,不如還他正常人的天地。”
……
這時,門敲得“咚咚”直響,蠟燭熄滅,一張藏於面具之後的臉龐出現在熱辣辣的驕陽之下。
“找我何事?”
“快點吧,村東理氏快要生了,可能是難產。”
面具心中一緊,卻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跟在穩婆那飛快的碎步之後。一路上,他的思緒飛轉,父親戰死的那一幕又一次出現在他的面前……
事情還要從五年前的夏天說起,那一年宋共公不幸離世,宋國大政旁落於右師華元的手中。共公健在的時候,以左師魚石為首的桓氏宗親便一直對宋國的國政大權虎視眈眈,如今共公離世,他們立刻變得蠢蠢欲動,預謀乘機奪權。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魚石僚屬的一名小妾偏偏和華元手下的一員將官有染,起事之前風聲便走漏了出去。華元怒不可遏,決定聯合整個戴氏宗族一舉將桓氏宗族這根肉中刺連根拔除。可魚石這個傢伙比狐狸還狡猾,他早就留有後手,宋都的守門官是他安插的親信。一看形勢不好,魚石便立刻率眾逃亡楚國。
由於自己的百密一疏,竟讓魚石這老小子從容地逃走了,華元氣得暴跳如雷,將守門將官一家老小悉數誅殺。新君宋平公初立之後,又命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百官封賞完畢,宋國的局面才暫時穩定下來。
俗語有云: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這話一點不假,魚石在楚國藏匿了三年,這三年里他上下打點,四處聯結,處心積慮,伺機報仇。公元前573年六月,在魚石的挑唆與煽動下,楚國興兵伐宋,一舉攻克宋國的彭城(今江蘇徐州)。楚軍得勝撤退後,留下三百乘兵車幫助魚石和魚府坐鎮戍守。
訊息傳到宋平王的耳朵里,身為一國之君的平王氣得臉都綠了:“這群該死的叛徒!寡人定要將他們食肉寢皮,挫骨揚灰!”
“請主君息怒,彭城乃我宋國要邑,如今淪於敵手,自然不可輕言放棄。但我軍新敗,士氣低迷,不宜馬上出兵啊。”華元對宋國形勢的急轉直下感到憂心忡忡,對當初放走魚石黨徒更是悔恨不已。
“寡人還就不信了,先君襄公不是就曾擊敗過強齊嗎?楚蠻欺人太甚,占我大邑,是可忍?孰不可忍!”
“主君莫忘泓水之辱!當年先君不聽公子目夷之策,結果一戰而使我宋軍精銳損失殆盡。泓水之畔,血流成河,哀聲遍野,想我全盛之時,尚不可與楚軍一爭高下,如今楚軍方退,我豈可再輕言挑釁?”
“怎么?相國這是以目夷自比,譏刺寡人無道嗎?”
“臣不敢,臣只是……”
“你不要再說了,寡人不想聽。想你也是隻身深入過楚營的人,當年的勇氣哪去了?寡人現在只想知道,你們誰能擊破楚軍,收復彭城,替寡人分憂?”
華元歷事昭公、文公、共公,如今又為平王右師,可謂“四朝元老”。飽經世事的他知道平王這是被憤怒沖昏了頭腦,當下也不好再說什麼。
“愚臣願為君上分憂!”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將眾人的耳膜都震得嗡嗡作響。只見此人目光炯炯,腮闊肩寬,眉宇之間自帶一分令人不寒而慄的肅殺之氣,他不是別人,正是剛剛走馬上任不久的左司馬——老佐。
“好!好!老將軍英勇善戰,定能得勝。寡人封你為上將軍,領兵兩萬,星夜出擊,務必要為寡人拿下彭城啊!”
“請君上放心,愚臣定不辱使命!”
……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遭遇犬戎之亂,西周滅亡。在諸侯的拱衛下,原太子宜臼即位周王,史稱周平王。平王為躲避戎兵的鋒芒,將都城從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西北)遷往雒邑。自此,王室衰,春秋始,其結果就是諸侯做大,周室日萎,大國打著尊王攘夷的口號要挾天子,小國則在大國實力的此起彼伏間搖擺不定。
宋國是黃河下游的一個二流國家,四面皆為平原,易攻難守,東南地區還有蠻夷之患。和它的鄰居衛國一樣,不論是哪個諸侯國想要借刀殺人或炫耀武力,都會首先拿它們開刀。
當年,晉文公重耳流亡在外的時候,宋國的國君曾有恩於他。宋國正是憑藉與晉國的這點恩情,為自己找到了一個自認為堅不可摧的靠山。然而宋國的統治者們始終沒有明白這樣一個道理:亂世之中,自勝者強。
死死依附晉國,並沒能給宋國帶來安寧太平的日子,就在晉楚爭霸的短短几十年間,發生在宋國境內的大小戰役就有近百次之多。長期的戰亂與上國的盤剝,使宋國的大地上滿目瘡痍,許多原本富庶肥沃的土地都因為民生的凋敝而變成了貧瘠的荒地。百姓們敢怒不敢言,始終於一片水深火熱之中任人宰割,任人拋棄……
周靈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年)五月,在宋國大夫向戌的努力撮合下,晉、楚、齊、魯、宋、衛、鄭、許、陳、蔡、曹、宋等十三個諸侯國決定在宋國的國都商丘再次舉行“弭兵大會”,以消弭綿延不絕的戰火,還百姓以休養生息的機會。這個訊息很快傳遍了中原大地,聞之者無不歡欣鼓舞,尤其是那些飽受戰亂之苦的宋國百姓。
有關“弭兵大會”的訊息同樣也在第一時間傳到了宋國的相邑(今安徽渦陽)。
這一天日光和煦,幾個赤腳的孩子在村口的一棵銀杏樹下奔跑嬉戲。已成合抱之勢的銀杏樹旁是一進樸素得有些簡陋的院落。很多年前,一位精通殷商古禮的老先生遊學至此,住進了這進院子。
老先生一身仙風道骨,超然物外,與世無爭,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來歷,只是都尊稱他為商先生。商先生博古通今,知書達理,清心寡欲,平易近人,方圓數百里內的年輕人紛紛慕名而來,投於其門下。
“先生,先生!出大事了!”一個目光炯炯,身材魁梧的少年從門外跌跌撞撞地闖將進來,臉上油光膩膩,激動之情溢於言表。
“文甦,如此大驚小怪,所為何事?”說話之人正是商容商先生,被稱作文甦的少年是他的學生秦佚。
“喜訊,喜訊呀!您大概還不知道吧?兩個月後,中原的十三個諸侯國將會在我們宋地召開弭兵大會。戰火一熄,還愁過不上好日子嗎?宋侯總算是聰明了一回。”秦佚神采奕奕地將剛剛得到的訊息悉數道來。
商先生輕拂長髯,望著身旁正襟危坐的一位年輕人微笑不語。此時此刻,屋外又傳來了孩童們嬉笑的聲音。五月的南風兀自灌入,堂前頓時花香盈室……
“佚天生愚鈍,不知先生為何發笑?”秦佚被商先生的笑而不答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伯陽,你最了解為師的心意,你來說給文甦一聞,如何?”
“弟子豈敢在先生面前造次。”被喚作伯陽的年輕人謙虛道。
“你我之間亦師亦友,何須拘於世俗之禮,但說無妨。”
伯陽不便推脫,於是起身執禮道:“我聽聞有道之君,從不依靠武力霸凌於天下。這是因為武力只會激起人們的怨恨,戰端一起便如離弦之箭,一發不可收拾。人心若被欲望所遮蔽,就會不擇手段地與人爭,與人搶。然而物壯則老,盛極必衰,逞一時之勇得來的勝利怎么會長久呢?個人如此,天下之勢也是如此。人與人相爭,國與國相侵,霸主的寶座頻頻易主,戰爭也因此總是周而復始。軍隊所到之處,流血漂櫓,白骨遍野,且大戰之後,必遇荒年,最終還是苦了百姓。”
“那么通過會盟的方式將戰火消弭於無形,不正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嗎?”秦佚反問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伯陽的話顯然只說了一半,“穿衣不是為了穿衣而穿,而是為了取暖,為了遮羞,戰爭同樣不是為戰而戰,不過是一種表象罷了,所以消弭戰火絕沒有你想像的那么簡單。《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你難道忘記了嗎?三十多年前,晉楚兩國的大夫就曾在宋都西門外的高台上會盟弭兵,他們信誓旦旦地說再不以兵戎相見,然而不到兩年時間,兩國便鏖戰於鄢陵。”
秦佚眉頭緊蹙,沉默不語,因為伯陽所說的都是事實。
“連年征戰,縱是萬乘大國也吃不消呀。齊桓勢衰之後,晉楚兩國為了爭奪中原霸權,幾十年里大小百戰,如今早已是人困馬乏,民怨沸騰,這就是輕言戰事的報應。如今楚國受困於晉人一手扶植的吳越諸國,而晉國內部士族大夫鼎立而起,內亂堪憂。一南一北兩個大國皆為守勢,它們需要以消弭戰禍為幌子,以便集中力量解決內部問題。這弭兵大會名為弭兵,實為緩兵。風雨欲來,必先寧靜,更加劇烈的戰禍恐怕離我們不遠了。”說罷,伯陽重新跪坐於案幾之前,並為商先生沏了一杯清茶。
“伯陽大哥的話,真是令我茅塞頓開啊。”秦佚所說的確是心裡話,他這一生中最佩服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德高望重的商先生,一個就是他的這位伯陽大哥。
秦佚是個孤兒,從記事起便一直跟隨在商先生左右,先生教他讀書識字,並將畢生所學悉數傳授。在伯陽前來拜師之前,秦佚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商先生最得意的門生。
伯陽前來拜師的時候也就二十歲上下的樣子,恰逢先生在為營造學館的事情積極奔走,兩人相談甚歡,一見如故。秦佚一度覺得先生因為伯陽的到來而冷落了自己,他與先生情同父子,所以在心底對伯陽產生了些許的隔閡。
秦佚負責先生的日常起居,一日,先生留伯陽於家中吃飯。秦佚在給伯陽盛取肉羹的時候,故意將湯水灑在了伯陽的新衣之上。伯陽對此不以為意,還主動幫秦佚舀取飯食。商先生明察秋毫,卻沒有責怪秦佚的無禮,而是在事後為他講述了一個故事。
“文甦,你來。”待伯陽離去以後,商先生將秦佚喚到了自己的近旁,“我知道,你對為師偏愛伯陽心有不滿。可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秦佚心頭一緊,原來自己的那點小心思早已被先生所洞穿,他慚愧不已,面頰滾燙無比。
“我問你,你是哪裡人?緣何在此?”
商先生這不是明知故問嗎,可秦佚還是畢恭畢敬地答道:“弟子乃秦國鹹陽人,母親難產而亡,父親從軍後便沒了訊息。幸而先生遊學到秦地,收留了弟子,否則弟子恐怕早已為虎狼食肉寢皮了。”
“那你可知伯陽的來歷?”
“弟子只知他姓李名耳,字伯陽,喔,對了,與他一同來的鄉友好像都管他叫老聃。”
“就只有這些嗎?”
“他平日沉默寡言,和我們這些師兄、師弟交往不多。”
“既然如此,就讓為師給你講一個故事吧。”商先生嘆了一口氣,他的面容忽然變得異常凝重,仿佛一下子衰老了許多,這讓秦佚感到十分詫異。
“在靈王即位為周王的那一年,為師在陳國的苦縣附近遇到了一位經年未見的老朋友,老友相見自然要小敘一番,於是便在那裡盤桓了數日。就是在那個時候,苦縣厲鄉的曲仁里出了一件怪事。為師的那位老友是本地人,平素最愛網羅散逸民間的各種奇談怪聞,他告訴為師,曲仁里的鄉村之中住著一位遭人拋棄的老婦人,她原本是宋國貴族,但不知何故流落民間,成了一位默默無聞的農婦。”
商先生略微停頓了一下,似乎在考慮如何繼續:“這位農婦本已是八十一歲的高齡,但她竟然還懷有身孕,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後來,又有人告訴為師,她在自己剛剛出生的時候便已經身懷六甲,如此說來,那腹中之子也應是八十一歲的高齡了。”
秦佚驚訝地睜大了眼睛:“這怎么可能?後來呢?”
“為師向來不信鬼神怪事,於是便親自去拜訪了那位農婦。”
“先生,您真的見到她了?”
“你猜得沒錯。”商先生話鋒一轉,“不過,她並沒有傳說中那么蒼老。”
“弟子有些糊塗了。”
“你不要著急,容為師慢慢道來。這位婦人乃理氏之女,顓頊帝高陽氏的後裔。她並不是什麼耄耋老婦,看上去正值桃李年華。”
“這么說,她出生時便懷有身孕的傳聞也是以訛傳訛的吧?”
“不錯。雖然她的確懷有身孕,卻並非像人們所謠傳的那樣。她告訴為師,在去年七月里的一天早晨,她正在河邊清洗衣物,上游竟莫名其妙地漂來許多黃燦燦的李子,起初她並沒在意,可後來終於還是禁不住好奇,沿著河流一路向上。只是,她沒有找到李子的來源,卻在河邊遇到了一位‘故人’。”
“喔?是什麼樣的故人?”
“一個身披鎧甲,渾身血污的男人。那人筋疲力盡地倒於河邊,臉上那道深可見骨的傷疤還在向外淌著膿血。可即便如此,理氏還是一眼認出,這就是自己失散多日的丈夫。”
“什麼?丈夫?理氏的丈夫是位軍士?”
“不錯,而且還是一位地位很高的‘軍士’。”
“弟子明白了,這一定又是一個始亂終棄的故事。”
“不錯,不過事情可沒有你想的那么簡單。”
“先生,這亂世之中,禮崩樂壞,人心難測,所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原來也不過是鏡花水月,空如一夢!為了不負他人,亦不教他人負我,看來弟子將來還是孑然一身的好。”
“莫說蠢話!兒女情長,在所難免。只是莫要輕言許諾,一切順其自然就好。人生天地之間,但凡有所希冀,必會有所失望,若問如何不失望,唯有不去希冀。”
“弟子謹記先生教誨。那後來呢?”
“‘軍士’甦醒後就悄悄地離開了。”
“哼!這樣的男人隨他去吧,只是要苦了那可憐的理氏。”
“為師初至苦地的時候,她已經有二十三個月的身孕了,村裡的風言風語俯拾即是,說她和男人野合,懷上了怪胎,結果把那個野男人也給嚇跑了。你看,人言可畏,更可恨啊!”商先生平生最恨流言蜚語和始亂終棄,所以在講到這一段時竟也不禁有些咬牙切齒。
“謠言固然可恨,但先生,懷胎二十三個月仍未生產,這,這恐怕確實不祥啊。”
“祥與不祥全在人心,為師看那理氏的眼神中分明已知天命。她行動不便,卻還要操持農活、家務,忍受他人的白眼。柔弱而被人欺凌,雖說是人生的不幸,但上天總是會眷顧弱者的。強弱之勢,只能定一時成敗,強非強,弱非弱,乾坤扭轉,以弱克強。成者常以弱為道,理氏雖弱,卻是生命之承載,這才是宇宙間最強大的力量啊!文甦,這些道理你慢慢就會明白了。”
“強非強……弱非弱……弟子愚鈍,還請先生明示。”
“自然有輪迴,人事有代謝。草木在生長的時候,柔軟而富有彈性,死去之後,才變得乾燥堅硬;人在活著的時候,身體柔韌,死去之後,才變得異常堅硬。這說明什麼呢?柔弱是生命的本質啊,而堅硬逞強乃死的象徵。女子柔弱卻往往長壽,男子剛強卻容易早夭,這就是關於生死的自然之道。”
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苦縣的上空突然出現了一團盤旋不去的紫氣,商先生自然也看到了,但在講給秦佚的那個故事裡卻對此隻字未提。村裡的老人家都說,紫氣沖天乃祥瑞之兆,理氏的這個孩子將來必定會有一番大作為。
楚人好鬼神,上至楚王,下至百姓,皆篤信神明。楚人生病之後,往往不像中原國家那般求醫問藥,而是先請大儺做法,憑藉神力驅除病魔。苦縣原是陳國的一個小縣,由於地鄰楚地,所以楚風頗盛。後來,楚國索性滅了陳國,將苦縣直接納入到自己的地界裡。
商先生不明就裡,他厭惡巫醫大儺,於是只為理氏請來了村上的穩婆。穩婆只看了一眼,便知大事不妙,立即表示自己對理氏的情況無能為力。她告訴商先生,這是難產的徵兆,弄不好會母子雙亡,況且懷胎過久乃是鬼怪作祟,唯一的辦法只有去請大儺來做一場法事,才有可能消災弭禍,保母子平安。
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商先生勉為其難地請穩婆出面去請大儺。
穩婆請來的這位大儺非常神秘,自從他定居苦縣之日起就沒有人見識過他的真實面容。於外人面前,他總是佩戴著一副古怪的面具,其家中的戶牖亦蒙以黑布,森森然有幾分鬼氣。
商先生與大儺打了一個照面,雖然看不清面具下的那張面孔,可心底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先生望著大儺踱門進屋的背影,想要說些什麼,卻欲言又止。
大儺來到理氏的床前,仔細察看了她的眼皮和瞳仁,然後從身後的褡褳里取出一柄象牙短劍。只見他劍尖輕輕一挑,手中的畫符與置於案上的香篆竟自行焚燒起來。畫符的黑煙與香篆的白煙裊娜纏繞,如兩條游龍般宛轉升騰,不一會就將整間屋子都籠罩在一種撲朔迷離的神秘氣氛里。
站在一旁的穩婆被眼前所發生的一切驚呆了,直到大儺請她借一步說話的時候,她才猛然間回過神來。大儺告訴她:“從方才的香篆上看,這位婦人腹中的孩子非同一般,只是其命雖清貴,但初生便逢劫難。此乃天意不可違,這母子二人我只能保一人性命無虞。”
這時,商先生恰好走進屋來,大儺的一番話在他的內心深處攪動起一波洶湧的暗潮,他感到一種難以抉擇的痛苦,雖然這個艱難的抉擇並不需要由他來做定奪。
言語之際,商先生無意間瞥了瞥大儺那雙文以彩繪的手掌。那是一雙厚重粗糙的大手,手背上青筋暴突,大大小小的傷疤猙獰可怖,給人一種孔武有力的感覺。
“大師不是本地人吧?”商先生很有禮貌地垂問道。
“喔?先生何以見得?”大儺愣了一下,停下了正要邁出的步子。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大師乃行伍出身,官銜卻是文官大夫。”
大儺顯然吃了一驚,他死死地盯著商先生的眼睛,似乎想從那瞳仁里看出些什麼端倪,然而那雙眼睛實在是太深邃了,深邃得讓他有些難以承受。大儺強作鎮定道:“先生誤會了,在下的確不是本地人,但卻不是什麼行伍、大夫之流,不過一介山野村夫罷了。”
商先生開懷大笑,並上前攤開大儺的雙手:“恕老夫無禮,掌中之繭如此厚重,手臂多有創痕,身形魁梧矯健而又不失清朗之氣,大師雖是習武之人,但又絕非莽夫,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你不是文官大夫便是公子貴胄。要知道,面具和彩繪可以遮蔽一個人的身形,可是卻掩飾不了他的談吐與氣度。”
“先生真乃高人也!”大儺對商先生的眼力深表佩服,“實不相瞞,在下確為行伍出身,為避禍亂,不得已而隱姓埋名,苟且於此。至於那些裝神弄鬼的伎倆,實在是讓先生見笑了。”
“無礙,無礙,亂世之中,自有全身之道,棄世隱去也不失為一種上策。只是你和老夫的一位朋友頗為相似……也許是老夫的錯覺吧,也讓你見笑了。”
“先生不妨說來聽聽,或許在下有所耳聞。”
“老夫的那位朋友不是別人,正是宋國的左司馬——老佐。”商先生意味深長地瞥了那面具一眼。
大儺又是一驚,他的周身微微顫抖,如牲牛般觳觫不止,而這一切自然都逃不過商先生的眼睛……
“這可如何是好,這可如何是好啊?先生你都聽到了吧,不行,俺得趕快告訴理氏妹子,讓她早作打算。”穩婆薄嘴唇,杏仁眼,一看就是個急性子。
商先生本欲阻攔,可穩婆的小碎步速率驚人,眨眼工夫已經躥到了理氏的身旁。大儺對此倒是不置可否,仿佛在他看來,生老病死都是過眼雲煙,冥冥之中已有定數。
穩婆心直口快,說著就抹起了眼淚。理氏顯得異常平靜,還反倒安慰起穩婆來:“媯嫂子,你不要為難,我已經想好了,孩子……孩子一定要保住。還有,孩子以後就隨我理氏吧……不,不,還是讓他姓李吧,對,就是李子的李。”理氏的眼神是那么的空靈而篤定,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她悄悄摸出藏於枕下的一把匕首,輕輕地劃破了自己的小腹。
“妹子,你這是,這是何苦哩……”穩婆接生無數,面對淋漓的鮮血連眼都沒眨過一下,可是這一次她卻不知如何是好,雙手顫抖著愣在那裡。
“媯……媯嫂子,你……孩子……就拜託你了……快……”望著理氏漸漸失去血色的臉頰,穩婆狠了狠心,顫顫巍巍地將理氏腹中的孩子取了出來……
“咦?這孩子的相貌好生奇怪。”穩婆拭淨孩子身上的血污,仔細地端詳了起來,只見初生的小傢伙生得耳長過腮,白髮虬髯,乍一看,竟宛如一位童顏老翁。穩婆用一條布單蓋住了理氏的身體——這位可憐的母親甚至沒有來得及看上孩子一眼,便永遠地睡去了。
“把孩子交給我吧。”商先生主動提出要收養這個孩子。站在他身後的大儺並沒有離去,而是目不轉睛地盯著穩婆懷裡的孩子,沉默不語。
“這,這事俺可做不了主,要不,要不俺去把比長(與鄰長相似,只不過比長設於國都地區,鄰長設於國都以外的地區。春秋戰國時,一里分五鄰,每鄰分為五家,每鄰都設有負責治安糾舉與收容安置之事的鄰長)請來,咱們聽聽他的意見咋樣?”穩婆見商先生沒有反對,便匆匆忙忙地請來了比長。
比長在了解了商先生的心意之後,不好意思地搓手道:“這位先生,你看,俺們都是鄉下人,這娃生得可憐,俺們作為鄉親父老的也不好將他託付給外人不是?況且將來葉落歸根,他總還是要回到這裡不是?外邊這兵荒馬亂的……”
“不!他本來就不屬於這裡,將來也不應回到這裡。”商先生面無表情,不怒自威。
“先生咋這么說呢?娃的親娘就是俺們村的,這娃咋就不屬於這裡咧?”比長似乎有些不高興。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孩子的母親也並非本地人士。”
比長心中暗驚,因為他很清楚,這理氏是被一夥楚軍逼得走投無路,投河自盡,結果大難不死,被村里人給救起來的。
“而且我還知道,她在這裡定居也不過就是兩年前的事情。”
“你究竟是什麼人?”比長那兩隻冒著精光的小眼睛警惕地盯著商先生,他擔心面前的這個老傢伙是來向理氏尋仇的仇家。
“這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孩子的父親是宋國人就可以了。現在,你還堅持說這孩子是本地人嗎?”
“啥?你說他爹是宋國人?你憑啥在這瞎咧咧?俺們四鄰五舍這么多口子都沒見過他爹,咋的,難不成你認識那個野漢子?”
“不錯。”
村民們大吃一驚,比長壓抑著心中的不快繼續問道:“那你倒是給俺說說,那野漢子究竟是誰?”
“不可說。老夫只能告訴你,這個孩子姓老。”
“放屁!娃他娘生前說了,娃姓李,李子的李,知道不?”
商先生微微一笑,並沒有因為比長的無禮而有所慍怒,他幽幽地說道:“老夫對這孩子的身世了如指掌,如有妄言願遭天譴。只不過老夫受人所託,要永遠保守這個秘密,所以只能向各位有所隱瞞了。”
比長暗想:“看來這老傢伙沒有騙人。”於是他又轉陰為晴,強堆起笑臉對商先生說道:“這位先生,你看,俺是個粗人,說話可能不太中聽,不過俺也是個講理的人。這樣吧,孩子呢還是由我們來撫養,您是讀書人,有文化,就給這孩子起個名字吧。”
“髭發皆白,耳長而墜……不如就叫他老聃如何?”
“好,好,老聃好。”
商先生似乎忽然想到了什麼,於是又繼續說道:“既然理氏執意要孩子姓李,那就兩姓並存,姓李名耳號老聃好了。”
“這個好,這個好,李耳,這個好,嘿嘿。”比長憨憨地笑了,比起那個拗口的“老聃”,他顯然更喜歡這個通俗易懂的“李耳”,至於號不號的那些文縐縐的東西他向來是漠不關心的。
比長將村里人召集起來,在他的主持下,孩子最終過繼給當地的一戶富農。商先生雖然有些不捨,但見苦縣清幽寧靜,民風淳樸,便尊重了當地百姓的意願。
“好吧,那就勞煩各位好生照顧這個孩子了,商某就此別過。”商先生起身告辭,最後又望了一眼襁褓中的嬰兒,“以後若是有什麼困難,可以隨時讓他來找我,在下宋人商容。”
正午的日光熾熱而刺眼,屋子裡卻伸手不見五指。一陣輕輕的嘆息打破了這令人窒息的死寂,黑暗中忽然亮起了一絲微弱的燭光,精緻的漆木案幾漸漸地變得清晰起來,案幾之上端放著一張詭異的面具,一個英俊而疲憊的身影投射在北面的牆壁上。
“老淵啊老淵,白日點燈,你意欲何為?”
“白即是黑,日即是夜,白日即為黑夜,我於黑夜點燈,有何不可?”
“老淵啊老淵,拋棄妻子,你該下地獄!”
“我已在地獄,何有再下之理?”
“老淵啊老淵,你是要苦了那孩子!”
“與其讓他跟著我東躲西藏,不如還他正常人的天地。”
……
這時,門敲得“咚咚”直響,蠟燭熄滅,一張藏於面具之後的臉龐出現在熱辣辣的驕陽之下。
“找我何事?”
“快點吧,村東理氏快要生了,可能是難產。”
面具心中一緊,卻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跟在穩婆那飛快的碎步之後。一路上,他的思緒飛轉,父親戰死的那一幕又一次出現在他的面前……
事情還要從五年前的夏天說起,那一年宋共公不幸離世,宋國大政旁落於右師華元的手中。共公健在的時候,以左師魚石為首的桓氏宗親便一直對宋國的國政大權虎視眈眈,如今共公離世,他們立刻變得蠢蠢欲動,預謀乘機奪權。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魚石僚屬的一名小妾偏偏和華元手下的一員將官有染,起事之前風聲便走漏了出去。華元怒不可遏,決定聯合整個戴氏宗族一舉將桓氏宗族這根肉中刺連根拔除。可魚石這個傢伙比狐狸還狡猾,他早就留有後手,宋都的守門官是他安插的親信。一看形勢不好,魚石便立刻率眾逃亡楚國。
由於自己的百密一疏,竟讓魚石這老小子從容地逃走了,華元氣得暴跳如雷,將守門將官一家老小悉數誅殺。新君宋平公初立之後,又命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百官封賞完畢,宋國的局面才暫時穩定下來。
俗語有云: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這話一點不假,魚石在楚國藏匿了三年,這三年里他上下打點,四處聯結,處心積慮,伺機報仇。公元前573年六月,在魚石的挑唆與煽動下,楚國興兵伐宋,一舉攻克宋國的彭城(今江蘇徐州)。楚軍得勝撤退後,留下三百乘兵車幫助魚石和魚府坐鎮戍守。
訊息傳到宋平王的耳朵里,身為一國之君的平王氣得臉都綠了:“這群該死的叛徒!寡人定要將他們食肉寢皮,挫骨揚灰!”
“請主君息怒,彭城乃我宋國要邑,如今淪於敵手,自然不可輕言放棄。但我軍新敗,士氣低迷,不宜馬上出兵啊。”華元對宋國形勢的急轉直下感到憂心忡忡,對當初放走魚石黨徒更是悔恨不已。
“寡人還就不信了,先君襄公不是就曾擊敗過強齊嗎?楚蠻欺人太甚,占我大邑,是可忍?孰不可忍!”
“主君莫忘泓水之辱!當年先君不聽公子目夷之策,結果一戰而使我宋軍精銳損失殆盡。泓水之畔,血流成河,哀聲遍野,想我全盛之時,尚不可與楚軍一爭高下,如今楚軍方退,我豈可再輕言挑釁?”
“怎么?相國這是以目夷自比,譏刺寡人無道嗎?”
“臣不敢,臣只是……”
“你不要再說了,寡人不想聽。想你也是隻身深入過楚營的人,當年的勇氣哪去了?寡人現在只想知道,你們誰能擊破楚軍,收復彭城,替寡人分憂?”
華元歷事昭公、文公、共公,如今又為平王右師,可謂“四朝元老”。飽經世事的他知道平王這是被憤怒沖昏了頭腦,當下也不好再說什麼。
“愚臣願為君上分憂!”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將眾人的耳膜都震得嗡嗡作響。只見此人目光炯炯,腮闊肩寬,眉宇之間自帶一分令人不寒而慄的肅殺之氣,他不是別人,正是剛剛走馬上任不久的左司馬——老佐。
“好!好!老將軍英勇善戰,定能得勝。寡人封你為上將軍,領兵兩萬,星夜出擊,務必要為寡人拿下彭城啊!”
“請君上放心,愚臣定不辱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