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式精神病:美國人一直致力於在全世界推廣美國對精神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和認識,其結果可能是導致美國式的精神疾病也開始全球化。這個結論是在不久前一個由人類學家、跨文化精神病學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發布的。
基本簡介,歷史背景,病例發展,現象,發病過程,發病現象,研究發現,傳播,產生影響,醫學領域,文化領域,社會影響,專家建議,
基本簡介
歷史背景
一些受過教育的左傾美國人有些擔心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文化入侵帶來的後果。如今我們又增加了一種憂慮,這恐怕是“全球美國化”造成的最嚴重後果。多年來,我們一直致力於在全世界推廣美國對精神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和認識,其結果可能是導致美國式的精神疾病也開始全球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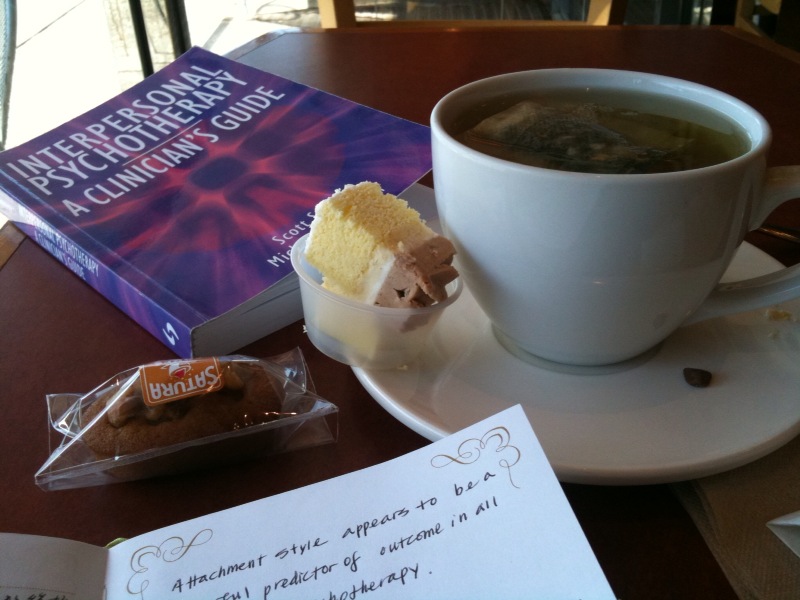 美國式精神病
美國式精神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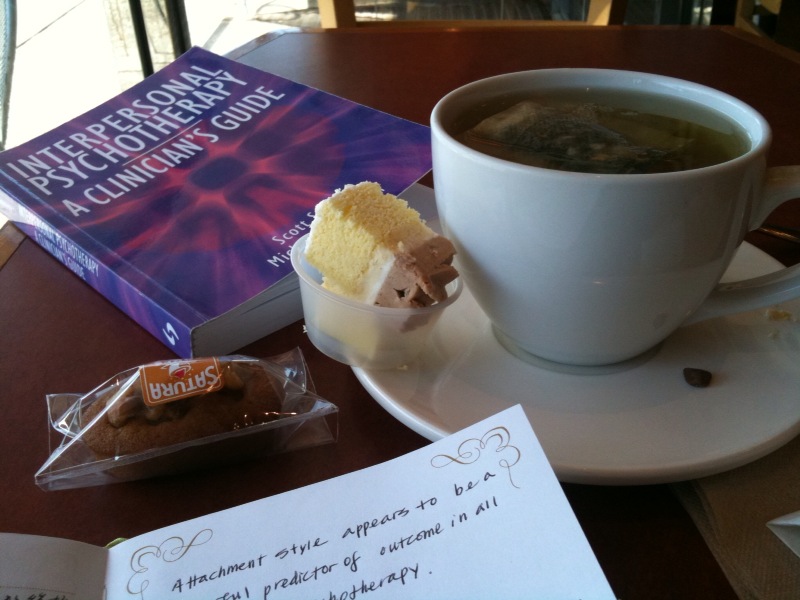 美國式精神病
美國式精神病病例發展
這個結論是在不久前一個由人類學家、跨文化精神病學專家組成的研究小組發布的。這些研究人員認為,精神疾病不像小兒麻痹症這樣有自己傳播歷史的獨立疾病,研究人員收集的大量個體案例證明,世界各地的精神疾病都各不相同,但都毫無例外地帶有一定的時代和地域特徵。在一些東南亞文化圈中,男人常會得一種叫“殺人狂疾病 ”(amok),這種疾病由記憶缺失症引起;而中東地區正在呈線性增長的精神疾病叫做Zar,這是由宗教對人的精神占據所引起的精神恍惚。而在1980 年代的歐洲,很多男人患有神遊症——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步行幾百英里;19 世紀晚期,患有腿部中風癔症的中產階級婦女數量激增,因為當時對女性權利的重重限制導致了女性對自己的身體產生了患病的假想。
現象
發病過程
美國式精神病
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病專家李欣博士(音譯)親眼見證了精神疾病的美國化。在1980 年代晚期和1990 年代早期,他都致力於研究一種帶有文化特色的香港式精神性厭食症。和美國式厭食症不同,他的病人無意節食,也不懼怕肥胖,他們厭食大多因為患有胃脹氣。李欣博士試圖理解這種本土厭食症,同時找出為什麼這種疾病如此罕見。
發病現象
當他開始撰寫厭食症的香港特例時,厭食症突然成了公眾熱議的話題。1994年11月24 日,一個十幾歲的厭食症少女暴斃在一條繁忙的鬧市區街道上。事後,中文媒體對此事的報導大多直接拷貝了美國醫生的診斷結論,大多數專家都認為這個香港女孩的厭食症和美國以及歐洲的厭食症一樣(即由怕胖節食而導致)。緊隨著少女之死,人們對厭食症的認識(包括致病原因、症狀、主要人群)都遵循了一條很簡單的道路:從西方到東方。
西方醫學不僅簡單地模糊了港式厭食症的特徵,甚至還改變了對港式厭食症的描述。在李欣博士此後接觸的厭食症案例中,由懼怕肥胖導致的厭食症比例迅速增加,2007 年,懼怕肥胖導致的厭食症占到了所有厭食症案例的90%,大多數患者都相信怕胖是他們讓自己挨餓的最重要原因。
研究發現
李欣和一些研究者注意到,患者的主觀期待和信仰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最終的病症。“文化有時能塑造精神疾病。當媒體、學校、醫生都認定、談論和宣傳厭食症是因為怕胖引起的時候,人們就會有意或無意地將進食障礙歸咎為怕胖。”  美國式精神病
美國式精神病
 美國式精神病
美國式精神病“當西方醫學對疾病的分類占據了主導地位,弱勢文化對個體疾病的定義就被剝奪了。”那么港式厭食症可能擁有一套區別於西方厭食症的定義嗎?看起來沒可能。李欣說,因為厭食症早在19世紀早期就出現在歐洲,西方精神病學專家花了50 多年給它命名,並把厭食症編入癔症的行列之一。
傳播
不止一代美國人將自己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傳播到世界各地。以科學的名義,相信對導致精神疾病的生物學原理的揭示,驅散了近代科學之前人類對精神疾病的神秘化解釋和治療。簡而言之,不僅改變了精神疾病的治療方法,還用自己的語言方式闡釋了其他文化中的精神疾病。事實上,一些精神疾病——憂鬱症、創後精神失調、厭食症——這些疾病的名稱就像傳染病一樣在世界各地跨文化傳播,混合和取代了精神疾病的固有形式。
產生影響
醫學領域
在專業醫學領域,很少有人談及西方精神健康和疾病的理念可能影響其他文化對精神疾病的闡釋。很多受到當代精神病學教育的年輕學者和從業人員,把已有的關於藥物和疾病分類當成了寶典,而忽視了精神疾病可能帶有的文化差異性。
但是,跨文化精神病學專家和人類學家卻告訴我們,所有的精神疾病,包括抑鬱症、創傷後應激障礙,甚至精神分裂症,都可能因為文化信仰的不同而有區別,就像前文提到的殺人狂疾病、Zar 以及腿部中風癔症一樣。如果不了解這些精神疾病患者的思想、習慣、體質(這些特殊的文化標誌),就不能真正了解這種疾病。
文化領域
跨文化精神病學家指出,我們輸往世界的精神健康理論絕非有十足的科學依據,在文化上也不完全中立。倫敦精神病學專家德里克·薩默菲爾德說:“西方精神健康論述的核心組成部分是西方文化,包括人性理論、人格定義,是對時間和記憶的片段認識,也是道德權威發揮作用的地方。其中沒有一樣是具有普適性的。可是當西方精神健康的論述處於全球化之下時,也得到了徹底的信任,就好像人性的版本只有一種,疼痛和苦難只有一種模式。精神病學沒有絕對。”
社會影響
西方精神病學的論述和治療大受推崇的背後,隱含著他們對人性的多樣化的臆測。西方人對什麼樣的事件可能導致精神創傷有著類似的看法;我們也認同傾訴比沉默寡言更利於心理健康;我們也知道人類的思想其實很脆弱,需要專業的干預手段(美國國家精神健康協會的報告中,每年大約有1/4的美國人診斷患有精神疾病)。我們輸往世界各地的精神療法都帶有明顯的美國標籤。這些療法深深受到笛卡爾的意識與物質分離的二元論、弗洛伊德的意識和潛意識二元論的影響,還受到將個體健康和群體健康分離開來的自救哲學的影響。這些思想觀念就像麥當勞、說唱樂一樣,對其他國家具有強烈的吸引力。
沒人願意承認我們醫學水平的發展抑制了別國醫學水平的發展,但是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我們對人類大腦的最深刻認識並沒能顧及到全人類。當先進的科學被轉化為流行信仰和文化事件時,它們包含的複雜科學含義常常會被剔除,剩下的只有滑稽的空洞敘述。網路上流傳的一種抗抑鬱藥廣告是這么說的:“和做蛋糕需要比例正確的麵粉、糖和發酵粉一樣,你的大腦也需要比例均衡的化學藥品來平衡,讓它運轉得更好。”被一代理論家和研究者分析闡釋的西方思想,最後只是被簡化成塞進大腦的化學藥品。
專家建議
所有的文化都在和難以痊癒的精神疾病做鬥爭,而我們自己也一步步更加墜入安全感減少和恐懼增強的漩渦中。很多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專家建議,我們應該把更多的金錢用來研究和治療精神疾病——讓醫學在人類歷史上發揮更大作用——因為我們突然間失去了古老的信仰體系,也讓精神失去了意義和依託。  美國式精神病
美國式精神病
 美國式精神病
美國式精神病如果說我們日益增長的精神健康需求是因為信仰的缺失,那么讓其他國家的人也像我們一樣思考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問題。用西方的精神健康理論、治療方法和分類,來嘗試治療現代化和全球化引發的精神疾病,可能會讓問題更加嚴重。
如果我們不尊重其他民族和文化中的自我認識和治療方式,則可能加劇全世界的精神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