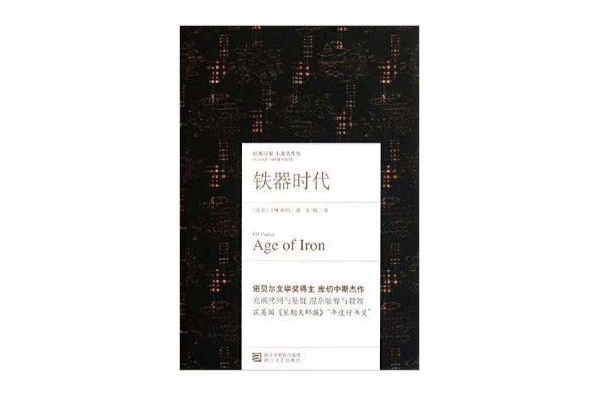《經典印象小說名作坊:鐵器時代》是2012年1月1日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J.M.庫切。
基本介紹
- 書名:經典印象小說名作坊:鐵器時代
- 作者:J.M.庫切
-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 頁數:217頁
- 開本:32
- 品牌:浙江文藝
- 外文名:Age of Iron
- 譯者:文敏
- 出版日期:2012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3932930, 7533932935
內容簡介,編輯推薦,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
內容簡介
《經典印象·小說名作坊:鐵器時代》講述的確,庫切——無論是他的人,還是他的作品——常常會讓我們想到鐵。他像鐵一樣冷酷,堅硬,不動聲色。但與其說這是出於天性,不如說更是出於需要,出於一種抵抗這個世界的需要。通過文學和虛構,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庫切式的抵抗風格,而《經典印象·小說名作坊:鐵器時代》就是這種風格最成熟最熾烈的表現:庫切的中期傑作——《鐵器時代》。一起來翻閱《鐵器時代》吧!
編輯推薦
《經典印象·小說名作坊:鐵器時代》反映了國家內部的這場衝突和悲劇。庫切研究專家戴維·阿特維爾(David Attwell)當時在南非工作,以目擊者的口吻評論說,南非已經變成一個“完全沉溺於爭奪權力的社會”。國家的悲劇使它年富力強的知識分子深感痛苦,我們從納丁·戈迪默和庫切等人的作品中,多少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作者簡介
作者:(南非)J.M.庫切(J.M.Coetzee) 譯者:文敏
J.M.厙切(1940—),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和學者。生於南非開普敦,先後在南非和美國接受教育。庫切學識淵博,在文學、哲學、社會學、倫理學和宗教方面造詣頗深,是一位學者型作家。幾乎囊括所有文學大獎,兩次獲得布克獎,是英語文學中獲獎最多的作家。1980年小說《等待野蠻人》一出版,即為庫切贏得了國際聲譽,英國企鵝出版社將此書列入“20世紀繹典”系列。
J.M.厙切(1940—),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和學者。生於南非開普敦,先後在南非和美國接受教育。庫切學識淵博,在文學、哲學、社會學、倫理學和宗教方面造詣頗深,是一位學者型作家。幾乎囊括所有文學大獎,兩次獲得布克獎,是英語文學中獲獎最多的作家。1980年小說《等待野蠻人》一出版,即為庫切贏得了國際聲譽,英國企鵝出版社將此書列入“20世紀繹典”系列。
媒體推薦
的確,庫切——無論是他的人,還是他的作品——常常會讓我們想到鐵。他像鐵一樣冷酷,堅硬,不動聲色。但與其說這是出於天性,不如說更是出於需要,出於一種抵抗這個世界的需要。通過文學和虛構,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庫切式的抵抗風格,而這本書就是這種風格最成熟最熾烈的表現:庫切的中期傑作——《鐵器時代》。
庫切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鐵器時代》緊張,具有諷刺意味,令人悲傷,最後,是令人驚訝。
——《洛杉磯時報》
一個現代南非的極其壯麗的場面,一部傑出作家筆下的非凡作品。
——《華爾街日報》
庫切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鐵器時代》緊張,具有諷刺意味,令人悲傷,最後,是令人驚訝。
——《洛杉磯時報》
一個現代南非的極其壯麗的場面,一部傑出作家筆下的非凡作品。
——《華爾街日報》
圖書目錄
在暴力的旋風中寫作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譯後記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譯後記
後記
庫切寫作《鐵器時代》時已經成名,這是他的第六部作品,此前出版的《等待野蠻人》(1980)、《麥可·K的生活和時代》(1983)都為他贏得了蜚聲國際文壇的美譽。值得注意的是,這兒出現了一道分界線:庫切此前的五部小說,雖說無一例外地表現了對殖民文化、種族主義、暴力與仇恨的思考與追問,但手法上都帶有笛福、卡夫卡和貝克特式的寓言風格,充滿了意象、隱喻和象徵意味;正是這部《鐵器時代》陡然來了一個轉折,那就是作者第一次施以寫實手法,直接切入當時南非的社會問題。
庫切擅長通過最簡單的人物關係去表現一個複雜世界,《鐵器時代》無疑是這種以簡馭繁的典例。這部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的小說,真正意義上的人物只有兩個:主人公卡倫太太和流浪漢范庫爾先生。卡倫太太是一個退休的大學歷史教師,獨自住在一幢大房子裡,丈夫早已離異,唯一的女兒遠在美國。她被確診罹患癌症的同一天,在自家車庫後邊發現了庇身於紙板箱裡的范庫爾。作為一個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女性,她對范庫爾這樣的弱勢群體懷有悲憫之心。幾次接觸之後,她開始向范庫爾提供食宿之便。可是范庫爾對於來自這樣一位中產階級老嫗的援助並不怎么領情,現實的磨難給他帶來了一副冷漠心腸。既然暴力、混亂和不公正已是社會常態,酗酒便成了他最正常的生活方式。這裡擺出了一副有趣的對立格局:一方面是卡倫太太的多愁善感,伴隨著病痛的靈魂拷問,面對死亡的自我救贖;一方面是范庫爾的心靈自閉,他的安之若素和渾渾噩噩。這種性格反差顯然容易製造一些話題,更重要的是,其中涵納了極為豐富的現實內容。
卡倫太太和范庫爾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喋喋不休,訴說自己的往事,談論自己的病情,感慨世道混亂。范庫爾通常默不做聲,也許是心不在焉,也許根本就接不上她的話茬(尤其那些有關生命與死亡的言談)。她的講述每每成了自言自語,就像“雨水落在荒漠的土壤里”。其實,不光在范庫爾面前嘮叨不休,她也跟自己的黑人女傭討論社會話題,開導黑人孩子如何去適應社會規則……甚至,她還愛跟警察去較真。如果說范庫爾的沉默意味著話語權利的淪喪(馬克思談到19世紀50年代法國農民時說過,他們不能表達自己,他們只能由別人替自己表達),那么卡倫太太的多嘴多舌是否可以認為是握有某種話語權柄呢?——不!當然不是。相比范庫爾的緘默不語,卡倫太太話癆似的言談恰好以另一種方式證實表達的困難。話語言說有時只是一種聲音,不幸的是沒有人肯傾聽她的聲音。
女傭弗洛倫斯和她的兒子貝奇,還有貝奇那個自稱約翰的朋友,以及開普敦郊外黑人棚屋區的芸芸眾生,構成了一個他者的世界。作為白人的卡倫太太正是通過自己的女傭跟黑人世界發生了關聯,並由此親眼目睹了白人種族主義對人性和生命的戕害。本書的敘述重點並非主人公自身的命運,一開始就陷入死亡陰影的卡倫太太難以續寫跌宕起伏的生命篇章,只是現實的罪愆一再激發她內心的救贖意識,而他者的厄運又使她不斷墜入恥辱的深淵。書中前後三次出現黑人的不幸事件,恰是推動故事發展的主要情節——
第一次是貝奇和約翰騎腳踏車玩耍,被警車逼向路邊撞上一輛小貨車,邁出家門的卡倫太太恰好目睹了這一幕。其實她的屋宅已被警方監視,就因為這兩個黑人少年住在裡邊。腳踏車事件給卡倫太太造成巨大的心理衝擊,白人專制政權的“維穩”政策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這深深刺痛了她。她去醫院看望傷勢嚴重的約翰,去警察局投訴肇事警員。可是受害者並不需要她的同情(因為她是白人),而施虐者顯然將她視作瘋老太婆(因為她替黑人說話),在種族隔離和階級對峙的社會裡,卡倫太太的人文關懷只是帶著知識分子腔的喃喃低語。
第二次是黑人棚屋區的騷亂之夜,卡倫太太駕車陪伴弗洛倫斯去找兒子。政府軍控制了那個地區,暴力與殺戮的結果是一場大悲慟。在被焚毀的房子裡,她們看到了貝奇和另外幾個黑人男孩的屍體。這些被槍殺的孩子顯然已成了抵抗戰士,在為自己的族群而戰。卡倫太太曾與弗洛倫斯爭辯過一個問題:孩子們是應該回學校讀書,還是投身反對種族隔離的戰鬥?卡倫太太自然記得,貝奇和約翰住在她家時是怎樣毆打范庫爾的——那鐵器般的冷血性格,讓她想到了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暴戾、殘忍,想到了斯巴達人的嚴酷、冷漠,想到了加爾文主義的鐵血教義……面對年輕生命的夭折,面對這些沒有童年的孩子,卡倫太太只有悲憤的哭泣,現實的殘酷使她陷人失語狀態。
第三次是警方捕殺約翰,事情就發生在卡倫太太家中,傷勢未愈的約翰從醫院裡跑到她這兒來了。幾天后警察找上門來。事後據警方稱述,約翰除了有槍,還藏有引爆裝置。作為女主人,她試圖阻撓警方的行動,但槍擊開始後被強行帶出家門。她雖然沒看見約翰被暴雨般的火力擊斃的情形,心裡卻在想像那個男孩富有“英雄氣”的抵抗場面。在這起事件中,卡倫太太的個人尊嚴遭受了可怕的踐踏,警方占領了她的屋宅,搜查了每一個房間。負氣出走的她,做了一整天的流浪者,還意外地遇見了被自己逐出家門的范庫爾。在路邊灌木叢里,她無法安睡,喋喋不休地向范庫爾陳述內心的憤懣。這時候,她開始意識到反抗的意義。她質問自己:“我有什麼權利希望貝奇和他的朋友別去惹麻煩?”雖然依然反感那些鼓吹年輕人去犧牲自己的起義號召,但她似乎已經明白:在這個時代,僅以廉恥感維護做人的體面是不夠的。這個時代要求的是英雄主義——對她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詞兒。
在卡倫太太的故事裡,這幾起黑人被踐踏、被殺戮的事件並非敘述主體,可以說它們只是某種插曲或是背景事件。卡倫太太被捲入這些事件的程度似乎漸次深入,但她不是黑人運動的參與者,只是一個“不想置身事外”的旁觀者。她對黑人的命運深感同情,對他們以暴制暴的鬥爭方式卻另有看法。她從未認真思考過黑人的命運與前途,只是最後當自身的權利亦被踐踏之時才對反抗的意義有所領悟。她是在基本人權的層面上,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譬如,面對警察的冷漠與蠻橫),感受到這個時代的荒謬。當局的種族主義政策讓她深感恥辱,讓她痛心疾首,這一切無疑像癌細胞似的吞噬著她的生命。
癌症,無疑是一個象徵。喻示著一個死結,一種不可救藥的局面。
轉向寫實路子的庫切並沒有完全拋棄他已駕輕就熟的隱喻手法。這裡依然有著他早期作品中擅用意象的敘述特點,就像《內陸深處》那樣揮灑自如地表現主人公的玄思臆想,他依然用那些寓意複雜的修辭手法編織大段大段極富感性的內心獨白。從血紅雪白的貝加爾湖到俄法戰爭的鮑羅金諾會戰,從布娃娃到螃蟹肆虐的意象……鎮痛劑的致幻效果總讓卡倫太太的大腦活動進入漂浮狀態,各種思緒密集而來,又極度跳躍。突兀的喻象,碎片化的言述,一閃而過或是勾連反覆;藉由病中的吟喔,道出了不乏詩意的悲情詠嘆。事實上,正是這些意蘊複雜的內心獨白構成了這部作品的敘述主體。
面對這個混亂的世界,感時傷物的卡倫太太不知道該譴責哪一方。阿非利堪人的種族主義也好,黑人等有色人種的反抗也好,那些鐵腕式的暴力統治和獻祭式的自我犧牲都與她信奉的價值觀格格不入。只是現實的痛感讓她愈益傾向於黑人,儘管她不喜歡過早失去童真的約翰,卻也敬佩他的“英雄氣”。這是一個崇尚英雄主義的“鐵器時代”,可這個時代沒有真理,沒有真相,一切都消解在你死我活的仇恨之中,一切都在相生相剋的話語纏繞中被遮蔽了。或許,真正的良知和教益只能從現實的苦難中去領受,舔著被人塞進嘴裡的泥沙才知道自己的愛恨所在。這時候她甚至都覺得自己那兩個在美國的外孫失去了生命意義,她女兒一家跟動亂的南非隔得遠遠的,她不必為他們擔憂,有時卻在想像著那種人生的乏味和虛幻。死亡愈益臨近之際,她不斷思忖生命的意義。生命,或許如她最後所想到的那回事——“生命就是溺水。徑直落入水中,沉到水底。”
她的內心在崩塌。癌症的疼痛深入骨髓,對於這個世界的失望更是讓她痛不欲生。她一直在想著自殺的事兒,甚至想過在政府大道上撞車自焚。流浪漢范庫爾不能理解她的憤世嫉俗,對她這種知識分子的唧唧歪歪很是不屑。在海邊的梅森堡山上,范庫爾告訴她,如果你想被人推下去,我會來幫你一把的。在約翰被警方獵殺的那天,卡倫太太終於做了一回“流浪婆”,看上去她的負氣出走像是一種自我放逐,其實她早已是一個精神上的流浪者。除了無時不在的痛感(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她已經無所歸依。在最後的日子裡,她只能靠范庫爾照料自己的日常起居;兩個完全不同的孤獨者多少有些歡喜冤家的意思,他們落到不得不相濡以沫的地步——“在互相的撕扯中移步換形,在跌倒爬起的過程中彼此扶持。”
最後,卡倫太太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藉助范庫爾之手,在他“沒有一絲暖意”的擁抱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可以說,整部小說就是一番“靈魂的自我梳理”的內心獨白。當然,並不完全是自言自語的內心活動,實際上她有一個傾訴對象,那就是她遠在大西洋彼岸的女兒。這是一部形式獨特的書信體小說,從頭到尾是她寫給女兒的一封長信。她讓范庫爾在自己死後把這些書信文稿寄給她女兒,她要讓已經成為美國人的女兒知道這一切。可是,為什麼要讓南非的噩夢去追逐自己逃離苦海的親人呢?卡倫太太不一定想過這個問題,但是她需要有一個傾聽者。弗洛倫斯不肯聽她的傾訴,塔巴拿先生(此人猶如黑人棚屋區的教父)也不重視她說的話,警察更不聽她的,甚至在她身旁的范庫爾也對此置若罔聞——她寫道:“從一開始,他就知道怎樣對我的問題進行篩選,哪些會聽進去,哪些根本就聽而不聞。”於是,她女兒就成了一個假定的傾聽者。她也懷疑這假定的傾聽者是否會傾聽自己的言說,她知道自己這是在用言語勒緊靈魂的套索。一個陷入“無物之陣”的孤獨者,還能怎樣確立自己的價值認同?四顧茫然的卡倫太太只能在那兒嘮嘮叨叨,喃喃自語……
這本書英文原名是Age of Iron,是否一定要譯作“鐵器時代”,最初我頗感躊躇。“鐵器時代”是一個考古學名詞,庫切的故事是否在某個層面上比附考古學意義上的人類發展階段,我不敢輕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換成“鐵的時代”顯然是穩妥的譯法,或者用“鐵血時代”也跟內容比較貼近。當然,就本書那種絕望、悲涼的意蘊而言,譯作“黑鐵時代”似乎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希臘和羅馬神話中專門有這一說法,是指走向邪惡和墮落的世界末期。全書譯出之後,我又反覆斟酌,考慮到下述兩個因素,最後還是選用“鐵器時代”作為書名。
首先,這裡是一個借用的說法。“鐵器”(iron)一詞在本書中最初出自黑人女傭弗洛倫斯之口,用以讚譽那些投身戰鬥的黑人少年。可是,卡倫太太決不贊成讓孩子們去作出那種犧牲。她認為,正是以牙還牙的流血鬥爭使人變得心如頑鐵。她用“鐵器時代”、“花崗岩時代”喻指野蠻、愚頑,用“黏土時代”、“泥土時代”表示人心柔順,而“青銅時代”大概是一個趨向堅硬的轉折點。器物材質的軟硬程度分別標示著某個時代的主調,譬如對抗還是和平。卡倫太太對“鐵器時代”這個詞顯然另有定義,並非簡單地套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一般概念,而且在她看來,文明與野蠻的嬗變有著某種“循環周期”。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卡倫太太的這種觀念無疑具有顛覆性。
其次,細審作為考古學名詞的“鐵器時代”,其本身亦包含了可以成為某種轉喻的歷史內涵。不妨看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關於“鐵器時代”的釋義有哪些要點:根據“石器——青銅器——鐵器時代序列中的最後技術與文化階段”的定義,該詞條概述了“鐵器時代”在不同地區的起始年代,最後總結道:
……隨著鐵製品的大規模生產,出現了一些比較固定
的新型居民點。另一方面,由於利用鐵製造武器,人民民眾
破天荒第一次擁有兵刃,引起歷時兩千年尚未結束的各族
人民一系列大規模的活動,使歐洲和亞洲的面貌發生變化。
這一詞條譯自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一九八九年版,不知為什麼其中沒有提到非洲大陸的變化。但是毫無疑問,“鐵器時代”除了標誌生產力發展之階段水平,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民間開始有了武器(兵刃)。就我們相對熟悉的中國歷史而言,民眾的造反大抵是秦漢以後的事情,這跟鐵器在中國廣泛使用的時間大致吻合。從革命與暴力的意義上說,這兩千年來人類其實一直未能走出“鐵器時代”,無論統治階級的鎮壓還是被壓迫者的反抗,無論疆界凶釁還是部落之間的征伐,迄今依然是打打殺殺的頑習阻礙著人類文明進程,也許這正是庫切以此作為書名的用意所在。
文敏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庫切擅長通過最簡單的人物關係去表現一個複雜世界,《鐵器時代》無疑是這種以簡馭繁的典例。這部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的小說,真正意義上的人物只有兩個:主人公卡倫太太和流浪漢范庫爾先生。卡倫太太是一個退休的大學歷史教師,獨自住在一幢大房子裡,丈夫早已離異,唯一的女兒遠在美國。她被確診罹患癌症的同一天,在自家車庫後邊發現了庇身於紙板箱裡的范庫爾。作為一個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知識女性,她對范庫爾這樣的弱勢群體懷有悲憫之心。幾次接觸之後,她開始向范庫爾提供食宿之便。可是范庫爾對於來自這樣一位中產階級老嫗的援助並不怎么領情,現實的磨難給他帶來了一副冷漠心腸。既然暴力、混亂和不公正已是社會常態,酗酒便成了他最正常的生活方式。這裡擺出了一副有趣的對立格局:一方面是卡倫太太的多愁善感,伴隨著病痛的靈魂拷問,面對死亡的自我救贖;一方面是范庫爾的心靈自閉,他的安之若素和渾渾噩噩。這種性格反差顯然容易製造一些話題,更重要的是,其中涵納了極為豐富的現實內容。
卡倫太太和范庫爾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喋喋不休,訴說自己的往事,談論自己的病情,感慨世道混亂。范庫爾通常默不做聲,也許是心不在焉,也許根本就接不上她的話茬(尤其那些有關生命與死亡的言談)。她的講述每每成了自言自語,就像“雨水落在荒漠的土壤里”。其實,不光在范庫爾面前嘮叨不休,她也跟自己的黑人女傭討論社會話題,開導黑人孩子如何去適應社會規則……甚至,她還愛跟警察去較真。如果說范庫爾的沉默意味著話語權利的淪喪(馬克思談到19世紀50年代法國農民時說過,他們不能表達自己,他們只能由別人替自己表達),那么卡倫太太的多嘴多舌是否可以認為是握有某種話語權柄呢?——不!當然不是。相比范庫爾的緘默不語,卡倫太太話癆似的言談恰好以另一種方式證實表達的困難。話語言說有時只是一種聲音,不幸的是沒有人肯傾聽她的聲音。
女傭弗洛倫斯和她的兒子貝奇,還有貝奇那個自稱約翰的朋友,以及開普敦郊外黑人棚屋區的芸芸眾生,構成了一個他者的世界。作為白人的卡倫太太正是通過自己的女傭跟黑人世界發生了關聯,並由此親眼目睹了白人種族主義對人性和生命的戕害。本書的敘述重點並非主人公自身的命運,一開始就陷入死亡陰影的卡倫太太難以續寫跌宕起伏的生命篇章,只是現實的罪愆一再激發她內心的救贖意識,而他者的厄運又使她不斷墜入恥辱的深淵。書中前後三次出現黑人的不幸事件,恰是推動故事發展的主要情節——
第一次是貝奇和約翰騎腳踏車玩耍,被警車逼向路邊撞上一輛小貨車,邁出家門的卡倫太太恰好目睹了這一幕。其實她的屋宅已被警方監視,就因為這兩個黑人少年住在裡邊。腳踏車事件給卡倫太太造成巨大的心理衝擊,白人專制政權的“維穩”政策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這深深刺痛了她。她去醫院看望傷勢嚴重的約翰,去警察局投訴肇事警員。可是受害者並不需要她的同情(因為她是白人),而施虐者顯然將她視作瘋老太婆(因為她替黑人說話),在種族隔離和階級對峙的社會裡,卡倫太太的人文關懷只是帶著知識分子腔的喃喃低語。
第二次是黑人棚屋區的騷亂之夜,卡倫太太駕車陪伴弗洛倫斯去找兒子。政府軍控制了那個地區,暴力與殺戮的結果是一場大悲慟。在被焚毀的房子裡,她們看到了貝奇和另外幾個黑人男孩的屍體。這些被槍殺的孩子顯然已成了抵抗戰士,在為自己的族群而戰。卡倫太太曾與弗洛倫斯爭辯過一個問題:孩子們是應該回學校讀書,還是投身反對種族隔離的戰鬥?卡倫太太自然記得,貝奇和約翰住在她家時是怎樣毆打范庫爾的——那鐵器般的冷血性格,讓她想到了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暴戾、殘忍,想到了斯巴達人的嚴酷、冷漠,想到了加爾文主義的鐵血教義……面對年輕生命的夭折,面對這些沒有童年的孩子,卡倫太太只有悲憤的哭泣,現實的殘酷使她陷人失語狀態。
第三次是警方捕殺約翰,事情就發生在卡倫太太家中,傷勢未愈的約翰從醫院裡跑到她這兒來了。幾天后警察找上門來。事後據警方稱述,約翰除了有槍,還藏有引爆裝置。作為女主人,她試圖阻撓警方的行動,但槍擊開始後被強行帶出家門。她雖然沒看見約翰被暴雨般的火力擊斃的情形,心裡卻在想像那個男孩富有“英雄氣”的抵抗場面。在這起事件中,卡倫太太的個人尊嚴遭受了可怕的踐踏,警方占領了她的屋宅,搜查了每一個房間。負氣出走的她,做了一整天的流浪者,還意外地遇見了被自己逐出家門的范庫爾。在路邊灌木叢里,她無法安睡,喋喋不休地向范庫爾陳述內心的憤懣。這時候,她開始意識到反抗的意義。她質問自己:“我有什麼權利希望貝奇和他的朋友別去惹麻煩?”雖然依然反感那些鼓吹年輕人去犧牲自己的起義號召,但她似乎已經明白:在這個時代,僅以廉恥感維護做人的體面是不夠的。這個時代要求的是英雄主義——對她來說,這是一個陌生的詞兒。
在卡倫太太的故事裡,這幾起黑人被踐踏、被殺戮的事件並非敘述主體,可以說它們只是某種插曲或是背景事件。卡倫太太被捲入這些事件的程度似乎漸次深入,但她不是黑人運動的參與者,只是一個“不想置身事外”的旁觀者。她對黑人的命運深感同情,對他們以暴制暴的鬥爭方式卻另有看法。她從未認真思考過黑人的命運與前途,只是最後當自身的權利亦被踐踏之時才對反抗的意義有所領悟。她是在基本人權的層面上,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譬如,面對警察的冷漠與蠻橫),感受到這個時代的荒謬。當局的種族主義政策讓她深感恥辱,讓她痛心疾首,這一切無疑像癌細胞似的吞噬著她的生命。
癌症,無疑是一個象徵。喻示著一個死結,一種不可救藥的局面。
轉向寫實路子的庫切並沒有完全拋棄他已駕輕就熟的隱喻手法。這裡依然有著他早期作品中擅用意象的敘述特點,就像《內陸深處》那樣揮灑自如地表現主人公的玄思臆想,他依然用那些寓意複雜的修辭手法編織大段大段極富感性的內心獨白。從血紅雪白的貝加爾湖到俄法戰爭的鮑羅金諾會戰,從布娃娃到螃蟹肆虐的意象……鎮痛劑的致幻效果總讓卡倫太太的大腦活動進入漂浮狀態,各種思緒密集而來,又極度跳躍。突兀的喻象,碎片化的言述,一閃而過或是勾連反覆;藉由病中的吟喔,道出了不乏詩意的悲情詠嘆。事實上,正是這些意蘊複雜的內心獨白構成了這部作品的敘述主體。
面對這個混亂的世界,感時傷物的卡倫太太不知道該譴責哪一方。阿非利堪人的種族主義也好,黑人等有色人種的反抗也好,那些鐵腕式的暴力統治和獻祭式的自我犧牲都與她信奉的價值觀格格不入。只是現實的痛感讓她愈益傾向於黑人,儘管她不喜歡過早失去童真的約翰,卻也敬佩他的“英雄氣”。這是一個崇尚英雄主義的“鐵器時代”,可這個時代沒有真理,沒有真相,一切都消解在你死我活的仇恨之中,一切都在相生相剋的話語纏繞中被遮蔽了。或許,真正的良知和教益只能從現實的苦難中去領受,舔著被人塞進嘴裡的泥沙才知道自己的愛恨所在。這時候她甚至都覺得自己那兩個在美國的外孫失去了生命意義,她女兒一家跟動亂的南非隔得遠遠的,她不必為他們擔憂,有時卻在想像著那種人生的乏味和虛幻。死亡愈益臨近之際,她不斷思忖生命的意義。生命,或許如她最後所想到的那回事——“生命就是溺水。徑直落入水中,沉到水底。”
她的內心在崩塌。癌症的疼痛深入骨髓,對於這個世界的失望更是讓她痛不欲生。她一直在想著自殺的事兒,甚至想過在政府大道上撞車自焚。流浪漢范庫爾不能理解她的憤世嫉俗,對她這種知識分子的唧唧歪歪很是不屑。在海邊的梅森堡山上,范庫爾告訴她,如果你想被人推下去,我會來幫你一把的。在約翰被警方獵殺的那天,卡倫太太終於做了一回“流浪婆”,看上去她的負氣出走像是一種自我放逐,其實她早已是一個精神上的流浪者。除了無時不在的痛感(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她已經無所歸依。在最後的日子裡,她只能靠范庫爾照料自己的日常起居;兩個完全不同的孤獨者多少有些歡喜冤家的意思,他們落到不得不相濡以沫的地步——“在互相的撕扯中移步換形,在跌倒爬起的過程中彼此扶持。”
最後,卡倫太太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藉助范庫爾之手,在他“沒有一絲暖意”的擁抱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可以說,整部小說就是一番“靈魂的自我梳理”的內心獨白。當然,並不完全是自言自語的內心活動,實際上她有一個傾訴對象,那就是她遠在大西洋彼岸的女兒。這是一部形式獨特的書信體小說,從頭到尾是她寫給女兒的一封長信。她讓范庫爾在自己死後把這些書信文稿寄給她女兒,她要讓已經成為美國人的女兒知道這一切。可是,為什麼要讓南非的噩夢去追逐自己逃離苦海的親人呢?卡倫太太不一定想過這個問題,但是她需要有一個傾聽者。弗洛倫斯不肯聽她的傾訴,塔巴拿先生(此人猶如黑人棚屋區的教父)也不重視她說的話,警察更不聽她的,甚至在她身旁的范庫爾也對此置若罔聞——她寫道:“從一開始,他就知道怎樣對我的問題進行篩選,哪些會聽進去,哪些根本就聽而不聞。”於是,她女兒就成了一個假定的傾聽者。她也懷疑這假定的傾聽者是否會傾聽自己的言說,她知道自己這是在用言語勒緊靈魂的套索。一個陷入“無物之陣”的孤獨者,還能怎樣確立自己的價值認同?四顧茫然的卡倫太太只能在那兒嘮嘮叨叨,喃喃自語……
這本書英文原名是Age of Iron,是否一定要譯作“鐵器時代”,最初我頗感躊躇。“鐵器時代”是一個考古學名詞,庫切的故事是否在某個層面上比附考古學意義上的人類發展階段,我不敢輕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換成“鐵的時代”顯然是穩妥的譯法,或者用“鐵血時代”也跟內容比較貼近。當然,就本書那種絕望、悲涼的意蘊而言,譯作“黑鐵時代”似乎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希臘和羅馬神話中專門有這一說法,是指走向邪惡和墮落的世界末期。全書譯出之後,我又反覆斟酌,考慮到下述兩個因素,最後還是選用“鐵器時代”作為書名。
首先,這裡是一個借用的說法。“鐵器”(iron)一詞在本書中最初出自黑人女傭弗洛倫斯之口,用以讚譽那些投身戰鬥的黑人少年。可是,卡倫太太決不贊成讓孩子們去作出那種犧牲。她認為,正是以牙還牙的流血鬥爭使人變得心如頑鐵。她用“鐵器時代”、“花崗岩時代”喻指野蠻、愚頑,用“黏土時代”、“泥土時代”表示人心柔順,而“青銅時代”大概是一個趨向堅硬的轉折點。器物材質的軟硬程度分別標示著某個時代的主調,譬如對抗還是和平。卡倫太太對“鐵器時代”這個詞顯然另有定義,並非簡單地套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一般概念,而且在她看來,文明與野蠻的嬗變有著某種“循環周期”。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卡倫太太的這種觀念無疑具有顛覆性。
其次,細審作為考古學名詞的“鐵器時代”,其本身亦包含了可以成為某種轉喻的歷史內涵。不妨看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關於“鐵器時代”的釋義有哪些要點:根據“石器——青銅器——鐵器時代序列中的最後技術與文化階段”的定義,該詞條概述了“鐵器時代”在不同地區的起始年代,最後總結道:
……隨著鐵製品的大規模生產,出現了一些比較固定
的新型居民點。另一方面,由於利用鐵製造武器,人民民眾
破天荒第一次擁有兵刃,引起歷時兩千年尚未結束的各族
人民一系列大規模的活動,使歐洲和亞洲的面貌發生變化。
這一詞條譯自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一九八九年版,不知為什麼其中沒有提到非洲大陸的變化。但是毫無疑問,“鐵器時代”除了標誌生產力發展之階段水平,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民間開始有了武器(兵刃)。就我們相對熟悉的中國歷史而言,民眾的造反大抵是秦漢以後的事情,這跟鐵器在中國廣泛使用的時間大致吻合。從革命與暴力的意義上說,這兩千年來人類其實一直未能走出“鐵器時代”,無論統治階級的鎮壓還是被壓迫者的反抗,無論疆界凶釁還是部落之間的征伐,迄今依然是打打殺殺的頑習阻礙著人類文明進程,也許這正是庫切以此作為書名的用意所在。
文敏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