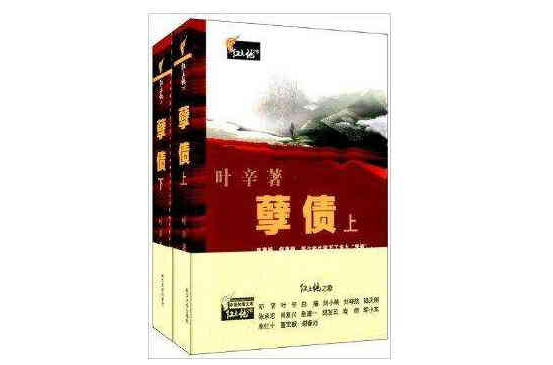《紅土地之歌:孽債(套裝共2冊)》講述了真離婚,假離婚,那個年代留下了多少“孽債”,又留下了多少無父,無母的孩子。5個孽債的產物,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上海,在大上海的燈紅酒綠中尋找父母,只是這裡竟沒有能容納他們的一張床……
基本介紹
- 書名:紅土地之歌:孽債
- 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 頁數:1002頁
- 開本:32
- 品牌:武漢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 作者:葉辛
- 出版日期:2012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7092655, 730709265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紅土地之歌:孽債(套裝共2冊)》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葉辛,1949年10月生於上海。1969年去貴州插隊落戶。1979年11月任貴州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花》雜誌主編。1990年在上海作家協會工作,任《海上文壇》雜誌主編。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大學文學院院長、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1979年發表處女作《高高的苗嶺》,共出版五十餘本書。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蹉跎歲月》、《家教》、《孽債》、《恐怖的颶風》、《三年五載》等。近年來出版《葉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當代名家精品》六卷本;《葉辛文集》十卷本;《葉辛知青作品總集》七卷本;《葉辛新世紀文萃》三卷本等。短篇小說《塌方》獲國際青年年優秀作品一等獎。中篇小說《家教》(上半部)獲《十月》文學獎。長篇小說《孽債》獲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長篇小說《基石》獲貴州省優秀作品獎。由其本人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蹉跎歲月》、《家教》、《孽債》,在全國引起轟動,分別榮獲全國優秀電視劇獎。1985年,被評為全國優秀文藝工作者,並榮獲全國首屆五一勞動獎章。
圖書目錄
孽債(上)
孽債(下)
孽債(下)
後記
十幾年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大返城的時候,具體的返城政策中有兩條規定:其一是已在當地安排工作的知青不能返回;其二是已婚知青(不論你在農村還是鄉鎮企業就職)不能返回。要鑽前一條規定的空子似不那么容易,不少顧慮到回城之後的遭際,也不敢貿然行動。而後一條規定的羈絆無非就是婚姻。於是乎已婚知青中便斷然地採取了行動:有假離婚的,那往往發生在男女雙方均是知青身上;也有真離婚的,那多半是和當地農村人結婚的。掙脫婚姻的鎖鏈,恢復知識青年赤條條無牽掛的身份,他們亦隨著那返城的大潮回歸了城市。這時候城市的誘惑力是那么強大,他們的舉動往往也能得到世人的諒解,但卻忽略了離婚隨之而帶來的負面影響。我是離開鄉村很晚的知青(遲至1979年10月)。當時我曾想,那些被回歸城市的知青離棄了的農村女人和已經生下的娃娃,未來將怎么生活呢?特別是那些孩子,長大之後問及自己的親生父母(多半是父親,也有少數母親),又該如何想像?
可以說長篇小說《孽債》的最初構思,該是起源於那一段生活本身。
儘管是可以構思小說的素材,但是“無米之炊’’是無法做出來的。我也不可能想像這些孩子將來和他的生身父母之問該演出哪些方面的一連串悲喜劇。
好幾年過去了,知識青年這個字眼已經讓人感到陳舊和麻木。儘管北京、廣州、武漢、成都好多大城市裡的老知青們舉行過類似“青春無悔”、“追憶當年”等等活動,頑強地想表現這一代人的存在,但人們再不像當年那樣看待用血汗和眼淚浸染過的“知識青年,,這四個字。恰在這時,我在回上海探親時,聽說了附近弄堂里發生的這么件事:一個寧波農村的漢子帶了兩個孩子,到上海來找當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到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後,早已重新嫁了人,並有了新的孩子。於是乎一個女人兩個男人三個孩子的故事頓時成了弄堂新聞。有人說女人離開農村時根本沒辦妥正式離婚手續,哄騙男人回歸上海之後還將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說第二個男人根本不曉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說兩個男人打起架來了;有人說這個家庭熱鬧非凡有戲文可看……
我沒去窮盡這個故事的底細,隨手按習慣作了札記之後,心裡思忖,這倒是個寫作素材,但是僅僅照生活的本來面貌去寫是不成的。上海生活著一千幾百萬人,上海的包容性又實在太大,同樣一件事發生在內地的村莊裡、小城鎮上會有“滿城風雨”之感,但在上海這僅僅是一條弄堂新聞而已,人們一天到晚聽到的奇聞逸事太多太多了,別說一個小人物小家庭的戲文,中國的外國的上層的下層的稀奇古怪的事兒他們聽得耳朵都起繭子了,他們早就練出了見慣不驚的本事和修養。
這以後不久,我在一家刊物上讀到了一篇小說,名字記不清了,但內容幾乎同我所說的弄堂新聞相差無幾,我特意留神了小說的結尾,似乎作者也沒交代出這一家人究竟如何處理種種解不開理還亂的矛盾,小說的結尾只告訴讀者,這個家正鬧得不可開交……
又隔開了兩三年,我又聽說了這么件事:在西雙版納的一條街子上,有位北京來的旅遊者打扮的中年女子,始終在屋檐下徘徊,嘴裡喃喃自語著失悔一類的話語。原來這女子是當初來西雙版納的北京知青,回城時離了婚,遺下一個孩子給當地的農民丈夫撫養。她走得很輕鬆,回歸北京之後落實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間的事有時總陰差陽錯,二度婚姻之後,她再沒生育。隨著時間的流逝,她越來越思念遺留在西雙版納的和第一個丈夫生的兒子。終於她徵得現今丈夫的同意,趕到西雙版納的故土上來找兒子。誰知這裡的農民從來便有遷居的習俗,她照著原先記憶中的地址尋去,再沒找到她渴念的兒子。於是乎她便有些失態地踟躕在趕場的街子上,逢到人便詢問打聽,便講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頗為曲折的經歷……
聽來讓人悲傷。
吸引我的還不只是這個故事,而是這個故事提供的地域:西雙版納。喔,這是一塊多么美妙無比的土地!那裡的風情習俗和上海相比,簡直判若兩個世界。上海是海洋性氣候,西雙版納是旱濕兩季的山地氣候;上海眾多的人口和住房的擁擠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雙版納的家家戶戶都有一幢寬敞的庭院圍抱的乾欄式竹樓;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樓和狹窄的弄堂,而西雙版納滿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綠的水;上海號稱東方的大都市,是僅次於北京的政治、經濟、文化、外貿、金融的中心,而西雙版納系沙漠帶上的綠洲,是一塊沒有冬天的樂土,既被稱為“山國”里的平原,又被形容為孔雀之鄉、大象之國,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測的自然保護區和獨特珍貴的熱帶雨林;上海人被人議論成精明而不高明、聰明而不豁達,而西雙版納的傣族兄弟姐妹,謙和、熱情、纖柔、美麗,無論是在電影裡和生活中,他們的形象都給人遐思無盡……對比太強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結婚、離婚手續比較簡單,恰巧當年的知青和傣家女子由於差別的巨大而更為相互吸引,因而大返城時知青的離異更加簡便一些。
最初的構思逐漸地在我心頭萌動、成熟。對我來說格外有利的是我有在西南山鄉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漫長經歷,潛心入神地研究過西南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變遷、差別和習俗;同時我畢竟出生在上海,在這個大都市裡生活了整整十九年,以後又常因出差、改稿、開會回歸故里,親眼見過上海近年來的變化。於是乎新的構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當把這些人物放在西雙版納和今天的大上海各個層次上展現時,多少藝術的亮點閃爍起來。
儘管我也正逢繁瑣不盡的調動和搬遷,儘管處於生活、工作、環境、人際關係的變動和新的適應,我還是按捺不住創作的激情,寫下了這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孽債》。
小說上半部分發表短短一兩個月時問,親戚朋友們都關心地詢問那幾個跑來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後來怎么樣了。在為賑災簽名售書的那天,人頭簇擁的讀者中冒出一張臉來,鄭重其事地詢問我書中一個孩子到底有沒有人收養?甚至一些同樣在搞創作的同行也問,那些孩子後來將怎樣生活?仿佛那些我構思的娃娃真存在似的。自然,讀者的好感也反映到影視部門,六七家影視單位前來找我商談改編拍攝事宜。最為令人稀奇的是1991年9月下旬的《新民晚報》上刊出了一篇真實的通訊報導《孩兒找媽淚花流》,寫的是一個北方少數民族的男孩子到上海尋找母親的真實事件。我的一位同學給我打來電話說:“真稀奇……”
稀奇不稀奇我說不上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讀者翻開這本書,將來這本書果真搬上螢屏,當蒙太奇閃現出花開四季、果結終年、江河常流的西雙版納和上海聳天的高樓及擁塞的馬路時,故事在這樣的兩種氛圍里展開,那會好看的。這不是我過於自信,而是我為這本書傾注了大量心血和度過了好些個不眠之夜。
謝謝。
葉辛 1991年底
可以說長篇小說《孽債》的最初構思,該是起源於那一段生活本身。
儘管是可以構思小說的素材,但是“無米之炊’’是無法做出來的。我也不可能想像這些孩子將來和他的生身父母之問該演出哪些方面的一連串悲喜劇。
好幾年過去了,知識青年這個字眼已經讓人感到陳舊和麻木。儘管北京、廣州、武漢、成都好多大城市裡的老知青們舉行過類似“青春無悔”、“追憶當年”等等活動,頑強地想表現這一代人的存在,但人們再不像當年那樣看待用血汗和眼淚浸染過的“知識青年,,這四個字。恰在這時,我在回上海探親時,聽說了附近弄堂里發生的這么件事:一個寧波農村的漢子帶了兩個孩子,到上海來找當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到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後,早已重新嫁了人,並有了新的孩子。於是乎一個女人兩個男人三個孩子的故事頓時成了弄堂新聞。有人說女人離開農村時根本沒辦妥正式離婚手續,哄騙男人回歸上海之後還將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說第二個男人根本不曉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說兩個男人打起架來了;有人說這個家庭熱鬧非凡有戲文可看……
我沒去窮盡這個故事的底細,隨手按習慣作了札記之後,心裡思忖,這倒是個寫作素材,但是僅僅照生活的本來面貌去寫是不成的。上海生活著一千幾百萬人,上海的包容性又實在太大,同樣一件事發生在內地的村莊裡、小城鎮上會有“滿城風雨”之感,但在上海這僅僅是一條弄堂新聞而已,人們一天到晚聽到的奇聞逸事太多太多了,別說一個小人物小家庭的戲文,中國的外國的上層的下層的稀奇古怪的事兒他們聽得耳朵都起繭子了,他們早就練出了見慣不驚的本事和修養。
這以後不久,我在一家刊物上讀到了一篇小說,名字記不清了,但內容幾乎同我所說的弄堂新聞相差無幾,我特意留神了小說的結尾,似乎作者也沒交代出這一家人究竟如何處理種種解不開理還亂的矛盾,小說的結尾只告訴讀者,這個家正鬧得不可開交……
又隔開了兩三年,我又聽說了這么件事:在西雙版納的一條街子上,有位北京來的旅遊者打扮的中年女子,始終在屋檐下徘徊,嘴裡喃喃自語著失悔一類的話語。原來這女子是當初來西雙版納的北京知青,回城時離了婚,遺下一個孩子給當地的農民丈夫撫養。她走得很輕鬆,回歸北京之後落實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間的事有時總陰差陽錯,二度婚姻之後,她再沒生育。隨著時間的流逝,她越來越思念遺留在西雙版納的和第一個丈夫生的兒子。終於她徵得現今丈夫的同意,趕到西雙版納的故土上來找兒子。誰知這裡的農民從來便有遷居的習俗,她照著原先記憶中的地址尋去,再沒找到她渴念的兒子。於是乎她便有些失態地踟躕在趕場的街子上,逢到人便詢問打聽,便講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頗為曲折的經歷……
聽來讓人悲傷。
吸引我的還不只是這個故事,而是這個故事提供的地域:西雙版納。喔,這是一塊多么美妙無比的土地!那裡的風情習俗和上海相比,簡直判若兩個世界。上海是海洋性氣候,西雙版納是旱濕兩季的山地氣候;上海眾多的人口和住房的擁擠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雙版納的家家戶戶都有一幢寬敞的庭院圍抱的乾欄式竹樓;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樓和狹窄的弄堂,而西雙版納滿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綠的水;上海號稱東方的大都市,是僅次於北京的政治、經濟、文化、外貿、金融的中心,而西雙版納系沙漠帶上的綠洲,是一塊沒有冬天的樂土,既被稱為“山國”里的平原,又被形容為孔雀之鄉、大象之國,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測的自然保護區和獨特珍貴的熱帶雨林;上海人被人議論成精明而不高明、聰明而不豁達,而西雙版納的傣族兄弟姐妹,謙和、熱情、纖柔、美麗,無論是在電影裡和生活中,他們的形象都給人遐思無盡……對比太強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結婚、離婚手續比較簡單,恰巧當年的知青和傣家女子由於差別的巨大而更為相互吸引,因而大返城時知青的離異更加簡便一些。
最初的構思逐漸地在我心頭萌動、成熟。對我來說格外有利的是我有在西南山鄉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漫長經歷,潛心入神地研究過西南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變遷、差別和習俗;同時我畢竟出生在上海,在這個大都市裡生活了整整十九年,以後又常因出差、改稿、開會回歸故里,親眼見過上海近年來的變化。於是乎新的構思形成了,新的人物呼之欲出,而當把這些人物放在西雙版納和今天的大上海各個層次上展現時,多少藝術的亮點閃爍起來。
儘管我也正逢繁瑣不盡的調動和搬遷,儘管處於生活、工作、環境、人際關係的變動和新的適應,我還是按捺不住創作的激情,寫下了這一部新的長篇小說《孽債》。
小說上半部分發表短短一兩個月時問,親戚朋友們都關心地詢問那幾個跑來上海找父母的娃娃的遭遇後來怎么樣了。在為賑災簽名售書的那天,人頭簇擁的讀者中冒出一張臉來,鄭重其事地詢問我書中一個孩子到底有沒有人收養?甚至一些同樣在搞創作的同行也問,那些孩子後來將怎樣生活?仿佛那些我構思的娃娃真存在似的。自然,讀者的好感也反映到影視部門,六七家影視單位前來找我商談改編拍攝事宜。最為令人稀奇的是1991年9月下旬的《新民晚報》上刊出了一篇真實的通訊報導《孩兒找媽淚花流》,寫的是一個北方少數民族的男孩子到上海尋找母親的真實事件。我的一位同學給我打來電話說:“真稀奇……”
稀奇不稀奇我說不上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讀者翻開這本書,將來這本書果真搬上螢屏,當蒙太奇閃現出花開四季、果結終年、江河常流的西雙版納和上海聳天的高樓及擁塞的馬路時,故事在這樣的兩種氛圍里展開,那會好看的。這不是我過於自信,而是我為這本書傾注了大量心血和度過了好些個不眠之夜。
謝謝。
葉辛 1991年底
序言
40多年前,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波瀾壯闊”四個字,不是我特意選用的形容詞,而是當年的習慣說法,廣播裡這么說,報紙的通欄大標題里這么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年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lO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lO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