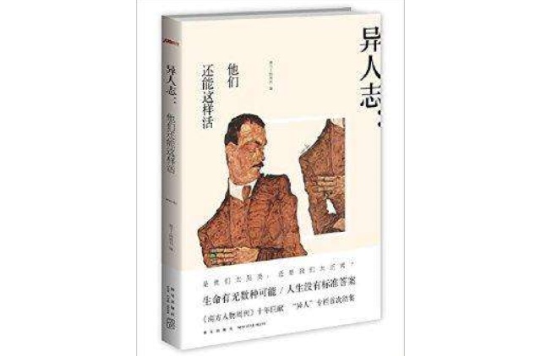《異人志:他們還能這樣活》內容簡介:雖然人類社會對於幸福和成功的定義迄今為止仍然單一乏味,但總有一些“異類”無懼世俗目光和壓力,勇於實踐獨特的生存法則。《南方人物周刊》的“異人”專欄記錄了這些真實的非典型生命體驗,提供了一份“活法兒大全”。《異人志:他們還能這樣活》從中精選了58種活法兒,展示了生存之上,生活的無數種可能。這裡有假冒乞丐的百萬富翁,有旅行全球舉行66場婚禮的恩愛夫妻,有住在停屍房裡的一家人。這些“異人”,都不符合流行的成功學標準,卻都快活得很,就算被質疑和嘲諷,也滿不在乎。在當今中國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中,每個人都在渴望成功,中國人的“累”超出了以往任何時代。“異人”則呈現了另一種可能——生活可以很好玩,生命可以很豐富,我們不必屈從主流,我們無須疲於奔命,依然能活得有滋有味。
基本介紹
- 書名:異人志:他們還能這樣活
-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 頁數:225頁
- 開本:16
- 品牌:新星出版社
-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
- 出版日期:2014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331538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生命有無數種可能,人生沒有標準答案。
是他們太另類,還是我們太正常?《南方人物周刊》十年巨獻, “異人”欄目首次結集
在一個常態的社會,每一個“異人”都是正常人;在一個變態的社會,每一個“正常人”都是異人
“異人”活得有滋有味,勝過一切富商巨賈、政要顯貴,牛逼閃閃周身放光芒。
是他們太另類,還是我們太正常?《南方人物周刊》十年巨獻, “異人”欄目首次結集
在一個常態的社會,每一個“異人”都是正常人;在一個變態的社會,每一個“正常人”都是異人
“異人”活得有滋有味,勝過一切富商巨賈、政要顯貴,牛逼閃閃周身放光芒。
作者簡介
《南方人物周刊》以“記錄我們的命運”為宗旨,以平等、寬容、人道為理念,時刻關注那些對中國的進步和我們的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人, 並從他們的故事中感悟時代的變遷和人性的複雜。多年來,《南方人物周刊》始終未改辦刊初衷,一如既往地打量那些和我們一樣的人,最大限度地撕掉神話和誤讀,抵達人性的真實。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我們不能說中國人不懂生活樂趣,不會挑戰庸常人生。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人的遊戲精神不強,尋找樂趣的本能很弱。往深里說,在一個長期奉行團隊精神、迄今仍在大力提倡中庸之道的社會環境裡,要想培養出萬水千山我獨行的人格氣質,實在很難。
——萬靜波 《南方人物周刊》常務副主編
年歲漸長,漸漸明白活得步入窠臼有多難。成長於我,就是不斷喪失可能性的過程。二十出頭的年紀,可以今天決定要改吧職業方向,明天就坐上開往陌生城市的飛機。而如今的自己,再做出任何決定,難免瞻前顧後,殘存的勇氣和衝動,早已拗不過患得患失的那點算計。再逢這種時候,看看這些“異人”,竟也會被不自覺地鼓動起勇氣。我經常在想:生活把他們怎么了?他們為何以這般邏輯面對人生?而這些,隨後都變成了我自己對抗庸常的秘密武器與抵擋痛苦的糖衣藥丸。如今的我還能抱有一兩分“混不吝”的自由放縱氣息,不能不說與見識過這些千奇百怪的人生有關。
——馬李靈珊 《GQ》記者
——萬靜波 《南方人物周刊》常務副主編
年歲漸長,漸漸明白活得步入窠臼有多難。成長於我,就是不斷喪失可能性的過程。二十出頭的年紀,可以今天決定要改吧職業方向,明天就坐上開往陌生城市的飛機。而如今的自己,再做出任何決定,難免瞻前顧後,殘存的勇氣和衝動,早已拗不過患得患失的那點算計。再逢這種時候,看看這些“異人”,竟也會被不自覺地鼓動起勇氣。我經常在想:生活把他們怎么了?他們為何以這般邏輯面對人生?而這些,隨後都變成了我自己對抗庸常的秘密武器與抵擋痛苦的糖衣藥丸。如今的我還能抱有一兩分“混不吝”的自由放縱氣息,不能不說與見識過這些千奇百怪的人生有關。
——馬李靈珊 《GQ》記者
名人推薦
我們不能說中國人不懂生活樂趣,不會挑戰庸常人生。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人的遊戲精神不強,尋找樂趣的本能很弱。往深里說,在一個長期奉行團隊精神、迄今仍在大力提倡中庸之道的社會環境裡,要想培養出萬水千山我獨行的人格氣質,實在很難。 ——萬靜波 《南方人物周刊》常務副主編
年歲漸長,漸漸明白活得步入窠臼有多難。成長於我,就是不斷喪失可能性的過程。二十出頭的年紀,可以今天決定要改吧職業方向,明天就坐上開往陌生城市的飛機。而如今的自己,再做出任何決定,難免瞻前顧後,殘存的勇氣和衝動,早已拗不過患得患失的那點算計。再逢這種時候,看看這些“異人”,竟也會被不自覺地鼓動起勇氣。我經常在想:生活把他們怎么了?他們為何以這般邏輯面對人生?而這些,隨後都變成了我自己對抗庸常的秘密武器與抵擋痛苦的糖衣藥丸。如今的我還能抱有一兩分“混不吝”的自由放縱氣息,不能不說與見識過這些千奇百怪的人生有關。 ——馬李靈珊 《GQ》中文版記者
年歲漸長,漸漸明白活得步入窠臼有多難。成長於我,就是不斷喪失可能性的過程。二十出頭的年紀,可以今天決定要改吧職業方向,明天就坐上開往陌生城市的飛機。而如今的自己,再做出任何決定,難免瞻前顧後,殘存的勇氣和衝動,早已拗不過患得患失的那點算計。再逢這種時候,看看這些“異人”,竟也會被不自覺地鼓動起勇氣。我經常在想:生活把他們怎么了?他們為何以這般邏輯面對人生?而這些,隨後都變成了我自己對抗庸常的秘密武器與抵擋痛苦的糖衣藥丸。如今的我還能抱有一兩分“混不吝”的自由放縱氣息,不能不說與見識過這些千奇百怪的人生有關。 ——馬李靈珊 《GQ》中文版記者
圖書目錄
總序有靈魂、有溫度的人生/萬靜波
序:對抗庸常/馬李靈珊
輯一行者
用40英里的時速征服世界/3
伊朗第一女“騎士”/6
騎腳踏車橫穿美國/9
做自己的自由/13
描摹宇宙/17
一隻沙發游天下/20
66場異國婚禮/24
02隱士
與山野比鄰而居/31
建造年近百歲的“報紙屋”/35
打造優雅的“蝸居”生活/39
像“魯濱孫”一樣活著/43
不做房奴,做霍比特人/47
另一個世界的聖徒/50
住在停屍房裡的夫妻/54
輯二帝王
壽司之神/59
選自己做教皇/63
一個人的餐廳/67
數字王國國王/71
車輪上的教堂/75
一個人的天氣預報站/78
小鎮“國王”/81
秘書搖身變女王/85
輯三鬥士
獨臂鋼琴家/91
無肢游越五大洲/94
成為冰人/97
活到死,學到死/101
印度愚公/104
“冰鎬手”登山家/107
永遠的贏家/110
燈光不曾熄滅/113
輯四兩生
搖滾物理學家/119
超級英雄清潔隊/122
夢遊畫家/125
揭秘核子彈的卡車司機/128
我老公變成了我老婆/132
白天銀行家,晚上“夜行俠”/135
乞討17年的富翁演員/139
用500英鎊擊敗NASA/142
輯五奇士
90歲的賣報人/149
96歲的應召女郎/152
英國“圍觀帝”/155
瘋子攝影家/159
我和另一個我/162
樓頂的風景和恐懼/166
傑夫,一個寂寞的男人/170
輯六布衣
看看我們丟掉了什麼/175
最好的爸爸/178
你好,企鵝先生/182
維多利亞的秘密/185
清潔工的每日金句/189
遠離中國的冒險/192
輯七新富
17歲的千萬富翁/197
YouTube上的化妝女王/201
惡搞短片造就的富翁/205
昆蟲經紀人/209
用大數據尋找真愛/212
花出去的錢還會回來?/216
一無所有的億萬富翁/219
序:對抗庸常/馬李靈珊
輯一行者
用40英里的時速征服世界/3
伊朗第一女“騎士”/6
騎腳踏車橫穿美國/9
做自己的自由/13
描摹宇宙/17
一隻沙發游天下/20
66場異國婚禮/24
02隱士
與山野比鄰而居/31
建造年近百歲的“報紙屋”/35
打造優雅的“蝸居”生活/39
像“魯濱孫”一樣活著/43
不做房奴,做霍比特人/47
另一個世界的聖徒/50
住在停屍房裡的夫妻/54
輯二帝王
壽司之神/59
選自己做教皇/63
一個人的餐廳/67
數字王國國王/71
車輪上的教堂/75
一個人的天氣預報站/78
小鎮“國王”/81
秘書搖身變女王/85
輯三鬥士
獨臂鋼琴家/91
無肢游越五大洲/94
成為冰人/97
活到死,學到死/101
印度愚公/104
“冰鎬手”登山家/107
永遠的贏家/110
燈光不曾熄滅/113
輯四兩生
搖滾物理學家/119
超級英雄清潔隊/122
夢遊畫家/125
揭秘核子彈的卡車司機/128
我老公變成了我老婆/132
白天銀行家,晚上“夜行俠”/135
乞討17年的富翁演員/139
用500英鎊擊敗NASA/142
輯五奇士
90歲的賣報人/149
96歲的應召女郎/152
英國“圍觀帝”/155
瘋子攝影家/159
我和另一個我/162
樓頂的風景和恐懼/166
傑夫,一個寂寞的男人/170
輯六布衣
看看我們丟掉了什麼/175
最好的爸爸/178
你好,企鵝先生/182
維多利亞的秘密/185
清潔工的每日金句/189
遠離中國的冒險/192
輯七新富
17歲的千萬富翁/197
YouTube上的化妝女王/201
惡搞短片造就的富翁/205
昆蟲經紀人/209
用大數據尋找真愛/212
花出去的錢還會回來?/216
一無所有的億萬富翁/219
後記
代跋:異的大小乘
楊波
完全地物化個人,是社會對人的管理一直企圖達到的理想境界。按法家慎到的說法,在這一境界裡,人人皆“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當一切事物和行為都建立了精確的度量和標準後,個人只需將其全部生活交付給模具即可。個人不必考慮任何問題,也失去了昕有建立自我的根據.或許沒什麼情趣和快樂,卻也一定沒有悔怒及憂傷。這是比老子“聖人之治……常使人無知無欲”更極端的社會學,不僅邏輯暢明,且行之有效。我們此時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不管東方西方,不管什麼制度,其實都是這種社會學程度不同的返照。
人與人本生來不同,卻如前所說,正因為社會矢志於要將昕有人都錘塑成同一個人,乃至同一塊石頭,才有了異人這一說法。之所以這種人人“棄知去己”的社會遲退沒有純粹地實現,一是緣於每個人的際遇不同,這令人們在處世和接徹上難以保持完備的一致;二是因為每個人的潛意識裡就有股要與眾不同的抗爭力,一種與自私同胚一胎的自我意識,這意識儘管遭到社會管理者的反覆碾斬,卻沒有齊根泯滅,一有機會就報復股地張揚起來。這么說來,每個人都有成為一個異人的本錢。
異人,即異於平常大眾的個別人。我姑且將之分為真偽兩種。真異人通過自己異於平常大眾的行為或思想對後者的價值體系做出挑釁、妨礙乃至顛覆。偽異人則僅止於異於平常大眾,甚至是為了討好、完善、裝飾這個社會一一譬如絕大多數的金氏世界紀錄創造者。此外,每個馬戲團都有許多扮演小丑的侏儒,若將馬戲團喻為社會,這些小丑就是偽異人。
通過金氏世界紀錄獲得者和侏儒小丑,社會獲得了獵奇和休閒的享樂,他們的異常之處也不會造成任何蠱惑與策動;同樣,因看到一個人用陰莖拉動了一輛載重卡車於是也想這么做的人亦屬於偽異人。因為真異人不僅能滿足你的獵奇心,還會讓你心亂如麻、夜不成寐。老子、釋迦牟尼、伽利略、盧梭、達爾文、馬克思……他們用其異常撬動的是社會為萬事萬物業已制定完畢的量度和定義,令其牽一髮而動全身地亂了套。他們不滿足於一己之異,而要將之變為傳染病。當然,這傳染病即便蔓延到將舊世界翻了個個兒,也只不過是為社會建立了一套新的標準而已,是從月一個角度,以月一股力氣,換另一種口氣,將每一個個體“棄知去己”罷了。
據說,林肯患有抑鬱症,貝多芬患有躁鬱症,米開朗琪羅患有自閉症,達爾文患有幽閉恐懼症,牛頓則患有多種精神疾病……不僅這些名人都是精神病,我們每個人也都是。這精神病就是我們從那些真異人處獲取傳染病毒的基因。
這既不值得慶幸,也不值得惋惜。有個童話講一名反人類者向井水裡下了致傻藥,村人喝了後都變成了傻子,然後皆認為下藥者才是唯一的傻子。他們要燒死還是驅逐傻子不記得了,總之,該反人類者為了活下去只好自斟自飲了一杯。致傻藥不止一種,不同的異入向同一口井及同一批人下不同的藥,這就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在一個人類體系中,某人乍現的異常毋寧說是社會整體從這種異常邁向那種異常的苗頭。你很難想像過去中國的多數父母會將女兒的雙腳弄殘,還有人在乳頭上鮮血淋淋地別毛主席像章,將他們放在今天就是貨真價實的異人,但正當時不僅是正常的,且是值得學習的。
所以,異不異並沒有一個合乎一切歷史階段的標準,只是我們都想努力與自己所處時代的大多數人保持一致。因此,書中提到的英國最老的賣報人、9O歲的查理·雷諾茲之所以被當做異人,倒不是因為他可以將這份工作堅持到很老,而是他所堅守的傳統在今天已經過時甚至被淘汰,因而顯得異常。在網路媒體快要顛覆整個傳統媒體的當下,賣報人當然不合時宜。
人類自古就將自利獻給了眾利,將個人自由連根拔除,扔進了社會契約的燴菜里。為了群居,個人除了一條命,什麼都交出去了。於是,徹底的異,或者說最為人所樂道的異就是離群索居,或曰隱居。隱居者自古有名的很多,在中國有陳仲和陶淵明,在外國則有瓦爾登湖畔的梭羅一一本書也舉了大衛·伯吉斯的例子。
我曾寫過一篇比較中西方搖滾樂史的文章,慶幸中國搖滾這20多年來不僅沒有一個非正常死亡的例子,竟連個失蹤者都找不到。一名不服氣的瀆者反駁說,鄭鈞最早的吉他手在北方某個冬天只穿一件襯衫推門而出,至今杳無音訊(此事筆者未考證)。這位吉他手當然是異人,且也不好稱之為偽異人,按佛教大小乘的分法,可將之歸於“異己不異眾”的小乘一派。即,若陳仲僅是去做吃土喝黃泉的蚯蚓,而沒寫下那本向眾人解釋他為何這么做的《於陵子》;若梭羅窮其一生僅去研究怎樣才能令橡果得以下咽且不便秘,而沒寫過《瓦爾登湖》和《論公民的不服從義務》,他們也不過是異的小乘。
被迫離群的魯濱孫當然不是異人,他是人類文明無法再合格的標誌物。陶淵明之流解甲歸日式的隱居,其田園美學正源自社會的訓誡和誘逼。我們雖不能因此說陳仲和梭羅就沒有受到過社會的訓誡和逼迫,但他們的隱居是為了避開人,而不是基於人,他們對文明的態度是反對,而不是反應。松尾芭蕉有首俳句:“吾之風雅,乃似夏爐冬扇。”瞧,跟陶淵明一樣,逆眾和特立竟成了一種風雅和顯擺。
不管怎么說,異總歸是一種能夠讓個人意志從群體的大熔爐里探出頭來喘口氣的辦法,即便它看上去是一種風雅和顯擺,其本人的生活至少會因此變得足夠精彩。例如阿德里安·格雷,造化令他罹患了一種奇怪的過敏症,電、電視、筆記本甚至手機都會讓他頭疼噁心,不犯病的唯一辦法是遠離現代生活和主流社會,這讓他因禍得福地去探索大自然本身的美一一他能不用任何黏合劑只靠尋找石頭本身的重心而將石頭壘疊起來,從而完成自己獨特的藝術創造。如今,他的過敏症已痊癒,他卻不願再回到人群中去。一個真正的異人由此誕生。
楊波
完全地物化個人,是社會對人的管理一直企圖達到的理想境界。按法家慎到的說法,在這一境界裡,人人皆“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當一切事物和行為都建立了精確的度量和標準後,個人只需將其全部生活交付給模具即可。個人不必考慮任何問題,也失去了昕有建立自我的根據.或許沒什麼情趣和快樂,卻也一定沒有悔怒及憂傷。這是比老子“聖人之治……常使人無知無欲”更極端的社會學,不僅邏輯暢明,且行之有效。我們此時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不管東方西方,不管什麼制度,其實都是這種社會學程度不同的返照。
人與人本生來不同,卻如前所說,正因為社會矢志於要將昕有人都錘塑成同一個人,乃至同一塊石頭,才有了異人這一說法。之所以這種人人“棄知去己”的社會遲退沒有純粹地實現,一是緣於每個人的際遇不同,這令人們在處世和接徹上難以保持完備的一致;二是因為每個人的潛意識裡就有股要與眾不同的抗爭力,一種與自私同胚一胎的自我意識,這意識儘管遭到社會管理者的反覆碾斬,卻沒有齊根泯滅,一有機會就報復股地張揚起來。這么說來,每個人都有成為一個異人的本錢。
異人,即異於平常大眾的個別人。我姑且將之分為真偽兩種。真異人通過自己異於平常大眾的行為或思想對後者的價值體系做出挑釁、妨礙乃至顛覆。偽異人則僅止於異於平常大眾,甚至是為了討好、完善、裝飾這個社會一一譬如絕大多數的金氏世界紀錄創造者。此外,每個馬戲團都有許多扮演小丑的侏儒,若將馬戲團喻為社會,這些小丑就是偽異人。
通過金氏世界紀錄獲得者和侏儒小丑,社會獲得了獵奇和休閒的享樂,他們的異常之處也不會造成任何蠱惑與策動;同樣,因看到一個人用陰莖拉動了一輛載重卡車於是也想這么做的人亦屬於偽異人。因為真異人不僅能滿足你的獵奇心,還會讓你心亂如麻、夜不成寐。老子、釋迦牟尼、伽利略、盧梭、達爾文、馬克思……他們用其異常撬動的是社會為萬事萬物業已制定完畢的量度和定義,令其牽一髮而動全身地亂了套。他們不滿足於一己之異,而要將之變為傳染病。當然,這傳染病即便蔓延到將舊世界翻了個個兒,也只不過是為社會建立了一套新的標準而已,是從月一個角度,以月一股力氣,換另一種口氣,將每一個個體“棄知去己”罷了。
據說,林肯患有抑鬱症,貝多芬患有躁鬱症,米開朗琪羅患有自閉症,達爾文患有幽閉恐懼症,牛頓則患有多種精神疾病……不僅這些名人都是精神病,我們每個人也都是。這精神病就是我們從那些真異人處獲取傳染病毒的基因。
這既不值得慶幸,也不值得惋惜。有個童話講一名反人類者向井水裡下了致傻藥,村人喝了後都變成了傻子,然後皆認為下藥者才是唯一的傻子。他們要燒死還是驅逐傻子不記得了,總之,該反人類者為了活下去只好自斟自飲了一杯。致傻藥不止一種,不同的異入向同一口井及同一批人下不同的藥,這就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在一個人類體系中,某人乍現的異常毋寧說是社會整體從這種異常邁向那種異常的苗頭。你很難想像過去中國的多數父母會將女兒的雙腳弄殘,還有人在乳頭上鮮血淋淋地別毛主席像章,將他們放在今天就是貨真價實的異人,但正當時不僅是正常的,且是值得學習的。
所以,異不異並沒有一個合乎一切歷史階段的標準,只是我們都想努力與自己所處時代的大多數人保持一致。因此,書中提到的英國最老的賣報人、9O歲的查理·雷諾茲之所以被當做異人,倒不是因為他可以將這份工作堅持到很老,而是他所堅守的傳統在今天已經過時甚至被淘汰,因而顯得異常。在網路媒體快要顛覆整個傳統媒體的當下,賣報人當然不合時宜。
人類自古就將自利獻給了眾利,將個人自由連根拔除,扔進了社會契約的燴菜里。為了群居,個人除了一條命,什麼都交出去了。於是,徹底的異,或者說最為人所樂道的異就是離群索居,或曰隱居。隱居者自古有名的很多,在中國有陳仲和陶淵明,在外國則有瓦爾登湖畔的梭羅一一本書也舉了大衛·伯吉斯的例子。
我曾寫過一篇比較中西方搖滾樂史的文章,慶幸中國搖滾這20多年來不僅沒有一個非正常死亡的例子,竟連個失蹤者都找不到。一名不服氣的瀆者反駁說,鄭鈞最早的吉他手在北方某個冬天只穿一件襯衫推門而出,至今杳無音訊(此事筆者未考證)。這位吉他手當然是異人,且也不好稱之為偽異人,按佛教大小乘的分法,可將之歸於“異己不異眾”的小乘一派。即,若陳仲僅是去做吃土喝黃泉的蚯蚓,而沒寫下那本向眾人解釋他為何這么做的《於陵子》;若梭羅窮其一生僅去研究怎樣才能令橡果得以下咽且不便秘,而沒寫過《瓦爾登湖》和《論公民的不服從義務》,他們也不過是異的小乘。
被迫離群的魯濱孫當然不是異人,他是人類文明無法再合格的標誌物。陶淵明之流解甲歸日式的隱居,其田園美學正源自社會的訓誡和誘逼。我們雖不能因此說陳仲和梭羅就沒有受到過社會的訓誡和逼迫,但他們的隱居是為了避開人,而不是基於人,他們對文明的態度是反對,而不是反應。松尾芭蕉有首俳句:“吾之風雅,乃似夏爐冬扇。”瞧,跟陶淵明一樣,逆眾和特立竟成了一種風雅和顯擺。
不管怎么說,異總歸是一種能夠讓個人意志從群體的大熔爐里探出頭來喘口氣的辦法,即便它看上去是一種風雅和顯擺,其本人的生活至少會因此變得足夠精彩。例如阿德里安·格雷,造化令他罹患了一種奇怪的過敏症,電、電視、筆記本甚至手機都會讓他頭疼噁心,不犯病的唯一辦法是遠離現代生活和主流社會,這讓他因禍得福地去探索大自然本身的美一一他能不用任何黏合劑只靠尋找石頭本身的重心而將石頭壘疊起來,從而完成自己獨特的藝術創造。如今,他的過敏症已痊癒,他卻不願再回到人群中去。一個真正的異人由此誕生。
序言
總序 有靈魂、有溫度的人生
萬靜波_《南方人物周刊》常務副主編
《南方人物周刊》三個知名專欄"逝者"、"異人"與"夢中情人"要出精選集,藉此機會,我想說幾句相關的話。
先說"逝者"。
這應該算是《南方人物周刊》最知名的欄目吧,年頭最長,投稿者也最多。最早的雛形版叫"懷念",那時還未創刊,雜誌主編、創始人徐列就談到要辦一個紀念亡者的欄目,而且放在最後一頁,取其"有始有終"之意,沒想到這一辦就是整整十年。
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宗教傳統,又深受儒家思想"未知生、焉知死"觀念浸潤的國家裡,如何面對死亡、正視死亡,殊非容易。
早些年,我曾有機會背著行囊在美國大地壯遊。飛機火車大巴,一路穿州過府,最愛看的地方有三類:教堂、大學和墓地。大學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頭腦,教堂決定了國民的精神氣質,墓地則直接體現出對生命的態度。中國文字中有所謂"墓門已拱"、"墓草春深",形容墓地之荒涼寂寥,這樣的場景在美國大致是看不見的。美國的墓地,沒有高大的墓碑,不講八寶山式的級別,也沒什麼規格,就是一片面積大致相當、高高低低或豎或躺的石條,不壯觀,有的也許就是比腳踝高几寸,勉強說起來,也可以叫墓碑吧。石頭除了寫上死者名字、生卒年月外,一般還會有一兩句話:"Tom和Mary的愛子"、"我永遠愛你"、"這裡躺著一個追求自由的靈魂"、"他曾為國效力"等,以寄託生者的哀思與懷念。
這是在基督教薰陶下美國人平等觀念的最直白體現:不管你生前是貴是賤,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區別和差異,只在墓碑上的那幾句評價,那是價值觀和私人情感的凝練呈現。這種差異,就叫文化。《紐約時報》著名版面"訃聞",由受過新聞職業訓練的記者,查訪資料,採訪死者親友,以克制之筆,簡練描述亡者一生。好的訃聞,甚至有傳誦萬口的動人力量。
《南方人物周刊》設立"逝者"欄目,其用心也在於此。我們希望來稿不要總是"為尊者諱",也別總是"歌德派",不管是一生得意的帝王將相,還是平凡至極的販夫走卒,不管生前有沒享受過尊嚴和自由(在中國,這是多么奢侈的待遇啊),至少在這個小小欄目里,版面的大小、字數的多少,是完全平等的。我們也不想文章總是寫"恩情難忘",更希望看到逝去的這個人過了怎樣的一生,開心還是倒霉,怎樣得到快樂,又怎樣面對厄運。總之,希望看到一個有靈魂、有溫度、真實地活過一場的獨特人生。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不管怎樣,作為歷時最久的欄目,投稿者可謂最為穩定,普通人居多,也有名家,文章質量也保持著一貫的水準,算是初步實現了目的。
再說"異人"。
某種程度上,這個欄目的設定,是受到老外刺激的結果。
"異人"迄今已向讀者介紹了數百個精彩紛呈、敢想敢為的異國人物:徒手攀爬世界超高建築的"蜘蛛俠",懷揣未遂的從軍夢想、把坐騎改造成軍用坦克的軍事愛好者,用火柴頭拼搭泰姬陵的創意手工者--這些活得汪洋恣肆、我行我素、讓人羨慕的傢伙,其實都是些普通外國人。
這當然不是說大多數普通中國人就不懂生活樂趣,不會挑戰庸常人生。不過,對比滿大街隨著《最炫民族風》起舞的廣場大媽、只會"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停車拍照"的跟團遊客、畢業不久便背上沉重房貸省吃儉用咬牙還月供的年輕人,那些有趣有料、有獨立人格意志的中國人之少,確實是令人難堪的現實。中國人的遊戲精神不強,尋找樂趣的本能很弱,往深里說,在一個長期奉行團隊精神、迄今仍在提倡中庸之道的社會環境裡,要想培養出獨立人格和萬水千山我獨行的獨特氣質,難啊!
四十多年前,安東尼奧尼等極少數外國人被允許來到中國旅行訪問,他後來評論中國說,"這是一個藍色螞蟻的海洋"。意謂中國人億人一面,全穿藍色工作服。四十年後,藍色工作服是脫掉了,在服裝色彩和樣式上已和國際接軌,但我們心裡的藍色中山裝,那五個紐扣還牢牢扣著。
希望以後會有中國異人、越來越多的中國異人,走進這個欄目。
最後是"夢中情人"。
這個欄目是編輯部年輕人的自由創造,隨著這個欄目的誕生,我很高興地見證了年輕一代記者編輯的成長。
在我的成長年代裡,哪裡會有"夢中情人"一說。美人哪個年代都有,王心剛、陳思思、李秀明、張瑜,算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男女偶像吧(如果那時有偶像這個詞的話),但性感和性,卻想都不敢想。1979年出品的電影《甜蜜的事業》里,李秀明有一段著名的戲--愛慕她的男主人公和她追跑,春情萌動。這場戲被處理成一組略帶誇張的慢鏡頭,因其中的曖昧情愛色彩,還激起了熱烈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切與身體、欲望有關的情愛想像,都不能公開言說,也許連"夢中"都不能存在吧。
從這個角度說,"夢中情人"能成為一個被正大光明公開敘述的脫敏詞語,確實彰顯出時代的進步。在80後甚至90後作者筆下,他們的"夢中情人"對我來說有些是那么陌生(幾乎未曾聽聞的電視劇和演員),有些是那么不可思議(有個女作者的夢中情人居然是一部日本漫畫的男配角)。對此,我和我的60後、70後同事,總是報以輕鬆一笑。我們這一代在石頭縫裡和鹽鹼地上踉蹌至今的媒體人,樂見其成。
落筆的此刻,《南方人物周刊》正籌備慶祝它的十歲生日。創刊那會兒,我兒子還沒出生,現在,他已是足球場上的追風少年。這是天翻地覆大時代下的十年,中國的十年,也是讀者和周刊同人的十年。有時忍不住會想,在這樣一個春風沉醉和暴風驟雨混雜的時代之夜,還有沒有人願意讀書,還有沒有人在讀到微妙處時,會陷入沉思,或展顏一笑?且不去管它吧。勞動者自會從揮汗耕作中得到樂趣,那些心有靈犀的讀者,也自會感覺到一絲溫暖與默契。
2014年6月3日深夜
萬靜波_《南方人物周刊》常務副主編
《南方人物周刊》三個知名專欄"逝者"、"異人"與"夢中情人"要出精選集,藉此機會,我想說幾句相關的話。
先說"逝者"。
這應該算是《南方人物周刊》最知名的欄目吧,年頭最長,投稿者也最多。最早的雛形版叫"懷念",那時還未創刊,雜誌主編、創始人徐列就談到要辦一個紀念亡者的欄目,而且放在最後一頁,取其"有始有終"之意,沒想到這一辦就是整整十年。
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宗教傳統,又深受儒家思想"未知生、焉知死"觀念浸潤的國家裡,如何面對死亡、正視死亡,殊非容易。
早些年,我曾有機會背著行囊在美國大地壯遊。飛機火車大巴,一路穿州過府,最愛看的地方有三類:教堂、大學和墓地。大學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頭腦,教堂決定了國民的精神氣質,墓地則直接體現出對生命的態度。中國文字中有所謂"墓門已拱"、"墓草春深",形容墓地之荒涼寂寥,這樣的場景在美國大致是看不見的。美國的墓地,沒有高大的墓碑,不講八寶山式的級別,也沒什麼規格,就是一片面積大致相當、高高低低或豎或躺的石條,不壯觀,有的也許就是比腳踝高几寸,勉強說起來,也可以叫墓碑吧。石頭除了寫上死者名字、生卒年月外,一般還會有一兩句話:"Tom和Mary的愛子"、"我永遠愛你"、"這裡躺著一個追求自由的靈魂"、"他曾為國效力"等,以寄託生者的哀思與懷念。
這是在基督教薰陶下美國人平等觀念的最直白體現:不管你生前是貴是賤,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區別和差異,只在墓碑上的那幾句評價,那是價值觀和私人情感的凝練呈現。這種差異,就叫文化。《紐約時報》著名版面"訃聞",由受過新聞職業訓練的記者,查訪資料,採訪死者親友,以克制之筆,簡練描述亡者一生。好的訃聞,甚至有傳誦萬口的動人力量。
《南方人物周刊》設立"逝者"欄目,其用心也在於此。我們希望來稿不要總是"為尊者諱",也別總是"歌德派",不管是一生得意的帝王將相,還是平凡至極的販夫走卒,不管生前有沒享受過尊嚴和自由(在中國,這是多么奢侈的待遇啊),至少在這個小小欄目里,版面的大小、字數的多少,是完全平等的。我們也不想文章總是寫"恩情難忘",更希望看到逝去的這個人過了怎樣的一生,開心還是倒霉,怎樣得到快樂,又怎樣面對厄運。總之,希望看到一個有靈魂、有溫度、真實地活過一場的獨特人生。
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不管怎樣,作為歷時最久的欄目,投稿者可謂最為穩定,普通人居多,也有名家,文章質量也保持著一貫的水準,算是初步實現了目的。
再說"異人"。
某種程度上,這個欄目的設定,是受到老外刺激的結果。
"異人"迄今已向讀者介紹了數百個精彩紛呈、敢想敢為的異國人物:徒手攀爬世界超高建築的"蜘蛛俠",懷揣未遂的從軍夢想、把坐騎改造成軍用坦克的軍事愛好者,用火柴頭拼搭泰姬陵的創意手工者--這些活得汪洋恣肆、我行我素、讓人羨慕的傢伙,其實都是些普通外國人。
這當然不是說大多數普通中國人就不懂生活樂趣,不會挑戰庸常人生。不過,對比滿大街隨著《最炫民族風》起舞的廣場大媽、只會"上車睡覺、下車撒尿、停車拍照"的跟團遊客、畢業不久便背上沉重房貸省吃儉用咬牙還月供的年輕人,那些有趣有料、有獨立人格意志的中國人之少,確實是令人難堪的現實。中國人的遊戲精神不強,尋找樂趣的本能很弱,往深里說,在一個長期奉行團隊精神、迄今仍在提倡中庸之道的社會環境裡,要想培養出獨立人格和萬水千山我獨行的獨特氣質,難啊!
四十多年前,安東尼奧尼等極少數外國人被允許來到中國旅行訪問,他後來評論中國說,"這是一個藍色螞蟻的海洋"。意謂中國人億人一面,全穿藍色工作服。四十年後,藍色工作服是脫掉了,在服裝色彩和樣式上已和國際接軌,但我們心裡的藍色中山裝,那五個紐扣還牢牢扣著。
希望以後會有中國異人、越來越多的中國異人,走進這個欄目。
最後是"夢中情人"。
這個欄目是編輯部年輕人的自由創造,隨著這個欄目的誕生,我很高興地見證了年輕一代記者編輯的成長。
在我的成長年代裡,哪裡會有"夢中情人"一說。美人哪個年代都有,王心剛、陳思思、李秀明、張瑜,算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早期的男女偶像吧(如果那時有偶像這個詞的話),但性感和性,卻想都不敢想。1979年出品的電影《甜蜜的事業》里,李秀明有一段著名的戲--愛慕她的男主人公和她追跑,春情萌動。這場戲被處理成一組略帶誇張的慢鏡頭,因其中的曖昧情愛色彩,還激起了熱烈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切與身體、欲望有關的情愛想像,都不能公開言說,也許連"夢中"都不能存在吧。
從這個角度說,"夢中情人"能成為一個被正大光明公開敘述的脫敏詞語,確實彰顯出時代的進步。在80後甚至90後作者筆下,他們的"夢中情人"對我來說有些是那么陌生(幾乎未曾聽聞的電視劇和演員),有些是那么不可思議(有個女作者的夢中情人居然是一部日本漫畫的男配角)。對此,我和我的60後、70後同事,總是報以輕鬆一笑。我們這一代在石頭縫裡和鹽鹼地上踉蹌至今的媒體人,樂見其成。
落筆的此刻,《南方人物周刊》正籌備慶祝它的十歲生日。創刊那會兒,我兒子還沒出生,現在,他已是足球場上的追風少年。這是天翻地覆大時代下的十年,中國的十年,也是讀者和周刊同人的十年。有時忍不住會想,在這樣一個春風沉醉和暴風驟雨混雜的時代之夜,還有沒有人願意讀書,還有沒有人在讀到微妙處時,會陷入沉思,或展顏一笑?且不去管它吧。勞動者自會從揮汗耕作中得到樂趣,那些心有靈犀的讀者,也自會感覺到一絲溫暖與默契。
2014年6月3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