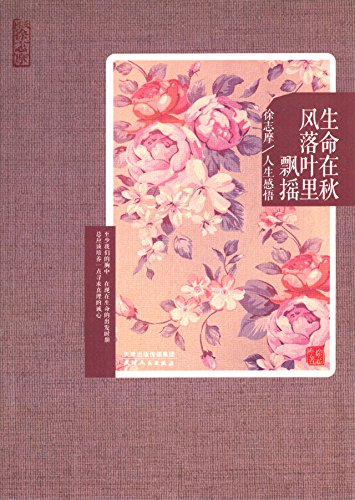《生命在秋風落葉里飄搖(徐志摩人生感悟)》收選了徐志摩最經典的散文31篇。有人說,散文可以比較直接而真切地反映一個作家的人生感受與思想歷程。這句話對於徐志摩而言,更是恰如其分。徐志摩的散文讀來好似與最親密的朋友對話,這份隨性和灑脫,使人在閱讀中得到最大的被尊重和被信任的幸福感。可以說,徐志摩的散文,成就了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下面,我們就一起來閱讀他經典的作品集《生命在秋風落葉里飄搖(徐志摩人生感悟)》吧!
基本介紹
- 書名:生命在秋風落葉里飄搖
-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 頁數:153頁
- 開本:16
- 品牌:天津人民出版社
- 作者:徐志摩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201080334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生命在秋風落葉里飄搖(徐志摩人生感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落葉
給郭子雄題詞
想飛
秋
海灘上種花
一個詩人
《超善與惡》節譯
海詠
“這是風颳的”
明星與夜蛾
阿嚶
吹胰子泡
我的祖母之死
我的彼得
悼沈叔薇
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
吊劉叔和
傷雙栝老人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話匣子(二)
——一大群騾,一隻貓:趙元任先生
《梁啓超來函》附志
《閒話》引出來的閒話
再添幾句閒話的閒話乘便妄想解圍
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自剖
我過的端陽節
山中來函
我們病了怎么辦
吸菸與文化
法郎士先生的牙慧
落葉
給郭子雄題詞
想飛
秋
海灘上種花
一個詩人
《超善與惡》節譯
海詠
“這是風颳的”
明星與夜蛾
阿嚶
吹胰子泡
我的祖母之死
我的彼得
悼沈叔薇
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
吊劉叔和
傷雙栝老人
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話匣子(二)
——一大群騾,一隻貓:趙元任先生
《梁啓超來函》附志
《閒話》引出來的閒話
再添幾句閒話的閒話乘便妄想解圍
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自剖
我過的端陽節
山中來函
我們病了怎么辦
吸菸與文化
法郎士先生的牙慧
序言
懷著理想雲遊
(代序)
你相信命運嗎?生活中,我們會遭遇許多帶著宿命色彩的事情,常常讓我們心中生出無限的迷惘。回望八十年前,看看徐志摩,我們也同樣看到了好些奇異的巧合——有人總是說,那就是命定。
1931年夏,楊振聲去北平,一次與徐志摩閒聊,說到北平與上海之間的旅行,楊振聲說坐火車更好,徐志摩卻說乘飛機更快。因楊振聲在青島供職,徐志摩開玩笑說:“飛機過濟南,我在天空望你們。等著,看我向你們招手吧!”
同年11月上旬,徐志摩見許地山時,許地山問他回上海後,什麼時候再回北平,他悠然地開玩笑說:“那倒說不上,也許永不再回了。”
11月10日晚,徐志摩去拜訪林徽音未遇,留下紙條說:“定明早六時起飛,此去存亡不卜……”驚了林徽音一跳,趕緊聯繫他,他卻笑著說沒事,“很穩當的,我還要留著生命看更偉大的事跡呢”。
而正是在11月19日,徐志摩所乘飛機在濟南上空失事。一代詩魂,自此永遠消失在茫茫長空。
徐志摩喜歡雪萊的詩,甚至曾經很羨慕雪萊的歸宿,以致他自己也說出了像讖語一般的話來。陸小曼《遺文編就答君心》一文中說:“他平生最崇拜英國的雪萊,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羨慕他覆舟的死況。他說:‘我希望我將來能得到他那樣剎那的解脫,讓後世人談起就寄與無限的同情與悲憫。”’而他最終竟然真的就在天上得到“剎那的解脫”。他去了哪兒?他仙逝的那年,還寫了《雲遊》詩,詩中的“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際雲遊”,“你的愉快是無攔阻的逍遙”,或可看作類似《莊子·逍遙遊》中萬物合一、回歸自然的心境的抒發吧。就好像他知道自己終將“雲遊”天際一般,他提前寫下了這樣的“讖詩”。
對此,林徽音有悲慟的慨嘆:
“我們中間沒有絕對信命運之說的,但是對著這不測的人生,誰不感到驚異,對著那許多事實的痕跡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盡有定數?世事儘是偶然?對這永遠的疑問我們什麼時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然而,徐志摩大約沒想過有沒有宿命的人生。他素來懷著對未來生活的向望,對人生的美好期望,對人對己,都是盡力從積極的方向去思考人生的意義。即使面對死,他也會說,“我們不能輕易的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
他對人談思想,談追求,曾是一派朝氣蓬勃的樣兒。“天時與人生都少不了相替的陰晴與寒燠”,“我們應得尋求幸福,我們卻不應躲避苦惱,只有這裡面我們有機會證明人的靈魂的高貴與偉大”。即使沒有能力解決人生問題。也要弄清楚阻攔我們的障礙究竟是什麼。他說的這樣一段話,多么具有高度:“我們先得要立志不做時代和時光的奴隸,我們要做我們思想和生命的主人,這暫的沉悶決不能壓倒我們的理想,我們正應得感謝這深刻的沉悶,因為在這裡,我們才感悟著一些自度的訊息。”
他把理想比作在海邊沙灘上種花,它需要人的精誠、毅力,即使如同一個小傻瓜,“花也許會消滅,但這種花的精神是不爛的”。
然而,理想是一回事,現實又是一回事。人生道路上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困境。即使像“《閒話》引出來的閒話”那樣的無謂事件,也足以讓人心煩意亂,感嘆人心不古。一些文人間的意氣之爭,不涉“為正誼為公道奮鬥”,讓卷在其中的人——尤其夾在中間的徐志摩嘗到了兩頭受氣的滋味。
那人事的糾葛,還只是一時的不快。事情還不至於大到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而山河的黑暗,社會的動盪,人世的慘澹,則更容易讓人感到人生的沉悶和壓抑。世道紛紜,在那樣一個時代,會形成一種普遍的生也苦、死也痛的迷茫觀念。
徐志摩曾一再“自剖”,找尋自己心境變得鬱悶的原因。國家大勢,當然影響個人的心緒。除此以外,對徐志摩來說,還有一點很令他不安:他發現原來自己曾有一種虛幻的希望,“自以為確有相當創作的天賦以及獨立思想的能力”。及至發現自己思想枯竭、創作無功、事業無成,頓時生出了一種強烈的幻滅感。好在他對自己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做一個輕鬆的、平和的人,過著自己平凡的生活,不要用那些大而無當的高遠虛幻的想法壓迫得自己喘不過氣來。這,也就算是他對人生道路的一次深刻的自省與調整吧。
人生,總是喜怒哀樂並存,有甜蜜就必有痛苦,有快樂就必有悲傷。生命的盡頭是死亡,許多自己親近的、敬重的人逝去了,也會讓人在不盡的哀思中,生出無窮的感悟。死亡固然可怕,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活著何嘗不是受罪,死亡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徐志摩說:“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兇險,比大漠更荒涼”;“我不定覺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人生亦不見得一路有陽光的照亮”。徐志摩對於他人之死,是這樣的態度;而我們對於他本人之死,也同樣可以用逍遙於濁世之外來看待。就像林徽音說的,“死本來也不過是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過的,不免過分地懷疑,死不定就比這生苦”。
生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生命旅途是否有一種崇高的理想追求,思想是否獲得了自由和解放。
還是再傾聽一下徐志摩心靈中的呼聲吧:“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著夠多厭煩,不說別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還是再重溫一下徐志摩關於理想的感悟吧:“至少我們的胸中,在現在生命的出發時期,總應該培養一點尋求真理的誠心,點起一盞尋真求理的明燈,不至於在生命的道上只是暗中摸索,不至於盲目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什麼發見都沒有。”
他對於人生的思索,已長留在了人間;他自身的人生軌跡,也長留在了世人的心間。
(代序)
你相信命運嗎?生活中,我們會遭遇許多帶著宿命色彩的事情,常常讓我們心中生出無限的迷惘。回望八十年前,看看徐志摩,我們也同樣看到了好些奇異的巧合——有人總是說,那就是命定。
1931年夏,楊振聲去北平,一次與徐志摩閒聊,說到北平與上海之間的旅行,楊振聲說坐火車更好,徐志摩卻說乘飛機更快。因楊振聲在青島供職,徐志摩開玩笑說:“飛機過濟南,我在天空望你們。等著,看我向你們招手吧!”
同年11月上旬,徐志摩見許地山時,許地山問他回上海後,什麼時候再回北平,他悠然地開玩笑說:“那倒說不上,也許永不再回了。”
11月10日晚,徐志摩去拜訪林徽音未遇,留下紙條說:“定明早六時起飛,此去存亡不卜……”驚了林徽音一跳,趕緊聯繫他,他卻笑著說沒事,“很穩當的,我還要留著生命看更偉大的事跡呢”。
而正是在11月19日,徐志摩所乘飛機在濟南上空失事。一代詩魂,自此永遠消失在茫茫長空。
徐志摩喜歡雪萊的詩,甚至曾經很羨慕雪萊的歸宿,以致他自己也說出了像讖語一般的話來。陸小曼《遺文編就答君心》一文中說:“他平生最崇拜英國的雪萊,尤其奇怪的是他一天到晚羨慕他覆舟的死況。他說:‘我希望我將來能得到他那樣剎那的解脫,讓後世人談起就寄與無限的同情與悲憫。”’而他最終竟然真的就在天上得到“剎那的解脫”。他去了哪兒?他仙逝的那年,還寫了《雲遊》詩,詩中的“那天你翩翩地在空際雲遊”,“你的愉快是無攔阻的逍遙”,或可看作類似《莊子·逍遙遊》中萬物合一、回歸自然的心境的抒發吧。就好像他知道自己終將“雲遊”天際一般,他提前寫下了這樣的“讖詩”。
對此,林徽音有悲慟的慨嘆:
“我們中間沒有絕對信命運之說的,但是對著這不測的人生,誰不感到驚異,對著那許多事實的痕跡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盡有定數?世事儘是偶然?對這永遠的疑問我們什麼時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然而,徐志摩大約沒想過有沒有宿命的人生。他素來懷著對未來生活的向望,對人生的美好期望,對人對己,都是盡力從積極的方向去思考人生的意義。即使面對死,他也會說,“我們不能輕易的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
他對人談思想,談追求,曾是一派朝氣蓬勃的樣兒。“天時與人生都少不了相替的陰晴與寒燠”,“我們應得尋求幸福,我們卻不應躲避苦惱,只有這裡面我們有機會證明人的靈魂的高貴與偉大”。即使沒有能力解決人生問題。也要弄清楚阻攔我們的障礙究竟是什麼。他說的這樣一段話,多么具有高度:“我們先得要立志不做時代和時光的奴隸,我們要做我們思想和生命的主人,這暫的沉悶決不能壓倒我們的理想,我們正應得感謝這深刻的沉悶,因為在這裡,我們才感悟著一些自度的訊息。”
他把理想比作在海邊沙灘上種花,它需要人的精誠、毅力,即使如同一個小傻瓜,“花也許會消滅,但這種花的精神是不爛的”。
然而,理想是一回事,現實又是一回事。人生道路上總難免有這樣那樣的困境。即使像“《閒話》引出來的閒話”那樣的無謂事件,也足以讓人心煩意亂,感嘆人心不古。一些文人間的意氣之爭,不涉“為正誼為公道奮鬥”,讓卷在其中的人——尤其夾在中間的徐志摩嘗到了兩頭受氣的滋味。
那人事的糾葛,還只是一時的不快。事情還不至於大到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而山河的黑暗,社會的動盪,人世的慘澹,則更容易讓人感到人生的沉悶和壓抑。世道紛紜,在那樣一個時代,會形成一種普遍的生也苦、死也痛的迷茫觀念。
徐志摩曾一再“自剖”,找尋自己心境變得鬱悶的原因。國家大勢,當然影響個人的心緒。除此以外,對徐志摩來說,還有一點很令他不安:他發現原來自己曾有一種虛幻的希望,“自以為確有相當創作的天賦以及獨立思想的能力”。及至發現自己思想枯竭、創作無功、事業無成,頓時生出了一種強烈的幻滅感。好在他對自己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做一個輕鬆的、平和的人,過著自己平凡的生活,不要用那些大而無當的高遠虛幻的想法壓迫得自己喘不過氣來。這,也就算是他對人生道路的一次深刻的自省與調整吧。
人生,總是喜怒哀樂並存,有甜蜜就必有痛苦,有快樂就必有悲傷。生命的盡頭是死亡,許多自己親近的、敬重的人逝去了,也會讓人在不盡的哀思中,生出無窮的感悟。死亡固然可怕,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活著何嘗不是受罪,死亡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徐志摩說:“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兇險,比大漠更荒涼”;“我不定覺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人生亦不見得一路有陽光的照亮”。徐志摩對於他人之死,是這樣的態度;而我們對於他本人之死,也同樣可以用逍遙於濁世之外來看待。就像林徽音說的,“死本來也不過是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過的,不免過分地懷疑,死不定就比這生苦”。
生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生命旅途是否有一種崇高的理想追求,思想是否獲得了自由和解放。
還是再傾聽一下徐志摩心靈中的呼聲吧:“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著夠多厭煩,不說別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還是再重溫一下徐志摩關於理想的感悟吧:“至少我們的胸中,在現在生命的出發時期,總應該培養一點尋求真理的誠心,點起一盞尋真求理的明燈,不至於在生命的道上只是暗中摸索,不至於盲目的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什麼發見都沒有。”
他對於人生的思索,已長留在了人間;他自身的人生軌跡,也長留在了世人的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