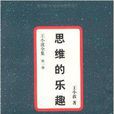《思維的樂趣》主要講述了:對於以思維為樂趣的人而言,王小波無疑是他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使越來越多的讀者體驗到了他那獨特、有趣而思辯的文字。
基本介紹
- 書名:王小波全集01:思維的樂趣
- 出版社: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
- 頁數:266頁
- 開本:32
- 品牌:鳳凰壹力
- 作者:王小波
- 出版日期:2009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29007454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1952年5月13日出生於北京
1968-1970年,雲南兵團農場職工
1971-1972年,在山東牟平插隊,後做民辦教師
1972-1973年,北京牛街教學儀器廠工人
1974-1978年,北京西城區半導體廠工人
1978-1982年,中國人民大學貿易經濟系學生
1982-1984在,中國人民大學——分校教師
1984-1988年,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88-1991年,北京大學社會學所講師
1991—1992年,中國人民大學會計系講師
1992-1997年,自由撰稿人
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逝世
媒體推薦
——周國平
圖書目錄
沉默的大多數
思維的樂趣
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古遺風
知識分子的不幸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
積極的結論
跳出手掌心
道德墮落與知識分子
論戰與道德
道德保守主義及其他
我看文化熱
文化之爭
“行貨感”與文化相對主義
極端體驗
洋鬼子與辜鴻銘
我看國學
智慧與國學
理想國與哲人王
救世情結與白日夢
百姓·洋人·官
警惕狹隘民族主義的蠱惑宣傳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人性的逆轉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有關天圓地方
優越感種種
東西方快樂觀區別之我見
肚子裡的戰爭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椰子樹與平等
思想和害臊
體驗生活
皇帝做習題
拒絕恭維
關於崇高
謙卑學習班
荷蘭牧場與父老鄉親
京片子與民族自信心
高考經歷
盛裝舞步
有關“錯誤的故事”
迷信與邪門書
科學與邪道
科學的美好
生命科學與騙術
我怎樣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對待知識的態度
有與無
虛偽與毫不利己
誠實與浮囂
不新的《萬曆十五年》
《代價論》、烏托邦與聖賢
海明威的《老人與海》
掩卷:《魚王》讀後
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
王朔的作品
《私人生活》與女性文學
從《赤彤丹朱》想到的
文摘
一
君特·格拉斯在《鐵皮鼓》里,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裡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歷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蕭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裡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里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里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裡吐痰。順便說一句,前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蕭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鬍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鬍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蕭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麼樣,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像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裡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腳踏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志,“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里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胎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面就說這么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面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大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蕭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麼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薰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面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里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台小鼓風機,嗡嗡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只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里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俱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飢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飢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國小時,在課桌後面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面有橡皮頭。我從後面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桿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麼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於把整支鉛筆吃得只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飢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
這個世界上有個很大的誤會,那就是以為人的種種想法都是由話語教出來的。假設如此,話語就是思維的樣板。我說它是個誤會,是因為世界還有陰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樣的話語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從我懂事的年齡起,就常聽人們說:我們這一代,生於一個神聖的時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負著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等等。同年齡的人聽了都很振奮,很愛聽,但我總有點疑問,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趕上了。除此之外,我以為這種說法不夠含蓄。而含蓄是我們的家教。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天開飯時,每人碗裡有一小片臘肉。我弟弟見了以後,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衝上陽台,朝全世界放聲高呼:我們家吃大魚大肉了!結果是被我爸爸拖回來臭揍了一頓。經過這樣的教育,我一直比較深沉。所以聽到別人說我們多么幸福,多么神聖,別人在受苦,我們沒有受,等等,心裡老在想著:假如我們真遇上了這么多美事,不把它說出來會不會更好。當然,這不是說,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於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這么想的:與其大呼小叫說要去解放他們,讓人家苦等,倒不如一聲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們解放,給他們一個意外驚喜。總而言之,我總是從實際的方面去考慮,而且考慮得很周到。幼年的經歷、家教和天性謹慎,是我變得沉默的起因。
二
在我小時候,話語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雞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說吧,人來到世間,仿佛是來游泳的,遲早要跳進去。我可沒有想到自己會保持沉默直到四十歲,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繼續生活的勇氣。不管怎么說吧,我聽到的話也不總是那么瘋,是一陣瘋,一陣不瘋。所以在十四歲之前,我並沒有終身沉默的決心。
小的時候,我們只有聽人說話的份兒。當我的同齡人開始說話時,給我一種極惡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寫了一本書,寫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書名為《血統》。可以想見,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給她的書寫個序。這件事使我想起來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見所聞。“文革”開始時,我十四歲,正上國中一年級。有一天,忽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學忽然變成了紅五類,另一部分則成了黑五類。我自己的情況特殊,還說不清是哪一類。當然,這紅和黑的說法並不是我們發明出來的,這個變化也不是由我們發起的。在這方面我們毫無責任。只是我們中間的一些人,該負一點欺負同學的責任。
照我看來,紅的同學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這是值得祝賀的。黑的同學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對他們——表示祝賀和同情,一些紅的同學就把腦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帶,站在校門口,問每一個想進來的人:你什麼出身?他們對同班同學問得格外仔細,一聽到他們報出不好的出身,就從牙縫裡迸出三個字:“狗崽子!”當然,我能理解他們突然變成了紅五類的狂喜,但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學在大庭廣眾下變成狗崽子,未免也太過分。當年我就這么想,現在我也這么想: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恆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