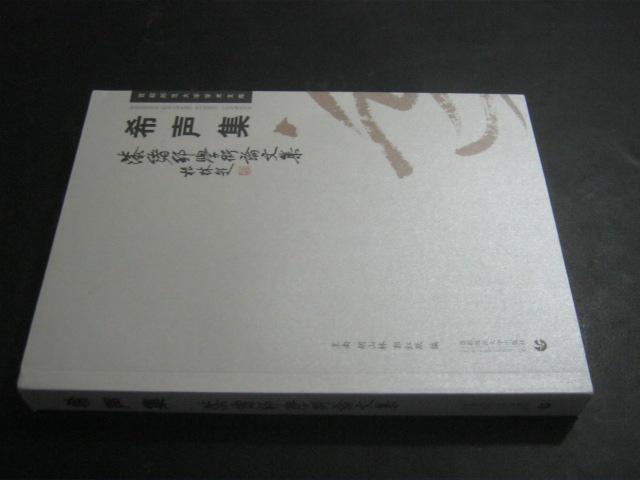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漆緒邦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重慶江津李市 鄉
- 出生日期:1938年
- 逝世日期:2008年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北京師範學院(首都師範大學前身)
- 主要成就: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 中國文學批評史教學研究工作
- 代表作品:《道家思想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盛唐邊塞詩》
時隔八年,懷念漆緒邦先生。
引自天涯論壇,樓主劉得水
按照慣例,教師節前,給過去教過我的老師打電話問候。可是2008年這次卻得到一個不幸的訊息——漆緒邦先生去世了。我的心裡一沉——一位多么好的老師,怎么說走就走了呢?
據說,他是暑期到北戴河旅遊,在當年曹操東臨碣石的地方游泳而遭遇不幸的。“他太自信,畢竟七十歲的人了!” 相熟的老師告訴我。
是的,漆先生從來就“自信”——自信者,相信自己也。他從來都是只相信自己的。只是沒有想到,最後的人生結局也就在此。命也夫!命也夫!
漆先生是我的大學老師。那時候,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名教授不多。記憶里似乎只有廖仲安先生、王景山先生(還有一位李燕傑先生,也可算是“名教授”,只不過輩分晚,且“名”不同),這是老一輩的。而漆先生他們(還有鮑霽、王世徵、王凱符先生等)六十年代初畢業的這一輩,不過剛到中年,學術地位尚未完全確立。我們這些學生,乳臭未乾卻不知天高地厚,頗有點自大且勢利,選課很挑剔。記得選課前,我曾向高年級的學生打探哪位老師的課值得一選,他們推薦的人中,就有漆先生。那是大二,他教我們古代文論,是兩個年級合上的大課。八十多人,擠在一間不大的教室里,聽先生講課。頭一節,他就告訴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指望從上課這裡得到什麼。然後開講。那課講的不是很吸引人,或者說不花哨,可是卻讓人感覺很實在。他從不照本宣科,也沒有講義,只是拿著一張紙,在前面一邊講一邊寫板書。口音是地道的四川話,嗓音沙啞,低沉,聽起來抑揚頓挫,對我是很有魅力的。最吸引我的,是他有自己的觀點,他喜歡道家的理論,認為莊子對人性深處的關注來得更深刻,遠勝於儒家的“興觀群怨”。他上課,著重對“文學是人學”的理論的闡發——那時候,階級論猶自甚囂塵上,反“自由化思潮”轟轟烈烈,我們耳朵都聽膩了,他卻在課上大講人學,對我們是有相當的吸引力的。講到魏晉南北朝,他稱那是中國古代百家爭鳴之後又一個人性覺醒的時代。他講曹操,講曹丕的《典論·論文》,至今我仿佛還能聽到他用四川話朗誦“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低沉沙啞的卻有力的話音。長長的黑板前,他高高的個子,光亮的禿頭頂,腰板挺直,甚至覺得有些向後仰,只是背微微有些駝,像一個點兒加在上面的“?”。精闢的見解,從那沙啞的話語裡汩汩流出……
他的課,持續了一年。中間考試,他只要我們寫一篇作業,題目自擬。我沒有忘記他“讀書”的告誡,把郭紹虞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南北朝前的部分通讀了一遍,認真地做了筆記,寫了一篇讀書心得。題目忘記了,觀點也是從人性的角度分析文學意識的覺醒。其實,不過是把他講課的觀點,用自己讀書得來的資料重新整理一遍。交上去之後,就放假了。開學第一節課,他叫課代表把作業發下來。高年級的學生很重視成績,尤其重視漆先生給的成績。他們告訴我,兩個年級,只有三個同學得了“優”,那神情是很羨慕的樣子。我趕緊看我的作業——第一頁的右上角,是一個紅筆寫的“優”。我一下子有些激動起來。八十多人,先生還是很看重我的呢!
此後,我不敢妄自菲薄了——可以在同學面前伸伸腳了。每次上課,都早早地去占座,挺直腰板,坐在前排。課間,也敢放開,湊上前和先生請教了。
可惜這門課只上了一年,只講到明代,再也不能在課堂上聆聽先生的精闢見解了。只是常常看到他腋下夾著書本,出入於圖書館的身影。
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沒想到大三的時候,學院搞改革,一批年輕學者擔當領導職務。據說是教員公推,漆先生當了我們的系主任。他沒有架子,與我們學生關係很融洽,無話不談。那時候我當班長,我們的接觸便又多了起來。記得還到他家裡去過。是一個晚上,他的住所是個兩居室,正趕上停電,我們坐在他滿是線裝古籍的書房裡聊天。我驚訝他的古書那么多,他笑了笑,說是先人留下來的。他向我了解學生對教師的反映。我說有些教師學問不是特別好,但是人品好,對學生很關心,對課也負責,大家還是很喜歡上的,並且可以經由自己的努力彌補。他聽了,回過頭,不無感慨地對師母說:“都說他們是孩子,其實我們的學生還是很懂事的!”他還諄諄地告誡我:到了大三,該好好地念點兒書了,四年時間一晃就過去,並勸我把班長職務辭掉,說乾那些瑣務,沒有太大價值。此外,有些課,像充滿政治性的一些課程,能考過就算了,沒必要下太多工夫。“我當年古代漢語可是補考才通過的啊!”——他甚至不惜揭了自己的老底。“那時候,一到複習考試,我就夾著一本線裝書,到紫竹院念去了,一去就是半天兒!本以為我古書都念的勁兒勁兒的,考試應該沒問題,可是沒想到居然考那些之乎者也是什麼詞性,這我可說不出來啦!結果呢,弄得個補考!”
聽了這些話,我的心裡充滿了感激——這是掏心窩子的話,是一個老師對學生說的話,是一個朋友對朋友說的話,哪裡是一個系主任說的話啊!
還說起那篇作業。其實已經過了很長時間了,原以為他已經忘了,可是沒想到先生居然還記得。他說我是真讀書了,就沖這個給我一個“優”。有些同學東抄西抄,連“黃初”這個年號,還講成“黃帝之初”呢!說著,連連搖頭,不勝惋惜的樣子。
他還以身為教,告訴我正在通讀《全唐文》,得到了不少有用資料。從此,在我的心裡,就把先生當作了一個模板,深深地印記下來。那滿屋的書籍,昏黃的燈光之下,兀自孜孜矻矻讀書不輟,成了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有時我想,一名教師,他課堂上教給學生什麼,似乎並不重要——至今,先生課堂上講的,我大多已經忘記了,重要的是他給學生的影響。這影響,更多的是他自己在做什麼,怎么做。
就是他當系主任那年,我破天荒地獲得過一次“三好學生”的獎勵。破天荒,是因為以前評三好生,總要政治上積極進步,各學科成績都要達到多少分。可我們這些“不務正業”者,政治上落後(那時是很鄙夷那些整天圍在政治輔導員身邊的人的),有些課要像先生一樣經過“補考”才通過,自然就與這榮譽無緣了。可是一旦到論文比賽,就沒有那些人的份兒,完全成了我們的天下。我的得以榮膺此號,是憑著論文比賽的獎狀的。後來聽說,這是漆先生力排眾議做出的決策。
那一年,師院曾經發生過一場風波。我們中文系的幾個同學與美術系的學生在食堂發生口角,不料美術系同學大打出手,把我們的同學打的鼻青臉腫。本來,學生口角以至動手,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美術系以打人者“剛剛在全國大展上獲獎”為由而不做處理的做法,引起了我們的不滿。意見反映上去,而美術系、院裡都不動聲色,一下子激怒了學生,由此而爆發了請願、罷課的所謂“中美大戰”。幾百名學生到行政大樓找院長理論,把樓道圍得水泄不通。這可忙壞了政治輔導員,勸說、要挾,最終只把幾名積極要求入黨的學生勸了回去。那天,我夾在人群里,鄙夷地看著那些同學離去。心裡罵道:“叛徒!”(如今想來,也頗覺可笑)可是一會兒,我再回頭的時候,看到了一個高高的身影——漆先生,就默默地站在我們的隊伍後邊。我不知別的學生怎樣,我的心裡是感到熱呼呼的!我踅到他身邊,悄聲問:“您怎么也來了?”他只輕輕說了一句:“我的學生挨打了!”
……
後來,聽說他還做了學院的副院長。我總想像不出,他,漆先生,一介學究,喜歡念書的人,怎么能出入那個場合!就像秀才披鎧甲舞大刀,總覺有些不協調。把這意思和一些老師說,老師也都笑,說曾看見過他夾著書,從會場上大搖大擺地公然離開。忘了是聽他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轉述的,是一句振聾發聵的話:“我怕什麼?大不了回去教課!”
漆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頓時高大起來!
大四實習的時候,他還作為領導,到實習學校來看過我們,讓我們著實感受了一回長者的關懷。記得我們還一起照了相,只是搬了幾次家,那照片不知放到哪裡了。
九五年暑假,我回母校讀研究生班,課餘,與三五同學在校園重溫昔日勝景,遠遠地又看到漆先生的身影,還是腋下夾著書,一件白色的短袖衫,禿禿的頭頂,邁著大步,從圖書館裡走出。可是忘了為什麼,也許是學無所成的愧疚感作祟吧,並沒有上前打招呼。如今想來,那是與先生見的最後一面了。
剩下的都是耳聞的訊息。那一年春夏之交,他是否還在院長任上已不得而知,說是有兩個學生(一個研究生,一個本科生)倒在血泊之中。人死了,但是名聲卻很不好聽。一些老師到醫院去認領屍體,其中就有漆先生。別人是只在病房外站一站,他卻獨自進去看望。出來的時候,抑制不住內心的激憤,高聲喊著:“法西斯!法西斯!”
自然,秋後要算賬的。審查的時候,據說他只是沉默,一言不發。有人問:“為什麼要花180元買骨灰盒?”(近二十年前,180元是個不小的數目)其意若曰:死的是暴徒,還要花那么多錢,究竟什麼意思?
這明顯是要整先生。漆先生毫不理會,只冷冷地扔去一句:“就剩這一個了!”
聽到這一節,我對漆先生由衷地肅然起敬!我仿佛又聽到了那低沉、沙啞聲音——
“我的學生挨打了!”……
由此,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更加高大起來!我為自己有這樣的老師感到驕傲!我為自己曾是漆先生的學生感到自豪!
現在,我在借書滿架的書齋里,昏黃的燈下,寫著這篇文章,先生卻已經不知在哪裡了。翻點舊篋,還有他的書:《道家思想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那是二十年前在首體旁的一間小書店裡買的;還有他主編的兩大冊《中國散文通史》,是研究生課程的教材;此外就只剩一張照片,那是他和我們“三好生”一起在師院主樓前的合影。黑白的照片,業已泛黃,顯示著歲月的滄桑。照片上,我們二十幾名學生,緊緊圍在他的身邊。我,就站在他的身旁……
僅以此文紀念敬愛的漆先生!哀哉,尚饗!
2008年9月5日晚,三餘書屋北窗之下,揮淚寫。
據說,他是暑期到北戴河旅遊,在當年曹操東臨碣石的地方游泳而遭遇不幸的。“他太自信,畢竟七十歲的人了!” 相熟的老師告訴我。
是的,漆先生從來就“自信”——自信者,相信自己也。他從來都是只相信自己的。只是沒有想到,最後的人生結局也就在此。命也夫!命也夫!
漆先生是我的大學老師。那時候,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名教授不多。記憶里似乎只有廖仲安先生、王景山先生(還有一位李燕傑先生,也可算是“名教授”,只不過輩分晚,且“名”不同),這是老一輩的。而漆先生他們(還有鮑霽、王世徵、王凱符先生等)六十年代初畢業的這一輩,不過剛到中年,學術地位尚未完全確立。我們這些學生,乳臭未乾卻不知天高地厚,頗有點自大且勢利,選課很挑剔。記得選課前,我曾向高年級的學生打探哪位老師的課值得一選,他們推薦的人中,就有漆先生。那是大二,他教我們古代文論,是兩個年級合上的大課。八十多人,擠在一間不大的教室里,聽先生講課。頭一節,他就告訴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指望從上課這裡得到什麼。然後開講。那課講的不是很吸引人,或者說不花哨,可是卻讓人感覺很實在。他從不照本宣科,也沒有講義,只是拿著一張紙,在前面一邊講一邊寫板書。口音是地道的四川話,嗓音沙啞,低沉,聽起來抑揚頓挫,對我是很有魅力的。最吸引我的,是他有自己的觀點,他喜歡道家的理論,認為莊子對人性深處的關注來得更深刻,遠勝於儒家的“興觀群怨”。他上課,著重對“文學是人學”的理論的闡發——那時候,階級論猶自甚囂塵上,反“自由化思潮”轟轟烈烈,我們耳朵都聽膩了,他卻在課上大講人學,對我們是有相當的吸引力的。講到魏晉南北朝,他稱那是中國古代百家爭鳴之後又一個人性覺醒的時代。他講曹操,講曹丕的《典論·論文》,至今我仿佛還能聽到他用四川話朗誦“東臨碣石,以觀滄海……”的低沉沙啞的卻有力的話音。長長的黑板前,他高高的個子,光亮的禿頭頂,腰板挺直,甚至覺得有些向後仰,只是背微微有些駝,像一個點兒加在上面的“?”。精闢的見解,從那沙啞的話語裡汩汩流出……
他的課,持續了一年。中間考試,他只要我們寫一篇作業,題目自擬。我沒有忘記他“讀書”的告誡,把郭紹虞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文論選》南北朝前的部分通讀了一遍,認真地做了筆記,寫了一篇讀書心得。題目忘記了,觀點也是從人性的角度分析文學意識的覺醒。其實,不過是把他講課的觀點,用自己讀書得來的資料重新整理一遍。交上去之後,就放假了。開學第一節課,他叫課代表把作業發下來。高年級的學生很重視成績,尤其重視漆先生給的成績。他們告訴我,兩個年級,只有三個同學得了“優”,那神情是很羨慕的樣子。我趕緊看我的作業——第一頁的右上角,是一個紅筆寫的“優”。我一下子有些激動起來。八十多人,先生還是很看重我的呢!
此後,我不敢妄自菲薄了——可以在同學面前伸伸腳了。每次上課,都早早地去占座,挺直腰板,坐在前排。課間,也敢放開,湊上前和先生請教了。
可惜這門課只上了一年,只講到明代,再也不能在課堂上聆聽先生的精闢見解了。只是常常看到他腋下夾著書本,出入於圖書館的身影。
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沒想到大三的時候,學院搞改革,一批年輕學者擔當領導職務。據說是教員公推,漆先生當了我們的系主任。他沒有架子,與我們學生關係很融洽,無話不談。那時候我當班長,我們的接觸便又多了起來。記得還到他家裡去過。是一個晚上,他的住所是個兩居室,正趕上停電,我們坐在他滿是線裝古籍的書房裡聊天。我驚訝他的古書那么多,他笑了笑,說是先人留下來的。他向我了解學生對教師的反映。我說有些教師學問不是特別好,但是人品好,對學生很關心,對課也負責,大家還是很喜歡上的,並且可以經由自己的努力彌補。他聽了,回過頭,不無感慨地對師母說:“都說他們是孩子,其實我們的學生還是很懂事的!”他還諄諄地告誡我:到了大三,該好好地念點兒書了,四年時間一晃就過去,並勸我把班長職務辭掉,說乾那些瑣務,沒有太大價值。此外,有些課,像充滿政治性的一些課程,能考過就算了,沒必要下太多工夫。“我當年古代漢語可是補考才通過的啊!”——他甚至不惜揭了自己的老底。“那時候,一到複習考試,我就夾著一本線裝書,到紫竹院念去了,一去就是半天兒!本以為我古書都念的勁兒勁兒的,考試應該沒問題,可是沒想到居然考那些之乎者也是什麼詞性,這我可說不出來啦!結果呢,弄得個補考!”
聽了這些話,我的心裡充滿了感激——這是掏心窩子的話,是一個老師對學生說的話,是一個朋友對朋友說的話,哪裡是一個系主任說的話啊!
還說起那篇作業。其實已經過了很長時間了,原以為他已經忘了,可是沒想到先生居然還記得。他說我是真讀書了,就沖這個給我一個“優”。有些同學東抄西抄,連“黃初”這個年號,還講成“黃帝之初”呢!說著,連連搖頭,不勝惋惜的樣子。
他還以身為教,告訴我正在通讀《全唐文》,得到了不少有用資料。從此,在我的心裡,就把先生當作了一個模板,深深地印記下來。那滿屋的書籍,昏黃的燈光之下,兀自孜孜矻矻讀書不輟,成了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
有時我想,一名教師,他課堂上教給學生什麼,似乎並不重要——至今,先生課堂上講的,我大多已經忘記了,重要的是他給學生的影響。這影響,更多的是他自己在做什麼,怎么做。
就是他當系主任那年,我破天荒地獲得過一次“三好學生”的獎勵。破天荒,是因為以前評三好生,總要政治上積極進步,各學科成績都要達到多少分。可我們這些“不務正業”者,政治上落後(那時是很鄙夷那些整天圍在政治輔導員身邊的人的),有些課要像先生一樣經過“補考”才通過,自然就與這榮譽無緣了。可是一旦到論文比賽,就沒有那些人的份兒,完全成了我們的天下。我的得以榮膺此號,是憑著論文比賽的獎狀的。後來聽說,這是漆先生力排眾議做出的決策。
那一年,師院曾經發生過一場風波。我們中文系的幾個同學與美術系的學生在食堂發生口角,不料美術系同學大打出手,把我們的同學打的鼻青臉腫。本來,學生口角以至動手,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美術系以打人者“剛剛在全國大展上獲獎”為由而不做處理的做法,引起了我們的不滿。意見反映上去,而美術系、院裡都不動聲色,一下子激怒了學生,由此而爆發了請願、罷課的所謂“中美大戰”。幾百名學生到行政大樓找院長理論,把樓道圍得水泄不通。這可忙壞了政治輔導員,勸說、要挾,最終只把幾名積極要求入黨的學生勸了回去。那天,我夾在人群里,鄙夷地看著那些同學離去。心裡罵道:“叛徒!”(如今想來,也頗覺可笑)可是一會兒,我再回頭的時候,看到了一個高高的身影——漆先生,就默默地站在我們的隊伍後邊。我不知別的學生怎樣,我的心裡是感到熱呼呼的!我踅到他身邊,悄聲問:“您怎么也來了?”他只輕輕說了一句:“我的學生挨打了!”
……
後來,聽說他還做了學院的副院長。我總想像不出,他,漆先生,一介學究,喜歡念書的人,怎么能出入那個場合!就像秀才披鎧甲舞大刀,總覺有些不協調。把這意思和一些老師說,老師也都笑,說曾看見過他夾著書,從會場上大搖大擺地公然離開。忘了是聽他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轉述的,是一句振聾發聵的話:“我怕什麼?大不了回去教課!”
漆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頓時高大起來!
大四實習的時候,他還作為領導,到實習學校來看過我們,讓我們著實感受了一回長者的關懷。記得我們還一起照了相,只是搬了幾次家,那照片不知放到哪裡了。
九五年暑假,我回母校讀研究生班,課餘,與三五同學在校園重溫昔日勝景,遠遠地又看到漆先生的身影,還是腋下夾著書,一件白色的短袖衫,禿禿的頭頂,邁著大步,從圖書館裡走出。可是忘了為什麼,也許是學無所成的愧疚感作祟吧,並沒有上前打招呼。如今想來,那是與先生見的最後一面了。
剩下的都是耳聞的訊息。那一年春夏之交,他是否還在院長任上已不得而知,說是有兩個學生(一個研究生,一個本科生)倒在血泊之中。人死了,但是名聲卻很不好聽。一些老師到醫院去認領屍體,其中就有漆先生。別人是只在病房外站一站,他卻獨自進去看望。出來的時候,抑制不住內心的激憤,高聲喊著:“法西斯!法西斯!”
自然,秋後要算賬的。審查的時候,據說他只是沉默,一言不發。有人問:“為什麼要花180元買骨灰盒?”(近二十年前,180元是個不小的數目)其意若曰:死的是暴徒,還要花那么多錢,究竟什麼意思?
這明顯是要整先生。漆先生毫不理會,只冷冷地扔去一句:“就剩這一個了!”
聽到這一節,我對漆先生由衷地肅然起敬!我仿佛又聽到了那低沉、沙啞聲音——
“我的學生挨打了!”……
由此,他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更加高大起來!我為自己有這樣的老師感到驕傲!我為自己曾是漆先生的學生感到自豪!
現在,我在借書滿架的書齋里,昏黃的燈下,寫著這篇文章,先生卻已經不知在哪裡了。翻點舊篋,還有他的書:《道家思想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那是二十年前在首體旁的一間小書店裡買的;還有他主編的兩大冊《中國散文通史》,是研究生課程的教材;此外就只剩一張照片,那是他和我們“三好生”一起在師院主樓前的合影。黑白的照片,業已泛黃,顯示著歲月的滄桑。照片上,我們二十幾名學生,緊緊圍在他的身邊。我,就站在他的身旁……
僅以此文紀念敬愛的漆先生!哀哉,尚饗!
2008年9月5日晚,三餘書屋北窗之下,揮淚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