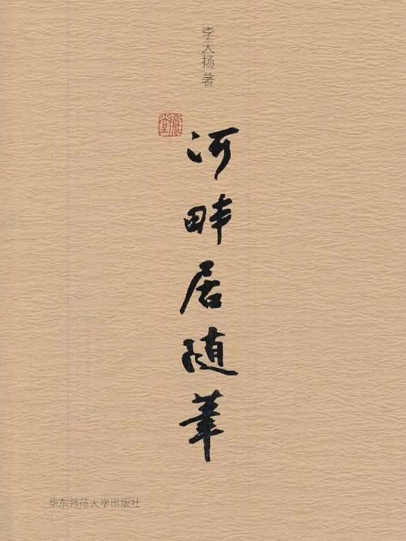《河畔居隨筆》
李天揚 著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14年3月
基本介紹
- 書名:河畔居隨筆
- 作者:李天揚
- ISBN:9787567509399
-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3月
正在閱讀李天揚的雜文集《河畔居隨筆》之際,在《人民日報》上讀到南丁先生追憶年初辭世的著名作家張鍥的文章,其中有一段1957年發生的故事。時任《蚌埠報》文藝組編輯的張鍥來訪約稿,說到他們副刊的來稿百分之八十以上皆為揭露社會陰暗面的,並為此感到憂慮。南丁對此表示同感,當即答應為副刊寫篇短文。隨後不久,《蚌埠報》副刊便發表了他的隨筆《請歌頌光明》。孰料,正是因為這篇隨筆,二十六歲的作者和二十四歲的編輯雙雙被戴上“右派”帽子,從此歷經坎坷受盡磨難。
為“來稿百分之八十以上皆為揭露社會陰暗面”而憂慮,呼籲“請歌頌光明”,這無論如何與官方的旨意相契合,與“主旋律”的基調相一致,在今天看來甚至有偏“左”之嫌,卻竟被打成“右派”,實在令人錯愕和費解。醜陋的年代、扭曲的人性、荒謬的邏輯,製造了多少悲劇,一篇隨筆惹禍,僅僅是國殤悲劇中一個“片段”。
這個歷史“片段”倒不禁讓我思索起隨筆如何“歌頌光明”的問題來。“隨筆”這類文章,既是散文的一支,也是雜文的一種形式,觸景生情,旁徵博引,並無理論性太強的詮釋,行文活潑而不失縝密,結構自由而不失嚴謹。所以我更傾向於將隨筆視作雜文,即如新近出版的《河畔居隨筆》。而雜文的本質,並不是“歌頌光明”,一如相聲的本質屬性是諷刺藝術,若不想、不能或不敢對無良的社會現象予以諷刺,那么相聲頂多只是逗樂伎倆,焉有存在之必要?同理,若雜文缺失揭露鞭撻的功能,磨滅了批判抨擊的鋒芒,哪有雜文的立錐之地?誠如魯迅先生所言:雜文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是“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也是“在對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這應該就是雜文的本質。有人認為,魯迅說雜文是“匕首和投槍”,是“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而現在已經是陽光明媚、春風蕩漾的新時代,當然應該“歌頌光明”。對此不敢苟同。且不說依然有“風沙撲面”,有“狼虎成群”,即便從辯證的意義上說,發現和報告陰影,戳穿黑暗與醜陋,不正是以另一種形式“歌頌光明”?
當代的雜文,則愈發緊密地與時評結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曰“雜文味時評”,或曰“新聞性雜文”。無論是哪一類,時下都已呈日趨活躍的態勢。但是讀多了連篇累牘的時評或雜文,總覺得有些作者愛呈叱吒風雲捨我其誰之狀,感性的宣洩有餘而理性的辨析不足,偏見、片面、武斷、臆想的成分充斥其間,難以令讀者心悅誠服,欣然接受。
有鑒於此,讀《河畔居隨筆》時便愈發對作者的冷靜、沉穩、理性、內斂印象深刻。這些文字固然猶如“匕首”、“投槍”,或如魯迅的另一個比喻,是“小小的顯微鏡”,“也照穢水,也看膿汁”,卻沒有聲色俱厲的苛責,不見刀光劍影的搏擊,大白話大實話,篇篇是對現實的洞察,對時弊的剖析,對藏污納垢之處的毫不留情,對魑魅魍魎之輩絕不寬恕。令人感佩的是,作者憤世嫉俗卻不慍不火,嫉惡如仇卻不亢不卑,亦莊亦諧中滿懷憂思,調侃幽默里蘊含真誠。他善於在談天說地間“亮劍”,不動聲色時“封喉”,其“撒手鐧”便是以足夠的智慧綿里藏針,文章的“亮點”與“看點”就在不似辯駁而勝於直斥的血性,就在以正壓邪激濁揚清的氣場。
倘真有“文如其人”一說,那么《河畔居隨筆》的作者堪稱典型。李天揚有一股“耿勁”,認準的事理便定會執著到底,作文與為人一致且始終如一。譬如他對陳凱歌拍攝電影時破壞環境的行為恨之入骨、耿耿於懷,連續撰寫“別把攝製組當回事”、“明知故犯,罪加一等”、“陳凱歌的‘綠與黑’”予以抨擊之後,又在“我為什麼不看 《梅蘭芳》”一文中寫道:“我堅決不看《梅蘭芳》,甚至不看陳凱歌拍的任何電影,與電影質量無關,而是因為他拍 《無極》時的行徑。”繼而在“‘好漢林’?恥辱柱!”一文里再次提及此事,指出“陳凱歌三年多來,從來未就此事向公眾說過隻言片語”。義正詞嚴,一以貫之,不僅以雜文的批判精神激揚文字,且自覺付諸行動。而類似的言與行,何止一二?在“兩面人”甚多,“文與人”分離、“言與行”相悖現象日盛的當下,何等難能可貴。文品與人品相統一,也可以說是其人其文的一抹亮色吧。
這本集子裡的文章,有不少在發表伊始就拜讀了。現在合集裡重讀,感觸和獲益更多。不過也發現有一點雜文或時評往往難以倖免的缺憾,那就是當初報導的某些新聞,事後被澄清、被證偽,但倉促間據此評說的作品裡,卻仍殘留著若干不實信息,並可能將繼續存世。這也讓人再次痛感虛假新聞之卑劣可惡,貽害當代,還會繆傳後世。時評雜文之類的急就章每每中招,委實無奈和糾結啊。
很長一個時期,李天揚難得以真名實姓在自己供職的報紙上發表雜文,在《聯合時報》的專欄亮相後,引發精英讀者的關注,卻畢竟範圍有限。現將專欄文章結集出版,相信可以讓更多的讀者賞讀這些佳作。他說自己在選編集子時重讀一遍舊作,覺得是對得起讀者的。信然。在此不由得回想起已故雜文家馮英子先生的一個趣聞。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供《新民晚報》頭版時評專欄《今日論語》刊發的言論,都署上筆名“方任”,每次將親筆撰寫的文稿送來時,他都會“呵呵”地說道:這是宣傳黨和國家的方針任務呀!而在副刊 《夜光杯》 上發表的雜文,或需要在頭版討伐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時,則堅持署上真名:馮英子。這位一向不願阿諛奉承違心說話的耿直老人一如鳥兒珍惜羽毛般呵護自己的名字。如今身為《新民晚報》的新一輩報人,李天揚也頗得老報人的遺風,希望以後能在報紙上讀到更多以其本名見報的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