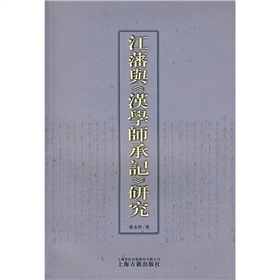內容簡介
江藩是清代乾嘉學派時期的著名學者,所著《漢學師承記》為研究清代學術的一大名著,歷來雖有所研究,但作為全面論述的專門性論著,尚未出現。所以本書在學術領域中有填補空白的作用。
全書資料收集豐富,圍繞《漢學師承記》的史源、成書、版本、得失之研究,以及江藩學行、年譜之考訂,皆可信可據。其中論及乾嘉以前清代大部分學者,不僅對讀《漢學師承記》有參考價值,對於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也多有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陳祖武教授評價此書“超邁前賢,後來居上。”
筆者研究清乾嘉時期學者江藩與他的名著《漢學師承記》十有餘年,從事《漢學師承記校箋》課題的研究,也有了八年抗戰的歷史。《漢學師承記》一書,纂成於嘉慶後期,因此對嘉道及以後從事漢學的學者未能撰傳,於是後來陸續有好事者對該書進行續補與注釋的工作。
從《漢學師承記》看西學對乾嘉考據學的影響
漆永祥
清嘉慶時期學者江藩(1761—1830),以纂《漢學師承記》一書而聞名於世。該書突出表彰了清代尤其是清中葉考據學家的經學研究成就。包括江藩在內的這部分學者中,在致力經史的同時,有的又兼擅天文、曆法與數學,他們或中西兼通,或專明中法,取得了相當出色的成就。本文即從《師承記》對當代考據學家天算學成就的記述以及他們對西學的認識等方面,來考察西學對乾嘉考據學的影響。
一、江藩本人的天算學觀念與水平
江藩,初名帆,字雨來,亦作豫來,後字子屏,一作國屏,號鄭堂,晚位元組甫,又自署竹西詞客、炳燭老人等,祖籍安徽旌德,後為甘泉(今江蘇揚州)人。少受業於薛起鳳(1734—1774)、汪縉(1725—1792),學詩古文詞;後師從惠棟(1697—1758)弟子余蕭客(1729—1777)與江聲(1721—1799),治漢學,為惠氏再傳弟子。又曾從朱筠(1729—1781)、王昶(1724—1806)游,在京時又久館於王傑(1725—1805)府邸。江氏既轉益多師,故其學博而能精,於經史、國小、詞章等兼擅其能。然而就天算學而言,江氏並無有師承,其業師余蕭客、江聲以及太老師惠棟皆不精此學。雖然惠棟之父士奇(1671-1741)精於歷算,但惠棟本人在此點上並未能繼承家學。江藩曾曰:
如松崖徵君雖淹貫經史,博綜群書,然於算數、測量則略知大概而已。此乃余古農師之言也。[1]
余蕭客敘述自己的老師,當然不會是故意貶抑,我們從惠棟的著述中,也看不出他在天算學方面有何特出的成就。即余蕭客、江聲二人而論,余氏的代表作為《古經解鉤沈》30卷,江聲代表作《尚書集注音疏》12卷,皆未有天算學專著。江藩的天算學,自稱是得之於與他同時的揚州學者汪中之啟發與鼓勵,江氏《漢學師承記》記其與焦循之交往時曾曰:
藩弱冠時即與君定交,日相過從,嘗謂藩曰:“予於學無所不窺,而獨不能明九章之術。近日患怔忡,一構思則君火動而頭目暈眩矣。子年富力強,何不為此絕學。”以梅氏書見贈。藩知志位布策,皆君之教也。[2]
江藩受汪氏鞭策才治算學,但汪中也正如他自己所說對此學不甚專門,其《述學》中涉及此方面的問題很少。但江藩卻與當時治天算有名的“談天三友”――焦循(1763—1820)、汪萊(1768—1813)與李銳(1773—1817)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江氏與焦循皆以淹博經史,為藝苑所推,時稱“二堂”[3]。江、焦又與黃承吉(1771—1842)、李鐘泗(1771-1809)嗜古同學,輒有“江焦黃李”之目。[4]江藩與汪萊為“密友”之關係。[5]他與李銳也是學友,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1764-1849)得知李氏已卒的訊息,還是江藩告知於他的。[6]同時,江藩與精於天算學的凌廷堪(1757-1809)、阮元也是摯友關係。江藩在“志位布策”方面有所提高的話,應該與和他們的交流與切磋有很大關係。
江藩的天算學觀點,與時人並無二致。一方面在談到歷學與算學之關係時,也認可西方天算學的成就。他說:
歷學之不明,由算學之不密,雖精如祖沖之、耶律楚材、郭守敬、趙友欽,而猶不密者,算法之不備也。自歐羅巴利瑪竇、羅雅谷、陽瑪諾諸人入中國,而算法始備,歷學始明。[7]
另一方面,江藩也有西學中源的觀點,他曾論“夫句股,《九章》之一也。以御方圓之數,曆象用以割圓、八線等術,皆出於句股。”[8]至於江氏本人的天算學研究與成績,我們現在可考見的是他在北京游幕期間,曾與凌廷堪共客王傑府第,研治天算。凌廷堪云:
乾隆癸丑,廷堪從座主韓城公於灤陽,公下直之餘,恆談論至夜分,往往謂廷堪曰:“顧亭林云: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者,此亦儒者之所恥也。”語次輒舉象緯之名以授廷堪,而未甚究心也。及寓公京邸,公季子更叔承家學,復相指示,遂與旌德江國屏共學焉。乃取《靈台儀象志》、《協紀方書》及《明史》、《五禮通考》互為比勘,晝則索之以圖,夜則證之於天,閱日四旬,大綱精得。[9]
此所謂江國屏即江藩。另外我們從江氏流布的文章中,也可得到數篇與天算學有關的文字。嘉慶三年,焦循《釋橢》1卷完成,該書專門討論傳入中國的義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G.D.Cassini,1625-1721)學說中的橢圓知識。江氏曾為制序,認為昔年秦蕙田《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雖出戴震之手,但未能述及橢圓,是其缺失,今讀焦氏書“以求日躔月離交食諸輪,無晦不明,無隱不顯矣”[10]。江藩在和阮元通信時,曾經對程瑤田“倨句之形生於圓半周圖說”表示不能苟同。另有《毛乾乾傳》,記載明末清初江西星子人毛乾乾“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推步,通中西之學”。毛氏明亡後隱陽羨山中,梅文鼎(1633-1721)造訪,與之論“周徑之理,方圓相窮相變諸率,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鼎以師事之”。[11]除此而外,江氏並無其他天算學的專門著述與文章傳世。
由以上論述可知,就江藩本人而言,他有一定的天算學知識,也對當時西方傳入的天算學說有大致的了解,同時也與當時天算學專家多有往來,但從江氏所論及其著述的情況來看,其天算學觀念與水平亦僅此而已!
二、《漢學師承記》所載考據學家之天算學成就與著述
《漢學師承記》一書所記載的清代考據學家也不乏精通天算學的大師與專家,如黃宗羲(1610-1695)、陳厚耀(1648-1722)、惠士奇(1671-1741)、江永(1681-1762)、褚寅亮(1715-1790)、戴震(1723-1777)、錢大昕(1728-1804)、孔廣森(1752-1786)、凌廷堪、焦循、阮元、汪萊、李銳等人。江藩對他們的天算學成果之記載,或略或詳,筆者在此試一一加以論析。
黃宗羲 《漢學師承記》論黃宗羲在明末“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歷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在敘列黃氏著述時稱有關天算學的有“《授時曆故》一卷、《大統歷推》一卷、《授時曆假如》一卷、《西曆假如》一卷、《回曆假如》一卷、《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諸書”。[12]至於黃氏具體成就與特點,《師承記》中並無發明。黃氏數學著作今皆不傳,其《授時曆故》4卷,是對元代《授時曆》的研究,其“水平未超過《授時曆》,但是他的貢獻是保留了前人的思想方法,並彌補某些不足”。[13]
陳厚耀 陳厚耀是《師承記》中所記人物在清初治天算學最為專門的學者。《師承記》記載他曾從梅文鼎受歷算,通中西之術。由李光地(1642—1718)推薦給康熙皇帝(1653-1722),召見時,帝命其繪製三角形圖並求其中線之長,回答有關弧以及弧所對弦等問題的計算方法。厚耀具札進呈,稱旨。後又特命來京,厚耀提出定步算諸書,以惠天下,康熙帝採納了他的意見,召梅瑴成等入京共同修書,書成特授陳氏為翰林院編修。康熙六十年(1721),厚耀等修成《律歷淵源》100卷,其中《數理精蘊》53卷、《曆象考成》42卷、《律呂正義》5卷,這些書籍尤其是《數理精蘊》的出版,基本上是一部初等數學全書,就其資料來源而論,從整體上說是西方數學著作的編譯作品。陳氏另有《陳厚耀算書》,包括《勾股圖解》、《算法原本》、《直線體》、《堆垛》與《借根方比例》等,其中大部分被《數理精蘊》所採納。[14]江藩書中,還重點介紹了陳氏《春秋長曆》10卷,此書乃糾補杜預《長曆》而作,對研究《春秋》時天文與曆法等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惠士奇 江藩稱惠氏“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15]案惠氏《交食舉隅》未見傳本,諸家著錄,或曰一卷,或曰二卷,或曰三卷,當為研究日月食的專著。惠氏《春秋說》卷11末凡列春秋時期自魯隱公三年(前720)至定公十五年(前495)間所發生的日食共34次,並言“詳見《交食舉隅》”。可見確有成書,後來大概散佚了。
江永 作為清中葉考據學派的代表人物,江永在天算學方面的著述有《推步法解》5卷以及《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1卷。他對梅文鼎的學問十分推崇,對其歷算著作也有深入研究,但對梅氏一些觀點存有疑問和不同認識,特別是對梅氏以中法牽強附會西法的說法多不認同。江永在其《梅翼》(又名《數學》)8卷中專門討論梅氏的著作,其卷2“歲實消長辨”系對梅氏“歲實消長”論之質疑。江藩論江永辨梅文鼎之說曰:
其論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之誤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為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沖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沖為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為率,隨其時之高沖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16]
案此段文中所謂本輪、均輪、高沖、盈縮等,都是自明末清初以來從西方傳入的丹麥天文學家第谷(B.Tycho,1546-1601)的天文體系概念。它採用本輪、均輪等一套小輪系統來解釋天體運動的變化。此所謂歲實即回歸年長度,歲實消長是指它將隨著年代推移發生緩慢變化。宋代《統天曆》與元代《授時曆》都採用了所謂“消長法”計算回歸年長度:
T =365.2425-0.000002t(t為從初始起用年開始經過的時間)
按此法計算,將逐漸縮短,亦即歲實消長。對於此公式之物理意義,當時歷算家從未給出過解釋。由於式中第二項的值非常小,自明朝《大統歷》後,即忽略不予考慮。梅氏是消長法的支持者,但對歲實單方向減小持懷疑態度。他接觸到西方天文知識後,開始從物理意義方面對消長法進行探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江永不同意梅氏的觀點,因此專題加以討論。日本學者中山茂認為,直到江永“才首次給予消長法以近代化的評價”[17]。
褚寅亮 《漢學師承記》在敘述褚寅亮天算學成就時曰:
寅亮精天文、歷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寅亮校正刊本誤字,如“中月相求六扐之數”句,“六扐”當作“七扐”;“推閏余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審。[18]
案褚氏《句股廣問》一書,今亦無傳。所謂句股和較相求諸法,和指相加之和,較為相減之差。《數理精蘊下編》卷12有“句股和較相求諸法”篇,主要討論直角三角形和句股弦及其與差的相求問題。如設句為a,股為b,則句股較為b-c,句股和為a+b,句股弦c-a,還可以有其他和較關係,這樣句、股、弦及其和較共有13種情形。如果已知其中兩個條件(兩種情形),即可求出其它未知的情形。褚氏之書,大概也是在《精理精蘊》基礎上的推演與釋解而已。
戴震 江藩記述戴震的天算學著作有《原象》1卷、《勾股割圜記》3卷、《策算》1卷、《九章補圖》1卷、《古歷考》2卷、《歷問》2卷等。論其成就時曰:
《周髀》言“北極璿璣四游”,又言“正北極樞璿璣之中”,後人多疑其說。解之曰:“正北極者,《魯論》之北辰,今人所謂赤道極也。北極璿璣者,今人所謂黃道極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璣,每晝夜環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是為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之左,是為東遊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之上,是為南遊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之右,是為西遊所極:此璿璣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為東遊所極;又進至夏至夜半,為南遊所極;又進至秋分夜半,為西遊所極:此璿璣之一歲四游所極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璣以擬黃道極,世失其傳也。”[19]
案戴氏此說,問題多多,筆者在此稍加釋解。《論語·為政》所指“北辰”,清以前學者皆以為赤道北極。晚近注《論語》者則多解為北極星,但孔子時代北極附近沒有明亮的星,因此將其釋為北極星,顯然不妥。戴氏解釋為黃極,與實際更不相符。與西方早期的黃道坐標體系不同,中國傳統天文學坐標體系是赤道坐標體系,在西方天文學傳入之學,一直沒有明確的黃極概念。至於《周髀算經》之“北極璿璣”,近代學者多認為是庶子星(小熊座ɑ星),尚不能確定。但戴震釋之為黃道極,實際上是借用西方天文學概念來釋“北極璿璣”,顯然更不準確。至於《尚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西漢學者或認為是北斗七星,以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北斗七星繞北極環行,觀其方向可建四時,以定曆法;東漢以宋代學者則認為是渾儀,渾儀上之圓盤為璣、望管為衡。各有其理,迄今無定論。但戴震另立黃極之新說,則更無根據。
算學方面,戴震的代表作為《句股割寰記》3卷,凡圖55幅,術49題。此書雖承梅文鼎《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要》而作,但不同處在於梅氏多用西法,而戴氏卻多以中法證西法。全書以中國傳統的句股弧矢、割圓術為立法根據,推演三角學之基本公式,以求中西算學之會通。上卷論平面三角的基本概念、公式及平面三角形之解法,其中包括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中卷論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介紹“方直儀”等立體模型之用法;下卷論球面三角形之解法,其中包括球面三角正弦定理和正矢定理。戴震對梅氏書有兩點不滿:一是其書繁難不清,二是只言西學三角而不言中法之句股。其實梅氏《平三角舉要》之序也稱“必先知句股而後可以論平三角”,但不像戴氏要“以句股御三角”而已。後來凌廷堪論戴氏此書“唯斜弧兩邊夾一角及三邊求角用矢較不用餘弦,其餘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20]凌氏所舉,即《句股割圓記》下篇最後第48、49兩術。筆者曾演算戴氏第48術,本術即在球面上知兩邊與夾角求對邊,戴震不用西法的餘弦定理,而是將其放在句股法範圍內,創“矢較法”以求解,所得結論與西法餘弦定理完全相同,用以證明他的西學中源、中優於西的天算學認識與實踐。[21]又如在談到中土句股法與西方三角形之關係時,江藩引戴氏之說曰:
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雲勾股不能御三角。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22]
案戴氏在其《與是仲明論學書》一文中也稱“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其三角即句股,八線即綴術。然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23]與戴氏之說相近的同時著名學者,還有錢大昕等人。
錢大昕 江藩對錢大昕天算學成就所論極少,他說錢氏:
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烺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時禮部尚書大興何翰如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時來內閣與先生論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諸家之術,翰如遜謝,以為不及也。[24]
錢氏天算學著作,今所傳有《三統術衍》3卷《鈐》1卷。漢時劉歆就《太初曆》造《三統曆》,其書不傳,然《漢書?律曆志》全本其書,歷代釋《漢志》者,錯訛甚熾,錢氏遂為廣采諸家,兼申己意,撰為是書,以糾謬正誤,演算草示,助其成書者則有褚寅亮。在談到中西之學時,錢氏所論與戴震完全相合無二。他說“以有定之勾股,御無定之三角,三角相求,特勾股中之一術,而說者謂勾股不能御三角,豈其然乎!”[25]
“談天三友”――焦循、汪萊與李銳 在《漢學師承記》中,江藩對其他幾位精於天算學者如孔廣森、凌廷堪等人,沒有提及其天算學成就。另如焦循、阮元、汪萊、李銳等人,因為當時尚健康存世,按在世之人不為立傳的體例,江藩未給他們立傳,但在又附的人物中,對他們的學術也都簡單提及。如其論焦循之學曰:
(循)聲音、訓詁、天文、歷算,無所不精。淡於仕進,閉戶著書,五經皆有撰述。刊行者,《群經宮室圖考》、《理堂算學》、《北湖小志》。[26]
又江藩述“談天三友”中汪萊與李銳之學及二人間關於算學之爭論曰:
(洪)榜同邑有汪萊者,字孝嬰,藩之密友也,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深於經學,《十三經註疏》皆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意。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之術,著有《衡齋算學》刊行於世。與元和李尚之銳論開方題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不合,遂如寇讎,終身不相見。噫!過矣!然今之學者,大江以南惟顧君千里與孝嬰二人而已,烏可多得哉![27]
案焦循算學代表作為《里堂算學記》,包括《釋輪》2卷,主要討論傳入中國的第谷天文學說中的本輪、次輪的幾何原理;《釋橢》1卷專門討論傳入中國的義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學說中的橢圓知識;《釋弧》3卷,則在梅文鼎、戴震等人基礎上討論三角八線的產生與球面三角形的解法。“這三種論著總結了當代天文學中的數學基礎知識”[28]。焦氏另有《天元一釋》2卷與《開方通釋》1卷,闡述李冶的天元術與秦九韶的正負開方術。汪萊《衡齋算學》的研究涉及到方程論、球面三角、三角函式表造法、組合、進位制以及《九章算術》校勘等幾個方面。其方程等的研究工作“標誌著中國傳統數學的方程分支由算法研究進入理論研究,謂之該分支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殆非虛譽”[29]。李銳是錢大昕天算學的傳人,他的代表作為《開方說》3卷,“不僅是一本介紹開方法的專著,更是一部研究高次方程理論的專著”[30]。在清中葉考據學家中,應該說只有他們三人尤其是汪萊與李銳才是真正以算學名家並終身以之的學者。
阮元 江藩在述及阮元之學時曰:
(阮元)於學無所不通,著有《考工車制考》、《石經校勘記》、《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曾子注》、《論語論仁論》、《疇人傳》等書。[31]
案阮元在天算學方面的最大貢獻是主持編纂了《疇人傳》46卷,但是書資料收集與編纂工作仍主要是由李銳來完成的,全書以人物傳記方式從三皇五帝時起,到清嘉慶四年(1799)止,記載了中國天算學家275人,西洋歷算學家41人,是一部集大成式的中國古代天算學成就總結性著述。
因為江藩編纂《漢學師承記》主要集中在嘉慶十二年到十六年(1807-1811)間,全書訂稿後於二十三年(1818)在廣州刊板行世。嘉、道時期的考據學家與天算學家,在此書中就無有明確的記載了。
三、乾嘉考據學家的西學觀念
以上筆者對江藩本人以及《漢學師承記》所記學者的天算學成就、著述與觀念進行了論述,如果就該書的價值取向再聯繫清代學術界的大環境,我們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第一,如果就江藩以及他在《漢學師承記》中立傳的學者之心理及學術表現來看,用中國傳統訓詁考據方法研究儒家經典在他們看來是天經地義、唯此唯大的第一等學問,天算學只是在經學研究中起一定的輔助性作用。戴震曾論“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即包括天文、曆法、文字、音韻、訓詁、名物典制、地理、算學、樂律等方面的知識,他認為儒者對這些知識“不宜忽置不講”。[32]正因為如此,江藩在《師承記》中選擇人物的標準也是以經學研究成績來取捨,例如他將陳厚耀入選,主要是因為他著有《春秋戰國異辭》56卷、《春秋長曆》10卷。江藩主要介紹陳氏《春秋長曆》也是因為此書為研究《春秋》有用之書。又如江氏為惠士奇立傳並介紹他的《交食舉隅》,是因為其書研究《春秋》中記載的日食現象。又江氏為褚寅亮立傳,也是因為其著有《儀禮管見》一書。而江藩為之立傳的考據學家,有半數以上的人如惠棟、沈彤、盧文弨、王昶、朱筠、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江聲、余蕭客、洪亮吉、孫星衍、臧庸等,對天算學有的粗知皮毛,有的根本就不涉此學,對西學接觸更少。而清代以天算學著名的學者如薛鳳祚(1599-1680)、王錫闡(1628-1682)、方中通(1634-1698)、梅珏成(1681-1763)、明安圖(約1692-約1764)、李潢(?-1812)等人,則為江藩所棄。由此可見,在清代正統考據學家心目中,天算學遠未占到舉足輕重的地步。不僅如此,隨著《算經十書》等的發現,自明末以來即有的“中法原居西法先”的觀點似乎得到更強有力的證據支持。[33]從黃宗羲稱“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34]梅文鼎謂學習西學是“禮失求野之意”。到乾嘉時期戴震、錢大昕等人大倡所謂“以句股御三角”,這種觀點似乎越來越有說服力,而阮元《疇人傳》雖然是專為天算學者立傳,但他卻把上述觀點更進一步強化。於是這種西學中源、中優於西的認識論在當時遂成為牢不可破的定論,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無所不包的自大心理,是導致西學不受重視的重要原因。
第二,從明末清初到嘉慶時期天算學界的大環境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自明季學者如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等與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熊三拔(Sabbarthin de Ursis,1575-1620)等外國傳教士合作翻譯《萬國輿圖》、《幾何原本》、《同文算指》等始,到稍後湯若望(Johann AdamSchallvonBell,1691-1666)等編定《崇禎曆書》,可以說是西方天算學著作大量被翻譯到中國的時期。從梅文鼎等人進行“會通中西”的研究,到康熙時的“中西之爭”以及《數理精蘊》等書籍的編纂,可以說是對西學進行會通、消化與研究的時期。《數理精蘊》等書的刊布標誌著明清以來西算輸入告一段落,同時也是第二階段西洋數學傳入中國的成果。[35]從乾隆時從輯《永樂大典》到修《四庫全書》,隨著《算經十書》與宋元以來天算學著作如李冶《測圓海鏡》、朱世傑《四元玉鑒》等書的發現、整理與刊布,以戴震、錢大昕、焦循、汪萊、李銳、李潢等人為代表的天算學家,在中國傳統天算學著述中找到了與西方學者著述中相同的命題,對這些傳統著作用純考據的方式進行校勘、注釋與演算。如果對照這三個時期,就會發現甚為有趣的現象,第一階段書籍的翻譯與編纂以及朝廷欽天監曆法的修訂與曆書的編纂等,大部分都是中西學者共同合作翻譯與編纂的;第二階段這種合作與交流已經減弱,學者在已翻譯著述的基礎上,進行會通、消化與研究;而第三階段則基本上是學者個人對某一種中國古代天算學著作進行個案式的整理、演算與研究,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誠如數學史家李儼所論:“這些成就的取得,雖然從時間上說可能比西方要晚些,但都是中國數學家們在閉關自守的情況下獨立進行思考和鑽研的結果。而且從他們所用的方法上講,也具有和西方數學家分道揚鑣、殊途同歸的特色。”[36]然而,就天算學界的整體情形而言,中國與西方不僅沒有產生越來越多的交流,反而有著明顯的漸行漸遠之態勢。
第三,從當時來到中國的西方學者的心理及他們傳入的天算學著述來看:其一,因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為傳教士,其根本目的在於傳教,宣揚西學只是其接近和歆動中國士大夫和皇帝的手段,故他們不僅不敢大張其鼓地宣傳西學的先進性,反而言詞中多要迎合中國士大夫的心理,這直接導致他們翻譯書籍時有一定的刪改、摘編與曲從,以迎合中國所謂之“大統之型模”,從而使所譯書籍的完整性與科學性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其二,從書籍翻譯的過程來看,“當時中國人不懂外文,因此翻譯都是一中一外,外國教士看看書中用中國話說出來,中國人用筆做記錄,中間當然商量譯法和名詞術語的確定。這樣,翻譯什麼主要由教士選擇,中國人是被動的。”[37]其三,從進入中國的天算學知識來看,由於傳教士們本身此方面知識有限,故他們所翻譯的書籍遠遠落後於同時期西方的天算學水平。如天文學方面採用的第谷體系,數學也是初等數學,而解析幾何、微積分、初等機率等尚未為中國學術界接觸與接受。以數學而論,這直接導致了“中國數學研究脫離了世界主流,後來越離越遠,18世紀以來外國數學的迅速發展,中國人竟然毫無所知”[38]。
第四,從清朝當時的國情來看,雖然經“康乾盛世”後至嘉慶朝已國勢日衰,但在對世界形勢並不了解的情形下,從皇帝到士大夫仍然生活在天朝大國的心態與生活中,無論社會政治還是經濟等各個方面,也都沒有產生革新圖變的土壤與氣候,學子勤奮努力的功課仍是八股時文,學者矻矻不休鑽研的學問仍是經籍之訓詁。此種情形之下,西學的傳播與交流就很難在帝王與主流學界產生很大的影響。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談到西學東漸的影響時所指出的,中國過去雖然同西方及南方鄰國有接觸,但“這種接觸從來沒有多到足以影響它所特有的文化及科學的格調”[39]。無獨有偶,七十年代末,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eque Gernet)在談到西方數學對中國的影響時也說:“西方的數學知識甚至在兩個世紀中導致了有關中國數學史上的一場大運動,這些新鮮事物並沒有動搖實質性的內容,即他們自己的世界觀。”[40]
因此,就清初至江藩所在時代而言,西學對當代考據學家產生的影響極其有限。民國以來學者稱西學細密的數理邏輯方法對考據學方法產生過重大影響,研究傳教士者又認為傳教士們的布教以及宣傳西方科學技術的活動,對中國人改變自己的世界觀也產生了相當大的作用,筆者認為這些說法都有所誇大。中國人真正重視西學與認識西學的先進性並主動向西方學習,是到鴉片戰爭後國門洞開,面臨亡國滅種關頭以後的事情。
--------------------------------------------------------------------------------
--------------------------------------------------------------------------------
[1] 清江藩撰、漆永祥整理《江藩集》附錄二《炳燭室雜文續補?算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3頁。
[2]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7《汪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冊第727頁。
[3] 江藩友人王豫曾云:“里堂與江鄭堂皆以淹博經史,為藝苑所推,時有‘二堂’之目。”見王氏《群雅集》卷19《焦循》注,嘉慶十三年王氏種竹軒刻本,第5冊第8a頁。
[4] 江氏摯友黃承吉亦稱:“予與里堂,弱齡締交,中歲論藝,儔輩中昕夕過從尤契洽者,則有江君子屏、李君濱石。當時以予四人嗜古同學,輒有‘江焦黃李’之目。或遺子屏而列鐘君菣厓,則稱‘鐘焦黃李’也。”見黃氏《夢陔堂文集》卷5《孟子正義序》,1939年燕京大學鉛印本,第2冊第1a頁。又黃氏有詩稱:“當時好事漫稱許,儷以黃李兼江焦。”見黃氏《夢陔堂詩集》卷20《挽焦里堂》,鹹豐元年刻本,第5冊第5b頁。
[5]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6《洪榜》,下冊627頁。
[6] 清阮元《揅經室二集》卷4《李尚之傳》:“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尚之歿矣!’見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上冊第483頁。
[7] 清江藩撰《炳燭室雜文·毛乾乾傳》,見《江藩集》,第112頁。
[8] 清江藩撰《續隸經文·與阮侍郎書》,見《江藩集》,第93頁。
[9] 清淩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1《懸象賦並序》,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5-6頁。
[10] 清江藩撰《炳燭室雜文·釋橢序》,見《江藩集》,第108頁。
[11] 清江藩撰《炳燭室雜文·毛乾乾傳》,見《江藩集》,第111-112頁。
[12]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8《黃宗羲》,下冊第788、819頁。
[13] 李迪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明末到清中期》第二編《中國數學家的會通中西工作》,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頁。
[14] 詳參李迪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明末到清中期》有關陳厚耀的部分,第351-357頁。
[15]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2《惠士奇》,上冊第159頁。
[16]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5《江永》,上冊第477頁。
[17] 關於消長法的內容與意義,可詳參中山茂《消長法研究――東西方觀測技術的比較》,載李國豪等主編《中國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89頁。
[18]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2《褚寅亮》,上冊第255-256頁。
[19]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5《戴震》,下冊第533-534頁。
[20] 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卷24《與焦里堂論弧三角書》,第213頁。
[21] 參拙著《乾嘉考據學研究》第六章《戴震考據學述論》有關戴氏天算學的部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75頁。
[22]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5《戴震》,上冊第535頁。
[23] 清戴震《東原文集》卷9《與是仲明論學書》,黃山書社1995年版《戴震全書》本,第6冊第371頁。
[24]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3《錢大昕》,上冊第270頁。
[25] 清錢大昕撰、呂友仁點校《潛研堂文集》卷17《雜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79-280頁。
[26]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7《凌廷堪》末,下冊第774-775頁。
[27]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8《洪榜》,下冊第627-628頁。
[28] 錢寶琮《中國數學史》第十六章《傳統數學的整理和發展》,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頁。
[29] 清汪萊撰、李兆華校正《衡齋算學校證·導言·汪萊及其〈衡齋算學〉》,陝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
[30] 李兆華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八卷《清中期到清末》,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頁。
[31] 清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卷7《凌廷堪》末,下冊第777頁。
[32] 清戴震《東原文集》卷9《與是仲明論學書》,《戴震全書》本,第6冊第371頁。
[33] 清阮元《揅經室四集》詩卷4《贈周朴齋治平》,《揅經室集》本,下冊第817頁。
[34]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匯校集注《鮚埼亭集》卷11《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引黃宗羲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全祖望集彚校集注》本,上冊第222頁。
[35] 詳參李迪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明末到清中期》第三編《康熙帝與數學》,第249-255頁。
[36] 李儼、杜石然《中國古代數學簡史》,中華書局1964年版,下冊第304頁。
[37] 李迪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明末到清中期》第一編《西方數學的第一次系統傳入》,第18頁。
[38] 李迪主編《中國數學史大系》第七卷《明末到清中期·第七卷前言》,第2頁。
[39] [英]李約瑟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分冊),科學出版社1978年等版,第337頁。
[40] [法]安田朴、謝和耐等著,耿升譯《明清間入華耶穌會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84-85頁。
(本文由中華文史網首發,引用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