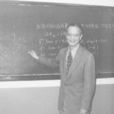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梅祖麟
- 民族:漢人
- 出生地:北京
- 出生日期:1933
- 專業方向:漢語語法史和漢藏語言比較研究領
- 職務: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文學和哲學教授
主要論著,台大演講,
主要論著
1.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of the Rising Tone,HJAS30.86-110,1970
2.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16th Century Mandarin,Journal of Chinese Liguistics 5.237-260,1977
3.《現代漢語選擇問句法的來源》,《史語所集刊》49.15-36,1978
4.《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427-433,1980
5.《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語言研究》1.65-77,1981
6.The causative and di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prefix in Old Chinese,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Section onLonguistics and Paleograph),33-52,1989
7.《唐宋處置式的來源》,《中國語文》3.139-216,1990
8.《詞尾“底”、“的”的來源》,《史語所集刊》59.1.141-172,1991
9.《從漢代的“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語言學論叢》16輯,1991
台大演講
時 間: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七日(星期一)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 點:國立台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梅祖麟 教授
主持人:葉國良 主任
--------------------------------------------------------------------------------
我今天很榮幸有機會到這裡來談“我的學思歷程”。我在大學學的是數學,在研究院學的是數學和西洋哲學。後來研究的是中國文學與語言學。我二十一歲進哈佛研究院時根本是個二毛子,大學是在美國念的,對中國文化只具備一個中學生的知識。在哈佛的兩年,我認識了董同和先生和高友工。董先生是台大的教授,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受了董先生的影響,我後來研究漢語語言史。高友工是台大中文系的高材生。他把我帶進中國文學的領域,後來我們還合寫了幾篇論唐詩的文章。我雖然不是台大的校友,但是我學術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良師益友是台大人。我今天回到台大來是抱著飲水思源的心情。
我1954年進哈佛研究院數學系,教過我的老師有Andrew Gleason, Lars Ahlfors, John Tate, Zariski, Brauer。Ahlfors教的課是complex analysis,後來我還跟他念了一門meromorphic function,當時年幼無知,心裡想反正得有一手,才能在哈佛數學系當教授。前幾年讀《陳省身文選》,才知道Ahlfors多偉大,得過兩次Wolf Prize,數學的諾貝爾獎。還有Andrew Gleason也是我的老師。1900年德國的David Hilbert-當時最偉大的數學家-曾經提出數學十大難題。過了半個世紀,三個數學家把其中的一道拓樸學的題目解答出來。Andrew Gleason就是這三個人中的一個。
進了哈佛不到一年就自己知道數學天份太差。Complex analysis和Real analysis是研究生的必修課,那年兩門課考第一名的是本科的一名新生。我做數學習題,往往一道題花一晚上的工夫還是做不出來。第二天要交,只好晚上十一二點鐘去找吳大鈞求救,吳大鈞五分鐘就找到答案。諸位也許不知道吳大鈞是何許人也。吳大鈞是數學天才,三十幾歲就在哈佛當正教授,後來跟楊振寧合作發表文章,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跟我同歲,1954年跟我一起進哈佛研究院,那時他主修的是套用物理和套用數學,可是在數學方面比我知道得多得多。
所以過了兩年自知不是學數學的料,就轉行到耶魯大學去學哲學。在數學方面唯一的收穫是跟Quine和王浩學了兩年數理邏輯。
跟我同一年進哈佛研究院的有高友工、余英時、張光直、林繼儉(生物化學,後來擔任哈佛醫學院生化系主任)、吳大鈞、楊振平(楊振寧的弟弟,當時學電腦,後來學物理)。當時哈佛中國學生總共一二十個人。我們都沒有結婚,也沒有女朋友,平時在飯堂里一起吃飯,周末就七個人擠進楊振平的老爺車到唐人街打牙祭。我們在一起聊天談的是自己的本行,這兩年從朋友口中學了不少東西。張光直講考古,余英時講中國歷史,高友工講文學,林繼儉講生化,吳大鈞講物理、數學,楊振平講電腦,可以算是我延晚的通識教育。
除了中國學生以外,1954年以後哈佛陸續來了一批中研院史語所的學者,來做哈佛燕京學社的訪問學者。最早的是董同和、勞乾,後來還有全漢升、張秉權、管東貴、張存武等等。趙元任先生1954-55那年休假,有半年在劍橋,住在他女兒卞趙如蘭家裡,趙如蘭,趙元任夫人都好客,於是卞家就成為劍橋華人經常聚會的地方,常客有董同和、勞乾、楊聯升夫婦、高友工、張光直、我。有一回還有李濟之先生。遇到過年過節大請客,是趙太太掌廚,趙如蘭二把刀,高友工和我管洗盤子,餐後打掃廚房。記得趙太太還誇獎過我們,說我們碗盤洗得乾淨,工作俐落。
1955-56年董同和先生和高友工、張光直同住在牧人街的一個樓里,在卞趙如蘭家和牧人街,我認識了董先生。
我去卞家和牧人街其實是因為嘴饞。學校宿舍的洋飯吃膩了,就五六點鐘到卞家、牧人街走一趟,說不定有人會留我吃飯。趙如蘭和高友工都把我當小弟弟看待,那兩年不知道吃了他們多少頓飯。
飯後董先生就在他的房間裡跟我們聊天。記得有一回高友工、張光直說,中國傳統尊師。老師錯了學生不敢駁正,結果中國學術進步不快。董先生生氣了:“你們該去看看段玉裁、王念孫給江有誥(ga$o)論古音的信。江有誥是晚輩改正了段、王的錯。以當時段、王的學術地位,他們給江有誥寫信,一點沒有擺前輩的架子,以事論事,江有誥說他們錯了,他們就承認自己錯了。”
還有一次董先生教訓我們:“你們不要以為自己得個屁也吃得(Ph.D.)就怎么了不起。我那本《中國音韻史》就有兩個洋博士搶著要翻譯。你們是不是學者不得而知。我這個“學者”的頭銜可是哈佛燕京學社封的!”那個時候哈佛燕京學社邀請到哈佛去訪問的學人都叫“Visiting Scholar”。“Scholar(學者)”就成為銜頭。
我認識董先生時他才40齣頭。當時的感覺是漢語音韻史中該知道的他都知道,而且他的學習和研究都是國內做的。董先生給我還有個印象是做學問認真。當時高本漢的《漢文典》修正本(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剛出版,董先生一個字一個字地去檢討他擬構的上古音,有時也發牢騷:“怎么李方桂先生跟我已經糾正的他還擬成老樣子。”同時他又在哈佛旁聽機器翻譯和印歐語言史的課。跟我們晚輩聊天碰到學術問題總是認真地討論,一點都不放鬆。還有對學生輩的關切。我第一篇文章發表後寄給董先生,他特別回信誇獎,說是“學人的文章,不是文人的文章”。
這兩年間跟董先生的接觸影響了我一生,在六十年代使我走向漢語語言學的路。
我第二個語言學方面的老師是勃勞克(Bernard Bloch)。1956年我到耶魯大學去學哲學,主要興趣在語言哲學,就覺得學點語言學總是應該的。1958年考完預考就去聽勃勞克為語言學系研究生開的語言學導論和語言結構兩門課。在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興起以前,勃勞克是結構主義學派的大師,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的傳人。上了他的課才知道語言學中別有一番天地。比方說,怎樣知道一個東西是同一個東西是柏拉圖以來哲學家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所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上勃勞克的課就學到“音位”這個基本概念:phonetic similarity and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兩個音如果聲韻性質類似而出現範圍互補就算同一個音位。這樣從語言學的觀點就能說明兩個不完全相同的音在什麼情況下算是同一個音位。勃勞克的課我1962-63在耶魯哲學系當講師時又聽了一遍,那時擴充到“雙份課”,占語言學系研究生第一年課程的一半時間。我總共上了勃勞克六門課,比哲學系任何一個老師還要多。
對語言學發生興趣另一個因素是教中文。夏天為了要賺錢謀生,就在耶魯教漢語。一連幾個夏天都是如此。美國漢語教學制度是一兩個教授講語法和音韻,負責一門課的整個教程。另外請一批中國人帶學生練習發音、句式、會話;上課不許講英文。我做的就是這種“操練教師”(drill instructor)。我也去旁聽語法的課。記得第一回聽到動補結構的分析,“打破”、“沒打破”、“打得破”、“打不破”。喔!漢語裡還有這樣的語法規律,有意思極了。
教了幾個夏天的中文,對現代漢語語法粗具知識。看到幾個英國哲學家討論主語和謂語的差別(Strawson),還有嘗試動詞和成就動詞的差別(Ryle)。他們舉例用英文,卻認為英文裡的差別是一般性的,是邏輯關係在語言中的體現。我讀後大不以為然,就發表兩篇文章指出漢語語法在這方面跟英文不同。這兩篇文章以後擴充就成為我的博士論文。
我第一篇發表的文章是哲學系逼出來的。1960年春季我收到哲學系研究生主任Wilfred Sellars的一封信,大意是說“閣下在本系已經待了四年,通過預考也將近兩年,但是博士論文還不見頭緒。三個月內如果不交上論文,本系非常抱歉地將勒令閣下退學。”
這封信把我嚇出一身冷汗。怎么辦呢?劍橋大學的Strawson是當時日常語言哲學學派(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的健將,他有篇文章講主語和謂語這兩個邏輯觀念在日常語言中的差別,比方說“John smokes”這個命題,我們怎么知道John是主語,smokes是謂語?Strawson說,語尾 -s加在哪個成分身上,哪個成分就是謂語。比方說smokes帶了-s,所以smokes是謂語。我看了Strawson的文章大不以為然。英語是個有曲折構詞的語言(inflected language),第三身單數現在式在動詞後面要加-s,所以語謂是帶 -s的成分。漢語沒有曲折構詞法。“老張抽菸”中的“抽菸”是謂語,“抽菸不好”這句話里的“抽菸”是主語,兩者完全一樣。英文可不同,一句是John smokes,另外一句是Smoking is bad,一看就看出來帶 -s的是謂語。顯然的,Strawson把英文當作所有語言的代表,值得寫文章駁正。
我記得我是六月開始寫這篇文章。時值酷暑,脫光了上身,開足了風扇,每天從早寫到晚,第一個禮拜只寫了一頁。那個時候我英文不好,第二天看前一天寫的,總是覺得不滿意,就動手改,改到每一個字每一句都滿意才繼續寫下面一段。可是開頭開順了,三個星期之內就寫成。投稿給Philosophical Review(哲學評論),三周之內收到回信,接受這篇稿子,1961年登出來時還登在首篇。
Philosophical Review是美國哲學界的權威期刊,我登了那篇文章,灰姑娘頓時變成公主。哲學系不但不要開除我,得了博士學位後還讓我留在系裡教書。我那年夏天又寫成一篇,登在導師Paul Weiss主編的《形上學評論》Review of Metaphysics上面。有了這兩篇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博士論文不必發愁,所以我1961-62在劍橋名義上是寫論文,大部分時間花在聽Chomsky, Jakobson和Quine的課,導師來信催論文,才把三篇寫成的文章加頭加尾拼成一部論文交上去。
最重要的,到美國十一年後,我終於學會了寫英文。那時的感覺是小鳥羽毛豐滿,能夠到天空上去飛翔一番。我有種種想法,現在能夠用文字表達,這真是非常開心的事。
五六十年代,我們都深受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響。維根斯坦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對話都是語言遊戲,但不同的語言遊戲有不同的遊戲規則。傳統的哲學家誤用規則,張冠李戴,結果墮入陷阱,不能自拔。在發展下去就是近年來所說的(西洋)哲學破產,哲學的結束。這有點像禪宗“如桶子底脫”-一個桶子整個底掉下來-的悟。我在研究院時受維根斯坦的影響很深,覺悟到哲學家的爭論是不可解決的假問題。既如此,就想找機會放棄哲學再改行。
1964年我到哈佛去教中文,一直待了七年,1971年才離開。這七年間我也學了不少東西。
第一,我了解了漢學。五十年代就聽余英時、高友工說有漢學這么一門學問。當時沒怎么理會。現在要教了,只得臨時抱佛腳。所謂漢學就是法國人、日本人對古代中國的研究,法國名家輩出,Chavannes, Pelliot, Maspers, Demieville, Gernet,尤其是馬伯樂和戴密微兩位,對漢語史都曾作出卓超的貢獻。日本學者有吉川幸次郎、小西甚一、有?秀世等等。他們的著作都使我大開眼界。
第二,劍橋在六十年代還是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派的天下。1965-66麻省理工學院的John Ross和哈佛的George Lakoff合教一門語法理論的課,兩校語言學系的師生都去聽,差不多有兩百多人,真是轟動一時。我也去聽。那一陣子喬姆斯基和麻省理工學派的語法理論變動很快,過三五年就有一套新理論出現,我漸漸覺得跟著人家跑有疲於奔命之感。
這只不過是語法理論部份。1968年鄭錦全來哈佛跟我們一起教漢語。他每個星期跑到麻省理工學院,同時在寫他的博士論文。他的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我是聽他口頭說的,同時也跟他學了衍生聲韻學(generative phonology)以及前後相繼的音韻演變規律(ordered rules)。
第三1967-68年我哈佛休假,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做一年Chinese Linguistic Project的訪問學者。本來計畫是去跟高友工合寫一本唐詩批評的書,結果遇見了羅傑瑞(Jerry Norman),他是我語言學方面的第三位老師 ,也是影響我最深的語言學家。
羅傑瑞1967年剛從台灣作了閩語調查回來,正在寫博士論文,用比較擬構的方法重建共同閩語。他比我小三歲,當時是研究生。我是助教授。但在上古音、閩語史、漢語音韻史方面他都是我的老師。他在加州柏克萊分校的三位老師,一位是趙元任先生,一位是Malkiel,羅曼史語言學(拉丁語系的義大利、法蘭西、西班牙等語言)的大師,另一位是Murry Emeneau,達羅毗茶(Dravidian)語言學的大師(梵文里有好多字在印歐語系的歐洲語言中找不到同源詞,是從印度土著語言Dravidian借來的),傑瑞跟他學越南語和南亞語言學。我從來沒好好學過歐洲語言史,跟傑瑞閒談時學了不少,此其一。傑瑞同時介紹我讀俄國雅洪托夫(Yakhontov)、法國奧德里古(Haudricourt),加拿大蒲立本(Pulleyblank)這幾個學者關於上古音的著作。我們談得最多的是上古漢語中的詞頭、詞尾、上古音和閩語之間的關係。在傑瑞口中,語言事實都變活了。一個音怎樣變另一個音,閩語的辭彙是怎么來的,都是我們聊天的話題,不知不覺地我學了不少漢語音韻史,此其二。從傑瑞那裡我學到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去研究借詞和同源詞,每個字的每個音都要用歷史的方法擬構,然後再去考察每個字的歷史。這種方法和傳統訓詁學的“一音之轉”大不相同,此其三。
傑瑞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改變了我的語言觀。喬姆斯基一派最注重的是語言中抽象的,邏輯性的語法現象。跟羅傑瑞接觸後深深地感到語言是人類社會在歷史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辭彙有底層(substratum),也有上加層(superstratum)。音韻演變我們固然希望能找出絕無例外的規律,但辭彙層層積累和借詞幹擾就會打破這種只能套用到屬於同一歷史階段的演變規律。反正碰到人的事情就不會像物理或數學那樣有機械性的規律。而且語言到底是可以觀察的事實,依時依地依語言類型有所不同。把語言理論弄得太抽象了,研究者就無法弄清楚這種理論能否能成立。60年代末期,最早追隨喬姆斯基的,如王士元、馬提索夫(James Matisoff)、拉波夫(William Labov),都紛紛脫隊,我也是其中的一個。
1971年我到康乃爾大學去任教。事業倒是蠻順利的。學業都陷入困境,1971到1976這五年之間我一篇文章都沒有發表,原因是我和高友工合寫書的計畫擱了淺。
1972年張光直來校演講,晚上在我的寓所聊天。談到高友工和我合寫的文章,光直說:“你們這套野狐禪,弄的滿熱鬧的。”光直是老朋友,不會故意出惡言相傷。不經意說的話,反而透露出老朋友對我學術方向的關心。
1975-76我休假在日本京都。到了京都後,就由我太太帶著,去拜見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方面的教授,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入矢義高。我見到這幾位,就呈上我和高友工合寫的文章。後來我也每星期去聽吉川先生講杜詩,小川先生也見過幾次,還送了我一本他譯成日文的蘇東坡的詩,可是他們兩位從來沒有跟我談我的文章。我跟高友工在《哈佛亞洲學報》發表的文章,他們根本沒有放在眼裡。吉川,小川兩位都是我太太的老師,吉川先生還曾經指導過我內人的碩士論文。論到唐宋詩,當然他們比我知道得多。他們冷漠的態度使我對文學批評這行更沒有信心。
本來嘛,高友工和我合寫文章就是抱著嘗試的態度。〈杜甫〈秋興八首〉〉是試用新批評(New Criticism)。不久Roman Jakobson的結構主義詩論(Structural Poetics)異軍突起,和Levi-strauss的結構人類學相呼應,成為當代顯學。唐代的律詩八句四聯,中聯需要對仗,整首詩形成起、承、轉、合的篇章,天生就適合用結構主義詩學去分析。於是我們第二篇文章就用結構主義。不過問題就來了。文學批評還有許多流派,如亞歷斯多德學派(Aristotelianism)、弗洛德學派、馬克斯學派,以及後來興起的讀者反應理論(Reader Response Theory)和解構(Deconstruction),我們是否要一一去嘗試?嘗試完了又怎么樣。
T. S. Eliot說,文學批評的目的是幫助讀者欣賞和了解(to understand and to appreciate)。我教唐詩宋詞,也介紹學生去讀《詩境淺說》、《讀詞偶得》、周振甫《詩詞例話》。捫心自問,是這些書對讀者有幫助呢?還高友工和我建立的文學批評體系?當然是前者。這是關於欣賞。至於了解,我們讀元白詩還是要靠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讀杜詩還是要靠錢注。
另一方面,我漸漸了解我的性格根本不適於研究文學。高友工碰到一首好詩、一場芭蕾舞、一場話劇,可以如痴如醉,講起他的文學理論,也可以手舞足蹈,我則是無動於衷。我太太也是學文學的。在中國文學方面比我知道得多,而且對詩詞很敏感。跟高友工、我太太在一起,我自覺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感受先天不足。我是比較善於分析,善於推理,而且有個強烈的結構意識。這種性格來研究文學,簡直是趕著鴨子上雞架。現在鴨子要從雞架上下來了,到池塘里逍遙自在地游一游。
於是,Meaning and Metaphor in T’ang Poetry 1976年發表後,我就跟文學分了家。
1976年我四十三歲,環顧哈佛研究院的同學,當時的感覺是“同學少年皆不賤”。這裡的意思倒不是說昔日的同學都據要津、得高官、賺大錢。而是說余英時、張光直、高友工都有卓越的成就,在他們的領域裡,取得學術上的領導地位。而我自己呢?雖然在哲學、文學、語言學三方面都發表過幾篇文章,但是好的是跟Jerry Norman,高友工合寫的,文章里好的意見是他們的,自己的平平而已。這也許就是“中年的危機”(Middle Age Crisis)。怎么辦呢?“收拾絲竹入中年”。我45歲以前是玩學問,45歲以後才打定主意做學問。
決定改行後立刻碰到一連串問題。第一,我的興趣在於漢語史,不過該做哪一方面的研究?羅傑瑞的音韻史和漢語方言學我一輩子也趕不上。在哈佛1968-70年跟鄭錦全同事,辦公室相鄰,常常互相切磋。錦全那時已經往計算機語言學方向走,但音韻史知道得很多。記得有回跟他談中古音,幾個關鍵字的《廣韻》反切他不假思索都背得出來,我卻要背半天書才能弄清楚中古音值。似乎董先生教過的學生都有這樣的本事,我是望塵不及。
漢語語法史是唯一我覺得還可能做出成績來的領域。那時只有三本書可讀:呂叔湘《漢語語法論文集》、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王力《漢語史稿》(中)。尤其是呂先生的書,開創了這門學問,書中論證之細密,引證資料之豐富,看了都使人愛不釋手。於是就按著太田和呂兩位列舉的書目一本一本去讀語法史的基本資料。從1968到1976我讀了八年基本資料。在京都那年,又在入矢義高,柳田聖山兩位領導的會讀班上讀《祖堂集》,自己又細讀《敦煌變文集》漸漸地從資料中看出幾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用哪種語言寫文章,在哪兒發表。寫文章的目的就是正於方家。自己有些看法,不知道站不站得住,就把看法寫出來,希望得到同道的批評和指正。七十年代末期,語法史方面的行家中國大陸有呂叔湘、朱德熙,日本有太田辰夫、志村良治,美國只有加州柏克萊分校的張洪年。用英文寫,根本沒有人看。討論漢語語法史,那個時候當然要用中文。
寫好了文章投給哪個學報?70年代《史語所集刊》不接受外稿,只有紀念專號、祝壽專號、所慶專號是例外。我有篇文章登在《史語所集刊》上,那是因為1978年正值史語所成立五十周年所慶,李方桂先生把我的文章推薦給《史語所集刊》。台灣還有《清華學報》,學術水準很高,但編輯委員中沒有中古漢語語法史的專家。
1975年我在舊金山遇到丁邦新,因為都是董同和先生的學生,一見如故。丁邦新先生要編一本論文集紀念董先生,約我寫稿,我趕出〈《三朝北盟會編》里的白話資料〉,1975年夏天就寄給邦新。論文集裡還有鄭錦全、嚴棉、管東貴、羅傑瑞的文章。本來說好是由丁邦新、鄭錦全合編。不巧鄭錦全上了黑名單,名字不能登在封面。錦全說,我又沒做錯什麼事,為什麼不許我的名字上封面?後來的發展我不太清楚。到了1980,丁邦新安排《中國書目季刊》出一期紀念董同和先生的專刊,論文集才得問世。
上面是說我在台灣發表文章相當困難。正巧1979年中美復交,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停刊了的《中國語文》,《語言學論叢》復刊,新的學報如《語言研究》、《方言》、《語文研究》創刊。我陸續收到好幾封邀稿的信,於是下決心好好地用中文寫漢語史方面的文章,投給大陸的學報。
這裡又遇到兩種困難。第一,我的語言學是美國學的,連現代漢語也是用趙元任《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的系統。用中文寫文章就得另學一套術語。這也不難。我把《中國語文》,呂叔湘,朱德熙,王力的著作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又買了一本英漢對照語言學術語字典,不知道怎么說就查。第二,我的中文只有高中的程度,以前雖然也用中文寫過三四篇學術文章,寫起來總覺得筆尖很澀。用中文寫文章,每天寫,寫上半年一年,自己覺得文筆熟練得多。但改寫英文,又覺得英文不能運用自如。因此1980年以後,非不得已,不用英文,只用中文。第三,為了給大陸的學報投稿,我學會了寫簡體字。現在我記日記,寫筆記用的就是簡體字。
這么一來,我的學術生涯就產生了雙重人格,分裂人格。中國大陸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研究漢語史的,我和高友工合寫的文章是用英文寫的,他們看不到,後來有人翻譯成中文,用《唐詩的魅力》的書名出了本書,也許這套理論不怎么時髦,沒有多少人理會。台灣正相反,高友工和我合寫的文章,黃宣范譯成中文,在《中外文學》上發表,據說轟動一時,但我在大陸發表的漢語史方面的文章,台灣不容易看到。我在台灣各大學演講,往往有老師同學來跟我說,讀過我和高友工合寫的文章,上個月還有某大學要請我去講唐詩評論、比較文學。我只好從實以告,“我跟文學早分了家了”。
1983年朱德熙先生約我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去客座一學期。那個時候我沒寫幾篇文章,對漢語語法史沒有很深的研究。機會難得,就硬著頭皮去。我想,有幾件事反正是要做的。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志村良治作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應該介紹,還有歐美流行的歷時語法理論。《祖堂集》,南北朝的翻譯佛經,日本學者早已拿來研究語法演變,大陸學者還不知道這些資料的重要性。至於漢語語法史中的主要問題,我能解決的只有幾個。其他就擺出來跟大家一起討論,大家就一起來找答案。而且漢語語法史裡面尚待解決的問題非常多,一個人一輩子也做不完,我早就想找幾個同道來一起研究。北大講學就是個難得的好機會。
班上註冊的是四年級生和研究生,總共十來個人。此外中文系語言專業的老師都來旁聽,還有師範大學的、語言研究所的、人民大學的、民族學院的、到北大來進修的教師、日本來的訪問學者,坐滿了一屋子,有八九十個人。第一堂呂叔湘先生還特別來說了幾句鼓勵的話。
那一學期想不到會那么成功。第一,劉堅、蔣紹愚和我合編《近代漢語基本資料彙編》就是那年開始的。第二,我教過的學生以及來旁聽的老師後來在語法史這個領域裡都有重要的貢獻。第三,跟大陸同道接觸給我很大的刺激。有幾個問題,班上講不出來,回美國繼續做研究。我有好幾篇文章就是為了回答同學問我的問題。
1989年我到新竹清華來客座一學期。台灣的同學大多數都會說閩南話。我想,如果能把閩南話當作教材,指出其中的語法現象可以跟文獻上的歷史語法現象聯繫起來,也許可以激發同學對語法史的興趣。我學語言是很笨的,想學閩南話一直學不會。不過我可以學別人研究閩語的成果。於是讀楊秀芳先生的《台灣閩南語語法(稿)》以及羅傑瑞比較閩語,閩語史的文章。以前我研究過“坐tiE椅·a頂”裡面tiE字的來源,1989年我跟同學討論,又和楊秀芳教授合作,開拓了閩語語法史的研究。
下面我說一下我對我自己學術歷程的感想。
第一,合群。
我在北京有一批朋友跟我一起研究漢語語法史,在台灣有一批朋友跟我一起研究閩語史、方言史。在美國,我的研究夥伴主要是Workshop in Chinese Linguistics的成員。
這是王士元的主意。每年一度在他加州柏克萊分校的研究所里召開一個非正式的研討會。核心成員有鄭錦全、陳淵泉、謝信一、我,後來有Alain Peyraube、曾志朗、丁邦新,偶而Jerry Norman也參加,還有路過柏克萊的訪問學人,如李壬癸、北大的陸儉明、蔣紹愚,語言研究所的劉堅。會議在客廳里開,圍著一個大方桌子,客廳不怎么大,只容得下十來個人。反正王士元不喜歡的,休想來開會,沒有他邀請的,也不能來參加。
參加這個會的人,都有個共同的抱負,就是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漢語語言學,至於這個新的漢語語言學是什麼樣子,誰也不知道。最早大家對聲調都很有興趣,王士元用儀器做電腦對於聲調的認知和合成,陳淵泉做連讀變調,鄭錦全做資料庫里上百個方言的調值統計,我做古文獻上記錄的調值。過了一陣,大家興趣轉向方言,鄭錦全從辭彙的異同來計算方言之間的親疏關係,王士元想聯繫語言學和遺傳學,丁邦新著重方言層次的斷代,我從虛詞來看方言之間的親屬關係。有幾年也沒有共同的題目,誰做了研究,誰就講;沒做研究,也可以不講。這個會我參加了十幾年,好幾篇報告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鄭錦全講“紅樓夢”里的主題鏈(topic chain),王士元和曾志朗講,英語用拚音文字,漢語用方塊字,因此認知過程中有左腦,右腦的差別。我有好幾篇文章最初是在這個會上講的,也有講後給打回票的。
語言學方面現役的五個院士都跟Workshop in Chinese Linguistics發生過關係。丁邦新是當選了院士才到柏克萊去的,所以參加這個研討會比較晚。王士元、我、曾志朗、鄭錦全都是參加了這個會以後才選上院士。我們在美國不同校、不同系,屬於不同的學會,說不上什麼成群結黨。院士的事,更是想都沒有想過。在漢賊不兩立的七八十年代,有的院士到大陸去一趟,國民政府就會有人出來表示不滿。王士元七十年代就致力於語言學方面的大陸和美國交流,屢次到大陸去講學。我從1983年在北大客座後一直和大陸學者保持親密的學術交流。像王士元和我這種親中的美籍華人,休想當院士。鄭錦全上了黑名單,曾志朗有一陣子也回不得台灣。現在政治氣候改變了,我們四個先後都選上了院士。我跟王士元最初認識的時候我還是個研究生,鄭錦全跟我最初認識的時候他還是個研究生,我們在學術領域可以說是打打鬧鬧一起長大的。還有,五個院士中,有三個是董門弟子,丁邦新、鄭錦全、我。董同和先生五十二歲就過世了,如果能再多活幾年,一定會當選院士。如果能活到八十一歲,也就是今年,就可以看到三個門生同時擔任院士。
跟我合寫文章的有高友工、羅傑瑞、楊秀芳、梅維恆(Victor Mair)、張惠英。我們六個人合起來辦箇中文系,陣容是相當強的。我跟高友工、羅傑瑞、潘悟雲都曾經密集通信,一個月兩三封,連續一兩年。信上所談到的看法,以後就發表成為文章。我們的信上引經據典,還帶上方言裡的證據。羅傑瑞很重要的閩語有三個時間層次的文章(《方言》1979),最初是信上看到他的想法。(福建政和的支脂之三韻)(《中國語文》1988),也是信上先看到的。
第二,做研究路子要寬,思路要活。
如果有人問我:“你學的數學、哲學,對你語言學的研究有沒有什麼幫助?”我想回答:沒有。唯一就是培養我的分析能力。不過下圍棋,打橋牌,也可以培養分析的能力。固然趙元任最初是學數學、哲學的,後來對語言學有巨大的貢獻。但我也可以說出來幾個數學出身的語言學家,並沒有很大的成就。
如果有人問我:你改了好幾次行,改行對你的研究有沒有幫助?我想,改行對我的研究沒有很大的幫助,而且耽誤了良好時光。我想改行的唯一的好處是使我學會了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這對我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舉例而言,我1979年寫過篇文章,討論吳語“吃仔飯”“仔”字的來源。我認為本字是“著”字,文獻上的證據找到了不少,但是一直不能解釋“著”字為什麼在吳語裡會變成“仔”。一直到1991年發現北部吳語有個魚虞有別的層次,在這個層次里,魚韻的“著”字會變成“仔”。四個月以前,我才知道北部吳語的魚虞有別,是南朝江東方言在吳語裡的遺蹟中的一小部份,最大的部份保存在浙南吳語裡。這個問題我前前後後做了二十年,以前以為是語法史中的問題,原來牽涉吳語的音韻史。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時,根本沒有音韻層次那個觀念,做夢也不會想到吳語會有個南朝江東方言遺留下的層次。幸虧和鄭錦全合教中國音韻史的時候,學了點中古音。魚虞有別這個現象從資料中浮出時,還認得出來這是《顏氏家訓》中所說的南人魚虞有別。
再舉一例。很早我想知道平仄是怎么來的,後來讀到日僧安然《悉曇藏》的記載,其中有八世紀長安音四聲調值的描寫,於是寫了篇文章說平是低調,仄是高調。後來發現平仄之別是六世紀建康產生的。八世紀長安音的調值與此風馬牛不相及。再讀《文鏡秘府論》,越發相信平仄和四聲八病是受梵文影響而產生的。苦在我不懂梵文,沒法自己找證據。好費了番周折,說服Victor Mair跟我合作。他果然找到非常強的證據,說明永明體中的平仄和八病是受了梵文詩律和文病論的影響而產生的。這個題目我也做了二十年,最初以為是聲調史上的問題,後來才知道是詩律學,中印交流方面的問題。
因為答案不知道會在哪個領域,所以做學徒的時候,各式各樣的武藝都學點,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而且研究面寬有個好處,某個問題擱了淺,可以做另一個問題。李方桂、趙元任兩位都是興趣極廣。李先生四個語言都是權威:侗台語、紅印第安語中的Athabaskan、上古漢語、藏文。趙元任先生是現代漢語語法、漢語方言、音樂、實驗聲韻學(acoustic phonetics)。他們之所以研究生命常青,就是因為他們興趣廣泛。
最後我想談談我的一些希望。
閩南話是台灣最大的語言。從語言史的角度來看,閩語又是最重要、最值得研究的方言。某些閩語的辭彙保存著秦漢音,還有些辭彙保存著《切韻》音的遺蹟。
閩南靠海,十六世紀或者更早閩南人已經渡海到南洋以及東南亞去謀生。有一批閩南人集中在菲律賓的馬尼刺市,他們被西班牙去的多明尼墾(Dominican)傳教士感化,信奉天主教。而西班牙傳教士為了要和說閩南話的教民交談,就紀錄了他們的辭彙,還編了一本語法,以便學習閩南話。為了讓教民能用閩南話祈禱,做彌撒,西班牙傳教士也把《基督教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譯成閩南話。這三百多頁記錄16世紀閩南話的手抄本,現在存在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里,是用羅馬拼音紀錄方言最早的資料。要知道泉州、漳州人十七世紀移民到台灣來時的語言狀況,西班牙人紀錄的閩南話是最早的資料。
此外當然還有《荔鏡記》,Carstair Douglas的《廈英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899))。
這些資料需要整理,閩語的辭彙需要做層次分析。做了這些基本工作以後,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地研究閩語史,閩語和其他方言之間的關係,反映在語言現象里的閩地移民史。
我想,台灣是做閩語史研究最好的地方。一則是台灣人大多數說閩南話,探索閩南話的來源是一種尋根活動。二則台灣學術風氣開放,市面上就買得到Douglas 的《廈英詞典》。三則是研究閩語史要用比較方法。我所接觸到的語言專業的同學老師都知道比較方法是怎么回事。這是因為李壬癸先生、龔煌城先生、何大安先生都在教比較方法,而且用比較方法。
明年台灣就要實施鄉土語言教育,而閩南話是最大的一種鄉土語言。實行的鄉土教育,早晚要給小朋友們講講閩南話的歷史,看看早期閩南話的樣子。還有,教閩南話早晚需要一本參考語法,一本辭典。閩南話好些個語詞往往有音無字,例如“坐tiE椅·a頂”的tiE字,考證本字要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一本好的閩南話辭典,如果得到教育部的認定,可以賺大錢。“書中自有黃金屋”就是這個意思。
在座的同學就可以做上面所說的閩話史的研究。剛才談到合群。台大的同學合群的能力是有名的。我最近在讀創辦《現代文學》的那幾個人的回憶錄,陳若曦、李歐梵、劉紹明都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歡白先勇的小說,人可沒見過。他們幾個人就是在台大本科生的時代創辦了《現代文學》,好幾個後來成為名作家、名校的教授,比他們的老師夏濟安先生成就還要高。
在座的朋友們現在就可以組織起來研究閩語史,整理文獻的工作可以分工合作,還有幾篇重要的關於閩語史的英文文章需要翻譯,本字研究就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水磨工夫,各自分頭去做,匯集起來,出本字典,包管比坊間所見的幾本要好。
我第二個希望是在台灣發展歷史語言學。
台灣的歷史語言學其實是很強的。龔煌城先生的漢藏研究,李壬癸先生的南島語研究,何大安先生的漢語音韻史、漢語方言史,都是世界級的。美國的大學裡,也很多同時有三個研究亞洲語言史的學者。
但是台灣弱的是在印歐比較,歐洲各大語系的語言史。歷史語言學的大本營在印歐比較,這門學問里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治漢語史借鏡的。有了印歐語言史,我們更可以探求漢語的演變方式是否和印歐語系的語言不同。康乃爾大學在人文方面並不能說是名列前茅,但是我的同事中有四個懂得梵文的,而且是教梵文的,用梵文來做研究的。如果沒有教梵文的,教印歐比較會相當困難。美國大學的中文系,好幾個有專人教漢語史,如柏克萊、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eattle、康乃爾大學。據我所知,台大外文系教英語史、法語史、德語史、西班牙語史的不多。在這種情形下,歷史語言學還只是片面的。台大如果要成為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是否要添設印歐比較語言學、梵文、歐洲語言史的教學和研究,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
問:您在語言學或漢學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後來卻沒有繼續往這方面研究,是否因為漢學的研究已經被日本人把持住了,所以日本人在漢學的研究上,比中國人的成就要來得高?
答:這是一個好問題,吉川先生是研究當代漢學的大師,在日本地位非常的高,日本有御前講習,會邀請學者到皇帝面前講述大道理,而吉川就曾經替日本皇帝講課。他個人十分自負,在哥倫比亞大學作訪問教授時,有人問他美國的漢學研究跟日本相較起來如何?他回答說:“大概還要一百年吧!”。其實我開始做研究時也遇到這個問題,當時在文學方面有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入矢義高以及其他研究唐詩、宋詞的名家,在研究語法史上也有不少名家,當然語法史注重基本資料,也就是早期的白話資料,這方面日本人比我們當時研究得遠及寬,也出現不少的著作,如1958年出版的中國語歷史文法,已經使用《祖堂集》,台灣及中國大陸都是我介紹進來的。剛才同學問到既然日本研究漢學這么的強,那我們是不是就直接到日本留學就好了?實際上確實是如此。也就是說真正在做學問時是沒有國界的。就如同有一個時期最偉大的音韻史學者不是中國人而是瑞典人,最偉大的英語語法史的學者,不是英國人而是丹麥人,最偉大研究泰國語的人不是泰國人而是中國人。所以我們撇開一個國際的觀點來看日本,日本的確在研究古代中國的文學、歷史及語法上有一個非常雄厚的傳統。所以我一開始做研究時的確遇到不少困難,因為研究不但要做得好,還要比別人做得好。日本人既然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們怎么可能比他們做得更好呢?所以我們需要引進現代的語法理論,就是結構主義。
其實在70年代以後在漢語語法史的領域中,我們己經逐漸超過日本,所以當我們吸收了日本人的研究成果,自己再掌握了基本語法的資料,下一步就是要研究從那個觀點來著手。1985年代學風有一個轉變,我們都都是由結構主義語法的觀點來問問題,任何一個學問都重視資料另外是方法及理論。
日本人在研究漢學上不太有方法,整個國學本身是一個通識(經、史、子、集),要如何加以整合,從五四以後就存在不少的問題了。所以之前同學提到日本的漢學是否很強?的確非常的強,吉川先生看不起美國的漢學,並非沒有原因。實際上,日本有中國文學大系40本,重要的中國經點不但翻譯成日文,更有著豐富的註解,比我們看到的漢文註解還要好並及精確,所以在語言史及語法史方面,日本研究漢語音韻史是相當弱的,日本人不怎么會用比較的方法,所以日本人對於音韻史的研究只能在文獻中打轉,但是日本人研究語法對於資料的掌握卻是第一流的,尤其是語文學的訓練,不但要讀通還要能看出值得研究的語法現象。
問:請教是否因為語言隔閡的關係,使得西方人研究文學的人比較少,而無法去理解中國文學的意境,,所以在世界聞名的諾貝爾文學獎一直到世紀末才頒發給華人,反而日本人比我們先得到獎。此外,對於語文改革方面,中共建立之初曾經將中文簡化改為簡體字,而德國也有意把文字簡化,但是由於人民適應不良而又回復到過去。簡化後的文字無法充分表達意識,這是否也意謂因著實用方便的語言改革不容易得到支持?
答: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我是學繁體字長大的,在1980年以前都是如此,後來學簡體字後一下子就學會了,同時為了在中國大陸的學報投稿,所以就以簡體字寫文章,常有人說若使用簡體字記載古老的文獻,就無法保存語言的原貌,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有時以簡體字表達不充分時,特別在稿子上註明即可。我學會簡體字後發現簡體字真的非常的方便,常在寫日記或做筆記時會自然使用簡體字,但在台灣寫信或教書我都使用繁體字。改用簡體字是非常成功的一件事,可以減少學童在學習上的困難。但是為了學習比較古老的東西仍然需要繁體字。
第二個問題提到為何中國人長久以來都無法得到諾貝爾獎,實際上在評審諾貝爾獎的瑞典人是高本漢的大弟子,對於左傳、古代漢語十分有研究,也翻譯當代及中國大陸詩及小說。我一個多才多藝的朋友在法國也是翻譯台灣及中國大陸小說的人,是法國世界日報的特約記者,對於中國文學及時事常寫評論。前幾年在討論諾貝爾獎時,中國大陸有若干作家就質問評審到底要如何寫作才可以得到諾貝爾獎,當時評審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如何寫作的話,早就已經得到諾貝爾獎了。”另外,當時中國大陸的作家又提到為何中國都沒有人得獎呢?評審又回答:“因為你們寫得不好,所以沒有得獎。”這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實際上不論是中文還是日文,要被世界上的讀者所接受,必須要有好的翻譯家,而日本人的確有好的翻譯家,將他們傑出的日文著作翻譯成英文或歐洲文字讓世界廣大的讀者接觸。高行健本身的法文很好,也有好的翻譯家將他的中文著作翻譯成法文,以致於他可以得獎。若說中國的作家沒有得到諾貝爾獎,是因為歐美人不能欣賞中文的說法,是一個不公平且不面對事實的說法。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反右以後)根本沒有所謂的文學能談,因此沒有好的作家,文學家首要條件必須要有安定的生活,如果說你生存在隨時會被下放或是被批鬥的環境之下,任誰也寫不出來文章來,所以我們必須就事論事。
諸位把自己認為台灣應該得到諾貝爾獎作家的文章,拿去與當代得到諾貝爾獎作家的文章相互比較,他們對於人生的探討是不是同樣的深,對於時代描寫的廣闊是不是一樣的動人?我覺得還是有差別。所以今後我們希望有中國人或是台灣人能夠得到諾貝爾獎,如果寫得好的作品,自然會有人翻譯成好的英文或法文,在沒有好的作品以前怪歐美人不了解中國的文學,這是一種鴕鳥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