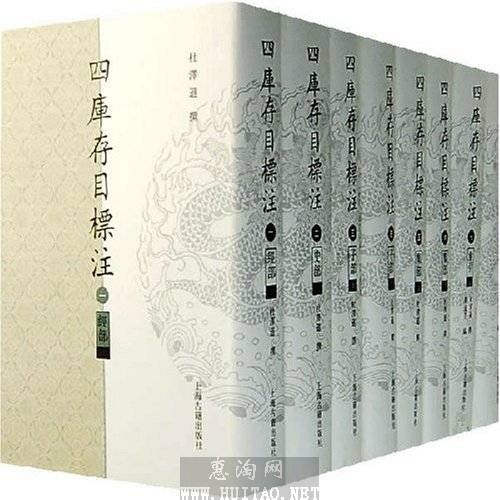人物簡介
杜澤遜,男,漢族,山東省滕州市人,1963年3月27日出生。1979年畢業於滕縣一中國中部。1981年畢業於滕縣一中高中部文科班,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1985年山東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1987年該校古籍所研究生班畢業,留所工作。2000年晉升教授。2003年在職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博士學位。現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2010年始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長。現任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
杜澤遜是古籍目錄版本學、四庫學和山東文獻研究領域知名的學者。2004年入選國家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2008年被評為2007年度山東大學十大新聞人物。2008年當選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2012年8月入選2011年度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著述
《四庫存目標註》成書始末
清代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萬多篇提要,實際上約三分之一的書收入《四庫全書》,三分之二的書僅僅“存目”。 當杜澤遜在琉璃廠發現《四庫存目》時,就決計以《四庫存目標註》為己任,開始了漫長的網羅資料工作。

1992年5月25日至31日,第三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在
北京香山飯店隆重舉行。杜澤遜在會後加緊進行《四庫存目標註》的同時起草了《四庫存目標註敘例》,寄給古籍整理界一些專家徵求意見,當時中華書局趙守儼先生、傅璇琮先生立即回信,給予充分肯定和熱情鼓勵,黃永年先生、章培恆先生、周勛初先生也在不同場合給予了肯定和支持。1993年4月20日杜澤遜又在《古籍簡報》發表《四庫存目標註·易類書後》,從易類標註對全部《存目》之書的存佚及版本情況作了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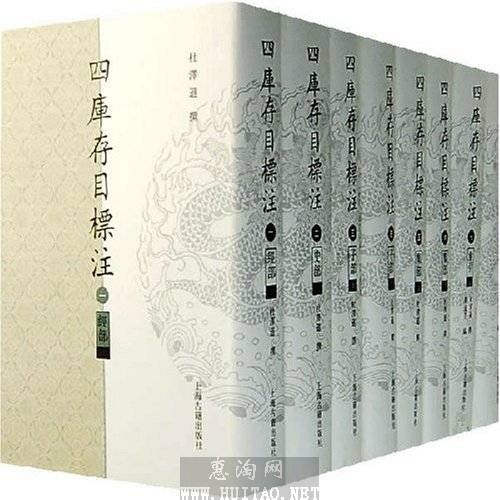
1994年5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正式成立編纂委員會,東方文化研究會會長季羨林先生任總編,杜澤遜任常務編委,應邀來北大任編目室副主任、不久改任總編室主任。到1997年10月底全書1200冊出齊,共收《存目》之書4508種,絕大多數為善本。11月杜澤遜返回山東大學,根據《存目叢書》學術顧問黃永年先生的建議,開始《四庫存目標註》清稿工作。 季羨林先生曾表揚杜澤遜作《存目標註》為編纂《存目叢書》“立了一大功”。
近5年間杜澤遜承擔著繁重的教學工作,為山大文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文史哲研究院等單位開設“文獻學”課(山大文、史、哲專業研究生必修課),為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開設目錄版本校勘學、清代目錄版本學研究、四庫學研究等課,同時參加了若干集體項目,個人為應教學之需撰寫出版了《
文獻學概要》(中華書局2001年出版)一書。 杜澤遜認為搞學術研究,一要打好基礎,二要善於捕捉信息,“現在不少人喜歡從網上找信息,認為信息一定是現代化的,甚至是洋玩藝兒,我看太狹隘了,信息到處都是,關鍵在自己去捕捉,要善於捕捉。”這是杜澤遜的經驗之談。三要抓機遇。選準課題,又要有條件做好,沒有條件,好課題也沒用。四要有耐心。這么大的項目,一星一點地積攢,一條一條地考索,字斟句酌地表述,比蝸牛慢多了,他的老師和朋友,知者無不為他著急,甚至善意地勸他“先出一本”,以便評職稱。他從沒動搖過,相反,他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2002年2月周積明教授在《四庫學200年》一文中寫道:“在《四庫全書存目》的研究上,山東大學杜澤遜副教授考索甚深,其所著《四庫存目書進呈本之亡佚及殘餘》、《四庫存目書進呈本知見錄》、《四庫存目標註》等,皆有專門之學的意味,令人注目與期待。”2007年,長達270萬字的《四庫存目標註》終於與讀者見面。
《十三經註疏匯校》緣起及構想
《十三經註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經典的經文、古注、音義、疏文。這十三部經典是:《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儒家的主要經典已包括在內了。這十三部經典在傳授過程中曾經產生過多家注釋解說,其中大部分失傳。保存下來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注,《尚書》漢孔安國注(據考是魏晉時人的偽作,卻有較高的水平),《詩經》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周禮》漢鄭玄注,《儀禮》漢鄭玄注,《禮記》漢鄭玄注,《春秋左傳》晉杜預注,《春秋公羊傳》漢何休注,《春秋穀梁傳》晉范寧注,《論語》魏何晏集解,《孟子》漢趙岐注,《孝經》唐玄宗注,《爾雅》晉郭璞注。主體部分是漢晉間人注。這些注有的不是漢人的舊注,但也汲收了漢人的舊注。相對於宋元人的注,這一批舊注被稱為“古注”。經文古奧,後人理解困難,往往首先求助於這些古注,原因是這些古注離經文產生的年代相對較早,並且古注本身又大都有更早的來源或依據,前人認為這些古注“去古未遠”,有較大的可靠性。

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學術研究的進步,對於經文和古注又逐步產生了更為詳盡的疏解,這些對經文和古注的疏解稱為“義疏”,南北朝時期比較發達。到了唐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了“五經義疏”,由於是朝廷主持,所以稱“五經正義”。這五部書是《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另有唐代賈公彥撰《周禮疏》、《儀禮疏》、徐彥《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論語疏》、《爾雅疏》、《孝經疏》,另有託名孫奭撰的《孟子疏》。總的看來,唐人的疏是總結南北朝至唐初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總結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來源和依據。《孟子》原來不在“經書”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動正式加入經書行列,北宋徽宗時成都的石經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現了成套的“十三經”。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經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條疏文開頭時提示“某某至某某”,如《關雎》首節疏,先說“關關至好逑”,然後再作疏,《關雎》的正文省略。歷史上稱這種文本為“單疏本”。
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一種解經的方式叫“音義”。主要是為疑難字注音、釋義。注音用反切,或直音。這種“音義”大概是受佛經的音義影響發展起來的。對於誦讀經典有很大幫助。現存的佛經當中有大量音義,還有人專門匯集為《一切經音義》。如唐代釋慧琳、釋玄應都有《一切經音義》。儒家經典的音義到隋朝由陸德明撰定為《經典釋文》一書,可以說集音義之大成。不僅包括當時確定的儒家經典的音義,還包括《老子》、《莊子》兩部道家經典的音義。《經典釋文》不僅保存了大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釋義,還保存了經文、古注在文字上不同文本的異文,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爾雅》、《孝經》、《孟子》有宋人的“音義”,也值得重視,尤其是孫奭《孟子音義》彌補了音義系統的缺項,到清代受到重視。後人把“音義”又叫“釋文”,是因為大部分經典的音義見於《經典釋文》。
總的看來,“十三經”的經文、古注、釋文、疏這四大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宋人對於儒家經書又有新的注釋,尤其是程朱系統的注釋,後來形成了《五經四書》,注釋完全是一種新的面貌,這當中借鑑汲收了註疏,但有許多新的見解。《五經四書》的注釋為:宋朱熹《周易本義》、宋蔡沈《書集傳》、宋朱熹《詩集傳》、元陳澔《禮記集說》、宋胡安國《春秋傳》、宋朱熹《論語集注》、宋朱熹《孟子集注》、宋朱熹《大學章句》、宋朱熹《中庸章句》。《周易》有的還附上程頤的《周易程傳》。南宋以來,到清代,一直非常流行,逐步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南宋以來學習儒學的,大都以朱熹等人注釋的《五經四書》為依據。漢唐人的註疏則被稱為“古學”。
“單疏本”由於經文、古注不全,閱讀不方便,到南宋初年出現了補齊經文、古注的經、注、疏合刻本,就是後來稱為“註疏”的文本。刊刻者是南宋初年紹興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傳世的《禮記正義》有當時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的福州人黃唐的跋語,十分重要:“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註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匯,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雲。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黃唐說得很清楚,合刻是為了方便。這個系統的本子經文是半頁八行,字比較大,稱“八行本”。現存的有《周易》、《尚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其中《春秋左傳正義》是紹興府地方刊刻的,不過是同一格式,顯然是配套的。有了經註疏合刻本,同時北宋時曾經刊刻過的單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傳世。“單疏本”有刻本或鈔本傳世的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爾雅》。
在南宋福建這一刻書中心,還出現了經文、古注、釋文的合刻本,叫“附釋文本”或“附釋音本”。比較有名的是余仁仲萬卷堂刻的。還有建安王朋甫刻的附釋文本《尚書》孔安國注,《尚書序》末有牌記云:“五經書肆屢嘗刊行矣,然魚魯混淆,鮮有能校之者。今得狀元陳公諱應行精加點校,參入音釋雕開,於後學深有便矣。士夫詳察。建安錢塘王朋甫咨。”顯示了《經典釋文》的必要性。更進一步,則出現了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合刻的本子。這種合刻,是以經注釋文合刻本為基礎,再加上“單疏”形成的。這種經、注、釋文、疏合刻本,有名的是劉叔剛刻的十行本。還有福建魏縣尉宅刻的《附釋文尚書註疏》。在四川眉山這一刻書中心也出現了《論語註疏》這樣的經、注、釋文、疏合刻本。
經註疏合刻、經注釋文疏合刻,都是為了方便閱讀。這一點朱熹在《答應仁仲》一函中論及《儀禮經傳通解》時說過:“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阮元《儀禮註疏校勘記》引用,文稍異)朱熹認為“經注本”和“單疏本”各自為書,是一種“弊病”,他把它們合起來,就“盡去其弊”了。事實上,把經文、古注、釋文、疏合併起來,很像清代以來的“集解”,這種集解古已有之,《論語》何晏注、《漢書》顏師古注都叫“集解”。舊注多了,匯起來方便閱讀,這是自然容易想到的。值得注意的是,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合為一編,恰恰是“古學”的合本,是在宋人新注之外自成體系的注釋。後來的學者講“經學”時往往以《十三經註疏》為依據,而講“儒學”或“宋明理學”時一般以《五經四書》為依據。表面看來還是這些書,而實際上注釋屬於兩個陣營。清代乾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阮元說過:“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經學當從註疏始。”他的立場顯然屬於“古學”一邊。而一般士子讀經事實上絕大多數是從《五經四書》始。明白了這個背景才能明白阮元的話是代表一個流派的,而不是當時人都認可的常識。
清代樸學家講求“古學”,對“十三經”作了更為深入的注釋,這些注釋最終凝結成一個系統,稱“清人十三經新疏”。其中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陳奐《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孫詒讓《周禮正義》、胡培翬《儀禮正義》、劉文淇《春秋左傳舊註疏證》、劉寶楠《論語正義》、焦循《孟子正義》、邵晉涵《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等等。有的新疏沒有作出來,例如《大戴禮記》,當代經學家劉曉東先生用三十年之力完成了《大戴禮記義疏》,其不平凡的貢獻就不可孤立地去看了。這些“新疏”顯然是對著舊的《十三經註疏》來的,訓釋有很大進步,但基本路線卻是“古學”的發展,依然是站在《五經四書》朱熹等註解的對面的。因此,就經書的注釋來說,仍是兩個陣營,我們姑且沿用舊的稱呼,叫“漢學”、“宋學”。《十三經註疏》基本上是“漢學”的代表。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間,朝廷組織學者撰定了《御纂七經》,包括《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彙纂》、《詩經傳說彙纂》、《春秋傳說彙纂》、《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其大體思路是不專主宋學,而是漢宋兼取,希望漢、宋合流。乾隆間曾下令各省重刊,清中葉以後也有各地重刊本,傳世量較大,而讀者不一定很多。這條漢宋合流的路子,現在看來沒有走通。
從現代的眼光看,總體上說,“漢學”較多地注重訓詁名物制度,而“宋學”更多地注重思想,在思維模式和興趣點上有較大差異,不具備“合流”的學術基礎,而是屬於“互補”的關係。當然不能“合流”,卻並不意味著不可“兼治”。清代“漢學”代表人物吳派惠棟、皖派戴震,都是主張“漢宋兼治”的。
既然《十三經註疏》是“古學”的代表,那么整理研究工作就格外重要。其中“整理”工作的重要基礎性工作是校勘。
校勘的主要任務當然是確定不同文本之間異文的是非,形成錯誤較少的文本。唐代顏師古等曾校定“五經”,形成《五經定本》。這種工作東漢蔡邕奉朝廷之命刊刻的《熹平石經》,唐代後期刻的《開成石經》(包括經書十二種),都是同等性質的“定本”。為了確定經典的用字,唐代還編成《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鄭玄在註解經書時,曾特別註明今文本、古文本有的字不同,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五代後蜀曾在成都刻石經,到北宋才刻完,稱《蜀石經》,南宋初年晁公武在四川做官,曾用國子監本校蜀石經,發現文字有不同,如《論語》“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蜀石經作“舉一隅而示之,而以三隅反。”等等。有些是非一時也不能確定,他就寫了《石經考異》,刻在石碑上,立在蜀石經旁,可惜失傳了。歷史上對儒家經書和古注的校勘工作一直持續不斷,取得了豐碩成果。清代初年張爾岐用《開成石經》本《儀禮》校勘當時通行的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十三經註疏》中的《儀禮註疏》,發現了不少脫文、誤字,寫成《儀禮監本正誤》。他還發現《開成石經》也有錯誤,寫成《儀禮石本誤字》。這對顧炎武啟發很大,顧炎武還抄寫一部帶到山西。顧炎武到了西安,看到《開成石經》,於是根據拓本校勘萬曆北監本《十三經註疏》,寫成《九經誤字》一卷,比張爾岐校勘的範圍更大。他在《日知錄》中批評北監本“脫誤尤甚”,舉出五條脫文例子,其中一處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十四個字。他慨嘆“秦火未亡,亡於監刻”。
清代對《十三經註疏》進行全面校勘的有乾隆初年武英殿刻《十三經註疏》附《考證》。這部《十三經註疏》刊印精美,第一次配齊了“十三經”的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四大項內容。每卷之後附有“考證”,也就是校勘記,討論了一些文字異同是非問題。乾隆中後期修《四庫全書》,其中的《十三經註疏》用武英殿本謄錄,但又根據舊本作了校勘,進一步增補了“考證”,從而比殿本又有所進步。嘉慶年間阮元在江西作巡撫,根據元刻明修本《十三經註疏》重新刻了一套《十三經註疏》,每卷附有更詳細的《校勘記》,歷史上稱“南昌府學本”、“南昌本”或“阮元本”。這個版本由於不少著名學者參加了校勘工作,因而受到廣泛重視。從那時到現在,“阮元本”都是權威版本,是學者最常用的版本,各種形式的重印本難以統計。
但是,阮元本並不完善。例如人們比較看重的他的《校勘記》,就存在一些缺點。前面說的《日知錄》批評萬曆北監本《儀禮》脫文的話,被《四庫全書總目》中《儀禮註疏》的提要直接引用,阮元把這一篇《儀禮註疏提要》刻在南昌本卷首,這樣世人都知道北監本《儀禮》不精不善了。可是在阮元《儀禮註疏校勘記》中,卻沒有指出北監本《儀禮註疏》的那五段脫文,而是僅僅指出明末毛晉汲古閣本脫去那五段文字。汲古閣本比北監本晚,並且是從北監本來的,那么汲古閣本的脫文當然是從北監本來的,單單指出“毛本脫”是不得其根源的。我們進一步校勘北監本之前的明嘉靖李元陽刻《十三經註疏》中的《儀禮註疏》,發現也同樣脫那五段文字,比李元陽本更早的明嘉靖間陳鳳梧刻本《儀禮註疏》也同樣沒有這五段文字。因此,阮元校勘記固然不到位,顧炎武批評北監本也同樣沒有得到脫誤的根源。進一步查對清代汪士鐘影刻宋本《儀禮疏》單疏本,我們發現其中沒有這五段經文的疏。就是說唐代賈公彥並沒為這五段經文作疏。顧炎武認為失去這五段經文的疏,是北監本的責任,慨嘆“秦火未亡,亡於監刻”,同樣也沒弄清脫誤的根由。因為這五段經文當初賈公彥沒有作疏,因此也談不上“亡”。我們上面說過,“單疏本”沒有經文、古注。後人在單疏本基礎上補足了經文、古注。很可能明中期陳鳳梧合刻《儀禮》經文、古注、疏文時,因為這五段經文沒有疏,導致添足經文時漏添了。如果我們不把各個版本對校過,這些問題就弄不清楚,就會得出錯誤結論。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校勘的任務除了發現並改正錯誤之外,還有兩個功能,那就是評判版本的優劣、梳理版本的源流。
上面說的陳鳳梧本、李元陽本、北監本,都是阮元見過並且用過的,卻沒有把脫文情況反映在《校勘記》中。還有單疏本,阮元也用了,對於這些疏文根本不存在,阮元也沒在校勘記中說明。這都是“漏校”。這樣做的結果是,誤導讀者,認為毛本極劣。其實顧炎武也誤導了讀者,認為北監本極劣。這都不是確切的答案。除了“漏校”之外,還有些古本阮元當時沒見到,例如《周易正義》單疏本、《周易註疏》八行本、《尚書註疏》單疏本、八行本、宋魏縣尉宅本、蒙古本、《禮記正義》八行本、《論語註疏》蜀刻十卷本、《孟子註疏解經》八行本等,阮元都沒見過。從而限制了校勘質量。這是古本。離阮元時代較近的乾隆武英殿本,阮元可能不太重視,沒有校勘,因面沒有很好地汲取其長處。例如《周禮註疏》卷二十八《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一節下疏文:“掌其戒令賞罰”下,阮元本有小字註:“原本實缺七格”。這七個字南宋八行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作:“則是于軍因為師”。阮元根據的底本沒有這七個字,他也添不上。但是武英殿本已經根據《州長》注推測出來,並且補上了。殿本補的這七個字和南宋八行本吻合,而且被後來的孫詒讓《周禮正義》採納(參日本加藤虎之亮《周禮經註疏音義校勘記》),十分可貴。阮元沒有見過南宋八行本,是客觀困難,但是武英殿本近在咫尺,卻沒有一校,導致這七個字無法校補,而僅僅注出原本“缺七格”,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失誤。直到今天,乾隆武英殿刻本也很少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視。鑒於這些原因,《十三經註疏》的校勘工作還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這是規劃《十三經註疏匯校》的學術理由。
前面說過,《十三經註疏》包括經文、古注、釋文、疏文四大項內容。前人在校勘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經文、古注、釋文方面,而在疏的校勘方面就相對薄弱。由於校勘工作規模很大,初步統計《十三經註疏》李元陽本、武英殿本都在11000頁以上。而歷史上《十三經註疏》(早期還不到“十三經”)的版本至少有南宋刻單疏本、南宋刻八行本、南宋刻十行本、元刻明修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陽福建刻本、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庫全書》本、清嘉慶阮元刻本等十個系統。之外還有單刻的。約略計之,總共有10萬頁。全部校一遍事實上校不乾淨,不免誤校、漏校,還必須二校、三校。校三遍,就是30萬頁。一個研究生一天坐班四小時可以校10頁,一年校3千多頁,十年校3萬多頁,30萬頁就要10個學生校10年。再合成一份《校勘記》即《匯校》,估計還要5年。15年時間那是在目前形勢下不大允許的。如果再進一步擴大校勘範圍,加上白文(無注)本、經注本、經注釋文等版本系統,還會進一步加大工作量,其可行性受到質疑。學問之道,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好大喜功、好高騖遠,只能欲速不達,壯志難酬。所以較為切實的方案仍是先把校勘範圍限定在前人工作較薄弱的“註疏”版本系統內。就上面的估算,如果從10人增加到15人,那么10年就變成了7年。如果熟練了,每人每天不止校10頁,而是增加到15頁,那就縮短到5年。加上合成一份《校勘記》的時間,初步合計8年可以完成。從程式上說,如果開始大家一齊校《尚書註疏》一種,分工合作,那么200天可以完成,先出版。一方面探索經驗,另一方面也徵求學術界意見,同時也為團隊打打氣,長長精神。這樣再校《周易註疏》、《毛詩註疏》,次第出版,就比較可行了。
阮元的《校勘記》附在他刻的南昌本《十三經註疏》每卷之後,乾隆武英殿本的“考證”也附在殿本《十三經註疏》之後。我們的《匯校》也同樣要附在《十三經註疏》的正文之後。那么,哪個版本適合作我們的“底本”呢?
適合作“底本”的版本應當具備以下條件:一、十三種書俱全。二、經、注、釋文、疏俱全。三、錯字少。歷史上具備這三個條件的版本並不多。南宋單疏本、八行本、十行本傳於今天的都只有幾種。元刊明修本缺少《儀禮註疏》,並且一半書版為明朝補刻,補刻的部分錯字較多,並且有的書頁有“墨塊”缺字。嘉靖李元陽本來自元刊明修本,缺字大都沒補上。都不適合作“底本”。北監本補上了缺字,是一個完整的官版,錯字也比以往的版本少。比北監本晚的汲古閣本因為校刊不精,錯字反而比北監本多,所以汲古本不適合。乾隆武英殿本是在北監本基礎上校刻的,改正了一些錯誤,增加了“考證”,補足了“音義”(主要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四種),事實上是歷史上第一次形成經、注、疏、釋文俱全的本子。並且也是第一次為全部經註疏釋文加了句讀(用類似於句號的小圈加了斷句標點)。翰林們斷句的能力一點不比今人差,甚至更強,所以斷句錯誤不敢說沒有,但確實不多。這個本子刻印精良,也適合影印。從這些優勢看,殿本很適合作“底本”。遺憾的是,殿本校刊時,翰林們對原書作了編輯工作。比如把解釋篇名(如《關雎》)的疏文從各篇移到各經卷首,再比如刪去了每條疏文前頭提示性的話“某某至某某”。有的地方因為刪去提示語,造成疏文眉目不清,乾隆殿本的整理者又重新增加了某些提示語。還有少數地方,對於疏文引用別的書,引文不完整的地方,作了增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十三經註疏》的面貌,這在校勘學上是不提倡的。其後的《四庫全書》本完全沿用了這一格式。這樣,殿本作為“底本”就不合適了。
剩下的只有北監本、阮元本。阮元本十分常見,並且每卷附有“校勘記”,我們如用作“底本”,就不能刪去阮氏“校勘記”,否則不是完整的阮本。如果保留阮校記,那么要把“匯校”附在阮校記之後,大有疊床架屋之感。況且,我們的“匯校”本來是針對阮元的校記不完善而來的,將來“匯校”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往往是針對阮元的,難以避免“同室操戈”的麻煩。所以阮本作“底本”也有不方便之處。不得已,只有選用萬曆北監本作底本了。
萬曆北監本的長處是規規矩矩,經、注、釋文、疏的排列格式沿用了南宋福建十行本的舊式,與元刊明修本、李元陽本、汲古閣本、阮元本一致。容易相互比對。再就是北監本十三部書完整,比在它之前的元刊明修本、李元陽本,以及在它之後的汲古閣本,缺字、誤字都少。因而選作底本具備基本條件。
當然北監本也有不完美處,那就是《論語》、《孟子》、《孝經》無音義,《爾雅》用的不是陸德明《釋文》,而是宋人的《爾雅音》。《周易註疏》的《釋文》沒散入正文,而是獨立附於《註疏》之後。這種格式元刊明修本、李元陽本、汲古閣本、阮元本也都如此。補救的方法是,影印北監本時,把唐宋人留下的《論》、《孟》、《孝經》、《爾雅》音義整體附在各經之後。這是不得已的辦法。殿本的句讀是了不起的科研成果,我們決定在影印北監本時,把殿本的句讀移到北監本上,供讀者參考。同時也避免我們作校勘記時摘句破句。至於殿本句讀偶有脫漏(應加而沒加)、錯誤,我們不予改正,以示謹慎,並取信於人。如果我們作了改訂,一是不能都改正,二是不能保證不出新錯誤,三是改的地方不能處處都加說明。將來告訴讀者:“殿本句讀錯誤和漏加的我們作了訂補。”讀者會問:“你改了哪些?改得對嗎?”想像的空間就大了。所以我們決定不改,保持原貌。
我們的《匯校》的基本面貌大體明白了:《十三經註疏》正文全部影印明萬曆北京國子監刻本,外加乾隆殿本的句讀。每卷影印的監本之後,附有排印的《匯校》。《匯校》除列出各本異文之外,還要把前人的校勘成果,例如張爾岐《儀禮監本正誤》、顧炎武《九經誤字》、殿本“考證”、庫本“考證”、阮元“校勘記”、孫詒讓《十三經註疏校記》等摘附各條之下,供讀者參考。
《十三經註疏匯校》具有以下功用:一、有利於進一步考證文本的是非,改正錯誤,整理出錯誤較少的《十三經註疏》通行讀本。二、有利於藉助異文,考察歷史上《十三經註疏》各個版本之間複雜的流變關係。三、有利於評價歷史上作為重大文化活動的刊刻《十三經註疏》工程的功與過。實際情況是:即使評價不高的汲古閣本,也往往有勝於他本處。這些先賢的努力和貢獻,哪怕是一字一句,也不應當埋沒。而不通過仔細的全面的校勘,這些學術問題是不可能給出答案的。四、《十三經註疏》各本的異文,有不少是異體字、俗體字、訛體字、避諱字,這些異文也許在經學家看來無助於經義的考證和理解,但對於考察宋元明清時期經典文本的用字狀況卻有一定的幫助。目前國家新聞出版署正在從事“中華字型檔工程”,清理歷代文獻用字情況,並對漢字的不同字元作數位化處理。根據有關檔案,初步估計,僅楷書字元就有30萬個。我們認為《十三經註疏匯校》在清理《十三經註疏》宋元明清各個文本異體字、俗體字方面足資參證。因此,《匯校》不僅對經學、經學史研究有直接幫助,而且在版本學、出版史、校勘學、文字學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