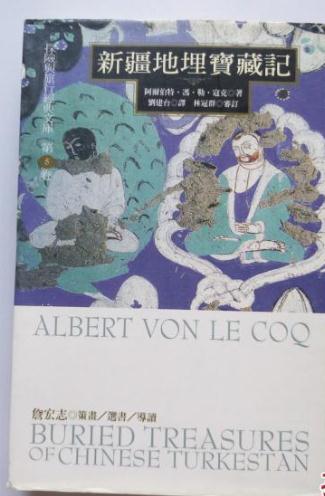《新疆地理寶藏記》是200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艾爾伯特。
基本介紹
- 書名:新疆地理寶藏記
- 又名: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 作者:艾爾伯特
- 譯者:劉建台
- ISBN:9789578278431
- 定價:480
- 出版社: 中國青年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0/6/30
- 裝幀:平裝
- 叢書: 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部分章節,
內容簡介
一八九五年冬天,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歷經千辛萬苦,深入危機四伏的中國南疆塔克拉馬乾沙漠,發現傳說中的古城遺址並帶走大批九百年前的佛教古物。這個事件震驚國際考古學界,掀起各國對絲路沿線凐滅已久的佛教文明的考古熱潮,一場國際尋寶競賽於焉展開。
作者簡介
艾爾伯特.馮.李.寇克
德國探險家,一八六○年出生在柏林世代經營酒廠的胡格諾派富裕家庭。先後在英美兩國接受商業訓練,並鑽研醫術,二十七歲時 回到德國接掌家族事業。但他心有旁騖,在經商十三年後毅然揮別商場,轉而追求他的真愛──中亞歷史與語言。他移居柏林,花了幾年工夫學習阿拉伯文、突厥 文、波斯文和梵文,隨後在柏林博物館當義工。一九○二年,也就是他四十二歲那年,正式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印度部門任職。當時德國第一梯次遠征隊正在南疆考察。
部分章節
自序
在柏林狄崔屈‧萊默(Dietrich Reimer)出版社的無私幫助下,有關我們在吐魯番綠洲發現的大量價值非凡文物的圖片,才得以公開出版。也因此,社會各階層對這些發現的興趣直線上揚。
同時,由於政府的資助,以及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友善的合作,在花費了大量心血後,這些文物都已被拍照存檔,而且公開展覽。對我多年的辛苦工作而言,這個結果確實是一個完美的句點。當然,我心中也時常產生一種複雜的情緒,深恐有些人對我的工作不甚理解。
在貝克(Dr. Becker)部長的協助下,我們從博物館的儲藏室取出了一百一十五箱濕壁畫和其他文物。在大戰期間,它們一直被存放在這裡。存放這些文物的展覽廳也已經開始籌建。
狄崔屈‧萊默出版社的老朋友和工作夥伴的大力幫忙下,我還出版了六大本畫冊,收集了我在歷次探險活動中發現的大量有價值文物的圖片,書名題為《後希臘化時期的中亞佛教藝術》(The Late Greco-Buddhist Art of Central Asia)。我必須對他們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謝,在這個經濟蕭條的時期,出版這批畫冊無疑地必須冒許多風險。
然而,我最想感謝的是政府相關部門,在他們的協助下,這個展覽才得以順利進行。
我還要向兩個人表示由衷的謝意,一是公共科學和藝術教育部長貝克博士,另一則是他的助手、樞密顧問賈爾(Gall)博士,他們兩人如實地具現了我的夢想。
我也要感謝國家博物館的建築師威爾(Wille)先生,在他的精心準備之下,我們得到了許多專業知識和正確建議,才使得這個展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在出版界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物,雖然並沒有直接參與此事,但在日後參觀者中我們發現,他們之間有許多人對此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也提供了許多專業的建議。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亞部門主任波須─萊茲(S. C. Bosch-Reitz)先生;倫敦頂尖的東亞文物收藏家尤莫菲波洛斯(Eumorphopoulos)先生;國家顧問拉瑟爾(Luther)博士;史彭格勒(O. Spengler)博士;我們的探險先驅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勇的中亞考古學家代表史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柏林普魯士科學院的諸位同仁們,特別是路德斯(Herren H. Luders)、麥雅爾(Ed. Meyer)、穆勒(F. W. K. Muller)和法蘭基(O. Frankie);哈雷大學的諸位教授,尤其是卡羅(Herren Karo)和韋伯(W. Weber),另外還有哥丁根(Gottingen)、漢堡、海德堡(Heidelberg)、土賓根(Tubingen)、法蘭克福、格來福瓦(Greifswald)、科尼斯柏(Konigsberg)、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瑞典諸大學的教授們;布達佩斯科學院的同仁們;其他著名的專家學者,以及重要收藏機構的擁有人,例如倫敦的史皮爾(Spier)夫人、紐約和倫敦的山中(Yamanaka)先生、柏林的瓦爾區(Worch)先生等等。這些人都一致認為,這次展覽不管是在展出的文物上,還是在展覽會的組織安排和對文物的收藏保護上,都堪稱是一流傑作。
但是,坦白說,專家和同僚們的讚許只是展覽的成功給我的部分安慰,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自發的關注和熱心。他們並不是這一領域的專家,對這次展覽的內容也不具備專業的知識。我們有幸接觸了許多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參觀者,當然還有道地的柏林人,向他們引介了與這些發現相關的最重要訊息,以及由這些文物延伸出來的新世界。隨著時間遷移,各界對這幾次遠征活動的細節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使得我產生了一個想法:用通俗的語言寫一本書,將遠征活動中經歷的艱辛、喜樂與困難紀錄下來。根據以前的工作安排,萊比錫的亨瑞克斯(J. C. Hinrichs)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使得我得以將它獻給我的讀者。這只是一本個人經歷的記錄本,並不帶有任何學術性,紀錄著我們在那片被驕陽烤炙的大地的生活。對歐洲人來講,那片大地無疑是那般遙遠與荒涼,但我們心裡將永遠牢記那裡所發生的艱辛和成功,以及考察期間所認識的朋友們。這本書里記載著當地東突厥人和漢人的生活,以及當地歷史和藝術的演進等,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讀者,我們這幾次探險活動大致的過程和成果。
假如這本書的成功能進一步證明我所從事的事的價值,我希望以後能再寫一本書,紀錄第四次探險活動的過程。這次考察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的。
艾爾伯特‧馮‧李‧寇克
柏林達勒姆區(Daglem)
一九二六年秋天導讀-新疆地埋寶藏記
詹宏志
中國後院的盜寶者
五年前(1995),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麥田出版的陳雨航要我為耶利米.威爾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寫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寫過任何與旅行史題材相關的文字,但多年的閱讀浸染與愛好,不吐不快,結果竟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序,弄得有點喧賓奪主兼不識趣了。
那篇文章寫三位前後探險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旅行家,軼事左右蔓生,年代縱跨百年,更兼手繪地圖以示足蹤,一發難以收拾。雖說文章述說的是三位外來的旅行家,卻也看見阿拉伯民族的近代歷史滄桑;我忍不住大發謬論說:「噫,旅行人所見豈祗風土人情咁簡單,我們從三個英國人在沙漠的故事當然也看見古國沉淪的歷史;而如果把這三個人換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換成另一個沙漠:戈壁,那這一段故事我們就看見鏡中的自己。」
這裡提到的其中一位,就是本書《新疆地埋寶藏記》(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的作者亞勃特.馮.勒寇克(1860-1930)。
而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讀中國近代史有時難免興憂國之感;十九世紀末,歐美諸強已進入現代國家社會的政經架構,中國卻仍像遙遠記憶中的古老國度,而兩者之間的「傲慢相遇」則預示著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國族屈辱,這個傷痕至今未能撫平,許多驕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說,海峽兩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與這段挫傷的歷史有關。
我可能扯得遠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歷史的後遺症;我曾經自問,何以西方數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旅行探險經典」在華文世界裡長期無人聞問,成為一塊出版與閱讀的空白?我始終猜想這些西方探險家曾經闖入我們的後院,窺探我們最頹唐不堪的一面,並把它形諸文字(我們因而不得不讀到落後、奇異、神秘、野蠻等屬於自己的描述),他們更趁著我們的昏昧無知,取走了無數的文化遺產,這段歷史是不容易面對的吧?
近幾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西北歷史時,光是對如何看待當年這些西方探險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場尷尬的考驗;這些西方旅行家進出中國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繪描地理、考察動物植被、更考掘古蹟文物,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民間並無現代知識可以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後來的中國學者有的把這些西方探險家指為「亡命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盜賊」,卻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的世界性學術貢獻(這些人許多是一流的漢學家,他們使中國的遺產廣為世人所知,甚至解決了某些中國學者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只是做為一個喪失大量珍貴文物的受害古國,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這一份探險家的名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許還應該加上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聞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亞地理考察而聞名,他常任意把俄國名字安在中國山川之上),以及美國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國籍、勒寇克的德國籍,這份穿堂入戶的探險家名單簡直另一個「八國聯軍」,心理上受辱似的的創傷之感可以想見。
如今我們再到「絲綢之路」(這也是其中一位闖入者斯文赫定發明的「異國情調」名字)觀光旅行,洞窟古蹟不時看到去了頭的佛像、和平整切去的壁畫(多半是本書作者勒寇克的傑作),不免令人興文物浩劫之嘆;這些美麗珍貴的古文物如今「花果飄零」,你得到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瑞典、德國等地才能見得齊全,有些流入私人收藏的就無緣得見了。
當然也有西方人說,這些文物當時無疑是帝國主義思想下的掠奪,但結果卻猶如天啟神佑,保護這些全人類共同遺產免於貧窮、愚昧或天災的破壞,至少躲開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性摧殘。而勒寇克也曾經說,他在1913年在新疆考掘壁畫時,有許多精美文物不及取出,三年後一場大地震毀掉許多廟宇,那些壁畫也隨之沒入煙塵,令他扼腕不已。從中國人的立場,歷史文物是被「偷」了,但從當時的西歐人來看,這些文物是被「發現」了,這解釋了當時並沒有人譴責這些探險家,英國皇家甚至頒授了爵位給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兩人,表彰他們對文明發現的貢獻;對劫掠文物這件事,後來在西方有了比較同情中國的立場,乃是晚近的事。
地埋寶藏的出土記
對於這段情感上難以接受的歷史,我還是主張要閱讀的。一方面,我們如今已有足夠的知識,了解這些事發生的原因與意義;另一方面,這些書所記錄的中國與生活,已經是消逝的景觀,它們的另一個功能,反而是「保存」了某種生活型態和社會狀態的記錄。
要了解那一段時間(差不多是清末到民國十幾年),西方人在中國西部與中亞地區的活動,也許可以從楊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讀起,看這些對東方的探險好奇是如何點燃的;然後及於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看到探險如何轉為對歷史與考古的追求,進而成為致富的傳奇;再讀到勒寇克,我們就看到追逐神秘東方寶藏如何成為一場帝國主義的競賽;如果行有餘力,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讀1935年銜命赴新疆查訪俄國人擴張活動的英國外交官艾瑞克.戴區曼(Eric Teichman)的《新疆之旅》(Journey to Turkistan, 1937),我們就能明白後續的結果,以及中國內部後來對文物飄零的感受。而我自己,也預備按照這條線索,在<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里,陸續收入上述人物的著作。
幾位在中國新疆探險兼考察(並竊取)古代文物的探險家,都是勇氣與知識兼備的人物;即使是聲譽不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顯赫那般的勒寇克,他也是多種中亞語言(至少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和歷史的專家。受了斯坦因在新疆發現大量古代文物的刺激,德國人也極力想取得這些令世人垂涎的寶物,以便增添帝國以及柏林博物館的收藏;勒寇克把握機會,不求報酬爭取參加探險隊伍的任務,一九O二年他以四十二歲「高齡」如願以償,參加了第一次德國在吐魯番一帶的考察發掘,那是由亞勃特.格倫威德爾(Albert Grunwedel)所領導的探險隊;這一次的考掘,帶回去了四十六箱的寶物,算是豐收了的。但如果和後來(1904年)勒寇克親自領軍的三次探險隊,所帶回的寶物收穫比起來,就顯得微不足道。
可能是運氣,也有毅力,以及一種強烈的尋寶企圖心,勒寇克是取走最多中國歷史文物的探險家。在《新疆地埋寶藏記》里,他生動地記錄了他的運氣,譬如丟擲銅板決定探險路線(這段軼事後來成為英國史家霍布科克的一章篇名,就叫做「勒寇克丟了一個銅板」)、以及他腳底沙地流動,竟然露出一面絕美上古壁畫的景觀;他也記錄了割取壁畫的方法,他把整面牆「片」下來,或仔細切割成駱駝可搬運的大小,前後都加了包裝,小心翼翼地運輸,我們今天仍可想像,那么巨大笨重的壁畫,必須千里迢迢運回歐洲(當中要越過艱難的地形,以及充滿盜賊的區域),其間的困難一定不在少數。
一次大戰爆發後,德國人不得不停止在中國新疆的掘寶行動;法國人伯希和接踵其後,取走了舉世著名的敦煌手卷;但在他之後,中國政府與民間學界再也不能容忍沙漠中的駝鈴,運走一隊一隊的中國歷史(以及一片一片的中國靈魂),探險活動從此對外國人關上大門,直到一九二六年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者共同考察的研究再起,但那已經不是私自穿越中國的「後院」,而是一個與主人配合的行動,所發現的結果也就不離開中國的土地了。
勒寇克帶走的寶物,後來終究流落何方?一開始,這些難得的寶物都保存在柏林的民俗學博物館;但二次大戰期間,盟軍轟炸柏林,民俗學博物館主建築被炸毀,失去了部分。勒寇克寶藏有一部分在戰爭時被移到較安全的儲藏處,但柏林淪陷時,這批寶物消失了;有證據顯示,蘇聯紅軍至少劫走了其中十箱以上的寶物,但到今天為止,這批失蹤的寶物還未重現於天地之間。
重讀勒寇克的書,心情不免是複雜的;他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塞外景致與生活情況,也記錄了他們克服萬難的探險生活,對他所親眼目睹的景物也都有一手的報導;也許我們應該慶幸他留下了這些已被遺忘的世界的描繪,使我們不至於失去一種記憶。但看到他取去的各種寶物,對照我們今日旅行所看到的空白牆面與失去頭顱的雕像,彷佛是一個難以痊癒的傷痕,如果連帶想起百年之間華人遷徙、文化流逝的舊事,也是很難不帶些傷感的呢。
在柏林狄崔屈‧萊默(Dietrich Reimer)出版社的無私幫助下,有關我們在吐魯番綠洲發現的大量價值非凡文物的圖片,才得以公開出版。也因此,社會各階層對這些發現的興趣直線上揚。
同時,由於政府的資助,以及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友善的合作,在花費了大量心血後,這些文物都已被拍照存檔,而且公開展覽。對我多年的辛苦工作而言,這個結果確實是一個完美的句點。當然,我心中也時常產生一種複雜的情緒,深恐有些人對我的工作不甚理解。
在貝克(Dr. Becker)部長的協助下,我們從博物館的儲藏室取出了一百一十五箱濕壁畫和其他文物。在大戰期間,它們一直被存放在這裡。存放這些文物的展覽廳也已經開始籌建。
狄崔屈‧萊默出版社的老朋友和工作夥伴的大力幫忙下,我還出版了六大本畫冊,收集了我在歷次探險活動中發現的大量有價值文物的圖片,書名題為《後希臘化時期的中亞佛教藝術》(The Late Greco-Buddhist Art of Central Asia)。我必須對他們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謝,在這個經濟蕭條的時期,出版這批畫冊無疑地必須冒許多風險。
然而,我最想感謝的是政府相關部門,在他們的協助下,這個展覽才得以順利進行。
我還要向兩個人表示由衷的謝意,一是公共科學和藝術教育部長貝克博士,另一則是他的助手、樞密顧問賈爾(Gall)博士,他們兩人如實地具現了我的夢想。
我也要感謝國家博物館的建築師威爾(Wille)先生,在他的精心準備之下,我們得到了許多專業知識和正確建議,才使得這個展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在出版界中還有許多其他人物,雖然並沒有直接參與此事,但在日後參觀者中我們發現,他們之間有許多人對此事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也提供了許多專業的建議。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亞部門主任波須─萊茲(S. C. Bosch-Reitz)先生;倫敦頂尖的東亞文物收藏家尤莫菲波洛斯(Eumorphopoulos)先生;國家顧問拉瑟爾(Luther)博士;史彭格勒(O. Spengler)博士;我們的探險先驅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勇的中亞考古學家代表史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柏林普魯士科學院的諸位同仁們,特別是路德斯(Herren H. Luders)、麥雅爾(Ed. Meyer)、穆勒(F. W. K. Muller)和法蘭基(O. Frankie);哈雷大學的諸位教授,尤其是卡羅(Herren Karo)和韋伯(W. Weber),另外還有哥丁根(Gottingen)、漢堡、海德堡(Heidelberg)、土賓根(Tubingen)、法蘭克福、格來福瓦(Greifswald)、科尼斯柏(Konigsberg)、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瑞典諸大學的教授們;布達佩斯科學院的同仁們;其他著名的專家學者,以及重要收藏機構的擁有人,例如倫敦的史皮爾(Spier)夫人、紐約和倫敦的山中(Yamanaka)先生、柏林的瓦爾區(Worch)先生等等。這些人都一致認為,這次展覽不管是在展出的文物上,還是在展覽會的組織安排和對文物的收藏保護上,都堪稱是一流傑作。
但是,坦白說,專家和同僚們的讚許只是展覽的成功給我的部分安慰,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自發的關注和熱心。他們並不是這一領域的專家,對這次展覽的內容也不具備專業的知識。我們有幸接觸了許多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參觀者,當然還有道地的柏林人,向他們引介了與這些發現相關的最重要訊息,以及由這些文物延伸出來的新世界。隨著時間遷移,各界對這幾次遠征活動的細節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使得我產生了一個想法:用通俗的語言寫一本書,將遠征活動中經歷的艱辛、喜樂與困難紀錄下來。根據以前的工作安排,萊比錫的亨瑞克斯(J. C. Hinrichs)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使得我得以將它獻給我的讀者。這只是一本個人經歷的記錄本,並不帶有任何學術性,紀錄著我們在那片被驕陽烤炙的大地的生活。對歐洲人來講,那片大地無疑是那般遙遠與荒涼,但我們心裡將永遠牢記那裡所發生的艱辛和成功,以及考察期間所認識的朋友們。這本書里記載著當地東突厥人和漢人的生活,以及當地歷史和藝術的演進等,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讀者,我們這幾次探險活動大致的過程和成果。
假如這本書的成功能進一步證明我所從事的事的價值,我希望以後能再寫一本書,紀錄第四次探險活動的過程。這次考察是在一個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的。
艾爾伯特‧馮‧李‧寇克
柏林達勒姆區(Daglem)
一九二六年秋天導讀-新疆地埋寶藏記
詹宏志
中國後院的盜寶者
五年前(1995),在一個偶然的機遇,麥田出版的陳雨航要我為耶利米.威爾森(Jeremy Wilson)的《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 1989)寫序;在此之前,我尚未寫過任何與旅行史題材相關的文字,但多年的閱讀浸染與愛好,不吐不快,結果竟寫了一篇一萬五千字的長序,弄得有點喧賓奪主兼不識趣了。
那篇文章寫三位前後探險於阿拉伯沙漠的英國旅行家,軼事左右蔓生,年代縱跨百年,更兼手繪地圖以示足蹤,一發難以收拾。雖說文章述說的是三位外來的旅行家,卻也看見阿拉伯民族的近代歷史滄桑;我忍不住大發謬論說:「噫,旅行人所見豈祗風土人情咁簡單,我們從三個英國人在沙漠的故事當然也看見古國沉淪的歷史;而如果把這三個人換成另外三位旅行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勒寇克(Albert von Le Coq),沙漠換成另一個沙漠:戈壁,那這一段故事我們就看見鏡中的自己。」
這裡提到的其中一位,就是本書《新疆地埋寶藏記》(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1928)的作者亞勃特.馮.勒寇克(1860-1930)。
而這樣的感觸其來有自,讀中國近代史有時難免興憂國之感;十九世紀末,歐美諸強已進入現代國家社會的政經架構,中國卻仍像遙遠記憶中的古老國度,而兩者之間的「傲慢相遇」則預示著長達一世紀以上的國族屈辱,這個傷痕至今未能撫平,許多驕傲、自卑皆因此而起;我甚至可以說,海峽兩岸今天相煎太急的局面都與這段挫傷的歷史有關。
我可能扯得遠了,但至少有一件事便是此一歷史的後遺症;我曾經自問,何以西方數百年來波瀾壯闊的「旅行探險經典」在華文世界裡長期無人聞問,成為一塊出版與閱讀的空白?我始終猜想這些西方探險家曾經闖入我們的後院,窺探我們最頹唐不堪的一面,並把它形諸文字(我們因而不得不讀到落後、奇異、神秘、野蠻等屬於自己的描述),他們更趁著我們的昏昧無知,取走了無數的文化遺產,這段歷史是不容易面對的吧?
近幾十年中國大陸學界在研究西北歷史時,光是對如何看待當年這些西方探險家兼考察家,就是一場尷尬的考驗;這些西方旅行家進出中國西北僻壤,踏勘地形、繪描地理、考察動物植被、更考掘古蹟文物,當時的中國政府與民間並無現代知識可以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後來的中國學者有的把這些西方探險家指為「亡命的機會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盜賊」,卻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的世界性學術貢獻(這些人許多是一流的漢學家,他們使中國的遺產廣為世人所知,甚至解決了某些中國學者無法解決的歷史問題);只是做為一個喪失大量珍貴文物的受害古國,感情上不能忍受也是可以了解的。
這一份探險家的名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大名家之外,也許還應該加上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取走大量敦煌手卷而聞名)、日本的大谷光瑞、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ejevalsky,以中亞地理考察而聞名,他常任意把俄國名字安在中國山川之上),以及美國的華爾納(Langdon Warner);想想看,加上斯文赫定的瑞典籍、斯坦因的匈牙利裔英國籍、勒寇克的德國籍,這份穿堂入戶的探險家名單簡直另一個「八國聯軍」,心理上受辱似的的創傷之感可以想見。
如今我們再到「絲綢之路」(這也是其中一位闖入者斯文赫定發明的「異國情調」名字)觀光旅行,洞窟古蹟不時看到去了頭的佛像、和平整切去的壁畫(多半是本書作者勒寇克的傑作),不免令人興文物浩劫之嘆;這些美麗珍貴的古文物如今「花果飄零」,你得到英國、法國、美國、俄國、日本、瑞典、德國等地才能見得齊全,有些流入私人收藏的就無緣得見了。
當然也有西方人說,這些文物當時無疑是帝國主義思想下的掠奪,但結果卻猶如天啟神佑,保護這些全人類共同遺產免於貧窮、愚昧或天災的破壞,至少躲開了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性摧殘。而勒寇克也曾經說,他在1913年在新疆考掘壁畫時,有許多精美文物不及取出,三年後一場大地震毀掉許多廟宇,那些壁畫也隨之沒入煙塵,令他扼腕不已。從中國人的立場,歷史文物是被「偷」了,但從當時的西歐人來看,這些文物是被「發現」了,這解釋了當時並沒有人譴責這些探險家,英國皇家甚至頒授了爵位給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兩人,表彰他們對文明發現的貢獻;對劫掠文物這件事,後來在西方有了比較同情中國的立場,乃是晚近的事。
地埋寶藏的出土記
對於這段情感上難以接受的歷史,我還是主張要閱讀的。一方面,我們如今已有足夠的知識,了解這些事發生的原因與意義;另一方面,這些書所記錄的中國與生活,已經是消逝的景觀,它們的另一個功能,反而是「保存」了某種生活型態和社會狀態的記錄。
要了解那一段時間(差不多是清末到民國十幾年),西方人在中國西部與中亞地區的活動,也許可以從楊赫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讀起,看這些對東方的探險好奇是如何點燃的;然後及於斯文.赫定與斯坦因,看到探險如何轉為對歷史與考古的追求,進而成為致富的傳奇;再讀到勒寇克,我們就看到追逐神秘東方寶藏如何成為一場帝國主義的競賽;如果行有餘力,也許我們還可以再讀1935年銜命赴新疆查訪俄國人擴張活動的英國外交官艾瑞克.戴區曼(Eric Teichman)的《新疆之旅》(Journey to Turkistan, 1937),我們就能明白後續的結果,以及中國內部後來對文物飄零的感受。而我自己,也預備按照這條線索,在<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里,陸續收入上述人物的著作。
幾位在中國新疆探險兼考察(並竊取)古代文物的探險家,都是勇氣與知識兼備的人物;即使是聲譽不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顯赫那般的勒寇克,他也是多種中亞語言(至少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梵文)和歷史的專家。受了斯坦因在新疆發現大量古代文物的刺激,德國人也極力想取得這些令世人垂涎的寶物,以便增添帝國以及柏林博物館的收藏;勒寇克把握機會,不求報酬爭取參加探險隊伍的任務,一九O二年他以四十二歲「高齡」如願以償,參加了第一次德國在吐魯番一帶的考察發掘,那是由亞勃特.格倫威德爾(Albert Grunwedel)所領導的探險隊;這一次的考掘,帶回去了四十六箱的寶物,算是豐收了的。但如果和後來(1904年)勒寇克親自領軍的三次探險隊,所帶回的寶物收穫比起來,就顯得微不足道。
可能是運氣,也有毅力,以及一種強烈的尋寶企圖心,勒寇克是取走最多中國歷史文物的探險家。在《新疆地埋寶藏記》里,他生動地記錄了他的運氣,譬如丟擲銅板決定探險路線(這段軼事後來成為英國史家霍布科克的一章篇名,就叫做「勒寇克丟了一個銅板」)、以及他腳底沙地流動,竟然露出一面絕美上古壁畫的景觀;他也記錄了割取壁畫的方法,他把整面牆「片」下來,或仔細切割成駱駝可搬運的大小,前後都加了包裝,小心翼翼地運輸,我們今天仍可想像,那么巨大笨重的壁畫,必須千里迢迢運回歐洲(當中要越過艱難的地形,以及充滿盜賊的區域),其間的困難一定不在少數。
一次大戰爆發後,德國人不得不停止在中國新疆的掘寶行動;法國人伯希和接踵其後,取走了舉世著名的敦煌手卷;但在他之後,中國政府與民間學界再也不能容忍沙漠中的駝鈴,運走一隊一隊的中國歷史(以及一片一片的中國靈魂),探險活動從此對外國人關上大門,直到一九二六年斯文.赫定與中國學者共同考察的研究再起,但那已經不是私自穿越中國的「後院」,而是一個與主人配合的行動,所發現的結果也就不離開中國的土地了。
勒寇克帶走的寶物,後來終究流落何方?一開始,這些難得的寶物都保存在柏林的民俗學博物館;但二次大戰期間,盟軍轟炸柏林,民俗學博物館主建築被炸毀,失去了部分。勒寇克寶藏有一部分在戰爭時被移到較安全的儲藏處,但柏林淪陷時,這批寶物消失了;有證據顯示,蘇聯紅軍至少劫走了其中十箱以上的寶物,但到今天為止,這批失蹤的寶物還未重現於天地之間。
重讀勒寇克的書,心情不免是複雜的;他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塞外景致與生活情況,也記錄了他們克服萬難的探險生活,對他所親眼目睹的景物也都有一手的報導;也許我們應該慶幸他留下了這些已被遺忘的世界的描繪,使我們不至於失去一種記憶。但看到他取去的各種寶物,對照我們今日旅行所看到的空白牆面與失去頭顱的雕像,彷佛是一個難以痊癒的傷痕,如果連帶想起百年之間華人遷徙、文化流逝的舊事,也是很難不帶些傷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