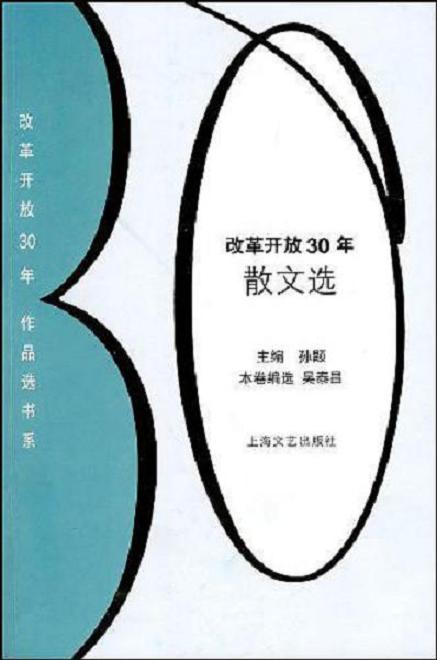《改革開放30年作品選書系》是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重點項目,是迎接改革開放30年大慶的獻禮圖書,而且也是對30年文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的集中展示,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影響;主持各分卷編選工作的都是文學評論界的權威人士,所以這套書系也具有權威性、代表性。
基本介紹
- 書名:改革開放30年散文選
- 出版社:7-5321-,3_7-5321-
- 頁數:443頁
- ISBN:9787532134021, 7532134024
- 作者:孫顒 主編 吳泰昌 編選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1日
- 開本:16
- 品牌:上海文藝出版社
- 定價:35.00元
內容簡介
圖書目錄
把心交給讀者
願化泥土
平原的覺醒
團圓
油海蕩舟
等待
綠的歌
工作著永遠是美麗的
太湖秋
可愛的故鄉
小鳥,你飛向何方
丁香花下
瀑布之歌
家鄉的閣樓
梨花,雪白的梨花
書桌
山泉水暖
又臨黃河岸
崑崙禮讚
醜石
鼓聲
匡廬八月
東京夜話
蓴鱸之思
黃花灘
霜葉
唱給豆腐的頌歌
枯葉蝴蝶
前門箭樓的燕子
雄關賦
紫藤蘿瀑布
蓬萊的童話
木偶的悲喜劇
桃花源記
河,就是海?
啊,你盼望的那個原野
生命猶如樂章
江上
曼哈頓街頭夜景
憶白石老人
紅紅的小辣椒
讀滄海
火箭總設計師速寫像
破冰船在破冰前進
離合悲歡的三天
鞏乃斯的馬
遺囑
雲霧茶
冬日抒情
冬至夜的夢
夕暮
爐火
大彌撒之思
橋
安塞腰鼓
布達拉宮之晨
山城水巷
秋天我在瀘沽湖
睛窗札記
自己的夜晚
蘇州賦
袁崇煥無韻歌
風雨天一閣
尋找姚元之
牡丹的拒絕
在高高的書架下
到了珍珠港
過不去的夏天
琴聲
在海邊
懷念星空
賦得永久的悔
淡之美
怎一個“閒”字了得?
蝶雪
下雨的時候
清風白水
享受高考
毀畫
腕上晨昏
從這裡到永恆
接近世紀初
筆直的陰影
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
地圖上的中國
家的概念
雨後
春風颳過
丟失的草地
扔掉的村莊
一個大黨和一隻小船
“非典”時期穿梭於兩岸三地
一九八二的故事
山居心情
尋親記
和諧是一種藝術
白雪紅燈的年
猜想井上靖的筆記本
廢墟上的風箏
我的長征,我的生命之歌
走,到西柏坡去
編後記
文摘
作者:巴金
前兩天黃裳來訪,問起我的《隨想錄》,他似乎擔心我會中途擱筆。我把寫好的兩節給他看;我還說:“我要繼續寫下去。我把它當作我的遺囑寫。”他聽到“遺囑”二字,覺得不大吉利,以為我有什麼悲觀思想或者什麼古怪的打算,連忙帶笑安慰我說:“不會的,不會的。”看得出他有點感傷,我便向他解釋:我還要爭取寫到八十,爭取寫出不是一本,而是幾本《隨想錄》。我要把我的真實的思想,還有我心裡的話,遺留給我的讀者。我寫了五十多年,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書,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吧,它們能夠存在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我回顧五十年來所走過的路,今天我對讀者仍然充滿感激之情。
可以說,我和讀者已經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關於我的寫作或者文學方面的事情,我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講,那就是對讀者講的。早講遲講都是一樣,那么還是早講吧。
我的第一篇小說(中篇或長篇小說《滅亡》)發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從一月號起共連載四期。小說的單行本在這年年底出版。我什麼時候開始接到讀者來信?我現在答不出來。我記得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說《光明》,描寫一個青年作家經常接到讀者來信,因無法解答讀者的問題而感到苦惱。小說里有這樣一段話: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裡,它們苦惱地望著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訴他。”
這難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惱?那個年輕的小說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從日本回來,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了幾種叢書,這以後讀者的來信又多起來了。這兩三年中間我幾乎對每一封信都作了答覆。有幾位讀者一直同我保持聯繫,成為我的老友。我的愛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讀者。她讀了我的小說對我發生了興趣,我同她見面多了對她有了感情。我們認識好幾年才結婚,一生不曾爭吵過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間寫過不少答覆讀者的公開信,有一封信就是寫給她的。這些信後來給編成了一本叫做《短簡》的小書。
那個時候,我光身一個,生活簡單,身體好,時間多,寫得不少,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回答讀者寄來的每一封信。後來,特別是解放以後,我的事情多起來,而且經常外出,只好委託蕭珊代為處理讀者的來信和來稿。我雖然深感抱歉,但也無可奈何。
我說抱歉,也並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從重慶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個星期左右。曹禺在戲劇專科學校教書。江安是一個安靜的小城,外面有什麼人來,住在哪裡,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剛剛住了兩天,就接到中學校一部分學生送來的信,請我去講話。我寫了一封回信寄去,說我不善於講話,而且也不知道講什麼好,因此我不到學校去了。不過我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我會經常想到他們,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他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我說,像我這樣一個小說家算得了什麼,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給他們帶來溫暖,不能支持他們前進。我說,我沒有資格做他們的老師,我卻很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在他們面前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地方。當他們在舊社會的荊棘叢中,泥濘路上步履艱難的時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夠做一根拐杖或一根竹竿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那我就很滿意了。信的原文我記不準確了,但大意是不會錯的。
信送了出去,聽說學生們把信張貼了出來。不到兩三天,省里的督學下來視察,在那個學校里看到我的信,他說:“什麼'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什麼'你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什麼'在你們面前我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這是瞎捧,是誘惑青年,把它給我撕掉!”信給撕掉了,不過也就到此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還打過小報告,但是並沒有製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來,多寫了二十多年的文章,當然已經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寫作的十年。
話又說回來,我在信里表達的是我的真實的感情。我的確是把讀者的期望當作對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貢獻一點力量,如果不是想對和我同時代的人表示一點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盡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盡的一份責任,我為什麼要寫作?但願望是一回事,認識又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絕不能由我自己一個人說了算。離開了讀者,我能夠做什麼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對了或者做錯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讀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貢獻呢?只有讀者才有發言權。我自己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倘使我的作品對讀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讀者就會把它們扔進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寫作。所以我想說,沒有讀者,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說,讀者的信就是我的養料。當然我指的不是個別的讀者,是讀者的大多數。而且我也不是說我聽從讀者的每一句話,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說,我常常根據讀者的來信檢查自己寫作的效果,檢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這樣地檢查,也常常這樣地責備自己,我過去的寫作生活常常是充滿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戰以前,讀者來信談的總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的苦悶以及為這個前途獻身的願望或決心。沒有能給他們具體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這樣地鼓勵他們: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乾淨。在回信里我並沒有給他們指出明確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說不同,在信里我至少指出了方向,並不含糊的方向。對讀者我是不會使用花言巧語的。我寫給江安中學學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憶中出現。我至今還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會見的那些年輕讀者的面貌,那么善良的表情,那么激動的聲音,那么懇切的言辭!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讀者,我同他們交談起來,就好像看到了他們的火熱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說《春》的序言裡說:“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當時是流著眼淚寫這句話的。序言裡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這說明我多么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啊!我後來在江安給中學生寫回信時,在我心中激盪的也是這種感情。我是把心交給了讀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說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說,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裡有兩座銅像:盧騷和伏爾泰。在這兩個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內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著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巴爾的冤案、為拉里一托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於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復名譽,倖存者免於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內,他們是雨果和左拉。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裡受到的教育。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著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至於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預生活”呢?“作家干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頭。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干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干預生活”,替我雪冤。我在夢裡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只好在“牛棚”里搖頭嘆氣。這樣說,原來我也是主張“干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說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里搬出來。那么法國讀者也是贊成作家“干預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得在這裡說明一件事情,否則我就成了“兩面派”了。
這一年多來,特別是近四、五個月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好像從各條渠道流進一個蓄水池,在我手邊匯總。對這么一大堆信,我看也來不及看。我要搞翻譯,要寫文章,要寫長篇,又要整理舊作,還要為一些人辦一些事情,還有社會活動,還有外事工作,還要讀書看報。總之,雜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單幹戶”,無法找人幫忙,反正只有幾年時間,對付過去就行了。何況記憶力衰退,讀者來信看後一放就忘,有時找起來就很困難。因此對來信能回答的不多。並非我對讀者的態度有所改變,只是人衰老,心有餘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況能有好轉,我也願意多為讀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讀者們表示歉意。不過有一點讀者們可以相信,你們永遠在我的想念中。我無時無刻不祝願我的廣大讀者有著更加美好,更加廣闊的前途,我要為這個前途獻出我最後的力量。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其實我已經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只是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選自《巴金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