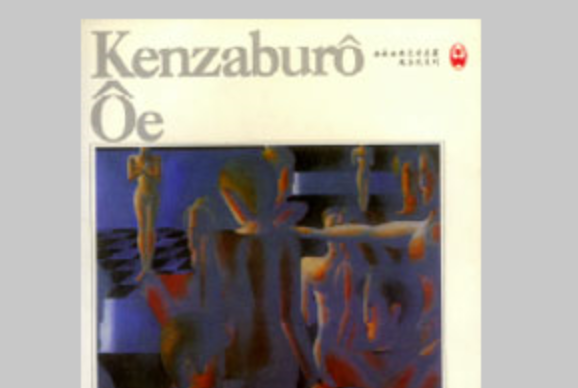內容簡介
當大江健三郎尚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日本讀者對他並不熟悉,我國也幾乎沒有譯介。大概主要因為他的純文學作品以不易捕捉的深刻思想和撲朔迷離的思維方式以及西方式的長句結構的語言表達“純”到使讀者退避三舍的地步。大江健三郎作為戰後派作家,一登上文壇,就表現出對戰後政治壓抑下的人的奇特的心態,塑造各種精神閉塞狀態里的象徵性形象,使他很快就成為新時代文學的旗手。
他生長的時代已經基本上失去了神話的存在,英雄主義的憧憬變成徒勞的負擔和失敗的根源。正如他在《我們的時代》中所說:“日本的青年人不可能具有積極意義上的希望。希望,對我們日本的青年來說,只能是一個抽象的辭彙。我很小很小的時候,發生了戰爭。在那個英雄的戰鬥的時代,年輕人滿懷希望,把理想掛在嘴邊……理想,是你死我活的殘酷戰場上的語言。理想,是同一時代人相互之間的友誼,但那也是戰爭的年代。今天我們的周圍只有欺騙和猜疑、傲慢和輕蔑。和平的時代,這是猜忌的時代,這是孤獨的人互相輕蔑的時代……理想、友誼、宏偉的共生感,這一切在我們的周圍從來不曾存在過。我生不逢時,生得太晚,卻又生得太早,趕不上下一個友誼的時代、希望的時代。”這就是大江作品中的“性的人”的思想背景,對時代的幻滅導致逸脫常規的行為,被“正常”人視為異端的舉動中所隱蔽的反社會的情緒往往在失敗的屈辱中體現出“反常”的正當性。大江把人抽象化,分為“政治性的人”和“性的人”兩大類型。前者具有與“他人”對立、爭鬥的本質,後者在本質上沒有“他人”,只有反權威的“我”。不言而喻,這裡的“性的人”的概念不是狹義上的性愛者,而是可以廣義到政治領域裡的官能性的愛。這是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失墜以後的必然產物,是對盲目信仰時代終結的一種反動。從《我們的時代》中的南靖男和“不幸的年輕人”可以看到對天皇制崇拜的心理崩潰是他的行為基礎,而《性的人》中的J也是對一切政治價值和社會秩序的否定者,在虛無的行為中最後是對自我的毀滅。他們以“墮落”擺脫舊的倫理道德的束縛,企圖從中發現人的真實本性,然而以無價值、無意義的偽善性為自己精神的拯救展示著痛苦的死角。當然,他們心理的反叛以肉體的頹廢為媒介,性與性愛的異常是對人性壓制的叛逆,這種通過靈與肉的激烈相剋尋覓本我的極端性選擇是基於虛無主義思想的作祟,也是絕對的孤獨感面對夢想的廢墟發出的哀嘆,肉慾的瘋狂不僅沒有平和心靈,反而加快反抗—自我懲罰—死亡這種生命體驗的進程。
大江健三郎的創作深受薩特、加繆的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常常運用荒誕離奇的想像把怪譎的情節與現實生活的存在交織在一起,表現人在不可思議的力量前無能為力的情緒,突出對現實世界以及自我世界的困惑和信任的危機,往往在一系列突發的、貌似怪異的戲劇性變化中機巧地剖析困厄在荒謬的世界裡的人的悲劇命運,展示著作者對被扭曲的現實的變形感受。這使他的作品有晦澀之處,但如果稍有耐性,習慣於他的以變形和寓意為核心的現代派創作手法以後,無疑會不知不覺地進入一個欲罷不能的奇妙世界。
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文壇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的“尋覓意識”、他的“自我忘卻”、他的“孤獨感”,揭示了生活在當今社會裡的人們的內心本質,讀者從貌似荒誕的情節構思和跳躍不安的語言形象中發現自我的影子以及命運的軌跡。從他獲得芥川文學獎的《飼育》,直至《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個人的體驗》《性的人》《我們的時代》《死者的奢華》等一系列作品,都貫穿著現代社會的人在與生命世界的衝突中所遭遇的悲劇性主題。這裡的“生命世界”,既是赤裸的本能世界,又是隱秘的靈魂世界,是人在封閉式環境裡與自然和心理的搏鬥中所經歷的種種精神的、倫理的、靈肉的磨難,人與命運的抗爭,不安與期待的糾葛,絕望與希望的交錯,倔強與妥協的矛盾,在不得不承受無法承受的現實中終於“忘卻”了自我。雖然作品中的人物對待孤獨的態度不盡相同,卻都無疑存在於介於現實與抽象的“中間世界”里,於是開始尋覓自我,企圖突破與生俱來的“孤獨感”,最終又往往丟失了自我。大江精心刻畫的人的異化的一面,揭示出“都市病”的病原就是現代社會本身這個深刻的內涵,所營構的仍然是人與現實的感覺空間,是複雜的人的內心世界,是在非個性的社會裡追求個性。在他的作品裡,黑暗的歷史背景總是在存在之外。無論是《性的人》,還是《我們的時代》,都沒有把性的肆虐提到道德的角度,從舊觀念解脫出來的日常,雖然具有瓦解家庭的侵蝕作用,但也對“家庭本位主義”的脆弱性和淡薄性造成刺激,出現日常本身正在溶解的場景。美國作家諾曼·梅勒的“20世紀後半葉給文學冒險家留下的墾荒地只有性的領域”的名言已成為陳詞濫調,然而性依然以極富魅力的微笑誘惑著文學家們,這大概因為對性的描寫已經成為探索現代生活模式以及死亡意義的一種象徵。J和靖男的“性”就是對自我存在不可缺少的確認,是被稀釋了的“愛”的生理解釋,以被扭曲的現實展現困厄在荒謬的世界裡的人的悲劇命運,暴露出現代文明社會的病理現象。如果說這也是對現實社會和舊我的反叛,那也是畸形的變態的發泄,意味著自我毀滅的開始。
儘管大江的文學思想融化著極其濃厚的西方文化理念,但最終還是植根於日本文化這個民族土壤。他緊緊把握現代社會的人在與生命世界的衝突中所遭遇的悲劇性主題,關注被異化的社會裡的人的個性與非個性的衝突,揭示現代人的孤獨,挖掘精神喪失的時代里人的本質。這大概是我們閱讀他以“性”為題材的作品時必須具備的眼光。
導讀
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兩部重要作品,反映一代對社會現實不滿的日本青年試圖以墮落擺脫舊的倫理道德的束縛,以肉體的頹廢作為心理反叛的媒介,將性與性愛的畸變當作對人性壓制的對抗。但這種肉慾的瘋狂不僅沒能平和心靈,反而加速了自我毀滅的進程。